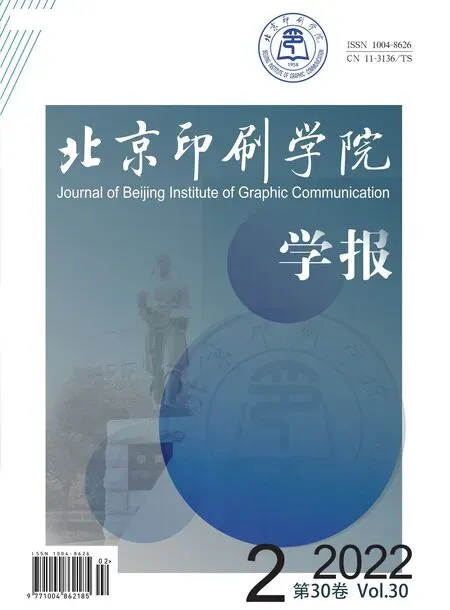新中国古籍刷印研究
2022-11-23彭俊玲
彭俊玲,魏 蔚
(1.北京印刷学院图书馆,北京 102600; 2.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北京 102600)
一、研究概况及研究意义
1.雕版印刷术与古籍
雕版印刷术,诞生于隋唐时期,又称梓行、版刻、雕印等,是指将文字、图像反向雕刻于木板上,再于印版上刷墨、铺纸,并给纸张施以一定的压力,使印版上的图文转印于纸张上的特殊工艺。它凝聚了我国雕刻术、摹拓术、造纸术、制墨术等优秀传统技艺,是具有鲜明民族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世界现代印刷术奠定了古老的技术基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开创了我国乃至人类印刷复制技术的先河,为文化的传播和文明的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 2006年5月20日,雕版印刷术被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9月30日,雕版印刷术申报成功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
“古籍”一词由来已久,最早出现于南朝谢灵运所作的《鞠歌行》中,即“览古籍。信伊人。永言知己感良辰。”[2]但是历代学者和藏书家对“古籍”这一基本概念的看法尚未达成一致。2006年文化部颁布的《古籍定级标准》将“古籍”定义为:“古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2008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古籍著录规则》将“古籍”定义为:“古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1911年以前、反映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古典装订形式的书籍。”本文对于“古籍”的概念界定依循国家标准定义。
2.相关研究成果概述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雕版印刷一直保持着一定数量的生产,不少机构还在利用晚清、民国时期旧刻书版刷印出版雕版图书。据粗略统计,雕版印书书版有千余种,大量的书版多次刷印。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刷刻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绝少人关注,对它的研究零散见于相关的著作和论文之中。
1988年魏隐儒编著的《中国古籍印刷史》中有一章为“民国和解放以后的雕版印书”,其中涉及新中国成立后雕版印书的内容仅有一页。1995年范慕韩主编的《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用两页半的篇幅概括了新中国成立后雕版印书的发展状况。1999年张树栋等合著的《中华印刷通史》中用一个小节的篇幅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雕刻木版印刷”概况。2003年王澄编著的《扬州刻书考》用一章的篇幅详细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雕版印书的情况。2005年徐雁教授所著的《中国旧书业百年》中有专门章节论述版片与古旧书,详述了雕版书版的保护与抢救。2006年罗琤发表的论文《金陵刻经处研究(1866-1966)》中有大量篇幅涉及新中国成立以后金陵刻经处的刻书活动。2015年刘洪权发表的论文《当代中国的版片保护历程与现状研究》中对现存版片进行了初步统计,提出了旧刻书版的保护措施。江苏、四川的出版志、出版大事记,浙江、江苏、吉林、河南、山西等地图书馆的大事记中亦有旧版保存和新中国雕版印书的零星记载。2015年秦嘉杭在论文《新中国雕版印书研究》中,从旧版新刷和新刻书的角度,梳理了新中国雕版印书的基本情况。然而由于论文的篇幅及所涉的内容有限,并未能展现新中国雕版印书的全貌。于是,2020年秦嘉杭出版了《新中国雕版印书研究》一书,系统总结了新中国雕版印书的成果。本文在系统吸收现有成果基础上,对新中国古籍刷印情况进行研究分析。
3.研究价值及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广陵古籍刻印社、金陵刻经处和德格印经院为代表的雕版印刷传承单位和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义时为代表的雕版印刷大师,均为雕版印刷技艺的保护和传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广陵古籍刻印社创建于1958年,专攻古籍的出版印制,是国内线装书生产的“龙头”单位,也是唯一完整保存全套雕版印刷工艺的单位。[3]金陵刻经处成立于1866年,完整地保存了古老的雕版水印和线装函套等传统工艺,将中国雕版印刷技艺与佛教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刻印风格。[4]德格印经院始建于1729年,专攻藏传佛教经典的出版印刷,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木刻雕版印刷中心,被誉为“保护最完好的藏文传统雕版印刷馆”。[5]雕版大师陈义时,以保护和传承雕版印刷技艺为己任,打破了“口传心授”“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等传统技艺传承方式,将其毕生所学传授给徒弟。[6]
雕版印刷技艺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只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当下,我们要在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技艺的同时,也要注意将其注入到现代文化产业中,使其具有更多的现代化元素,使之更能符合现代人的价值观念。由此看来,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雕版印刷状况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非常有意义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强民族强,文化兴国运兴。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浩如烟海的中华古籍,是我们华夏文化的基础,是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也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历史基石,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智慧源泉。中华古籍的整理和出版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关乎民族精神命脉延续的大事,因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中华古籍的现代价值和世界意义,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以来,刷印古籍的出版发行所占的市场份额非常小,但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继承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古籍刷印是古籍再生性保护的重要手段,也是解决古籍藏用矛盾的有效方法,更是文化传播的有力支撑。由此看来,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刷印古籍的出版状况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是非常有意义的。
二、新中国古籍刷印历史及案例分析
1.新中国古籍刷印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刷印的古籍除了极少数是利用新刻书版外,其他大多数都是利用晚清和民国时期刊刻且保存较为完好的旧刻书版刷印而成的。换言之,旧版重刷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刷印古籍的主体。直到20世纪50年代,旧刻书版才开始得到有关专家学者的关注,其整理、收藏和利用的建议也得到相关政府的支持,许多旧刻书版被用来印刷出版书籍,专门从事雕版古籍整理和出版的单位也由此诞生,即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
具体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刷印古籍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前
这一时期,木版刷印本所用的书版大多刊刻时间并不长,且保存较为完整。由于先前的书版刷印数量有限,仅有几十套至百套不等,有的书版甚至从未刊行,书版的有磨损情况较少,故刷印效果精良,可与民国时期的印本相媲美,如《龙溪精舍丛书》《咫园丛书》《友林乙稿》《音韵学丛书》等。这批木版刷印本在文物拍卖会上曾经出现过,其中保存较为完好的书籍,其成交价格甚至超过明清时期的旧刻本。据中华书局统计,这一阶段累计收录古籍2336种,其中木版刷印本大约有58种,占比不足2.5%。此外,还有一些没有收录其中的木版书,如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自成立之后刷印了18种木版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57年之后刷印了24种木版书(著录其中的仅有9种),杭州古籍书店1964年前后重印了5种木版书,粗略估计总数应该在百种左右(不包括南京金陵刻经处、四川德格印经院等专业印经单位印制的经书),仅占这一时期古籍整理出版总量的4%左右。
(2)第二阶段:改革开放—2006年
这一时期,人们对古籍的需求量日益增长,同时随着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恢复营业,中国书店再度恢复复制出版整理工作,文物出版社也加入了木版刷印的行列之中,旧书版的保护和利用工作受到了空前的重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三家单位利用自藏的旧书版刷印出版了一批极为珍贵的木版印本。1982年之前,这些木版刷印的书籍由大中城市的古籍书店经销,发行目的主要是为专业研究者和图书馆提供原始古籍资料,故普通读者难以看到这些木版印本。1982年之后,木版刷印图书才开始统一由北京市新华书店交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尽管出版单位刷印的木版古籍品种较多,但往往每种图书的刷印数量仅有几百部。如广陵古籍刻印社自复社至1982年年初,共刷印木版古籍43种,且每种印量仅有数百部。此外,这一时期刷印的古籍中有不少是大部丛书,如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81年出版《四明丛书》刷印本178种,1986年出版《适园丛书》刷印本76种,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畿辅丛书》刷印本173种等。
(3)第三阶段:2006年至今
这一时期,雕版印刷技艺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籍刷印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方面,一些新的刻本开始出现,如广陵古籍刻印社2011年出版的《唐诗三百首》和2013年出版的《广梅花百咏》等。另一方面,一些文化公司和书商也加入到了雕版印书的行列之中,如2011年成立的扬州古籍线装文化有限公司和2013年成立的微山县古籍线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等。此外,中国书店以《中国书店藏版古籍丛刊》的名义利用古旧书版刊行雕版古籍,到目前为止已经刷印了百余个品种,为学术研究、古籍整理和收藏提供了珍贵的版本。这批古籍以前大都刷印出版过,再次刷印的效果相比于影印本更加清晰,也最接近于古籍原貌,受到不少读者的喜爱,往往是一经出版便售罄。
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关出版单位及个人刷印出版古籍的大致情况如下:广陵古籍刻印社木版刷印的古籍有140余种,中国书店木版刷印的古籍有240余种,文物出版社木版刷印的古籍有30余种。此外,还有一些单位利用旧刻书版零星刷印了一些木版书,但是品种较少,每种的数量也不多。如上海古籍书店、四川人民出版社、杭州古籍书店等单位利用旧刻书版刷印的木版书从几种到几十种不等。再如南京十竹斋、华宝斋、线装书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室、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扬州市邗江古籍印刷厂、衡阳市博物馆、陕西中医研究所等单位刷印的木版书甚至只有一种到几种而已。也有一些单位鉴于整理、保护和研究书版的需要,利用所藏的古旧书版少量刷印书页样张,仅供内部使用,并未流传及在公开渠道售卖,如天一阁藏书楼、章丘市博物馆等。除了相关单位,也有极少数个人利用收藏的旧刻书版刷印古籍,如卢前、陈垣、沈瘦东、朱鼎煦、潘世兹等。
2.新中国古籍刷印案例分析——以《嘉业堂丛书》为例
《嘉业堂丛书》,共计收书57种,另加附录5种,凡62种,是民国时期藏书家刘承幹聘请著名学者缪荃荪等人校勘编纂的一部大型综合性丛书辑。刘氏刻书自1913年起至1918年陆续刻成100余种,择取其中50种,并附以所得《金石录》等数种版片,编印成书,以藏书楼命名之,因此称之《嘉业堂丛书》。由于该书所择底本均系嘉业堂藏书精品,且刻印、校勘质量俱佳,因此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1951年,刘承幹致函浙江图书馆,表示愿将嘉业堂藏书楼和四周空地并藏书书版连同各项设备等悉以捐献,以满足发展新中国文化事业之需要。其后,浙江图书馆并没有将版片束之高阁,而是多次借予中国书店、广陵古籍刻印社、上海古籍书店、文物出版社等单位进行重印。如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刷印出版《嘉业堂丛书》56种,文物出版社1982年刷印出版《嘉业堂丛书》62种。原版刷印的《嘉业堂丛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特别适用于小批量古籍的复制,因此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7]北京印刷学院图书馆馆藏有文物出版社刷印的《嘉业堂出书》,版面精美,装帧精致,完美呈现了古籍原本风貌,为印刷出版专业师生观摩利用该套丛书提供了良好的文献便利。
三、新中国古籍刷印存在问题及发展对策
近年来,虽然以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为代表的单位还在坚持着雕版印刷古籍,但是从整体上看,雕版印刷技艺仍然面临着失传的危险。
1.存在的主要问题
(1)书版保护意识淡漠
新中国成立初期,明清时期和民国时期的雕版线装书留存尚多,可谓是汗牛充栋。可以继续使用的书版,刊刻的时间大都不长,刻印的书籍都尚未受到人们重视,又何谈书版呢?更早一些的书版早已弃之不用,就更没有人注意了。况且书版的保护难度大,又占地甚多,因此书版的保护工作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正值百废待兴,国家对私人藏书家捐赠的珍本秘笈极为重视,而对他们捐赠的书版却不予理会。在这段时间里,大量珍贵的古旧书版被当作柴火烧掉,发挥了它们最后的价值。
(2)重复出版现象严重
新中国成立以来,古籍出版事业实现了快速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专业古籍社和非专业出版社都投身于古籍出版的领域之中,兴起了一股古籍热,与此同时,重复出版现象也达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粗放型的出版方式,不仅造成了效益低下的后果,还严重制约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发展和精品出版战略的实施。
(3)雕版印刷师匮乏
在现代印刷工艺的冲击下,古老的雕版印刷术正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和考验。同时,雕版印刷师的培养难度较大,口传心授的单一带徒方式也大大提高了雕版印刷术的传承难度。老一辈的非遗传承人感叹:“(学艺)要沉得下心,吃得住苦,耐得住寂寞,还要有一定的悟性,但是许多年轻学艺者耐不住枯燥乏味的生活早已改行”。因此,雕版印刷面临专业人才匮乏的严峻状况。
2.发展对策建议
(1)重视旧书版的利用
书版为木制文物,极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因此,我们要加强书版的保护性工作,使其处于适宜的保存环境中。此外,书版的最大价值仍然在于印书,唯有印书流布于世,才能实现书版的最大价值。所以,笔者以为,进入公藏机构的书版,仅仅保存在库房中,是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的。有计划地修补、限量刷印,最大限度延缓书版的寿命,才是保护书版的根本目的。通过对比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印古籍和刷印古籍的定价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利用旧书版刷印古籍的成本并不比影印古籍的代价高。特别是资料性、专业性较强的书籍,市场需求较少,影印或重新排版的代价较大,利用旧存书版少量刷印即可满足需要,这为雕版印书的发展找到了途径。广陵古籍刻印社修版印书的做法,可谓是生产性保护雕版印刷技艺的唯一途径。此外,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的建成,适时解决了扬州大批古旧书版的保存问题。
(2)完善出版管理机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古籍整理的方针政策,如1981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199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发布《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等。但是从管理体制上看,古籍刷印出版缺乏统筹规划,这也是造成古籍重复出版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应制定严格的古籍出版标准,加强古籍图书质量抽查,提高古籍出版单位和个人的从业门槛。同时,利用大数据建立智能选题数据库,减少或避免大量重复选题的出版。此外,古籍编辑要加强工匠精神,在坚持正确出版导向的同时努力打造自身复合型的知识结构,提高自身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做好编辑出版工作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和技术基础。
(3)创新雕版印刷传承模式
大部分中国传统技艺信奉“父子相传”“师徒相授”“传内不传外”的传承模式,这极大影响了继承人的选择范围,也使得许多传统工艺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因此,相关部门应该充分运用高校人才资源,促成雕版印刷传承人和高校教育的有机结合,打破传统的师徒传承模式,为行业源源不断地输出专业人才。同时,为传承人收徒授艺、被传承人拜师学艺创造更好的环境,鼓励年轻人走上学习非遗技艺的道路,为非遗的传承和保护注入更多的年轻力量。
四、结语
古籍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发展过程中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也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瑰宝,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鉴赏性等重要价值。作为一种弥足珍贵的传统文化遗产,古籍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作为古籍再生性保护的重要手段,古籍刷印出版在继承和传播传统文化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传统的雕版印刷术之所以能够一直保留至今,并不是刻意保护的结果,而是由市场需求所决定的。尤其是21世纪以来,雕版印书逐渐引起越来越多的藏书爱好者的注意,一些刻印精美、书版保存完整的木版书甚至多次刷印。这是因为中国雕版印刷技艺所独有的文化底蕴和审美艺术感是现代印刷技术无法比拟的。因此,我们有必要调动一切有利因素推动古籍刷印事业的发展,让古籍活起来,真正走向大众,充分发挥它们的史料研究价值和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