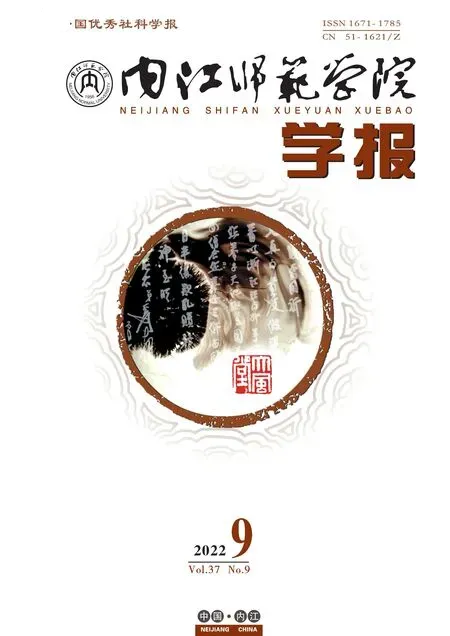应制诗风格的发展演变及其文化内涵
2022-11-22贾先奎
贾 先 奎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山东 菏泽 274000)
所谓应制诗,乃是古代臣子应帝王之命而作的一类诗歌。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十三云:“凡被命有所述作则谓之应制”,命即指帝王之命。《云麓漫钞》卷一又云:“上言之为制,下承之为诏。”[1]22所以应制诗又称应诏诗。应制诗一般创作于君臣之间的曲宴聚会、佳日游赏、节日庆典或者是奉祀礼典等场合,具有君臣唱和与君命臣作两种形式,主要表达臣子对朝廷、君主的赞美、歌颂,抒发臣子的荣恩之情等等,在古代诗歌中属于比较独特的一类。
一、应制诗的创作历史概述
应制诗的创制,在我国可以称得上是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尚书》载帝庸与皋陶所作《赓歌》,如“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明哉”等等,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已包含应制的因素。《诗经·大雅·卷阿》云:“岂弟君子,来游来歌,以矢其音。”描写君臣出游,群臣献诗之盛况,则当时应该已有诗歌应制酬唱之活动,惜乎史无明文,难以确指。但至迟到汉武帝时期,应制诗体已基本形成。汉武帝以文学侍从之臣待诏金马门,应制奏赋,《东方朔别传》云:“孝武元丰三年,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者,乃得上坐。”则此《柏梁联句》一诗实为应制诗之祖。此后汉宣帝、汉成帝等皆有命侍臣即席作诗作赋之举,建安时期,亦有“命诗”“命赋”之风。魏晋六朝时期,随着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对文学作用的重视,诗歌应制活动逐渐增多。据史书记载,当时诸帝大多举行过应制赋诗活动。特别是晋武帝、梁武帝时期,虽开国未久,政事初立,但应制活动最为频繁,应制诗数量也最多。可惜的是,这些诗歌现在大都亡佚,据对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统计,现存两汉魏晋六朝诗,标明应制的不到100首,难以窥见当时作品的全貌。
隋唐时期,应制诗创作彬彬大盛。隋代尽管享国日短,但君臣之间的应制酬唱活动却相当频繁。史传炀帝“善属文”,每有制作,常令文士属和,如虞世基、卢思道、薛道衡等人,都曾有较多应制属和之作。至唐代,应制活动更为繁盛,特别是初唐、盛唐时期,应制诗创作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高峰。据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统计,仅自武德九年九月至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唐太宗与臣下相与唱和及联句等文学活动就达58次之多,这些活动无疑大都属于应制的范畴。又《全唐文》卷225张说《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云:“自则天久视之后,中宗景龙之际……每豫游宫观,行幸河山,白云起而帝歌,翠华飞而臣赋。”《新唐书·李适传》云:“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合焉。”可见当时应制诗的繁盛状况,杨慎《升庵诗话》卷八指出:“唐自贞观至景龙,诗人之作,尽是应制。”[2]787据笔者对《全唐诗》的统计,现存安史之乱之前仅题目标明应制的诗歌就有600余首,未标明应制而有应制之实的诗歌数量更为可观。
五代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各割据政权忙于军事纷争,无暇他顾,应制诗创作处于低谷,只有江南李氏,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有一些应制活动。北宋建立之后,应制诗迎来了第二个创作高峰。特别是在宋初百年内,应制诗的创作极为繁盛,作家群体极为庞大,作品数量极为丰富,是历史上唯一可与初盛唐相媲美的时期。宋朝诸帝频繁举办宫廷宴会、祭祀典礼以及观书讲习、赏花钓鱼等各类文娱活动。凡有活动,概有应制。宰辅、宗室、馆阁等天子近臣,几乎无不有应制诗作,有人甚至因为未能参加活动,事后又专门写诗奉和,可见朝廷上下对应制活动的极度热衷。如《君臣赓载集》收录太宗与臣下唱和达30卷,天禧二年(1018),龙图阁待制李虚己应诏编群臣所和御制诗为《明良集》,竟有500卷之多,可惜这些书已佚。据对《全宋诗》的统计,这百年内应制诗现存创作,仅题目中标明应制的尚有300余首,再加上一些侍宴、奏御、帖子、郊祀等属于应制范畴的诗歌,数量则不下数千首。
宋之后,元代不文,应制诗几乎阒然无闻,明清两代则得以恢复和继承。据《明史》记载,《明史·范常传》记明太祖时期:“帝宴闲,辄命儒臣列坐赋诗为乐。”成祖及仁帝、宣帝时期,当时台阁大臣如解缙、杨士奇、杨荣、杨溥、黄淮均作有诸多应制诗,如杨士奇现存应制诗尚有近百首。清代康、乾时期,统治稳定,帝王喜好,应制活动更为频繁,节庆、宴饮、游园、巡幸、出游等等,几乎无不伴随应制活动,此可视为应制诗创作的第三个高峰。王士祯《居易录》记康熙时期:“每有御制,必命和进。”[3]241并且有多次效仿汉武帝柏梁赋诗活动,纳兰性德、张英、陈廷敬等多有应制之作。乾隆时期的纪昀其文集中有8卷应制诗,刘墉有3卷应制诗,可见当时应制诗创作之活跃与丰富。
二、应制诗风格的发展演变
应制诗作为内容、情感特殊的一类诗体,在风格上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追求。《韵语阳秋》卷二云:“应制诗非他诗比,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于典实富艳尔。”[4]28所谓典实,是指诗歌的典雅平实,即重视用典,文辞应该高雅而不浅俗;所谓富艳,是指诗歌的富丽华艳,不出以寒伧素朴之语。对此观点,《竹庄诗话》也曾给以称引,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七指出:“应制诗无出乎典丽富艳。”[5]118无论是“典实富艳”还是“典丽富艳”,意思大体相似,主要是强调应制诗应该外表艳丽,内含典雅,具备一种富贵华丽之气。这种典丽富艳的风格既体现在语言、修辞等外在形式方面,更体现在诗歌的内在气象、情趣等方面。
从应制诗的创作历程来看,其典丽富艳之风格并非初始即充分表现出来的,而是有着一个发展变化而至成熟定型的过程。我们看六朝时期的应制诗,如刘孝绰《侍宴饯张惠绍应诏诗》:“风度余芳满,鸟集新条振。”庾信《咏春近余雪应诏诗》:“丝条变柳色,香气动兰心。”另外还有沈约、谢庄等人的应制诗,皆清丽秀美,语言精巧,写景抒情与其他诗歌几无二致。写景咏物之外,还有一些记叙日常事务、游戏文字笔墨之作亦是争妍斗巧,颇有宫体特色[6]。这一时期,诗坛弥漫着一种追求艺术美的形式主义文风,应制诗亦深受此影响。当然,这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表明时人对应制诗在风格上的特殊要求还缺乏明确的认识,对应制诗的创作还没有形成固定统一的规范。
初盛唐应制诗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一是承继六朝的绮丽秀美风格。如杨师道《赋终南山用风字韵应诏》:“眷言怀隐逸,辍驾践幽丛。白云飞夏雨,碧岭横春虹。草绿长杨路,花疏五柞宫。登临日将晚,兰桂起香风。”语言清新流丽,精巧细致,六朝诗风未除,与富丽典雅的风格还相差甚远。再如上官仪《八咏应制》:“翡翠藻轻花,流苏媚浮影……残红艳粉映帘中,戏蝶流莺聚窗外。”辞藻绮丽,柔美妩媚,与宫体诗颇为相似。《蔡宽夫诗话》云:“唐自景云以前,诗人犹习齐梁之气,不除故态,率以纤巧为工。”[7]25正指出了因时代文风、诗风而导致初唐应制诗精致柔婉、庄重不足的原因。二是体现盛唐气象的宏伟博大风格。唐立国以来,国力全面繁盛、文化全面发展,海纳百川,兼容并包,诗歌因此多呈现出宏阔的视野,宏伟的气象,风格一变而倾于宏伟博大,这在应制诗中也有鲜明表现。如苏颋《兴庆池侍宴应制》:“山光积翠遥疑逼,水态含青近若空。直视天河垂象外,俯窥京师画图中。”诗人身处一隅,而视野上彻日月,远极天际,视山河大地如指掌之中,表现出了极为宏阔的视野和宏伟的气象。又如李峤《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主家山第接云开,天子春游动地来。羽骑参差花外转,霓旌摇曳日边回。”金圣叹评道:“纯用大笔大墨,不着一丝纤巧,允为一代冠冕。”[8]4再如王维《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的名句:“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境界阔大,风格雄伟,充分表现出唐人自信豪迈的心态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发展到宋代,由于国力衰弱、士民心理缺乏自信、心态趋于保守内敛等原因,初盛唐宏伟博大的风格在应制诗中基本上不可复见。同时,由于宋人学养更加丰厚,诗歌追求才学化、雅化,对于应制诗创作规范有着更为明确的认识,富丽典雅逐渐成为应制诗的典型风格,甚至可以说是写作者追求的唯一风格。这表现在应制诗作的各个方面。
首先,在语言和意象方面,诗人往往大量使用金玉锦绣等富丽堂皇的辞藻,如杨亿《后苑赏花钓鱼应制》(以芳字为韵):“波平鳌背浮昆阆,日转金茎艳赭黄。满酌流霞侍臣醉,暖风宫蕊杂炉香。”词语艳丽,色彩缤纷,表现了皇家园林高严华贵的气象和群臣欢饮的优雅场面。这些由诸如“玉斝”“珠躔”“绛燎”“金釭”“琼籤”“金扉玉宇”“珠网金铺”等构成的种种意象,充满了浓厚的富贵气息和华丽非凡的色彩,令人一望即知是非同寻常的事物,作者浓墨重彩地对此进行描写,有力地渲染了应制场合的富丽华贵和人物活动的雍容典雅。
其次,应制诗极为重视用典。如颜延之《应诏观北湖田收诗》,全诗26句用了11个典故,沈约《侍宴乐游苑饯吕僧珍应诏》,全诗20句用了19个典故[9],用典之密集可谓达到惊人的程度。应制诗用典,往往使用一些富有历史色彩和文化意味的高雅庄重的词汇或典故,如称颂帝王必称尧舜禹汤、文武汉唐;君臣酬唱必称“庚歌”“柏梁”,近于千篇一律。这种写作方式一方面容易使诗歌的内容情感呈现出一种雷同性和重复性,艺术独创性不高,另一方面却也特意由此营造出一种庄严凝重的意味,有效地增强了诗歌的典雅格调,极富有君臣贵族气息,特别适宜于台阁雅士的身份和情趣,因而深为应制诗人所赏爱与运用。
再次,典丽富艳的风格不仅仅来自辞藻和技巧的修饰,更来自其内在的气象和意蕴。《西清诗话》卷上云:“是真得应制体,不在于南金大贝,叠积满前……诗家何假金玉而后见富贵!”[10]178《韵语阳秋》卷二在指出应制诗的应具备风格后曾引数例以证:“夏英公《和上元观灯》诗云:‘鱼龙曼衍六街呈,金锁通宵启玉扃(京)。冉冉游尘生辇道,迟迟春箭入歌声。宝坊月皎龙灯暗,紫馆风微鹤焰平。宴罢南端天欲晓。回瞻河汉尚盈盈。’王岐公诗云:‘雪消华月满仙台,万烛当楼宝扇开。双凤云中扶辇下,六鳌海上驾山来。镐京春酒沽(霑)周宴(燕),汾水秋风陋汉才。一曲升平人尽乐,君王又进紫霞杯。’二公虽不同时,而二诗如出一人之手,盖格调当如是也。丁晋公《赏花钓鱼》诗云:‘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钓迟。’胡文恭公云:‘春暖仙蓂初靃靡,日斜芝盖尚徘徊。’郑毅夫云:‘水光翠绕九重殿,花气浓熏万寿杯。’皆典实富艳有余,若作清癯平淡之语,终不近尔。”这几首诗辞藻华丽、意象华美倒还在其次,主要是其内在的那种繁华气象和华贵意蕴,使之呈现出一种典丽富艳的风格来。这种典丽富艳风格在宋代应制诗中的普遍化,表明了应制诗创作观念的成熟和定型。
明清时期的应制诗,总体上承继了这种典丽富艳的风格,用词遣句、内容情感等,基本上没有大的创新和特点。如明代解缙《武英殿应制》:“绛蜡珠帘光照曙,紫驼银瓮色浮春……草野书生何以报,愿随丹禁捧丝纶。”杨士奇《文华门侍朝观录囚多所宽宥喜而有作》:“日丽文华霁色新,炉烟不断上麒麟。大臣论谳持王制,睿旨全生体帝仁……”颂圣德,歌太平,文辞富丽,风格典雅,气度雍容,与宋代应制诗歌一脉相承。此时期,仅有个别诗作略有不同,如纪昀《恭和圣制雨六月十七日原韵》:“雨过晴偏好,晴余雨又宜。青山如膏沐,绿叶如华滋。泉涨鸣相答,花散重欲垂。斜阳邀睿赏,更喜对烟姿。”写景抒情清新脱俗,不落窠臼,似远承六朝诗风。他的部分应制长诗,篇幅宏大,气势磅礴,记录王朝发生的重大事件。如《御试土尔息特全部归顺诗》《西域入朝大阅礼成恭纪三十首》等,一定程度上突破藩篱,拓宽了应制诗的题材范围,提升了应制诗的唱和内涵[11],可看作是应制诗体最后的一点突破和创新。
三、应制诗的文化内涵
对于应制诗,人们一向视之为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内容空洞、缺乏真情实感、毫无价值之作。如杨慎《升庵诗话》称其:“命题既同,体制单一。”薛雪《一瓢诗话》更称其为:“此等诗竟将堂皇冠冕之字,垒成善颂善祷之辞,献谗呈媚,岂有佳作。”[12]105从应制诗的整个历史来看,这种观点基本上可以成立。由于诗体所限,无论是直接抒情议论,还是写景叙事,最终大多都要曲终奏雅,归结到对君主神功圣德和太平盛世等方面的歌颂上来。从这一点来说,应制诗的艺术价值的确要大打折扣。
歌功颂德虽然是应制诗的基本内容,但并不是唯一的内容,更不是它一开始即充分具备的形态之一。如吴聿《观林诗话》云:“汉武柏梁台,群臣皆联七言,或述其职,或谦叙不能,至左冯翊曰:‘三辅盗贼天下尤。’右扶风曰:‘盗阻南山为民灾。’京兆尹曰:‘外家公主不可治。’则又有规警之风。及宋孝武《华林都亭》,梁元帝《清言殿》,皆效此体。虽无规儆之风,亦无佞谀之辞,独叙叨冒愧惭而已。”可见应制诗产生之初,并非全以颂扬为事。至于像李密的《赐饯东堂诏令赋诗》“官无中人,不如归田”云云,借应制而发牢骚之语,范晔《乐游应诏诗》“探己谢丹黻,感事怀长林”有归隐之意,皆足以看出当时臣子并没有把歌颂当作应制的必要内容。此后应制诗歌颂的成分虽然有所增加,但像沈约、谢庄、刘孝绰、庾信、庾世南等人的众多应制诗,也几乎看不出什么应制的特点,歌颂的意味仍然并不鲜明突出。直到唐代,特别是贞观后期以来,应制诗歌颂褒扬,谀声大作,如沈佺期、宋之问、许敬宗、李义府等人的诗作,歌功颂德才渐渐成为应制诗的常态。《昭味詹言》引沈德潜语曰:“初唐应制,多谀美之词,况当武后、中宗朝,又天下秽浊时也,众手雷同,有颂无规。”[13]385可说是指出了初唐应制诗人谀美失真的事实。宋代之后,歌功颂德甚至成为应制诗唯一表现的主题,无论是郑重盛大的奉祀礼典,还是一般的曲宴聚会、佳日游赏、观书讲习等场合,其应制之作均充满浓厚的颂扬意味。《观林诗话》云:“近世应制,争献谀辞,褒日月而谀天地,惟恐不至。古者赓载相戒之风,于是扫地矣。”对应制诗谄谀之风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因为应制诗一味地歌功颂德,其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受到严重削弱,虽然如张说、张九龄、王维等人的一些应制之作尚有较高的艺术成就,但总体来看,远远达不到诗人其他作品所达到的高度。应制诗毕竟是属于应酬之作,限于场合和时机,作家都极难产生内心最真切最深沉的生命感动,缺乏激情与灵感,也就从根本上导致了诗歌生命与价值的缺失。罗时进先生指出:“奉和应制场合和邀宠的狭隘用心,必然带来思维的局限和卑弱的气度,抹杀人格精神和个性特征。庙堂性的文化心态、供奉性的文人心理和公开性的唱和形式,决定了他们的创作难免异口同声、众人一面。”[14]13聂永华先生说,应制诗“由于创作环境的封闭性与皇帝在场的庄严性,以及奉命作诗的局限性,导致题材内容的狭隘与体式风格的呆板滞重”[15]336。这些论断,都指明了应制诗总体艺术成就不高的重要原因。
不过,对于研究者来说,应制诗创作不仅仅是一种诗歌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与政治方针、社会风气、文学思潮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应制诗以其特殊的创作场合、创作对象和创作心态,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状况、国家政策的施用重心和道德风尚等诸多方面的情况。这一切,无疑使其具备了一定的社会政治意义和历史文化价值。比如说,我们从应制诗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它在一定时期,特别是往往在王朝兴起之初,其创作人员及作品数量最为突出,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开国君主对于“文治”和“武功”的强烈追求。从应制诗歌的内容,也可以发现它与政治的密切联系。如宋代的赏花钓鱼应制赋诗,反映了稳定太平的社会状况和统治阶层优雅的休闲享乐之风,同时期的观书讲习应制赋诗活动则反映了宋初的尚文政策,体现了君主对文化的促进和倡导作用,有助于我们理解宋代文化高度发达和繁荣的原因。
应制诗与文学思潮、诗歌风气也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葛晓音指出:“宫廷文学是直接为皇帝服务的,所以各种不同类型的应诏诗最能显示出政治的特点,反映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文风的变化。”[16]25我们从应制诗风格的演变与定型就可以看出它与当时文风与诗风的关系。如六朝时的应制诗清丽秀美,体现了当时追求艺术美的形式主义文风,初盛唐时期由绮丽精致到宏伟博大的转变,与当时文风诗风的转变是一致的,宋代应制诗富丽典雅的风格,也体现了宋诗以才学为诗、注重用典的共同特点。
另外,应制诗多是在一种比较悠闲、轻松的场合和氛围中制作出来的,属于一种君臣佐欢的手段,或是一种才艺的较量比较。许多应制活动,如汉武帝时柏梁联句、则天时的夺锦袍、龙门应制等,也早已成为应制诗历史上的佳话。这些活动,有助于融洽君臣之间的感情,密切彼此之间的关系,激发臣子忠君爱国、报效皇恩之情绪,可以说,这既是一种文学活动,同时也是上层社会一种高雅的交际活动,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