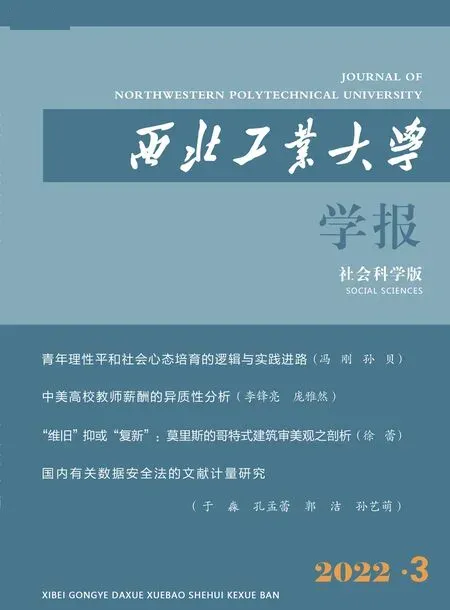让-菲利普·图森小说中的城市过渡空间
2022-11-21赵佳
赵 佳
法国当代作家让-菲利普·图森的小说中有一种强烈的时间意识,评论家德拉诺在对其处女作《浴室》所作书评中指出:“移动的静止和静止的移动是《浴室》的两个悖论。”[1]怎样在移动中追求内在的静止?怎样在相对的静止中发现永恒的运动?这是图森小说中“时间和空间的悖论”[2]。麦凯瑞注意到动与静这对时间上的矛盾关系对图森作品中空间的塑造。图森的人物喜欢在旅途中的狭小空间中思考,“所有这些空间的共同点是狭窄、封闭,同时又以某种方式和旅行,以及任何一种形式的移动有关”[3]。麦凯瑞所举的例子很多是过渡空间,如高速公路服务区、电梯、车厢、机舱和铁路。过渡空间的最大意义是连接两个目的地或主要空间,因此和移动、中转紧密相关。图森小说中描绘了大量的城市过渡空间,过渡空间实现了空间之间的连接,使原本静止的空间获得了时间性。人物在城市过渡空间中的行动和感受能够揭示当代人如何感知和实践城市中典型的,甚至是新型的空间。正如法国社会学家马克·奥杰所言,在当代社会中,“不再会有任何对个体的分析可以无视个体所中转的空间”[4]。
何为过渡空间?崔阳等认为:“城市过渡空间是由建筑内部空间向城市空间过渡或城市内不同功能、形式空间相互过渡的一种模糊空间形态……起到过渡、连接、铺垫、衬托的作用。”[5]这里提到的过渡空间有两类:区分建筑内外的空间、在外部空间中连接两个建筑或地点的空间。我认为还有第三种过渡空间:在内部空间中连接两个“主要空间”的过渡地带。
第一类是区分内外的空间。戴志中等将城市“中介空间”描述为“那些外部和内部,公共和私用,多数集合和少数集合,嘈杂和宁静,动与静之间的过渡空间”[6]。中介空间是连接内和外的过渡空间,是公与私的界限所在,比如建筑的入口、立面。法国学者桑苏在《城市的诗学》一书中将阳台、露台、窗户均归为此类过渡空间。①内部空间建立了私人生活的秩序,外部空间建立了公共生活的秩序,两者之间的过渡地带既可以成为明确划分公私的屏障,也可以成为内外部秩序的缓冲地带,甚至是延续地带。
第二类是在内部空间中连接两个“主要空间”的空间。法国建筑学家达伍迪认为主要空间(房间、卫生间等)和起连接作用的空间(走廊等)共同构成了一个起特殊作用的空间群,如接待空间、起居空间等。[7]内部空间可以小至公寓内的一个空间群,大到一幢楼房内连接各个次空间的过渡地带,如走廊、楼梯、电梯等。
第三类是在外部空间中连接两个建筑或地点的空间。此类过渡空间可分为线型空间和非线型空间。“线型空间是建筑沿街道两侧平行连续布局而形成的。它的基本表现和功能是联系和交通。它具有‘动’与‘续’的特质……非线型空间具有‘静’与‘终’的特质。”[8]线型过渡空间的代表是道路;非线型空间的代表是道路交叉口处的街头公园、绿地、各类广场等。在这类空间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马克·奥杰所说的“非地方”(nonlieux),“地方”塑造了个体的身份、关系和历史。反之,“非地方被定义为,在一个空间中,身份、关系和历史均不能获得象征意义”[9]。奥杰给出的例子有机场、铁路、高速公路、交通工具、旅店、游乐场、超市等。“非地方”中起到交通、运输和中转功能的空间是当代城市中典型的过渡空间。
本文将选取上述三类过渡空间中部分典型的城市过渡空间,分析它们在图森小说中的意义:这些过渡空间如何揭示人在现代城市中的感受?如何塑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参与动与静之间的矛盾?
一、连接与断裂:迷失、监视和死亡之地
在图森的小说中,一个反复出现的过渡空间是走廊,走廊起到连接各个独立空间的功能,使其成为有序的整体。但当整体本身呈现复杂与模糊的特点时,走廊只起到似是而非的指示功能,使整体看起来像有机的整体,实则是一种被割裂的无用的复杂。“城市是按合于理性的原则建造的,其规划管理本来是为了要变得更加通畅、快捷和方便,谁曾想其表现出来的结果却更加令人焦虑不安,更加接近迷宫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深不可测的非理性。”[10]当代城市规划中的功能性和其产生的迷宫效果暗示了在城市的理性下蕴含的非理性。
人物在走廊中时常处于迷失的状态。比如在《浴室》中,主人公迷失在意大利的旅馆里:“回到旅馆,我迷失在层与层之间。我顺着走廊,走上楼梯。旅馆空无一人;这是个迷宫,没有任何标识。”[11]同样,在《做爱》中,主人公也迷失在东京的旅馆中:“到达旅馆的第27层,我撞到好几扇门都是紧闭的,没有出口。这一层的照明晚间关掉了,黑暗中只有安全出口的绿色荧光标识在透明的包装壳中闪耀,出口,出口,出口。我听到电梯的门在我身后关上。我朝右走,到了一个昏暗的走廊里,稀稀疏疏的照明灯泛着惨白的光,给了这个地方古怪的、幽灵般的氛围。”[12]旅馆是连接故乡和异乡的过渡空间,它既提示外乡人已经进入陌生之地,又在进入未知的探险之前为他提供一个避难所。“这个地方使他们免于艰苦的社会斗争和竞争,但又已经提供了一个必要的转折。因此既有背井离乡,又有对一个具有威胁感的城市的谨慎而耐心的征服。”[13]在图森的小说中,旅馆中的房间呈现出和公寓一般的日常性,是和故乡的连接;而走廊、电梯、楼梯这些公共的过渡空间则引起异乡人的迷失,提醒他正在经历身份的转变。
车站和旅馆一样揭示了现代都市人在不断的空间移动中所经历的熟悉和陌生交替的感受。“车站既在城市之外,又在城市之内”[14],车站中的人会以一种混合的身份打量这个过渡地带,“同时是城市的公民和人类学家”[15]。在《做爱》中,主人公迷失在日本的高铁站:“我沿着地下通道的走廊走,穿过几公里长的传送带……我继续走在无休无止的潮湿的走廊里……地铁走廊和潮湿的动物发出的发霉的气味扑面而来,不经意让我想起巴黎……我走上自动扶梯,再次迷失在一个巨大的车站里。”[16]车站、地铁和商场的连接使车站成为一个“超级综合体”,它既是所有现代城市的缩影,属于已知的经验,又因其巨大而复杂的结构,成为一个制造迷失的地方。日本的高铁站是罗兰·巴特所说的“空无的城市中心”“中心不过是一个缥缈的念头,它残存着,并非为了彰显权力,而是以其虚无的中心给了整个城市的运动以支撑,迫使交通处于永恒的迷失中”[17]。它不再如市政厅、教堂一般输出一个稳定的意义,它是各种意义中转、混合和流动之处。
医院的走廊也呈现出迷宫般的复杂。《浴室》的主人公在意大利期间,女友遭遇不测,他到医院寻找受伤的女友,迷失在医院的走廊里,“我站起来,在长凳前走了几步。我慢慢地走远,走向走廊的深处。我穿过玻璃门,到达一个狭窄而昏暗的大厅,有一架备用电梯和一个楼梯……我重新站起来走上楼梯,上了一层楼,左转,沿着长长的走廊走……我停下来问一个护士……忘了是什么问题……我加快脚步,走上别的楼梯……我走进大而灰暗的电梯间……自动门打开,我走出电梯,推开走廊的玻璃门……”[18]。医院是机体失调后的治疗之地,体现了一种断裂:习以为常的日常性突然失灵,揭露了在熟悉的环境中视而不见的失调。突然失灵的机体揭示了有问题的日常性,伴随着旅行者身份的转换猛然被推到意识的前沿。主人公在医院的过渡空间(楼梯、电梯、走廊)中穿梭,找不到出口,体现了现代都市人突然意识到的失根和漂浮。
图森不仅描绘异乡人在陌生城市中的迷失,也呈现个体在熟悉的环境中的迷失。作为交通工具的出租车是城市的中转空间。出租车司机因为职业关系,对自己的城市了如指掌,“他感觉对道路和城市拥有权力”[19]“他的移动体现了自由”[20]。在《自画像(在国外)》中,图森描写了在京都的时候,自己乘坐的出租车迷失在京都的道路里:“司机认真地读名片,走下出租车,在路上溜达了一会儿,向一位女士问路,回到车上,一脸怀疑,又沿着人行道缓慢开了几分钟,下车到了人行道,关掉发动机。”[21]出租车司机身处双重的过渡空间中(道路和出租车),他的职业使他处于永恒的过渡状态,他既有对城市道路的掌控,又因为临时的任务需要面对不可预见的下一刻。他的迷失体现了城市在其熟悉的面孔下暗含的陌生和未知。
在19世纪作家的笔下,迷局一般的现代城市形象在其发轫之初就已经存在,比如在波德莱尔的诗歌中,城市“蕴藏着宝藏,发散着诱惑,洋溢着诗意,激发着欲望,同时也潜伏着诸多问题,充满了神秘和阴谋,代表着混乱、危险和毁灭”[22]。在图森笔下,城市依然具有塞壬般的迷惑力,但不再具有危险的致命的诱惑。迷失不再激发探究的欲望,当代人不再幻想在表象的迷宫的终端还有有待发掘的秘密。迷宫不再导向出口,问题也无需答案,城市如同一个庞大的过渡之地,没有终点和休憩,人在城市中移动就是处于恒常的过渡和迷失状态,找不到落脚之处。
城市的过渡地带是迷失之地,也是监视和死亡之地。走廊作为连接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过渡地带,成为典型的监视之地。在《逃》中,作者和同行的女人在列车上私会,他想象自己被他的向导张详之(音)监视:“他一直在监视我们,现在他藏在门后等我们。他潜伏在走廊角落的阴影中,监视着卫生间的门……我监听着走廊里丝毫声响。”[23]之后,他们进入一家旅馆,主人公处于高度警觉的状态,他“在黑暗中睁着眼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监听走廊里的声响”[24]。主人公感到被监视的同时也在监视别人。走廊和门在这里显示出模糊性,既有公共领域对私人领域渗透的威胁,又有个人试图抵抗和掌控外部世界的努力。“中间领域”的“暧昧和流动”②,向内和向外的双重可能性滋生了警惕和不安,象征了城市中自由表象下的隐形的监控。
城市令人不安的一面在死亡恐惧中达到顶峰。《玛丽的真相》中,作者屡次提到门的象征意义。主人公从前女友玛丽家望出去,看到对面法兰西银行的大门,“银行铜做的沉重的大门慢慢地打开一半”,随即又关上,“在空无一人的道路上投下弥散的威胁,因为不可见而愈加有效”[25]。门是连接内与外、生与死的过渡空间。门的背后是未知,是无穷的可能,门的打开可能是危险,也有可能是重生。巴什拉说:“门是整整一个半开的宇宙……诱惑我们打开存在最为隐秘的部分。”[26]通过门,城市具备了厚度,它不再只是符号堆积而成的网络,或是平面移动的路线集合。相反,它是探索存在的场域,在表象背后,城市生活的各个层面在隐秘中层峦叠嶂地打开。门的后面还有门,道路的尽头连接着道路,墙的后面是未被明言的生活……打开城市之门犹如打开存在之秘密,不断逼近存在的深处。
在《玛丽的真相》中,门所激发的想象总是和死亡的迫近有关。玛丽的情人让-克里斯多夫深夜突发心脏病,他在去世前望着对面法兰西银行厚重而沉默的大门,心生不安,“重重的铜制大门紧闭,周围毫无动静。让-克里斯多夫·德·G有一种阴郁的预感,确信一桩悲剧将会在这个宁静的暴风雨的夜晚降临。他即将见证暴力、震惊和死亡汹涌而来,法兰西银行的围墙外即将响起救护车的鸣笛,下面的道路将上演一场混合着追赶、尖叫、碰撞、关门的声音、枪响,警车和炫闪灯将突然涌进道路,摇摇晃晃,照亮黑夜中的墙面”[27]。图森的人物时常会经历死亡焦虑。在室内日常空间中,他们陷入对死亡的思考或是突发的暴力行为;在旅行途中的过渡空间中(比如道路),他们预感到一种即将到来的死亡威胁。死亡在此是日常性的断裂。正如桑苏所说:“真正的城市是恐怖流连的地方,至少蕴含着一种暴力。”[28]此处的暴力是象征性的暴力。日常性作为一种规训的力量被普遍化,成为当代人无法逃脱的命运。但日常性本身又包含着一种反日常性的破坏冲动,死亡冲动便是这种反日常性的体现。死亡和对旅途、远方的想象联系起来,成为城市生活地平线之外诗意的凝结。城市如随时将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既会让人产生不安和死亡恐惧,又构成了城市日常表象下的幻想的空间。
二、靠近与远离:有距离感的社交之地
图森的小说呈现了一群囿于自己的内在性中,拒绝走向外界、走向公共领域的个体。“从此社会性的存在消失了,人们不再试图在社会上寻找一席之地或竭尽所能去保存他的位置。因此当代人放弃拼搏,甚至在比赛开始之前就喊停。”[29]室内空间成为图森小说的主导空间,是人物自我封闭之地。即便当人物走向外部空间,也同样处于孤独和隔绝的心境中。从内部走向外部的过渡空间反倒成了社交关系萌芽的地带,过渡空间中的社交关系呈现出转瞬即逝、程式化、尝试性的特点。
转瞬即逝的特点集中体现在男主人公和女性的艳遇上。《照相机》中,男主人公在驾校学车,学员中有一个年轻女人,每次和他一同下车,“当教练车远去时,我和她在人行道上停留了一会儿,在我门前聊了几句。很奇怪的是,她倚靠在门上,一只手撩着头发,好像并不想告别”[30]。这段似乎即将开始的情愫被叙事者的反讽打断,原来她只是住在同一幢楼里而已。刚刚萌生就终结的艳遇同样出现在《先生》中,“先生”应彭斯·罗马诺夫夫人邀请去其乡间别墅度假,夫人对其发出共度良宵的暗示。在她起身去房间换衣服时,先生“不知道该去哪里,决定在那里等着,在走廊里反复踱步,时不时到楼道口,朝楼梯上望一眼”[31]。被预示的艳遇却无疾而终,先生被迫接受路过楼道的朋友的邀请,一同走向花园。如此有头无尾的艳遇是图森的情境反讽的一种,展示了蜻蜓点水的人际关系和日常性语境下激情爱情模式的消解。《逃》集中呈现了过渡空间中转瞬即逝的爱情。主人公在列车里和翻译李琦(音)私会,他们穿过重重走廊和车厢,为了找到一角幽会之地:“我悄无声息地和李琦在走廊里碰头,一前一后在沉睡的车厢里走着,沿着窗户跌跌撞撞从一节车厢走向另一节车厢……在车厢入口的狭小更衣室这个过渡空间中,我们坐在地上,互相拥吻,喧闹的车厢在黑夜中前进。”[32]车厢和走廊这个过渡之地催生了偶遇的激情,只有在过渡空间中被应允,因为没有明天,不会妨碍正常的轨迹。过渡空间像是游离在日常性之外的中立之地,“是偶然性的领地”[33],允许暂时的脱轨,承诺片刻的冒险,但在抵达终点之时被迫重回日常轨道。
图森的人物并不完全避世,相反,有些人呈现出融入人群的努力,由此产生了程式化的社交关系。“先生”名校毕业,在大公司中担任中层管理,收入颇丰。他在工作中奉行能不多使一分力就不多使一分力的原则,他怀着游戏的心态有限地入世。公司的电梯是典型的公共空间中的过渡空间,是人们相遇的地方。“先生”在电梯中展现了伪装的社交性:“先生和总经理一起在电梯里,先生问他想去哪个楼层,以便为他按按钮。整个过程,他们两个看着电梯墙面的不同地方。先生低垂着眼。总经理玩弄着钥匙扣。有时,他们交谈几句刻意选择过的话。总经理专心地听先生说话,双臂抱在胸前交叉,样子像在思考这个人是谁。”[34]在图森式的漫不经心的幽默中,公共空间中人和人之间的交流被缩减为一种程式化话语,最小限度地维持人际往来的幻象,被桑苏称为小资产阶级的“楼梯上的礼节”[35]“在这个公共空间,动作具有某种严肃性,人们尽量回避有损他人尊严的举动”[36]。人们并不试图走近别人,精密计算着自我与他人的最佳距离,无需靠近,但要维持连接的功能,形成一种经过计算的有距离的社交关系。
同样,客厅作为内部空间中容纳外来者的过渡地带,本应是滋生人际联系、连接自我和外部的地方,但在图森小说中变成了一个程式化的交流之地。《浴室》中两次在客厅中的交谈体现了勉力维持的社交性,人物操持着程式化的语言,假装对他人感兴趣,实则鸡同鸭讲,互不关心。有距离感的人际关系应和了当代室内设计的原则:室内布局打破了传统资产阶级的等级分明、强调中心,具有道德意味的空间原则;家居的功能性不再体现为具体的实际功能,而是元素和元素之间的组合效果。③客厅的布局“和技术性话语呈现出不可置疑的默契”[37]“真诚,不再是通达透明,通达我们最为隐秘的部分,而是以钢筋、水泥、玻璃等不畏惧展示自己的材料的方式活着”[38]。人际交流的目的不再是敞开自我、走近他者,在他者中重新发现自我,而是以一种设定好的方式敞开,在契约双方共同划定的界限中展露格式化的“透明”。在某些社交过渡空间中,人际之间的连接被媒体的独语所代替。比如《浴室》中叙事者如此描述意大利旅馆的迎客厅:“电视机的声音应该是关掉了,没有任何声音。饭厅里毫无声响,时不时听到我身后的老年女人用刀叉发出的短暂的金属声音。晚饭后,我到旁边的迎客厅里,坐在电视机前。”[39]旅馆的门厅和走廊是“外部秩序的延伸”[40],这是人们会面、交谈的地方。因为媒体的介入,社交空间中人和人之间的交流被人和媒体的单向交流所替代。人似乎通过媒体与外界连接,实则处于孤立的状态中。图森通过对公共的过渡空间中社交活动的描写,揭示了“在人际关系和想象力的层面,我们经历了双重的贫瘠化”[41]。
虽然人际交流出现萎缩,但过渡空间中的人们仍然尝试着相互间建立短暂的、点状的联系。图森喜欢描写人物在国外时因为语言受限,试图用仅有的外语词汇和外国人进行沟通的场景。比如《浴室》中主人公在意大利的旅馆,每次在楼梯上和吧台服务员相遇时,都会点头问好,“当我傍晚去喝咖啡时,我们有时会交谈。我们谈论足球和赛车。虽然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但不妨碍我们”[42]。两人交换着仅有的单词,津津有味地交谈着。通过颇具喜剧性的场景,图森想要展示人们对交流的渴望、遭遇的困难和进行的尝试。
对交流的渴望和尝试在“非地方”类型的过渡空间中显得尤其珍贵。在传统意义上的地方,人们可以通过相同的语言、文化和生活习俗等建立起集体身份认同。在“非地方”中,共同的身份认同是暂时的、契约式的。“非地方”以其文字、图示、物品等符号化的规约方式(如车票、路线图、手推车等)在陌生人群中建立起一种默契。“非地方”使用者的身份被缩减为车票信息、身份证件等,是对其个人性的短暂剥夺。“最终他所面对的是他自己的形象,但实际上是非常奇怪的形象。文字组成的景色和他,以及其他所有人一样,进行着无声的对话,唯一成形的脸和声音,是他们自己孤独的脸和声音,唤起了千千万万其他人共有的孤独,显得尤其令人迷惑……非地方既不制造独特的身份,也不建立联系,只炮制孤独和相似。”[43]奥杰将“非地方”中所产生的人际关系或人和物之间的关系称为人和自己的相遇:人们在其他人中、在物品中,看到的是与自己相似的脸,共同的脸被抹去了个人特色,在同一空间中既相连又隔绝。为了制造共同的身份,“非地方”需要一门简单的人人都能懂的语言,一种“普遍化的语汇”[44],这种功能指向的语言将导致“语言的弱化”[45]。在“非地方”中,匿名的两个旅行者所产生的真正的交流将打破契约式语言的藩篱,恢复人际交流的乐趣。图森在《浴室》中描写了主人公从意大利回国,在机场的候机室偶遇一位俄罗斯人,两人用有限的意大利语谈了“当代史和政治”[46],并“回顾了一圈二十世纪意大利史”[47]。图森特意强调了受限的交流语言,正是语言上的障碍指示人们正在跨越边界,边界的两头是两种文化各自建立起来的身份。人们虽然经历了因为不同语言和身份产生的交流障碍,但这种障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非地方”所提供的同质化、简单的共同语言的抵抗。图森小说中随处散落着外语和蹩脚的交流,人物试图在抹除个性和文化的契约式语言之外艰难地建立起另一种交流。
过渡空间不尽然只有浮光掠影的联系,它也能唤起最为深沉的情感。图森的主人公在过渡空间中感受到爱、安全和依恋,也因其过渡的性质被迫接受分离和距离。电梯既可以是公共空间程式化的社交之地,也可以是情侣相拥之地。《做爱》中主人公和玛丽一起坐电梯下楼,他们在狭窄的电梯中并排站着,感觉自己在一个酒壶中穿行,电梯“底部是圆形的,包裹起来,女性化,虽然线条严谨,但其光亮有一种流畅如水的感觉”[48]。电梯因其女性化的线条给了主人公安全感,爱人的在场给了这个公共空间以私密性:“我们在电梯里下降时,我把她的一缕头发放正。她看着我。我搂住她的肩,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脸颊。”[49]除电梯外,昏暗的走廊也是催生亲密关系的地方。在《玛丽的真相》中,作者和玛丽分手后重逢,“在公寓昏暗而杂乱的走廊里相拥”[50]“我们在昏暗中互相望着,沉默无语,但我们懂彼此,我们已懂得”[51]。走廊是失而复得,也是即将失去;是深沉热烈的爱,也是不可挽回的分别。图森式的爱情就像过渡空间,是相反两极的中间地带,没有完全的融合,也没有绝对的分离。这种矛盾状态在第一部小说《浴室》中便已显现。主人公在意大利的旅馆里每日和女友打电话:“我坐在门口的地毯上。埃德蒙逊跟我说话,我感觉很好;我背靠着墙,双腿交叉,边抽烟边听她说话……我需要感觉离埃德蒙逊很近……我们有时在电话里会有长时间的沉默。我喜欢这些时刻。紧贴着听筒,我努力想要听到她的气息和呼吸。”[52]在旅馆的入口处打电话,地点的选择意味深长。主人公想要走出自我封闭,重拾与他人的连接,但又在门口徘徊,坚守自己的壁垒。电话是带有距离感的亲密关系的传送方式,电话和入口这个过渡空间一起揭示了无法处于稳定状态的爱情,唯有在靠近和分离的往返中,人物才能感觉到和他人的深层联系。
分离的痛楚在扶梯中达到顶峰。《玛丽的真相》中,主人公和玛丽分手后,在自动扶梯上相遇。他们乘坐相反的扶梯,相遇的瞬间又被迫远离。在想要靠近又无法靠近的焦灼中,主人公感到“这是关于我的缺场的生动的画面”[53],而玛丽“远离我,在扶梯上同时是静止和运动的,就像突然围困在现实的下沉和世界的滞坠中……我看着她远离我,感到她正走向另一头,走向彼岸,一个不可言说的彼岸,在爱和生命的那头……扶梯把她带向神秘的地方,我无法进入,移动扶梯是通向那个地方的载体,一条垂直的冥河(被垂直划分的金属楼梯,扶手是黑色的橡胶)把他们带向死亡”[54]。在扶梯的逆向运动中,主人公感到生命的悖论:我们如此渴望抓住生命中纯粹的见证自我在场的瞬间,却只能在偶然的片刻中获得与自我重逢的喜悦,之后又被运动中的现实所裹挟,奔赴与死亡的邀约。自动扶梯就像我们的存在之路,在相对的重逢中无可挽回地走向绝对的分别。过渡地带不再只是人和人互相连接之地,也是人和自我、生命和死亡、相对和绝对互相交汇之地。
三、运动与静止:从过渡空间到过渡状态
过渡空间中的中转空间总是和移动、速度联系在一起。奥杰认为快速流通成为超现代的特征之一:“城市化的普遍化首先是官僚技术的暴力和对流通、沟通的瞻念所导致的结果,就如同城市空间和城市周围空间的存在仅只是为了方便移动,或者相反,它们只能通过交通道路被看到。”[55]城市内的中转空间的流通功能被价值最大化,以至于效率成为此类过渡空间的唯一美德,“最重要、效率最高的当然是人的流动,因此,在那里是不会产生生活的情感的”[56]。以速度为目标的城市空间改变了人们的感知,人们对时间的流逝尤其敏感,身体也总是处于一种蓄势待发的状态。当代人具有一种“对时间近乎病态的敏感”[57],其身形的敏捷、迅速、灵巧和机械并存成为一种社会必须,由此产生了“极其会移动,极其有可塑性,具有无穷适应能力的个体”[58]。
图森在《逃》中描写了人物在过渡空间中对速度的追求。主人公、李琦和张翔之三人骑摩托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我们三个倾斜的身体就像属于同一个三头怪物,贴在这个发出轰鸣的钢筋结构上,在黑夜中穿行,马达无穷无尽地狂啸着。”[59]三个人虽然在高速移动的机器上,但他们“好像被凝固,僵硬,如雕塑一般,固定在这个姿势,追求令人眩晕的速度”[60]。处于高速公路上的人感官极度敏感,他们在速度中追求一种震惊的效果,一种追求速度又害怕被速度追上的亢奋。反之,《照相机》中的主人公所感受到的是嗜睡而僵硬的状态:“当波露加耶夫斯基先生开着雪铁龙凯旋全速在环城大道上行驶时,我在后座上打盹,想到我所碰撞到的现实,远未显示出偃旗息鼓的态势,似乎围绕着我慢慢变硬,从此我被一种无力感包围,感觉无法脱身于这个坚硬的现实。”[61]这一“坚硬的现实”可以解释为人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塑造下,自觉地使自己的身体和机器的节奏同一:“调整他们自己的‘运动以便同一种自动化的统一性和不停歇的运动保持一致’。”[62]
图森的主人公在面对过渡空间中的速度崇拜时具有三种反应:一是通过逃离,以速度战胜速度;二是试图静止,以不动来对抗运动,它有一个变体,即以闲暇和慢速度的运动来恢复对城市的实践;三是投身于移动中,与移动合二为一。
《逃》讲述的是在异国城市空间中的逃离,主人公坐在摩托车后座上,任由别人带着他在北京“巨大的如迷宫般的高速公路”[63]上穿梭:“整条路上有白光在我们身边持续闪烁着,在天地之间,夏日巨大的天空像宇宙,抑或是脑海中荧光组成的风景,微小的红色和蓝色的电光闪烁着,划出实线、虚线和斑纹状线条。最终我不再看道路、树或是路上的持续的白线,不再看天空和星星,我握着李琦的手,在夜色中逃离,在这静止的无穷的瞬间。”[64]逃离不是为了逃避具体的地方,也并不去向哪个目的地。逃离是一种持续的状态,一种内在的需求,似乎城市中不再有可以落脚的定点,整个城市成为一个巨大的过渡空间。逃离中的人试图超越速度,通过战胜速度进入一种心醉神迷的静止的状态。
与逃离者以速度作为武器来防止被速度所超越不同,《浴室》的主人公则试图在运动的过渡空间中保持自身的静止,而这一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我在一节车厢度过了夜晚,一个人,关掉了灯,一动不动。我对运动敏感,仅仅只对运动敏感,外在的明显的让我发生了位移的运动。尽管我一动不动,我也对我正在走向衰败的身体内的运动敏感,我开始只关注这种不可察觉的运动,并竭尽所能想要使之固定。但是怎么固定?如何证明?一个小动作都能使注意力涣散。”[65]主人公区分了两种运动,一种是外在的空间载体的移动,另一种是内在的机体自然的节律。主人公试图以身体的静止来对抗外部的移动,却发现内在运动是生命绝对的形式,无法固定或克服。运动是生命的必须,过渡空间中的移动通过和生命的节律挂钩获得了合理性。
对静止的渴望有一种变体是漫游者的人物形象。斯特尔勒在《符号之都,巴黎和关于它的话语》中说道:“漫游者生活在完满的时间中,他品味时间就像品味自己的财产,因为他意识到躲避了加速的社会法则。漫游者是城市之眼。让他激动万分的是看;这是瞬间的展现。”[66]漫游者游离于都市时间之外,他试图用自己的节奏丈量城市,他是动与静的结合,是静止的愿望在速度面前的智慧的妥协。漫游者眼中的城市也摆脱了加速的命运,每一个细节的停留都是瞬间在展现其自身的魅力。图森小说的主人公喜欢在城市过渡空间中漫步,时而在街道上,时而在商场里,甚至公寓的走廊也是他们闲庭信步之地。他们以双脚实践城市,有时也借助交通工具(如公共汽车)穿梭于大街小巷。他们表面上无所事事,漫游所至皆以琐碎庸常的景象为主,但正是通过漫不经心的游戏态度,他们试图引入一种“当下的、断裂的、‘交际的’”[67]空间实践形式。他们在漫游的当下发掘了城市无数可能性中的一种,通过选择自己的线路以点状的方式串联起属己的城市空间语言,并在每个分散的地点之间建立起联系。
人物的第三种选择是顺应速度,和速度合二为一。在《照相机》中,主人公讲述飞机上升时的体验:“我任由被飞机飞离地面的运动所牵引,试着和机器不可遏止的加速运动融为一体,借助于它的冲力让我自己起飞。”[68]交通工具不再只是一个工具,通过使自己的内在性和机器共鸣,主人公超越肉体的局限获得极限的速度。《逃》中的主人公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穿梭后,抵达了一条车水马龙的主干道:“如同在长时间顺着小航道航行后,我们突然抵达了大海。我们随后投身于加速器的有力加速中,任由自己被公共汽车和出租车组成的持续不断的洪流所牵引加速。”[69]人顺应过渡空间的加速运动,和交通工具组成的洪流合体,到速度中去,成为过渡空间的一部分,让渡个人性,参与到由物所象征的抽象整体中去,这是现代城市体验中的物我合一。如果说通过逃离,人在追赶未来,那么在与过渡空间融为一体的过程中则只剩下永恒的现在时。正如维斯特法尔所说:“图森想见证现在时的在场。”[70]在加速运动的过渡空间中,人们置身于浓缩的、强烈的现在时中,过去和未来被遗忘在瞬时速度所激发的出神状态中,大城市所引起的陶醉“其实质是时间的放大或强化”[71]。
在另一些段落中,过渡空间不只是现代性“过渡、转瞬即逝、偶然”[72]特性的体现,它甚至成为存在的唯一形式。在《自画像(在国外)》中,作者描述面对河内川流不息的交通时的感受:“河内的交通就像生活本身,大方、无穷无尽、充满活力,处于永恒的运动中,持续的不平衡,任由自己顺着它的走向,融入其中,就是获得生的体验……我在街道中穿行,脚贴着柏油路面,任由自己被时间的流向所牵引。我接受生命的运动,我毫无抵触地伴随着它,我的思想最终融入车流中。”[73]运动是生命的表现形式,是存在中的人唯一能把握的现实。图森的人物虽然想用静止固定存在的瞬间,并在瞬间中获得生命的洞见,但最终发现静止是徒劳,我们无法遏制生命向前的运动,唯有顺应它,进入它,在时间的行进中感知存在,与存在合一。如此,过渡空间成为存在铺展自身的场所,是存在的形式。人在过渡空间中的体验便是存在的体验,图森将此称为“过渡状态”。《逃》的主人公从北京飞向意大利的埃尔贝岛,飞行途中一直处于漂浮嗜睡的状态:“我持续处于旅行的暂时的中间状态,好像这种可延伸的有弹性的过渡状态可以延展至无穷。最终我的思想不停留于任何一处,既不在北京也不在埃尔贝岛,总是处于我所穿越的过渡地点的表面,同时是静止和运动中……好像这次旅行是我生命中所有旅行的精华。”[74]存在是永恒的过渡状态,是生与死之间无目的的旅行。在存在的表象中滑行,既在外面又在里面,既是运动又是静止,既在某处又无处停留,图森在过渡空间中实现了关于存在的矛盾体验。
刘波认为,现代情感“充满了矛盾和悖论”[75],现代城市的体验是一种矛盾的体验。图森对城市过渡空间的描写呈现了人在现代性面前的一些恒定的感受,同时揭示了当代社会特有的问题。首先,城市过渡空间传达了现代城市复杂的、令人迷惑和不安的一面,又将恐惧转换成魅惑,将空间批判转换成空间诗学,过渡空间成为打开城市缺口、打破日常和已知、激荡想象力的地带。其次,它体现了矛盾的社交关系。过渡空间连接内与外、公与私,既在孤立的个体间建立了联系,甚至助推了亲密关系的建立,又在关系中设置了屏障,使人与人无法真正地靠近。它建立了一种程式化、契约式的人际关系,揭示了人和他人、人和自我不可弥合的距离。最后,城市过渡空间集中体现了现代社会对速度和效率的追求。个体在此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或是超越,或是抵抗,或是顺应高速运动。人们既渴望成为过渡空间中机器的延伸,在速度中获得亢奋的感官体验,又希望恢复慢与静止,在运动中获得永恒的片刻。
注释
①参见Pierre Sansot,Poétique de la ville(Paris:Payot&Rivages,2004).
②参见黑川纪章:《新共生思想》,覃力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
③参见Jean Baudrillard,Le système des objets(Paris:Gallimard,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