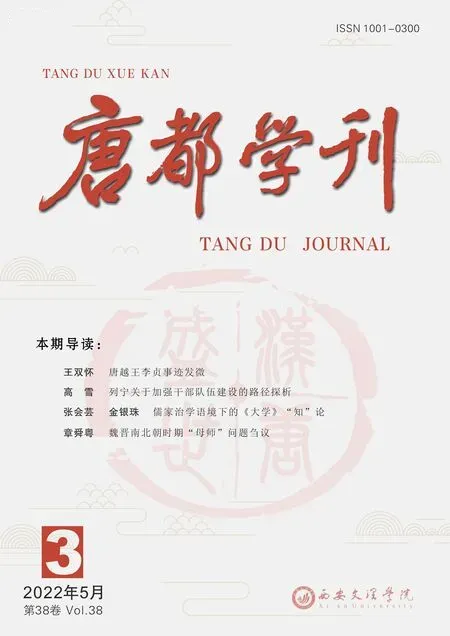北族传统复起与北魏政局的走向
2022-11-21禅馨
禅 馨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契胡酋长尔朱荣率领的军政集团于六镇之乱后迅速崛起,武泰元年(528),尔朱荣率军南下洛阳,开启了对北魏政权的控制。北魏末年镇民主导的一系列对抗朝廷的暴动主要受孝文帝改革造成的北魏统治区域内南北分隔的影响,被汉化政策割裂并遗留在北方的拓跋核心集团逐渐集结到尔朱荣麾下,以政变为契机,突破南北畛域进入洛阳。伴随集团的扩张和对朝局的介入,尔朱荣急需整合集团内部和洛阳朝廷的政治势力,以统合南北、重塑政权。为了加强掌控力并与洛阳上层抗衡,扬弃孝文帝的“汉化”、依托平城时代的北族传统,就成为尔朱集团汲取权力的不二法则(1)学界针对北魏末动乱的性质究竟是“胡化”与“汉化”的对立,抑或源于阶层矛盾的反北魏政权斗争,存在不同看法,对北朝后期一系列“胡化”制度的论述也各有侧重。陈寅恪指出北魏末的六镇之乱和继之而起的尔朱氏集团具有反对汉化的性质,随后宇文泰在构建关陇集团时引入了胡族体制,以“继述成周”“缘饰塞表鲜卑之胡制”。唐长孺认为北魏末的动乱源自北镇豪强与洛阳汉族和鲜卑门阀政权的阶层矛盾。川本芳昭认为六镇之乱是有民族斗争性质的反北魏政权斗争,北魏末以尔朱氏集团为代表的新兴势力对以拓跋皇室为中心的制度和习俗的归属感很淡薄,他们恢复“代都旧制”的举措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复兴。岡田和一郎总结了北魏末至北齐时期“胡化”势力标榜的政治体制,认为这些“代体制”存在的目的是反对孝文体制,不具备完整的体系。罗新则以高欢主导下的北魏皇帝元脩的继位仪式为例,指出北魏末以来种种所谓“反汉化”的现象,都延续了内亚的传统。参考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7-48、197-200页;唐长孺《试论魏末北镇镇民暴动的性质》,载于唐长孺《山居存稿》,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7-61页;川本芳昭《北族集団の崩壊と太和二十年の謀反·北鎮の乱》,载于川本芳昭《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东京汲古書院1998年版,第325-340页;岡田和一郎《北斉国家論序説》,载于《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39),2011年版;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在此种背景之下,“铸金人”“西郊祭天”等传统仪轨亦成为他们争取法统的重要举措。
一、“铸金人”与孝庄帝之立
武泰元年二月,北魏孝明帝暴毙[1]294-295。胡太后扶植孝明帝年仅3岁的族侄元钊为帝,以便继续把持朝政[2]505。但此举遭到已成气候的尔朱荣反对,他公开质疑明帝死因,提出改立宗亲中有“年德”“声副遐迩”者为帝,同时勒兵南下。为宣示出兵之正当,尔朱荣着手寻觅合适的拥立对象,在议定人选时采用北族传统的“铸金人”仪式,借以表明正源之本[1]1782-1784。
铸造金属偶像的行为早于拓跋鲜卑,系北族流俗(2)部分学者认为尔朱荣所铸的金人可能为佛像,这一习俗或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参见金申《北魏铸像以卜的风俗》,载于《文物天地》2007年第9期;王爱民《北魏立皇后铸金人占卜习俗考论》,载于《滨州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但就金属铸像的流传而言,铸像以卜更可能源于草原诸部族的传统,如匈奴的休屠祭天金人。参考James R.Ware,“An Ordeal among the T'o-pa Wei”,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32, Livr. 4 (1936), pp. 205-209;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版,第9-11页;江上波夫《匈奴的祭祀》,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 第九卷 民族交通》,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3-25页;孙小敏《北魏立君、立后“铸像以卜”制度溯源》,载于《西夏研究》2016年第1期。。铸像作为窥天问卜的手段,流行于魏晋南北朝。十六国时期的羯胡石赵养子冉闵自立为帝并遣使鲜卑慕容儁,因称帝前铸像未成、有丢失传国玺的嫌疑受到燕臣封裕之诘难,质疑其得位的正当性。可见无论羯胡、鲜卑,均知晓铸像问卜可以传达某种“天命”;更重要的是,其在北族政治习俗中的君权正当性,堪可与华夏之传国玺并埒(3)参见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32页;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163页;《通鉴》与《晋书》对冉闵铸像一事的记载多有不同,二书应当各有所本。参见陈勇《〈资治通鉴〉十六国资料释证(汉赵、后汉、前燕国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83页。同样面对封裕对冉闵铸金像未成的质疑,在《晋书》中常炜只用“铸形之事,所未闻也”将此事略过,《通鉴》中则记载常炜在“不闻”的否认之外,强调冉闵的“受命”来源于手握符玺,而非取决于金像。但无论常炜借由何种话术否认铸像一事,他与封裕的对话均围绕冉闵是否“有天命”与传国玺和铸像两个重要标志的关系展开,二人对铸像代表天命的观念都是十分了解的。。拓跋氏建立政权之后,又进一步将铸像问卜制度化,在立皇后之前采用“手铸金人”的方法测试妃嫔[2]486,相较于北族习俗,北魏的铸像立后仪式的流程更为详细和规范,强调候选妃嫔必须亲自参与[3]。孝文帝改制时重新厘定后宫制度,北魏的铸像立后仪式遂被废除(4)史料中出现的铸像立后事例只有北魏早期的道武皇后慕容氏、道武宣穆皇后刘氏和明元昭哀皇后姚氏,其后该制度被继续保留,直至孝文帝欲立小冯氏为后,卢渊依制提议“简卜”被孝文帝否决,小冯后成为第一位明确没有经过“手铸金人”测试的北魏皇后。参考魏收《魏书》,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155页;潘敦《可敦、皇后与北魏政治》,载于《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4期。。
尔朱荣铸像立君的过程如《魏书·尔朱荣传》所云:“(尔朱)荣抗表之始,遣从子天光、亲信奚毅及仓头王相入洛,与从弟世隆密议废立。天光乃见庄帝,具论荣心,帝许之。天光等还北,荣发晋阳。犹疑所立,乃以铜铸孝文及咸阳王禧等六王子孙像,成者当奉为主,唯庄帝独就。”[1]1783这与北族传统仪式、特别是纳入北魏早期国家制度的铸像立后仪式略有不同[3]。第一,仪式的主导者是尔朱荣,旨在检验他人而非自己的资质,这是铸像立君、立后诸事中仅见的一例,更与北魏强调妃嫔“手铸”的仪式有别。这应是尔朱荣定计晋阳与候选者身处洛阳的地理限制下的变通之举。第二,尔朱荣瞩意的对象是元子攸即上文的庄帝,但他测试的范围囊括了“孝文及咸阳王禧等六王子孙”,理论上无法保证元子攸中标。北魏在立后铸像之前有一个群臣奏议人选的环节,部分候选者议前已在某种程度上享受皇后的待遇并履行职能,铸像毋宁说是一种对准皇后的最终认证(5)道武慕容皇后铸金人前,经历了卫王拓跋仪等上奏、皇帝准奏的流程。铸像前已有皇后之实者如道武刘皇后、明元姚皇后。参考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92-493页;孙小敏《北魏立君、立后“铸像以卜”制度溯源》,载于《西夏研究》2016年第1期。。候选者的唯一性、准合格身份和参与度,是构成铸像立后仪式权威性的重要因素。尔朱荣的改动弱化了元子攸的存在感,凸显了自己的主动地位,这种选择与双方的合作模式有关。
那么,尔朱集团为什么要拥立元子攸为帝呢?
我们首先看看《洛阳伽蓝记》与《魏书》所述铸像与议立过程的异同。前者云:
(尔朱)荣即共(元天)穆结异姓兄弟。穆年大,荣兄事之。荣为盟主,穆亦拜荣。于是密议长君诸王之中不知谁应当璧。遂于晋阳,人各铸像不成,唯长乐王子攸像光相具足,端严特妙。是以荣意在长乐。遣苍头王丰入洛,约以为主。[4]15
这里描述尔朱荣因铸像成功瞩意元子攸,而《魏书》则将铸像一事置于尔朱荣联系元子攸之后,这并非单纯的文字编排差异,表明的是二者关系的疏密。纵观尔朱氏与元子攸的合作,可知尔朱荣择立新君的决定并非独立做出[5],《魏书》“荣发晋阳,犹疑所立”进而再行卜问的描述可能更为合理。作为契胡酋帅出身的尔朱荣,其家族于北魏迁都洛阳后仍居旧都平城附近的秀容,保持部落形态和游牧生计[1]1779-1781;尔朱荣及其父尔朱新兴虽在洛阳出任直寝、散骑常侍等随侍职位,但只是“冬朝京师,夏归部落”[1]1780,与洛阳的联系并不紧密;非但如此,随着洛阳朝廷汉化的加深,尔朱氏与政治中心的关系却在疏远。如此一来,即便身处洛阳,任职禁军的同族尔朱世隆亦参与谋划[1]1804,但他们对洛阳政局的影响力十分有限。这意味着此时的尔朱氏势力尚无法直接干预朝廷的动向,于是,联络洛阳那些“异见者”弥补自身的不足就成为尔朱荣加强势力的一个办法(6)元子攸兄长元劭在孝昌末年因有“异志”而被安丰王元延明告发,元子攸也曾多次庇护朝廷犯官及其亲眷,显示出对抗胡太后等当权者的倾向。参考魏收《魏书》,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656、1851页;令狐德棻《周书》,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365页;苏小华《北镇势力与北朝政治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1页。。
其次,在洛阳任职并早怀“异志”的宗亲元子攸也没有被动待选,而是主动与尔朱集团接洽。据《魏书·李季凯传》记载:
坐兄事,与母弟俱徙边。久之,会赦免,遂寓居于晋阳,沉废积年。孝昌中,解褐太尉参军事,加威远将军。寻除并州安北府长史。肃宗崩,尔朱荣阴图义举,季凯豫谋。[1]987-988
元天穆于孝昌年间(525—527)曾任安北将军、并州刺史[6]276-279,这个李季凯正是他的长史佐官。元天穆是尔朱荣的心腹,李季凯虽列其属下,但并不属于尔朱集团,而是出身汉人的士族陇西李氏,孝文改革之后,汉人士族在中枢政局的影响逐渐扩大,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他们通过联姻,与帝室近支结成政治同盟[7]。陇西李冲之女被孝文帝指婚彭城王元勰诞下元子攸兄弟[6]148-149,元子攸遂得依托陇西李氏及其交好的汉人士族以作靠山[5]。李季凯之支持元子攸自在情理之中,其人豫谋乃是受元子攸为首的“异见者”群体意志的驱动,并非个人行为。
尔朱集团拥立元子攸,是二者积极配合的结果。尔朱荣声称以“年德”“声副遐迩”者为君,针对的就是胡太后扶持的幼帝,他由此指责太后“奉未言之儿而临四海”。元子攸之年龄、从政经验和政治声望均超越幼帝具有君主之资质,这是尔朱集团依凭的优势(7)《魏书》卷10《孝庄纪》记录元子攸因“家有忠勋,且兼民望”受到尔朱荣的重视,及前述《洛阳伽蓝记》中尔朱荣与元天穆“密议长君诸王之中不知谁应当璧”,都是在针对胡太后所立幼帝元钊的弱点。参见魏收《魏书》,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303、1783页。。他因此率军挺进洛阳,胡太后失去支持、在洛阳禁军和朝廷上层倒戈的压力下被迫退位,元子攸顺利登上皇位[8]314-316。这就是武卫将军费穆为尔朱荣分析入洛局势时所说的“长驱向洛,前无横陈者,正以推奉主上,顺民心故耳”[1]1107。
元子攸即位,形式上是元魏宗室内部的皇位更迭,但背后反映的却是朝廷权力格局的新变化,即以尔朱荣为代表的蛰居在北部的胡系势力向洛阳皇权发出挑战,这个皇权就是孝文帝通过汉化改革塑造起来的[9]165-206。尔朱荣的崛起正是北魏内部南北分裂和对峙导致的结果,尔朱荣若能成气候,势必借此形势为其所用。他除了招收北镇各路兵马、吸纳那些迁都洛阳后被边缘化的原拓跋氏核心集团成员之外,若要继续壮大,就势必将矛头对准洛阳,洛阳的依托对象就成为重要目标,元子攸的出场恰逢其时。
但元子攸的直接对手是幼帝元钊,他的上台不仅意味着掌握朝政的胡太后势力倒台,也是迁都以来宣武、孝明、幼帝等不断强调“体自高祖”而继承的孝文体制合法性的崩塌。元子攸所缺少的外部条件可以由尔朱荣提供,但证明其资质的证据显然不能依托洛阳的那一套,只能通过北魏的旧俗传统获得合法性,铸金人的仪式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选项。它对那些濡染汉风的洛阳权贵似乎无足轻重,但对保留北族传统的尔朱集团成员却有不可忽视的感召力与聚合能量。考虑到铸像仪式的政治涵义在传达中的有效性,以及会师前公开铸像结果对元子攸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此次铸金人的受众必然是尔朱集团内部。重要的是,这套礼仪规范将尔朱荣的举动与旧统契合进而获得合法性,以为其下一步——起兵造反建构自身势力的行为张本。
二、河阴之变前的“祭天”动议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尔朱荣率军南下抵达河内,元子攸秘密潜出洛阳与之汇合,驻守河桥的禁军临阵倒戈,元子攸遂携军渡河并于邙北即位,是为孝庄帝[1]1363。胡太后败势已成,被迫携六宫落发入道[2]505,郑俨、徐纥等太后亲信仓促逃离[1]2175-2177,其他大小官员则前往河桥奉迎孝庄。然而就在这转替之中,发生了史称的“河阴之变”,尔朱集团与部分洛阳禁军联手于河阴之野将胡太后、幼帝及上千王公大臣以“祭天”为借口除掉[1]303-304,1784-1785。据《魏书·尔朱荣传》记载:
十三日,(尔朱)荣惑武卫将军费穆之说,乃引迎驾百官于行宫西北,云欲祭天。[1]1784
《北史·尔朱荣传》的记录是:
(尔朱)荣惑武卫将军费穆之言,谓天下乘机可取。乃谲朝士共为盟誓,将向河阴西北三里,至南北长堤,悉命下马西度,即遣胡骑四面围之。[2]1753
二者对事件虽有“祭天”与“盟誓”之差,但指代的都是西郊祭天仪式(8)有关北魏西郊祭天仪式的研究,参考康乐《国家祭典的改革》,见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稻禾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206页;杨永俊《论北魏的西郊祭天制度》,载于《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杨永俊《论拓跋鲜卑的原始祭天》,载于《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徐迎花《魏晋时期拓跋鲜卑祭天问题》,载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7期;佐川英治《从西郊到圆丘——〈文馆词林·后魏孝文帝祭圆丘大赦诏〉所见孝文帝的祭天礼仪》,载于余欣主编《中古中国研究 第一卷》2017年版,第1-26页;赵永磊《争膺天命:北魏华夏天神祭祀考论》,载于《历史研究》2020年第4期;罗新《拓跋祭天方坛上的木杆》,载于《云冈研究》2021年第2期。。河阴之变是尔朱集团与禁军策划的屠杀[8]319-320,西郊祭天是预谋中的一环。此时正值拓跋魏举行西郊祭天仪式的四月或“孟夏”(9)《魏书》卷108《礼志一》载:“天赐二年夏四月,复祀天于西郊”,同书卷109《乐志》则载:“孟秋祀天西郊……孟夏有事于东庙”,《南齐书》卷57《魏虏传》载:“城西有祠天坛……常以四月四日杀牛马祭祀”。康乐认为《魏书·乐志》混淆了西郊与东庙祭时间,实际上西郊祀天在孟夏。参见魏收《魏书》,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988、3079-3080页;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85页;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台湾稻禾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注。,百官被引至“河阴(今河南孟津县)西北三里”也正处洛阳“西郊”,尔朱荣以此为借口不易引起洛阳百官的警惕,河水与南北长堤行成的特殊地形亦有利于将他们一网打尽。
西郊祭天固然是尔朱荣屠杀王公大臣的借口,但这并不意味着祭典有名无实。事实上,它与拓跋氏从部落联盟走向政权的过程紧密相连。北魏的西郊祭天源于北族中广泛流行的春祭[10],部落联盟时期,臣属各部均可自行祭天,拓跋氏则通过主持部落联盟祭典确立统治地位[9]176-177。公元258年的西郊祭天仪式中,诸部大人通过参与拓跋力微主持的祭典承认其领导者的权威就是一个突出证明[1]3。登国元年(386),道武帝拓跋珪在即代王位的同时进行西郊祭天:“登国元年春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会于牛川。”[1]22(10)《魏书》此处没有明确指出拓跋珪实行的是西郊祭天,但根据《魏书》卷108《礼志一》中“太祖登国元年,即代王位于牛川,西向设祭,吿天成礼”的记载,“西向设祭”即为西郊无疑。它的举行时间不在常规的四月,则可能是当时情况所迫。参考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台湾稻禾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176页正文及注。天兴元年(398),拓跋珪亦举行该仪式:“天兴元年夏四月壬戌,帝祠天于西郊,麾帜有加焉。”[1]36他在这一年还先后主持议定国号、迁都平城、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改元等一系列重要活动[1]36-37。这些都表明西郊祭天仪式是拓跋氏在部落联盟和北魏政权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仪轨,它是拓跋魏君主统治、政权运行的礼仪象征。
拓跋珪建立北魏后,以“散诸部落,同为编民”[1]3274为手段打散与拓跋氏关系密切、势力强大的部落,加强君权(11)关于北魏的“解散部落”政策与“领民酋长制”的研究存在诸多分歧,尤其是学者间对被解散的部落是化为编民抑或只是将大的部落组织打散分居各地,以及部落解散的对象与实行领民酋长制的群体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有不同的理解。部分学者通过对北魏早期官制的研究,强调从前身为酋长的那些人在担任北魏官员的同时,与皇帝之间的关系仍带有部族制属性。但这些被解散部落的前酋长与旧部民之间的联系确实已逐渐断绝,而由领民酋长对部落的统率则一直维持到北魏末年。参见松永雅生《北魏太祖の“離散諸部”》,福岡女子短大纪要1974年第8期。川本芳昭《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问题》,东京汲古書院1998年版,第124-186页。松下憲一《北魏胡族体制論》北海道大学出版会2007年版,第9-27页。。没有完整部落组织为依托的部族无法自行祭祀,只能以内、外朝臣的身份参与由北魏皇帝主持的国家祭典[1]2988。未解散的部落仍保有自行祭天的权力,如文成帝朝五部高车“合聚祭天”时,北魏皇帝便是祭礼的亲临者而非主导者[2]3273,这些首领在北魏国家祭典中则扮演“宾国诸部大人”的边缘角色。在北魏早期的国家祭典中,他们的角色和地位区分相当明确。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废除西郊祭天[1]207,拓跋氏不再主持北族祭典,转而继承华夏正统,尔朱荣等领民酋长则仍可以在本部落内维持该传统。孝文帝改革后的北魏改变了以武力征服中原的统治方式,代价则是统治集团的分化,北部的六镇军人、领民酋长和洛阳的禁军丧失地位。尔朱集团中聚集的这些军人、诸高车杂胡及徙代的汉人强宗有共同的鲜卑化特质[11],与之合作的禁军也有相似的出身背景,他们多“武质”特征,均被排斥于“文华”的北魏上层之外[12]。这个群体是尔朱荣依托的力量,若要在朝政转替之中发展自己的力量,重建西郊祭天正是尔朱荣壮大势力的一个步骤。但尔朱荣的意图只完成了一半,以祭天为饵的河阴之变消除了他的政治对手,但尔朱荣的权威却未通过祭典树立起来,仪式并没有真正践行。
在这场以祭天为名义进行的屠杀行动中,本应主持祭典的孝庄帝不在现场,这应是出自尔朱荣的授意。据《北史·尔朱荣传》记载:
(荣)命二三十人拔刀走行宫,庄帝及彭城王、霸城王俱出帐。荣先遣并州人郭罗察共西部高车叱列杀鬼在帝左右,相与为应。及见事起,假言防卫,抱帝入帐,余人即害彭城、霸城二王。乃令四五十人迁帝于河桥。[2]1753-1754
尔朱荣声称的祭天地点在“行宫西北”,即河阴西北三里的南北长堤,而孝庄帝及左右均被控制在行宫帐内。尔朱荣借西郊祭天发难,将百官公卿除掉,随后命人造禅文、铸像占卜,这与拓跋珪西郊祭天后即代王位、建元、议定国号等举措有微妙的相似。毫无疑问尔朱荣在借机展现他的政治抱负,但仪式的半途而废也源于此。北族旧典于孝文改革后在洛阳逐渐湮没,曾经主导西郊祭天仪式的拓跋氏和诸内外朝臣早已抛弃了这套仪式,谙熟旧俗的诸部酋长身处外围,其政治地位在旧典被废后变得更加边缘化,诸群体对祭典的认同程度与他们原先在其中的地位高低完全逆转。离开代北环境、将参与者从集团内扩大到北魏朝廷整体后,政治、文化的撕裂亦使得西郊祭天难以完全复原,何况尔朱荣还试图在仪式中突出自己的主导地位。
三、尔朱荣自立的“异图”
清除掉政治对手、软禁孝庄帝之后,尔朱荣试图再行铸金人仪式,如《魏书·尔朱荣传》记载:
(尔朱)荣遂有大志,令御史赵元则造禅文,遣数十人迁帝于河桥。至夜四更中,复奉帝南还营幕。帝忧愤无计,乃令人喻旨于荣曰:“帝王迭袭,盛衰无常,既属屯运,四方瓦解。将军仗义而起,前无横陈,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规存性命,帝王重位,岂敢妄希?直是将军见逼,权顺所请耳。今玺运已移,天命有在,宜时即尊号。将军必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任更择亲贤,共相辅戴。”荣既有异图,遂铸金为己像,数四不成。时幽州人刘灵助善卜占,为荣所信,言天时人事必不可尔。荣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悟,遂便愧悔。于是献武王(高欢)、荣外兵参军司马子如等切谏,陈不可之理。荣曰:“愆误若是,惟当以死谢朝廷,今日安危之机,计将何出?”献武王等曰:“未若还奉长乐,以安天下。”于是还奉庄帝。[1]1784
《北史·尔朱荣传》亦云:
(尔朱荣)乃令四五十人迁帝于河桥,沉灵太后及少主于河。时又有朝士百余人后至,仍于堤东被围。遂临以白刃,唱云:“能为禅文者出,当原其命。”时有陇西李神俊、顿丘李谐、太原温子昇并当世辞人,皆在围中,耻是从命,俯伏不应。有御史赵元则者,恐不免死,出作禅文。荣令人诫军士,言元氏既灭,尔朱氏兴,其众咸称万岁。荣遂铸金为己像,数四不成。时荣所信幽州人刘灵助善卜占,言今时人事未可。荣乃曰:“若我作不吉,当迎天穆立之。”灵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长乐王有王兆耳。”荣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遂便愧悔,至四更中,乃迎庄帝,望马首叩头请死。[2]1754
从尔朱荣萌生“异图”、迁孝庄帝于河桥、作禅文、铸金人、考虑另立元天穆为帝,到刘灵助等劝阻、孝庄帝传信、尔朱荣反悔而迎回孝庄帝,事态的反复发生在一日之内,尔朱荣内心的激荡及其政局变幻的眩晕,颇能反映他的欲望与朝政瞬息万变的扭结,终将他的嬗替欲望压制而未得释发。细究起来,可能受到如下因素的制约:
首先,软禁之下的孝庄帝面对危局表现出了他的沉稳机智。他降低姿态,传言尔朱荣声称自己不敢妄希“帝王重位”,强调他与尔朱的结盟关系及“存魏社稷”的必要。考虑到孝庄的安危存于尔朱的一念之间,他的支持势力更因尔朱荣的背叛遭受重创,孝庄帝的传信与其说是威胁,毋宁是绝境下的殊死一搏,这当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其次,尔朱荣于河阴现场下令辞臣“造禅文”,企图通过禅让即位。这种行为自曹魏代汉以来已成为那一时代中原政权更替的惯常方式[13],身为契胡酋帅的尔朱荣如此作为,显然是顺应华夏化的洛阳朝廷之正统性需要,针对的是洛阳公卿。当然这种没有遵循禅让政治流程、通过刀兵胁迫得来的禅位只是尔朱荣一次敷衍的尝试(12)禅让政治需要遵循封国建制、九锡殊礼、揖让虚礼与禅让仪文等完整仪程才具备改朝易代的合法性。参见杨永俊《禅让礼仪——禅让模式的载体》,载于杨永俊《禅让政治研究——王莽禅汉及其心法传替》,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276页。。禅文可作,尔朱荣却并未成功上位,最根本的原因是铸像的失败和部下的反对。铸金人作为北族政治传递合法性的仪式,“唯庄帝独就”的铸像案例是尔朱荣登上权力顶峰前必须跨越的障碍。然而铸像“数四不成”透露的“天时人事未可”,至少揭示出他在正统性上尚有缺失,这种缺失的背后就是“人事”,即集团内部的意见分歧。换言之,尔朱荣的称帝并未获得部属的倾力支持(13)尔朱荣在集团内不乏支持者。史书对诸尔朱氏的反应未予记录,但他们既然积极参与此前的政变、在第一次铸像时表现活跃,便不可能在此时隐形,从尔朱氏的家族利益出发,他们应该都会支持尔朱荣。尔朱荣欲称帝之后还曾“令人诫军士,言元氏既灭,尔朱氏兴,其众咸称万岁”,支持他的还有随从南下的“军士”“其众”,他们是尔朱集团的核心军力,主要由尔朱氏世代统领的部落民组成。参见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54页。。
文献对此记载有差异且相互抵牾,譬如《北史·尔朱荣传》《北齐书·司马子如传》就与《魏书·尔朱荣传》颇为不同,并没有后者述及的高欢、司马子如劝阻尔朱荣称帝一事。《魏书·刘灵助传》也缺乏相关的记录,作为备受尔朱荣信任的方士,刘灵助不仅反对尔朱荣称帝,还驳回了其改立元天穆的提议,直言“唯长乐王有王兆”,他在事件中的重要角色使其本传的失载也引人怀疑。不过刘灵助曾在河阴屠杀中庇护“州里”范阳卢氏及同行者数十人[1]2123,侧面表明他与尔朱荣的立场并非一致。从而从侧面增强了他反对尔朱荣称帝的可能性。另外,《北史·齐神武纪》与《魏书·尔朱荣传》亦有差异,将高欢反对尔朱荣称帝置于铸像之前,并认定是高提出铸像:“(尔朱荣)因将篡位,神武谏恐不听,请铸像卜之,铸不成,乃止。”[2]211但《周书·贺拔岳传》的情况又不相同:
(尔朱)荣既杀害朝士,时齐神武为荣军都督,劝荣称帝,左右多欲同之,荣疑未决。(贺拔)岳乃从容进而言曰:“将军首举义兵,共除奸逆,功勤未立,逆有此谋,可谓速祸,未见其福。”荣寻亦自悟,乃尊立孝庄。岳又劝荣诛齐神武以谢天下。左右咸言:“高欢虽复庸疏,言不思难,今四方尚梗,事藉武臣,请舍之,收其后效。”荣乃止。[14]222
贺拔岳成为力排众议、坚决反对尔朱荣自立为帝的意见领袖。《周书·贺拔岳传》虽未提及尔朱铸像一事,但将高欢描绘成与《魏书·尔朱荣传》《北史·齐神武纪》完全相反的、怂恿尔朱荣称帝的角色,并强调“左右多欲同之”,似乎尔朱集团多数成员都支持称帝。
这种史料的差异至少与此后朝政形势的遽变有关:河阴之变沉杀幼帝、胡太后,除掉元子攸兄弟元劭、元子正,清除百官公卿,这些行为引起的震荡不可能轻易消解。北魏分裂后,对峙双方与尔朱集团关系密切,且牵涉河阴之变等事件颇深,东、西两政权各自尊奉自己的元氏皇帝,都想争夺国统以彰显自身的合法[15]。在此情形之下,他们与尔朱氏的关系,要么自我标榜而特立独行,要么攻讦对手而斥责僭伪,譬如宇文泰在讨伐高欢的檄文中指责他“劝尔朱荣行兹篡逆”就是一个典型[14]10。高欢、贺拔岳自然被各自的国史编纂者塑造成阻止尔朱荣称帝的功臣,渲染对手在河阴屠杀和尔朱荣为帝等事件中扮演的帮凶角色。如《北史·尔朱荣传》就删去了《魏书》同传中高欢、司马子如劝阻尔朱称帝的内容。但无论这些史料如何分歧,尔朱荣自立为帝一事并不为其属下所支持,这一点是非常分明的。
尔朱荣两次铸像,急需统合集团意见,尤其渴望获取新附六镇人众的支持。那些曾支持尔朱荣南下、拥立元子攸为帝的部属,对他的第二次铸像非但不积极,反而表露出抗衡的心态,暴露出尔朱集团聚合中潜藏的矛盾。这应由集团构建中诸多复杂的因素所致。按尔朱荣原有“部落八千余”[4]13,后又“散畜牧,招合义勇”[1]1781,试图将游牧组织改造为军事化集团,但部落的形态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入洛时其核心军力仍是契胡部落兵[16]。六镇乱后至南下洛阳间,尔朱势力主要向平城以南并、肆、汾诸州扩张,有如《魏书·尔朱荣传》所云:
秀容内附胡民乞扶莫于破郡,杀太守;南秀容牧子万子乞真反叛,杀太仆卿陆延;并州牧子素和婆崘崄作逆。荣并前后讨平之……内附叛胡乞、步落坚胡刘阿如等作乱瓜肆,敕勒北列步若反于沃阳,荣并灭之……敕勒斛律洛阳作逆桑乾西,与费也头牧子迭相掎角,荣率骑破洛阳于深井,逐牧子于河西。[1]1781
尔朱荣正是通过平叛而吞并与其组织形态、生活相类那些杂胡部族(14)有关北魏末的山胡敕勒反叛及其族属、社会形态问题,参见唐长孺《北魏末期的山胡敕勒起义》,载于唐长孺《山居存稿》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8-81页;唐长孺《魏晋杂胡考》,载于《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25-430页。,六镇人众投靠其麾下的也不少,过程亦波折起伏。如正光五年(524)六镇之乱爆发后,部分镇民及周边人群避乱南下转投尔朱荣;孝昌元年(525),河北出现暴动,人群再次涌入并、肆[17]。大量涌入的镇民与尔朱集团原有的契胡部落以及诸胡部族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六镇多“乡里”,虽有诸如高车等降附部群和一定的部落传统,但其支柱是贺拔胜、宇文肱这些“州里豪杰”。镇民在饥荒、战乱和迁徙的磨难下,与“豪杰”结成密切关系,形成了凝聚性很强的团体,投靠尔朱荣成为其属下军府机构的成员(15)有关北魏末“州里豪杰”的组成和性质,部分学者认为其与中原的“乡里”社会相似,镇民集结在“豪杰”身边,形成有较强自主性的团体。参考直江直子《北朝後期政權爲政者グループの出身について》,载于名古屋大學東洋史研究報告(5),1978;直江直子《北魏の鎮人》,载于《史学雜誌》1983年第2期;谷川道雄《武川镇社会与武川镇军阀》,载于谷川道雄著、李济沧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84-291页;薛海波《北魏后期六镇豪帅的社会地位》,载于薛海波《5-6世纪北边六镇豪强酋帅社会地位演变研究》,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29-77页。川本芳昭则强调六镇内部存在部族性的联结关系,参考川本芳昭《六鎮「乡里」社会》,载于川本芳昭《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东京汲古書院,1998年版第173-178页。。
尔朱荣曾任北道都督,担负恒、朔讨虏诸军使职,旋又都督并、肆、汾、广、恒、云六州诸军事。肆、恒交接的马邑要塞是尔朱荣势力范围北端[1]1781-1782,他担任“恒、朔讨虏”“都督恒、云”等职位纯系朝廷恒、朔失守后整编六镇流民之需要,他的军府在朝廷直属军队溃败之后就成为招徕六镇军人的重要平台,势力迅疾扩张。六镇成员步入尔朱军府后多任僚属、军将,但他们似乎仍旧具有自身的独立特性,时间的短促,亦未给予尔朱荣以充分的整合空间。他对待那些降众的基本办法,就是选择六镇豪杰为心腹,“私使统焉,若有犯者,罪其帅,则所罪者寡”[2]213,避免与镇民直接沟通;同时借用这些豪杰的影响力扩大战果,如与葛荣对战时,尔朱荣令高欢招降葛荣旗下“别帅称王者”,万余人立时倒向尔朱军[1]307-308。总之,以权宜计,尔朱荣尽可能地维持其原有镇民组织,借以稳固自己的统辖秩序。
入洛后,尔朱荣又面临新的形势尤其外部的挑战。掌握北魏朝政的百官公卿并不会因尔朱荣兵力雄壮和拥立元子攸之功就理所当然地归顺于他,尔朱荣恢复北魏早期的西郊祭天仪式、限制元子攸以窃居主位的图谋亦无法顺利运行。那些躲避战乱投入其帐下谋求前程的六镇民众,固然有“翼戴之勋”,但他们获取的好处仍旧有限,远不及尔朱近臣,这些人忠奉于尔朱荣是否超过孝庄帝还很难说。事实上,六镇人众并非第一次尝试拥立元魏宗室为帝,此前广阳王元渊之死便与此相关[18]。可见这一群体有独立伸张政治目标的立场,其尝试甚至早于尔朱荣。这一切都表明,尔朱荣在那个紧迫的时代凝聚自身势力、形成所属集团,却并没有来得及完善处置,历史也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妥善安排。事实上,这个集团汇聚的人群来路复杂,利害相争,远非精诚团结,这种情况下尔朱荣奔向权力的每一步举措,都面临属下的不同姿态,单纯复制“铸金人”仪式并不能将内部协调完备,此时问鼎皇权之功败垂成,也就势属必然了。
四、余论
尔朱荣势力的崛起,无疑是附随六镇叛乱的一个结果;六镇起兵又是针对洛阳朝廷而来,孝文帝的转型最终导致王朝内部南北的撕裂而引起了北部的震荡。但这也不能将这一系列行为简单地一股脑归咎于孝文帝的举措。可以说,正是孝文帝的转型,才将拓跋政权置身于更加广阔的空间并得以拓展,这也是周边势力入主中原采取治理的一般通则。问题的关键是怎么调整、调整到什么程度,如何处理转型带来的诸多问题和麻烦。北魏的转型不可谓不成功,但即使如此,它也并未能阻挡由此导致的政权解体。在此过程中,尔朱荣的“反弹”举措,又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解释呢?
尔朱荣之起家蒙惠于六镇的造反,他所吸纳的必然是这些势力。为了强化自身,招兵买马、从者俱纳就成为制胜的法宝,但这也带来相应的问题,即部从鱼目混珠,难有齐整的配置。这些乌合之众一旦聚集在尔朱荣属下,就按照他的意志奔向洛阳。尔朱荣“异图”的目标不可谓不明确,但他采取的手段却颇为曲折,前文述及的“铸金人”“西郊祭天”之所以被他采纳,就是为迎合北族的政治动向,借以寻求他举措和行为的合法。遗憾的是,这些照搬“代都旧制”的行为未能有效地发挥整合作用,尔朱荣无法简单地通过复制拓跋氏确立主导地位的方式取代拓跋氏。尔朱集团仓促崛起后进军洛阳,辅助新君发动了“河阴之变”,这虽使朝廷百官遭受重创,但未能为尔朱荣自己的“问鼎”带来相应的便利;更重要的是,他的行为尚未成为跟从他的属下的广泛共识。
尔朱荣最终还是失败了,但他恢复北族传统的做法为后来者提供了思路。高欢在立元脩为帝时,“用代都旧制,以黑毡蒙七人,欢居其一”[2]170,宇文泰整合关陇集团时以诸将比附鲜卑旧姓[14]36,他们转而青睐那些未在北魏前期制度建设中被固定化、甚至无法考证来源的北族传统,以获取灵活施用的空间。高欢、宇文泰这些继之而起的势力最终造成北魏东西对峙,整体王朝不复存在。这虽顺遂尔朱荣轮替的意念,但并非由他而完成;尔朱荣个人的仕途虽然完结,但北魏覆亡的趋势表明它潜存的南北对抗性矛盾难以弥合、终究再度调整化解,这个化解衍变成为继起的东西魏及随后的北齐北周的对抗和博弈。就此而言,尔朱荣之兴亡,应属北魏后期朝廷政治转轨中矛盾化解的一个步骤,他的失败在于仓促崛起、整合未逮的用力过猛,但其呈现的北魏政治重新洗牌的势头并没有中断,他无疑为继起者提供了进一步施展的空间,高欢、宇文泰及其跟随者就是据此而释放他们的政治抱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