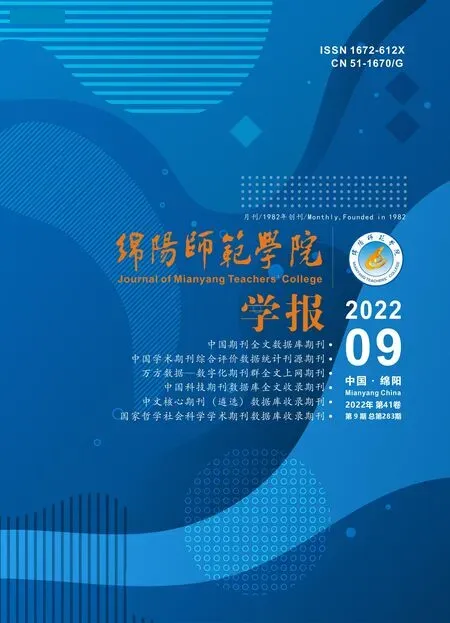儒家生活美学之“本真”生存论
2022-11-21李天道魏春艳
李天道,魏春艳
(四川师范大学,四川成都 610068)
一、引言
儒家生活美学认为,“为仁由己”,“求仁得仁”,“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人”之生活应当努力追求“仁性化”“本真化”与“诗意化”“审美化”,通过“为仁”“求仁”“安仁”“乐仁”以保持生活的本真,由此“成人”“做人”。儒家生活美学认为,真正的本真化、审美化的生活,是真、善、美的理性和感性都自然而然、中庸和谐,“本于仁”“据于仁”“依于仁”“发乎情,止乎集体生活、社会生活”的“乐仁”的生活。这里所谓的“乐”是“乐生”,“乐仁”是“诗意栖居”和“本真化生存”的表征,是“乐乐”,即以愉悦的生活态度来维系“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包括“人”与自我的关系,把生活的审美意义、审美化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作为探讨的重要问题。
在生活的本真化、生活的审美价值以及生活审美理想与生活审美境域问题上,孔子把“人”与生活一体化,从“人”之“生”与生活的合一进行思考,指出:“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1]184天地万物之中,“人”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所谓“斯人之徒”指的就是处于生活中、超越了自然状态而文明化的人。生活中的“人”乃是天地之间最为尊贵的、最有价值的,故而孔子强调指出:“天地之性,人为贵。”[2]2553人是生活的参与者和创造者,殷周的礼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之生活的一种体现。正是由此出发,所以孔子满怀敬意地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65可以说,“从周”,实际上就是孔子对人以及人之生活审美意义的确认。因此,应该说,儒家生活美学之审美观源于“重人事”“轻天命”与“贵人”“重人”“好生”“尚生”的生活旨趣和审美指向,以及“本于仁”“依于仁”“归于仁”,以“仁爱生生”为核心的生活审美态度。儒家生活美学所推崇的“颜子之乐”“曾点之乐”“以和为美”“求仁得仁”“里仁为美”等意趣,其实质就是“人”之生活本真化、诗意化态度的鲜活呈现。儒家标举“仁者安仁”,所推崇的“乐于仁”“安于仁”之“仁者”生活方式归于“天人合一”的“仁”,“仁者”“求仁”“安仁”“尚仁”“乐仁”。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1]367《中庸》云:“仁者,人也。”[1]28“仁者,人也”也就是“人者,仁也”。“仁”之生活审美域乃是“人”之为人的本真规定性,达成“仁”之生活审美域,才称得上本真意义上的“人”。同时,有关“人”之生活审美诉求又表现为“循天道,尚人文”“致中和,得其分”,即如《中庸》所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达道。”[1]18“中和”是致使生活美好的路径和保障,也是生活美好的诗意化语境和达成生活美好的重要维度。因此,儒家生活美学主张“崇礼乐”,以“赞化育”。所谓“崇礼乐”,就是通过“礼乐”活动,以增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和谐,美化生活。
二、以“仁”为美的生活审美态度
据此,儒家生活美学倡导“允执厥中”“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乐而不淫”“以‘仁’为美”的生活审美态度与审美诉求。显然,这些生活美学的审美态度与诉求对成就“人”的生活美好,和谐人的生活,具有极为重要的效用。并且,这种审美规范突出地表现在“人”之生活方式与本真化、诗意化生活方式问题上。受此审美观念的影响,儒家生活美学崇尚“中和之美”,为达成“人”之审美化、本真化、诗意化生活,主张生活简朴,人之生活以素朴为美,生活的极致,或者说生活的本真化就是素雅与质朴,“天然去雕饰”,崇俭抑奢的简单生活,可以缓解压力,即如《周易》所指出的:“天地节而四时成。”[3]70孔颖达疏云:“天地以气序为节,使寒暑往来,各以其序,则四时功成之也。”[3]70就字面意义讲,“节”,其意为季节、调节、节奏、节省、节制、节气,天地有所节度,由此形成一年四季。换言之,天地时空节之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引申到日常生活,则在生活技巧方面,以务实为主,简约、朴实,反对奢华和浪费,过日子勤俭节约,节省用度,保持身心安康、心灵平静、神清气爽。由此出发,“人”应该“修己”“克己”“安仁”“守仁”,与自己和解,同时,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立其诚不妥协,不委曲求全。简单、简易、单纯地生活,不强求,不强取,顺其自然,该来的总会来,该要的自然要,该走的也留不住。诗意化、审美化的生活是简朴平静的,也是本真化的。所谓真理粗朴,大道至简,大象无形,大美简朴,唯有至简,方能够达成至丰,犹如至柔才能够至刚。如此,至简的生活,也就是一种至真、至善、至美的生活,美好的生活。
基于此,儒家生活美学将关注的重心移向现实日常生活,将目光从外界投向“人”自身,个人的生活也摆脱了政治和功利的目的,注重“人”的品貌、才情、言谈、风度、识鉴、智慧、个性,主张对物质生活条件不必强求,不必贪奢,不必过于计较,即使生活艰难,“一箪食,一瓢饮”,困顿,“在陋巷”,也不气馁,而应该保持健康的心态,自强不息,对生活充满希望,“不改其乐”,热爱生活超越趋利避害的本性,发愤图强。这是一种达观的生活态度,也是儒家生活美学所推崇的一种审美域。在这里,诗意化、审美化生活中,不仅是人与社会的和谐、人天的和谐,即人与自然的和谐,更是人我的和谐,也就是人与自身肉体的和谐。这种和谐触及灵魂,乃是身心、心灵的和谐,故而“无往而非乐”,生活中的一切都会给人带来快乐。这就是儒家生活美学所推崇的审美化生活方式。在这种审美化生活中,“各遂其性”,“人”能够“随心所欲”“各得其所”,以达成“尽善尽美”之心性本真化审美域。
正是本着这种生活审美意念,儒家生活美学极力推崇“曾点之乐”似的诗意化生活方式,认为这种生活方式与生活审美态度能够给人以启迪。曾点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在一次有关生活理想与审美志向的讨论中,曾点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1]130显然,这里就主张一种安居乐业、悠闲自在的生活。当然,这种生活的背景是世道安定、邻里和谐;生活和平安定,不施妄为,随顺世事,顺其自然;心境纯真素朴、淡然超越,让人直接感受到一种纯真淳朴、恬淡超然。故而深受孔子赞许,感叹云:“吾与点也!”[1]130说自己的生活审美理想和曾点的一样,表达出对“曾点之乐”审美旨趣的憧憬。到宋代,理学家二程特别推重“曾点之乐”,将其提升到“尧舜气象”的审美境域:“孔子与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4]846曾点这种乐得其所,正是孔子所向往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1]82的社会安宁、民众生活平和、万物各遂其性的生活理想,因此受到孔子的赞赏。在二程看来,孔子之所以赞同曾点,是因为其知道圣人之志在天下太平、人人安居乐业、各得其所。故而,将“曾点之乐”提升到“尧舜气象”的审美境域。朱熹也对曾点“乐得其所”的生活意趣加以赞赏,说:“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个体生活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1]130朱熹认为曾点所推崇的“乐”乃是“天理”的一种生动呈现,是“天理流行”[5]8,表现在日用生活之中,则呈现出“天理流行”的妙处,体现出来的,是人对自身美好生活怡然自乐;是乐道知时,是万物竞荣、各遂其性。生活之美正体现于这样的日用常行之内,体现在寻常生活之中,“人”之生活审美态则是自得其乐、从容洒脱,随处发见天理,天理处处皆是,所以说是万物遂性、各得其所之“尧舜气象”的生动呈现。当然,要达成这种生活审美域,必须“本于仁”“依于仁”,克去人的私欲,从而才能使天理在万事万物上得以充分体现。惟其能够突破私欲、超越自我,才能包容天下所有人和所有物,推己及人,使万物的天赋本性得到充分的发展,达到万物并育而不害的生活审美境域。朱熹认为,孔子之所以赞赏曾点的生活审美意趣,表示对此的向往与推崇,赞美“曾点之乐”,是因为曾点这种“乐”的审美指向乃是“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1]130。
三、“万物各遂其性”的生活审美境域
应该说,所谓“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也就是“与天地同和”。这种境域富有生活气息,实质上就是审美化、诗意化生活场景,既是儒家生活美学所推崇的最高的生活审美域,也是生活的本真域或审美域,艺术和道德在生活审美域的极致上得到了统一。“曾点之乐”所体现的儒家审美态度是洒脱自在、各遂其性、各称其心、各满其意、各得其所、自其所自、在其所在。这种生活态度,也即一种审美态度,也就是儒家生活美学所推重的“尧舜气象”的生动呈现。当然,要达成这种生活审美域,必须克去人的世俗杂念,超越私心妄想,彻悟因杂念而迷失了的原初本心、本性,去蔽存真,归复仁心仁性,使天理澄明,在寻常生活的所欲所见中得以敞亮。
所谓“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日常生活中的“吃不吃”“谁吃”“吃啥”,包括所有饮食男女方面的内容与主要元素,诸如“饮食、衣服、事为、异别、度、量、数、制”[6]552,日常生活的情境式规范、饮酒食肉的规范、饮食内容、食品制作、宴饮席位、饮食器具,包括进食次序、进食细节等涉及餐桌艺术方面的内容,以及日常生活中人际交往的秩序、等级贵贱等种种生活之道都是“人之大欲”,皆“同于天”。所谓“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既然“以食为天”,寻常生活也就是“天”,“乐其日用之常”,即切入日常生活,达成“人天合一”“浑然与万物同体”。故而,儒家生活美学主张,“人”与日常生活中“乐生”“乐在”“即景生情”“寓目辄乐”“胸次悠然”,如此,则可达成本真之生活审美域,“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乐其日用之常”,则要求“人”于日常生活中“端祥闲泰”、心态平和,“俯仰自得,心安体舒”,以进入“鸢飞鱼跃”“浑然天成”之理想诗意化生活审美域。达成此种审美域,“人”之“心性”透彻,“天理”“天道”具体而真实地澄明与展开。由此,儒家生活美学要求“人”默识心通、反躬践履、静存动察,体认“天道”与“人”之“仁心仁性”,进而回归“仁心仁性”,以达成“天人一理”“万物一体”“性与天通”的生活审美境域。万物流行不息,“人”之“心性”显发须虚明心体,拋却私欲障,摒弃有为之心,纯任“天理”“天道”“天命”“天性”之自然显现流行,使身心与“天理”相互融通、一体合一、无间无隔,致使生活审美境域无限提升与超越,实现“曾点之志”“孔颜乐处”,达“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一体”的生活审美境域,领悟到“心通”“自得”之妙境“乐”,透悟见性。因此,朱熹认为,“孔子之志,在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曾点知之,故孔子喟然而叹曰:“吾与点也。”也就是说,“曾点之志”即“孔子之志”,“曾点之乐”即“孔子之乐”,二者相通相契。虽然曾子所描述的是“个体生活尽处”,人心纯乎“天理流行”的湛然纯粹之生活审美境域,这种生活审美境域使“万物莫不遂其性”,超然纯粹、顺适自在、天道流行,是“人”所能够达到和应当追求的生活审美境域。在这种本真化审美域中,天地上下同流不息,飞潜动植,万物各得其所,“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缺,太极、阴阳、五行、万物流行,各乐其所,洒脱超然,顺适自在,大道流行不息,左右逢源,身心所发,纯为“天理之自然”,无纤毫滞碍。行役羁旅,江山花村,怡情悦性,高蹈世外之致,“孔颜乐处”。故而,儒家生活美学主张“人”应该“正心养性”,日用常行,进退出处,都应当切己身心、形逸神闲、乐处知足、精神充实、情性舒畅,应当有体有礼、谦退安静、涵容洒脱,应当安详稳重、谦虚退让、涵养宽容、潇洒超脱,致使“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真正合一,内心深处自然而然,本心自然呈露,无一毫之私伪,纯是本真流露。因此,“曾点之乐”又被称为“泰然之乐”“圣人气象”“虚明广大气象”“平旦虚明气象”“凤凰翔于千仞之气象”。由于孔颜所乐者是在对“天命之性”与“天理”全尽与呈露中所得之乐,因此只有“尽颜子之学”,即在变化气质、切己践履、复性体道、全尽天理的实践中方能真切体证“孔颜乐处”。
因此,程明道有一首诗历来为古人所称道。诗云:“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7]156闲暇生活,从容淡定的心境中,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理”之呈现,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显得自在自得、闲适清静、从容不迫;睡醒起来,太阳已照进向东的窗户。“天下万物皆可以理照”,“万物皆备于我,不独人尔,万物皆然”[7]157。静观万物,有所体会,都是得自于心。“曾点之乐”的“乐”,是指“天人合一”的情感体验,是一种具有审美愉悦感的超越体验。这种体验指向生活,以生活为本,以“乐”为本真化审美域,是“人”与自然、“人”与生活的高度合一、和谐一体,是自我生命的生活化。生活世界花开花落、风云变幻,都能够与“人”之生命共感,“人”因感物而动,物我交融,吟风弄月,“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
四、本真化、诗意化生活态度与心灵的升华
儒家生活美学所推重的充满审美趣味的诗意化生活,其审美实质指向生活,在于通过“静观”以“自得”“自乐”,在一种生活诗意化的超越体验中,贴近生活,进入生活,感受与领会到人与生活一如、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达成“入于神而自然,不思自得,不勉而中”[7]482之“化”审美域。在这种审美域中,“人”之精神生命自由自在、胸襟开朗、心怀宽阔、气象宏伟、气度飘逸、性格洒落、超然物外,融天地人为一体。在这里,人的心灵获得飞升,精神得到升华,与道合而为一,人能真正地“从心所欲”,以进入诗意化、审美化生活之境域。这种诗意化生活追求是以“人”之生活方式与本真化生活态度的探讨为其确立审美意识体系的要旨,是以人学为其理论基础的,重视“人”之生活问题,建立了“人”之生活美学,从“生活”的意义上解释“人”之生活方式,认为“人”之生活,是自然生命与精神生命的结合体,“和”之本真化审美域就是“人”之生活应该持有的生活方式或生活状态。并且,从重视“人”之生活方式出发,热爱社会与自然,无论是“孔颜之乐”“颜子之乐”,还是“曾点之学”“曾点气象”“曾点之乐”,都表现出一种切入生活、仁爱生活、珍惜生活、体验生活、体味生活、美化生活、本真化生活的审美意趣,其本真化、诗意化生活态度则是心灵的升华,追求生活之审美化。
在“人”之审美生活方式与本真化、诗意化生活态度问题上,儒家生活美学所推重与标举的是“上下与天地同流”“随心所欲”“随遇而安”“从心所欲不逾矩”“天人合一”,与天地万物一如、即兴即乐的生活方式与自在自由的审美态度。在此生活审美域,“人”所怀抱的是真善美合一的心胸,所持有的是完善全美、美美与共的天地襟怀,其生活境况则是这种心胸与胸怀在生活中生动鲜活的再现。处于这种生活审美境域中的“人”,归依天地,随顺人我,心有所归依、有所随顺。“天人地”三才合一,“人”生而与“天地”不可分离、不可相违,“天地之道”生生不已,顺于“天地”生生不息之道,立地有根,从而才行有所成,自足圆满;依顺“天地人一体之仁”,人性与天地之性互通、感通为一,以得生活之大圆满,生命之圆满;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刚健中正,顺乎天命,要有敬畏之心、崇高之志。以生生为本,知所取舍,与道合真,诚心向道,以道为归,达于上下与天地合流,万物与我为一之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立大人之志,尊道贵德,乐仁好义,知所归依,德配其位,奋而有为,必然有成。尽人合天,以身合道,思天道如风之流行,随风而动,顺道而行,合于天命,行事有成,达成“天地人”和谐一体之本真生活审美域。尽物之性、尽人之性,从而赞助天地万物,使万物生生不息,实现天地人和谐发展、美美与共。如孟子更是认为人性乃是人心的本来属性,生活的最高追求,就是要回复本心,使人性与天性合一,从而达到“上下与天地合流”,而万物皆备于我的自由真善美合一、愉悦舒畅的“人”之审美生活方式与本真化、诗意化生活态度。必须指出,儒家生活美学这种对自由愉悦的审美艺术化、诗意化生活态度的追求还突出地表现在孔子“乐以忘忧”的“人”之审美生活方式与本真化、诗意化生活态度追求上。
就审美倾向来看,儒家生活美学推崇的“人”之生活审美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几句话,其意涵涉及人文生态方面的内容。据《论语·子路》篇记载,孔子曾经说过:“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1]144显然,这里所表达的意蕴,为孔子自己的生活审美意向与理想之所在。所谓“期月”,意指一周年。这也就是说,孔子表白,自己的生活审美抱负倾向于社会人文生态方面的治国理政,是以维护社会人文生态为旨趣的,如果有当权者起用他,他会先轻徭薄役,使民以时而富之,生活平和安康,日子过得富有,人人安居乐业,一年就会有起色,三年则强盛可待!必定达成国家富足、生活兴旺、发达兴盛、丰饶富裕、充足优裕。这以后再加以礼节教化、导化万民,使国泰民安。然而,他所渴求的这种“人”之审美生活方式的获得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儒家生活美学以生活的审美化、诗意化为审美旨趣,祈求风调雨顺,岁岁丰衣足食,生活闲和,安康严静,寻常生活闲适自在,融乐自然山水,陶冶情志,逍遥自得,忘世自乐,寓意生活,跨越世俗杂念的藩篱,超越个体人生有限的时空,在无穷的宇宙境遇中任心遨游,自由飞翔,生活自由、审美化,以达成至乐的生活。追求精神的自由、心灵的逍遥,人与人之间和谐安乐、自由自觉,自我生命与实际生活合一,从中获得一种美感体验。
五、“仁”之生活审美域乃人之心性需求
儒家生活美学认为,“人”应该“克己”“克身”,不应该贪图物质享受,而应该安贫乐道,追求“仁”之本真生活审美域的达成。所谓“为仁由己”“求仁得仁”,“为仁”“求仁”是“人”之为人的本心和本性需求,是“人”之审美化生活与诗意化生命时空的终极依据。或者说,“仁”之生活审美域是“人”之生命与诗意化生活的审美意义所在,是“人”之自我身份的认同与确立和人之为人的规定性意涵。“为仁由己”,需要“克己”,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个体生活的彻底消解,不是说个体生活与集体生活发生冲突,就必须单纯地压抑个体的物欲而迎合集体生活。这是对“为仁”“求仁”的误读。应该说,“为仁”“求仁”意味着个体生活的提升、升华,是本心、本性臻于澄澈境域时的心灵升华,是天地人的一体合一,是顺于生生,是“求仁得仁”之“仁”生活审美域的达成。在此审美域,“人”顺乎天命,生其所生,活其所活,与道合真,如其所生,如其所活,上下与天地合流,“依于仁”,乐仁好义,尽人合天,天性、人性互通,以得生活之大圆满,与天地合其德,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人和谐发展,达成“保合大和”之审美域。
故而,“天人合一”“与天地参”“保合大和”之审美域也就是“求仁得仁”生活审美域。只有尽物之性、尽人之性才能达成“得仁”生活审美域,从而以仁心、仁性赞助天地万物,使万物生生不息,实现“天地人”美美与共、和谐发展。“得仁”“安仁”生活审美域的达成是人道顺应天道,“效天法地”,天之法则与人之准则一如。“人”自身德性修养、践履而上契天道,“上下与天地合流”,“与天地合其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在这样的基础上,“仁”之本真生活审美域就呈现为通过道德的涵养而达到的超越的人生境域和天地境域。所谓“随顺皆应,使虽有喜怒哀乐,而其根皆忘”,“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得仁”“安仁”本真生活审美域的感受。达成“得仁”“安仁”本真生活审美域就把人的世俗杂念洗涤殆尽。所以“孔颜乐处”之所谓“乐”的生活并非“贫困潦倒”,而是一种审美意义上“得仁”“安仁”似的超越及其所获得的审美乐感。所谓“一箪食,一瓢饮”,住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之“乐”,用周敦颐的解释来说,“颜子”之所以“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乃是因为“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8]490。这就是说,“贫”是“淫奢”的一种反面体现。“孔颜乐处”之所“乐”的是“天地间”之“至贵至富”的生活,与一般所谓的富贵贫贱等属于物欲的生活不一样,一旦能够体味到这种“天地间”之“至贵至富”的生活乐趣,则会致使自我的心性得到升华、心灵受到净化,从而达成宠辱不惊的生活审美域,于此审美域,则会以平常之心看待生活际遇,视金钱如粪土,视名利荣耀如镜花水月,由此而凸显生活之本真化、审美化。据此,周敦颐接着加以解释云:“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8]491“心泰”,即内心泰然欣然,处之怡然。所谓“处之一”,就是以“一”处之。此“一”乃“天地如一”之“一”,是“道通为一”之“一”。因此,“处之一”,就是看待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包括“人”自身所遭际的一切,都给以平常心,一天人,齐万物,化富贵贫贱如一,超越物质利益的局限,胸中洒落,以达成一种光风霁月般的生活审美境域,与天地万物之生生精神上下同流、浑然一体。显然,这种“处之一”之“乐”就是“孔颜乐处”之“乐”。这种“乐”是在“人”之日常生活中以平常心自然而然地获得的,是达成“得仁”“安仁”本真生活审美域中获得的。
“仁”的呈现要发自“本心”,然后才可以“无适不然”,“利仁”“安仁”“乐仁”。“仁”审美域的达成是“无所为而为之”,是自然而然,不勉强,不强自为之,是发自本心、本性的“求仁”“欲仁”“乐仁”,表现为自然而然的审美态。“仁”者“安仁”强调的是“人”之感情自然流溢。儒家生活美学认为,“求仁”“乐仁”“安仁”是真善美的一体化,是理性和感性都自然而然地呈现。其情感色彩是中庸和谐,是“发乎情,止乎集体生活、社会生活”的“乐仁”的生活。这里所谓的“乐仁”是“乐生”“乐山”“乐水”“乐时”“乐事”,是“诗意栖居”,是“乐乐”,即以愉悦的生活态度来维系“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实际上是指一种与自然合一所达到的生活诗意化体验。因此,儒家生活美学之诗意源于“重人事”“轻天命”“贵人”“重人”“好生”“尚生”的人生旨趣和生活美学指向,以及以“仁爱生生”为核心的“生活诗意化态度”。儒家生活美学所推崇的“颜子之乐”“曾点之乐”“以和为美”“里仁为美”的实质就是“人”之生活的本真化、审美化态度。儒家标举“中和之美”,所推崇的“人”之生活方式归于“天人合一”的“和”“仁”“好生”“尚生”之生活审美境域。同时,有关“人”之生活审美化诉求又表现为“循天道,尚人文”“致中和,得其分”以及“崇礼乐”“赞化育”“参天地”。
六、“人”之生活方式与审美化生活态度
儒家生活美学主张对物质生活条件不必强求,不必贪奢,不必过于计较,推崇“曾点之乐”似的诗意化生活方式。“曾点之乐”是以“人”之生活方式与诗意化生活态度的探讨为其确立审美意识的要旨,重视“人”之生活问题,是“人”之生活应该持有的生活方式或生活态度,以生活之本真化、审美化为审美诉求。在“人”之诗意化生活方式与本真化、审美化生活态度问题上,儒家生活美学主张“求仁”“得仁”“安仁”“乐仁”“乐以忘忧”。这就是说,孔子表白自己的治国理政之策,如果有人起用他,他会先轻徭薄役、使民以时而富之,而后制为礼节、导化万民以教之,一年就会有起色,三年则强盛可待!然而,他所渴求的是国泰民安、生态和谐。所谓“乐”,快乐、悦乐。就生活美学而言,“乐仁”“乐以忘忧”之“乐”,建立在由生活中得来的感官与精神一体、快感与美感一如、肉体与心灵合一的诗意感受与生命体验之上。“君子”之“乐仁”,是“道”“欲”一体和合之“乐”。“曾点之乐”的“乐”之意涵与此相同。同时,儒家生活美学还标举“颜子之乐”的审美域。“颜子之乐”又称之为“孔颜乐处”。孔子、颜子、曾子都是儒家生活美学的践行者,通过本真化、审美化的生活态度超越现实生活的局限而达到的诗意化与诗意化之本真审美域。“曾点之乐”,体现出儒家生活美学寓无限于有限的心灵超越,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得到诗意和诗意化的升华。“曾点之乐”,蕴藉着人在日常生活中得到诗意和审美化的升华与暂时疏离社会关系的诗意化取向。这种诗意化、审美化期待的核心旨趣,则在于把日常生活看成一个充满情感的场域。于此审美场域中,天地生命之“美”与人的仁心、仁性相通相融、一体与共、完美融合,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心物与情景协调一致。“曾点之乐”也体现了儒家生活美学快乐的生活态度。这里的“乐”,是“乐天”“乐生”“乐活”“乐仁”。“乐生”“乐仁”,来自诗意化、审美化中获得的心性涵养。孔子曾经赞扬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1]87这里所谓的“回”,即颜回,乃七十二贤之首。颜回生活简朴、安贫乐道、与世无争、乐道安命,安于贫穷的生活环境,以坚持自己的信念为乐,尽管居住在陋巷,却自得其乐。其生活的清贫、艰苦是一般人不能忍受的,足见其品质的高尚,与由满足欲望而得来的世俗快乐截然不同。生活诗意化之乐,为本心、本性的“仁”,才能“乐处”,不受物质的束缚,进入自由的生活诗意化之境,这样的生活诗意化审美域也就是“颜子之乐”和“曾点之乐”的“乐仁”之生活审美域。
故而,《论语·卫灵公》云:“君子忧道不忧贫。”[1]167“忧道”之“忧”,意指“人”之精神与心灵方面的活动,具有形而上之思的意蕴。孔子曾经说过,本真化、审美化的生活,是“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在他看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所谓“知之”“好之”“乐之”的“之”,也就是指儒家生活美学所标举的“道”,即本真化、审美化生活的奥秘与生命的真谛。孔子认为,一个人仅仅“知”“道”、“好”“道”,晓得“道”的可贵,是不够的,还只是较低的、一般的生活层次,必须进一步升华,上升到“乐之”的程度。“乐之”,即“乐道”,以“生活之道”为“乐”,把玩“道”,体悟“道”,以“达道”“悟道”“得道”“以道为乐”“与道合一”为生活的审美乐趣。
“道”就是“仁”。本真化、审美化生活态度与诗意化境域就是“求仁得仁”“安仁”“乐仁”,就是“颜子之乐”“曾点之乐”。在儒家生活美学看来,达到这种诗意化生活境域,则为“君子”,因此,“颜子之乐”“曾点之乐”又被称为“君子之乐”。要使生活本真化、审美化,确立了生活之路,进入到诗意化的生活流程,内心平淡明静,以达成生活方式的本真化、审美化、诗意化。可见,“颜子之乐”所推崇的不仅是一种“人”之诗意化生活方式与本真化、审美化生活态度,而且是一种极高的诗意化、本真化、审美化生活态度,是通过审美化、诗意化的生活态度超越人生局限而达到的本真审美域。“曾点之乐”,蕴藉着人在日常生活中得到诗意和本真的升华、暂时疏离社会关系的审美取向。天地生命之“美”与人的仁心、仁性相通相融、一体与共、完美融合。“孔颜乐处”“曾点之乐”体现了儒家生活美学快乐的生活态度。这里的“乐仁”,安贫乐道,坦荡无忧,精神与心灵至大至广、至真至乐。“君子”发现了人心的本来面目,即作为本心、本性的“仁”。这里的“仁”,不完全等同于世俗理解的为善助人之意,孔子曾在《论语·里仁》篇中明确指出:“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1]69只有仁者,才能“贫而乐,富而好礼”,“乐以忘忧”,不受物质的束缚,进入本真化的生活审美之境,这样的生活审美域也就是“颜子之乐”和“曾点之乐”的“乐仁”之审美域。
七、结语
具有本真生活审美情操的人,即“君子”,才能诗意地、本真地、审美地对待生活、仁爱生活、把玩生活。“君子”就是本真性生活审美者,或者说是以本真审美生活方式与本真化、诗意化生活态度生活的“人”,“乐道安贫”“求仁”“安仁”之“人”。所谓“乐道”之“乐”,其原初意是指一种来自生活中的审美悦乐。这里就指出,“乐”的本意是快乐,为一种生活审美快感。后来,则派生出含蕴“形上之乐”的“乐道”本真生活意义。“乐道安贫”之所谓“道”,其实质就是“仁”,具有生活美学层面的意涵。故而,“求仁得仁”“安仁”之“仁”,即意指“人”之精神与心灵方面的活动,具有形而上之思的意蕴。据《论语·为政》记载,孔子曾经用极为简洁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生活经历:一生坎坷,到了三十岁才稳定下来,确立了生活之路,进入到审美化的生活流程,内心平淡明静,使自己达到一种审美升华。可见,“颜子之乐”与“曾点之乐”所推崇的不仅是一种“人”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而且是一种极高的本真化、诗意化“求仁”“安仁”之生活审美境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