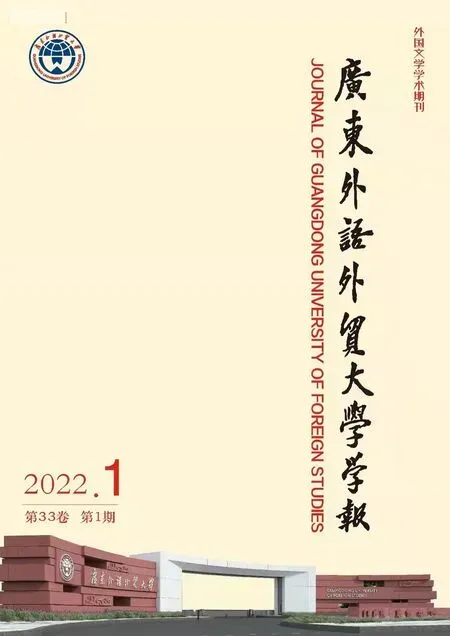小说《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中的“梅尼普体”研究
2022-11-21胡颖
胡颖
引 言
维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Venedikt Yerofeyev)的小说《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Moscow-Petushki)是公认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开山作之一,也是俄罗斯当代文学中日益被赋予经典地位的一部作品。苏联解体前已有学者将叶罗费耶夫列为俄罗斯经典作家,并称其小说《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的“原始文本”(Зорин,1989:256-258)。这部作品以其嬉笑怒骂的语言风格、颠覆一切的狂欢式的世界感受、鲜明的互文性和游戏性、大胆荒诞的虚构与幻想、杂糅的体裁等特点著称,这些特点赋予《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鲜明的不可复制性,使其成为深刻影响俄罗斯当代文学进程的一部作品。正是这样一部不可复制的“原始文本”,很难被简单归类到某一文学流派和体裁中去,因而在研究过程中,追溯它的文学源头显得尤为必要。“体裁是创造性记忆的代表”(巴赫金,1988:156),对《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小说体裁的历史回顾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更深入地理解这部作品的体裁结构和情节布局。《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古希腊罗马的诗学传统,与欧洲古典文学中的“梅尼普体”十分接近,但又不是“梅尼普体”简单的摹仿者和再现者,而是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融合、利用和翻新。
巴赫金(1988:156-163)曾指出,“梅尼普体”(或称“梅尼普讽刺体”)属于古希腊罗马文学中的“庄谐体”,由“苏格拉底对话”演变而来,但其直接根植于狂欢体的民间文学,这一体裁名称取自公元前3世纪加达拉的哲学家梅尼普之名,正是他创造了这一体裁的经典形式,公元前1世纪罗马学者发禄采用此词作为特定的体裁术语。古希腊作家赫拉克利特·波基克、比奥·鲍里斯芬尼特、卢奇安,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伯雷、塞万提斯以及19世纪俄国作家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创作都与“梅尼普体”有深刻的渊源。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对“梅尼普体”进行了详尽的定义和阐述,而“梅尼普体”的几乎所有重要元素(或其变体)都能在《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中找到。本文将从其中的几个突出特点入手,分析这部作品对“梅尼普体”的复现与革新。
荒诞与哲理结合的精神心理实验
“梅尼普体”被巴赫金(1988:165-166)称为整个世界文学中最为自由地虚构和幻想的体裁,直到今日仍是文学中狂欢节世界感受的主要代表者和传播者之一,这一特征在《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中鲜明地展现出来。小说中极为荒诞不经、大胆自由的虚构和幻想首先体现在内容的构思上。整部小说可以被总结为一部“醉旅纪事”,这段旅途中不论是混乱的叙事、怪异荒诞的见闻、颠转的时空,还是主人公不安紊乱的心理状态、离奇而血腥的结局以及主人公自述死亡经历的方式都像极一段漫长的噩梦,而小说中火车区间的精确记录,对一系列见闻生动而富有细节性的描写又赋予这个迷梦一定的真实性。
主人公维涅奇卡的形象构建也同样极尽荒诞之能事,他是一切复杂矛盾的综合体,是连日酗酒呕吐的知识分子,是满口污言秽语的长诗作者,也是细腻柔情的情人与父亲,还在自己构建出的不同历史场景中分饰多角,因而他自称“最悲伤的酒鬼,最轻浮的白痴,最忧郁的臭狗屎……集傻瓜、魔鬼和话痨于一身”(叶罗费耶夫,2014:52)①。巴赫金(1988:168-170)提出,“梅尼普体”区别于诸多体裁的一大特点是关于人们不寻常的精神心理状态的描写,如躁狂题材、个性分裂、耽于幻想、怪异梦境、癫狂欲念、自杀倾向等。此外,有悖常理的种种闹剧和古怪行径、鲜明的矛盾结合和剧烈的升降更迭都是“梅尼普体”的典型特征。这一切在维涅奇卡身上都得到体现,他把自己终日沉浸于醉梦之中,却对周围的一切都有着犀利而独特的认识;他向往美好温暖的生活,却又难以自控地趋向自我毁灭;他既麻痹又清醒,既疯癫又理智;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又粗鄙庸俗、叫爹骂娘。主人公的身体和心灵都轮番上演着种种极致的感受,例如他认为人身上除了生理与精神外还存在着超精神的维度,而他“每时每刻都准备着从这三个维度被恶心到”;他分不清究竟是“举世皆醉我独醒”,还是“举世皆醒我独醉”,但不论是上述哪种情况他都能感受到灵魂深处蔓延开来的不安,“孤单单一个人,心底一片茫然。这甚至根本算不上茫然……而是正在过渡到悲伤的不安而已”(164)。可这种不安在他想到正在等待自己的情人时,又变成深切的爱意和悔恨,于是便“给自己脸上来了一巴掌,又灌了三大口,落下泪来”。这种对极端的心理感受和精神状态的尝试被巴赫金称为“精神心理实验”,人物对自己本身具有一种“对话态度”,梦境、幻想、癫狂使主人公及其命运无法获得史诗和悲剧中的那种完整性和单一性,而是使主人公身上存在着另一个人,而这种双重性中除了悲剧因素还常带有诙谐的性质。
值得指出的是,“梅尼普体”小说即便运用最为不着边际的大胆虚构,但它始终可以得到内在的说明、解释和论证,其目的始终是服从于思想和哲理的。在《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中,承担着“合理化”任务的就是“酒”,它是小说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基础和推助物,也为一切的矛盾和荒诞提供了解释和途径。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格尼斯(Генис,1997:228-229)指出,“维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是关于酗酒的形而上学的伟大研究者。对于他而言,酒精是一切异在的高度浓缩。醉酒是奔向自由的方式,是逃离现世的途径。主人公的心灵经历了分娩般的阵痛,伏特加就是新现实的助产士”。酒也催生了小说中的“贫民窟的自然主义”(巴赫金语)。让身为知识分子的主人公与最为底层的堕落、庸俗、污秽和贫困结合一起,把受难者、疯癫者与思考者、哲思者结合起来。小说中以酒助力的“合理的幻想”同极为深刻的哲理与对世界极其敏锐的观察结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梅尼普讽刺里的主人公上天堂入地狱,游历人所罕知的幻想国度,面对异乎寻常的人生境遇,不是为了考验人的某一性格,也不是为了从正面体现真理,而是为了寻找真理,启发它并考验它。
俄罗斯当代文学史家利帕维茨基(Липовецкий,2006:210)称《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是一次深刻的“哲学实验”。维涅奇卡是一个思想者,即巴赫金所说的哲人,他是真理的追寻者,并认为自己正在与真理无限接近。“梅尼普体”小说中的种种惊险游历是对哲人所处哲理立场的考验,而非与其立场无关的个人性格特点,因此从这一层面说,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的旅行就是主人公探寻真理的过程。“佩图什基”这一地点在小说中充满乌托邦色彩(社会乌托邦的成分同样也是“梅尼普体”小说的一大特点),那里的人即便对原罪都不会产生心理负担,即便没有戒酒数周,眼睛也同样清澈见底。维涅奇卡对佩图什基从来都心向往之,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就是“从痛苦走向光明”。但这位哲人在经历痛苦的折磨和幻念的捉弄之后,却葬身在寻找真理的终点,也是朝圣之路的起点。尽管肉身将灭,哲人自身的思想立场却经受住考验:“我到死还是我自己,没有接受这个世界,虽然前前后后、里里外外我把这个世界看了个遍,我还是接受不了”(196)。维涅奇卡的形象是反抗一切的,是对思想垄断的极权国家中人的不自由的隐喻(Козицкая,2001:15),而他到死都坚持自己对一元话语世界的抵抗与不认同。就这一层面而言,作品也展现出较强的政论性,这是“梅尼普体”的又一大特点。叶罗费耶夫借醉醺醺的维涅奇卡之口讽刺苏联时期的诸多政治与社会现象,如对年轻一辈目光短浅的“革命接班人”的批判;用虚构的儿戏一般的选举、建国和革命解构苏联革命;用简洁而诙谐的寥寥数语点出苏联公务人员的嗜酒如命:“高级查票员谢苗内奇……把事情简化了:你身上没票,那就按照一公里一克伏特加的价码给他酒吧”。叶罗费耶夫突然转换成官方文书语体,“这一改革新举措加强了查票员与广大群众的联系,而且使这种联系更便宜,更简便,更人性化”(136-137)。这种诙谐的讽刺语调显而易见、锋芒毕露,又将政论“降格”和“世俗化”,削弱了刻板性与严肃性,更好地完成其介入文本的功能性价值,更为巧妙地实践了“梅尼普体”手法。
内在的对话性
“梅尼普体”的前身是“苏格拉底对话”这一对话型体裁,同时它还吸收了几个相近的小体裁,如交谈式演说体、自我交谈、筵席交谈等,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内在的对话性(巴赫金,1988:172)。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梅尼普体”风格时,就曾指出其充满争辩气氛的语言和内在的对话性是典型的“梅尼普体”现象,《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的内在核心也正是这种对话性。有学者认为,叶罗费耶夫与巴赫金所评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让人物用对话的方式进行交锋,作者自己也对他们采取平等的对话立场,因而整个作品都被他构成一个大型对话场(余一中,2004:156)。而处于这个大型对话场中心的就是具有作家和主人公双重身份的维涅奇卡,“对话式的双重情感的集中化身就是这部长诗的中心人物——维涅奇卡·叶罗费耶夫本人和他的主人公,作家与叙述者这对孪生兄弟”(Лейдерман,2003:394)。围绕维涅奇卡所进行的对话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自我对话。小说中主人公的大量独白也具有双声性和多声性,采用不同的人称代词,如:“‘你说你孤独,遭人误解?你灵魂里外有这么多东西,在佩图什基,在佩图什基,你都有那么一个人做伴,你怎么能说孤独?’‘不,不,我不再孤独了,也不再被人理解了’”(65)。此外还存在另一种类型的自我对话,即“心灵与理智的对话”,如心灵与理智之间关于喝酒多少的争辩(45-46),关于明天是否美好、良心与品位等问题的讨论(48-49),关于光明与黑暗的一对一的争斗等(116)。
第二类是与其他多个臆想中的交谈主体间的对话。如与读者的对话,小说篇首就出现了对读者的告白,小说中也不时穿插在独白中对读者的发问;还有与天使、撒旦、本都王米特里达梯、火车上的旅客、斯芬克斯、复仇女神、公爵夫人和男仆、情人与儿子等人的虚拟对话。与此同时维涅奇卡还一人分饰多角:他在库尔斯克车站餐厅时是要去彼尔姆却没去成的旅客;在车厢上喝酒后又摇身一变为正在排练着《奥赛罗——威尼斯的摩尔人》的夏里亚平,所有角色都由他一人演出。这些文本构建于自身与外部的对话声中,俄罗斯学者波格丹诺娃称其为“将叙述戏剧化的对话法”。这种手法所具有的并非只是叙述性,而是舞台性,更主要的就是对话性,“叶罗费耶夫打造了大量隐含人物的面具,同时保证了文本内部交际多声的状态。舞台式的独白、对话和多声代替了小说的叙述性,构成了《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的文本基础”(Богданова,2003:16)。
第三类是与各时代文学、艺术、哲学观点的对话。瑞士学者、叶罗费耶夫研究者斯·盖谢尔-什尼特曼(Гайсер-Шнитман,1984:135)指出,小说中“充斥着大量或公开或隐晦或虚谬的引用、借用、引喻、摹仿、戏仿、体裁改装、假托……文中出现的国内外作家、哲学家、作曲家、政治家、演员、圣经及文学人物名多于100个,书籍、歌剧、绘画、电影等艺术作品的名称与各种历史事件、地名等数量高于70个。这成为组织作品内容与形式结构、贯穿整部作品的关键要素”。《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的互文性在叶罗费耶夫创作的“艺术密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每个研究者都不能绕过的话题。小说与各类历史人物和同时代人作品的互文实为“梅尼普体”中“同当代各种哲学的、宗教的、思想的、科学的学派、流派、思潮等进行的公开和隐蔽的辩论”(巴赫金,1988:171),使整部小说充满诙谐的争辩气氛,将“新闻性、政论性、讽刺性和尖锐的现实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如维涅奇卡在被米特里达梯追杀后见到“工人与集体农庄女庄员”雕像时,工人用铁锤猛敲他的脑袋,女庄员则用镰刀割他的睾丸,他感到“我的一切都在抽搐,不论是脸、衣服、心灵还是思想”(194)。这句话仿写了契诃夫的名言:“人的一切都应当是美好的,不论是脸、衣服、心灵还是思想”。官方霸权话语所虚构的真相和现实就隐藏在互文之中,当人们身处极权势力的步步紧逼,被“镰刀”阉割肉体,被“锤子”剥夺个性和思想,连保全自己都十分困难,要保持自身“一切的美好”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又如“世上什么东西最美好?——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而比这更美好的事是:日古利啤酒100克,‘萨多科’洗头水30克……”(82),这句话的前半部分引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维涅奇卡以其醉汉特有的个性化思维与官方所宣扬的解放全人类的集体理想对话,叶罗费耶夫把“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去崇高化,认为鸡尾酒配方高于一切,光荣而伟大的人类理想所固有的崇高性和严肃性在这里立刻被荒诞不经的讽刺所瓦解、重构了。
除了以上3种以外,还有一类较为特殊的对话,那就是小说中多种语体和体裁所形成的对话。与上述对话不同的是,这不是内容和思想层面的对话,而是一场形式对话。后现代主义艺术的一个显著手法是“拼贴”(collage),把多种形式、风格、体裁的艺术创作手法混合在一起(陈彦华, 2018: 52)。多种语体和体裁的广泛插入也是“梅尼普体”的一大重要特征,增强了小说多体式、多情调的性质。巴赫金(1988:170-171)认为这“对于作为文学材料的语言,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态度,是小说发展史上为整个对话一派所特有的”。因此本文第三部分将着重分析小说这一特征的体现和对“梅尼普体”的发展。
多语体性与多体裁性
《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广泛采用多种语体,也插入了多种文体,并且十分符合“梅尼普体”所惯有的“散文语言与诗歌语言的混合”(巴赫金,1988:170),主人公在回忆自己远在佩图什基的情人时就插入了一段诗歌。值得注意的是,《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相较于巴赫金所定义的“梅尼普体”而言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多种语体运用的密度和广泛度都更大。除了小说作品中常见的文学语体和宗教语体外,《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还运用许多文艺作品中较为罕见的语体,如科技语体,小说中多次运用图表(员工酒精饮量曲线图、日常生活和饮酒量关系的曲线图)以及以秒为单位记录酒嗝间隔时间的数列;又如说明语体,文中多次出现以说明书格式出现的鸡尾酒配方;日常口语体中出现了大量社会底层语言,黑话、脏话、俚语等也层出不穷。
《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对多语体运用的最大特点是同一段落中多种语体的转换,这是传统的“梅尼普体”中不常出现的。如在第一章中提到的公文语体的转变,又如第二章中提到的“世上什么东西最美好?——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而比这更美好的事是:日古利啤酒100克,‘萨多科’洗头水30克……”,寥寥数句中包括了文学语体和政论语体到说明语体的转换。类似的转换还有突然的降格和升格,如“毕竟,放屁嘛——属于本体论范畴……这里面跟现象学没有任何关系”(34);又如“啊!自由与平等!啊!博爱与坐享其成!啊!不必向其说明的无比欢乐啊!啊,我的人民生活中最惬意的时刻呀——也就是商店从开门到关门的时刻”(37)。就在这一升一降之间,诙谐的比重陡然增大,固有的观念得到解构,崇高与庸俗的界限也变得不再明晰。
《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还是一部多体裁作品。俄罗斯学者、叶罗费耶夫研究者别兹鲁科夫(Безруков,2015:225)在其专著《文学文本的接受》中指出,《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中呈现出不同层面的语言和言语形式,通过无意识外在化而实现体裁的演进,对其体裁的界定也一直是研究者广泛讨论的问题。首先,作家本人称这部作品为长诗(поэма),目前在大部分与之相关的研究专著、论文和介绍性文章中都沿用了“长诗”这一用法。“长诗”一词来自古希腊语, 是由描写全民族历史意义事件的叙事诗(эпопея)发展而来的,因此长诗一般来说是叙事诗,是一种把心灵叙事同社会历史重大事件、把内在情感和历史观念结合起来的体裁。正如黑格尔所说,长诗世界的构建中“必须存在充分反映出民族之精神的全民族事件”(Гегель,1971:574)。此外,长诗不论是从主题上来讲,还是从词汇、意象、语体等方面来说都是较为高雅、庄严的。但不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在乍看之下并不符合上述体裁特点,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高雅体裁背道而驰的。事实上,这在百年前就已存在先例,果戈理曾将自己的长篇小说《死魂灵》定义为“长诗”,并在为俄国青少年编写的语文学教科书大纲中的“史诗的较小型种类”板块中提出,“在新世纪产生了一种叙事作品种类,这些作品仿佛构成了小说和史诗的中间物,其主人公尽管往往是个别的、不显要的人物,然而在许多方面对人类灵魂的观察者具有重要意义……许多作品虽然是用散文写的, 但仍应归入诗歌创作”(果戈理,2018:207)。在“长篇小说”这一板块他同样认为,“长篇小说虽然是用散文写的,但可以成为崇高的诗歌创作”(果戈理,2018:211)。俄罗斯文学理论家哈利泽夫(2016:392-393)在界定体裁时也举了《死魂灵》的例子。他认为作家们有时会随意确定自己作品的体裁,即使这并不符合约定俗成的用法,因为“体裁特征”本身就是极具多样性的,并不存在严格按照某一标准对体裁进行逻辑分类的可能性。叶罗费耶夫效仿果戈理称自己的作品为“长诗”,不仅展现了作者对自己作品本身的高度自信,也体现出其作品的宏大构思。在这部作品的时空发展中涵盖了两条线:一条是外在的、浅层的线,也就是主人公前往天堂般的佩图什基的旅途;还有一条是内在的、深层的线,是作者对苏联现代社会与生活图景的描述和感知。《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兼有叙事性和抒情性,同时具有诗歌典型的偶然性和随意性。主人公的内心煎熬,看似粗糙凌乱,实则细腻深刻;关于俄罗斯历史、文化以及诸多社会问题的思考都构成了这部作品复杂的抒情图景。因此从这一角度说,《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可以被称作是“长诗”。
除此之外,在之前提到的“长诗”这一体裁范围内,还包含着另外的体裁形式——旅行记形式。《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运用了与但丁长诗《神曲》一样的幻游形式,叙事结构上与拉吉舍夫《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两者都是以乘车旅行者的见闻和思考为主要线索,每一章又都是以车行走的站段或区间为标题,余一中(2004:155)认为在这里可以看到斯泰恩的《感伤的旅行》的影响以及关于伊万王子寻找公主的民间童话的影响。但与这些作品不同的是,《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将叙述重点放在火车站与站之间的区间,而前人的叙述重点都是在站点,因此《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主人公的生活、思想和状态是随着窗外的变化流动的,时间和空间是在一起往前行驶的,这样更有利于展现抒情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外在行为的变化。叶罗费耶夫仅仅套用了旅行记小说的外壳,它表面上是沿旅途进行的线性叙事,实际上在情节上缺乏关联性,缺乏旅行小说中会大量出现的与不同人的会面与旅途见闻等,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独白和内心对话,许多情节与旅行本身没有太多逻辑关系。皮野(2017:85)认为,《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之所以运用旅行记形式,是在与拉吉舍夫、卡拉姆津的《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简》和普希金的《从莫斯科到彼得堡旅行记》进行一种隐性的论辩,这同小说反思俄国道路命运的核心主题紧密相关。事实上,这种隐性辩论与体裁套用也是《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故意为之的反体裁特征,在传统现实主义叙事方法的面具之下,打破了传统常规的体裁结构,呈现出一种杂糅各家的混合主义风格。
《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兼具众多体裁特征,米·爱泼施坦(Эпштейн,1993)、娜·日瓦卢帕娃(Живолупова,1992)、谢·楚普利宁(Чупринин,1988)等研究者认为它属于自白小说(исповедь),因为小说呈现出较强的自传性和自白性。叶罗费耶夫写作这部小说时就在莫斯科-佩图什基支线上的一个电缆工程队工作,当时作者非常渴望坐上火车,到他向往已久的佩图什基去,因此小说本身是以真实的现实为背景的;小说主人公也与作家同名,里面充斥着大量作家本人的影子,比如其出色的创作才能和嗜酒如命的特征。除此之外,西尼亚夫斯基(А.Терц)认为它可以属于幽默小说(роман-анекдот),1994年这部作品也是在一个幽默小说系列丛书里出版的。此外还有利帕维茨基提出的“侦探小说”,什尼特曼提出的“散文诗、巴拉达叙事诗、神秘剧”,马·阿里特舒列尔(М.Альтшуллер)提出的“远行长诗”,亚·卡瓦杰耶夫(А.Кавадеев)、奥·谢达科娃(О.Седакова)等人提出的“圣徒小说”(Брыкина,2009:36-37)等说法,学者多加拉科娃(В.Догалакова,2015:217)甚至仿照俄语中“梅尼普体”(Мениппея)的命名法,直接将这部作品定义为“叶罗费体”(Еропея)。
总的来说,《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在体裁上呈现出自由化和多样化、阐释上的开放性等特征。叶罗费耶夫本人也在小说中点出了这一特点。在“43公里——赫拉普诺沃”这一章中主人公携带的酒不见了,他说道,“鬼才知道我将采用哪种体裁到达佩图什基,刚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一切还都是哲理性随笔与回忆录,还都是像屠格涅夫那样的散文诗,可现在么,侦探小说开始了”(68)。这种体裁上的高度杂糅,对传统体裁的模仿和解构,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体裁本身的抗拒和反崇高。
结 语
《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中继承了“梅尼普体”的多个主要特点,可以说,“梅尼普体”在《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中保持了惊人的完整性,小说中运用“梅尼普体”的部分也是最为重要和关键之处,因此“梅尼普体”实质上是为这部后现代主义文学“原始文本”创作定调的。但是,《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并不是对“梅尼普体”的简单模仿,它将虚构和幻想进行得更为大胆荒诞,其内在的对话氛围、争辩性和反抗性更为突出,范围更加宽广,多种体裁和语体的运用和转换更为灵活、自由、多样,密度和广泛程度更大,其中对体裁这一概念本身的反抗和反崇高性也十分鲜明。“一种体裁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在各种独具特色的作品中,能不断地花样翻新”(巴赫金,1988:199-200)。可以说,《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展现了“梅尼普体”本身强大的延续性,也在极大限度地丰富“梅尼普体”内涵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外延,使其在当代文学中焕发出新的生命。
注释:
①本文中《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的引文均出自叶罗费耶夫.2014.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M].张冰,译.桂林:漓江出版社。后文中均仅标注页码,译文有部分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