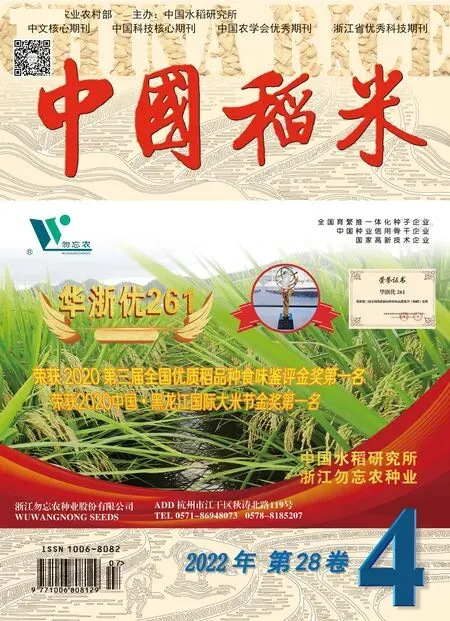稻文化和浙江稻作文化漫谈
2022-11-20杨雨菲
杨雨菲
(绍兴文理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作者:yufei010710@163.com)
浙江自古以来山灵水秀、人文蔚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数千年以来,浙江人民创造了千姿百态、光辉灿烂的文化成果,为丰富和繁荣中华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丝绸文化、茶文化、诗路文化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良渚文化时期就已出现蚕桑纺织业,并发现了世界最古老的丝织品;唐宋时浙江茶文化频繁传至国外,南宋时期成为世界茶文化中心;浙江诗路文化带文化底蕴丰厚,李白、孟浩然、陆游等历代文人在浙江游历论学,留下了《梦游天姥吟留别》《舟中晓望天台》等大量诗词名篇[1-2]。浙江还拥有上万年稻作文化历史,留下了许多光辉灿烂的稻作文化遗存习俗,如上山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青田稻鱼共生、杭州南宋八卦田等遗迹遗存、农耕景观[3]。稻作文化一般是指水稻耕作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造和约定俗成的民俗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4]。这些文化是各族人民血汗的结晶,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至今深刻影响着全球半数人的生活。
1 关于稻文化的古今记忆
从世界农耕发展史看,大约在1 万年前,在生存环境变化等因素促进下,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即开始对野生动植物进行驯化,使得人类祖先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由狩猎采集向农耕养殖的转变,也是人类文明起源的里程碑事件。据统计,约有250个物种进行了完全驯化,其中水稻、小麦和玉米等成为世界主粮作物,为全人类提供了50%以上的能量。现在,世界水稻90%以上种植在亚洲国家,稻米一直是亚洲人餐桌上的主食,却少有人清楚其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
太湖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网密布,适合发展种植业和渔业,构成了江浙地区经济发展的自然优势。东晋在建康(今南京)建立政权后,北方士族大量南迁进一步繁荣了江浙一带的经济文化水平。“鱼米之乡”一词,顾名思义,就是指盛产鱼和米的地方,当然这只是狭义之说,广义上应指富饶之地。其文最早出自唐代王睃的《清移突厥降人于南中安置疏》:“谄以缯帛之利,示以麋鹿之饶,说其鱼米之乡,陈其畜牧之地”。隋炀帝下令修建京杭大运河,除贯通南北加强统治外,将江南富余的粮食布帛等北运也是其主要目的之一。
既是“鱼米之乡”,自然与稻田脱不了干系,在我国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时代里,稻田便是随处可见的人类生活记忆。《诗经》中早有记载“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是为西周时期河水灌溉公侯稻田的生动写照。唐宋时期中国的经济中心开始不断往南迁移,水稻逐步取代小麦成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5]。宋朝王应麟所作《三字经》已将“稻”置于首位:“稻粱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宋朝诗人苏轼、陆游曾在诗词里如此描述过“插秧”,那正是“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陂塘处处分秧遍,村落家家煮茧忙”;董嗣杲、连文凤、戴复古也如此描述过“稻花”,说它们“四海张颐望岁丰,此花不与万花同”“纷纷儿女花,为人作颜色”“雨过山村六月凉,田田流水稻花香”。而于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宋朝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辛弃疾本是宋代名将,一生金戈铁马,既写下了豪迈热血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也写下了豪壮悲凉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然而他在贬官闲居江西上饶时,也能写下一首吟咏田园风光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足见只有乡村的清风明月、稻香蝉鸣才能带给诗人这样的愉悦之境,才能写下如此清新安逸的田园词作。
我的家乡在绍兴诸暨,属于浙东南和浙西北丘陵的交接地带,四周群山环抱,境内丘陵山地居多,但在那山水之间,总还是错落分布着一块块整齐而金黄色的稻田,衬映着山水,美不胜收。那还是在我特别小的时候,大约刚开始记事吧,夏日的傍晚总喜欢跟在外公后面,搬一张小板凳静静地坐在稻田边上,听风吟、听蛙鸣。外公总会指着夏日里刚栽下去不久的小禾苗对我说,农民伯伯们插秧之后,五至七日,这些秧苗便可返青,之后便经过分蘖、拔节、扬花、灌浆、结实等一系列生长,直到立秋时节谷子成熟,向着大地弯下腰身,便是一年中最为喜悦、忙碌的秋收景象。随着慢慢长大,这样美好的场景却越来越少,钢筋水泥混合的城市越来越大,稻田却离我们越来越远。外出求学后,更是远离了老家,只在暑期返乡偶尔经过时,还会远远地望一下那些孤单、落寂的稻田,却很难再有童年时的心境了。听外公说起,每到秋收时候,村子里就是一台台轰鸣的收割机在作业,只是它们似乎不再对稻子怀有敬意,纯粹在展示没有灵魂之美的喧腾。诚然,从刀耕火种到铁犁牛耕,再到全程机械化,这无疑是时代在不断进步,但似乎总有些东西在渐行渐远。
2 浙江稻作文化漫谈
“十月获稻,为此春酒”“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些我们从孩童时期就耳熟能详的古诗,在一代又一代的流传中已经蕴藏了丰富的稻作文化密码,只待我们层层揭开。
一直只知道浙江是“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殊不知浙江还是世界栽培水稻的驯化起源地。直到大二暑假,我先后去了杭州良渚古城遗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和浦江上山考古遗址公园,方才对源于我国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有了更深入了解。北京大学的严文明先生曾经有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说浙江的遗址名很有内涵,从美丽的小洲(良渚)出发,过一个渡口(河姆渡),跨一座桥(跨湖桥),最后上了山(上山)。这是一条通向远古的诗意之路,也是中华文明的探源之路。
良渚文化距今5 300~4 300 年,良渚文化的中心为良渚遗址。“渚”,意为水中间的小块陆地;“良渚”,其字面含义即为美丽的小洲。相传古时这里多“渚”,后垦为良田。良渚坐落于杭州市区西北部,属于典型的江南水乡,此说自有渊源。从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浙江博物馆前身)的施昕更1936 年首次发现良渚遗址,到2007年发现良渚古城,再到2015 年确认了设计合理、规模浩大的良渚遗址群水利系统,最后到2019 年良渚古城遗址正式成为中国第55 处世界遗产,实证了5 000 年前的古老中国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以及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在同时期进入了国家文明社会阶段。在良渚古城遗址,考古学家们先后发现了水稻从耕种到收获使用的成套的石制工具、大范围的稻田耕作区、配套的灌溉水渠和超过10 万kg 的炭化稻谷,直观展示了良渚时期逐步成熟的稻作农业,为良渚文明的早期国家形态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6-7]。
从良渚到河姆渡,再到跨湖桥,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历史再次向前推进了2 000~3 000 年。1973 年,河姆渡遗址被发现发掘,造型别致的象牙雕刻艺术品、精美的漆木器和连片的杆栏式木构建筑遗迹等令人耳目一新。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在河姆渡遗址第4 文化层较大范围内,普遍发现有稻谷、谷壳、稻秆、稻叶等遗留痕迹,出土了大量的炭化稻米;农史学家游修龄先生鉴定后认为河姆渡出土的水稻遗存属于栽培稻,同时伴随出土的大量农具——骨耜,表明河姆渡先民的稻作农业已经进入“耜耕农业”阶段[8-9]。跨湖桥遗址的发现则将浙江的人类文明史提到了8 000 年前,同时也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骨器、木器、石器,以及人工栽培水稻等文物,还发现了距今约8 000 年、人类历史最早的独木舟。
这条漫长的中华文明之路、稻米之路,部分始于金华市浦江县一个被当地人称为“上山”的小土坡。2000年,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遗存逐渐被考古学家们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大口盆、夹炭陶片、圆石球、石磨盘等古老的事物被逐一发现,迥然不同于已知的新石器时代器物,后被命名为“上山文化”,距今约11 000~8 500年。在上山文化考古工作中,陆续发现了10 000 年前属性明确的栽培水稻、迄今最早的定居村落遗迹和大量彩陶遗存。当然,其中最耀眼的自然是那一粒跨越万年之久才得以与世人相见的炭化稻米,上山遗址发现了包括水稻收割、加工和食用的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遗存。10 000 多年前,上山先民从洞穴走向旷野,迈出了人类走向文明的一大步[10-11]。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尽管上述几种文化在发现的住所、石器、陶器及其他代表性器具方面所呈现的面貌各具特色,但仅从稻作农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看,上山、跨湖桥、河姆渡和良渚等四种文化实际上分别代表了我国稻作农业发展的起源、发展、演进和成型等不同时期;水稻栽培历史演变就像一根绳索一样,紧紧地将不同文化牵在一起,稻作农业的不断发展最终也推动我国农业社会由上山文化“最早的村落”走向良渚文化“最早的国家”,完成了中华文明的初步演进。
3 尾声
原来一片稻田的时光是没有尽头的,只是翻来覆去的稻谷青了又黄,黄了又青。我们所阅的每一株稻穗的风姿,所食的每一碗米饭的能量,都是一部绵延万年的史诗。如今,我们的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多姿多彩,城市里闪烁的霓虹灯照耀着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白天和夜晚,喧嚣和宁静,常常让人忘却了曾经我们一路走来,那些最朴素、最寻常的美好。原来那些渐行渐远的,正是渐渐丢失的农耕记忆和稻作文化。这也许便是发展的代价吧,如今我们要做的不正是寻找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么。当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文化正在回归,城里的人们正重拾对稻田的敬意,试着放慢自己的脚步,在周末去赴一场稻田的盛大约会,只因那时,稻花开过,稻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