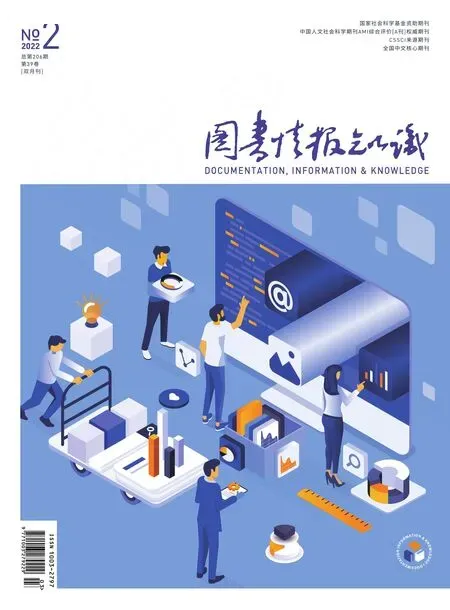以史发端的图书馆学探索之路
——谢灼华教授口述史访谈
2022-11-18口述谢灼华
口述:谢灼华
访谈:黄鹏2宋登汉2
整理:宋登汉 鄢珞青2
访谈时间:2017年5月22日;访谈地点:武汉大学图书馆
(1.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430072;2.武汉大学图书馆,武汉,430072)
1 家庭环境与青少年时代
· 谢老师,您是广东梅县人,听说梅县文化教育是非常发达的,我们想请您谈谈您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包括您的父母、家庭教育等方面。
我是广东梅县人。这个地方主要汇聚的都是客家人。客家人是指我们国家历史上从唐宋以后中原往南迁来的这部分人,现在客家人的主要居住地是在广东、福建、江西,其他省份如湖南、广西、四川、台湾都有。所谓客家是做客的,你不是本地的居民。因为客家人可能长期以来接受中原文明的影响和文化的熏陶,逐步形成一些很重要的传统,比如说耕读传家,这一点上很多家族都有。但是客家人这一点非常明显,读书、耕田,还有尊师重教,对教育这一点非常重视,凡是有能力的送小孩子上学不说,像我们南洋华侨挣到比较多的钱,首先会到我们本地本乡支援地方办学。所以我们这些穷苦的人家,能够上小学、中学,那基本是受当时社会影响的,就是社会支持才能够上学。还有叫作积德行善,客家人在这一点上确实保存了很多中原文化的遗留和传统。
我一共有六个姊妹。我的父亲是没什么文化的、农村的农民。我六个姊妹里面,其中文化最高的就是我,上了大学。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很小的时候就得到非常好的文化的熏陶,像读书会的活动,我们在这时候往往得到一些读书、阅读的乐趣。我小学毕业以前,像《三国演义》《西游记》,还包括《水浒传》这些先听他们讲,以后借书来看看。到了五、六年级,基本上很多章回小说,慢慢读完了。我们小学是比较正规的教育,业余活动比较丰富多样,而且比较早就养成了对读书的兴趣爱好。我自己一生基本上是喜欢读书,有机会可能写点书,有条件可能藏书。我这一生一世对书扯不开、脱不了。
1951年到1954年,我上的中等技术学校是梅州农校,这个学校当时是比较好的。现在是全国比较著名的中等专业学校,解放以前它就成立了。上这个学校对我生活上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毕业以后可包分配。这对我们这些农村子弟来看是感到非常需要。(这个学校的)教育程度包括管理水平、教学设备、教师水平比较好,很重要的影响我一生的就是有一个图书室,图书室比较大,图书馆的馆员对我特例,凡是我进去以后都可以坐下来看,解放初期就出了一套《新文学文库》,包括鲁迅、巴金、茅盾、老舍、许地山等作家的作品,我基本阅读这些新文学著作,弥补了我小学阶段只读了一些古典小说、章回小说的缺陷。1956年,当时报考图书馆学,可能就是因为“图书馆”三个字在我的脑海里影响太深了。
2 大学教育
2.1 报考与入学
· 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报考武汉大学,并选择这个专业呢?
1954年林校毕业以后,开始在粤东行政公署里面的林业处驻地汕头上班。1956年,在惠阳专员公署农林水办公室工作(驻地惠州),当时政府部门开始选派比较年轻的公务人员上大学,听说准备送我到现在华南农业大学的森林科。健康检查时出现了情况,说我是色盲,我实际上是色弱,辨色率比较差的这种,只能报文科。高考的第二天我就下乡了。到八月中旬,我收到录取通知书,被录取到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当时学制是三年。当时广州到武昌这里的时间还要两天,我是8月30号出发,31号来到这。9月以后就正式在武汉上学了。
当时上武汉大学,我们进校以后还是有一些感觉不一样的,车子进到武大以后,高年级同学现场去迎新。刚好是傍晚,外面还有些蒙蒙亮的。那个同学带着我进校,从现在“六一”亭对面的那地方进来慢慢往上走,沿着那个坡儿上来,特别是看到老斋舍,那对我们还是很震撼的。那么高的楼,透出的灯光,确实很诱人。
我们当时居住的要求是,一年级住樱园老斋舍最下面这一级。当时宿舍名号是用千字文排列,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嘛,我们一年级住的是“宇”字(斋)。
2.2 老师印象
· 大学阶段有哪些老师给您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呢?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有几个印象我比较深的。应该说他们是中国图书馆学界第一批学者,比如说皮高品教授、徐家麟教授,还有黄元福教授、吕绍虞教授、沈祖荣教授等。第一个他们这批人非常有特点,在家里受到的国学教育,经史子集的古典传统文化的水平很高,又是上私塾的,又留过学,外语很好。第二个他们因为解放以前在文华图专,他们入学就是必须大学毕业,或者说大学肄业两年以后来上这个专业,而且毕业以后一般就是到图书馆当主任、当馆长,所以基本上都是曾经担任过图书馆的一些具体工作,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前面一个就是古今中外贯通,第二个就是理论和实践方面比较强。比如皮高品教授,他大学学哲学的。他给我们讲中国图书史,讲到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时候他就发挥他的专长,什么老子、庄子、公孙龙子,特别又是“白马非马”,这些人物和哲学知识都出来了,所以从图书馆学的要求上来看,他们使我们接触的知识面是非常广泛的,我们感到受益匪浅。第二学年,图书分类学又是他教的。他本来就是研究图书分类学的,他编了一个很有影响的《中国十进分类法》,一般叫它“皮氏分类法”。还有一个张遵俭老师给我们上的“目录学”。张遵俭老师是张之洞家族的,属于孙辈,清华大学学历史的,因为当时抗战以后转到文华图专,之后就在湖北省图书馆工作。他教我们《普通目录学》,用的教材是吕绍虞教授编的。吕绍虞教授原来是文华图专毕业的,之后在各大图书馆做过图书馆工作,特别是在英士大学,就是现在的浙大的前身,还在原来南京的“中央图书馆”,以后到了武汉大学教书;张遵俭先生给我们上课,他知识广博,我还记得他讲到汉代的刘向、刘歆的时候,给我们讲了学术源流与目录以及分类体系的发展的关系,他讲到刘向、刘歆分析当时儒家经典,以及各种不同的家、不同的派,最终选择汇总有个目录叫《七略》,也是对当时的学术进行分类,后来又变成四分,就是经史子集。所以我们感到从受教育的情况来看,能够得到第一代的图书馆学家们的亲自教育和训练很重要。
2.3 第一届图书馆学本科
· 当时是专科,是怎样成为本科的呢?
我们来了以后感到很高兴的一件事就是图书馆学专修科改为图书馆学系,学制就变成了本科四年制。1956年,我们这届也算是“黄埔”第一期,就是四年制的本科第一届。当时,全国实际上只有两所大学有图书馆专业,一个北大一个武大,所以整个教学计划都是协作制定的,课程设置基本相同,包括其他科研方面的合作都有。在为我们制定的培养目标这一点上,明确地说我们是培养三大类型图书馆的干部,即省市公共图书馆、高等学校图书馆、科研系统图书馆。当时我们这些人属于图书馆学教育比较高层次的要求,但是没有像80年代以后出现的叫研究能力的。因为当时还没有提到这方面的要求,所以有这样的教学计划,有几个特点:首先,要求学生必须要知识面宽,要懂得更多些。我印象非常深,我们的《中国文学史》学两年,《世界通史》学两年,《中国通史》学一年,《世界文学》学一年,像这一类的文史类课程,分量比较重,希望我们同学们在文史这方面的基础要打得比较好,适应图书馆知识面要宽的要求。其次,还有一个科学知识的问题,所以当时的教学方案里面专门有设《科技概论》,实际上就是要把数理化生各方面基本分支、学科特点,还有重要作家和著作等等这些和同学们进行介绍。这门课程的老师实际上是武汉大学最好的老师。齐民友教授是数学知识面特宽的一个人,还有给我们上课的那个曾昭安先生有点厉害,他曾经在外国得过几个博士,是武汉市数学学会的会长。为什么选他呢?倒不是因为他课讲得好,而是因为谁也没有办法像他那样懂得那么多,对于数学这一类。还有生物学,给我们上课的余先觉教授,美国留学博士,讲得比较好。最后,对我们语言的要求比较多,两门外语,主修俄语,还有副修英语。一年级、二年级学俄语,到三年级开始学英语。按照培养目标、课程设置这些方面要求,文史比较多,面比较广,而且包括文理各方面的基本知识,还有比较好的语言能力等等。
除上课以外,我们学生也没有什么其他可分心的东西,唯一一个是每个礼拜六或礼拜天泡在东湖,现在凌波门游泳池里面,我们一个小班可用一、二条小艇。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我们经常就是五六个人,大家从食堂带些馒头,划船划到湖心亭。平常的时间有空就游泳,我们同学游泳都非常好。还有每个星期六有电影晚会,每晚5分钱,月票是一角五分,可以看四场。寒暑假回家火车票半价,但回家的同学很少,因为实在没有钱买火车票。当时的考试方式对我的印象很深,譬如考《中国图书史》这门课,当时是实行口试,每个人进入考场,向老师要考题,稍作准备即向老师陈述,老师还可临时提问和补充,完成后出考场。记分用五分制,当然有些也用笔试。为什么印象深呢?一是武汉一月份气温很低,一般都会冻手冻脚,考场里往往生一盆火,对我们在外面等考的人,教室里简直是两重天地;二是当时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考分,如果得个5分,那高兴劲儿就别提了。总之,当时学生生活还是比较简单的,但这几年的文史基本知识的学习对我们是受用终身的。
3 教学生涯
3.1 提前毕业
· 我们知道您是提前毕业的,当时是怎样一种情况让您提前毕业的呢?
从1956年开始,国际上风云变幻,政治上的讨论、辩论比较多。到1958年,高等学校为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选留比较多三、四年级的学生,加强政治工作。(因为)我是共产党员,还有一个邹同学也是共产党员,学校通知我们去人事处报到,说了以后你们可把课听完,一直读到毕业。当时我在管一个年级,就开始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从1958年的教师队伍情况来看,1957年后,有些教师可能就离开了。当时对高等学校教育改革的要求是培养和造就一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就把我们几个比较年轻的共产党员补充到教师队伍。我们图书馆学系当时在这个基础上参加了武汉大学图书馆的图书改编,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来改编武大图书,最后在改编完以后,我们编了一部图书分类法,当时起名叫作“红旗分类法”。以后经过教师不断的修改直到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就变成《武汉大学图书分类法》。“武大法”在当时图书馆学教育里面是个很重要的成果。
·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上课的?上的什么课?
1958年11月份,文化部举办了全国的省市以上公共图书馆馆长的研讨班,武大派我参加这个班的教学工作。最后的成果就是出了《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是当时唯一的一本图书馆学理论的一个著作,到现在有不同的评价。我还是这个班教学小组的成员。教学组一共三个人,一个是文化部图书馆处的李峰,很厉害,他原来是西南联大的学生,搞“学运”的;还有一个是北京大学的朱天俊,还有武汉大学的谢灼华。学员是老干部,都是比较高的干部,所以他们有些图书馆的问题,有些业务上的什么问题,我们当时从业务上帮助学员。
1958年的11月份我就到北京,到1959年1月初回来,回来后出现一个情况,就是1959年必须按原来教学计划安排一些课程。结果一查,“中国图书馆事业史”这个课程没人教,所以我从北京回来以后准备这课程。1959年9月开始我就给学生上“中国图书馆事业史”。1958年的教育革命对我们整个图书馆界的影响是比较大的。特别是1961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国家有个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所以1961年的时候,中共中央有个《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我们称之为“六十条”。“六十条”出来进行调整,具体到我身上有几个问题。一个是当时我已经是教研室主任,因为教研室主任(要求)教授以上,我还不是,教研室主任不做了。第二个,有些课学生还没法上课。所以到1962年的时候,就这几年我有时间读书,我就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前四史进行阅读。这样就填补了我以前阅读上的一个缺陷,而且我本身是搞历史的,必须对古典著作进行阅读,这对我是比较重要的。
3.2 1966-1976年
· 在这段时间,当时教学是怎样的情况?您受到什么影响吗?
留校任教到1966年之前这段时间,我除了教学,科研成果也算是开始起步了。从1959年开始,我在《武汉大学学报》上就发表了文章;在1962年到1964年这期间,武汉大学提了一批讲师,彭斐章老师,他原来在苏联得过学位,他定为讲师。黄宗忠老师、陈光祚老师,还有我一个,1964年就定为讲师。我到1966年刚好是30岁过一点,在学业上已经告一段落,主要是工作上和研究上应该说都起步比较好,也成了家,生了个小姑娘。1964年到1965年有一年时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我们是到乡下待了一年,回来以后,我开了《图书采购》课,《中国图书馆事业史》那门课就已经停了。
· 在这期间还招生吗?
1966年以后就不能正常办学了,学校逐步恢复办学实际上已经到了1970年,我当时印象比较深的就是70年哲学系这些学科开始招生,图书馆学到了1972年才招生,那时招的是工农兵学员。所以开始那几年没招生,还没毕业的跟着我们一起去下乡搞(运动)。1969年冬天的时候,我们正在襄阳,直接领导我们的叫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当时叫作宣传队指挥部。下面分成几个部,有个报道组,把我和陈光祚老师两个人抽调到那,那为什么当时会选上我们呢?从我个人知道的是因为五十年代学校办《武汉大学报》,我本身也是记者,也参加过编辑,就是我们学校的那个报纸。1969年10月4号,我们按中央第一号令下去的。我们几个往乡下搬的时候,最早我们当时叫作四大队,四大队包括中文、图书馆学两个系就搬到襄阳,在襄阳隆中那个地方,靠近马路那边有个叫广德寺,那个寺很大,我们就住里面。1970年哲学系他们开始办学了,图书馆学系也要办学,当时把我们几个年纪比较轻的教师调回来办系。当时办系恢复招生是非常可怜的,教研室在老图书馆二楼,八个人,当时我们叫八条枪,来做筹备,准备教材,搞教学计划,到1972年,工农兵学员就来了,我们也开始教学。
3.3 1976年到成立图书情报学院
· 正式恢复高考到1984 年成立图书情报学院,这之间也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成立学院,当时是很大的事,在图书馆学系下面,当时开设了好几个专业,像图书馆学专业、图书发行专业、档案学专业,这些专业为什么都设置在图书馆学系下面呢?
1976年的时候,我还没有当系主任,是教研室主任。1978年以后,开始筹办情报系。当时就成立了图书馆学教研室和情报学教研室,两个专业基本上分开了。1979年黄宗忠、彭斐章、谢灼华,我们三个人曾经写过一篇图书馆现代化方面的文章,我还曾经到西安,到好些地方讲到过现代图书馆新的变化,其中讲到计算机的问题,我们觉得必须引起重视。80年代开始的时候,我们当时考虑比较多的是图书馆学教育怎么改革的问题,所以1983年的时候,文化部和教委做了个调查,把国内图书馆学教育发展情况和国外图书馆界现代化情况一起汇合起来,相当于提供领导参考、考虑这些问题。1983年还比较集中地做了这么一项工作,考虑怎么扩大人才的培养。
图书情报学院成立,包括图书馆学、情报学,还有当时叫图书发行、档案在筹备了。整个像图书系列,能够连起来对整个教育系列是特别好的。听说当时学校领导也觉得如果把图书生产整个过程,如编辑、出版、发行、收藏、管理、利用,分别设立专业,武大如果办成是很有特色的。所以1984年就成立了图书情报学院。整个世界的图书馆界都起了很大变化;而当时因为要办这个,我们领导还到了国家科委,希望国家科委支持一下,希望他们出点钱。新华书店总店感到要办出版发行专业给我们出点钱。当时一共有250万,我们学校再垫点钱,就在我们校门口建设那个大楼,5,000平方米。当时成为亚洲第一大图书情报学院,是第一个图书情报学院。当时管理体制,图书情报学院叫两者互相结合的,院里管党务、人事这些,系里面(管)教学、科研,它这两个是分不开的。当时(学校)还有经济学院,它是院里是虚的,系是实的,就系里操作。就这两个学院先试点,看看以后怎么办法,再慢慢地过渡到现在。
图书情报学院,开始实际上是两个系出现,一个是图书馆学系,一个是情报学系。专业在慢慢增加。当时发行专业师资基本上是图书馆学系毕业的同学和老师转来的。一个孙冰炎老师,还有乔好勤、廖延唐等老师,还有把图书馆学专业毕业年轻教师分到这地方做筹备,像罗紫初、吴平、方卿,好处就是这些老师了解图书馆学有些情况,当时校领导好像还想把编辑专业让我们接过来管,当时编辑专业在中文系,但后来没过来。新华书店总店要求我们主要是培养图书发行系统干部。你不能说我拿他资助的基金,你办的专业培养的学生结果又回不到他这个行当里去,这样就办了好些专科班和进修班。
至于档案方面,其实中国的档案人才教育最开始也是从文华图专里出来的,当时文华图专因为抗战的原因搬到了重庆旁边的那个县,国民政府就在重庆那地方,有些部门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文华图专在这方面有几个人做了些工作,一个叫周连宽,他就是最先研究县政府档案管理这一类的。抗战时期在重庆,文华图专就招了几届,属于短期训练班,一般是适应当时的需要。原来文华图专招收的人要求大学毕业或者肄业,一年两年以后才能做这个。在抗战时期就有些改变了,它有关的学科就把招生资格降下来,一般高中毕业就(可以)进文华学图书馆学,还有愿意上档案的专修班,这样就适应了当时的人才需要。但是档案专业是行政管理型人才,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基本上整个行政领域里面已经全部有所变革。整个党的行政部门档案里比较重视,各方面条件要比较好。企业、事业单位,管理档案当时还不是很迫切。到80年代,行政部门包括事业、企业单位,就感到这方面的人才好像还是需要的,所以就又找到武汉大学,武汉大学考虑还是我们恢复这个专业。所以1984年开始主要是图书馆学力量很强,我们的图书馆学系就有了这三个专业,先是图书馆学,后面发行、档案专业加进来。
1978年以后调进了几个从事科技情报工作的同志,一个是严怡民老师,他曾经在国家科委工作过,还调进王昌亚老师夫妇俩,还有就是当时湖北教育厅田光先老师。因为情报专业苏联当时办的情况是怎么样?对我们这个适应情况好不好?我们是否就这样办?还有西方国家当时怎么样?作为情报information,有各种不同的翻译,像广东,它以前就不叫信息管理,它就叫资讯管理(现在改过来叫信息管理,像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资讯管理学院,现在改为信息管理学院),港台那边也一直是用这个名字(资讯管理)。其实这(是)我们引进的词,当时苏联一直叫情报所,实际上是(从)科学技术情报这一点上去办学。
我们当时两个系。我们图书馆学系比较稳定,办系经验比较丰富,教师力量原来比较多,基本上就是从教学单位出来的。他们(情报学系)还有个师资来源问题,就是有一部分“文革”中间毕业的大学生,采取回炉,就是把他们经过考试招回来在武汉大学里再学两年。比如邱均平老师原来学化学的,胡昌平老师原来学物理的,还有学数学的有两个,一个黄凯卿老师,一个是雷春明老师。教师来源就是有三个部分,相当一部分和情报事业沾个边,还有部分学自然科学的,比较熟悉科技的人才,第三部分是学语言的老师,比如焦玉英老师,她就是原来和陈光祚老师一起搞文献检索,以后她就在情报检索方面搞下去了。
· 陈老师后来就搞科技情报检索去了?
他主要搞科技情报检索,他搞得不错的。系里面当时还有个图书馆学研究所,把一个北京大学比较早毕业的张琪玉老师调进来,他原来是(在)文化部编《图书馆工作》,以后支援新疆办图书馆,他就在新疆干的时间很长。干了一段时间后,到80年代就想回到内地,这个老师各方面很不错。还有原来我们这毕业的同学俞君立老师、黄葵老师。80年代,图书馆学系很吃香的。我印象很深就是中央宣传部要几个人,我们最后一个人都没给。我们没有啦,都分完了,这几批的学生现在在全国他们都是顶梁柱。
· 在成立图书情报学院后,院长和系主任的关系,职责和分工是什么样的。您作为系主任,在任职期间,主要的工作有哪些?
我们这个院的系主任是校长任命,正式的作为正处单位;所以当时系里也想做些事,有些事都是由我出面的,比如1986年IFLA(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在北京开会后会。会后会筹备组的成员是我代表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出面的;1990年召开全国高校图书馆学系主任会议是由我主持的。这个系在整个院里面当时是最大的系。1984年开始,实际上把我们前几年研究国外的图书馆情报教育这些基本问题,包括应该注意的方向问题,包括现在有些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实施新的教学计划,1984年一直到1989年的时候,武汉大学作为先进教学单位,图书情报学院以图书情报教育改革这一点得了全国国家级的教学优秀成果奖,其中有三个人,彭斐章、谢灼华、王昌亚这三个人得奖的。
· 您当系主任的时候,特别是在教学改革上,当时是否还遇到一些阻力呢?争论有没有?
从我这个班子的情况来看,当时图书馆学系我当主任,郭星寿老师副主任。当时我们图专和其他有点不一样,我们很注意选拔在图书馆干过的老师,因为我自己的观点就是图书馆学它是实践性比较强的,像郭星寿老师他是从图书馆过来的,原来是武大毕业的,还有俞君立老师、黄葵老师,他们是从陕西省图书馆回来的。还有查启森老师,他原来在四川省图书馆。我们觉得这样子其实有好处,就是他们了解图书馆究竟是怎么干的,干些什么,图书馆需要的知识是哪些方面,我们的同学适应不适应?这些他们都应该比我们了解多了。我们这个班子年纪稍微大一点,平常像比较具体的课程门类的设置内容上,当时还是争论比较多。比如当时图书史和图书馆史原来基本上是两门课,80年代以后要进行课程改革,如果你照以前按历史过程讲下来肯定重复很多,后面一些新的课程,自然科学要插进去就比较困难。原来我们有些同学就说怎么到处都是讲刘向、刘歆。确实也是这样,我们图书馆肯定要讲到,按照我的看法就是我们官府藏书成型就是成为一个国家藏书,汉代是最重要的开始,因此总要讲当时的刘歆,他编的《七略》,刘向编的《别录》,目录学也讲、分类学也讲。从同学学习更多些知识来看,80年代学计算机数据库,这些新的内容必须加进去,还要加上数理化知识,高等数学一定要学的。所以80年代非常突出的这些课程必须要插进来,有些课程必须(通过)把有些内容删减或者取消、或者合并等各种不同的途径来搞的。比如图书和图书馆史我就比较大胆改革,但是有些课程就感到不能改。不同意见、问题是存在的。我们虽然都是师生关系,讨论问题争论非常激烈,从上午讨论到下午,不能因为是师生关系我就说了算,我没有这个权威,第二个你也不能这样做。我这人还有个好处比较包容,也不可能一个人说了算。
3.4 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 在图书馆学学科建设方面,您很多提议都是非常具有远见卓识的。
我们刚才谈到过80年代初期以后,要扩大同学们的专业知识,这是一个方面。我们图书馆学很重要的还必须扩大其他方面的知识,所以80年代初考虑通过加大文献知识(来实现)。以前我们曾经送同学跟着某个系学四年,5年毕业以后来教我们这个专业的课,这样也行不通;还有北大当时采取这个形式――2年学专业、学文学、学历史,两年学图书馆学,这样来我们感觉到也不行。1984年以后我们就比较倾向说能不能加大文献知识,来建设我们的学科特点,这样我们当时是考虑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方面的著作,而且这方面是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从)它这个思想基础觉得应该设立相关的文献学的课程。所以当时有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学,还有文学文献学、历史文献学,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学等。社会科学文献学由郭星寿老师来搞,文学文献学由我来搞,历史文献学由王余光搞。这样比较明确,从我们指导思想(来说)也必须加大专业方面的知识,比如文学历史方面,结合我们的文献来谈它的主要著作、重要作家。讲到文学文献学,这门课以前在1966年前也曾经开过,当时北大是张荣起老师,武大是陈光祚老师,以后就没有开了。但是当时开的名字叫书目学,就叫文学书目学,历史就叫历史书目学,靠在书目方面。我们80年代是比较注重文献方面,《文学文献学》这方面我编了个很详细的提纲,十几二十页,还编了两厚本参考资料,因为当时一下子要形成一本教材那不是很容易的。这出来以后,书目文献出版社他们有关人看到,他们觉得当时在目录学方面,北大一个陈秉才老师曾经出版过《历史书籍目录学》,文学书籍目录学没有人写,他们问我,我就说我搞吧。他已经定了是目录学,不是文献学,实际是目录学的整个体系,文学目录学。最后出版的是《中国文学目录学》,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1987年出的。当时在目录学方面算是专科目录学比较早的,所以有人曾经评论说这本书为目录学理论联系实际这方面开了个路,提供了可操作的内容。
· 从80 年代开始图院在教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像教学改革、课程设置、人才建设、人才培养方面,进行了很多的探索。
20世纪80年代,首先很突出的是武汉大学当时曾经进行了一些比较好的探索性的改革。比如武大曾经有学分制、转系、选课制,还有其他创新的地方。其次很重要的(一个)是我们办校本身还要考虑到作为用人单位,它对我们的毕业生的要求,要求些什么?第二个我们作为大学里面的系、科,我们对办学条件进行改革,必须朝哪些方面发展?还有当时全国除了北大、武大,还有东西南北,慢慢地都办起了图书馆学系。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想法,就是说图书馆学要不断的发展,而且发展要符合图书馆的需求。1984年图书情报学院成立以后,为了探讨图书馆学教育的若干问题,我与彭斐章老师合作写过几篇文章,如《关于我国高等图书馆学教育体系》《评建国四十年的图书馆学教育》《七十年历程――文华大学图书科到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以及《当代中国》中的《当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一书中关于图书馆学教育部分,此外,我还单独写有《图书馆专业人员的知识结构》《关于图书馆学专业核心课程的几个问题》。我与彭斐章老师合作是非常愉快的,一般是大家先共同讨论,集中到研究的问题,一起撰写纲目,动笔则一人一半地写出初稿,互传讨论和修订,最后交稿。所以,这些文章中的观点是(我们)共同认可的。
现在我用我1986年提交IFLA北京会后会的论文《图书馆专业人员的知识结构》为例,说明当时我对图书馆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的一些看法。我认为图书馆工作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职业,所以,图书馆专业人员的知识结构应包括四方面:管理知识,文献信息知识,技术方法知识和语言知识。而且必须注意解决好理论与技术方法、基础知识与专业知识、传统方法与现代化手段等方面的关系。1997年,海峡两岸图书馆学资讯学讨论会上,我对图书馆专业核心课程的建立和实施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如提出核心课程应从图书馆专业人员的知识结构方面考虑,应该考虑专业基础知识的广泛性、技术方法的实用性、素质能力的多面性等方面,确定哪些课程应定为图书馆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哪些课程则定为专业课。这样可以使图书馆学专业本科教学的基础更加扎实、全面,为硕士研究生等的教育衔接创造条件。
教育部抓整个文科教育,一部分叫核心课程,采取这样的形式,一部分就作为这门课比较成熟的内容,比较好学的,把它列进国家统编教材系列,叫作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当时不是所有的课程都可以列进去的,相当(于)以前说的通用教材,全国各地方都用。所以是一个什么样的课程,这些课程和其他课程,课程与课程之间怎么联系,而且不同的阶段,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是怎么样的来学习?就是所谓的那个核心课程,我们又进行讨论。还有具体组织,这些核心课程确定出来以后,我们再研究,首先定个大纲,像“目录学”课程由彭斐章主持,“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由谢灼华主持。我这个课程大纲编写组有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大、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等校图书学的老师,《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教学大纲》最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些课程大纲是全国一起合作编写的,这种合作编写的方式也符合我们图书馆学教育这方面不断地进行深化和改革的要求。
· 那个时候图院出了一批重量级的教材,包括像彭(斐章)老师有目录学方面,还有您自己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黄(宗忠)老师的《图书馆学导论》,张琪玉先生的《情报检索语言》,陈光祚先生的《科技文献检索》,这一批都是国家文科教材。
这是图书馆学发展的重要成果,教材我们经常在编,也曾经合作编写过几次。1962年北大、武大两家合作编教材,当时有个《读者工作》,就是我们讲的读者服务,我曾去参加《读者工作》讲义的编写。但《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不好)合作,因为其他学校没有搞这方面的人;有些可以合作,像《读者工作》《图书馆学概论》。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高等学校教材,质量是相当高的,大致可从这么几点来说明:一个就是根据当时整个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工作发展,那时候西方国家计算机,已经进入到图书馆,像IBM,对我们专业教学影响上其实还是比较大。第二个就是1983年以后,中学毕业的学生,经过考试进入到武汉大学,学生比较活跃,也对知识各方面的要求比较迫切。要求把知识面不断地扩大,把专业知识和文献的知识结合,建立起来叫作专科文献学。当时建立了一些课程,像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文献学、社会科学文献学、文学文献学、历史文献学,还有科技文献学。此外,必须加强相关专业知识,比如图书馆学专业学生也可以去听情报专业的一些专业课,以扩大专业知识面。
3.5 研究生培养
· 您指导了很多研究生,这方面您有何体会呢?
研究生培养,我们比较早,是1978年。当时目录学方向由彭斐章、谢灼华两个人合招,第一届毕业生里面四个读书算是比较用功的。乔好勤原来留在院里面,之后是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馆长;张厚生毕业以后到南京东南大学图书馆当副馆长,在文献检索方面他开辟了一个阵地;倪晓建原来分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以后当系主任,后来又到首都图书馆当馆长,现在是很活跃的;还有一个分到天津商学院,叫惠世荣,这个人去世了。第二届曹之,早两年是廖延唐老师带的,最后一年由我指导;第三届黄慎玮,分到华东师大图书馆系,现在退休了,她跟着我搞过文学目录学。到1983年我开始招“中国图书馆史”这个专业方向的研究生。程焕文第一届,现在是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馆长;第二届是徐鸿,现在是杜克大学图书馆的副馆长、昆山杜克大学图书馆的馆长,曾经在匹兹堡大学图书馆当过东亚图书馆馆长,又到香港,(在)香港科技大学还是中文大学当过馆长。招得最多的一届是85年,王子舟、李婷、胡先媛和周晓燕,现在王子舟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教授,李婷是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第三个周晓燕是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系,胡先媛毕业以后留在我们学校。
1986年那一届有彭海斌、邹桦,彭海斌工作后还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生,现在深圳做公务员。以后我们这个方向的王清,现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系做教授;还有张晓华,在安徽大学任教;刘蔷是北大图书馆学系来的,她现在在清华大学工作,是古籍方面的专家。其他在高校图书馆、出版系统做事的很多,如华南师大的刘青、华南理工的王磊,深圳大学的赵奕,还有好几个同学出国深造。招博士生是1995年,1996年的王子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任教;1997年的周晓燕,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98年的王桂平,现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2000年的贺子岳,现在武汉理工大学任教。他们都学有所长,是学界的中坚力量。
培养硕士生、博士生,我是没有什么经验的,重要一点是用自己成长的经历考虑学生的培养,很关键的是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的培养、历练,譬如做学问,首先要读书,读书有泛读和精读之分,指导性著作、专业经典不仅是文化知识的涵养,作为从事专业研究也是一门基本功。指导性著作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找到方向和加强理论素养,而对于专业经典,我是主张精读、讨论和写出学习心得,并从中找到研究的切入点。我对同学强调阅读,并要求阅读中要思考,要动手写提要,摘录材料和不断分类,引导进入更高层次的归纳和总结。当然,阅读要面宽一些,读书要读进去,有心得一定要写出来。我的认识也可能不全面,我觉得做学问,脑子要好是一方面,坚持努力、百折不挠,善于学习、巧用方法,也是成功的关键。
(提升)办学水平,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很关键,就是必须有个明确的学术观念、研究方法,还包括为人、志向都要有自己的规划。王子舟他们几个学生,我没有上很多课,但是每个礼拜都必须到我家。我们到时候就聊,主要是发展,包括这方面的具体牵涉到的一些内容,包括他提的一些问题。一般我很强调要学生(研究)他最愿意搞的、最感兴趣的,不然指定某个题目,或者老师的那个课题范围你完成一部分,那有些可能不一定有比较好的成果。
4 学术研究
· 您这一生整个学术生涯在图书馆学研究方面有比较完整的一个体系,围绕图书和图书馆,您的研究形成了文献史、藏书史、图书馆史、藏书文化、目录学等方向,以图书为中心,逐步地包括图书、目录、文献,这三者相互地交织不断地深化。
以前有些学生曾经这样问过我,谢老师您怎么写那么多东西?怎么有那么多时间?我说鲁迅曾经这么说过: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上了。那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双肩挑的干部,是最辛苦的,他要教学,教学业务他必须承担,因为你教师不教学是不可能,第二个你还要出成果。在高等学校我以前一直很支持这个理念要求,就是说高等学校的教师和其他地方那是不一样的,你如果没有东西你待不下去。我反复和一些同学交流过,我这个人不是很聪明,但是我这人比较勤奋。图书馆学、目录学、文献学,这些我都有所涉猎,而且有些方面我基本上应该说是开这方面研究的一些路子。
首先我感到我自己研究了这么多年,在我成长道路上比较深刻地体会到,如果我能够把自己的事业和整个民族、国家的事业联系在一块,往往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在图书馆学这方面,1956年到1967年十二年的科学研究规划里面,图书馆学科学规划项目里面就有一个“中国图书馆事业史”这个项目。1959年叫我开这个课,可能看到我文史方面还有点基础,以后就结合自己爱好做了这个工作。第一次发表在学报的文章就是《关于图书馆事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里面如果从研究图书馆的历史来看,它应该是属于什么性质的,它应该包括哪些内容,还包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而且我还涉及了中国图书馆发展史的分期。这个分期和意见,有段时间还算一家。从讲课内容来看,1959年还是比较粗糙,1962年就比较充实了。特别是1963年,当时写一篇文章叫《论古越藏书楼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上的地位》,中国图书馆学会编的《百年文萃》一套书,把我的这篇文章也选进去了。我们做研究,如果说你在这个领域里面有一两篇文章在几十年以后人们感到你这篇文章还站得住,那你就可以了。不可能你写的文章都好,那是不可能的事。其次还感到很重要的,自己要努力要坚持。有些时候,像60、70年代的时候我搞的书的研究,当时全国人民都在研究鲁迅,我去研究鲁迅的版本。我还到上海、到绍兴各地去调查鲁迅博物馆的藏本,以后写了两篇文章在学报上发表。所以说自己要坚持。再还有个体会也是很重要,就是如果研究一个方向的话,应该有短期的计划和长期的想法。在中国古代叫作古代藏书,中国图书馆历史方面来看,我在这方面做的工作是有点系统。你看教科书《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现在是第三版,一直在修订;专著就是傅璇琮(中华书局的总编)和我两人合编的一本叫《中国藏书通史》,2001年曾经得过中国图书奖,这本书现在已经十几年了,特色还很明显。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研究这一点来看,实际上我比较集中地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搞成一个系列,有教科书、有专著、有通俗读物,还有教学大纲和教材;第二个就是我重点对古代私人藏书方面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达到了系统化。(我)对整个藏书文化这方面大致有几个观点,在国内还是得到肯定的。一方面,古代藏书,集中到明清两代,像明清两代的私人藏书,我写了好些文章。另一方面,就是对近代图书馆我做了系统的研究。近代图书馆,这个时期的图书馆一定意义上来看,实际上我们中国的所谓近代的这种图书馆比较多是西方的形式,还有当时包括图书馆三个字都是从日本传来的。近代社会中国长期以来封建社会藏书逐步衰落,近代图书馆在近代社会文化这种条件下获得逐步发展。所以我把它当成一个研究的重点,一直发表一些看法,比如说我谈到的辛亥革命对图书馆是有影响的。近代图书馆兴起,藏书研究成为我研究的主要东西,发表一些文章,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因为本身我们在研究古代藏书楼,包括一些我们接触的文献,其中提到目录,因为他们藏书家所进行的工作实际上就是,要么鉴定版本,要么就编成目录、写成题跋,要么就是出版图书。目录在目录学的发展来说当然很重要。
1978年彭斐章老师和我两个人开始招目录学的研究生,参加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目录学概论》,然后从事文学文献学的教学,有些时候叫文献目录学,所以这样我的重点就转向专科目录。专科目录里面除了文学目录,还有个地方文献目录,这个我接触比较多。地方文献主要是地方志,我曾经是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曾经给他们讲过地方文献。因为1963年的时候吕绍虞先生给我们同学开的一个选修课是地方文献,当时我跟着当助教,教授在上课我们在下面帮忙,我听了地方文献(方面的)一些课程,1976年差不多有年把时间接触湖北省的地方志。199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在地方文献方面由我写两个条目,一个是“地方文献目录”书目,另一个是“方志目录”,我还写了篇比较长的文章在《中国地方志通讯》上全文刊载。除了参加这些研究,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里面分了几个专门委员会,我是目录学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从第一届开始,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做了四届的主任委员。目录学这一点上,很重要的是和彭斐章老师合作写的几篇文章在整个研究领域里面曾经起过很重要的作用。普通目录学当时和彭老师曾经有段合作以后,他就比较着重普通目录学这方面,我就专攻专科目录学,上面提到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我是目录学分支的副主编。
文献学。从比较大的范围来看,感觉我们文化传承的发展各方面来看,文献恰恰和整个社会发展上面联系得非常紧密。我主要做了两个工作,一个是梳理了从古代到近代文献观念上的一些变化,在《图书情报工作》发表了文章;另一个是在理论上探讨了一下文献和社会,在《武汉大学学报》发表过很长的文章。我主要从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研究(社会)和文献的这个关系。因为社会发展必然出现有什么制度、有什么文献,可能是扶植它或者是消灭它。和文献学有关的就是参加了三个五年计划关于社会科学方面的信息咨询工作,全国的一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指南”,其中文献学是我写的。当时是80年代后期90年代,算是当时研究报告的一部分。怎么认识文献的发展、观念的变化,以及文献和整个社会的联系,这些方面我做了些研究。这些研究有些是通过写文章,有些通过专门著作,还有些是通过会议的形式来宣传自己的材料。刚才说到图书馆有目录学,包括文献学各方面,我对自己评价往往把图书馆学看成和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相联系的。所以为什么我有几点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当时我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从文化角度来看待图书和图书馆的发展,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图书和图书馆发展的历史,所以这样来写的。图书馆学我把它看作是整个大的文化发展影响和推进的过程,最后形成的。谈到教学,包括学术上的一些观点,我和其他一些图书馆学家可能有些不太一样。(这和我)我自己接触到,包括我自己的文化修养上面比较宽有些关系,这是一个方面;研究过程还有第二个体会感到你必须写东西,你有什么见解你要把它写出来。我比较喜欢动笔,本身写作过程是提高自己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 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还特别注重对一些名家进行研究,比如皮高品先生,还有很多藏书家。为什么选择对人的研究?
对一些图书馆学家的研究,我做了这么一些:杜定友、李小缘、刘国钧、王重民、皮高品先生。近代的这些图书馆学家,我感到他们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我通过对他们一些著作的研究,写了一些文章。从这些人的研究过程自己学到些东西。比如说杜定友先生,杜定友先生在中国图书馆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对他的专业领域专注、全面、反应快,理论联系实际。他这个人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是收藏图书,他当时点名把他的著作全部送给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我回广东去访问他,把杜定友先生赠送给武大的这些东西带一部分回来,用藤箱子提了一箱子他的著作,有些是很好的,比如菲律宾得的学位论文,很珍贵的,还有包括他的著作出版物,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的第一版的,当时都有。还有一套是自己用小木头筷子做成书架、阅览桌子、阅览椅子等,还有阅览桌子上面转动的像书架一样的东西,就是整个图书馆的用品,他把它做成那个样品。我们一看就知道,都在那个箱子里面。我提回来就交给系里面了。非常可惜的是我们系搬了好几次家,每次搬的过程中这套东西就慢慢散失,要恢复那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