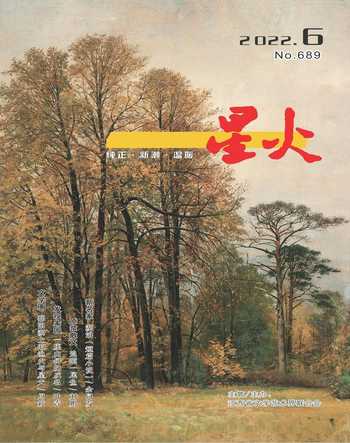素珍姑娘的深山集市
2022-11-10夏海琴
夏海琴
去石仑上的路,车道弯转,山影重叠,车速只能在四五十迈以内兜兜转转。车窗外路人的喊话清晰可辨:“去咯,去石仑上噢!”一个村民在邀人同去石仑上干农活。
石仑上在罗溪乡最偏远的朱家山上。罗溪乡又在武宁县西南部的九岭深山里,和宜春市靖安县接壤。从石仑上翻过几个山头,开车只需要十分钟即可抵达靖安境内。
我和那两个村民是同路人,石仑上是我此行的目的地。他们是去干农活赚工钱,我是去寻访一位叫李素珍的姑娘。
第一次见到素珍是在她的农庄里开谷雨诗会,朱家山上鲜红的杜鹃花正在怒放。她一大早就在附近的山里砍来许多杜鹃,插在一排黑褐色石头垒起的老院墙旁边,院墙上爬满了青苔和藤蔓植物。倘若摆上其他的盆景便显得俗气,插上杜鹃倒宛若天成,这般审美让我对这位姑娘充满好感。
当天诗会上,本地青年作家张雷用罗溪方言朗读了她即兴写的一首诗,那一声呼唤:“去回(归家的意思),去回,去罗溪。”那一声母亲唤你回家的调子的模拟:“崽俚呀,回哦,吃饭喏。”伴随着老屋升起的青烟,在场的人无不动容甚至哽咽。那一刻我情绪激动,她的农庄凝结了我的乡愁,但我是在远离了农村生活后才去怀念和赞美。
罗溪乡被群山环绕,平整的土地很稀少。罗溪人拥有和其他山里人相同的技能—开垦梯田。自古以来,天南地北的山里人都有这样的本领。这种技能最早是如何传播的?为了生存,不同的山里人开发出相同的智慧,在人类发展史上,这样的不约而同大概多不胜举。
关于梯田,罗溪流传着一个笑谈:有人种了一百块田,插完秧后清点一下,数来数去,发现只有九十九块,还有一块怎么都找不着,他拿起斗笠准备回家,发现最后一块田竟在斗笠下面。
这当然是罗溪人的幽默。但罗溪地少山多却是个不争的事实,大家不浪费任何一寸可以耕种的土地,仅能容下几十株水稻的梯田这里并不少见。村民们随手往家门口一指,那些很小的梯田都被划为基本农田管理保护。山里温度低,稻谷生长周期长,冷水梯田一年只能孕育一季稻谷。虽然山里种出来的大米软香可口,远近闻名,但是产量不高,加上交通闭塞、人口增长,穷困是必然现象。几十年来,罗溪人陆续外出寻找机会,都形成了一种风气,但凡能在外面立足生活,就不再选择回乡。所以这里的老屋很多,这里的村庄没有太大的扩张。
在这样的地方搞农业开发,不仅耕种成本高,产量低,劳动力也不好找,投资者有着怎样的胆量和眼光?这个姑娘是不是和我一样混淆了田园和农村的真实概念?这是我一路上都在揣度的问题。
素珍的父亲是已经离开农村进城生活的那一代人,是县乡村振兴局退休的老干部。素珍原本也离开了农村,八〇后的她从省卫校毕业后,把两个妹妹带去浙江做市政工程,业绩可观。在父亲退休后,她却接过乡村振兴的接力棒,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这既是机缘巧合,也有一种传承的味道。
饮食习惯是每个人不需要费力就能轻易保留的习惯,味蕾在无形间掌控了她的创业方向,用一个个微妙的契机将她引领回乡。在外面做生意的時候,素珍总惦记着老家的土特产,每次回来都要带上许多土货去给朋友和客户分享,大家都赞不绝口。三年前父亲退休了,作为长女的她,和妹妹们商量,公司留给她们继续经营,自己回乡探索农业项目,推广老家的特色农产品,刚好也方便照顾父母。
乡村振兴不是将整个农村理想化、牧歌化,而是需要给乡村注入长久发展的力量,并且让老百姓有抗风险的能力,既过得了丰年,也受得住荒年,这需要长远谋划,还要有能跟上时代步伐的年轻人回乡助力。
素珍的归来,无疑是受到当地村民和政府极大欢迎的。
她在老家出生,但不在老家成长。老家对她而言,只是精神上的故乡,并未分给她一方田地,也没有一砖半瓦属于她。当她选择回来后,村庄和乡亲们接纳了这个孩子,他们将自己闲置的老屋租给了她,将田地和山场交给她打理。第一年,大家没指望她能干出什么名堂,就像对待自家的孩子一样宽容,允许她失败。
她慢慢地把房子一栋一栋修整,原来的土坯房刷上了新黄泥;那些被废弃的罐子坛子种上闲花野草摆在墙下,坍塌的院墙重新用当地山里特有的黑褐色石头筑好;在小溪上架起了木头廊桥,桥头又搭起几间小木屋;直播带货间打造成荷兰风车的造型,可以爬到风车上方仰望星空。不远处的南山尖上,铺满了童话般的草甸。
她的农庄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注意,乡政府希望她能增加配套功能,把农家饭馆经营起来。可她这餐馆不像餐馆,就是自家的厨房,来了客人,就地取材,有什么做什么。春天的时候,她摘到什么野菜就给大家做什么,非常随意,又常常让人惊喜,多少人在她的厨房里吃到了多年未曾回味的家乡菜。春季的小竹笋晒干后,到了冬天配上腊肉,在小火炉上炖着,下饭也下酒。冬天霜降后的萝卜又水灵又脆,配上山里的牛羊肉是滋补佳肴。萝卜多得吃不完,切一切,晾一下,只需少量的盐和辣椒粉做配料,就可以腌成又脆又甜的萝卜干。鱼腥草随手在水沟边撸一把,搁在院墙上晒干,需要时就拿来煮水喝,代替了消炎药。她一双灵巧的手,把这些活做得熨熨帖帖,让她的厨房里飘出踏踏实实的人间烟火气。无心插柳柳成荫,饭馆生意非常好,短期内竟然成了主营业务。大家都快忘了她身后还经营有稻田和果园,以及农副产品的加工。
这里的土地主宰着生活节奏,世世代代的人都过着慢生活。所有的农作物生长周期都要比山外的长,享受了充足的阳光雨露后,瓜果蔬菜变得格外香甜。老人家总说这里的米饭不要菜都能吃三碗,这绝对是对罗溪大米最好的形容词。神仙叶、水蕨柳、小竹笋是当地人饭桌上的家常菜。石耳对生长环境格外挑剔,要长在干净裸露的岩石上,最好是硅质岩,岩石还要有水汽经常滋润,产量稀少,采摘艰难,兼具美食和药材的功效,这种珍稀物种在罗溪变得家常,在这里,石耳肉丸汤很容易就能吃到。南山尖上的草甸是村民的牧场,野生茶叶简单制作一番便清香回甘,猕猴桃和八月灿九月黄是纯天然无公害水果,从来不需要人工干预,到了季节,就去山里采摘。这是罗溪传统的生活节奏,大家遵循着节气过日子,老一辈的人明白,急也没用,他们活得像庄子笔下的人物一样,安身立命。
素珍显然把外面的快节奏生活带进了山里,她忙于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做了三、四月的事,八、九月才会给她答案。她要努力经营当下,直至未来明朗。
我去找她的时候,虽已提前预约,但她忙得没有时间迎接我。几条小土狗懒懒地卧在地上,见我来了,狐疑地围着我绕了几圈。其中一条小土狗前几日患了病,素珍抱着它去镇里找兽医,兽医说他只有给猪看病的药,在乡下没有人会给一只小土狗看病。她只好买了猪吃的药来喂狗,假如不能奏效,她准备把小土狗带到县城的宠物医院去看。在素珍看来,每个生命都可贵,与品种无关,她珍惜着属于她的一切。
我像造访亲朋一样,闻着香气,钻进厨房去寻她。她已备好了菜等我,黄瓜豆角茄子苦瓜,都是她种的菜,她的菜地完全可以供应饭庄的日常需求。还养了几头猪,一大群鸡。在她看来,这才是农村生活的合理模式。厨房剩余饭菜养猪,猪圈里的农家肥肥沃了土地,土地慷慨的馈赠又满足了厨房所需。鸡群散养在竹林和树林间,林间的杂草和丰富的昆虫让它们每日都忙于低头啄食,鸡群的粪便也为林子提供了天然肥料。这是一个良性循环,避免了食物的浪费和垃圾的产生,自从有农耕文明以来,已延续了几千年。然而近年来的农村,家禽和牲畜已经越来越罕见,新式楼房没有它们的容身之处,年轻的主人也不屑于养鸡饲狗,没有鸡鸣犬吠的村子总觉得少了几分生气。
对于我的来访,素珍并不太在意,就像她的性格,只勤于埋头做事,并不热衷宣传自己,至今我未在媒体上看过关于她的报道。
她在刨黄瓜皮,我就在旁边跟她聊天,顺手掰了半个咬起来。我还没啃完黄瓜,她又端出一篓秋葵对着山泉水像给孩子搓澡一样一个个洗得滑溜溜;这边我才刚帮她捡起被水冲走的秋葵,那边她又转身去了砧板前咔嚓咔嚓切着菜。我的目光远不及她的手脚麻利,只好作罢,等她忙完再聊。
暮色四合,群山沉寂,她终于有时间主动来找我聊天。我们在她的农庄里散步,月亮从山谷升起,几片薄薄的彩云如纱飘动,星星在云彩中轻拢慢移,月光下的廊橋显得非常浪漫。我说她的农庄满足了我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从小我就喜欢被我妈喊去菜地里摘菜,去挖红薯,挖花生,大多果蔬是摘来就能生吃的,那种收获感给我极大的满足,犹如婴儿吸饱了乳汁后的快乐。她说假如让你天天做这些,你未必就喜欢了。我不置可否,“种豆南山下”“乐与数晨夕”毕竟是一种被我加了滤镜的理想化生活。我和她的区别在于我只会肤浅地向往诗意栖居,而她却有创造诗意生活的能力。
素珍外出多年,但乡音不改。罗溪人一说起罗溪话舌头便活泛起来,这种像含着石头说话的口音,如果不是有着本地的基因,外人很难模仿。方言总让人乐于交流,我喜欢听她用罗溪话给我介绍她的生活。
琐事太多,田间地头,灶前灶后,她忙得团团转。田里种了水稻,果园里有不同季节的水果,地里有花生,各种蔬菜,它们依着各自的节奏生长,该开花的开花,该结果的结果,这可忙坏了素珍,一年到头都有农活要干。既要学农业方面的技术知识,又要管理工人,里里外外都是她一个人在操持,许多事情不得不亲力亲为。我总觉得她不像是在创业,而像小鸟衔枝筑巢一样,是在给自己打造一个温暖富足的家。
我问她平时累不累。她说累是累的,但那仅仅是身体的累,脑子里却很放松,生活节奏大多时候由自己掌握,每天晚上早早地和整个村庄一起睡去,清晨在蛙鸣鸟叫中苏醒。生活的环境和吃的东西都很健康。
相比第一次看见她的印象,如今的她黝黑了不少,衣着朴素,一条麻花辫简单地约束着头发,没有任何化妆品的修饰,整个人焕发着一种质朴干净的美。
搞农业项目,事实上是一件非常寂寞的事,漫长的回本周期,投资者要有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大多数搞农业开发的都是男人。一个瘦瘦弱弱的女子,在这深山里,顶着巨大的资金周转压力和身体上的劳累,一干就是三年。她做的事业和她的身形有着强烈的对比,我惊讶于这样的反差。
寂寞只是我矫情的表达习惯,事实上素珍几乎没有时间“寂寞”。
第一年打造基地,她要卖自己种的东西,而不是像许多搞农产品加工的人那样只是收购和贴标签。她把附近的土地都流转了过来,签订了三十年的合同,房屋租了十五年。
第二年开始种果树、水稻,经营她的饭庄。每年从五月到十月忙于水稻播种、管理、收割。果园目前已有红心火龙果、百香果、海棠、蓝莓、樱桃等品种初具规模。她把附近年过半百在外不好找工作的闲散劳动力和老家亲戚都雇来帮她打理果园,种田种菜,我在路上遇到的那两个扛着农具的村民就是她请的工人。饭庄厨师则是村里红白喜事时掌厨的大厨官,最好吃的菜往往出自她们的手艺。
素珍要把这里打造成一个“四季有花,四季有果”的地方,每次县里林业、农业、乡村振兴、就业等部门开展技能培训她都亲自去学,学完了回来再教给工人。县里搞农业开发的人都有抱团理念,大家互相帮忙,取长补短,这给了素珍极大的温暖。
因果树的丰果期还未到来,趁这空档,第三年开始打造民宿。陆续建造了几栋小木屋,把老房子装修成客房,如今可以接待十几个人住宿。
这三年来可谓一步一个脚印,她有一个“三五八”规划蓝图,三年打基础,五年保持收支平衡,八年开始盈利。
假设梦想和现实衔接时毫无矛盾和冲突,生活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每一个回乡创业的人必定都经历了各种考验。
她从小在城镇生活,钢筋水泥隔离了土地,也阻断了蚊虫的侵扰。回到山里,第一关就是身体上的不适应,被蚊虫叮咬后浑身过敏,红肿胀痛难以忍受。在城里习惯了群居生活,山里人家都是独门独户且平日里没有年轻人常住,白天充满温情和年代感的老屋一到了晚上,就空旷幽静得让人发怵,加上当地的老婆婆老公公们又擅长讲神讲鬼,吓得她一到了夜晚就寻着姑姑做伴,寸步不敢离。
三年下来,身体层面早就适应了农村的生活,皮肤变得黝黑健康,还星星点点地分布着晒斑,蚊虫叮咬已无法让她的肌肤产生变态反应,晚上敢一个人出入在村里,单独住一栋房子也能安然入睡。
最让她伤感的是她回村创业过程中遭受的非议。因素珍未成家,单独做这么大规模的农业项目,有不少村民质疑她的资金来源“不光彩、不干净”。聊起这个话题时,她的眼圈有那么一瞬间是红的,但是她在抹汗水的时候把眼眶里的泪水也一并抹去了,这个动作细节让我看到了她的坚强。她说这些流言曾经让她哭了好几次,好在老父亲一直在山里陪伴她,鼓励她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她的姐妹们也一直支持她,需要资金周转时,她们就挤出一些钱给她投资,她说以后有能力再还,还不了的时候就当她们是入股了。入股意味着风险共担,从这句话可以听出她们姐妹情深。
未来几年里,她不打算盲目扩张,不想给自己和家人太大的经济压力,如果每天睁开眼就想着怎么快速赚钱还债,这违背了自己的规划,也不是自己喜欢的生活状态。先稳打稳扎,把已经开拓的土地和项目精耕细作,争取早日实现收支平衡,这是她当前给自己设定的近景规划。
我问她为何不通过政府和相关部门多争取一些项目资金扶持,她说自己不善于人际交往,不习惯去经营各种关系。再者她也深知,整合了各种项目资金,必定要迎合項目要求进行打造,农庄就不能按照她的规划来发展,她想坚持自己的理念和审美。
尽管目标很坚定,方向也很明确,但也会经常涌现出新的烦恼。农村宅基地交易和使用有严格要求,打造好的民宿是租来的房子,使用期限并不长。并且当地有不少人见村子被她打造得有模有样,就有了房屋到期后不再出租的念头。房屋之间的间隙原本是村子最好的留白,但大家伙有要建集体祠堂的计划,这个计划的落地必将破坏农庄整体的美感。这些都是素珍一己之力无法解决的困扰。她一想到十来年后就要将自己一点一滴修缮好的农庄忍痛割爱归还给当地村民,不免踌躇伤感。
素珍把她的农庄取名为“深山集市”,她希望能把家乡的农副产品和美好风光通过直播的方式介绍给大家,为家乡打造一个线上集市。如今山里的村民纷纷将自家晒的干菜,山里挖的葛根粉、蜂蜜等农副产品送来托付素珍帮忙卖出去,素珍一一答应,热情帮忙。
但带货过程中也有不少事情让她颇为头疼。有时候乡亲拿来的农副产品会短斤少两,以次充好。明明付了二十斤葛根粉的钱,货拿到手后只有十七斤,并且还掺了不少红薯粉。明明订的是今年新晒的梅干菜,拿来后却发现只有上面一层是新的,底下全是掺杂着沙石的陈年梅干菜。遇到这样的情况她选择默默吃下这些哑巴亏,乡里乡亲的她无法开口去退货,人情大于生意。
这让我想起住在朱家山另一个屋场的一位远房亲戚,他曾经是这山里拥有田地最多的人家,别人只要遇到急事需要钱,就把田地卖给他,他也不管田地是好是差,是远是近,只要别人开口,统统都买。家人不解,问他为何有些田地又远又贫瘠也还要买来,买货总归要挑选一下吧?他说:“乡里乡亲的,别人有难,我们给钱帮忙都是应该的,何况人家还有东西卖给你,为何不帮?”
这同一方水土养育出来的人,不管隔了多少代,果然都是相同的秉性。
告别素珍的时候,她在水池前洗碗,我们用简单的言语代替了迎来送往的寒暄。她没有停止手上的动作,只是目送我,目光柔和而坚定,我知道她的回乡行为是理性的选择,绝对不是像我这样只是为了急于表达自己的向往。我只是结束一次短暂的归乡体验,而她将继续留在深山里自足又孤独地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