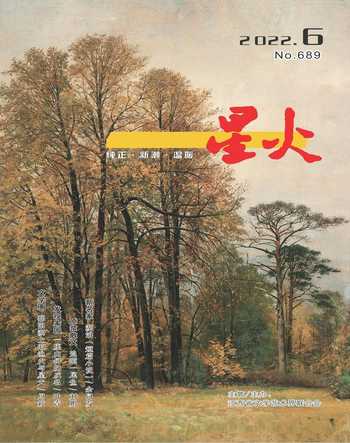九十六天
2022-11-10李冬凤
一
小城进入朦朦胧胧的夜色,与友相约美食城。
我低估了小城人对美食的追寻。偌大的广场人与车乱作一团,喧闹声爆棚。
电话打进来了,我找了一个人车相对较少的路灯下接电话,影子被路灯拉得老长。
突然,“咚”的一声响,声音很沉闷。出啥事了?我愕然。接着是“嘎—”的长音,车轮摩擦地面的声音。有人喊,撞人了。我脑子里想,撞谁了?有人冲我喊,没事吧?还向我伸出手。所有的喊叫声和脚步声都向我涌来。
撞倒的人居然是我。我脸瞬间臊红。大庭广众之下,躺在地上,着实难堪。我想站起来,逃离所有人的视线,可是,我的右脚不听使唤,疼痛也迅即向我袭来,从大腿蔓延至全身。右脚肯定断了!恐惧和眼泪形成了第二轮冲击波,彻底将我击倒。我这辈子……
有人要打110,也有人要打120,还有人要打保险公司的电话。有人说,救人要紧,先打120。有人说,不行,保险公司要看现场。还有人说,有病吧,不报警,谁来处理交通纠纷?众人七嘴八舌,我成了待宰羔羊。
我努力用左脚和左手支撑起身体,寻找我的手机。关节的撕裂痛得我龇牙咧嘴。我终于看到了摔出一丈多远的手机。我对正在争论先给哪里打电话的那群人说,别争了,好吗?帮我把手机捡过来。他们没有理我,看我的目光很冷漠。终于有一个旁观者听到了我可怜的求助,捡起我的电话,轻轻放在我手上。
“喂,喂,喂。”刚才的电话居然没有挂断,我小弟一直在那头喊。我说,老弟,我被车撞了,在美食城。
小弟憨厚老实。想到撞我的那伙人,他一个人做后援显然不够。我又打了几个电话,居然都没人接。人要是倒霉,没一个事能顺利。我再也坚持不住了,进入昏沉状态。
救护车的灯很亮,强行进入了我昏睡的世界。我醒了,睁开眼,眼前是一个闺蜜的脸。我问,这是去哪?闺蜜说,中医院。我随即想起,中医院的骨伤科非常强。很庆幸,我脑子没被撞坏,还能想起这些。这是我遇到的最大灾难,我的潜意识一直在丈量我与死亡的距离。
我被抬下救护车,嘈杂的脚步跑起来,带着风,深秋的夜更加凉了。四轮车穿过漆黑,向左拐,又向右拐,又向左拐,弯弯绕绕,这是推我去哪?我已身不由己。
灯,异常亮,如白昼。我被抬上冰冷的铁板,接受射线的穿透。医生在外面说,股骨粉碎。又说,股骨碎成了三节,很严重!摆到45°角,再拍一张。这时,有一双手向我伸来。我在极度恐慌中反抗,不要动我。声音肯定达到了一千分贝。医生说,占院长电话交代了,他一会儿就过来。我想起来了,在救护车上我曾给占院长打过一个电话,他是骨伤科最好的医生。我有些蛮不讲理地说,那就等他来。对未知的恐惧让我的心变得非常脆弱,就如一张薄纸,风吹即破。我闭上眼睛,浑身发抖,静静地等待。
占院长终于来了,他手脚麻利,帮我正骨,复位,动作干净利落,尽管有钻心的疼痛,但时间很短。
我又被推进了弯弯曲曲的廊道。这时吼叫声、询问声、脚步声、推车声,从廊道尽头向我奔涌而来。谁撞的?站出来,瞎了眼吗?这是我亲人的声音。我不难想象,此刻的他一定是怒目圆睁,凶猛得像一只老虎。其实,他就是一只轻轻一戳就破的纸老虎。我大弟弟也在喊,撞人还有理了?去缴费,办住院!大弟弟一般不吼,这是被逼急了。小弟在带着哭腔打电话喊人,姐被车撞了,在中医院抢救,快点来,好严重!
我很沮丧,怎么就成了众矢之的。
二
我被抬上病床。四个男人摁住我。右脚被拉得笔直。医生的手在膝盖处摸索,然后捏住两个点,擦上麻药,拿起锤子,一根长长的钢钉被敲进膝盖骨。我如被杀的猪临死前一样嚎叫。我的亲人不忍直视,躲到门外去了。钢钉两头是直角支架,钢索连着支架,固定在床上,钢索下吊着沉重的砝码。我被牢牢锁在床上,无法动弹。
哥哥进来问,报警没?有人答,好像没有,当时只顾着救人。哥哥叫来交警,小弟随警官去调现场监控。
疼痛,一夜无眠。
天亮了,病房进出的人多了起来。护士量体温,测血压,抽血,做例行检查。接着是医生进来,一长串,主任、副主任、负责床位的医生例行会诊。然后是家人亲人友人进来。疼痛被揉作一团,让我麻木了。点滴挂了二十四小时,没有间歇。医生说,碎裂的骨头插入肉中,内出血严重,又无外伤,淤血无法排出,很容易淤堵,形成血栓。骨折不会要命,血栓却是“催命符”。
一切渐归平静。病房的白炽灯下,几捧鲜花散发着淡淡的清香。点滴依然挂着,冰凉的液体缓缓流进我的体内,一种悲凉油然而生。我怎么就躺在这儿了?是谁让我躺在这儿?为什么至今无人给我一个说法?我的火气上来了,摸出手机。我绝不许邪恶盛行。
有一首诗说,向天空钉钉子,一锤,一锤,越来越准,越来越狠……我不知道天空有没有疼痛感,却知道钉子钉进骨头,钉进血肉之躯,痛是从心尖尖上开始渗进每一个細胞,呼吸都是痛的。这样的痛持续了三天,且与日俱增。痛有多深,恨就有多强烈。
护士说,账上没钱了,明天要停药。
医生也进来提醒,已经预约了省里的专家,三天后做大手术,骨头碎得太厉害了。还要做好输血准备,要准备好髓内钉,主要还是准备好费用。
弟弟打电话,让撞我的人来医院交钱。对面的人在电话里吼,钱?老子有的是钱,有种就开车到港头来拿。我怎么就这么善良,没撞死你!
我气得七孔冒烟。后来是与乡政府沟通,逼他父亲现身,才交了一部分住院费。
三
牵引是骨伤治疗最常用最有效的办法,也是最残忍的做法。人几乎是倒立而卧。最初,我并未在意。第二天隐隐感觉不对,原来是尿意爆满。下床是不可能的,接盆又上低下高。闺蜜说,只能用纸尿裤。
我双手紧紧抓住吊环,努力抬起下半身。闺蜜从左边一点点地塞入纸尿片,又在右边一点点地掏出纸尿片,再倒转,遮住该遮盖的地方。在基本生理需求面前,颜面和自尊已没有意义。纸尿裤用了六天,我仍无法适应自如。我渐渐对尿意有一种恐慌。接着又遇上一个大问题,腹胀,大便出不来。吃香蕉,喝蜂蜜水,开药贴肚脐眼,都没有用。闺蜜让吃火龙果,也毫无用处。医生查房时说,可以请护理帮你揉捏,加速肠胃蠕动。要保证下身干爽,防止褥疮。闺蜜中恰好有一个专业护理。她间隔两个小时就给我按压腰部、腹部和肩部。身子转不了,她就把手伸进去揉。每次解决完小问题和大问题之后,又帮我用清水擦拭。我是家中唯一的女孩,这些“私密”活全落在我的“闺蜜团”身上,连着几天,她们衣不解带,都满脸倦容。
占院长拿着片子与我商量。股骨粉碎手术,他做过很多。用微创法,可以有效减少骨膜剥离,用髓内钉固定。骨膜损害少,血运供给就好,骨骼恢复就快。我反复问,你能确保手术万无一失么?能保证我正常走路么?他说,不能保证。你和家人商量,也可以请省里专家来做!大弟媳说,也别请什么专家,直接去上海做手术。武汉也行。
人躺在病床上,最不吝啬的就是钱。我情绪不受控制地吼起来,我不转院,我相信占院长。两个弟弟直愣愣地看着我,有点不解。我说,不是钱,是痛。转院又得搬动我。我闭上眼睛,泪水滚落下来。当然,占院长也有很多让我相信的理由。
这时,医生要把我从普通病房挪到VIP病房—骨科一号。那里是骨伤科最好的病房。
我大叫,不要,我不要换床!谁来拉伸我的腿,疼!
人很奇怪,腿拉伸了一个星期,现在不拉还不行。
医生说,不换床也得移动,还要去做检查,为手术做准备。
占院长拿着片子还没有离开,他在等我回答。我问,省里设备是不是比我们先进?占院长说,完成这样的手术,用不上先进的设备。就这手术,和省城没有区别。我又问,省城有什么优势?占院长说,见得多,做得多,更游刃有余。我说,我选择相信你,能不能请省城专家来?占院长说,能。专家出诊要收出诊费。我说,专家费我出。
我不知道很多人什么时候开始不相信医生,但我却从他们眼里看到了生命最初留下来的一丝亮光。
四
拉开窗帘,阳光满地,又是一天。专家已从南昌出发,我也从病房被推进了手术室。
专家是省一附医院的医生,出诊费五千,与其级别相比,算是友情价。他只是一个指导老师,不亲自操刀。手术室里灯光刺得我睁不开眼。护士给我插上氧气管,并用一张纸把我脸蒙住。麻醉师进来问护士,体重?病史?过敏史?护士回,体重106,无病史,无过敏史。麻醉师用一根长长的弯弯的针从我颈动脉插入,麻药缓缓导入我体内。护士也在消毒,冰凉的消毒液从大腿根部往下流。我全身不自觉地发抖,脉搏跳得异常快。万一出不了手术室怎么办?儿女,父母,兄弟,闺蜜,还有保险柜里的小秘密,我还没有道别,还没有道谢,很多事没有安排。
我有些伤心。有声音问,专家到了么?有人回,快了。好,准备手术。再等会儿,病人还有意识。我有些不甘心,想努力保持清醒,可是眼皮不争气。我昏沉沉睡去。
…………
意识散乱,又有些迷糊,我困极了。一个声音说,盯着这个仪器,注意波段变化,一有不正常,就喊医生!
渐渐确定,我已经被送回病房。我庆幸自己还能醒来。
醒了,醒了!小姨抹着眼泪冲我说,吓到我们了。出手术室已经六个小时了。医生说你输了五瓶血。再不醒来,你妈也要跟你去了。我惨淡地笑,有那么久吗?我就小睡了一会。
晚上八点,麻醉震动棒药物耗尽。深夜,疼痛再次如洪水般袭来,且一浪高过一浪,右脚在不断地膨胀,似乎要迸裂。我撕心裂肺的喊叫声穿透门窗,穿透夜空。侄女不断用毛巾给我擦汗,又试图通过抚摸缓解我的疼痛,可是没用。她又去找值班护士,要来两粒止痛药,痛才渐渐退去,睡意随之而来。
术后第五天,我浑身乏力,体温37.5℃。占院长看着我闺蜜说,低烧是术后大忌。闺蜜有些愧疚地说,昨天推她去复查,没注意有穿堂风。又说我昨天帮她洗头了。我说,洗头是我坚持的,头发都沤馊了。占院长没有再追究,沉着脸要我开始做康复训练。他抓起枕头,墊高我大腿说,腿尽量往后缩,膝盖拱起来,然后再绷直。上午一百下,下午一百下,明天再加。
术后第六天,我勉强能进行支撑式的90度左侧身,右膝盖能微曲,右侧卧还是无法做到。深夜是痛魔的世界,痛感从右脚大拇指开始,到大腿根部,上蹿下跳,在膝盖骨附近逗留的时间最长。我没法不妥协,又吃下一粒止痛药。术后一周,肿胀的大腿肌肉开始松弛,手指在腿上滑走也有了感觉,缝针的部位也有了痒的感觉。护士长说,这是神经末梢在生长。
穿白大褂的小罗是占院长给我安排的康复师。他腰板笔直,走路迈着方步,沉稳有力,特像一个军人。他动作麻利,双手抬着我的脚,外拉内推,再做内旋外展,抬高压低,侧压膝盖。
侧压膝盖是我最害怕的动作,身体紧挨右边床沿,右脚伸出,交给医生。小罗医生用一只手托起我的小腿,另一只手握住脚踝,使劲下压,保持腿肚子贴住床沿。我双手紧抓床头边的铁杆,痛得额头上的汗赶趟儿流。这样的动作做满二十个,医生才放过我。
有时我觉得,铁石心肠莫过于医生。
五
霜降是秋的最后一个节令。阳光的威力已消耗殆尽。
入院二十天,熬过的苦比半辈子的苦加起来还多。疼痛渐渐远去,另一种痛又来了。
医院的账上又没钱了,交警的话似乎不管用,肇事者的钱像挤牙膏,挤一点出一点,最后一点都挤不出来。要钱?你上法院去,找保险公司去。家里人都窝着一肚子的火。我也窝火,不停地打电话,总想把肇事者逼到我面前,哪怕是你说一声对不起,我给你写感谢信,行不?可是,我所有的电话都石沉大海。
术后两周,可以拆“线”了。所谓的“线”,其实就是钉子。我不明白,这些如订书钉般的东西是如何钉进肉里的?用装修的气压枪?给我拆线的医生叫伍亮。他用镊子小心翼翼地拔,铁钉落在盘子声,丁当地响。我问,缝合为何不用线,而是用钉?他说,线缝合不平整,疤痕会更突出。气钉平整度高,疤痕修复快。缝合的钉果然是用气压枪射入我的肉体。
正聊着,修车的胖子表弟来看我。我这表弟是个狠角色。他对我很亲,姐上姐下叫个不停,人也大方,花钱如流水。我嫌他狠,有意疏远他。他全不计较,放下一大堆食物,不问我伤情,而是问,姐,谁干的?我也是窝的火没有出处,便把来龙去脉都告诉了他。他气得哇哇直叫,港头的?老子拆了他的骨头。我说,别乱来,拿钱来治伤就行。
他打了一通电话,最后锁定了一个目标。电话是免提。
儿子,你儿子把我姐撞了,还躲在家里装爷爷?听说还想轧死我姐?
胖子哥,没有的事。谁他妈的害我。
信不信,一分钟内我让你装孙子找不着地方。
胖子哥,我不知道是你姐。钱我马上送到,要多少给多少。
我姐心善,钱够用就行。好话不怕多。
遵命,胖子哥,你也心善。
胖子挂了电话,嘿嘿地笑,姐,妥了。
疙瘩解开了,我觉得心里那片天空也秋高气爽。
六
黑夜是一张巨网,网住喧嚣,网住嘈杂,网住一切有声的、无声的、有色的、无色的、有形的、无形的……无法网住的是痛苦。现在的疼痛不再汹涌,而是一寸一寸地咬噬。我知道疼痛与我在打持久战,或许要伴我终身。
医生说,康复进程是呈抛物线式的前进。我接受与否,都是这样。
术后第三周,科主任刘名帮我检查脚的后曲膝弯。我俯卧在病床上,努力后曲膝盖,想在医生面前表现得好些。刘名并不领情,用手捉住我的脚,这是要一抬一压。我惊恐大叫,不要掰,不要掰,我自己会练!他说,不掰。我刚放下戒备,他的手还是压了下去。我感觉膝盖内侧肌在撕裂。我又哭又叫,快放下,我的腿断了。他仿佛是聋子哑巴,依然持续地下压,直至停留在90度的点有一分钟之久才松开。我的泪水和汗水洇湿了一大片。
我也是一个有脾气的人,自从进了医院完全没了脾气。我先前不爱说,喜欢雷厉风行,现在在医院里不能行,却变得爱唠叨了,特别是一次疼痛之后更是喋喋不休,逢人便说,医院就是人间地狱,医生就是魔鬼。
刘名走后,占院长过来查房,我又对他唠叨。占院长说,CPM机上如果做到了120度,就可以不要强掰了。我哭笑不得,原来是被“魔鬼”盯上了。为了尽量不去惹“魔鬼”,我拼命地在机器上练习,我也想秀腿美步。闺蜜又帮我支招,把学过的瑜伽功用到康复中。背对椅子,右脚后抬搁在座位上,左脚直立,身子下压,双手支撑在她肩上。把康复训练当成练瑜伽,果然事半功倍。
医生说,膝弯110度是临界点。跨过这点,就可以无疼痛地继续深入弯曲,直至回到从前。他让我看到了希望,哪怕膝盖肿得像馒头,发烧发烫,我还是一边用冰块敷,一边继续训练。
七
母子连心。我入院后,儿子也变得焦躁不安,每天晚上都要和我打视频电话。只要不上课,他都会从景德镇赶来,帮我按摩脚。儿子的按摩自然对我是莫大的安慰,仿佛比止痛片还管用。儿子知道我是个闲不住的人,心总向着大自然,便哄我,天晴了,我背你去看鄱阳湖。我躺在病床上还特别爱听这话。
一个周三,阳光早早地爬满了窗台。我热切盼望的儿子出现了。儿子是裹着风进来的。
儿子背着我,尽管用手托着的我右边大腿部位有刺骨的痛,我也只敢龇牙咧嘴,不敢叫出声来,否则这次大自然之行就可能夭折。
初冬,鄱阳湖里的水丝毫没有隐退,依然浩瀚无垠。我坐在湖边大理石长凳上,仰着头,让阳光洒在脸上,人顿时就有了生机。早来的雁儿划破长空,一字排开,如画家不小心泼出的一点点墨,俊逸洒脱。几艘货轮从平静的湖面驶过,牵动了一湖的波光粼粼。蓼子花应该还在湖底沉睡,只能期待有缘时再见。所有的美好都不可常见。
术后三十八天了,切口的结痂已经脱落干净,颜色暗沉有结节,摸着也无痛感。
湖边的风已经有些寒意。我穿的衣服也有些单薄。儿子说,回去吧,有时间再来。我说,好。
晚上,闺蜜说,伤筋断骨,吃牛筋补筋,又是小雪节气,补也合时宜。便弄来一大砂缽炖牛脚筋,外加一高压锅炖白鹅,还搬了一箱白酒。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闺蜜又说,为曾经的痛苦煎熬,总算苦尽甘来,当举杯庆祝。于是众人把病房里的茶几拉开,椅子摆上,杯子满上,斗室变成了酒场。酒过三巡,闺蜜的话便都多了起来,滔滔不绝,满口人生哲理,让我一愣一愣的。
我说,我这个经历了大灾大难的人还没说呢!
闺蜜说,你闭嘴,别扫兴。
我真的便失去了说的兴趣。人还是活在自己的哲理里好。
八
我的复查结果很好,内侧碎裂的骨头已经向主骨靠近,并生长出了雾状。外侧碎裂的部分愈合得差一些,康复训练时,要尽可能减低内收肌的动作强度。从明天开始,伤肢要考虑适量负重。也就是迈右脚的时候,双拐上前,双臂下压,控制好身体,分一些重量到右脚。迈左脚时,可以自由承重。右脚,左脚,交替前进。我按医生的指导练习,走路像跳霹雳舞。
术后二月,我开始用单拐走路。
占院长考我,拄单拐,拐棍放伤肢,还是搁好肢?
我说,自然是在伤肢。
占院长笑而不答,他拿起拐,让我亲自体验。拐放左边胳肢窝,迈右脚,同时出拐,让拐承受身体重量,帮助右脚减负。再迈左脚,拐和右脚提起。居然是放在好脚一边更合适。
我的右脚功能康复基本及格,开始挑战人体最末端的动作—穿袜子。穿袜子牵扯到腕关节、膝关节和髋关节的屈曲。只有屈曲度达到足够时,才能协调完成。
昨晚下了一场雪,今天地面都结冰了。表姐清早从地里挖出了新鲜萝卜。萝卜很嫩,不刨皮,切成丝,用清油爆炒,再加上生姜大蒜辣椒,鲜美可口。鱼也是昨天买的,腌了一个晚上,今早用油炸,一块一块的,清清爽爽,加了小米椒,辣是辣些,但开胃,下饭刚好。这是表姐给我准备的午餐,就俩菜,真好!
我家表姐很多,不下十个。我和这个表姐好。我小时候经常去滨湖外婆家,跟着表姐去湖滩放牛,追赶捕捞的渔船,偷别人家的红薯花生,摘酸掉牙的橘子……干过不少坏事。有时也做好事。如给外婆捡拾满满一土蔸牛粪。湖边柴少,做饭烧牛粪。不过,烧牛粪做出来的饭真难吃。
吃完饭,我试着丢弃拐棍,用自己的双脚行走。表姐小心翼翼地在一旁“护驾”。我先从站立练起,左脚独立,右脚悬空外展,停留五分钟,再转换到右脚独立,身子摇摆厉害,肌肉僵硬,脚下意识绷得笔直。右脚独立时间无法超过三分钟,只能又换左脚独立,右脚做外旋,三十个。右脚内旋,又三十个。简单的动作,让我后背心被汗浸透。
双脚并立,稍作休息,右膝盖不能配合弯曲,髋关节无法协调,感觉伤脚比左脚长了。我哭丧着脸对查房医生说,我双脚不一样长了。医生让护士长找来绷带,让我躺平,用标准的测量方法,测量从耻骨到距骨的长度,长短一致。医生说,你感觉是不是一样长,或者说今后走路拐不拐,就看你恢复性训练了。我点点头。我每次在找医生的问题,最后问题都回到了自己身上。
我又像婴儿学走路一样,试着迈出右脚,左脚急急慌慌地跟上,唯恐右脚难以支撑。我迈出左脚,右脚则气定神闲。左右脚迈出的频率不一致,我成了十足的跛子。
九
二月余的禁足,家里一切都变得乱糟糟的,我的心性也在变。
平日里上班忙,走路急匆匆,做事急匆匆,回家弄个饭也是急匆匆。尽管都是急匆匆,生活的轨迹却很流畅。而我的右脚罢工之后,一切都像敲下暂停键。手机成了我与家里的专线。从来没管过家里柴米油盐的男人事事都要“请示”。到了做饭的时候,我的手机基本上都是热线。如粉蒸肉怎么做,我都说过很多遍了,男人就是不长记性。他干脆把手机免提放在案板上,做到哪问到哪。将五花肉切片,洒少许盐,倒大半包蒸肉粉,加入适量生抽,用手轻轻揉捏,使肉片沾满粉,再添一点火锅酸菜料,微辣,上锅,蒸一个小时。直到开锅,香气四溢,撒点大蒜。电话才能挂断。
男人问,送饭过去?
我说,不用了,我父母已经送饭来了。
父母加起来有一百五十岁,却从未停歇,除了张罗家里的一堆农事,还隔三差五走十多里路,再乘公交来医院送菜送饭。在他们眼里,我永远也长不大。
父母老了,一脸的沧桑让我想流泪。
十
“笃、笃、笃”,几声敲门声。我习惯性回应,进来。一个男人问,是李冬凤?我说,是。他说,有人送花给你!我很诧异,入院都有八十多天了,已经很久没有人送花。朋友的鲜花陪我熬过了最痛苦的时段,现在伤痛过去,谁还会送花?他说,里面有卡片。我一蹦一跳过去接过鲜花,迫不及待地拿出卡片。卡片上是一首诗:
湖水抚摸星子,松影伸进
消失的昨日。黑暗中,我们沉溺得太久了
如果我愿意,我可以
坐成一块石头,用切割后的嘴唇
说出痛苦,说出美
我也可以弯腰,树木一样,孤绝成
一种爱
而我们在黑暗中,沉溺得
太久了,星光,云层,还有
无数的风,汇聚到这里—
在这里,寂静满山,青草带着光芒
行走
它真绿啊—
翠绿得,就像我们的新生。
—灯灯
是灯灯,我只见过一次面的浙江诗人灯灯。我与诗人周玲去接她。她戴着鸭舌帽,大墨镜,一身牛仔服,双肩背包,长腿迈开,人就像一首诗。我们陪她在鄱阳湖北岸走了很多地方。
鄱阳湖北岸很多风景叠加起来也像一首诗。千眼桥从远古走来,逆着光,迎着风,往皱褶深处而去。影子被拉长,惊讶,消失在苍茫沙漠。我开车在诗中狂奔,大港的山路十八弯。灯灯说,她喜欢,狂野和奔放。我便任性地在重峦叠嶂中狂欢,在绿草青青的湖滩上狂欢。她还能像男人一样小酌两杯。
我不善于写诗,但喜欢灯灯,因为她的生命一直在燃烧,给人以温暖和力量。
灯灯的鲜花和诗尽管迟了些,却有益于我康复训练。
十一
已是滴水成冰的季节。
清早,母亲做了一大袋米粑来,口里呼出来的气如白烟。母亲说,今天是你的生日,生日要吃粑。粑的意思是“巴根”。母亲宠爱我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几十年都没变。村里人笑母亲是“穷人家养画眉”。有人溺爱是万年修来的福气。
我住院的骨科在四楼。骨科有三个清洁工,年龄相仿,都在六十岁以上。一个姓邵,一个姓陈,还有一个是我娘家的村里人,按辈分我喊她一声阿嫂。
其实入院的第三天,阿嫂就认出了我。她来我病房搞卫生,双手撑着拖把,杵在我房间说:“我看着你长大,上学时,背花布书包,扎两小辫子,个子小巧,好秀气……”乡下女人套近乎都喜欢翻老黄历。我无力接话,也不想接话,只是翻了翻白眼,瞄了她一眼。她身材中等,微胖,着一件蓝色清洁服,头发圈进蓝色帽子里,脸像大柿子,那种熟透后被风干又微露褐色斑点的柿子。
那天中午,阿嫂又出现了,她是进来倒垃圾。她轻手轻脚进来,站在我床前好一会儿没说话,我也没有说话。她看我不说话,也不敢说话,但我明显地感觉到她的喉咙里有话堵着。我男人正好提了开水瓶进来。她似乎找到了说话的机会。脚离身体最远,伤了气血运行难,容易怕冷!她喉咙堵的应该不是这句话。说完,她轻手轻脚带上门,出去了。不大一会儿,她又步履轻盈地进来说,我找了两个玻璃瓶,装了热水,搁你脚板这里,捂捂!接着,她慌不择路地出去了,我听见她磕碰到椅子的声音。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卑微的讨好?!只是不大明白,她为何要来讨好我?
她来的次数多了,遇上疼痛好些时,我便会与她搭几句腔。
她问,脚是不是特别痛?我给你捏捏。别觉我粗手粗脚,很多受伤的人都喜欢我捏,我一般不给人捏。阿嫂为了让我接受她的服务,努力把她的按摩说得更专业,就像她给地板“按摩”一样专业。我惊恐地躲避。
过了两天,她又来问,院领导说,你请护工?她脱下工作服。自家妹妹请,我愿意做,130块一天,别人请至少150。我还兼搞妹身上的卫生。请她护理?她那种喇叭嘴,我这病房里还有秘密吗?不要!我很冷漠地拒绝了她,没留一点情面。请人做事,还是嘴巴严实的好。我怕给她留面子,给自己埋祸害。
阿嫂沉默了好一会,然后叹了一口气说,我家的如果不出事,何须看人眼色!我开始后悔自己的态度,就是要拒绝,也该婉转一些,毕竟是一个村的阿嫂,要是传到村里,村里人还不知道如何鞭挞我。
阿嫂风光时我没有见过,落魄时我也没有见过。只是知道她丈夫原是乡里的干部,后来犯了错误,被开除回家。眼前的阿嫂也曾是一个“官太太”,就是精于算计,少了雍容华贵的气质。
我没请她做护理,阿嫂很失望。但依然每天来卫生间消毒,清扫地面,带走垃圾。只是不再与我主动套近乎,甚至对我冷淡如陌生人。
有一回,我去护士站,想称体重。护士站吵成了一锅粥,三个清洁工差点厮打起来。老邵说,13床的护工,是我请的,钱不能给你们。老陈说,死不要脸。明明是先找到我,再叫你去请。13床与我是一个村的。阿嫂骂,清扫垃圾从不倒干净,都是我倒,还好意思叫。房间里有纸箱子、空瓶子,眼睛都睁开了!老邵说,谁不要脸?冲上去,推了老陈一把又说,一把年纪还找男人,你知道要脸?老陈也推了老邵一把,男人在哪儿?阿嫂在玩浑水摸鱼,有就是有。老邵却是针锋相对,男人在你裤裆里,你敢脱裤子让人瞧瞧?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拉开阿嫂,让她去我房间。她站在我床前,一点看不出是刚吵完架的样子,眼睛盯着桌上一篮鸡蛋问,人送的?这年头还有人送鸡蛋,倒是新鲜!我原想劝劝阿嫂,这时没了劝她的心思,冷冷地说,我娘拿来的。阿嫂愣了愣说,你娘命好,子女个个有出息。我说,都六十多岁的人了,还争啥!阿嫂说,不争啥,做做便去死。
之后阿嫂很久没有进我的病房。或许是在回避我,又或许与我无话可说。她在时,我嫌煩,她不在,我又嫌寂寞。这些日子,我在想一个问题,阿嫂是做错了什么吗?似乎没有。我有些迷惘。
十二
过了新年,终于可以出院。
出院前,又做了一个复查,我康复得比预期要好。
我选了一个晴好的日子办了出院手续。被压榨的九十六天终于伸直了躯体,自由呼吸。尽管我还不能走直线,或许永远都难以走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