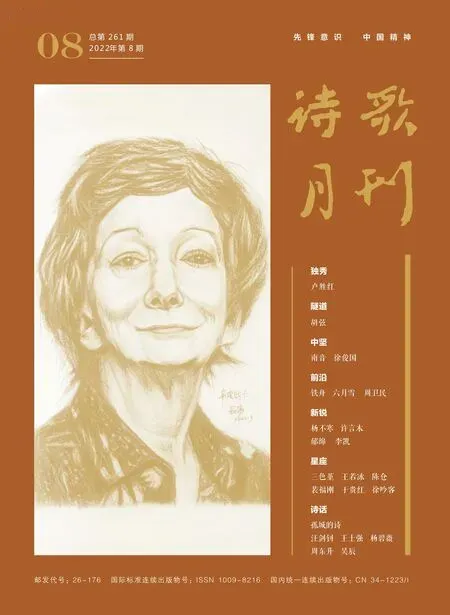访谈:从修辞的根基上釜底抽薪
2022-11-10南音徐俊国
南音 徐俊国
1.缘何写诗?
南音:2016 年春,偶然接触到几个诗人,然后跟他们一起习诗。起初,是有点懵懂的,但随着视野的不断打开、阅读的跟进,开始惊讶于诗歌的魅力。琐碎岁月中的苦闷、狂喜、忧郁……居然都可以放置其中。是的,当你最终沉浸于词语的迷宫,为一首诗所承载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而焦灼又兴奋时,你才意识到,这一次,你对了。你找到了平行于生活的另一条道路。它仿佛一直在等待着你进入。而你顺便也明白了其他:多年来的默默阅读和思考,都为这一刻而准备。
徐俊国:不为“缘何写诗”的“何”而写诗,我所有写诗的笨拙、静定、持久和赤诚,都不被“何”所限,我为自己获得的这种生命自由而写诗。诗激活了沉默寡言的我,鼓励我借助汉语的恩赐,饮鸩止渴般,无声而激烈地,一次次,再塑我的生命。那架母语租借给我的马车,我喜欢它在纸上颠簸前行时“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的即时性和在场感。
2.你的诗观是什么?
南音:基于真诚之下的终生探索吧。首先我还是相信,当表达的欲望在你的内心形成隐秘的涡流,你才愿意去写作。是你想说话的欲望在推动你的写作轨迹。当思考成为惯例,你其实还是会爱上写作这回事的,更何况诗歌这特定的形式,还被赋予了某种独特的技巧的趣味。在真诚的基础上,再有技巧的加持,我想你会在诗歌的光辉里徜徉终生。即便它没有成为志业,还是会以朋友的方式陪伴你。
徐俊国:再伟大的诗人、再好的诗观也只能砌出诗歌之一角,谈论诗观是一件很锋利的事,可能误伤自己和写作。我不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写作者,但我对自己的诗歌工作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和步骤。“鹅塘村” 系列是确立一个“大地诗人”的谦卑形象,留下一个诗人生而为人的证据,生于斯而长于斯,民胞物与,念兹在兹。“致万物”系列是探求一个“自然信徒”的灵魂样本,研究一套勾连世间万象的修辞体系。
3.故乡和童年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南音:我的前十六年都是在农村度过的。童年有时候就是耳朵里时远时近的蝉鸣,是河边钓不完的龙虾,是石头、泥巴、玻璃弹子。我小时候被家里人当男孩养。我熟悉农村质朴又辛酸的生活,但并不觉得痛苦。现在看来,农村也只是一帧毛掉的底片。后来,我到城里生活,又返回小镇。我经常想到童年的时光。竹床下的夏夜,大雪中奶奶的背影,多是美好而温暖的场景。你说这意味着什么呢?可能就是一颗过期的糖果吧。你剥开它,尝一尝,肯定不是最初的味道,但它终究是甜的。这是每个人口袋里的一笔秘藏。
徐俊国:“用鞋底打我又把我紧紧抱在怀里的那个人/我泪汪汪地喊她 ‘娘’。/娘生我的地方我终生难忘/那天,蟋蟀在草墩上把锯子拉得钻心响/钻心响的地方叫故乡。”故乡意味着生养,即使哪天父母都不在了,故乡永远是故乡。而童年意味着消逝:“我们用过的光和岁月,/已经生锈了。//人老了,要灭了,/不知道如何亮着才好。”(《童年灯》)
4.诗歌和时代有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与对应关系?
南音:每个人的诗歌或多或少都呈现了时代。譬如,你只写抒情诗,但你的诗歌成品肯定是所属时代下的抒情方式。你偏哲理诗,更不可能背离时代背景。你的行为、语言,哪怕叙事诗里的人物,也是深藏了时代的烙印的。当下时代里的个体命运,永远都是诗人们取之不竭的主题。
徐俊国:诗与时代的关系,不能局限于短兵相接,还可以绵里藏针,甚至从修辞的根基上釜底抽薪。我希望我的诗歌,从更远的地方,以微观的角度,卑微地回应和回答这个令人爱恨交加的问题。互文也可以。任何诗人都逃不出他的时代,逃不出诗人与时代的互文关系。
5.对于当下的诗歌创作,你的困惑是什么?
南音:写诗六年了,从没有在“写什么”的问题上纠结过。有时会在自己能够抵达的境地上,显得没那么自信。如果几十年后,文本依然没有达到心目中的那个理想状态(这个状态,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常改变),我是否会觉得做点别的更有意义呢?譬如我喜欢的画画、园艺。说不好,先写个二十年再说。
徐俊国:一部分诗人隐秘前进,一部分诗人顺风顺水大踏步后退,还有一部分诗人寂寂无名却身怀绝技。真正的困惑是,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诗人形象、什么样的汉语气质,介入现在的新诗现场。
6.经验和想象,哪一个更重要?
南音:如果诗歌是那只衔着意志飞翔的鸟儿的话,经验与想象就是左右两只翅膀。相互依傍,相互支持。主要是你的诗歌,需要怎么平衡它们不同的部分。
徐俊国:记不清在哪里看见的,大意是,假如有足够的想象力用来写作,那还要经验干嘛?我当然看重想象力的激发,也特别在乎经验的TNT 当量,更对知识带给我甄别诗歌真伪的能力心怀敬意。倘若没有随身携带望远镜的自然观察经验,我哪能开启“对景写诗”的“致万物”写作。就像苇岸如果没有研究过蚂蚁营巢的三种方式,哪能被称为“自然之子”?再如臧棣,如果没观察过小蓟,哪能写出“一千根针插进它小小的花苞”这种只能发生一次的妙句?在北大校园的瘦石下,我真的往玉簪花的耳蜗里呵过气,它响了一下。
7.诗歌不能承受之轻,还是诗歌不能承受之重?
南音:都可以承受。有时那上面是一根羽毛。有时是万吨的铁石。
徐俊国:诗歌可以怒目,因为不能承受之重;诗歌可以低眉,因为不能承受之轻。
8.你心中好诗的标准是什么?
南音:沉郁如杜甫,湛然如苏子,我都爱啊。那只是外壳,能入我心者,皆视为好诗。何况新诗主张的就是自由与包容。
徐俊国:好诗之好,经得住刀砍斧劈式的文本细读,经得住抽丝剥茧式的逻辑分析。好诗和一部好电影、一部好戏剧一样,必须有一个得以成立的充足理由,必须有一个可靠、可信、可见的修辞支撑物。好诗确立了某种标准,又堵死了一条可供别人模仿的羊肠小路。
9.从哪里可以找到崭新的汉语?
南音:现在很多年轻诗人都在尝试不同的写作架构。我看到他们在跳跃、断裂的语序中寻找生机。也有那些早年就成名的中年诗人,他们也在进行崭新的探索。这些都是诗歌未来的生命力。
徐俊国:从老子的“复归于婴儿”和庄子的“我与天地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中,皆可找到崭新的汉语。崭新的汉语在古老的“赋比兴”中,隐藏着取之不尽的修辞源流。在古老而崭新的汉语面前,诗人应是一个独身主义者,语言的孝子。天地之间,中国诗人的胸腔里,一直孤悬着一枚月亮,一双现代性的手抚摸它、按压它,碰响的是古老的忧伤。
10.诗歌的功效是什么?
南音:灵魂的抗氧剂。
徐俊国:诗歌就是阿波里奈尔的那支芦笛,它让灵魂有趣,让世界的耳朵充满音符。诗歌有时候是马蒂斯的艺术“安乐椅”,有安卧、止息、平衡、安抚、慰藉之作用,有时候是老虎凳,诗人替我们坐上去,受刑。
11.你认为当下哪一类诗歌需要警惕或反对?
南音:伪诗、注水诗,还有那些不知所云的忘情歌手的歌词。
徐俊国:诗歌只有两种,好诗与坏诗。我对坏诗保持警惕,对制造坏诗的各种先锋和流派投反对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