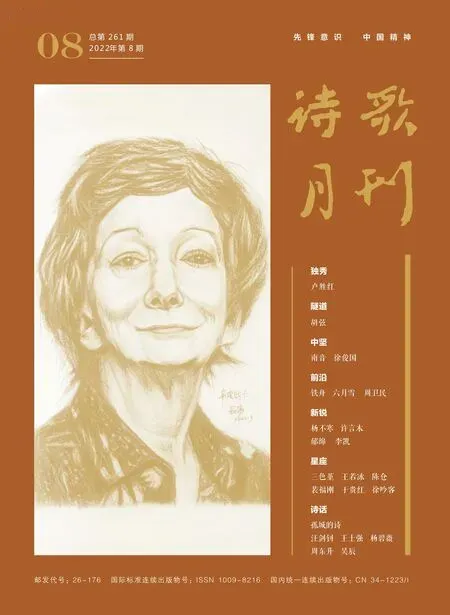静谧的力量(组诗)
2022-11-10南音
南音
午后
铁线莲的铃铛,在风中摇晃。
无尽夏硕大且饱满的花冠上,阐释着
它独特的序列之美。
一棵耧斗菜,在形成的暗房中,悄悄孕育种子。
这是五月末的阳台。
你看到,垂射的阳光,镀亮了每一片花瓣。
蜗牛睡了,花壳瓢虫睡了,守护的小天使也睡了。
流浪猫收回利爪的浓荫里,每一根绿枝
都承担了清凉趋静的意义。
雨后
一夜新雨。
花园里,红与绿都更加葱茏了。
旅行家蜗牛先生,背着它的家园,在朽木上散步。
苔丝均匀的呼吸,在微镜头里细若可辨。
一个卷发小姑娘,从铁皮画框中,走了下来。
在蔷薇花架下,她拱着手,垒起小小的花冢。
身后,透明的翅膀,才刚刚冒出脊背。
火焰兰
后来,通过形色软件里的存贮,
你最终确定了那段记忆的真实性。
宛若他在某个春夜,仍为你竭力描述:
细长花茎上,花舌如火,亦如牙贝。
作为植物学的共同爱好者,你惊讶于它的命名
——龙牙花。多么独特的形态和纯正的色彩。
你不知道,一朵花,伸出它的贝齿,
在喧嚣的尘世想要诉说什么。
正如你此刻,凝神于另一棵植株——
青绿的箭镞,仿佛带来野生溪流的气息。
柔软花茎上,分蘖的花穗顶端,
无数团小火焰跳动,嗞嗞燃烧。
而窗外,铅灰色云团快速移来。
在沉闷而趋暗的背景中,你仍可见它向四周
释放着热力与光彩。它在表达什么?
抑或在涣散的生活中,替我们抗拒着什么?
微小的电流,从空气传向你的指尖。
噢,它有好听的名字——火焰兰。
寄居
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无非是今日无事,更无人造访。
用小盅泡茶,读闲诗两行。
午后,在书桌前发呆。
天蓝得像有人在云端擦拭。
从潘越云、齐豫,再听到李健。
若时间只够凑一句诗行:
上阕:浮生若寄,下阕:梦比花轻
雪雁*
被视为蛮荒之地的远方,
也可以是孤独者的天堂。
当褐色的沼泽地,
在画纸上拖动着凝滞的色块。
鸣叫的海鸟,在天空麇集,
像一小片飞溅的海水。
没有一种爱,
不能被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
不是吗?
当手执画笔的手与拿手术刀的手,
在塔影下重叠,这优美而细腻灵魂的
另一个孤本。
我确信,我完整看到:
一个怯生生的眼神,
在季节的推移里,怎样融化、松动。
一只雪雁,用它的迁徙史,
缔结起两个相似的灵魂。
五月的防波堤上,你们并肩而立,
目送那生灵。
我将再次祈祷:趁战事还没有来,
分离也没有来。
噢,雪雁。请张开硕大的翅膀,
在我们的头顶,多飞一会。
*题名为何多苓画册《雪雁》。
参观吴为山雕塑馆
展馆里,他们是:孔子,弘一法师,齐白石
马三立,阿炳……
一群不同时代的人,被领到同一个空间。
仿佛一场盛会,正在举行。
而我,所感叹的是:这些青铜、铸铁、石膏……
它所承载的表情与精神,是怎样被一双魔术之手铸成?
你久久地凝视,从那些履历里
提炼出每个人独一无二的部分。
又如何重新融合,塑造?
一切看起来,像是他们最终完成了不同的你。
瞧。这些线条,这些面孔,通过简洁终于抵达深邃。
那件《睡童》,被放置在展馆的中心。
我多么相信,正是它,呼应着你艺术之殿中
最纯朴、且宁静的初心。
北安门
从饭店出来,
滚烫的热浪制造了短暂的眩晕。
但我们,还是决定去附近的公园走走。
初夏的玄武湖,风景并未减损。
角堇、百子莲、金鸡菊、鸢尾……
铺就着不同的花境。
而一棵大桑树,用密匝匝的浓荫,
美妙地款待了我们。
姐姐陈陈指着一棵叫秤锤的树冠,
向我们描述它花期时的惊骇。
而烂漫的二小姐和小米,围绕着一丛蒲苇,
捕捉一束最佳光线。
噢,寡言的树春先生,
当我们谈论荷尔德林、海子……
你当然知道,在各自的生活里,
我们同样承担了虚无与重力。
我们又能说些什么?
无非是花草盛开,无非是
面朝着这宽阔且闪光的湖水,
一种可被眺望的生活?
一如来时,在街头,我们匆匆告别。
车里,宋冬野唱起那首《安和桥》,
而我,刚刚穿过的城门,它叫北安门。
静谧的力量——给米勒
你只恪守这唯一的信条
“艺术的使命即是爱的使命”
你用结满茧子的手
在巴比松的大地上:播种、拾穗、晚祷
并勾勒出无数的米亚、潘恩与狄尼俄索斯
你终生吝啬使用颜料
只让劳作本身,在暗质的画布上
散发出它肃穆的光芒
正如你笃信的那样
自然的母体将不断诞生美与生命
而她并不需要任何冠冕的加持
瞧,亲爱的米勒先生
那么多的人,光着脚站在这里
只为靠近你心中的圣地
一棵雪松——纪念姑父
记得最后一次去看你,
因为疼痛,你过于僵直的脊背,
勉强撑在床沿。
你有没有落泪?当我们说起过往,
一些你还惦记着的人。
桌上的牛奶,你示意我喝掉。
五斗柜上的塑料花,依然开得和上次一样热烈。
我们又说了些什么?
仿佛所有话题,只为打破宁静本身,
但我们知道,那黑暗的入口处。
命运的绳索早就悬在那里。
后来,去山上送你。
那天,天气格外晴朗,但山风猛烈。
在所有的仪式完成后,我们迅疾散开,
奔向各自的生活。
是的,我并没有时常想到你。
只是偶尔听到你送我上学的那列绿皮火车,
哐当哐当地开着。
你离开后,我在花园里种了一棵雪松。
这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仍然不知道。
有时,我说不出话来。
像冬天的松枝顶着厚厚的雪盖。
捕词者——给蒋立波先生
多雾的磨石山上,你耸动肩膀,
奋力去向山顶的身影依稀可辨。
在那里,你忙于垒屋、筑篱、植花。
同时,也是一个捕云者,听风者。
正如西蒙娜薇依一样,你秉持朴素
与坚韧的意志,获得最终的个人空间。
而更多时。我看到,在大楼的格子间,
或一间夜晚书房中。
你像尾透明的海豚,在自我的大海上卜居。
你彻夜倾听词语,从幽暗处发出音律。
这多像,当年倚树观云的乡村少年。
变幻的星云,在天穹聚合,流泻。
他竖起耳朵,整夜捕获群星的低语:
一种尚未被翻译的生命奥义。
那个少年,多年来。他从不长大。
也从不消失。
父亲的花瓶
这是平常的一个早上。
天刚蒙蒙亮。
一个佝偻的男人,在村道上走着。
他去向哪里?
当他在村口的小公园停下。
把那些隔夜的枯叶、矿泉水瓶,以及
散落的纸屑,
一一归拢,再分装到
不同的垃圾箱里。
他负责这片小广场的保洁工作。
在这里,要忙碌上两个小时,
直到细密的汗珠,在稀疏发间闪烁、发光
而手术后遗症造成的微跛,让他归去的背影,
看上去分外劳累。
这只是平常的一个早上。
当他走进小院,阳光照临在白兰花树上。
他放下一捆旧纸盒后,像魔术师
从黑色塑料袋中取出了什么。
——一个完好的,玻璃材质的花瓶。
他把它捡了回来,送给他的小女儿。
带着微微的窘迫,又有一丝得意。
客厅的旧餐桌上。一大捧油菜花,
正在花瓶中绽放。
它金色而耀眼的光芒,像从某个
很深的地方提炼出来。
我木讷的老父亲,在他的七十岁
送给我们一堂朴素的美学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