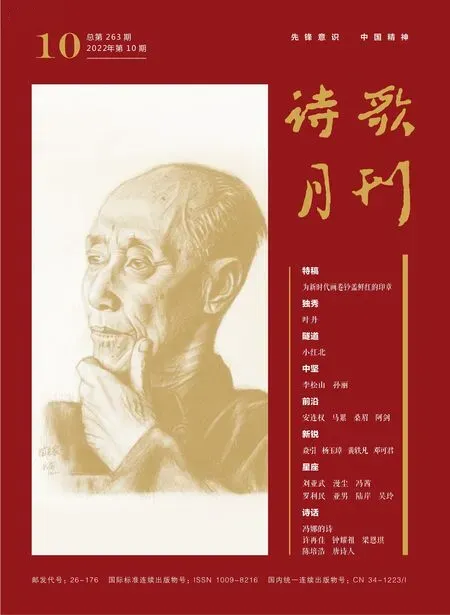从劳作中生发的自然之诗
2022-11-10钟耀祖
钟耀祖
对于作诗,冯娜似乎领悟到一种类似于古希腊人的诗学观念——将作诗与制作器物等同视之。冯娜追忆起诗歌与劳动的古老羁绊,将诗人作诗与农夫劳作关联起来,让人隐隐瞥见留存于《诗经》《工作与时日》里那个诗人与农夫尚未截然分离、“劳者歌其事”的远古时光。冯娜从小浸润于云南丽江那秀丽淳朴的山水之中,对于乡土的劳作也多有体验,往往会在诗作中流露出一种对于自然与农事的细致感知,并由此生发出对于诗歌创造的领悟。
自然是作诗与劳作的共同对象,联结着作诗与劳作。冯娜说“诗人本来就是自然之子”,作诗是诗人与自然交流的方式。诗人保持着与微小生灵和谐共栖的谦卑姿态,去接触自然,书写自然,进而更深入地领悟自然。而农夫与自然接触的方式则是劳作,他们可以“抬头看云预感江水的体温”,可以“用一个寓言”指点“五百里外山林的成色”,能够轻易地“辨认一只斑鸠躲在鸽群里”,而这一切都是“长年累月的劳作所得”——劳作让农人的生活深深地植根于自然,让农人可以深切感受自然的脉搏,这种农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让向来钟情于自然的诗人慨叹:“我并不比一个农夫更适合做一个诗人”。
于是,“作诗—劳作”“诗人—农人”构成了冯娜诗歌中的两组隐喻关系。“一个人终生只播种一种作物,算不算好农夫?”,这似乎是在问:一个人终生只写一种诗,算不算好诗人?“他拣选的种粒也拣选着他”,也即是说:与其说是诗人在挑选诗歌,倒不如说是诗歌在非常严苛地挑选诗人;当诗人观看农人削去枝叶,制作出“一个拙笨的容器”时,又怎不会想起萨福、狄金森她们取材于自然生命,质朴率真的作诗过程?
既然“诗人作诗如农夫劳作”,那么作诗的成果与劳作的果实也可建立联系,“诗作—作物”乃至“诗作—植物”的隐喻关系便延伸而出:过度成熟的诗作便如熟透的果实,“果实带给人安慰,让人忘记事实上这是另一种衰老”,它们成为“一座正在朽掉的宫殿”,充满了过度的“甜蜜”与做作。而诗人执着于“尚未熟透的山楂”,从已有的“酸涩”憧憬着“会有”的“甜蜜”,这种对于诗作“欲达高潮”的审美观念,与莱辛“包孕性的顷刻”有共通之处。
这样,冯娜从诗人与农人、作诗与劳作的古老渊源中重新发现诗歌与自然的密切联系,生发出了以自然观照人事的诗性思维——这是一种“我不能放弃”的“魔术”,是一种极具个性的“魔术”:以纯粹本真的美为尺度,独抒性灵,不必勉强自己学习那些“从来没有学会过的技艺”,不流于陈套俗见。从这种自然的诗性思维出发,诗人以种种自然事物来象征人事,来解读人事,来丰富对于人事的阐释,遂产生了一些颇为新异的理解:“我”会从强悍的“母豹”来理解女人未被规训的另一面;坦然地用危险而“迷人的蜃楼海市”来点缀人生“困顿的旅途”;借助大自然“广大的沉默”来解救被尘世“声音”所俘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