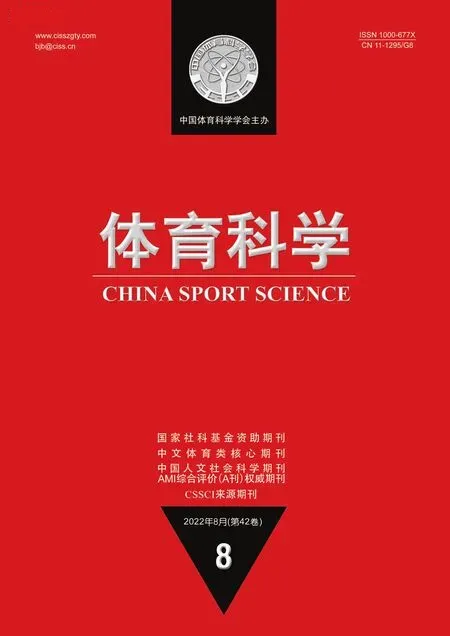近代体操教育的流变及当代启示
2022-11-07王水泉姜金红李永春
王水泉,姜金红,李永春
(1.浙江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2.浙江师范大学 行知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近代体育课程诞生于欧洲,早期主要以近代体操为载体,后被现代竞技运动(sport)取代。然而,此前的相关研究在体系性与深入性上均存在不足,甚至一些基础性问题仍有待清晰。如,近代体操因何及如何进入学校教育体系?竞技运动比近代体操历史久远且内容更为丰富,为何成为近代身体教育、体育课程主要载体的却是近代体操?近代体操教育如何演变、扩展?后来又因何被现代竞技运动所取代?厘清这些问题,不仅有重要的体育史学研究价值,还对从根源上探寻今日国际性体育课程边缘化问题(Hardman et al.,2002;Lux et al.,2011)有所帮助。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本文将在梳理近代体操教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分析其当代启示。研究思路是:从梳理近代体操教育诞生的思想渊源着手;结合时代背景等探寻其诞生在德国的契机及其特征;进而以“三大体操”(“德国体操”“瑞典体操”“丹麦体操”)为主分析近代体操教育的发展脉络,各流派的特征及相互关系;最后归纳其当代启示。
1 近代体操教育的思想渊源——身体教育的关注
文艺复兴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身体随之得以解放。在此背景下,最先强调近代社会中身体教育的重要性的是医学领域(森田信博,1988)。1569年,意大利医学家美尔库里亚利斯(Hieronymus Mercurialis),在分析古希腊体育基础上发表的《艺术体操论》()中,论述了古希腊身体训练的医疗效果和重新开展身体训练的方法(森田信博,1988)。该文将体操(Gymanastik)分为 3类:医学体操(Gymnasticamedica)、军事体操(Gymanasticabellica)和运动体操(Gymansticaathletica),并认为有益健康的医学体操最重要,而以获胜为目的的运动体操则属多余(沃尔夫冈·贝林格,2015)。
文艺复兴后的启蒙运动,进一步推动了欧洲自然科学、哲学、教育学等领域的发展。18世纪后半叶,以德国人弗兰克(Johann Peter Frank)为首的一批医学家,开始倡导把身体训练作为国民教育手段予以体操化。其中,专门对运动与健康的问题进行探讨,且对后来的健康教育论产生深刻影响的是浮士德(Bernhard Christoph Faust)。他在1792年的《健康问答书》中指出,“健康才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它为人类带来幸福,使精神得以自由,使每个人的人生快乐、美好。”强调为了积极维持与增进健康,有必要超越单纯的养生方法,进行有强度的身体训练,儿童教育的意义在于,“引导他们成为身体健康与精神完善的人”。他把身体教育看作教育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领域,认为总目的在于完善人格的培养,具体目标在于身体、感觉、社会性的塑造。据此,他主张学校教育中有必要设置身体教育(körperliche Erziehung)科目,对儿童进行身体运动方面的专门指导(成田十次郎,1977)。在近代体操教育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弗兰克等在医学上的论述,为后来的体操教育家向世人解答体操的必要性,选编教材,归纳教学注意事项时,提供了理论支撑。
在医学领域之外,近代早期的思想家、教育家、艺术家夸美纽斯、洛克、卢梭、歌德等也均已注意到身体教育的必要性。从思维方式来看,在“理性主义”的时代,总体上他们是在身心二元的框架下将身体教育与精神教育一分为二,看重身体运动的生物学(体质健康)效果,将身体运动看作精神教育的物质基础或实施途径。国内体育学界围绕洛克、卢梭等人体育观的已有研究对此多有涉及,在此不再展开。
2 近代体操教育的形成
近代体操教育形成过程中,“近代体育之父”古茨穆斯(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GutsMuths)贡献巨大。不过,其体操教育体系的确立得益于巴泽多(Johann Bernhard Basedow)等泛爱教育家的前期铺垫,维劳密(Peter Villaume)在思想上的直接启发;后来,其体操教育体系的发展过程中维斯(Gerhard Anton Vieth)在运动学方面予以完善,裴斯泰洛齐(Johan Heinrich Pestalozzi)在教育学理论方面加以充实。
2.1 巴泽多:身体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初步探索
18世纪前近代身体教育的思想已经登场,但更多的是停留在了思想层面。把这些思想整合,并具体化为教育实践的是泛爱派教育家。受蒙田、夸美纽斯、洛克,尤其是卢梭的影响,泛爱学校的创始人巴泽多非常重视“身体教育”。他主张完整的教育不能脱离身体,意志品质的教育比知识的教授更为重要,教材的选择要以“必要”为原则,而在教学方法上,提倡在游戏氛围中的快乐学习取代体罚、灌输的方式(清野市治,1971)。1758年《实践哲学》()一书将身体教育与学问教育放在一起作为了教育的两大领域(成田十次郎,1977)。
《父母、教师用书》(,1770年)在卢梭身体教育论的基础上,强调身体运动具有性格塑造、感觉形成、身体技能提升等价值。该书列举出适合青少年男子的运动教材有游泳、平衡运动、爬绳、滑冰、舞蹈、骑马等(成田十次郎,1977)。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把这些教材在徳绍泛爱学校的正课教学中进行了实验。他的后继者及其创办的其他泛爱学校同样重视身体教育活动。不过,近代体操教育成为学校特色之一,占据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领域,则要等到古茨穆斯时代(成田十次郎,1977)。这一时代的开启者是维劳密。
2.2 维劳密:缔造近代体操教育理论雏形
1787年,维劳密发表《完人与幸福为目的的身体培养——以身体教育为主》(),开启了讨论国民教育体系中体操教育必要性的序幕,在德国近代体操教育理论形成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该文立足于近代医学与教育学,批判以前的修道院式教育,强调教育可促进人多种能力的发展,提出国民自由、幸福的生活中体操必不可少。基于这样的考虑,他把国民教育(Volkserziehung)中体操“理论的确立”作为时代课题,从体操的概念与领域、目的与目标、指导的原理、教材的分类与排列等方面描绘出了近代“德国体操”教育理论的蓝图。
自此,维劳密、古茨穆斯、维斯一脉相承的3位体操教育家相继登场。该文发表2年后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对德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民教育思想随之由重视阶级性、有用性开始向弘扬自由及平等的观念转变。该文的很多观点契合了法国大革命的诉求,更加坚定了他们探寻体操教育价值的信念。此后,以建立属于每个国民的体操教育为共同追求,维劳密构想了理论雏形,古茨穆斯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论述,维斯使之更加“科学”。
维劳密以“自然性”为教育方法的总原则(原理),批判当时的“知识偏重主义”,指出“我们无视身体盲目追求精神的形成,到头来不仅身体,心灵也将变得脆弱”(成田十次郎,1977)。在他看来,身体形成与理性及道德形成同样重要,均离不开与“自然”相符的教育技术(成田十次郎,1977)。他把身体看作“心的命令得以实现的道具”,倡导生理学基础上的教育技术。在他看来,身体教育(physische erziehung)可划分为3个领域:1)器官感觉的形成及运用方面的训练;2)身体健康与锻炼的关注;3)身体及其各部位的强化与塑造。这3类身体教育得以实现的身体运动有:由学习者选定的自由的游戏(freie Spiele)、由指导者决定的技术性运动(künstlich eingerichtete übungen)、严肃而艰辛的劳作(ernsthafte,anhaltende Arbeit)。他把这些身体运动均归入体操,在实施方法的原理上,强调“自然”(成田十次郎,1977)。
2.3 古茨穆斯:为近代体操教育体系奠基
如果说维劳密是国民教育中体操教育理论的提出者,古茨穆斯则为该理论体系的构建者。当时德国市民阶层自由、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受之感召,古茨穆斯把培养自力更生、明智、有德性,具有行动力的人作为其教育追求。在他看来,这样的教育必须以身体方面诸素质的发展与完善为基础,而实现这样的教育,则不可能仅靠传统的医药及养生,唯一值得信赖的是欢快的“教育性身体活动”的教化(ヴァンダーレン,1958)。在其心目中,欢快的“教育性身体活动”即体操教育。
古茨穆斯的体操教育论深受近代医学、教育学影响,尤其是受到了维劳密体操教育论的直接启发,但更主要的是得益于其泛爱学校长期的探索性执教经历。实践性,是古茨穆斯体操教育思想特色之一(成田十次郎,1977)。1793年首次面世,被誉为世界体育学经典的《青少年的体操》(GutsMuths,1793),正是其8年执教经验的结晶。古茨穆斯非常重视体操的教育性。为此,他并未局限于提升学习者运动技能与体质,还强调运动乐趣的强化,期望通过体操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其中的身体性(生物学)、人格性(教育学)价值,并付诸实践(成田十次郎,1977)。他还倡导过体操改善社会矛盾,让所有阶层人士皆能幸福生活,最终实现他心目中的“繁荣社会”。为此,他把古代日耳曼人与当时的德国人进行对比,认为古代日耳曼人身强体健、技艺精湛、顽强不屈、诚实守信、勇敢顽强,而当时的德国人身体羸弱还丢弃了英雄气概。在他看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并非自然因素,而是错误的教育与生活(グーツムース,1979)。于是,他主张在“繁荣社会”建设过程中有必要将体操列入国民教育体系。国民教育离不开弘扬爱国精神,体操与此何干?他于 1814年完成的《关于爱国教育》()对此的回答是,爱国精神的教育要以强健的体魄为根基(成田十次郎,1977)。
关于“体操(教育)”的含义,有必要与另外一个词汇“身体教育”对照理解。《青少年的体操》中,与吃饭、穿衣、行走等所有身体运动行为的培养,对应的德语有Leibeserziehung,Körpererziehung或Erziehung等,在该书的日译本中成田十次郎将这几个词汇统一翻译为了日语的“身体教育”(グーツムース,1979)。以游戏、跑、跳等身体活动为手段的教育,对应的则是Gymnastik,即“体操”。古茨穆斯关注的是后者,正因他看到了体操人格教育的价值,才将其置于国民教育的高度,强调“体操唯一正确的目的在于使身心得以和谐”。体操绝非难登大雅之堂的打发闲暇时光的活动,而是具有身体教化价值的一门课业(arbeit)。且从更易于成为国民习惯的角度来看,体操应是“由青少年的乐趣包裹而成的一门课业”(成田十次郎,1977;GutsMuths,1793)。从教育目标来看,体操“是以身体的耐力、力量、技能与美的提升为目的的身体运动体系。”这样的界定方式,既考虑到了社会的需要,也考虑到了学习者的需要。另,关于身体教育中体操的位置,古茨穆斯认为只有体操才是身体教育的中核,缺失了体操,身体教育的作用将无法充分发挥(成田十次郎,1977)。1804年《青少年的体操》按时代将体操教育分为2大类,原始时代无意图的自然体操(natürliche Gymnastik)和文明时代有意图的技术体操(künstliche Gymnastik)。后一时期的技术体操又可划分为4类,兵式体操(kriegerische Gymnastik)、竞技体操(athletische Gymnastik)、医疗体操(medizinische Gymnastik)、教育体操(pädagogische Gymnastik)。他强调,唯有技术体操中的教育体操具有高度教育价值(成田十次郎,1977;GutsMuths,1804)。
《青少年的体操》还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论述了开设体操教育的必要性。为此,该书延续且发展了维劳密的思想,把体操教育看作身体教育(Leibeserziehung)中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把之赋予了“通过身体运动的教育”(相当于当今意义上的“体育”)的位置(成田十次郎,1977)。古茨穆斯这样定位体操教育,还有体育学学科建设方面的用意。他已意识到,体操教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除了概念清晰,还要有可靠的理论基础和独立的研究对象(成田十次郎,1977)。他在《青少年的体操》中指出,“教育的目的一般被看作人格形成,因而,体操必须以身体方面人的素质的发展与形成为目的”,在他看来,“自然赐予人类的身体素质(Leibliche Anlagen)的发展,与精神素质的发展同样不能无视”(成田十次郎,1977;Guts Muths,1804)。依据古茨穆斯的表述,成田十次郎(1977)认为,古茨穆斯体操教育学的独立研究对象为“与身体素质发展、完善有关的行为”,这样的“体操教育理论建立在生理学基础上”(成田十次郎,1977;GutsMuths,1793)。
古茨穆斯的体操教育观鲜明地体现在他对体操教育目的、目标的思索方面。在他看来,“身体方面人类的所有素质作为精神的教师和仆役,具有最大限度地塑造身体的美和适用性的作用”(成田十次郎,1977;GutsMuths,1804),体操教育的目的存在其中。“美”被他看作为区分人与动物的决定性因素。他对“最大可能的适用性”(Brauchbarkeit)的解释是,“身体具有2种机能,一是,身体接受外界环境的刺激,将其引向灵魂,这一机能可看作‘身体是精神的教师’;二是,身体接受精神的命令,在物理世界予以实施,这一机能可看作‘身体是精神的仆役’……作为教师,身体必须具有强健的神经系统……作为仆役,身体必须健康、体力充沛、结实有力、技艺精湛”(成田十次郎,1977;GutsMuths,1793)。进而,他依照身体运动的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提示了体操教育的具体目标。身体运动直接作用的对象是身体,具体包括:活动肌肉和四肢,锻炼皮肤,掌握运动技能,训练感觉。身体运动间接作用的对象是精神,包括:身体的健康有助于精神的明晰;体力、技能的增强有助于提升自信、沉着、勇敢的气质;坚持不懈的锻炼有助于提升男性在克己等方面的气质,灵活的身体有助于精神的活泼;身体的美有助于道德的美;敏锐的感觉有助于知觉准确、思维敏锐;运动有助于养护精神(成田十次郎,1977)。他这样考虑体操的目的、目标的意图在于把当时羸弱的德国青少年培养成“伟大的实践家”“锐意进取、勇于担当的男子汉”(グーツムース,1979)。
正因对体操教育的目的(目标)、教材、方法、评价进行了细致且开拓性的论述与实践,古茨穆斯才被后世称为“近代体育之父”“德国体育的祖父”。不过,后世学者认为,他在体操教育理论方面的功绩,更主要的是体现在体操教学“方法论”上。如门泽(Clemens Menze)所言,“古茨穆斯的固有研究领域为教育实践、方法论、教授论,但他并非从一般本质论上进行探讨。他主张教育学要反映到日常生活中去,却并未限定在教育学的框架内思考教育的本质、限界、可能性”(成田十次郎,1977)。古茨穆斯的体操教育遵循“自然主义”方法论,深受维劳密的启发。然而,维劳密停留在了原理层面,古茨穆斯则将之具体化为学习导入、教学条件配备、个性化指导、差异性评价等方面(成田十次郎,1977)。立足于“自然主义”,他认为“体操教育的基本原理排斥强制,依靠强制不会取得任何成功”(成田十次郎,1977;GutsMuths,1793),他强调体操教育的开展必须遵循2个原则:必须与学习者的发育、发展保持一致;必须尊重学习者的自发性(成田十次郎,1977)。
在教材论方面,古茨穆斯的成就同样斐然,正是他构建了近代体育教材论的原型(成田十次郎,1977)。他认为,体操教材的选择只能以“身体素质的发展、完善”这个目的为标准。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虽然他的观点明显带有道具色彩,但切实超越了之前“骑士运动”的教材观。如1793年《青少年的体操》第七章至第十八章的标题所示,体操教育的教材主要包括跳跃、投掷、格斗、攀登、平衡运动、提拉牵引、舞蹈、步行、游泳等(グーツムース,1979)。这样的设置方式,亦体现了他立足于“自然主义”,结合民众生活的教材观。深受当时教育思潮的影响,他的教材观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防火训练、熬夜训练、断食训练、朗读、感觉训练等也在其体操教材中。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众多教材如何体系化?他提示可按4个分类标准进行分类:运动目的、运动特征、运动的解剖学、运动类型。他最为看重按运动类型进行分类,另外,受当时教育思潮的影响,他把教材看作完善个人身体素质的材料,强调要与学习者的生活相结合。在他心目中教育体操的教材包括3大领域:真正的体操运动、手工作业、游戏。在年复一年的学校教育中,如何排列体操教材?他并未采用依据年龄或学年进行排列的方式。在他看来,这样的排列方式有违学习者之间实际存在的个体差异。依据多年实验、观察、测定、记录的结果,他从各体操教材中提炼出多个具体课题,按每个课题的发展顺序进行排列。例如“跳短绳”教材的具体课题如下排列:前摇跳—后摇跳—跑跳—踏跳—前摇跳接交叉跳—后摇跳接交叉跳……(成田十次郎,1977)。
古茨穆斯紧扣时代危机,积极倡导把体操列入国民教育体系的构想与实践,不仅对德国,也对欧洲其他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德国,伴随《青少年的体操》的问世,此后只要谈到体操,就无法回避古茨穆斯,在“德国体操”教育发展过程中涌现出的代表性人物扬及施皮斯等,均从古茨穆斯身上汲取了大量养分。而在其他国家,如“丹麦体操”的开创者那哈戈尔、瑞典体操的创建者林、“法国体育之父”阿莫罗(Don Francesco Amoros)、“瑞士体育之父”库利亚斯(Phokion Heinrich Clias)等也或多或少受到了古茨穆斯的启迪(成田十次郎,1977),即使是20世纪体操教育的影响力被削弱,但其影响亦未终结。从“通过身体运动的教育”的角度审视今天的体育课程,很难说真正超越了古茨穆斯的体操教育观。
2.4 维斯:揭开体操教育“科学化”研究的序幕
维斯、古茨穆斯、扬被体育史家称为“德国体操教育的三大巨星”(成田十次郎,1977),但长期以来,维斯的名气却远不如另外2人。直到20世纪后半叶,随着运动人体科学研究的兴起,他的成就才逐渐被关注。与维劳密、古茨穆斯相比,维斯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对身体运动科学化的探索上。这也是体育教学理论史上其功绩所在(成田十次郎,1977)。
为了把体操列入国民教育体系,依据维斯探索体操教学理论的同时,亦注重身体运动的实际效果。他把培养具有行动力的市民作为体操教育的目的,将该目的划分为3个方面:1)身体方面包括,健康的维持与增进,肌肉与肌腱的力量、稳定性、灵敏性的强化,关节柔韧性的提升,良好姿势的形成,完美体形的塑造;2)精神方面包括,鼓舞士气、获得精神的自由,激发投身思维工作的欲望;3)其他方面,如自由时间的高效使用等(成田十次郎,1977)。他期望通过体操教育塑造的市民形象为:体力充沛、技艺精湛、体形完美,洋溢男子汉气概,能够尊从自己的意愿行动。为此,在体育设施建设、教师配备、指导注意事项等方面,他均发表过见解。但其最具特色之处为体操教学的运动学(Bewegungslehre)分析。在他看来,运动学才是体操教学理论得以成立的基础(成田十次郎,1977)。
维劳密、古茨穆斯立足于医学及教育学,看重的是身体运动的生物学及人格教育作用,论述的重点为教学方法、设施、用具等。维斯关注的重心则在运动机制的物理学探究方面。他曾列举出4个运动分类的原则(原理):1)史学·社会学原则,2)心理学原则,3)解剖学原则,4)物理学原则(成田十次郎,1977)。他不关心前2个原则,同时认为依据第3个原则分类后,身体运动的效果模糊且复杂,他最终采用的是第4个原则。维斯从实用角度出发,对跑、跳、投等运动进行物理学分类,进而以“身体使用状态”“身体移动的方向”“使用的身体部位”等为标准进一步细分。他对身体运动的力学探索属于对自然科学范畴运动机制研究。这正是他被后世称为“运动理论家”“运动学先驱”(成田十次郎,1977)的缘由。
依据柯林恩(Eike Klinge)及诺伊恩多夫(Edmund Neuendorff)等人的观点,与古茨穆斯重视教育方法与教育实际相比,维斯关注的则是身体运动的体系性和学术性。维斯采取这一立场的初衷是为了最合理(科学)、有效地实现体操教育的目的。这也正是他在体育教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开拓性贡献所在(十次郎,1977)。不过,他是站在身体运动之外“检视”身体运动,未能在身体运动的力学分析与运动文化的传承与创造之间架起通畅的桥梁(クルト・マイネル,1981)。另外,受分类视角所限,在其机械的运动分类体系中,完全舍弃了游戏运动(Spiel)。还有,他在探索体操教学理论的过程中,并未从“我”的运动体验出发,采用的是“置身事外”的方式。
2.5 裴斯泰洛齐:洞察到近代体操的完人培养价值
与古茨穆斯等不同,德语圈瑞士民主主义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关注的是整个教育。古茨穆斯为苦难时期的德国找到了身体运动的“适用性”,裴斯泰洛齐则深刻洞察到了完人教育中人格陶冶方面体操教育的必要性(ハンス・グロル,1982)。他的教育追求具有鲜明的平民情怀。针对当时工业、经济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他期望借助教育全方位予以解决。说其毕生都在与破坏人类幸福的社会问题不懈斗争,并不夸张(成田十次郎,1977)。这是他被称为“民主主义教育家”(裴斯泰洛齐,1992)、“贫民教育家”(王小丁,2005)的原因。
1807年,裴斯泰洛齐的一篇关于体操教育的论文中,列举了产业革命初期大量侵蚀民众身体的现象,并从根源上分析了其背后的社会原因,强调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人格陶冶”方面的身体教育。接着,他站在卢梭自然主义教育的立场追问,“自然如何教育儿童?自然培育儿童什么?即,人身体方面的自然属性,应该被开发的素质到底是什么?身体的自然属性能为儿童身体的发展提供什么?人格陶冶的技术,在自然的这些作用之上必须要添加的是什么?”在解答这些体操教育的根源性问题时,他把儿童看作“由心脏、精神、身体多方面素质构成的,本质上有机统一的整体。”自然的作用在于促进儿童的心脏、精神与身体的素质同步、协调发展(ペスタロッチー,1962)。这让我们看到了身心二元论的泛爱主义体育,向身心统一的人文主义体育转变的迹象(成田十次郎,1977)。
自然意义上身体素质的发展,究竟意指什么?在裴斯泰洛齐看来,那既不是某项运动技能的获得,也不是跑、跳、投等基本运动能力的提升,而是切切实实的手、脚的强健使用。为此,他并未止步于把现有的运动、动作看作身体陶冶手段的观点,而是回溯到儿童的本性中探寻根源(成田十次郎,1977)。在他看来,根源上陶冶儿童身体的手段,越多从儿童固有的活动冲动出发,越合乎自然(ペスタロッチー,1962)。儿童的活动冲动得以充分的表达,依靠的是儿童自身的身体,即关节。“为了让儿童能够活动,自然赐予了他所有肢体上的关节。他游戏,他运动……很明显除了关节训练之外别无其他。自然引导着儿童……渐次拓展他的关节技能范围”(ペスタロッチー,1962)。
基于关节运动的意义,裴斯泰洛齐指出“基本体操(Elementargymnastik)的本质……连续纯粹的身体关节运动之外,别无其他”(ペスタロッチー,1962)。只不过,他把基本体操为主的体操列入教育体系,并非为了增强儿童的体质、健康,而是为了培养完人。这正是后世研究者对其体操教育给予极高赞誉的原由。他的基本体操具有如下特征:1)从身体发展的角度看,重在提升儿童的身体素质,“使之转化为自身能自由、自主掌控的能力”;2)从认知的角度看,重在帮助儿童直观到“自身的运动能力及固有法则”“驾驭自身运动能力的可能性”,并理解其意义;3)从审美的角度看,重在使儿童具备有品位的身体及态度;4)从道德的角度看,重在使儿童遵从理性与意志;5)从职业发展的角度看,重在让儿童掌握关涉将来职业的必备能力(成田十次郎,1977)。总之,他从健全人格培养、身体陶冶的角度考虑体操教育,既突出了体操的实际教育意义,也将之赋予了心理学意义上教育认识的高度。
3 近代体操教育的国际化
以古茨穆斯为首的近代体操教育家的探索,为体操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之后,在多重因素合力下,“德国国民体操之父”扬(Friedrich Ludwig Jahn)创造的“德国体操”,及施皮斯开创的近代学校体操教育制度在德国真正得到认同(ヴァンダーレン,1958)。这段时期,还诞生了“瑞典体操”“丹麦体操”。以“三大体操”为策源地,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近代体操教育被世界众多国家所采用。
3.1 扬的以培养“国民性”为使命的“德国体操”
古茨穆斯时代以平等、自由、幸福生活为追求,重视人格教育价值,突出以“自然性”为教育方法论的体操教育,在战争面前不得不发生转变(清野市治,1971)。1805年俄国、奥地利联军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战败,1806年普鲁士在耶拿战役中战败,自此德国完全被法军占领。历史学家认为,耶拿战役失败后德国进入了进步与反动并存的动荡时期(成田十次郎,1977)。与其他时期相比,这一时期德国的体操教育与政治结合得更为紧密。以扬的“德国体操”(Turnen)为代表的国民体育运动,亦是1806年后德国社会态势的缩影(成田十次郎,1977)。从体操教育被定位为“培养德国青少年在道德方面、身体方面投身于德国解放事业的能力”(清野市治,1971)的手段来看,扬的体操教育并非仅为体力强化、技能提升,还被植入了政治性、道德性意志培养的元素。尤其是他创造的“德国体操”,更可看作其人生志向与体操教育理想的具体化。
扬体操教育理念的转变,离不开黑格尔等思想家的启发。1806年,德国被法国占领后,时任中学校长的黑格尔举行了题为《兵士运动的教育意义》()的演说。这一举动,于1809年最终促成了政府批准他所在的中学开设兵士训练。另,费希特为了唤起德国人的斗志,亦非常重视自由与独立方面的思想教育。他强调体育在国家重获独立的道路上必不可少,应与知识类科目同样考虑(费希特,2010;ヴァンダーレン,1958)。但直接为扬等人创造条件的则是1808年在普鲁士柯尼斯堡(今,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成立的反法地下组织“道德联盟”。该联盟汲取古茨穆斯体操教育思想,在结合时代需要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向布伦斯堡(Braunsberg)议会提交了议案《国民教育中体操教育必不可欠》()。进而,1809年,为了培养富国强兵的青年男子,该联盟布伦斯堡分部制定了联盟规约,开设了由军人执教的公共体操学校,把兵士体操(Miltärische Gymnastik)作为核心课程,实施古茨穆斯的体操与兵士操练(成田十次郎,1977)。强烈的军事色彩,是该联盟体操教育的最大特征。
尤其是1809年“道德联盟”向普鲁士内务部提交了《国民教育导入案》()其中的《体操学校设置案》(),更是为扬指明了方向(成田十次郎,1977)。该提案第16条对体操课程性质的解释是:“作为教育科目的体操,其目的是培养身心健全的国民,体操学校与普通学校要紧密配合,所有课程应合而为一,以发展人的整体素质为目的”(成田十次郎,1977)。
不过,“道德联盟”的提案,只在个别地区得到落实,难以称为国家行为。体操真正进入国民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普鲁士政府的体育政策。1804年,古茨穆斯曾向普鲁士内政部部长马索(Julius Eberhard Wilhelm Ernst von Massow)提议把体操教育列入国民教育体系,并同时提交了第2版的《青少年的体操》。转年,马索感谢古茨穆斯时答复,“青少年的身体技能及身体运动,将会作为我的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成田十次郎,1977)。1806年,普鲁士战败,加之随后“道德联盟”的提案,及普鲁士首相施泰因(Baron vom und zum Stein)男爵的推动,当局终于开始切实重视体操教育。当局认可体操为学校教育科目之一的同时,也迫切希望尽早确立学校体育制度。这为扬的“德国体操”的确立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扬的青年时代是在法国统治下度过的,当时德国的民族主义已经萌芽,如何培养担起民族解放重任的爱国青少年,是当时德国最重要的命题(高橋健夫,2015)。顺应时代的需要,扬把“统一的德国国民国家建设”作为了毕生的最高追求。只不过他心目中的国民国家,并非人人平等的国家,而是君主至高无上,身份有别,秩序分明的国家。他认为“国民国家”存在、发展的保障,唯有“国民性”(Volkstum)(成田十次郎,1977),而“国民性”正是扬缔造“德国体操”的思想依据。
1810年,体现扬的根本思想的著作《德意志国民性》()对“国民性”的解释是:为使每一个国民凝聚在一起的最高、最大、本质的统一力(Einungskraft)。“国民性应为国民所共有,它是国民的内在本质,国民的生命力,它是生产力、繁衍力……在以此结成的国民共同体中,每个国民的自由与独立不仅不会被破坏,反而会愈加强固”(成田十次郎,1977)。这样的“国民性”从何而来?在扬看来,只有采用德国人的方法,激发德国人固有的潜力,才能将之根植于德国人的骨子里。德国人的方法,即“国民教育”,在他看来,国民性的培养唯有依靠国民教育,且迫于形势,要加速培养。
关于国民教育的内容,扬列举出10个方面:真人的教育、国语教育、读书教育、国家学(公民)教育、国史教育、手工劳动教育、职业规划教育、艺术教育、体操教育、女子教育(成田十次郎,1977)。其中“真人的教育”可理解为真正、真实的人的教育,这样的人应具有理性、仁爱、自主的精神气质。深受卢梭、裴斯泰洛齐的影响,扬认为“真人的教育”应远离调教式、强制的方法,“儿童就应该有儿童的样子”“把人本就拥有的自发性激发出来,才是人的教育”(成田十次郎,1977)。“体操教育”则主要是对国民教育中身体运动(Leibesübungen)含义及作用的阐释。
扬在《德意志国民性》中感叹,德国人的祖先通过运动、训练获得的“精湛的技艺”“严谨务实的态度”曾令罗马人叹服。然而,“最近的德国人身体僵立在那里,已懈怠获得必要的身体技艺,也不能正确理解自身原本拥有的高贵的能力。”正因身体能力与技艺不堪,才造成“德国人厌恶自己”“德国人已无可救药”的状况。“孔武有力、坚忍不拔才真正是取得胜利的力量”。培养这样的德国人,才是身体运动的中心课题(成田十次郎,1977)。只不过,该书对身体运动培养国民性的论述,停留在了与意志力有关的“体力”“技能”的培养上。书中列举出的增进“体力”“技能”的教材有走、跑、跳、投、搬运、攀登、平衡、登山、游泳、滑冰、滑雪、射箭、划艇、帆船、剑术、骑马、跳马、捕鱼等(成田十次郎,1977)。
为了将培养“国民性”落到实处,1811年,扬不再使用Gymanastik(体操教育)与Leibesübungen(身体运动)这2个外来语,而是用母语Turnen(“德国体操”)代之,并与其团队在柏林郊外的哈森海德建造了最初的“德国体操”设施。主要设施有圆木、攀登棒、梯子、爬杆、跳跃用具、梯形跳跃沟、长枪、格斗场、8字型跑道、挂臂水平移动棒(Hangelreck)。这一年夏天,共有约300人参加了首次“德国体操”训练营。很快,扬被奉为了爱国志士,“德国体操”成了热议的话题,也引起了法国当局的警惕。扬的合作伙伴博尔内曼(Bornemann)把“德国体操”与之前的身体运动进行比较,概括其特征为:打破了学校、阶级、年龄等既有的教育框架,突出平等、解放、集体的观念,向每个国民开放。“在运动场身着相同的服装······只有技巧与道德是个人优秀与否的最好证明”(成田十次郎,1977)。扬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德国的解放与统一,在平等、开放的氛围中培养与其国民教育思想相符的具有行动力、锐意进取精神、团队意识的青少年。
由此,扬的体操教育思想已超越体力、技能培养层面,融入了政治意识、道德品质培养的内容。这是思想上他与古茨穆斯的明显不同之处。另,古茨穆斯体操教育体系中的感觉运动、发声运动也被他弃之不用(山本徳郎,1979)。还有,“德国体操”是在周三、周六下午放学后开展,与学校体育并无直接关系。1816年他的第二部代表作《德国体操术》()出版,进一步提升了他的影响力。该书出版的第2年,古茨穆斯亦受其影响,在其发表的文章中也开始放弃“Gymanastik”,改用“Turnen”。然而,因自由主义色彩强烈,1819年哈森哈德体操场被关停,扬也因“煽动革命”的罪行遭逮捕入狱。紧接着,1820年扬的“德国体操”在全德被明令禁止。直到1842年,“德国体操”才再次成为德国男生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成田十次郎,1977)。
概而言之,扬把实现统一的国民国家,作为其人生的最高志向,但他眼中的国民形象绝非是希特勒时代的纳粹军人形象;他的人生志向具有鲜明的国家主义特征,但在教学方法上并不赞同军事化的方式。这也许是即便他宣扬培养战斗民族的人格,也依然得到当时进步的教育家、思想家认同的原因。他批判当时德国教育现状时列举出的问题有:基于阶级差别的学校制度;只有针对少数人的教育,没有根据的全球化市民教育;学习内容片面,学问与生活的游离;反自然的教育方法等。他期望通过“德国体操”培养的是具有批判精神的社会活动家。构成他思想的关键词包括:人权的解放、平等、开放、独立精神、结合生活。也正因此,扬的“德国体操”在瑞士、美国、斯拉夫等国家(地区)得到认同。另,扬在体操教学方法方面采用了分班教学、小组教学及循环学习的方式,在体育术语的创立、体育文献学方面更是取得了开拓性成就(成田十次郎,1977)。
3.2 林的科学主义的“瑞典体操”
林(Per Henrik Ling)的“瑞典体操”与扬的“德国体操”的诞生背景极为相似。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瑞典一直处于国际纷争中,在此背景下,瑞典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迅速高涨,以增强国力为名义开设体操的呼声越来越高(水野忠文など,1969)。
早年,林留学丹麦期间,在那哈戈尔的体操学校阅读了古茨穆斯的著作后,认为那哈戈尔的体操教育缺乏新意(水野忠文など,1969)。他的体操教育思想间接学自古茨穆斯,致力于体操事业的志向又与扬极其相似,是“爱国心”驱使他走上探索体操教育的道路。另外,他与扬同样把体操看作了培养战斗民族的手段,但在开设体操的直接目标及实现目标的理论依据上,两人又有很大差异。扬的“德国体操”带有鲜明的唯意志论的特点,林的“瑞典体操”则以生理学、解剖学、生物学等作为其理论支撑,具有鲜明的科学主义特征(清野市治,1971)。他认为,“真正的体操教育理论建立在生理学基础之上,每种运动实践都必须考虑个体的身体特征。”可以说,在探索体育的科学基础的道路上,林倡导的运动的生理学与维斯开创的运动力学、解剖学,具有先驱意义(成田十次郎,1977)。
林致力于体操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认为体操运动能够使有机体得到充分协调发展,而“健康是协调(发展)的表现”(ヴァンダーレン,1958)。围绕“有机体的协调发展”,他对体操教育进行了分类。其遗作《体操的一般原理》()把“瑞典体操”分为4类,教育体操、兵士体操、医疗体操、塑美体操(Aesthetische Gymnastik)。从目的上看,教育体操在于塑造充分协调发展的有机体,发展与生俱来的身体潜在能力;兵士体操以军人需要的作战能力、意志品质为指向,重视塑造环境适应能力、灵敏性、紧张气氛的耐受能力;医疗体操强调使虚弱者恢复健康的可能性;塑美体操侧重身体内在情感、情绪、思想的表现。为了实现“有机体的协调发展”这一总目的,他强调4类体操相互依存,相互统一。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他的这一构想更多停留在了理论模型层面,实际开展过的只是前3类。即便在前3类中,体现“瑞典体操”特色的也并非兵士体操,而是教育体操和医疗体操(ヴァンダーレン,1958)。
根据是否使用器械,林把体操分为徒手体操和器械体操。教授体操之初,他采用了丹麦期间学到的“古茨穆斯-那哈戈尔方案”(GutsMuths-Nachtegall program)(ヴァンダーレン,1958)。这一方案具有运动内容丰富、器械运用灵活的特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删除了与其科学理论不符的运动,最后留下的大部分是徒手体操,和一小部分轻器械体操,击剑、跳马等则不再教授。林执着于徒手体操,主要因他认为有以下几个优势:1)1名教师便能胜任;2)基本不受场所限制;3)无需器械及修理费用;4)小组或班级一起运动,能更有效地发展肌肉力量、灵敏性和身体调控能力;5)附以号令有助于提升严格的军事训练效果;6)更容易做到适合不同个体的身体特点;7)在改善身体笨拙、僵硬方面,比器械体操更有优势。林把徒手体操分为主动运动和被动运动,主动运动有屈伸、捻转、旋转等,被动运动有压迫、摩擦、震动、击打等。林如此看重徒手体操,很大程度上与那个时代的军事需要有关。在看待器械体操的观点上,林与扬也有明显差异。林认为器械体操的开展应该以身体的需要为依据,扬则认为首先要考虑器械、器具的性质,身体的需要则其次。此外,林还认为很多德式器械体操过于复杂,身体练习的效果值得怀疑(ヴァンダーレン,1958)。
值得一提的是,林开创的“瑞典体操”的延续性及国际影响力,在他去世后,呈多面开花的态势,一批后继者继续发展了“瑞典体操”。教育体操、兵士体操、医疗体操均有专门的后继者。另,因大众化思想与实用性特点,他的体操教育思想在1842年的瑞典教育法中得以体现的同时,也得到了其他国家的认同。1904年英国制定的体育教学大纲(Syllabus of Physical Training)的基本内容参照的正是“瑞典体操”体系。美国近代体育初创期的代表性人物比彻(Catherine Esther Beecher)、刘易斯(Dio Lewis)均承认受到林的影响。1899年美国《体育手册》大部分内容取自“瑞典体操”。明治时期“瑞典体操”就已开始影响日本,整个大正时期及昭和时期的前10年,更可说是“瑞典体操”的时代(清野市治,1971)。
即便在近代体操教育的诞生地德国,亦曾受到“瑞典体操”的影响。1830年,马斯曼(Hans Ferdinand Massmann)发表的论文《为了兵士体操教育》(),在德国第1次较为深入讨论了“瑞典体操”教育发展状况及林的功绩;1842年发表《瑞典体操教育与林的体操教育体系》(),成为首篇真正阐明林的体操教育体系的德语论文。该文指出,“瑞典体操”不只是“经验性的体操”(ein empirisches Turnen),更是“合理而全面的体操”(eine rationelle,allseitige Gymnastik),“能把青少年培养成出色士兵的体操”。1861年,一次以“林追思演讲”为题的追思会上,马斯曼高度评价林的功绩,“不得不承认教育家林的体操教育理论合理而严谨,是他开启了根基扎实,思路清晰的体操教育研究。但我们也应看到他的体操教育并非凭空而来……”对林的体操教育思想产生影响的思想家有蒙台涅(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麦卡利亚里斯(Hieronymus Mercurialis)、天梭(Simon Andreas Tissot)、富乐(Francis Fuller)、裴斯泰洛齐、萨尔兹曼(Christian Gotthilf Salzmann)、古茨穆斯、维斯等。但罗斯坦认为,这些人“对体操教育理念的理解均不够全面,林深刻地把这些理念予以统一把握,使之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得以体系化”(成田十次郎,1977)。
3.3 从军事化转向民众化的“丹麦体操”
初期的“丹麦体操”教育,同样主要学自古茨穆斯。1884年,丹麦的考察团在观摩德国施尼普芬塔尔(Schnepfenthal)泛爱学校的过程中,学习了古茨穆斯的体操。这是体操进入丹麦国民教育体系的源头(成田十次郎,1977)。拿破仑战争期间,丹麦追随拿破仑,失败后其挪威领土被瑞典剥夺,他们称此为“国耻”。在此背景下,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19世纪初的“丹麦体操”教育,亦开始被国家主义支配。其首要目标是军事作战能力与爱国心的培养。另,如古茨穆斯所言,在欧洲,丹麦官方最早把体操教育列入了国民教育体系,这一举措也刺激了“瑞典体操”教育的切实发展。他还特别强调,真正为“丹麦体操”教育发展奠定基础的是“丹麦国民体育之父”那哈戈尔(Franz Nachtegall)。
大学时代的那哈戈尔原本专攻神学,阅读了古茨穆斯的著作后,才最终决定致力于体操教育(成田十次郎,1977)。19世纪初期的那哈戈尔,同样身处风云变幻的历史环境中。拿破仑战争前,他期望通过体操教育塑造刚健的民众。战争期间,他有意把其教育方案转向军事能力的培养,战后,他又把体操教育的重心转回培养拥有“万能体力”(all-round bodily fitness)的民众(ヴァンダーレン,1958)。
丹麦能够成为欧洲最早在学校专门设置体操课程的国家(ヴァンダーレン,1958)。1799年,他在哥本哈根开办了体操俱乐部(Gymnastische Gesellschaft),后在此基础上于同年秋创办了欧洲最早的近代体操学校。该体操学校采用的内容随后被公立学校及军队所采用。受此影响,1809年颁布的政令规定,具备条件的中学可随时开设体操课程。1814年丹麦颁布的首部义务教育法(针对7~14岁儿童)规定,应在运动场地、器具及授课课时数方面保障小学男生接受体操教育。
初期的那哈戈尔的体操学校,教授的内容基本上是古茨穆斯方案的翻版,后结合丹麦的现实,并借鉴扬的体操思想,其特点才逐渐显现出来。在此过程中那哈戈尔的主要贡献有:1)加强陆海军体操教育制度,强化体操教育的社会影响力。丹麦国王接受该提议,于1804年下令筹建军队体操教官培训学校,并任命他为校长。上任伊始他就编好了专用教科书。考虑到体操进入普通学校的现实,1808年他及时增设了民众学校体操教师培训课程,1809年又专门开设了海军体操教官培养课程,至此,他担起了丹麦所有类别体操教员培训的重任。为使丹麦军队体操教育有章可循,他还在1818年编写了《丹麦军队训练学校新兵体操教育条例》(),并于1837年将该书明确修订为《丹麦军队体操和相关武器练习教学规定》()。2)完善学校体操教育制度,统一体操教育内容。他在推动丹麦农村学校体育发展方面的贡献亦为显著。虽然1814年已有规定农村学校也要开展体操教育,但那哈戈尔直言“直到1826年,也几乎没有落实”(成田十次郎,1977)。针对此状况,丹麦教育部门于1927年发文规定:体操为有志于教师职业人士的必修科目。1928年,在丹麦学校体育发展史上尤为值得纪念。这一年,丹麦国王下旨,全国所有学校必须把体操切实列入教学计划中。为做到有章可循,那哈戈尔组织编写了《丹麦中小学体操课本(1828年)》()、《丹麦学术学校体操课本(1833年)》()(成田十次郎,1977)。总体来看,那哈戈尔的体操教育带有鲜明的军事色彩,在实施过程中注重号令的使用、组织纪律性和动作的统一性、规范性,而否定了个人表现。这样的做法,最终削弱了学习者对体操的兴趣(ヴァンダーレン,1958)。那哈戈尔去世后,管理权移交到军方,体操教育更是大不如前。
1864年后逐渐普及的民众高等学校(The Folk High Schooll),在使“丹麦体操”教育步入民众化的道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864年,普鲁士联合奥地利向丹麦发动战争,再次使丹麦政府认识到提升国民体质的重要性。战争期间,丹麦的体操教育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但随着战争的结束,以及民众高等学校的逐渐普及,军事色彩被削弱。为了使沮丧的国民焕发生活热情,民众高等学校中有教师意识到了重新修订体操教育方案的必要性。特里尔(Tirier)校长的一段发言,更是为“丹麦体操”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说:“这些体操,决不能被军事性等特定目的所左右,决不能以训练的方式制定教学方案。另外,它们也不仅仅是为了提升身体的肌肉力量和灵敏性,而是旨在提高整个人的素质,是连接人格教育的纽带”(Begtrup et al.,1929;ヴァンダーレン,1958)。这段话最终在丹麦民众中引起强烈共鸣。随后,体操被看作了使国民身体健康,精神振奋,促进团结的手段(ヴァンダーレン,1958)。
1884年,拉斯穆森(Niels Hansen Rasmussen)把林的“瑞典体操”引入了西兰岛的瓦尔基尔德民众学校(Vallekilde Folk School),后又很快被推广到了其他民众学校、射击俱乐部及大中小学。随着1899年体操手册的刊发,“瑞典体操”最终被正式列入丹麦学校教育体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瑞典体操”动作不连贯、缺乏整体性、缺乏美感、僵硬、呆板、乏味等问题的批判越来越多(王恒等,2017)。在这样的批判声中催生了布克(Nicls Bukh)的“丹麦体操”。
通常来说,“丹麦体操”并非指那哈戈尔的体操,而是20世纪20年代民众高等学校的布克借鉴古茨穆斯与扬的体操思想,对“瑞典体操”进行改造后的“基本体操”(primitiv Gymnastik)。总体而言,“丹麦体操”由那哈戈尔开始,布克完成。布克开发“基本体操”的意图是纠正、治疗当时生活造成的丹麦青年身体姿态方面的缺陷与不足,使他们天生的协调美与体能得以均衡发展(竹之下休蔵等,1962)。在练习目标上,“基本体操”突出3点:强健性、柔韧性、灵敏性。强健性,意在改善练习者身体肌肉力量方面的不足,要求练习要有一定力度;柔韧性,意在提升练习者身体各部位的活动范围,使僵硬的肌肉、关节变得顺滑;灵敏性,意在使身体机能更加灵活、迅捷,改善钝化的神经机能。与之相应的练习内容有3个:基本体操、韵律体操、手持器具体操。基本体操主要用于改善身体僵硬、无力、笨拙等问题;韵律体操强调伴随节拍,享受身体各部位自由运动中的跃动感;手持器具体操把手持器具看作身体的一部分(延长),意在增加活动范围与提升动作效果(笹川スポーツ財団,2019)。这一改造,最终把丹麦的体操教育切实引入了民众化的道路。
20世纪20年代,日本体操之父三桥喜久雄留学丹麦见到布克的“基本体操”后感叹,“所谓体操,不能缺失令参与者与观众感动的艺术性。”受布克的启发,才有了三桥的“生命体操”。1929年,倡导“全人教育”的教育家小原国芳(1887—1977)创立玉川学院之始,正是三桥的极力推荐,才引入了“丹麦体操”。小原的理想是,“日本青年必须要有灵活的头脑、灵巧的手、美好的心情、完善的健康”。而这一理想的实现离不开“丹麦体操”。1931年,受小原国芳的盛情邀请,布克一行26人在日本停留了48天,在日本各地进行了40场巡回演讲,由此,直接催生了日本“海军体操”“航空体操”“国铁体操”。1932年,全日本体操联盟创编的“广播体操”(第二体操)也是以“丹麦体操”为原型(玉川大学,2019)。
3.4 施皮斯的形式化学校体操教育
施皮斯(Adolf Spiess)最突出的贡献体现在德国近代学校体操教育(一般称“学校体育”)的创建方面。19世纪后半叶,他的体操教育开始成为德国近代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的主流,并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施皮斯的体操教育能够登上德国历史的舞台,并长期占据统治位置,不仅是顺应了当时社会、教育状况的需要,还与政府期望用它抑制反体制的扬的社会体操有关。1820—1942年为“体操禁止”时代,但并非完全禁止。19世纪20年代末期,在一些进步人士的强烈要求下,普鲁士当局做出让步,允许在严格监管下开展体操教育。当然,扬的“德国体操”仍在被禁之列。30年代普鲁士当局开始在学校推行体操,这可看作抑制扬的影响力的一种积极应对。当局对学校体操教育的开展进行了几个方面的调整。在目的上,培养军事能力及维持健康,在内容上,城市中室内的医疗体操、秩序体操取代了郊外阳光下的自然运动(成田十次郎,1977)。
1842年,“体操禁止”令解除后,近代“德国体操”教育的开展,与以德意志统一、自由为己任的社会体操教育对立的格局。推出的相应规定包括:将学校体操教育的目的限定为身体的塑造、健康的维持与增进,以及兵役的训练准备。禁令解除后成立的“德国体操”团体的政治色彩更加强烈,也逐渐失去了民众的信任(成田十次郎,1977)。
在上述背景下,施皮斯登上了德国近代体育的舞台。他与其追随者的体操教育活动,得到了政策上的支持,反动派和中间派的声援。然而,其代价则是抛弃了古茨穆斯及扬的进步性(成田十次郎,1977)。概括而言,前文提到的维劳密、古茨穆斯、扬等人倡导体操,意图是把之作为德意志国民教育的一部分,塑造具有进取精神的新式德国人,实现德国的统一,把封建的德国改造为以市民精神为支撑的德国。施皮斯的学生时代曾深受扬与裴斯泰洛齐的影响,他在阅读了扬的《德国体操术》后亦曾公开表示“我在《德国体操术》中找到了热爱祖国的食粮。”只不过,他所说的“祖国”是当时腓特烈·威廉四世统治下的普鲁士王国。在他看来,开展体操是为了维护现有社会体制,培养为之奉献一切的“臣民”。
古茨穆斯及扬极力否定的军事训练方法,施皮斯却大为推崇。在施皮斯眼中,只有体操教育才是培养“臣民”的最好方式,理所应当与军事训练相结合。这样的想法,在他1842年向普鲁士提交的《体操列入国民教育的提案》()中就已显露。该提案明确提出的一条条款为:“作为后备军训练的体操”。另,在论及导致道德沦丧、偏重智育、体质低下这些当时民族生命力弱化问题的原因时,他归结为国民教育乏力。这与泛爱派体操教育家的观点非常一致,只不过,追究造成这一问题的社会根源时,古茨穆斯等人将之归结为封建社会本身与教会强权教育的必然,施皮斯对此则避而不谈(成田十次郎,1977)。可以说正因理论上契合了独裁的政治学、教育观,他的体操才得以“名正言顺”地进入学校(ヴァンダーレン,1958)。
施皮斯创建了德国近代学校体操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赋予了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各自应有的位置。虽然皆把体操看作国民教育的重要手段,但扬认为这一愿景的实现,应主要依靠体操学校中开展的针对青少年男子的有组织的体操活动,施皮斯则认为这一愿景的实现,首要条件是学校体操教育体制的确立。为防止社会思潮“毒害”青少年,他认为最合适的教育只有学校体操教育,因为藉此可营造井然的校园秩序。他强调,学校体操不只是一门教育科目,还是青少年学校生活的场,具有真正的学校教育意义。他看重学校体操教育,跟他认为唯有学校体操教育才是社会体操教育的基础的观点有很大关系。这扬弃了学校体操与社会体操之间的对立(成田十次郎,1977)。
1842年,施皮斯向普鲁士政府提交的《体操列入国民教育的提案》,对内容设置、教材排列、师资配备、教学时间安排、设施配置、评价方式、惯例体操活动安排、体操教育与军人培养的关系均做了详细说明。这可以看作他的学校体操教育实施方案。进而,在1847年的《关于学校体操教育》()中,他又细致分析了学校体操教育成立的条件。在他看来,首要条件为所有学校体操课程必修制度的确立,“与其他科目同样,必须在学校法规中明确规定参加体操教育是所有学生的义务”“体操教育应面向所有青少年,即,它不仅应面向在校学生,还应面向毕业后的青年及成人,是男女都必要的教育手段”(成田十次郎,1977)。他用这样的标准衡量认为,之前的体操教育在设施、受众范围、师资力量、指导力度等方面做得完全不够。他称之前德国的体操教育为“旧式体操教育”,即“扬-艾思林(Eiselen)的体操教育”(成田十次郎,1977),及对此发展的柏林派的体操教育。
施皮斯指出“旧式体操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培养的是有违道德、狂妄傲慢之流;2)把学校体操与社会体操对立看待;3)由不懂教育的人指导、管理;4)体操设施设置在偏远的户外,且在天气恶劣时无法活动;5)仅适合少数身强体壮的青年;6)女子被排除在外;7)教材体系无视学校、年龄、性别的差异;8)练习时间的安排欠周全;9)批量化指导(成田十次郎,1977)。在他看来,正是这些问题阻碍了体操的国民化。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的改进措施有:采取年级学分体操(Klassenturnen)教学制度;与其他课程同样在正课时间内安排稳定的体操教学时数;根据学校性质培养不同类别的体育教师;在校内建设体操场馆;配备相应的器具;以有秩序的徒手集体运动为中心进行教材分类、排列;在命令下开展有秩序的徒手集体运动;不分男女,体操是每个学生的必修科目。正因这些举措,施皮斯才被后世称之为“德国学校体育之父”“女子体育之父”(成田十次郎,1977)。
针对施皮斯的批判,扬的阵营予以了猛烈反击。其中扬的学生马斯曼的反击最具代表性(成田十次郎,1977)。1843年,马斯曼就任普鲁士体操教育最高行政长官,各地体操教育重建状况调研报告让他喜忧参半。喜的是,他在教育一线看到了“德国体操”复兴的希望;忧的是,在学校中被强制推行的“自上而下”(von obenherad)的体操教育,“仅仅是一门压迫青少年的科目,并未被看作强化、锻炼青少年的身体,提升他们的精神境界的课程。”在他看来,“德国体操”绝非只是身体活动,更是生活。”承载着唤醒国民精神与共同体意识的“德国体操”,决不能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必须采取“自下而上”(von unten auf)的方式。基于这样的考虑,他认为施皮斯的体操教育“脱离青少年,且无根基”,只不过是“荒唐的形式主义”(成田十次郎,1977)。进而,他提出了复兴普鲁士体操教育的方案《今后体操教育制度的特征》()。 该方案与施皮斯针锋相对,主要主张有:在快乐共同体中活动,依据年龄及运动能力分班,自由参加,一地一设施,“体操教育委员会”负责体操教育管理,周三、周日午后练习(成田十次郎,1977)。遗憾的是,马斯曼的方案并未被反动的普鲁士官僚政权采纳,最终被强行实施的依然是施皮斯的方式(成田十次郎,1977)。
概括而言,施皮斯激烈批判扬的体操教育时,犯了根本性的错误。他并未能正确领会扬的国民体育理念,即,扬倡导的“超越已有学校教育框架,以自由、自主、平等、共同体为基调的,注重青少年政治、道德活动的‘德国体操’教育理念”(成田十次郎,1977)。扬的国民体育体系中,实际上包括学校体操教育与社会体操教育,他之所以把重心放在社会体操教育上,很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在已有体操教育体制之外,寻求新的可能性。但也的确如施皮斯所言,扬的体操教育确实存在教材体系、学习形态等方面的不足。
使施皮斯的体操在制度上成为德国近代学校、社会体操教育主流的,并非其本人,而是他的学生摩尔(A.Maul)。“国民教育中体操教育的确立,要以学校体操教育为基础,把社会体操教育赋予继续教育的位置,以使体操成为‘国民的习惯’。”施皮斯的这一夙愿,在19世纪60—70年终于由摩尔为其实现。由此也成就了施皮斯-摩尔体操教育时代(成田十次郎,1977)。
摩尔忠实地继承与发展了施皮斯的体操教育思想,恪守“身体的完善”为体操教育的使命。“身体的完善”意指身体(体能)的灵活与技能的掌握。身体的灵活,指能够做到精神自如地支配身体活动。“要把青少年的身体培养成不易生病,结实有力,生命力旺盛,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听候精神召唤的道具。”于是,他认为“体操教学既是青少年(身体)的训练(Zucht),也是秩序的修炼(Ordnung)。”“必须从根本上使学生习惯尊从这样的要求。”为此“在体操教学中,必须做到让学生毫不犹豫地听从命令。”教学方法方面,他在施皮斯基础上提出了5级练习法:自由练习、课题练习、号令练习、棒令练习、连续练习(成田十次郎,1977)。
在德国近代体操教育制度化过程中,施皮斯-摩尔的体操教育占据了主流。大力倡行形式主义的集体徒手秩序体操。在这样的信条下,注定要抛弃泛爱派体操家及扬等人倡导的自然主义、进步主义精神。“自然主义体操教育”(Natürliches Turnen)(一般称之为“自然体育”)创始人高尔霍夫尔(Karl Gaulhofer)与斯特蕾西(Margarete Streicher)曾批评指出:“在那样的方式下,教师只能依据被规定好的套路(drill)教授,没有自由发挥的空间……摩尔与施皮斯一脉相承……此前我们的学校体育,除施皮斯-摩尔方式之外,别无其他,作为教师入门材料的教科书、辅导材料亦然”(成田十次郎,1977)。
3.5 三大体操的传播
进入19世纪后,在战争频发的大环境下,欧洲诸国的国家主义色彩极为鲜明。“严整的体操训练对处于战争威胁下的国家而言,独具魅力。”这一时期,欧洲诸国积极引入三大体操,尤其是德国、瑞典的体操,即便作了适当的修正,也并未脱离备战的意图。巴尔干半岛长年交战,保加利亚于1931年立法,规定所有人在21岁前必须接受德式体操教育。南斯拉夫对“德国体操”“瑞典体操”进行改造,注重器械体操及双人组合造型体操,突出动作的连续性。总体来看锻炼身体、保家卫国是这段时期巴尔干半岛体操教育的主旋律。比利时于1830年获得独立,但受战争余波的影响,及其非洲殖民地刚果热带病的困扰,更为关心体操的健康促进作用,学校中广泛采用的是“瑞典体操”。1918年建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其体操教育的国家主义情结孕育已久。19世纪中叶解放斗争时期,他们就已成立全国体操协会,倡导以“民主、平等、友爱、爱国”为理想追求的索科尔(Sokol)宣言下的爱国体操运动。其他欧洲国家体操教育开展的状况大体类似,芬兰起步于“德国体操”,希腊先后推行过“德国体操”及“瑞典体操”,挪威则深受瑞典与丹麦的影响。(ヴァンダーレン,1958)
与欧洲国家相比,这一时期美国的国家主义色彩明显淡化,他们并不看重体操教育在道德及意志品质方面的功效,主要关注的是体质健康方面的功效(Siedentop,1977)。17世纪欧洲人登陆美洲大陆开始,就已有竞技运动(sport)活动的记载。不过,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美国学校体育课程的主要载体同样是体操。19世纪50年代,受欧洲体操教育的影响及南北战争期间战斗力培养的需要,体操开始成为美国中小学教育课程体系的一部分。三大体操在美国均能见到,只是地域不同、类型不同而已。
日本引入欧洲近代体操,主要与幕府末期的军制改革有关。1872年,学校开始出现体操课程。该年,模仿荷兰学制“体术”作为学校教育课程之一。该学制颁布初期的体操教育,强调身体为立身处世之基,与军事无关,采用的练习内容以榭中体操法图与东京师范学校体操图为主。1878年,为了培养体操科师资,文部省开设了体操传习所,聘请美国人李兰土(George Adams Leland)传授普通体操(normal Gymnastics)、轻体操(light Gymnastics)(竹之下休蔵,1962)。藉此奠定了日本学校体操教育的基础。“使健康者的身体更健康,使虚弱多病者的身体恢复强壮。”此时的体操带有鲜明的保健性质(高橋健夫,2015)。然而,自1884年开始,文明开化的体育启蒙论日渐式微,富国强兵主义的体育论迅速抬头。在森有礼的推动下,1885年的《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将兵士体操列为了学校法定内容。以此为铺垫,1886年后的明治时期,日本的学校体育步入了普通体操与兵式体操并重的时代(高橋健夫,2015;竹之下休蔵,1962)。
清末民初我国的体操教育效仿明治后期的日本,以兵式体操为主。1840年鸦片战争后,新式军队及新式学堂中已见到体操活动(白刚,1999;潘志琛,1989)。甲午战败,八国联军入侵,最终迫使清政府于1901年推行新政。在赴日考察、留学人员的影响下(周亚婷等,2017),清政府于1904年初公布了《癸卯学制》(《奏定学堂章程》),该学制对开设兵式体操必要性的解释为:“中国素习,士不知兵,积弱之由,良非无故……兹于各学堂一体练习兵士体操以肆武事……”清末民初军国民体育的时代由此开始。进而,1906年的《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附上谕》明确把“尚武”列为了教育宗旨之一,强调体操科应以兵士体操为主(舒新城,2012)。概而言之,晚清政府倡导军国民教育,重视兵士体操的主要意图有:1)“强兵”,扩充兵源;2)改变“士不知兵”的状况,培养懂军事的官吏;3)“全国学校隐寓军律”,通过军事纪律管控学生(苏竞存,1994)。民国政府成立之初,迫于当时国内外形势,蔡元培的推动(苏竞存,1994),以及戊戌变法后逐渐形成的强兵、强种、强国的体育观念(罗时铭,2008)的影响,采用的仍然是军国民教育理念下以兵式体操为主的体操教育。
4 启示
1)清晰“身体教育”的内涵是反思近代体操教育的前提。“身体教育”何谓?追溯近代体操教育出现的背景可知,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背景下,身体得以解放,近代医学、思想领域开始讨论身体教育的重要性,这为近代体操教育的创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可见,近代体操教育的上位概念为“身体教育”。而“身体教育”的同位概念为“精神教育”或“学问教育”,在众多近代体操教育家眼中,“身体教育”为完人教育一个不可或缺的领域,近代体操被看作了实现“身体教育”的载体。“身体教育”的载体不仅有体操,还包括吃穿住行等日常性身体运动活动。在产业发展、民族危机的背景下,日常性、劳作性身体运动活动已经难以满足时代的需要。于是,近代体操被人为制造出来。在内涵上,体操教育比“身体教育”狭窄得多。如果从当时把“身体教育”与“精神教育”并列考虑的逻辑来看,“身体教育”类似于“感性教育”,而“精神教育”则类似于“理性教育”。如此解读,可以发现从“感性教育”角度思考“身体教育”内涵的新思路。重新审视把“增强体质的教育”称之为“身体教育”的观点,会发现这样的界定方式并不恰当,“增强体质的教育”充其量只是“近代体操教育”的一部分,且内涵上不如“近代体操教育”丰富。
2)正确认识身心关系是提升体育课程地位的出发点。身体教育与学问教育或精神教育是何关系?如前所述,欧洲近代社会身体解放后,身体教育的讨论成为可能。只不过,身体教育与学问的教育(或精神的教育)虽然被看作了同位概念,但是二者关系则是“手段-目的”的关系,身体教育更多被看作了增进健康、精神教育的手段。实际这一关系在近代体操教育出现之前就已注定,洛克的“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的观点(《教育漫画》),卢梭的“身体健康是所有精神教育的基础”的观点(《爱弥儿》)正是这一关系的早期揭示。近代医学领域则主要从身体健康的角度倡导身体教育。近代体操教育发展过程中,维劳密把身体看作“心的命令得以实现的道具”的观点,古茨穆斯的“人所有身体方面的素质既是精神的教师,也是精神的仆役”的观点,均未跳出“手段-目的”关系的框架。在这一关系中,更被看重的是“目的”,而非“手段”。今日,这一关系的影响依然深远,国际性体育课程边缘化问题正是其体现,“在学校课程,它至多被认为占据一个卑微的位置,在许多国家,体育课程并没有被接受为一个能提高孩子智能的高级传统学科”(Hardman等,2002)。可以说,体育课程地位的提升,离不开学理上身体教育与学问教育或精神教育的关系的重新讨论。
3)尊重“自然性”是体育课程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体育课程、教学中应该如何处理“自然性”问题?近代体操教育创立过程中维劳密、古茨穆斯均把“自然性”(“自然主义”)看作体操教育方法的总原则。尊重“自然性”,即古茨穆斯所说的,必须与学习者的发育、发展保持一致,必须尊重学习者的自发性。然而,在近代体操教育发展过程中,随着维斯把力学原理作为体操分类原则,放弃游戏运动;扬抛弃“感觉训练”内容;林以生理学为理论基础,注重身体机能的发展;尤其是施皮斯在“臣民”教育理念下,把体操教育改造得整齐划一,机械僵化之后,近代体操教育一步步远离了“自然性”的初衷,愈加变得形式化。高尔霍夫尔与斯特蕾西提出自然主义体操教育(自然体育)的主张,正是为了解决近代体操教育的弊端。从学习者发展的角度来看,“自然性”可看作由感觉、感动、感情构成的主体的感性能力。体育课程中“自然性”问题的清晰化,一方面需要深入探究“自然体育”内涵,另一方面需要理清体育与感性的关系。
4)统筹考虑运动文化本身的属性是客观定位体育课程的基础。体育课程的根本使命应该如何界定?一门学校教育课程的定位,需从国家(社会)需要、个体(学生)发展、课程载体本身的属性3个方面综合考虑。近代体操教育创立阶段,古茨穆斯等秉持“自然性”(自然主义)教育方法论,在考虑体操教育体系时尚能做到从国家(社会)需要出发,兼顾个人发展。但随着国家主义的兴起,为了储备军事力量和产业劳动力,则主要是从国家需要出发,这一点在施皮斯的学校体操教育中体现的最为鲜明。在近代体操教育发展全过程中,与另外2个方面比,“课程载体本身的属性”的讨论则被严重忽视,并未从历史性、社会性存在的身体运动文化本身的属性考虑体育的根本使命何在。20世纪20年代后,世界各国相继把田径、游泳、球类等竞技运动作为体育课程的主要载体后,这一问题是否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变?从近100年来体育课程目标表述上游移不定的状况,以及当下“目标引领教材”的说法来看,这一问题依然未根本解决。
5)竞技运动作为体育课程主要载体的依据有待深入探讨。近代以来,最初成为“身体教育”手段的何以是近代体操?后来又因何用竞技运动代之?把近代体操与竞技运动对比的话,会发现竞技运动的历史要久远得多。据沃尔夫冈·贝林格的梳理,自古希腊奥运会以来,竞技运动的开展不但从未真正间断,而且运动项目数量蔚为壮观,开展方式异彩纷呈,竞技运动在人类文化史上完全堪称一枚耀眼的活化石(沃尔夫冈,2015)。即便在“自然性”方面,竞技运动比近代体操也并不逊色。然而,何以最初进入近代国民教育体系、近代学校课程体系的,不是竞技运动,而是近代体操?梳理可知,这与近代产业发展、时局动荡背景下近代国家需要的人格样式有关。但除此之外,是否与当时竞技运动本身的样态等亦有关系?另,又因何于上个世纪竞技运动取代了近代体操?竞技运动取代近代体操之后,体育课程的性质是否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近代体操教育时代的问题是被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另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