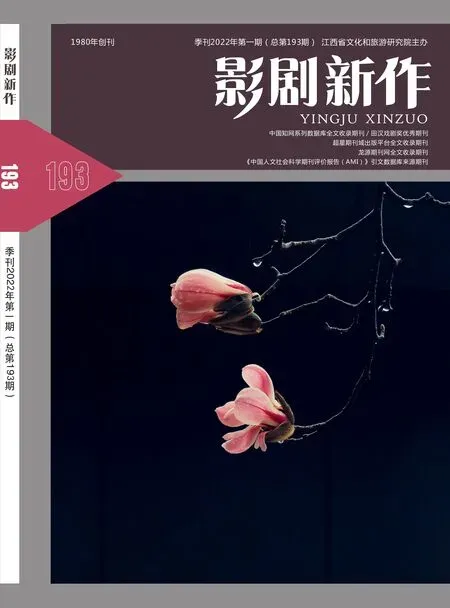近代日本民族音乐在上海的传播与实践
——以《申报》为例
2022-11-05田哲雅
田哲雅
中日这两个“一衣带水”的国家,拥有其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但溯源中华文明却更为久远,为东亚文化之宗邦。历史上,中日间因较近的地理位置而交流频繁且甚早,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中就已记载“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的信息。发展至隋唐时期,日本的留学僧、留学生、东渡日本的鉴真和尚等两国人才的互动,也促进了彼此文化的交流,此时中日间的文化、政治、经济的交流也达到了鼎盛时期。正是因为中日地理与历史、空间与时间上的紧密关系,中日间文化传播交流与比较的研究在国内学者的域外研究中始终都是一个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其相关研究成果也非常之丰硕,如张前的《中日音乐交流史》、徐元勇的《中日音乐文化比较研究》、李美燕的《日本正仓院“金银平文琴”的音乐图像研究》等等。胡斌、洛秦在其《中国学者的音乐人类学域外研究》一文中对中国学者的域外观察与研究进行了梳理,勾勒出了国内学者作为观察主体与表述主体的发展状态,其中关于中日音乐文化传播与比较的研究,还以专题的形式对其进行了梳理分析。可见这一领域研究成果之丰富性与重要性。
对近代存在于我国的任一外国民族音乐的研究,都离不开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上海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巴黎”,更是日本人眼中“魔都”与“欧罗巴”。早在建国以前,上海就已拥有电车、商会、银行、舞厅等先进的现代化设施,繁华的都市、夜夜笙歌的十里洋场吸引着不同国家的商政精英、红男绿女。在多变的时局下,上海坚持以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做基础,兼收并蓄,将世界音乐多元文化展现于上海的市民文化生活当中,使得丝竹琴箫、歌剧、芭蕾交相奏演。
而创刊于上海《申报》中就记载有关于日本民族音乐的讨论与研究,这些讨论不仅丰富,而且能看出日本民族音乐以新闻、音乐会及论文等不同形式传播到上海市民的文化生活当中。本文意图对建国前日本传统民族音乐传入情况做一梳理,同时结合上海的都市化背景,对日本民族音乐进入上海市民音乐文化生活状态进行解读。另外,从《申报》这个大众媒介的角度探析日本民族音乐传入的程度,以及上海市民对于日本民族音乐的接受态度。
一、《申报》中日本民族音乐史料概貌
《申报》创刊于上海,始自1872年,于1949年终止发行。作为中国第一份商业报纸,《申报》以盈利为第一目的,因此创刊人美查等人对《申报》的发刊内容做出了不同其他报刊的调整,包括允许发表政论文章、重视新闻的真实性、希望内容能够真实的反应人民的实际生活等。正因为《申报》受到了市民、学生、各领域学者等不同人群的喜爱与支持,它存在于中国达78年之久。它以新闻、图片、文论、广告等形式记录了1872年至1949年之间中国社会、历史、市民生活的发展,是研究近代史的一个重要窗口。《申报》中的日本民族音乐资料,从数量、内容及性质三个方面来看,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即萌芽期(1872~1911) 、 繁 荣 期 (1912~1926)和成熟期(1927~1949)。笔者在下文分而述之,以此梳理、介绍《申报》中刊发的日本民族音乐概貌。
1872年~1911年,可以称之为《申报》中有关日本民族音乐报道的萌芽期。有关的资料数量比较少,报道的形式主要以短篇文论为主,广告、新闻不多。内容上多以日人在沪组织的音乐活动为依据,使用百姓能够接受理解的词汇,以简介的方式出现在“纪事”或“剧谈”一类的栏目中,但缺少对日本民族音乐进行详细说明与介绍的报道。如1908年5月31日“剧谈”一文中的简述:“四日人合奏胡琴,三女一男,并坐调弄,音节和谐。与中国古乐相似,亦美观也。”除外,此时期《申报》中还集中报道了有关日本音乐学务内容,它们以文论、新闻的形式对日本学校教授的音乐内容、音乐课程的设置等问题进行了阐述。1903年,清政府迫于朝野上下压力兴办学校废除科举制度,上海的新式教育事业加速发展,促使许多新兴知识分子开始借鉴外国学务设置与自我反思,此时《申报》中有关日本学务、音乐的报道正反映了社会的时事,使民众对日本音乐的发展有了不同的认识。整体而言,早期市民虽不能从《申报》中对日本民族音乐获得充分了解,但已有部分认识。
1912~1926年,可以称之为《申报》日本民族音乐报道的繁荣期,不仅相关报道数量是上一时期的两倍之多,而且内容与形式也异常丰富。从形式上看,新闻及文论仍占主要地位,但广告的加入使得日本民族音乐在上海乃至中国的影响有所扩大。从内容上看,有关日本传统艺能具体内容的介绍开始大量出现,包含了日本传统艺能的三个艺术种类即古典戏剧、乐器、舞蹈,并有非常专业的、内容详尽的文论对其进行阐述,报道大多集中在日本古典戏剧方面,但此时期报道最多的还是不同性质、类型的日本民族音乐类实践活动。不同于上一时期的活动主要由旅沪日本人组织,此时期活动组织者中,日人团体、中国团体、民间团体、政府团体均有出现。如由国人薛芳女组织的筹资活动,活动中有演日本艺伎歌舞(见“贫民女子职业传习所演剧筹资”)。再如由俄国盲诗人爱罗先坷组织的歌舞大会,会中有日本著名艺术家(见“俄盲诗人发起之歌舞会”)。或许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各种新思潮、新理念使当时文化发展呈现出多元化,这时期《申报》中也有学者在论文里表达“面对日本音乐的迅速发展而国人仍思维保守”的感叹,如1926年8月8日《论我国俗歌的和声》一文,作者就日本音乐和声的丰富性说到:“其实这在于我国早属过去了,但现在反落于人后真令人可惜”,这些论文展现了逐渐觉醒的国人对世界及日本的理性认识与反思。整体而言,这时期《申报》的日本民族音乐丰富多彩,从中也可看出上海市民对日本民族音乐不仅有了基础理论上的认知,也已有实践上的感受。
1927年~1949年,是《申报》日本民族音乐报道的成熟期。首先,单从数量上看,它是《申报》日本民族音乐报道最多的一个阶段,内容上继续出现了介绍日本传统声乐、器乐、舞蹈的新闻、论文及广告,但研究程度更加深入,尤其是介绍日本民族音乐书籍、论文的报道,内容涉及日本舞蹈发展变迁、日本教育理论及日本传统乐器等等,主题丰富。《申报》中有关日本民族音乐实践活动的报道在此时期达到顶峰,其中又以政治性的演出报道为主,这也是该时期内容中的最大特点,如日居留民团欢迎汪主席的演艺大会、日本东宝歌舞团庆祝国府还都三周年的演艺等。总之,此时期的报道内容更加深入、多样,间接体现了近代学者对于日本民族音乐研究的程度。
二、《申报》中有关日本传统艺能的报道
《申报》中的有关日本民族音乐形态史料分布在1887~1949年之间,大致可归分于日本的古典戏剧、舞蹈、乐器三类,可以说已涵盖了日本民族音乐的主要方面。这些资料来自于《申报》的新闻、剧评、专业论文、广告中,有详有略,从不同角度呈现了日本民族音乐。
相较于其他传统艺能,《申报》中日本古典戏剧的演出报道与研究是相对丰富详实的,包含四种艺术形式:狂言、能乐、歌舞伎和人形净琉璃,还有其他一些小型舞台表演形式的简介。从《申报》的资料看近代日本古典戏剧的传入,可见其具有一定的层次性,既有现场的演出与相关剧评,如《看守田剧后记》一文记录了守田勘弥全班表演的日本狂言名剧;也有细致的介绍性文章,如《日本音乐之概观(二)》一文,对能乐的概念、发展、研究现状及相关表演团体、舞台的资料等。更有相关书籍的出版,如北新书局发售的《狂言十番》(周作人译)。由此可见,近代日本古典戏剧在《申报》以不同的表现方式和不同程度的介绍使上海市民对其有了深入的了解。
《申报》中对于日本传统的舞蹈表演艺术的报道也较为丰富。从资料上来看,日本传统舞蹈虽有商业娱乐性的演出,但几乎都依托于国内外民间团体组织的公益募捐活动、政界组织的联欢会以及各种开幕、闭幕式等,并以配角的形象出现,起到调节气氛以及娱乐的作用。如“四郑路通车纪详”中,“日本舞蹈、日本戏”就曾作为娱乐助兴的活动出现在四郑铁路的开幕式。但也有部分存在于广告或论文中对日本传统舞蹈表演艺术的文字介绍或研究,如作者林一的《日本舞蹈变迁简史》;再如,1935年1月26日“荣记共舞台”的广告中对扇舞的介绍:“扇舞用摺扇舞具,由来甚古,日本歌舞妓至今犹自採用,遮掩半面,姿态最美。”整体上看《申报》中对日本舞蹈艺术的详细、具体的介绍不多,但在上海市民的娱乐生活中,日本舞蹈并不少见,它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市民的日常娱乐生活。
相较于古典戏剧与舞蹈,《申报》中有关日本传统乐器的报道较少,除了1929年3月17日“聆日人福田氏吹奏尺八纪”一文,对演奏者、尺八的形制、发展现状以及现场演出情况等多方面进行了较细致的描述、说明,其余只算 是提及到,例如日本筝、三味线、日本琵琶、日本胡琴、尺八、大鼓、小鼓、腰鼓等乐器。在介绍方式上,也多以简介的形式出现在广告、新闻、剧评甚至是小说里,如:1925年5月30日小说《上海蜃楼》(一九一)中:“日本的乐器本传自中国,不过他们把去略略改造,就似琵琶一种,和中国的还不甚相远,不过比较得小一些他们不用手弹,是用一种象牙片拨的,没有我们轻拢慢捻之习,一作声便是一种刚劲之音,也没有中国琵琶的那般幽细绵渺之意。”
三、《申报》中有关日本民族音乐实践活动的介绍
《申报》中关于日本民族音乐实践活动的报道刊发于1891~1949年之间,是了解近代日本民族音乐的重要资料。通过整理、分析,我们对《申报》中日本传统音乐实践活动产生了一个立体、直观的印象。以此时期《申报》中的史料为基础,从活动场地、举办内容以及参与人员三方面来解读近代中国日本民族音乐实践活动的特点。
近代上海日本民族音乐活动场地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半开放性质的活动场地,这也是近代日本民族音乐演出的主要场地,一般由私人、政府或团体组织、建设而成,如日本人俱乐部、南京路市政厅、六三园、四川路青年会、宁波同乡会、中西女塾、外白渡桥偕行社、黄家阙路专科师范学校等。能够进入观演参与其中的大多是某团体会员、知识分子或社会上层人士,在这类地区传播的日本民族音乐文化相较于其他场地更为传统与严谨,虽大多数节目是为助兴,但也不乏有意为中日文化传播交流所设的节目与演讲会。如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学音乐俱乐部组织音乐团,于1922年8月28日入沪至日本人俱乐部交流奏技,并研究中国音乐。另一类是具有商业化的舞厅、剧院、饭店等地,如九星大剧院、大华歌舞厅、新东方剧场(横滨桥演艺馆)、共舞台、英中街利顺德饭店、南京大戏院等地。还有一类距离市民文娱生活最近的演出场地,即不需被邀请或缴纳费用即可进入的公共休闲活动空间,如张园、金神父路青年花园等地。从上述近代日本民族音乐活动演出的场地可以看出,日本民族音乐活跃在各个阶层的上海市民文化、娱乐生活当中。同时,它依托于各种不同性质的实践活动,令上海市民或浅或深的了解、认识了日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特点。
近代传入上海的日本民族音乐主要存在于四种性质的活动当中,一是依赖于各舞剧院及资本公司运作的以谋取经济利益的商业娱乐性质音乐会,他们是近代日本民族音乐在中国商业化传播的例证,如新东方剧场斥重金邀请日本青鸟舞踊场演出,票务分日场与夜场,连演四天。虽然此类活动出现次数较少,但还是利用其良好氛围与精良的设备满足了观众猎奇的心态,促进了日本民族音乐在中国的交流和传播。二是社会各界联欢会。主办人往往是政府、高官、商界领袖等名流,其中作为助兴节目出现的日本民族音乐,要比平日市民所见到的更具有代表性,如1944年2月26日“日德交欢会今日举行”中所报道的会中表演为外间所不多见的剑道方式及日本舞。因此这类活动使日本民族音乐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交流过程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三是慈善募捐音乐会,从《申报》中整理出来的资料来看,日本民族音乐出现在慈善募捐音乐会中的次数最多,活动举办者多为社会团体,观众一般为市民阶层,所以此类活动更好的帮助了上海市民去了解日本民族音乐。四是文化交流音乐会与座谈会,一般由两国音乐文化类部门、团体组织而成,旨在向国人介绍友邦之优秀文化,加强两国音乐文化的交流,出席现场的学者或演员一般为日本音乐文化代表性人物,对近代日本民族音乐在中国的传播与交流产生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在众多不同性质的实践活动中,也涌现了一些入沪传播日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组织团体及人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日音乐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也构成了近代上海音乐舞台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从《申报》中的资料看,以日本音乐名家个人演出,数量上相对较少,但仍具有价值,其中既有日本传统乐器的演奏名家,如“聆日人福田氏吹奏尺八纪”中出现的尺八音乐名家福田氏,还有入沪传播音乐理念与思想文化的音乐理论家,如“专科师范音乐理论之演讲”中所说的日本宫内省乐部讲师理学士、日本有名之音乐理论家田边尚雄。近代入沪演出的团体则有东宝歌舞团、日本帝国剧场守田勘弥等全班人员、青鸟舞踊场,以及资料中记载的无具体名号的“日本歌舞团”,他们的演出内容大多是日本传统歌舞、戏剧等。他们入沪有些是为商业娱乐,有些则是为“文化交流”研究中国音乐,目的各不相同,但都为近代上海市民带去了思想与感官上的新体验。
四、《申报》日本民族音乐史料的价值与意义
自19世纪40年代上海开埠以来,中外的商业贸易中心就开始转至上海,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更加完善纯熟的社会功能如文化娱乐功能也在以这座城市相适的形式满足着城市居民的需求。从《申报》看近代传入的日本民族音乐对上海的影响,第一,它们的出现满足了市民的娱乐需求,尤其是对近代日本在沪居留民。早在1914年,日本在沪资本总额就已超过了3000万美元,日本人在沪居留民团体也不断扩大,到1926年更是突破2万人。正如“看守田剧后记”中所记的守田全班入沪演出的目的:“这一次来沪的原因,初非营业关系,不过是因为旅沪日本人没有名剧可看,所以请他们来开演几天。”与本国市民相比,近代传入上海的日本民族音乐一定程度上更满足了日本在沪居留民的娱乐需求。此外,不止于书案的研究与舞台的娱乐,近代传入的日本民族音乐还丰富了上海的音乐教育内容。在学校教育方面,据1940年11月3日“聘请教员”的广告可知,沪南学校教务处已公开招聘能教授初级学校之日本式歌舞教授入校,可知近代上海学校教育中已有日本民族音乐的课程设置。而在社会教育事业方面,日本同样也产生过影响。众所周知,艺伎为日本的国粹之一,她们以“侍酒筵业歌舞”为职业,主要依靠经过长期严格训练的技艺获得顾客的光顾,是象征着女性独立的一份事业。在上海也曾有过类似此种培养艺伎的学校,据1912年4月30日“心直口快”一文所记,该校由三名国人发起,内设两等学级,教学中用日本各种乐器,学日语及日本跳舞法等。辩证地看,近代日本民族音乐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影响利弊皆有,也侧面的证明了近代日本民族音乐对上海社会、市民影响之深。
作为近代上海发行量最大,影响力最广的报纸,《申报》中的日本民族音乐史料也体现了其重要的作用,首先是《申报》中日本民族音乐资料所体现的商业作用。概观近代上海的音乐文化市场,书籍、报刊、无线电广播、商业音乐会等形式在日本民族音乐中皆有涉猎,并在其中占有一定的比例。而上海市民对有关日本民族音乐的出版物、商业娱乐音乐会以及无线电台的消费无疑促进了上海音乐文化市场的发展。此外,《申报》中有关日本民族音乐的报道和广告也具有一定商业作用,广告中的创作者通过巧妙的构思设计、新颖图片以及一些介绍性的信息,增强了民众的好奇心以及消费欲望。而一些有关日本民族音乐活动的评论或书籍推荐的文章,也会通过专业的介绍、剖析以及导读使读者加强了解和好奇,进而产生消费行为。如《介绍日本的歌舞伎 》一文中作者欧阳予倩的推荐语:“大凡戏剧的组织,除剧本可细读外,其馀台上的顽艺,不看总不能了然。目下日本帝国剧场的名优守田勘弥女优嘉久子等全班到沪,在虹口横浜桥演艺馆开演,大家不妨去看看。”
其次《申报》中有关日本民族音乐的论文,对读者也起着重要思想启蒙作用。自日本明治维新后,其国力以及文化软实力都迅速发展起来,尤其在音乐发展与教育方面有了巨大的转变,这样的巨变也引起了国人的思考与反思,近代学者开始重新客观地认识日本音乐,《申报》中一系列有关日本民族音乐的论文就反映了该现象。在笔者整理的论文类资料中,近一半以上的文章都会在开头或末尾表达“需客观看待今日之日本音乐,寻国乐之出路”以及“国人应摒弃人不及我之狭见”等进步思想。如《日本音乐之概观(一)》一文中的一段话:“日本近代文化进步之速率,实足以引起世界之注意及惊服。他端姑弗论,单观其努力提倡音乐这好现象,已可易人,向日蔑视被邦人态度,进而生敬羡之念矣惜国内社会间,尚有多数‘自尊自大’之民众,素抱‘人不及我’之狭见,不特无世界观念及进步思想,且顽冥拘古,不能享领艺术文化,余有感于是,特草本篇以促励国人......”可见,这些具有警世性的文章不仅使读者对日本民族音乐有了新认识,而且促进了其思想的开化。
最后,《申报》日本民族音乐还体现了政治号召的宣传作用,如果说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等战争是日本对我国国力的削弱,那么“兴亚论”、“大东亚共荣圈”等具有欺骗性质的舆论引导则是对我国国民思想的荼毒。自1941年12月8日,日本联合当时的上海华文报纸《申报》、《新闻报》等以及日文报纸,组建了“旧华新闻联合会”,从而形成了当时战时言论的控制机关,自此,《申报》中的文化交流活动已然成为了所谓的“东亚共荣”战略构想的宣传工具。1942年12月13日,日本著名音乐家山田耕作来沪坦言了它入沪的目的,即从音乐文化入手调和中日人民关系,希望达到真正的亲善,并力促产生与东京音乐文化协会相呼应的音乐文化运动机构,进而在大东亚共荣圈内完成音乐文化网。客观来看,由于受到“兴亚主义”的蛊惑,当时确有一部分日本人是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前来“拯救”中国,因此不能否认这一部分好意,但鉴于“大东亚共荣圈”本身的欺骗性,《申报》中这些类似上述的活动应该被认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借《申报》这个大众传播媒介,向广大读者传递其政治号召。
总之,通过上述对《申报》中有关日本民族音乐史料的梳理与分析,我们从中可以观察到近代日本民族音乐在中国的传播是一种较为全面且具有一定深度的传播。它的全面不仅体现于日本民族音乐文化传入的内容之广,也在于其对上海及各阶层市民的影响之广、之深。从商业的刺激到娱乐和教育,再到文化思想的交流与碰撞,它们极大地丰富了上海的城市文化与各阶层市民的文娱生活。虽说近代日本民族音乐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政治性,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但整体看来其利大于弊。同时,《申报》中有关日本民族音乐的资料不仅为我们构建了近代日本民族音乐在上海的传播轨迹,也推动了近代日本民族音乐文化在中国的交流与发展,是研究中日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