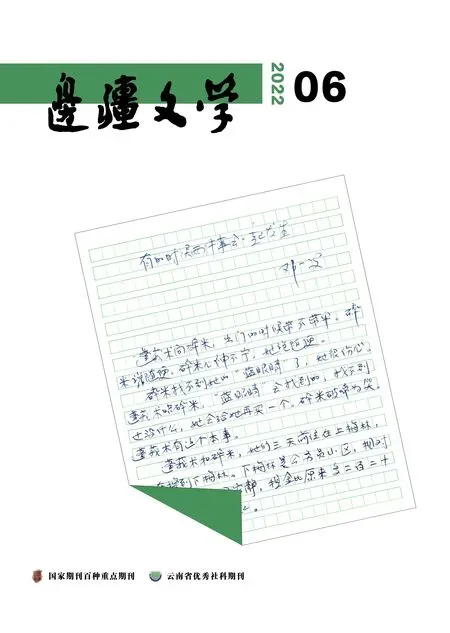失联者 短篇小说
2022-11-05赵丽兰
赵丽兰
在一个饭局上,一个自称狡猾的男人,用酒伤害一个女人。女人用瓢舀酒喝。女人喝一瓢,男人喝一杯。女人表示伤心,却又甘愿。男人说,女人的心,是用来让男人伤的。男人的话真实不虚。这个狡猾的男人其实很可爱。没有谁会当众宣称自己是一个狡猾的、坏的人。只有这个男人做到了,敢于说出真话。《皇帝的新装》里那个说真话的小孩,已经不多见了。眼前这个狡猾的男人,算其中一个。
男人说,女人其实并不海量,他较量过女人的酒,总之,喝不过他。男人还说,一个女人的一生,如果连被男人伤心的时候都没有过,是不完整的。言下之意,女人就是专门等着男人来伤心的。这个男人的确坏。他看透了女人,捏准了女人的七寸。女人的心,从长出来的时候,就是用来被男人伤害的。女人总是等着男人来侵略她们,伤害她们,然后抛弃她们。
人间不可想象,也不可虚构。男人一虚构女人,人间就邪恶。女人一虚构男人,就自我伤害,甘愿被骗。哪怕最后沦落为被男人随手丢在椅子上的那条干瘪的小裙子,也愿意。
人间不可想象。伤心也是,喝酒亦然。
她坐在酒席上,埋头吃菜。坏男人说,人过中年,如果还能坐在一张桌子上喝酒吃肉,一定是生命里的至交。这个饭局约了大半年了。她本想缺席。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就是约一场酒,世界上最不容易的事情,也是约一场酒。想到“容易”或“不容易”,她还是去了。
如果只是喝酒,这个饭局就简单有趣了。男人和女人,偏偏要谈什么伤心不伤心的。试想一下,谈话如果涉及“伤心”与否,似乎就有了男女之间的瓜葛。她早已烦透了这样的逢场作戏。这些货真价实的伤害,一点都不虚伪。这似乎又是有趣的另一种方式。真实的表达,有多种套路。诚如狡猾的男人当众宣称自己坏。承认自己是《皇帝的新装》里那个说真话的小孩。其实,这个坏男人的好,她是晓得的。
这是一次有趣的饭局。有人称自己坏。其实,坏男人并不坏。坏男人像一种冷兵器,有时候,会发出具有侵略性的光。这光,对他认可的人,是善意的。对他不认可的人,是武器,具有杀伤力。有人称自己是糟老头,其实,糟老头并不老。糟老头很好玩,甚至有些可爱。
让她意外的是,一个消失很久很久的人,出现在饭局上。下面,就称他为失联者。
人间不可想象,一如失联者的出现。她刚认识失联者的时候,失联者半隐于尘世。
饭局上,失联者对她笑笑。陌生混杂着熟悉。失联者已然是一个完整的隐者。事实上,失联者一直都是一个隐者。
失联者没有参与“伤心”与“喝酒”的讨论。失联者也没有和她说太多的话。只是时不时地抬起头,看她一眼。失联者和糟老头,头逗头地嘀咕了一晚上,声音很低,不知道失联者和糟老头在说些什么。她只听清楚一个词“干净”。两个人把这个词说了好多遍。某种意义上,干净是一个被人间用脏了词。她不喜欢。
六月里,一个风很好的夜晚,失联者和她在湖边坐了一夜。湖心,渔火点点。天快亮的时候,风大了。失联者说,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事实上,失联者只是穿了一件薄薄的单衣。她的黑裙子被浪花打湿了,裙角,泛上水的亮光。她的脚趾埋在沙粒里,脚腂露在星光下。
那个夜晚的风,真的很好。湖滩上的贝壳,印证了某种干净和互不侵犯。只有流淌的风,异常坚挺。
后来的某一年,失联者给她拍过一张照片,黑白。十一月,暮晚七彩的光,是有一缕落在了她左边锁骨上的。失联者故意忽略了色彩的意义,把它处理成了一缕白光。她的蓝裙子,也被处理成了黑色。只有上衣,黑色依然是黑色。她那天是涂了口红的,颜色,是透明的光感色。失联者假装看不见。
摄影与现实的关系,侵略性是其中的一种关系。拍照的时候,失联者掌握着话语权。因此,拍照片的过程,具有某种强烈的侵略性。那张照片,失联者并没有把她面部清晰的线条感拍出来。失联者只是霸道地强调了光感及黑白的意义。他想制造视角清晰的辨识度,以此扩大情感区域的空白面。照片之于照片,就是拍摄者之于被拍摄者。
假设一下,如果失联者那天手里拎着两条鱼,腾不出手,她可能收获的是另一种意义的失联。关于两条鱼,后面会进一步叙述。
失联者傲慢地忘却了那个夜晚的风,以及那张黑白照片。接着,失联者失联了。
夜有些深了,糟老头建议收杯,就此别过。坏男人还不尽兴,要求再坐一会。女人又多喝了几瓢酒,方得散去。糟老头又和失联者,有更多的时间继续讨论“干净”。
临别,用瓢舀酒喝的女人,大概是真的对其中的某一个人舍不得。坏男人?糟老头?失联者?她猜不准,也不想猜。人间不可想象,人间也不值得想象。用瓢舀酒喝的女人要求和他们一一抱别。于是,大家相互抱了抱。夜色里,来来往往的车辆,无法辨清行驶的方向。城市涌动着细碎的被捕捉又被丢弃的玩场。一如猫和老鼠的游戏。而人的心,永远处于如饥似渴的状态。一如拍照时,镜头后面的那个脑袋。那些转瞬即逝的记录,是使人惊慌的证据。
坏男人抱了抱她,是那种不具侵略性质的抱抱。那一瞬间,坏男人不是冷兵器,是一个暖水袋。失联者也抱了抱了她,是那种看不见灵魂,带着些许原罪感,又互不惊动的抱抱。糟老头只和失联者抱了抱,他们一直谈论的“干净”,在两个糟老头的抱抱里,微距离,对焦精准。在场的人,都看着他们。
这个夜晚的饭局,像一阵风。每个人都能感觉到某种情绪的流动,却看不见,摸不着。
回家的路上,这座城市因为空气质量不好,空气中固体杂质多,颗粒大,折射出来的光就显得强烈。月亮浮在高架桥的半弧上,扁的,被很多大颗粒的杂质晕染包裹,轮廓模糊不清,样子很难看。她第一次觉得月亮这么难瞧。
她的电话响了,是失联者打来的。天气很热,车窗开着。电话里只有风声,听不清楚失联者在说什么。风,大概是摄影唯一无法拍出具体物像的事物。只能借助其他的载体,表达它的形状和颜色。电话里呼呼的风声,惊动了她。饭局上,她面对失联者,尽量把自己装得只是一阵风。她又想起了那张黑白照片。照片上,除了落在左边锁骨上的一缕白光。她的左边锁骨上,还落了一阵风。风的形状,可以借助飘动的发丝看见。
为了听清失联者电话里的声音,她关上车窗。她听清了,失联者问她要糟老头的电话号码。她不解。失联者怎么连糟老头的电话号码都没有。酒桌上,一整个晚上,看他们那么心意相通。一直在热烈地讨论“干净”。临别,失联者和糟老头相互拥抱,紧紧的那种拥抱。她甚至觉得两个糟老头的拥抱,是有能力用来相互伤害的。
她想,失联者真的和人间失联了。失联者瘦了很多。身瘦处便是心瘦处。她也不知道,这些失联的日子里,失联者经历了些什么。
失联者还记得她的电话号码。
挂了电话,她打开车窗。风,一会大,一会小。像某些情绪,一部分在收紧,一部分在延展。有些东西消失了,有些东西显现了。有些在哭泣,有些在欢笑。
靠着车窗玻璃,她在风里,睡了一会儿。腕上的手环响了一声,她滑亮手机。失联者发来一条彩信。自从有了微信,就没有人用短信的方式联络了。除了银行、保险公司、公积金中心、淘宝网站等等机构发来的生日祝福、贷款信息等。失联者像一个穿越到科技时代以外的古旧的糟老头,还玩短信。
彩信是一张照片,落日像一个过期的印章,盖在高架桥的半空。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来来往往的车流里,被碾压。失联者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应该是站在两棵树之间。落日恰好卡在了两棵树之间。有了这两棵树,她不再担心,落日会掉下去。画面中橘黄的光圈,有点像是失联者的沉默不语。艺术是一种保存情绪经验的方式,那些稍纵即逝的触动,一闪而过,如果不记录,就真的会从高架桥的半空,掉下去,被来往的车辆一点一点碾碎。
有天去上班,她看见一个女孩子,举着手机拍天空中的云朵。女孩子拍了一张又一张,换了各种角度各种姿势。她突然担心,女孩子再这样拍下去,如果去约会,就要迟到了。她担心,如果女孩子迟到,被男朋友埋怨,女孩子是否会回答,因为拍一朵云。这是男朋友需要的答案么,显然不是。她期待女孩子的男朋友更多地去强化一朵云的情感意义,而不是女孩子本身。她还希望女孩子会说服男朋友花更多的情感去识别一朵云的形状、纹理,观看云朵色彩变化时,心情的变化,从此,会爱女孩子更多一点,更持久一些。
日落处便是天尽头。
她看着失联者发来的这张图片,一部分情绪在哭泣,一部分情绪在欢笑。
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失联者拍的照片都是黑白。有些照片,故意强调粗糙的颗粒感和硬像。失联者刚刚发来的这张图片,彩色。这是否说明,失联者的内心有了色彩。即使哭泣,也是婴孩般的透明的眼泪。透明,也是一种颜色。
黑白摄影,带给人强烈的故事感。恰到好处的错位性,总是在某个点上断裂、对抗,紧张的胶着状,会让人疯狂。那些需要通过照片陈述的故事,不再是故事,而是事故。
车窗外,橱窗里一闪而过的广告牌,竟然是维米尔的油画《读信的蓝衣少妇》。哦,人间,总是存在着另一个无可想象的世界。这个广告牌,是有思想的。
《读信的蓝衣少妇》描绘了一位少妇,在浑然忘我地想着一个远方的人物或一些事情之时,微微握紧的拳头。维米尔用少妇微微握紧的拳头,传达少妇的专注和与众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少妇读信时嘴巴微张,仿佛正在把一个人的名字念出声来。
少妇笨拙的动作,打动了她。
失联者发来的这张图片,除却欢欣的色彩。却又仿佛在询问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向落日讨要一个答案。她想,失联者在去赴饭局的路上,恰巧碰到高架桥、落日,以及两棵树。失联者拍下这张照片,照片让失联者的内心,在那一瞬间,获得完整,亦获得破碎。印章已过期,人间已然没有了多少意义。
获得完整的失联者,更沉默了。获得破碎的失联者,又加剧了这种沉默。
太多的人,选择了沉默。沉默和安静,是两个层面的意义。失联者是沉默了,而不是安静了。这是一个生命个体不为旁观者所知的伤痛。失联者有些消极厌世。她想,要理解他。糟老头可能就是理解失联者的那个知音。怪不得他们“高山流水”了一个晚上。怪不得他们的拥抱有能力用来相互伤害。可以相互伤害的两个人,关系必是非同寻常。
望着夜空里那个扁扁的难瞧的月亮,失联者和她开始短信对话。
失联者:我应该是消失了。
她:为什么要消失?
失联者:世界不好玩了。
她:以前你并非这样啊。
失联者:也未必像以前那样存在。
她:何种状态存在都好,只要自己快乐。
失联者:谈不上快乐。只是想沉默。
她:是因为世界与你格格不入?
失联者:是我与世界格格不入。
她:希望你在沉默中,开开心心的。
失联者:也不用太计较,反正每一个人都不容易。
她:你要快乐。
失联者:你们快乐即可。
她:不可以,要一起快乐。
失联者:你快乐就好。你瘦了。
失联者已经不是她所熟悉的样子。某一年,失联者喝醉了,坐在大街上,望着电线杆上的一个“爱”字傻傻地笑。电杆上,不知是谁,用白色的油漆,写了一个大大的“爱”字。她用手机拍下了失联者傻傻地看着电线杆上的“爱”字的样子。那个时候,醉酒后的失联者,多么可爱。不用滤镜,镜头后面真实的物像就是黑白。失联者的白发里,夹杂着黑发。黑衣、黑裤、黑脸。电杆上的“爱”字,白的。照片比视频更能保存记忆,可以把流动的风的形状定格成整齐的时间。
她没有把这张照片发给失联者,存在手机里一段时间后,删掉了。她把这张照片的颜色分成了两半,一半黑,一半白。一些如风一样的情绪包含在照片中,风的形状、色彩,甚至味道,都是具体明确的。她用照片保存着某种欲望,在某段时间内唤醒一种称之为柔软的东西。欲望和柔软,有时候是对等的,更多的时候,是相反的,失衡的。一如黑和白的对立。照片可以保存情绪,但无法对公众进行解释。如果有好奇者需要推测、想象、猜想,我们所理解的事实,就成为理解的反面。
这个晚上,失联者喝酒,沉默。
她想起在一本书上看到的一个小故事:
一个男人消失了很久,忽然有一天,他的魂回来了,来见守寡多年的妻子。他不知道哪儿弄了两条鱼,自己提着回来,跟妻子说,我给你带了两条鱼。
这个晚上,失联者像是那个带个两条鱼回来的鬼魂,对酒桌上的人,拱拱手说:
各位兄弟姐妹,很久不见,抱歉抱歉,我只有这两条鱼。我也想带点酒啊、肉啊、烟啊、美女啊,或者快乐啊、荤段子啊,或者别的什么给你们,可是,没有办法啊,我只有这两条鱼。
然后,失联者沉默。除了和糟老头谈论“干净”。
这个世界是如此荒诞,失联者带来的这两条鱼,也是荒诞的。那些照片,发生在荒诞的时间里,必须用荒诞才能解释。
这个晚上的饭局也是荒诞的。坏男人、坏女人、糟老头、失联者,以及她,都是荒诞的。
风吹月亮,月亮还是那么难瞧。拍下这个夜晚的风。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为了在一张照片里,找到风的样子,然后终结。
日落处便是天尽头。身瘦处便是心瘦处。
明明是失联者瘦了,失联者偏说是她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