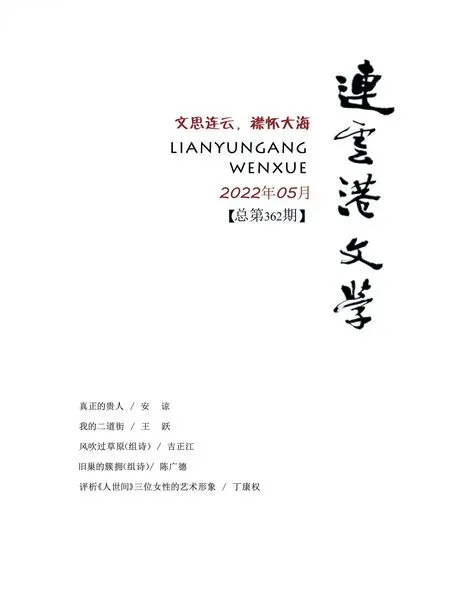乡音乡情
2022-11-05俞雪峰
俞雪峰
乡音是一个温暖的词语,它被文人诠释了更多的内涵,构成了国人独有的一种文化基因。在异乡,举目无亲,听到乡音,就如同见到了亲人。乡音连带着乡情必然会释放出更多文化情感,心照不宣的乡音乡情,也会像炊烟一样,微小,又强大地四处漂泊。
我不知道,身在异乡说着浓重的乡音,是否就意味着对家乡的一种依恋?乡音流淌着血脉亲情的味道,浸润着我的生命之源。我深知家乡对我的重要性,其意义远胜于概念本身,它更像我生命的记忆和符号。
中年从感动自己的家乡出发,或许带走的只是一种流于表象的形式,而承载着感情的内容却沉淀在故乡风土人情里。任凭如何,它都会深刻在故乡流动的光阴里不改初衷。走时,神经脆弱的就像随风摇摆的杨柳,紧缩的心站在故乡延伸的路口徘徊不定。
离开家乡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啊。大客车准时到达,准时离开,不差一分一秒。送别的亲人们,自觉担负起场景描述记录的职责,拉完手、再挥手之间没有电影镜头那般生动形象。因为亲人们都不是演员,描述的手法没有渲染和铺垫,都是自然而然的情动于中的送行者。记忆犹新的情景,难以割舍乡音乡情。痛苦的场面和难舍难分的告别,都沉浸于眼泪和脆弱的心灵。离开了家乡,便意味着离开乡音乡情。乡音辗转到另一座城市的时候,立刻就变得陌生了,就像在陌生的城市见到陌生的老乡一样。虽然彼此感觉非常亲切,却还是那么孤单。有独特方言的城市,自然有它吸引人的地方。身心流离失所,乡音乡情也流离失所……
在异乡触摸到的是全新的、陌生的东西,我带着乡音,说着乡音,猛然之间被异乡庞大的方言所吞没,就像身在洪流中,只能随波逐流了,可又不甘心被洪水吞没,还想奋力上岸。游上来,体味着身在其中却无法融入的疏离感。感到自己孤单又可怜。在异乡的方言里,担心自己迟早会被同化。
刚到异乡,很难一下子适应。我不禁拷问自己:我们背井离乡,到底与家乡有多大因果关系?生活中许多事是无法预知,不可抗拒的,生命中能够被我们所掌握的东西又有多少?家乡的一山一水,在我眼里都是难以割舍的,但在外人的眼里,或许根本就不值得留恋。本来没有雾霾的天空,感觉就像罩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浓雾。所以离开家乡的人注定是漂泊的、无根的,也是悲哀的。
带着悲哀置身异乡的我,就像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漂到哪算哪,哪怕触礁也无所畏惧。漂到头了,再回过头来审视自己低落的情绪。异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让我联想到自己生命的起点,因此勾起浓浓的乡愁。被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所围裹。置身异乡,体验异乡风情,感觉故乡是那么遥远又那么亲近。很想寻找一种乡音的氛围,难遂愿时,自己就是自己乡音,那感觉也是好的。一个人对着自己说家乡话,相当于在自己开创的王国里随心所欲。
异乡的方言时刻撞击着我的乡音,没等我开口,它已经让我“哑口无言”了。我感到乡音微弱的同时,也感到自己的渺小与单薄。家乡在我心里开始隐退,退到脑海中没有一点清晰的记忆。我开始想如何淡化家乡,如何在异乡开始新的生活。然而,无论如何痛苦,无论如何矛盾,乡音却时刻响在耳畔,不时往返于我生活轨迹,即使我不说乡音,可是乡音不是在电话里,就是在眼前萦绕着我。熟悉的乡音,难以改口的乡音,让我在梦里另类生活着。
时间冲淡了乡音乡情。我说着乡音,却很少回去,家乡似乎离我越来越远了。回去得少了,殷殷思念也就少了。除了逢年过节,回去看望父母,其他时间都把自己交给了现在的城市。现在的城市,毕竟是我工作生活的地方,是我生命重新定位的地方,是提升儿子命运和希望的地方。吸引人的地方,往往也是让人丢弃乡音乡情的地方。只要生活好了,一切如意了,口上乡音淡就淡了,心上乡音终究不会淡的。口上不说,都放在心上说。
过去的朋友,随着我的远离,很少来往互动,我和朋友就像故乡和异乡两个天空的云朵,很难碰撞到一起,融合在一起。即使偶尔聚在一起,情分似乎也没有以前那么纯粹了,分开久了,环境抹杀彼此身上原有的味道,连乡音也没有以前那么醇厚了。
有时候,我也突发奇想:让自己彻底抛弃乡音,说所居城市的方言,又觉得太不可能,也有些难。虽然,我也常常学说几句拗口难懂的异乡方言,融入异乡方言的语境里,假想自己也是本地人。却无论如何说得也不够好,不够像。只好苦笑一下,何必难为自己呢?偶尔在有些大场合下发言,用普通话,会被说普通话不太标准的本地人啧啧称赞。不一时丢弃了乡音,而又不会说生活所在地方言,我不知自己从何处来,属于何方。倒羡慕起那些到老都离不开乡音的前辈,他们就像一棵树一样永远深扎在一个地方。一张口,就告示自己出生的位置。
我的户口已经迁出故乡,我不知道我惦记着故乡什么。户口本积压着我的乡音乡情,乡音乡情并没有因为户口迁出而风流云散。乡音留在心中,也留在我生活的这座城市。语言需要交流,文化需要碰撞,碰撞出来精华既要留在本土,也要输送到家乡。这时,我才真正觉得我不留遗憾,不带伤害,走到哪里都有乡音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