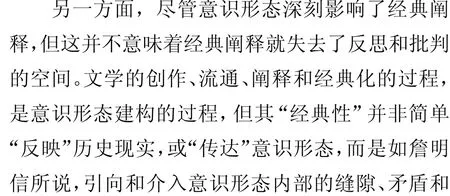“中国卡列班”:《暴风雨》、中国想象与英帝国的文学经典重塑
2022-11-04王冬青
王冬青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英语语言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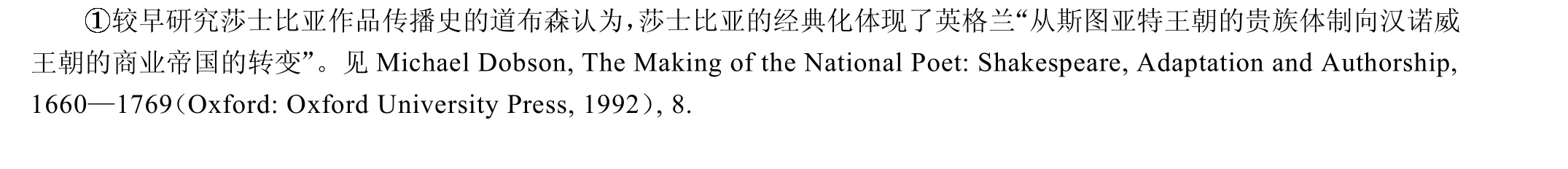
一、英国米兰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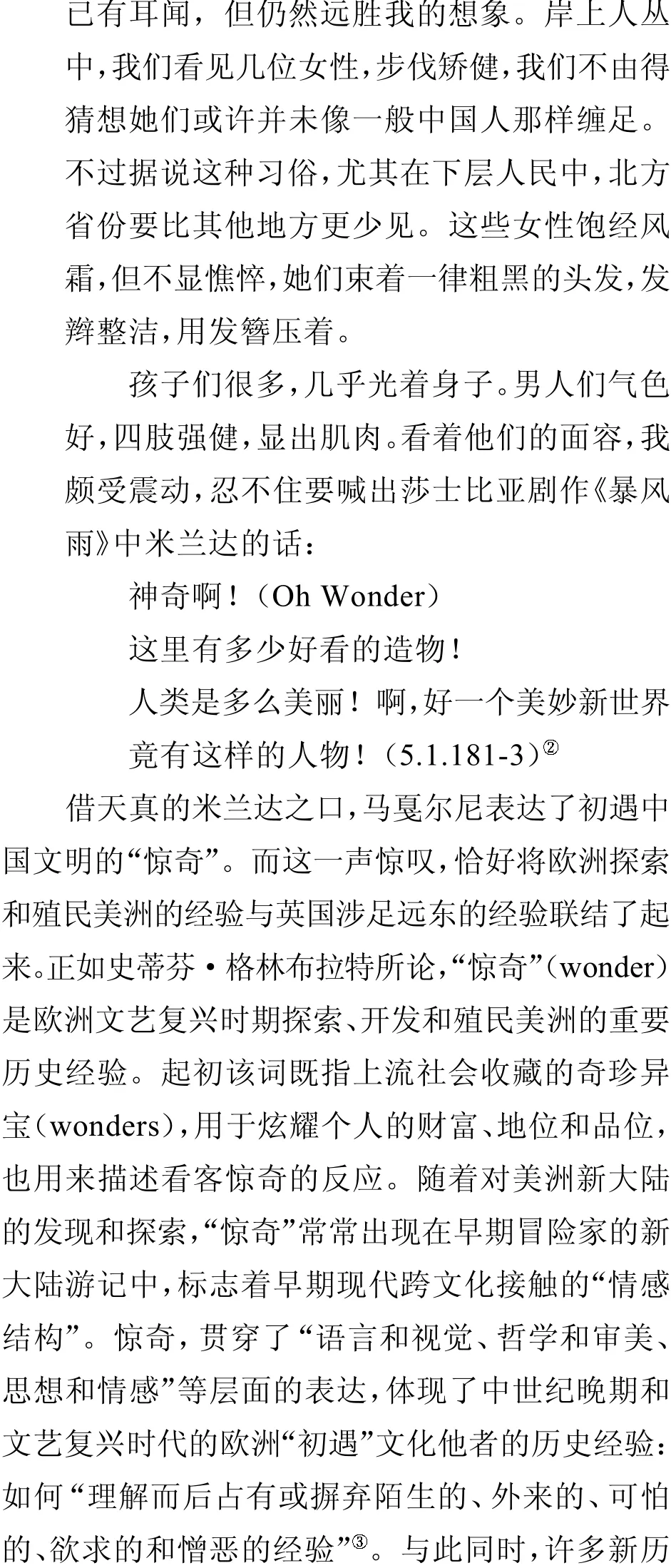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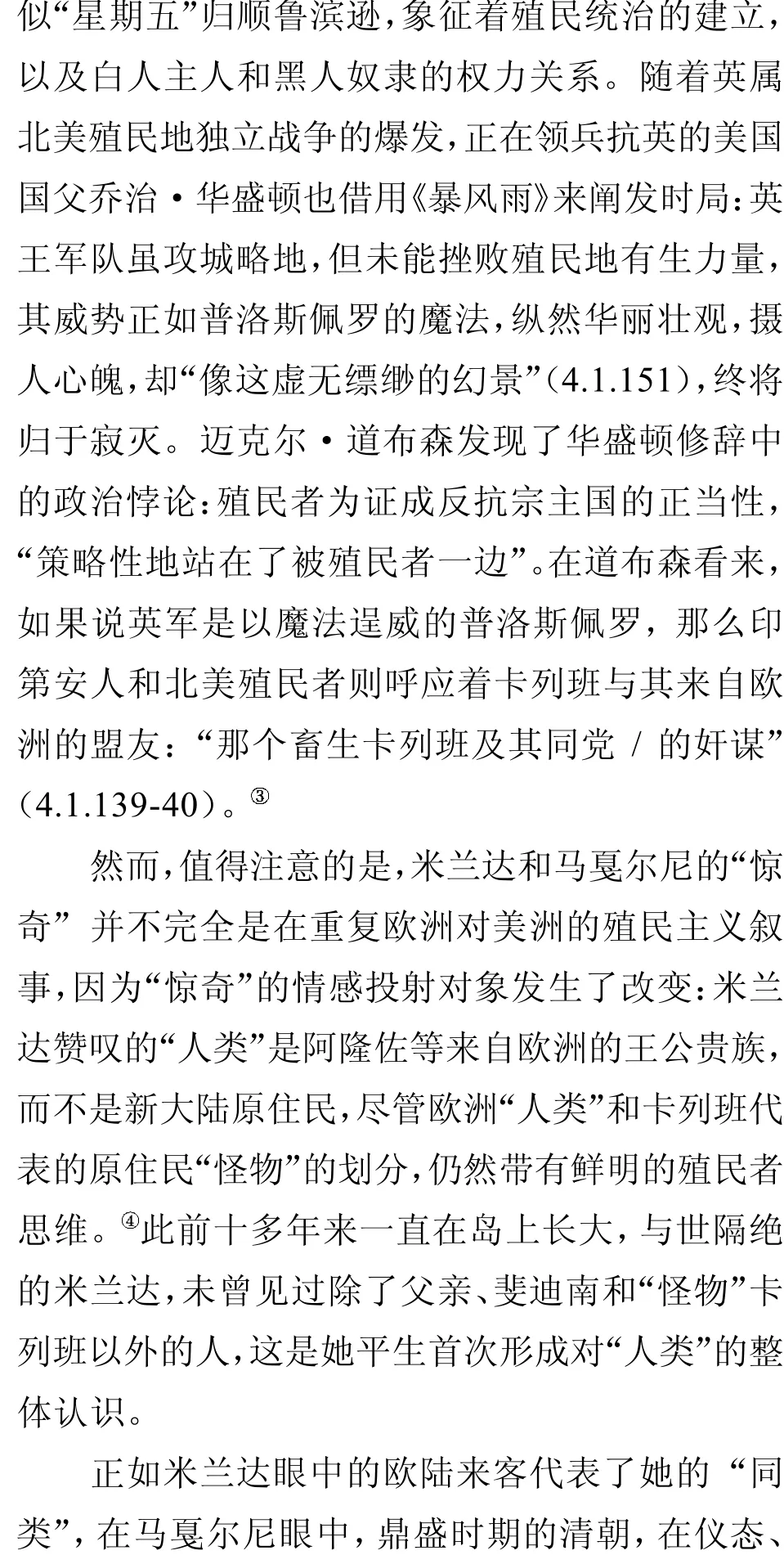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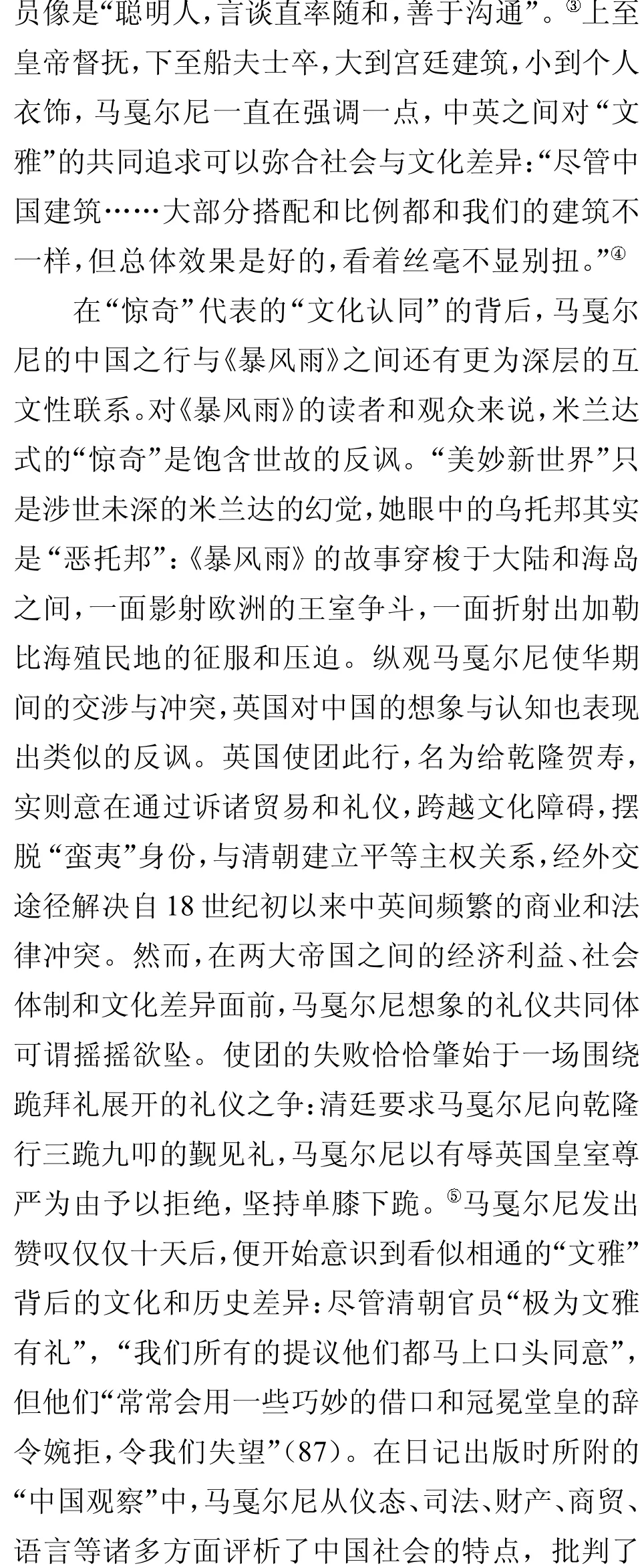

“美妙新世界”的假象:[清朝]朝廷的性格是一种独特的组合:外表好客,内心多疑……(223)。
与神通广大,主宰众生命运的普洛斯佩罗不同,在中国,马戛尔尼代表的英帝国扮演了米兰达的角色,生活在普世主义的幻想中,是女性化、孩子气的,远非日后那个父权式的帝国形象。马戛尔尼的“美妙新世界”,与其访华之行一道,见证的是帝国梦的挫折和启蒙价值观的危机,也标志着包容性的“文雅社会”逐渐走向排他性的“文明—野蛮”的认识论。
二、中国卡列班
在马戛尔尼所处的18 世纪末,清代中国在亚欧贸易中仍处于主导地位,英属东印度公司正竭力争取对华外交地位和贸易特权,因此马戛尔尼总体认可中国的稳定社会秩序、繁荣的商业和文雅的生活方式。然而,马戛尔尼使团和随后1816 年阿美士德使团在访华交涉中遭遇的挫折和冲突,深刻影响和改变了19 世纪的中英乃至中西关系,为鸦片战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美妙新世界”的乌托邦光环褪去,英帝国的征服和教化的冲动开始主导对文化他者的认知。维多利亚时代英帝国海外殖民和贸易的迅速扩张,逐渐召唤出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殖民隐喻:如果说《暴风雨》是一部帝国的传奇,那么如今马戛尔尼的米兰达退场,托马斯·德·昆西笔下的普洛斯佩罗和卡列班登上了历史舞台。威在文化领域的投射,经典化的莎翁作品由此成为帝国文化资本的代表。其中,《暴风雨》在形式上(宗主国的文学作品升华为世界文学经典)和内容上(海外殖民隐喻)都契合这样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在这股风潮下,《暴风雨》阐释的焦点也从普洛斯佩罗-米兰达的婚恋教诲转移到普洛斯佩罗-卡列班的帝国统治,从中产阶级家庭走向了海外殖民地,尽管二者都隐含了父权制的结构。就在维多利亚女王就任“印度女皇”的同年,菲尔伯茨编注的新版《暴风雨》出版了,并成为“拉格比公学版”莎士比亚选集丛书系列之一(the Rugby edition)。他在编者序中主张,在文艺复兴时期英格兰海外扩张的语境下,普洛斯佩罗扮演着殖民者角色,肩负着“教化野人”的“文明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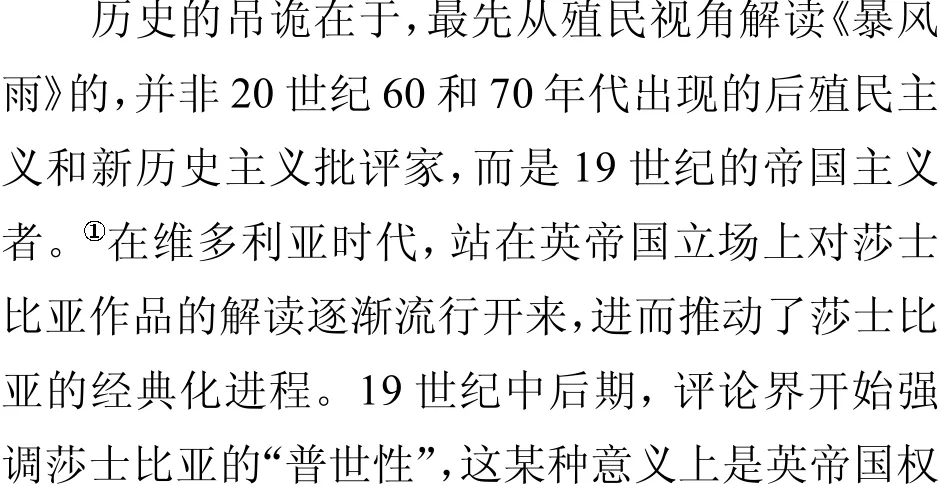
这个角色可能和那个时代的重大命题有着特殊关系,当时我们正发现新国度,驯服未知的野人,建立全新的殖民地。如果普洛斯佩罗可以剥夺(dispossess)卡列班,英格兰也可以剥夺殖民地土著。即使起初接触文明社会会给野蛮种族带来特别的危险,但我们可以证明,由精神和道德上的强者夺取权力是合理的,只要夺权是为了教化野人,使之通人性。这套拉格比版《莎士比亚剧作选》为小八开本印制,是利文斯顿出版社面向中学生推出的平价文学读本。除《暴风雨》外,还包括《皆大欢喜》《麦克白》《哈姆莱特》《科利奥兰纳斯》等,大部分作品的编者为拉格比公校的教师(Assistant Master),而菲尔伯茨亦曾在拉格比公校任教12 年之久,1875年接任贝德福德校长。作为英国历史上最早和最有名望的公学之一,拉格比是文化权势的象征,这些读着莎士比亚长大的贵族学生,日后将肩负帝国的重任。正如霍华德·菲佩林指出的,进入维多利亚时代贵族教育体制的莎士比亚作品肩负着两大使命:英帝国的巩固和英国民族文学经典的形成,《暴风雨》中,如果借用马克斯·韦伯对政治合法性的论述,普洛斯佩罗是魅力型领袖和僭主的结合:一方面,科学和魔法知识奠定了他的政治权威,得以“解放”爱丽儿,“启蒙”卡列班;另一方面,知识和真理又转化为暴力,以“暴风雨”之势驱使爱丽儿,奴役卡列班和惩罚篡位者。


然而,我们往往不甚留意的是,德·昆西的焦虑也暴露了权力话语的危机:和鲁滨逊招抚“星期五”不同,《暴风雨》中殖民者的教化并未成功,普洛斯佩罗教授卡列班语言,却被卡列班用来诅咒,密谋反抗,并要“烧了他的书”,将帝国统治连同与其共谋的知识体系连根拔起,一同摧毁。这表明,历史并未遵循奈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等人的“帝国必胜”式线性叙事,即使在19 世纪英帝国走向巅峰之际,其文化领导权仍在经受挑战。德·昆西的中国论述在中英关系的历史纠葛和现实冲突中穿梭,时而捍卫英国的文明和尊严,时而谴责英商见利忘义地对华妥协,时而咒骂中国是“最恶毒和最愚蠢的国家”,摆出“非人的傲慢”。在这样近乎歇斯底里的仇恨和侮辱看似咄咄逼人,却掩藏着深刻的文化身份焦虑。无论是叛逆的卡列班,还是“傲慢”的中国,都指向了德·昆西焦虑的核心:英帝国虽然凭借暴力建立了半殖民统治,但却尚未建立文化领导权。帝国代表的“真理”尚未确立和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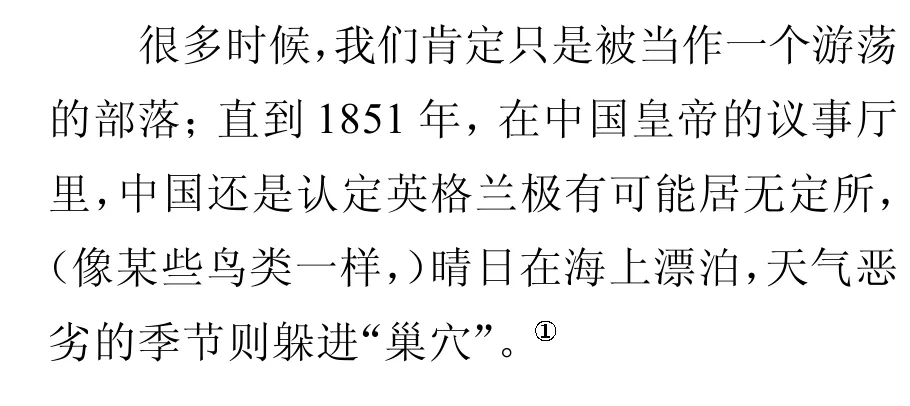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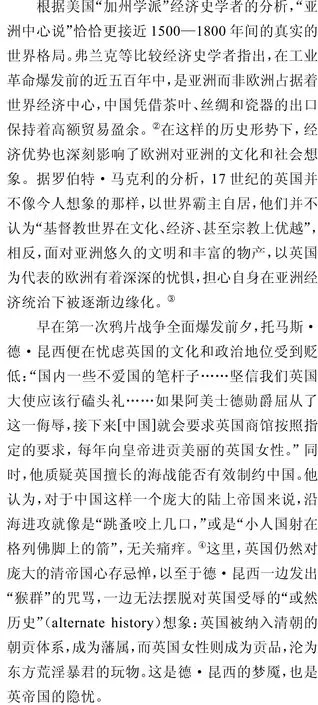

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从小人国眼中的巨人格列佛变为了普洛斯佩罗眼中的野人卡列班,地位一落千丈,但德·昆西的文化焦虑却依然强烈。帝国虽然“制服”了格列佛,却尚未“驯服”卡列班,因此以“书”代“箭”,从暴力征服走向意识形态的教化。在德·昆西看来,英帝国贸易、传教和外交的受挫有着根本原因,那就是“接种”文明的失败,帝国“教化”的失败。运用有机体“免疫”的隐喻,德·昆西称“接种”对中国这个社会有机体是无效的,因为没有古希腊知识传统中对真理的“爱”,中国不具备生产思想的能力。这种无知表现在中国并未认识到不列颠文明的“重大优势”:



结语
如前文所述,许多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研究已经分析了莎士比亚作品中关于非西方“他者”的权力话语,如《奥赛罗》中的种族问题和《威尼斯商人》中的犹太人形象等,揭示了“文本的历史性”。由此,本文进而强调的是,对“帝国”和“殖民”的指涉并不完全是莎士比亚文本的固有“属性”或“内涵”,而是体现在批评家、文人和公众对作品的阐释、编注和传播过程中建构出来的文学形象、审美效果和社会功能。18 和19 世纪莎士比亚的经典化,代表了英国“民族文学”观念和英国文学学科建制化的形成,也作为一种文化运动参与了英帝国迅速扩张并称霸全球的历史过程。以《暴风雨》为例,故事虽然取材于英格兰早期海外扩张,并隐含了帝国的想象,但尚未形成清晰自觉的帝国意识。马戛尔尼和德·昆西在中英交往与冲突中对《暴风雨》的挪用和重释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暴风雨》的殖民话语不仅“反映”了大航海时代海外贸易和殖民的历史现实,同时也是18 和19 世纪英帝国事后建构的产物。可以说,自文艺复兴至维多利亚时代,一部《暴风雨》的改编、评注和阐释史,也是英帝国危机和发展的“症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