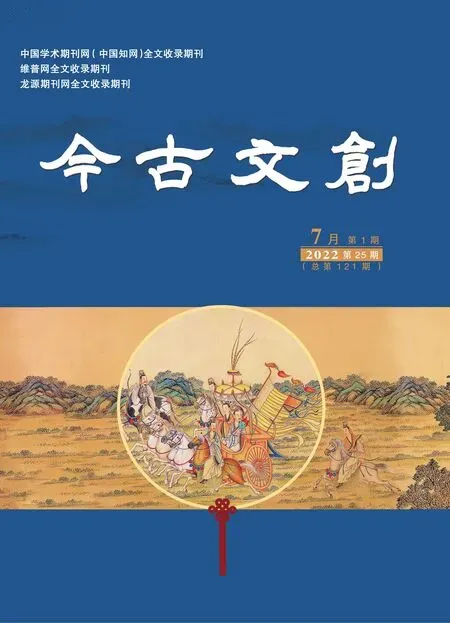先锋文学的崛起与转型
2022-11-01陈小琪
◎陈小琪
(海南师范大学 海南 海口 570100)
先锋文学是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一支,先锋文学的“先锋”性质体现为反对传统文化,有意识地破坏惯有的创作原则和审美趣味,小说追求创作形式和风格上的新,技巧上多用暗示象征、联想通感、剪切拼接等手段组合人事,让读者感受到一种晦涩的阅读阻滞。在先锋文学内部,可以发现象征主义、意象主义、达达主义、意识流等诸多文学流派的痕迹,它反映着作家对身处当代的个人与外界、自我之间畸形的异化关系的不满以及对传统文学的告别和决裂。
一、先锋文学的崛起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外现代主义作品的涌入革新了我国文学创作者的创作观念和方法,先锋文学便在此时异军突起,成为继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思潮之后的又一重要思潮。
先锋文学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改革开放增强了人们对“异类”文化的接受度,也给予了文学创作者大胆实验的勇气,他们不愿纠缠于之前的“反思伤痕”“寻求复古”“生活真实”等问题,转而走向颠覆从前的现实主义传统叙事模式的道路。他们以一种反叛传统的姿态进行创作实验,强调“叙述”本身。正如陈晓明在他的《无边的挑战》一书中所写的那样,先锋小说就是对广义的“传统小说”美学趣味的“挑战”。他们自觉地寻求“形式主体”意识,把“叙述”当作写作目的,在他们的实验中如何去讲一个故事比故事内容本身更重要。他们更青睐于对想象、夸张、虚构等写作手段的运用,借拼接、剪贴内容引起的故事的变形来创造稀奇古怪的情节与细节,并以此更新读者的阅读体验,使读者产生一种对陌生、异常形式的阅读趣味。
先锋文学创作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集中爆发,并以马原、洪峰、莫言、刘索拉等为代表,创作出一大批极具魅力的作品。但后来,先锋小说的技巧性叙述被引向极端,形成了“纯形式”类型化探索的怪圈,先锋作家纷纷走入“自我重复”的创作死胡同里。20世纪90年代,创作队伍的分化使先锋文学走向了新的阶段。
二、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创作表现
(一)“致力于真实谎言编造”的马原
马原是先锋小说作家群体中较早进行叙事实验的,马原的先锋小说最重要特点即其“虚构”真实的叙述手法,李劼对此评价道:马原的小说“全然立足于语言的真实,它可以不关注情感和辞藻,而致力于真实的谎言编造”。在马原的小说中常常会出现“马原”这一人物形象,如在《虚构》中,马原声称他在作品中讲述的只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让读者无需当真,但他在行文的开始就说“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结尾又强调“读者朋友,在讲完这个悲惨故事之前,我得说下面的结尾是杜撰的”。作者“声称虚构”与“强调杜撰”,拆解了真实世界与虚构的小说世界的界限,这种非虚构亦非写实的叙述手法被吴亮称之为:“马原的叙事圈套”。吴亮一边戏称马原是“一个玩弄叙述圈套的老手,一个小说中偏执的方法论者”,一边毫不吝惜地给予了马原极高的评价“马原是属于最好的小说家之列,它是一流的小说家。”由此,“叙事圈套”成了对马原的“纯形式”先锋创作实验最好的概述。
马原并不在乎故事能不能获得意义,甚至是带给他无限创作源泉的神秘藏地在他的叙述中也均未获得那些传统小说所追求的“意义”,在这些故事里,叙述不是获得故事意义的手段,叙述本身就是目的。
(二)“沉迷于死亡叙事”的余华
“死亡叙事”是余华先锋文学的鲜明标志。在文学研究中,死亡一直受到文学家的青睐,就如法国的莫里斯·布朗肖在评论作家卡夫卡时所说的那样:“死亡是那种极端,谁把握住死亡,谁就能高度地把握住自己,就会同艺术所能及的一切东西相连,就是全面的具有能力。”从美学的角度讲,大多数作家对于死亡书写的冲动是隐含在文旨中的一种审美意识,他们大多不直接描述死亡本身的血腥与恐怖,而是从不同角度观照人生,将死亡隐含在或喜或悲的事件中,将其与悲剧、荒诞等不同美学特征联系在一起,或割裂、或补充情节。然而余华并不将死亡隐含在文旨中,他冷静地描写赤裸直观的死亡与暴力,在《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等作品中,将人们之间荒谬的自相残杀描述得细致而逼真。
在余华的作品里,关于死亡精神价值的思考往往会呈现出一种缺失的状态,他几乎不对死亡作悲壮伟大等倾向的描述,与此相反,他冷静地对死亡过程进行客观叙述。无论是《古典爱情》里关于“人肉市场”的种种,还是《一九八六年》里疯子自戕的慢条斯理,甚至是《现实一种》中儿童摔死婴儿的平静……余华始终在用一种毫无波动的、似无正常人类情感的创作意识来谋求一种冷漠的死亡叙事形式。这不禁让人困惑余华是否想借助对死亡的冷漠叙事消解传统意义上的死亡价值观?事实上,在这一阶段,余华创作了《现实一种》 《河边的错误》 《死亡叙述》《世事如烟》等充斥着死亡与暴力的作品,的确是想以消解死亡意义的方式颠覆传统创作思维,并对人类的生存困境进行有价值的思考,而不仅仅是描述悲剧。
(三)“以先锋姿态书写古典宿命”的苏童
苏童的先锋创作就稍显温和,然而人们依然能够在苏童极具江南地域古典韵味的创作中感受到鲜明的先锋特色。他的作品曾以多重方式被论及——现代主义小说、先锋小说、新古典小说、新历史小说……多重命名中,先锋作家的身份是最早也是最为确凿的。苏童的确是一个难以概括的作家,然而其作品表现出来的反叛和决绝的姿态正是先锋作家所具备的。
苏童的先锋性主要体现在他那古典气韵下展现出的意识流叙事。他的笔端有着福克纳式溃烂的阴谋,也有着马尔克斯式的奇思异想。作为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异端作家,苏童也喜欢叙述死亡,但是他认为有比死亡更绝望的生存状态。苏童善用想象勾画出人物宿命般的阴郁状态,苏童小说中的人物往往会在熟悉的环境中表露出格格不入的隔离感,他们与人群背离,显示出敏感脆弱、偏执阴郁的心理状态。这种隔离感常常体现在他的意象里,如“香椿树街”和“枫杨树乡”中对“水”的意象的运用。在江南水乡中,水是美丽梦幻的,但在苏童笔下,江南的水与死亡相连。《舒家兄弟》中的涵丽与舒工相约投河自尽,《城北地带》的美琪在被强奸后投水而亡,苏童将死亡安排在如斯美景中,仿佛死亡就如梦境般唯美而意境悠长,与传统的重生轻死的死亡观背道而驰。在这些意识流叙事中,苏童的小说阐释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一切都如水中游丝般梦幻无形,却又极具神秘与美感,悄然揭示着苏童对人生与命运的理解。
三、20世纪90年代先锋文学的蛰伏与转型
20世纪90年代,先锋文学逐渐衰退或转型。一类以马原为代表的作家意识到先锋文学力量的流逝,一度停止了先锋写作;另一类以余华、苏童为代表的作家则在保持并凸显个人特色的基础上“部分地与现实妥协”,以研究界提出的“先锋转型”实现个人跨越。
(一)从“小说已死”到再度归来的马原
再度回归文坛,马原的最大改变在于他不再封闭在“纯形式”创新的叙事模式中,而是把注意力拉回到对外在世界的关注,收敛起张扬的反叛姿态,将晦涩的形式表达向一种较为平和、现实的维度。“在对经验的娓娓道来中,马原的叙述方式变得内敛、平实,但叙述却重新散发出了一种新的张力与力度。”从2012 年的《牛鬼蛇神》到2013 年的《纠缠》、2017 年的《黄棠一家》再到 2017 年底的《唐·宫》,马原在新世纪的尝试与他的年龄与阅历是相匹配的。一场略带魔幻色彩的肺病带给马原新的生命启示与写作冲动,如《牛鬼蛇神》中那些对生命的思考与对自然的感悟,虽然没有刻意重复过去的元叙事,但是仍可从中发现许多旧时的先锋元素。
如果说《牛鬼蛇神》是对新世纪中人的生存与鬼神幻想等问题的新思考,那么《纠缠》与《黄棠一家》则鲜明地表现出马原对新世纪社会的关注与不满。《纠缠》以大量琐碎的细节讲述姚亮姐弟无端卷入一场因捐赠引发的遗产官司,与卡夫卡的《审判》有许多相似之处。而《黄棠一家》则是描写出身富裕家庭的黄棠一家人的许多荒唐的冲突与磨难,正如“黄棠”此名所隐喻的那样,马原将他们置身于现实主义叙事模式中,却带着明显的现代主义的荒唐。这种叙事处理也隐隐透露出马原的创作道路的困惑与纠结,即传统现实主义创作和现代主义创作倾向之间的矛盾。
(二)与现实和解的余华
在先锋文学大举溃败的20世纪90年代,余华却迎来了个人创作新高潮。1991 年,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在《收获》上发表,毅然开启了新的创作模式。吴义勤认为“《呼喊与细雨》可能是他对自己先锋写作的最后总结, 是对自我和艺术的双重否定与双重解构。”但余华本人亲口否认了对先锋的反叛,然而他既不执着于为先锋正名,也不纠缠于人们对他的定位。
在对创作调整与自我定位上,余华一直走在时代的前端。尽管他在2008 年发表深耕多年的《兄弟》之后,一直饱受学界的争议,然而这其中仍不乏对余华再度转型的赞许之声。陈思和就判定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余华“走到了理论的前面,给我们描述了另一种传统”,此后历经五年,《第七天》的问世再度引发热议,这又是一部在争议声中被认知的新作。然而,人们依然能在这些转型中感到一些内在不曾变更的东西,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余华经典的“重复性叙事”。后来的长篇小说也经常能够看到这种叙事的重现,例如《活着》《第七天》无一例外地重复“死亡”的命运。这样的“重复性叙事”在展现荒诞的同时,也消解了死亡带来的浓烈悲剧氛围,的确是余华对先锋叙事的一种延续。
20世纪90年代以后,余华对创作模式的转变始终保持着平静的心态,尽管有评价说转型后的余华过于温和反而失去了其先锋价值,但人们仍能够从这些“温和”的作品中感受到他骨子里的桀骜与戏谑,或许余华只是在先锋的创作模式里尝试与现实主义握手言和,寻求新的平衡点。
(三)走向另类古典书写的苏童
作为先锋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苏童一直走得比较平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创作模式一成不变。“从苏童的作品中能够明显感觉到作家在寻求改变的创作调整上一直不懈的努力。”与先锋时期追求极端叙事相比,苏童在有意弱化“纯形式”的叙事游戏倾向后,转向了“新历史主义”。
苏童的叙事模式在新历史主义作品中大放异彩是凭借《妻妾成群》这部作品,这部小说也让他的古典气质再次得到关注。《妻妾成群》中最动人的仍是苏童式的阴郁而极具古典韵味的叙述方式,尤其是繁复生活细节和女性人物细腻的心理刻画。如果说《妻妾成群》在颓废绝望中盛开的古典诗意更新了历史题材作品的叙事模式,那么《我的帝王生涯》则是探入到历史本质中的另一种绝望的诗情画意。“《我的帝王生涯》表现了中国封建帝制文化窒息生命的本质,同时又表达了精神的异化与救赎的全过程。”而这些也是这些年来苏童始终如一的创作追求,苏童单纯地将它们作为一种叙述手段,探讨光怪陆离的生活和复杂无常的人性,就这一角度而言,他的作品的确不失为现代主义写作的一抹亮眼色彩。但即使转入新历史主义创作,就文学风格而言,苏童始终保持着他在先锋时期独特的个人魅力:融于感伤忧郁与诗意梦幻的江南地域文化中的古典文韵。
四、对先锋文学转型的思考
先锋实验的落潮从一开始就有迹可循。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先锋文学植根于西方化的写作经验,因此当它初进入中国文学的内部时,确实可以引起新奇的陌生化叙事效果,但是这种晦涩的叙事模式必然会疏远大部分的读者,最终走向萎缩。并且,先锋文学与传统的“文以载道”理念相背离,也不符合当时国内的文学审美需求。彼时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体系已经十分成熟了,如美国式的极端主义和对异常事物的趣味、法国式的荒诞和黑色幽默。而我国的文学仍然沉浸在东方式的对意识形态压迫的抗争、传统的忧患意识与家国意识之中。一言以蔽之,彼时西方文学的对立面是“理性”,而“理性”恰是当时中国文学所呼唤的。
那么,人们该如何判断先锋文学转型究竟是一次文学内部的自我调整与沉淀,还是一场思潮的铩羽而归?回顾20世纪80年代因先锋写作而一举成名的那些先锋作家,他们的转型究竟是背离还是坚守先锋文学?
余华曾在1996年的媒体访问中间接回应过这两个问题,他说:“我们最早起来的时候,是以反叛者的姿态出现的。现在应该说先锋文学成了新的权威……我认为我现在还是先锋作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还是在中国文学的最前面。这个最前面是指我们这些作家始终能够发现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需要前进的方向又在什么地方。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先锋派作家。”从这个回答里,可以大致做出两个判断:第一,作为先锋文学的核心人物,余华也在思考先锋文学的走向,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是以反叛权威的姿态出现,既然“先锋文学成了新的权威”,那么20世纪80年代先锋实验盛行的辉煌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被复制。第二,在余华看来,先锋文学不局限于在创造上做大胆形式创新的先锋实验,更在于内在的先锋精神,无论转型与否,只要内心仍然秉承带着怀疑与批判始终向前的先锋精神和自由意识,先锋作家就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