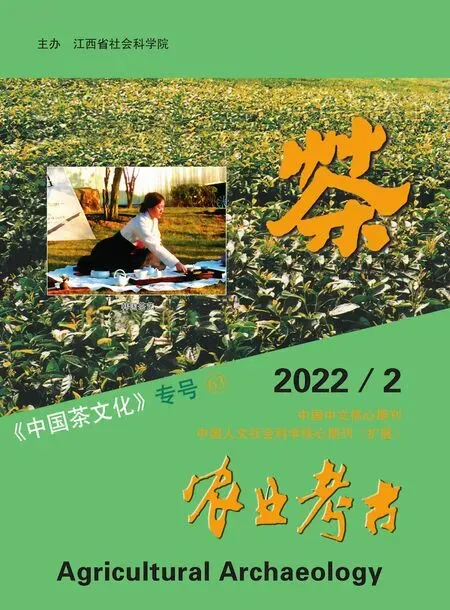从丝绸之路到茶马古道:论“宝货”源流与民族八宝茶文化*
2022-11-01韩冀宁霍维洮曹艳梅
韩冀宁 霍维洮 曹艳梅
茶文化是人们在茶饮生活中通过相互交流逐渐发展形成的,表现出民族文化的一种“语根”。民族茶文化是中华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蕴含有中原茶文化的元素,又显示着民族的文化因素。八宝茶是一种流行于边疆民族地区的民族茶文化,它是由茶叶和各种干果,如红枣、芝麻、枸杞、桂圆肉、葡萄干、核桃仁加上冰糖等,共同冲泡而成,清香爽口、回味悠长,显示出中国民族文化独具个性的“根语”。同时,民族八宝茶文化独特的民族韵味也在于其独特的文化个性。民族八宝茶中的各类果品来自祖国的天南地北,它们在民族茶文化的牵引下共聚边疆合而为“一杯清香浓郁的八宝茶”。这不仅反映边疆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也从侧面展示中华文化融合演进的发展轨迹,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目前,学界对中华茶文化的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但更多偏重于对中原茶文化的讨论。对作为中华茶文化重要内容的民族茶文化的研究还相对薄弱。就民族八宝茶文化而言,学界的探讨基本局限于对民俗现象的简单考察,相关的讨论还很不充分。本文拟从组成“八宝”的“宝货”入手,梳理“宝货”演变的历史轨迹进而探讨民族八宝茶文化的基本特点。笔者不揣浅陋,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教。
一、古代丝绸之路与“宝货”的历史流变
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丝绸之路”命题。在李希霍芬看来,东、西方间的物质交流和商业贸易以丝织品为对象,因此他将联通双方的商路称为“丝绸之路”。从秦汉至宋元,随着海陆丝绸之路的兴盛,流入中国的宝货数量和种类不断累加,形成“众宝”齐聚中国局面。明清时期茶马贸易兴起,宝货从东西流动变为南北互通,其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与之相应,宝货也从异域商品转变成国产土货,实现由一而多的发展进而聚合为八宝,广泛而深入地渗透中国的社会生活。一直以来,这种情况都不为人所关注。
海、陆丝绸之路中的宝货流动。闻名天下的陆上丝路贸易始于汉代。西汉武帝时,朝廷提出“断匈奴之臂”的主张,多次派遣张骞前往西域探听虚实,游说西域诸国同汉亲好。张骞遂携带“牛羊万数”“赍金币帛巨万”出使西域。随后,汉朝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实现了“开玉门,通西域”的政治意图。对于强匈的失败,西域及中亚诸国深受震动,“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 皆重译贡献”。诸国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代表了东、西地域之间“宝货”的正式流动。自此以后,西域诸国的商贾沿着陆上丝路往来不绝,他们“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翦伯赞先生指出:“西域道通以后天山南北地区第一次与内地联为一体,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这种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也丰富了中原汉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各类“宝货”通过陆上丝路进入中国,如“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 殊方异物, 四面而至”。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当时中西方大国都在积极推动对外贸易,汉和贵霜、帕提亚之间,贵霜和汉、罗马之间,帕提亚和罗马、汉之间,罗马和印度、贵霜、帕提亚之间都存在着一定规模的贸易往来。然而,西域输入中国的“宝货”虽然较多,但“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却只“盈于后宫”“充于黄门”,并没有真正流入民间社会。这是由陆上丝路贸易官方性质所决定的。
唐宋时期,在陆上丝路贸易不断发展的同时,海上丝路也逐渐开辟形成。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中原王朝以及封建王朝的开明政策吸引了更多的西域胡商来华贸易。比如唐文宗曾谕说:“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宋高宗亦云:“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记,岂不胜取之于民?”。海上丝路贸易的繁荣促进了“宝货”在中国的流通。据《唐国史补》记载:“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其中师子国贩运来华的商品主要是胡椒、香料、药材、蔗糖、宝石、象牙、珍珠、犀角、玉佛像、佛经等。可以说,唐宋王朝出于扩大国家财源的考量是推动“宝货”在中国进一步聚集的重要因素。此外,来中国贸易的西域商贾相聚时,“胡客法,每年一度与乡人大会,各阅宝物。宝物多者,带帽居于坐上,其余以次分列”。可见,在西域商贾眼中“宝货”作为论资排辈的依据有着特殊的身份意义。宋代,通向内地的陆上丝路为北方游牧民族所阻隔,宋朝只得专心经营海上丝路贸易以补国用不足。海上丝路贸易的发展呈现超越陆路之势,“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货往还,昧旦永日”,使得“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 而经西域胡商之手输入中国的“宝货”有珠宝、香料和药材等,“福建市舶司,常到诸蕃舶船,……则有真珠、象牙、犀角、脑子、乳香、沉香、煎香、珊瑚、琉璃、玛瑙、玳瑁龟、筒栀子、香蔷薇、水龙涎等”。由此可见,当时“宝货”的数量和种类比之以前更加丰富了。
从上述讨论可知,自汉代起,海、陆丝路贸易的持续发展不仅促进了中国和世界的交流,也促使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同时,来自域外的、品类繁多的“宝货”在中国逐渐积聚,这为“八宝”之说的出现奠定了历史基础。
二、“八宝”的历史演变与明、清茶马贸易
自“张骞始开西域”以后,诸多“宝货”云集中国。但明代已降,随着海、陆丝路贸易的后继乏力,取而代之的则是茶马贸易的兴盛。众人皆知,茶马贸易是农耕经济和畜牧经济互补互利、有无互通的产物。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如前所述海、陆丝路贸易是沟通东、西的对外商贸活动,其中的重要承担者是西域胡商。在丝绸之路衰落以后,众多附籍中国的西域胡商仍然是茶马贸易的主要参与者,他们甚至主导了西北畜牧产品与内地农业、手工业产品之间的商品交换。这表明,明、清之际的茶马贸易实际上继承了较多的丝路遗产,其中“宝货”的性质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并呈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从“众宝绮丽”到“茶马并行”。凭依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宝货”繁多,其中“宝马”即是“宝货”中的重要一员。如史载“吕光太安二年(387),龟兹国使至,献宝货奇珍、汗血马”;天宝三载(744)“七月,大食遣使献马及宝于唐”。无独有偶,“宝货”和“茶叶”的联姻则始于唐代中原内地和边疆民族地区之间的“有无互通”。唐代中国的茶叶经济迅速崛起,饮茶风俗不仅盛行中原,还在边疆民族地区广泛流传,“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自此茶叶成为边疆少数民族“须臾不可离”的必备饮品。从茶马贸易的发展来看,唐代茶马贸易尚未形成规模,宋代茶叶在市马物资中的地位也不突出,而元代蒙古人拥有广袤牧场和大量马匹,更没有进行茶、马互通的需要。但明代情况则为之一变,此时西北、西南“番人嗜茶”蔚然成风,这为唐王朝“以茶驭番”的政策创造了条件。明朝统治者认为通过茶马贸易不仅能够获取大量马匹,还有羁縻边疆民族、维系边疆稳定的效用,正可谓“摘山之利而易充厩之良,戎人得茶不能为我之害,中国得马实为我利之大。非唯马政军需之安,而驾驭西番不敢扰我边境矣”。随后,明、清封建王朝在西北边疆推行了大规模的茶马贸易,中国南、北地域间的茶、马交换迅速展开。需注意的是,推动“茶、马并行”局面形成的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在海、陆丝路贸易衰微而茶马贸易兴起之际,“宝货”的流动逐渐从东、西互通转变为南、北互换,而“宝货”的性质同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何以会如此?实际上,这与从事茶马贸易的“商业民族”有着直接关系。唐、宋以前,从事海、陆丝路贸易的是来自西域、中西亚的商贾。元代以后,中国的民族格局发生了改变。蒙古人建立起地域辽阔的“大一统”政权,并将这些“商业民族”迁徙至中国境内。西域胡商从事商业活动更加便利,他们“无此疆彼界,朔南名利之相往来。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形成了横跨东、西的庞大商业网络。他们还凭借自身的特殊地位把这种商业网络向中原内地延伸,史载胡商“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域区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还有论者指出,元代“回回商人在国内贸易中主要活动于全国大小城镇,但也不辞劳苦地深入到边远山区”。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经西域商贾之手流通的“宝货”不仅包括此前海、陆丝路贸易中的如“犀玉”“珠宝”等珍稀产品,还囊括了中国产出的茶、马、盐、糖等货物,所谓的“宝货”也由域外商品转变为本国土产了。因此,当明、清的茶马贸易迅速展开时,西域胡商的后裔们据其便利条件又很好地承担了商业民族的社会角色,成为推动茶马贸易发展的重要民间力量。由此,茶叶和宝马并行,成为“宝货”的典型代表。
其次,从“宝货”聚集到“八宝”成型。明代蓬勃兴起的茶马贸易把南茶、北马联结在一处,促进了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清朝延续了明代的官营茶马贸易政策,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清中期以后,随着西北社会经济的变迁,官营茶马贸易开始变得难以为继。康熙当政时官营茶马就已呈现颓势,如康熙三十二年(1693),西宁茶马司奏报“无马可中”,不得不将“年久浥烂”的茶篦折价变卖,在俸饷中按成搭放。因为官营茶马贸易经营困难,清王朝只得改弦更张,乾隆元年甘肃官茶改征折色是清朝茶马贸易政策的重要转折,“在中国历史上,自唐代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重视并大力经营的茶马贸易,实际上到清朝乾隆年间便宣告终结”。对茶马贸易的管制放宽以后,民族民间商业贸易迅速发展并突破桎梏。这在西北边疆地区尤为典型,彼时的民族民间贸易无论是规模还是水平均超以往,“扩大化的民族贸易发展到清代,贸易范围由内地扩展到西北再到西域,单纯以茶叶为主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贸易物品的种类扩展到丝绸、布、棉、绢、畜产皮毛”。边疆民族民间贸易的“扩大化”为“宝货”的聚合创造了必要条件。西北边陲民族民间的密切交流、交往,促进了西域饮食文化和中原茶文化的深层次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八宝”茶文化。而可以入茶的各类南、北“宝货”即是“八宝”之属。这些“宝货”取得了更加贴近民众生活的新身份,同时,它们虽然平凡但并非不够珍贵。这在西北婚俗中也有所体现,古时西北婚俗有载:“既复,择日为茶饼,具羊酒,并物,首饰送女家,曰‘下茶’。”将茶叶和羊、酒等相提并论,表明茶叶在当时西北的社会生活中有着不菲价值,而要求在茶水中添加各类干果或果品的八宝茶文化,就更加殊为难得了。茶叶和各类果品仍被西北民众视为“宝货”也就不难理解了。可见,中国的各类南、北“宝货”在民族茶文化的“合和”中被“融为一炉”,化为了一杯清香爽口的民族八宝茶。
三、从“宝货”到“八宝”的内涵变化
“宝货”和“八宝”,两者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其义固然有所区别但更多的仍是联系。古人认为,“宝货”是关系天下兴亡之物。古代国家对“宝货”非常重视。如唐朝“每岁计其所出而度其所用……皆量其贵贱,均天下之货,以利于人。凡金银宝货绫罗之属, 皆折庸调以造”。因此,作为古代国家主宰的君主,如果他们“犹以宝货为奇,终日游宴,边幅是讨”,其国必有危亡。谢天佑先生指出,“封建社会生产每一周期都不一定是扩大的,不扩大是经常的,扩大则是偶尔的、间歇性的”,如果君王奢侈无度痴迷“宝货”,势必造成社会危机。显然,“宝货”在古代社会中具有货币的社会功能。最初,古人认为“宝货”是指龟壳、贝币、布币等古钱币和“五色”金属,“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颜师古释曰:“金谓五色之金也。黄者曰金,白者曰银,赤者曰铜,青者曰铅,黑者曰铁。刀谓钱币也。龟以卜占,贝以表饰,故皆为宝货也。”关于宝货的规格, 史籍中有细致规定,如“其金银与他物杂色不纯好,龟不盈五寸,贝不盈六分,皆不得为宝货”卷十。“宝货”也指古钱币。比如“周景王时患钱轻,更铸大钱,文曰‘宝货’”,“中一国之币为三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
但自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以后,“宝货”之意却又不限于上述所论。在海、陆丝路贸易中经过西域胡商之手贩运至中国内地的珍稀货物亦可称之为“宝货”。而“宝货”与“八宝”则联系甚深,从“宝货”到“八宝”的发展过程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社会历史演变。探讨这一转变过程,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八宝”的内涵做一番考察。
先秦之际,“八宝”和玺印的渊源颇深。当时官、私印章均可以称为“玺”,加盖印玺是一种表达意愿的方式。始皇帝“一统六合”后,他的玺印被尊为“天命象征”。自此,历代封建王朝都把皇帝玺印视为皇权象征,奉为国之重器。比如,宋太祖曾“自作受命宝,其方四寸有奇,琢以白玉,篆以虫鱼。镇国、受命二宝,合天子、皇帝六玺,是为八宝”。此时的“八宝”就是“天子之宝”。所谓“天子有八宝,其文各异”,其内容有着多重意义,“一曰神宝,所以承百王,镇万国;二曰受命宝,所以修封禅,礼神祇;三曰皇帝行宝,答疏于王公则用之;四曰皇帝之宝,劳来勋贤则用之;五曰皇帝信宝,征召臣下则用之;六曰天子行宝,答四夷书则用之;七曰天子之宝,慰抚蛮夷则用之;八曰天子信宝,发番国兵则用之”。作为皇权象征的“天子之宝”有严格的管理规制,唐朝有“符宝郎”掌管“天子八宝及国之符节,辨其所用。有事则请于内,既事则奉而藏之……凡大朝会,则捧宝以进于御座”,旧皇驾崩,新帝才能“受八宝于殿”。这些记述充分体现了“八宝”唯一性和珍贵性。
明清以来,“八宝”之词不再专属天子,但其“珍稀贵重”的意义并没有改变。其一,“八宝”一词可以冠名御赐之物,以示天子对臣下的恩荣。儒家强调纲常伦理、君臣之义,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天子和臣下的感情是共同维持的,所谓君对臣以礼则臣对君以忠。赐予“八宝”器物就是君臣维系感情的一种手段。例如,明臣张居正 “抵郊外……赐八宝金钉川扇”;清臣张廷玉被“赐御用冠一顶……八宝如意一柄”。 其二, 藩王和部族首领也可使用“八宝”器物以示其尊贵。如“赐脱脱不花王可汗,织金四爪蟒龙膝襕八宝衣一”,“王饰八宝冠,箕踞殿上高座,横剑于膝”。“宝货”一词不再是天子专享,其使用主体的范围有所扩大。其三,在社会历史变迁中民间文化对“八宝”一词有着更加深刻的诠释,其可以指代民间珍品所组成的吉祥图案。随着“八宝”一词流传,佛、道两教也开始借用其说表达宗教内涵,较为常见的形式是八宝图案和八宝装饰。佛教“宝货”多指各类表示祥瑞吉庆的佛教法器,如吉祥结、莲花、法轮、双鱼、华盖、宝瓶、法螺、尊胜幢等共同组成“佛八宝”。同时,道教“宝货”指道家八仙所持法器,如葫芦、花笼、团扇、阴阳板、宝剑、莲花、横笛、渔鼓等共同组成“道八宝”。佛、道两教的“宝货”蕴含吉庆有余、福禄寿禧、金玉满堂等吉祥寓意,即“七珍八宝之说,番语谓吉祥物也”。在宗教文化的诠释和推动下“八宝”一词的流传更广。明清已降,人们逐渐将一些触手可及的赏玩珍品视为“宝货”,如银锭、犀角、火珠、火轮、法螺、珊瑚、祥云、灵芝、馨、鼎等,并将这些珍品合称为“杂八宝”。当时,杂八宝已经较为常见,如“嘉靖时烧造瓷器,所画有……灵芝捧八宝”
综上所述,宝货的持有者从天子、勋贵到普通百姓,其主体范围的扩大使得“宝货”概念不断丰富进而形成“八宝”之说。在传统文化中“八”有着特殊含义。除“九”为汉字最高数用以特殊场合外,“八”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已堪称极数。如儒家原典《易经》阐发事物阴阳变化以“八卦”称之;孔子逝后“儒分为八”;《左传》有“节八风而行八音”;《史记》记述司马相如故事说关中江河有“八川”,称域外为“八方”“八荒”。从“宝货”到“八宝”的概念演变,背后蕴含着的是“宝货”历史内涵的不断丰富,赋予了民族八宝茶文化独特而深刻的意蕴。
四、民族茶文化中的“八宝”再释
中华茶文化整体呈现多元特色,蕴含着各种韵味独特的民族茶文化。民族八宝茶流行于西北边疆地带,它是由茶、冰糖加上红枣、芝麻、枸杞、桂圆肉、葡萄干、核桃仁等干果果品共同冲泡而成,清香爽口、回味悠长。显然,民族八宝茶中的上述果品即可认为是民族茶文化中的“宝货”。民族八宝茶文化盛行西北民间,关于它的起源和形成问题,诸多学人莫衷一是,尚无定论。有关民族八宝茶文化的缘起,在西北流传着一个著名传说故事:“公元1251年,忽必烈率军南征云南,‘回回人’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奉命运输军需,中暑昏倒。一位叫尤努斯的老人用花瓷碗放上茶叶、果干、菊花泡了一碗味道香浓的药茶,老人怕灰尘弄脏了茶水,就用一个瓷盘盖在碗上,献给瞻思丁。瞻思丁喝下药茶,顿感清甜香郁、顿消暑气,他夸赞道:‘美哉,盖碗茶。’”从此,八宝茶在云南流行起来;而“瞻思丁的儿子纳速刺丁从云南调任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把喝盖碗茶的风俗传到了陕西,后来随着战乱迁徙,这一习俗也就传到了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地方”。这一传说及其记述出自民间的“口耳相传”,其虽非信史但有一点值得肯定,即民族八宝茶文化是中国茶文化和西域饮食文化传承之间文化相融合的结晶。此外,也有论者提出质疑,认为民族八宝茶文化并非形成于云南而是诞生在西北边疆民族地区,尤其是陆上丝绸之路中国段的沿线地带,但并未对其原因做出解释。笔者较为赞同后者的观点,对此试论述如下:
首先,西北边疆民族地区有着更适宜民族八宝茶文化生长的社会土壤。前文已经述及,民族八宝文化的形成依赖于“宝货”的聚集。从西北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时段来看,“‘丝绸之路’虽然在西北极其漫长,曾是东西贸易的主干通道,但西北并不是对外贸易产品的出产地,如丝绸、瓷器、茶等大宗出口产品几乎全部来自西北以外的地区,因此,西北在东西贸易中的地位是中转站,在中转中捎带一些出口产品。这种状况是由西北农耕和手工业经济的孱弱所决定的”。漫长发展的古代丝绸之路逐渐贯通了整个西北地域,种类繁多、数量众多的“宝货”曾经借道中国西北边陲而进入中原腹地。此后,随着茶马贸易的繁荣发展,实现了“北马”和“南茶”的商品交换,又使得西北边疆由“中转”变为“产出”了,而茶马贸易也作为一种经济纽带把中原内地和西北边疆更加牢固地联结起来。不难看出,在陆、海丝路贸易和西北边疆茶马贸易前后相继的推动下,“宝货”在西北边疆地区不断积累进而形成了民族八宝茶文化,它也在西北陆上丝路沿线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和民众的普遍接受。
其次,民族八宝茶“尚甜属热”,使用的辅料多是干果,适合干旱、半干旱地区的远途携带和长期存放。同时,和民族八宝茶配套的茶具是“盖碗”,有着“一防灰(清洁),二防冷(保温),三防茶叶卡喉咙(安全)”的作用,这无疑更适宜西北边疆的社会生活状况。那么,民间传说中为何会有民族八宝茶文化形成于云南的说辞呢?这是因为,对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化和民俗的研究,长期为正统学者所忽视,加之民族茶文化复杂而悠久的历史传承,使人们的讨论更加难以入手。另一方面,古人也常有“托名”的文化心理习惯。赛典赤·瞻思丁治理云南“功勋卓著”,是元代著名的“回回”大臣,他也和西域胡商有着密切的联系,若把民族八宝茶文化的创立同他联系起来,则能够提高民族八宝茶文化的人文历史价值。因此,有关民族八宝茶起缘的“云南说”固然有诸多疑点,但却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
在探讨民族八宝茶文化的起源和形成问题以后,我们可以发现:民族八宝茶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其主要如下:其一,形成于西北边陲的民族八宝茶文化有着独特的文化韵味。唐朝时饮茶风尚遍传华夏,书写、总结茶文化的书籍也相继问世,中原茶文化孕育形成。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认为:“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陆羽把饮茶和儒家“精行俭德”的道德操守相联系,使“饮茶”成为象征儒士品行的文化符号。庄晚芳先生也说:“‘中国茶德’的精神,有四字廉、美、和、敬的守规。”与结合儒家文化的中原茶文化不同,边疆民族的茶文化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如民族八宝茶文化,它是由天南地北的各类“宝货”(果品)聚合而成,无疑具有“合”的特性。但其茶德由“合”而“和”,则是在中华民族“一体化”力量的整合下,边疆多民族交错杂居、和谐共处中逐步形成的,表达了民族八宝茶文化“和”的文化意蕴。这亦如庄晚芳先生指出的:“饮茶也是人际间来往的桥梁,要和好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平共处,增进人情向上,世间永处和平。不但外表和,同时内心要诚,把和诚结合一起,才可以使茶德达到完善之地。”
其二,民族八宝茶文化是西域饮食习俗和中原茶文化互融的美好结晶。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饮茶历史传承,它的发展经历了祭品、菜食、药用、饮用等几个发展阶段。其中,茶叶在食用、药用方面有着显著价值。茶叶最初是被视为药材的。唐代陆羽在《茶经》所引司马相如《凡将篇》中就将“荈诧”和“桔梗、贝母、白芷”等中药材相并列,而“荈诧”就是茶叶。因此,茶叶也有“羹饮”之法,如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有载:“今人饮茶,未知所始。释木云:槚、苦茶。郭璞云: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一名荈。”可见,“冬生叶”即可作“羹饮”。而民族八宝茶文化在中国传统茶文化中的药用、食用两个方面有着突出表现。民族八宝茶有着“解热去毒、能解饥渴、消夏去暑、能去腻膻”的功效。同时其药膳之名也是名扬天下,依据西北民俗,在喝完八宝茶以后还可以直接食用其中的果品。不仅如此,民族八宝茶文化还有着“含糖缀茗”的特点,这是西域胡商的独特的饮食文化传承。据朱彧《萍洲可谈》记载:“蕃坊献食,多用糖蜜脑麝”;宋人岳珂和胡商宴饮时云:“龙麝扑鼻,奇味不知名……几与崖蜜无辨。”民族八宝茶将传统西域饮食“甜香”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们“不论自己平时饮茶还是待客,都要在茶叶中配以白糖或红糖、冰糖、方糖等”。饮用八宝茶时,“若要茶汤浓些,就用茶盖对茶水轻轻刮一刮,使整碗茶水波翻浪起,沉于碗底的糖、枣、荔枝、葡萄干、茶等许多东西被带起”。
其三,民族八宝茶文化的形成和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着直接关系。其实,民族八宝茶文化中的“八宝”为虚数。除“八宝”的饮法以外,尚有其他几种饮法:一是“红糖砖茶”、“白糖清茶”或“冰糖窝窝茶”,配料仅为糖和茶;二是“三香茶”,配料是糖、枣、茶三样;三是“红四品”,配料是砖茶、红糖、红枣、果干四样。或是“白四品”,配料是陕青茶、白糖、芝麻、柿饼等四样;四是“五味茶”,含酸、甜、苦、辣、香五味,由绿茶、山楂、芝麻、白糖、姜组合而成;西北各地民族八宝茶中所含辅料的差异,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因素就是西北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滞后性和不平衡性。古代的西北边疆长期处于贫瘠状态,合成“八宝”的茶叶和各种果品都要仰赖经济发达地区的物质输送,这对西北民众的民族八宝茶文化有着较大的限制。于是,在西北边疆才时有红白糖茶、三香茶、红四品、五味茶等“八宝”不全的权宜之计,如“河湟各地有的讲究加入冰糖、桂圆、红枣,即‘三圆、五枣茶’”等。
综上所论,在中国西北边陲,特殊的社会经济环境孕育了民族八宝茶文化。在中国茶文化和西域饮食文化相互交流和交融的趋势下,民族八宝茶文化把茶叶和各类南、北“宝货”果品“聚合为一”,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民族茶文化,它的茶德由“合”至“和”,体现了中华民族茶文化“和合至美”的精神。“一碗清香的民族八宝茶”,不仅反映出西北社会复杂的历史演变,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的历史缩影。
①较为重要的有:庄晚芳《中国茶文化的传播》,载《中国农史》1984年第2期;姜天喜《论中国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陈瑜《唐宋文人茶的文化意蕴及其形成过程》,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虞文霞《新时代茶文化的多向度创新发展思考》,载《农业考古》2021年第5期。
②较为重要的有:施由明《感悟民族茶文化——从中国少数民族茶文化看民族特性》,载《农业考古》2006第5期;段继业《砖茶与西北少数民族社会》,载《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禹虹《回族的饮茶习俗与茶文化解读》,载《回族研究》2011年第3期;王欢《云南少数民族茶文化的内涵挖掘与社会功能解析》,载《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7期。
③较为重要的有:勉卫忠《河湟回族的罐罐茶与盖碗茶》,载《农业考古》2004第4期;武回忆《西北回族的茶文化研究》,载《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王正伟《回族民俗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④本文在此所讨论的“西域”,是广义的西域而非狭义的西域。
⑤江伯勤先生认为:“中世纪早期的东西方贸易,是由特殊的‘商业民族’担当的”,他们“以一种特殊的宗教纽带、聚居形式生活在中世纪的缝隙中”(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其实,这些“商业民族”早已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汉代称其为“西域商贾”,唐宋时称“蕃商胡贾”,元代以后被称为“回回商人”。他们通过海、陆丝路参与东、西方国际贸易。明清时期,其后裔“回回商人”又成为西北诸民族间商业流通的“承担者”。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些“商业民族”以“宝货”为纽带同中华民族长久地、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最终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部分。“宝货”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着深远意义。
⑥具体参见李德宽《西北回族“复合型经济”与宏观地缘构造的理论分析》,载《回族研究》2003年第4期。该文认为“回回”民族正好位于“三块高原(青藏高原、黄土高原、蒙古高原)和两种经济类型(青藏高原藏族的单一的畜牧经济、蒙古高原蒙古族单一的畜牧经济)”的中间,他们担当了商业中转的角色。
⑦就笔者所见,对此传说故事有所记述的有丁一波《回族的盖碗茶》,载《中国土特产》1994年第5期;林更生《回族盖碗茶茶文化》,载《农业考古》2002年第4期;马超《回乡盖碗茶》,载《金融经济》(宁夏)2004年第2期;武回忆《西北回族的茶文化研究》,载《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拜学英《回族喝盖碗茶的习俗探源》,载《中华合作时报》2012.2.14,第B03版;王正伟《回族民俗学》(第三版),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6页。
⑧具体参见王敏《八宝茶宁夏味》,载《银川晚报》2019.01.14;曹向涛《宁夏回族八宝茶茶艺挖掘及推广研究》,载《产业与科技论坛》2018年第6期;景曦《八宝茶养生文化及推广研究》,载《产业科技论坛》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