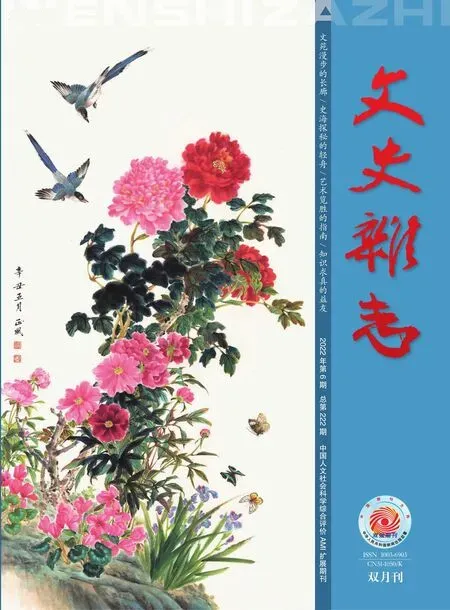『水行仙,怕秦川』探微
2022-10-29浙江傅绍磊
浙江 傅绍磊

陶穀《清异录》:“王建僭立后,有一僧常持大帚,不论官府人家寺观,遇即汛扫,人以‘扫地和尚’目之。建末年,于诸处写六字云:‘水行仙,怕秦川。’后王衍秦川之祸,方悟‘水行仙’即‘衍’字耳。”就时间线而言,后唐同光三年(公元925年)十一月,前蜀后主王衍在成都出降后唐,闰十二月,获得后唐“裂土而王”的政治承诺;四年二月,因为后唐政局剧烈动荡而引起猜忌;三月,罹难长安秦川驿。所以,所谓的秦川之祸事发突然,极为偶然,不可能在王建末年就为人所知,更不可能以“水行仙,怕秦川”言之。
秦川之祸是偶然事件,但是,前蜀政权覆灭却是渊源有自,源于由来已久的内部矛盾,到王建末年,终于失控,形成覆灭的必然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水行仙,怕秦川”的出现、传播、流传并不是空穴来风,反映的是前蜀政治危机越来越为人所知,从而成为普遍文化共识的事实。
前蜀政权从建立到覆灭的过程反映的是从武功到文治转型的艰难,在唐末五代割据政权中极有代表意义;但其长期以来却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本文梳理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从而为前蜀政权、唐末五代政治提供一个认识的新角度。
王建在建立前蜀政权的过程中,武力征战,形成武将集团,获得助力,也面临严峻的挑战,甚至是政治诉求,于是,逐渐重用士人,制衡武将集团,深刻影响前蜀政局。
唐光启三年(公元887年),王建攻占阆州,逐鹿两川,就已经有了相对长远的战略规划,从而意识到武力的局限性,《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六:“前龙州司仓周庠说建曰:‘唐祚将终,藩镇互相吞噬,皆无雄才远略,不能戡济多难。公勇而有谋,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谁!然葭萌四战之地,难以久安。阆州地僻人富,杨茂实,陈、田之腹心,不修职贡,若表其罪,兴兵讨之,可一战而擒也。’建从之,召募溪洞酋豪,有众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袭阆州,逐其刺史杨茂实而据之,自称防御使,招纳亡命,军势益盛,守亮不能制。部将张虔裕说建曰:‘公乘天子微弱,专据方州,若唐室复兴,公无种矣。宜遣使奉表天子,杖大义以行师,蔑不济矣。’部将綦毋谏复说建养士爱民,以观天下之变,建皆从之。”唐末五代乱世,虽然需要武功立足,但是,武功与文治相结合才是长久之计,而养士爱民最直接的压力正是来自武将集团的暴力。大顺二年(公元891年)八月,王建攻占成都,虽然对于武将集团的暴力早有禁止措施,但是,还是引起混乱,《新五代史·前蜀世家》:“建将入城,以张勍为都虞候,戒其军士曰:‘吾以张勍为虞候矣,汝等无犯其令,幸勍执而见我,我尚活汝,使其杀而后白,吾亦不能诘也。’建入城,军士剽略,勍杀百人而止。”事实上,张勍以暴制暴,维护的只是基本秩序,不可能完全禁止武将集团的暴力。所以,前蜀政权建立以后,民间对于王建君臣颇有微词,《蜀梼杌》卷上:“二月朔,游龙华禅院,召僧贯休,命坐,赐茶药彩段,仍令口诵近诗。时诸王贵戚皆赐坐,贯休欲讽之,因诵《公子行》曰:‘锦衣鲜华手擎鹘,间行气貌多轻忽。艰难稼穑总不知,五帝三王是何物。’建称善,贵幸皆怨之。”时在永平二年,距离前蜀政权建立已过五年,贯休诗歌针对的正是武将集团的肆意妄为;就王建和贵幸的态度而言,应该没有言过其实。
武将集团的暴力对于前蜀政权的稳定颇为不利,而政治诉求则直接威胁王建的最高权力,从而更加引起王建的注意。大顺二年十二月,王建攻占西川,图并东川,却因为王宗弼等人的泄密,无功而返,《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八:“以顾彦晖为东川节度使,遣中使宋道弼赐旌节。杨守亮使杨守厚囚道弼,夺其旌节,发兵攻梓州。癸卯,彦晖求救于王建;甲辰,建遣其将华洪、李简、王宗侃、王宗弼救东川。建密谓诸将曰:‘尔等破贼,彦晖必犒师,汝曹于行营报宴,因而执之,无烦再举。’宗侃破守厚七砦,守厚走归绵州。彦晖具犒礼,诸将报宴,宗弼以建谋告之,彦晖乃以疾辞。”王宗弼泄密等于是违背王建的意志,兹事体大,华洪等三人不可能不知情。王建基本控制西川是在大顺二年十月;而顾彦朗早在王建入西川求取方镇之前的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就已经是东川节度使,卒后,军中推其弟顾彦晖为留后。就后来的事实而言,王建直到乾宁四年(公元897年)十月才攻破梓州,吞并东川,而且,过程颇为艰难;所以,当时王建与顾彦晖之间强弱形势并不明朗,从而导致王宗弼等人的消极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华洪、王宗侃、王宗弼都是王建同乡,所谓的“许州故人”,引申而言,以“许州故人”为核心的武将集团在前蜀政权早期就已经有了微妙的政治诉求。

王建石像(在成都永陵博物馆永陵地宫)
《鉴诫录·产麒麟》:“王蜀田尚父第三子太尉生自雅安,小字獦獠儿。其母崔氏初梦一人,峨冠褒袖,自称周公山神,牵一五色兽逼其裙,既惊且寤,因而有孕焉。后有加持崔和尚者忽自雅安来于成都打病,瘟疫者寻差,挛躄者立行,指人乱言,往往有据。田是时童呆,宦者抱著于窗前。和尚看之,欣然抚其背曰:‘怪来近日贫道所居之山气色稍微,其山之神孕灵于此。此子麒麟之精也,必为王者之瑞焉。’宦者以告,其母曰:‘往年梦中之兽,今获解之。’遂施和尚珠金,以酬异说。田后累迁郡守,节制洋州,蜀将之中颇闻兵法。乃知异梦信而有祥者焉。”王宗侃任雅州刺史大约在大顺、景福年间,距离王建攻占成都,控制西川不久。就行迹而言,王宗侃很可能在雅州就已经与崔和尚有所关系,而不是相识于成都。所以,崔和尚之言应该不是空穴来风,代表的是王宗侃的意志,实际上是通过王宗侃之子对王宗侃进行政治宣传。值得注意的是,王宗侃等假子封王是在乾德年间。所以,所谓的“周公山神”“麒麟之精”“王者之瑞”云云,已经大大超越王宗侃当时的政治身份;引申而言,王宗侃的政治诉求不但极为强烈,而且,由来已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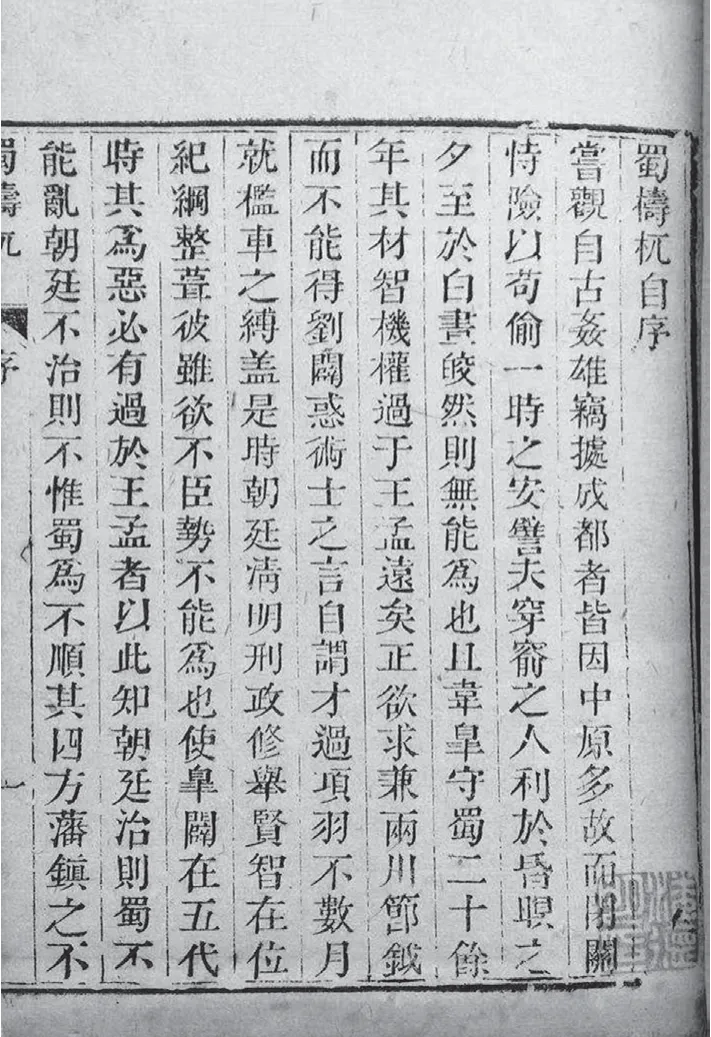
《蜀梼杌》(清刻本)
前蜀政权建立以后,武将集团的政治诉求更加强烈,《十国春秋·王宗训传》:“王宗训,本名茂权。初为刁子都虞候,高祖攻彭州,茂权斩杨晟于陈前,论功受上赏,赐名宗训,与诸子比。永平中,累官武泰军节度使,镇黔州。宗训恃恩贪暴,骄纵逾制,不奉诏,辄回成都,多所邀求。高祖见宗训,大怒,命卫士扑杀之。”王宗训在王建假子中并不是核心成员,至少与王宗侃等人难以相提并论,尚且肆无忌惮,“多所邀求”。这说明当时武将集团政治诉求已经普遍化、公开化,所以,王建扑杀王宗训,以儆效尤。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士人进入前蜀政权,成为王建制衡武将集团的主要力量,影响王建对于武将集团的态度逐渐从隐忍不发到多忌好杀,《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八:“建既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纳直言,好施乐士,用人各尽其才,谦恭俭素;然多忌好杀,诸将有功名者,多因事诛之。”因为分别是重用和制衡的对象,所以,王建对士人和诸将的态度也就截然相反。在这个过程中,士人甚至直接参与诛杀武将。《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三:“宗涤有勇略,得众心,王建忌之。建作府门,绘以朱丹,蜀人谓之‘画红楼’,建以宗涤姓名应之,王宗佶等疾其功,复构以飞语。建召宗涤至成都,诘责之,宗涤曰:‘三蜀略平,大王听谗,杀功臣可矣。’建命亲随马军都指挥使唐道袭夜饮之酒,缢杀之,成都为之罢市,连营涕泣,如丧亲戚。”王宗涤就是华洪,是攻占、经营东川的最主要成员,先后被唐朝册封为东川节度使、山南东道节度使,已经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终于成为王建“多忌好杀”的对象,这强烈震慑住武将集团。唐道袭是前蜀刺史唐峰之子,后来长期任枢密使,而枢密使在宋光嗣之前专用士人。《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初,蜀主虽因唐制置枢密使,专用士人,及唐文扆得罪,蜀主以诸将多许州故人,恐其不为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所以,唐道袭正是王建信任的士人集团核心成员,在诛杀王宗涤的过程中,应该不只是具体操作而已,很可能参与筹划,甚至决策。
天祐四年(公元907年)九月,前蜀政权正式建立,王建重用士人的政策完全明朗化,《新五代史·前蜀世家》:“秋九月己亥,建乃即皇帝位。封其诸子为王,以王宗佶为中书令,韦庄为左散骑常侍判中书门下事,唐道袭为枢密使,郑骞为御史中丞,张格、王锴皆为翰林学士,周博雅为成都尹。蜀恃险而富,当唐之末,士人多欲依建以避乱。建虽起盗贼,而为人多智诈,善待士,故其僭号,所用皆唐名臣世族;庄,见素之孙;格,浚之子也。建谓左右曰:‘吾为神策军将时,宿卫禁中,见天子夜召学士,出入无间,恩礼亲厚如寮友,非将相可比也。’故建待格等恩礼尤异,其余宋玭等百余人,并见信用。”士人对于武将集团在前蜀政权中的隐患颇为关注,《十国春秋·冯涓传》:“永平初,高祖屡兴兵旅,涓上疏曰:‘古之用兵,非以逞威暴而肆杀戮,盖以安民为先,丰财为本。汤武无忿怒之师,高光有鱼水之士。故能应天顺人,吊民伐罪。今自土德云衰,朱梁逞虐,雍都洛邑,尽是荆榛。江南山东,各有割据。斗力则人各有力,用兵则人各有兵。陛下欲以一方之强,举万全之策,臣恐陛下之忧,不在于秦雍,而在于肘腋之下也。’”冯涓是唐朝吏部尚书冯宿之子,大中年间就已经入仕,对于黄巢起义之后,强藩悍将威胁唐朝君王的历史有着深刻体会,所以,引以为戒。事实上,冯涓不是反对王建用兵,而是提醒王建注意在频繁用兵的过程中要极力避免武将集团坐大,从而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所谓“肘腋之下”的忧患就有可能来自武将集团。
正因为如此,武将集团与士人集团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浮出水面,《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六:
蜀太师王宗佶既罢相,怨望,阴畜养死士,谋作乱。上表以为:“臣官预大臣,亲则长子,国家之事,休戚是同。今储贰未定,必启厉阶。陛下若以宗懿才堪继承,宜早行册礼,以臣为元帅,兼总六军。傥以时方艰难,宗懿冲幼,臣安敢持谦不当重事!陛下既正位南面,军旅之事宜委之臣下。臣请开元帅府,铸六军印,征戍征发,臣悉专行。太子视膳于晨昏,微臣握兵于环卫,万世基业,惟陛下裁之。”蜀主怒,隐忍未发,以问唐道袭,对曰:“宗佶威望,内外慑服,足以统御诸将。”蜀主益疑之。己亥,宗佶入见,辞色悖慢。蜀主谕之,宗佶不退,蜀主不堪其忿,命卫士扑杀之。贬其党御史中丞郑骞为维州司户,卫尉少卿李钢为汶川尉,皆赐死于路。
枢密使是前蜀军政中枢,权力核心,在宋光嗣之前专用士人,所以,王宗佶与唐道袭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个人恩怨,而是武将集团与士人集团矛盾的集中反映。王宗佶上表所请的正是后来王元膺所任的“判六军诸卫事”,也就是禁军的控制权,足以抗衡枢密使,威胁皇权,所以,唐道袭对王宗佶也难以继续隐忍,所谓“宗佶威望,内外慑服,足以统御诸将”,暗示以王宗佶为代表的武将集团通过控制禁军威胁皇权的意图,这终于真正引起王建的警觉。就王建对唐道袭和王宗佶的态度而言,正是重用士人、制衡武将的政策使然。王建扑杀王宗佶之后,就以王宗懿为皇太子,判六军诸卫事,控制禁军,是就王宗佶上表所请的善后;目的在于强硬回应武将集团,却为王元膺事件埋下伏笔。
前蜀武成元年(公元908年)七月,王宗懿成为皇太子,与士人集团格格不入,矛盾难以调和,终于导致王元膺事件,引起政局剧烈动荡,为易储埋下伏笔。
王宗懿是王建第二子,因为长子王宗仁“幼以疾废”而顺位成为皇太子。其就气质才华而言,孔武有余而守文不足,与士人难以相容,《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八:“蜀太子元膺,豭喙龅齿,目视不正,而警敏知书,善骑射,性狷急猜忍。蜀主命杜光庭选纯静有德者使侍东宫,光庭荐儒者许寂、徐简夫,太子未尝与之交言,日与乐工群小嬉戏无度,僚属莫敢谏。”
王宗懿与唐道袭矛盾公开化是在武成三年三月,经过王建居中调控而暂时缓和,《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七:“蜀太子宗懿骄暴,好陵傲旧臣。内枢密使唐道袭,蜀主之嬖臣也,太子屡谑之于朝,由是有隙,互相诉于蜀主。蜀主恐其交恶,以道袭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道袭荐宣徽北院使郑顼为内枢密使,顼受命之日,即欲按道袭昆弟盗用内库金帛。道袭惧,奏顼褊急,不可大任。丙午,出顼为果州刺史,以宣徽南院使潘炕为内枢密使。”由此可知,王建对王宗懿和唐道袭的态度都颇为积极,极力避免二人交恶。
所以,永平元年(公元911年)五月、十月,王建两次出征利州,都以皇太子监国;永平二年八月,甚至炮制膺昌铜牌祥瑞,为皇太子进行政治宣传,《蜀梼杌》:“八月,什邡县获铜牌、石记,有膺昌之文,改什邡为通计县,改太子名为元膺。”《五国故事》:“建在位,有汉州人郭迥,耕得古铜牌以献,有‘王建王元膺’以下六十余字。建乃改其长子名元膺,以应其事。”《新五代史·前蜀世家》:“元膺,建次子也,初名宗懿,后更名宗坦,建得铜牌子于什邡,有文二十余字,建以为符谶,因取之以名诸子,故又更曰元膺。”膺昌铜牌祥瑞在当时声势浩大,朝野皆知,引起高度关注,《太平广记·禽鸟四·仙居山异鸟》:“王蜀永平二年,得北邙山章弘道所留瑞文于什邡之仙居山,遂出缗钱,委汉州马步使赵弘约,缔构观宇。洎创天尊殿,材石宏博,功用甚多。是日,将架巨梁,工巧丁役三百余人缚拽鼓噪,震动远近。”所以,武成、永平年间,王元膺储位极为稳固。
唐道袭则在永平元年伐岐过程中,以三招讨使之一的身份独当一面,颇有军功,甚至在青泥岭之败后,力排众议,坚守兴元,为后来蜀军反击奠定基础,《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八:“众议欲弃兴元,道袭曰:‘无兴元则无安远,利州遂为敌境矣。理必以死守之。’蜀主以昌王宗 为应援招讨使,定戎团练使王宗播为四招讨马步都指挥使,将兵救安远军,壁于廉、让之间,与唐道袭合击岐兵,大破之于明珠曲。”
永平三年二月,唐道袭自兴元归,复为枢密使,与王元膺矛盾逐渐激化,终于导致王元膺事件的爆发,《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八:

庚戌,赠唐道袭太师,谥忠壮;复以潘峭为枢密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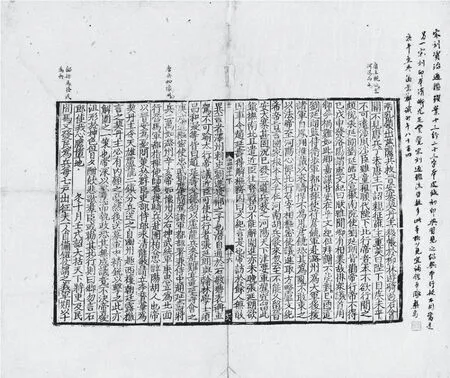
《资治通鉴》(宋刻本)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前蜀政权中的士人虽然获得重用,但是,几乎没有直接参与军事行动,遑论率军征战,所以,唐道袭自伐岐以后,军功赫赫,已经成为士人集团事实上的代表人物,也就意味着士人集团势力的上升,从而对王元膺形成更加强烈的压力,导致王元膺必欲除之而后快。值得注意的是,王元膺亲信徐瑶也是所谓的“许州故人”,而且,对士人态度恶劣,甚至肆意凌辱士人,《蜀梼杌》:“瑶字伯玉,长葛人。从建入蜀,勇猛善格斗。建初在韦昭度幕府,其兵皆文身黧黑,衣装诡异,众皆称为‘鬼兵’,称瑶为‘鬼魁’。建克成都,瑶多污辱衣冠士女。富人李希妻俞氏有异色,瑶虏而逼之。俞氏曰:‘吾夫夙尝为乡贡进士,风流儒雅,人比之相如,我尚以非吾匹。尔健儿也,焉得无礼于我。’瑶仗剑谓曰:‘尔畏此乎?’俞氏曰:‘吾宁死,必不受辱。’瑶欲杀之,左右谓曰:‘城中妇人无限,何必逞暴于此。’遂杖而释之。”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元膺对唐道袭等人的态度代表的并不是个人意志,而是武将集团的意志,所以,唐道袭所谓“太子谋作乱,欲召诸将、诸王,以兵锢之,然后举事耳”能够说服王建召屯营兵入宿卫,内外戒严;因为王建对于武将集团的制衡由来已久。后来潘炕言于王建“宜面谕大臣以安社稷”,也是在提醒王建解决王元膺事件的关键在于稳定武将集团。值得注意的是,王宗侃、王宗贺、王宗鲁等人奉诏而来,态度极为暧昧,行动迟疑,只是“陈于西球场门”,只有王宗黯力战平乱。这就再次证明武将集团对于王元膺的支持,因为王元膺针对的是以唐道袭为代表的士人集团。引申而言,王元膺事件意味着当时武将集团与士人集团之间的矛盾已经难以调和。
王元膺事件之后,王宗衍成为皇太子,宦官集团颇有力焉,《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八:“蜀潘炕屡请立太子,蜀主以雅王宗辂类己,信王宗杰才敏,欲择一人立之。郑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贤妃有宠,欲立其子,使飞龙使唐文扆讽张格上表请立宗衍。格夜以表示功臣王宗侃等,诈云受密旨,众皆署名。蜀主令相者视诸子,亦希旨言郑王相最贵。蜀主以为众人实欲立宗衍,不得已许之,曰:‘宗衍幼懦,能堪其任乎?’甲午,立宗衍为太子。”王宗衍是王建幼子,气质才华也难以获得王建认同,主要是因为母妃徐贤妃是唐朝眉州刺史徐耕之女,容易获得士人集团的认同,而与武将集团存在距离,从而为王建所接受,终于使之在储位之争中反败为胜,继王元膺之后成为皇太子。时在永平三年十月,距离王元膺事件仅仅一月。这说明了王建继续制衡武将集团的坚定意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唐文扆遵循的是王建的意志;所以,能够以一介飞龙使的身份居中联络,推动宰相张格、功臣王宗侃等前蜀政治核心人物支持王宗衍成为皇太子。
宦官集团在前蜀政权易储之后获得王建的扶持而逐渐崛起,势力全面扩张,意味着前蜀政局已经难以挽回。
永平五年十一月,前蜀击破岐军,获得秦、凤、阶、成四州之地,为宦官集团进入前蜀方镇体系提供了可能。通正元年(公元916年),唐文扆之弟唐文裔以匡国军使为东北面第三招讨,与都招讨王宗绾、第一招讨刘知俊、第二招讨王宗俦等十万之众出秦州伐岐;十月,为天雄军节度使,镇秦州。秦州是前蜀控扼后唐、秦岐的战略要地,极为重要,却由宦官集团控制,隐患之深不言而喻。从这个意义上说,“水行仙,怕秦川”最初的指向或许正在于此。
《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蜀飞龙使唐文扆居中用事,张格附之,与司徒、判枢密院事毛文锡争权。文锡将以女适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庾传素之子,会亲族于枢密院用乐,不先表闻,蜀主闻乐声,怪之,文扆从而谮之。八月,庚寅,贬文锡茂州司马,其子司封员外郎询流维州,籍没其家;贬文锡弟翰林学士文晏为荥经尉;传素罢为工部尚书。以翰林学士承旨庾凝绩权判内枢密院事。凝绩,传素之再从弟也。”张格与毛文锡争权遵循的是宦官集团的意志,反映的是宦官集团对枢密使的觊觎,而宦官集团的背后是王建。所以,王建虽然以庾凝绩权判内枢密院事,但是,还是贬毛文锡等人,意味着宦官集团距离控制枢密使已经近在咫尺。
王建扶持宦官集团也是为了制衡武将集团,从而引起武将集团的强烈反弹,形势终于失控,《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
丁酉,削唐文扆官爵,流雅州。辛丑,以宋光嗣为内枢密使,与兼中书令王宗弼、宗瑶、宗绾、宗夔并受遗诏辅政。初,蜀主虽因唐制置枢密使,专用士人。及唐文扆得罪,蜀主以诸将多许州故人,恐其不为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始用事。

五代十国(含前蜀)图
武成元年(公元908年)七月,王元膺判六军诸卫事,控制禁军。所以,王元膺事件前夕,唐道袭请召屯营兵入宿卫,却还是难以抗衡禁军,必须王宗黯勤王才能够控制形势,足以说明当时禁军对于皇权的重要意义。就徐瑶等人与王元膺的关系而言,武将集团已经通过王元膺与禁军形成颇为密切关系,从而严重威胁皇权。所以,王元膺事件之后,王建就以宦官判六军诸卫事,控制禁军,避免武将集团与禁军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唐文扆是因为王建扶持而参预机密,矛头所指正是以王宗弼为代表的武将集团。所以,唐文扆的流放只是王建在王宗弼等武将集团直接压力下的妥协而已,并不意味着宦官集团的失势。事实上,宋光嗣成为枢密使,反而意味着宦官集团势力的扩张,从禁军、方镇正式渗透到政治中枢。所以,其能够在乾德年间左右政局,终于导致前蜀覆灭。
值得注意的是,王建在逐鹿蜀中之前,先后在杨复光、田令孜麾下,与宦官集团关系密切,又为神策军将,宿卫禁中,扈从僖宗播迁,对于宦官专权的危害有着切身的体会。所以,王建在建立前蜀政权之后,虽然致力于恢复唐朝典章制度,但是,却极力避免宦官专权,而以士人为枢密使,以皇太子控制禁军。惜于王元膺事件之后,他却改弦更张,逐渐推动宦官集团控制禁军、方镇,出任枢密使,终于形成前蜀政权的宦官专权。其路径与唐朝几乎如出一辙,最终也导致前蜀政权的内忧外患,难以挽回。追根溯源,也是源于他对武将集团的不信任。引申而言,前蜀政权几乎是对唐朝的“复盘”。这也说明了唐朝政治经验的局限性,从而昭示唐宋政治转型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水行仙,怕秦川”反映的不但是前蜀政权由盛转衰的必然趋势,也是唐宋政治转型的历史走向。

永陵神道(在成都永陵博物馆)
[1]陶穀:《清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
[2][5][7][9][10][11][14][15][16][21][22][24][25][26]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346、8347页,第8422页,第8728页,第8420页,第8581页,第8826页,第8689、8692、8693页,第8773页,第8721页,第8745、8746页,第8768、8773、8774、8775、8776页,第8777页,第8816页,第8825、8826页。
[3][12][19]欧阳修等:《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85页,第787页,第789页。
[4][6][8][13][17][18][23]傅璇琮等:《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6075、6076页,第5912页,第3946页,第3952页,第6076页,第3186页,第6076页。
[20]李昉等:《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8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