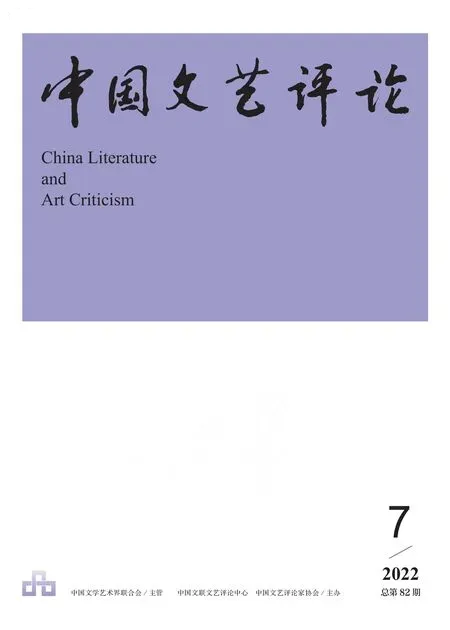回到美学,重启美育
2022-10-29刘成纪
■ 刘成纪
中国现代美学,自从20世纪初叶一批先贤将它引入中国以来,它的发展过程一直与审美教育相辅相成。美育作为美学理论的实践形态,一方面受美学理论的规约和指导,另一方面也反向检验着美学理论的实践价值。但从近年来我国的美育实践看,美学与美育原本应有的互动关系正日益变得松弛,原本具有相对普遍意义的美育一步步被狭隘化为艺术教育,美育所应具有的思想深度和精神高度也被艺考式的技能学习所限制。在这种背景下,重新回到美学理论,看它如何界定美育,以及如何看待艺术教育在审美教育中的位置,就成为对相关教育实践进行纠偏的关键。
一、当代社会的“美学时间”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学这门学科自成立的那一天开始,自身就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到今天也没有改变。比如它早期被称为“感性学”,后来被称为“艺术哲学”,20世纪60年代之后被称为“文化哲学”,等等。甚而言之,西方20世纪的美学取消主义者认为美不过是一个形容词,缺乏明确的专指对象,围绕它根本不应该建立一门学科。可以认为,在当代社会,人们一方面认为美像真、善一样,都是人的基本需要,审美教育大有可为;另一方面在实践方面却一再遇到障碍和困难,根本原因就是它在理论上存在问题。或者说,美学基本理论的多变必然带来美育实践目标的多变,使它很难像德育、智育、体育一样,有一个形成共识的工作方向或相对稳定的教育方案。
但是近年来,随着对美学这门学科的体验和领悟不断加深,笔者却愈来愈倾向于接受这种现状。这是因为,在当代自然人文科学日益体系化、学科壁垒日益森严的背景下,美学自我定位的不确定,正预示着它的开放性和兼容性。这种特性使它能够成为穿透种种知识壁垒的利器,促进人对自然和人文问题的综合思考,进而促进多种学科之间的协调发展。也就是说,在现代自然和人文科学领域,美学可能是仍保持着人类文明早期“知识无区分”特性的唯一一门综合学科,它仍在用近于原始的生命精神,对科学时代的本质主义或知识的专精化倾向进行顽强抵抗。这预示着,当代美学在理论层面常常被人们视为的所谓“缺失”,恰恰使它有机会摆脱诸多固有知识范式的钳制,显现出更强大的生命活力。同样,当代美育研究者之所以屡屡会谈到审美教育的人文性、开放性、包容性和跨学科性,原因就在于美学在理论层面没有给它太过严苛的关于实践边界的限定。
二、美学三变与美育的领域
当然,说审美教育给人带来的是具有解放感的“美学时间”,并不是说它没有领域、没有规则、没有价值导向,而是讲它设定的规则相对宽泛、相对富有弹性。比如有人认为,对于幼童而言,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就是放弃教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守护他们的自由天性和想象力不受损伤。但是从逻辑上讲,任何放弃都是以曾经的给予作为前提的,没有教育作为先导,所谓“放弃教育”必定是一句空谈。也就是说,唯有教育才能构成放弃教育的前提,审美教育也是一样。那么,在美学和美育之间,长期缺乏确定性的美学理论到底能够给予美育什么?
首先,美学学科在创立之初,德国人鲍姆嘉通将它称为“感性学”,这意味着人的审美活动是一种感性活动。它一方面基于人的自然本性(甚至身体),另一方面必须在具体的、活生生的感性事物中进行,永远离不开人的看和听。对于审美教育,尤其是对于长年生长于都市的学生和一般居民而言,这种理论定位具有重大意义。这是因为,现代都市是被科学规划的人居环境,它高度抽象化、几何化、规则化,这种环境有利于训练人的数学或理性思维,但对人的自然天性和想象力的释放却构成了限制。这样,作为感性学的美学对自然的重视、对事物感性形象的重视,就有助于激发人的内在生命活力,能使人在理性与感性、抽象与具象、遵守规则与保持个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审美教育中的自然教育,以及通过郊游、旅行等活动与自然保持亲近,均属于美学作为感性学引发的工作目标。
再次看美学被定位为文化哲学。这种看法是在当代艺术日益与生活融合的背景下被提出来的。现代以来,随着人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人们不仅可以按照美的规律创作艺术作品,而且可以直接创造现实,使城市的小区、街道乃至整座城市都成为人类的艺术作品,这导致了现实生活的艺术化;另一方面,在当代业已充分艺术化的城市中,审美标准往往难以使艺术与非艺术区隔开来,这反向诱使艺术家开始弱化艺术的审美品质,变得向生活靠拢,这就是艺术的生活化。这种艺术和生活的互化,将传统社会在两者之间设置的壁垒打破了,我们很难在现代城市公共空间中看到哪些是纯粹的生活,哪些是纯粹的艺术,而更多是作为两者融合形态的文化。就此而言,建立在文化哲学基础上的审美教育,往往意在培养受教育者对当下现实的反思和反观能力,让人在看似庸常的日常文化景观中探寻人生和世界的意义。
在现代美学领域,感性学主要指向自然,艺术哲学主要指向艺术,文化哲学主要指向社会现实,这意味着完整形态的现代审美教育,至少应该包括自然美育、艺术美育和社会美育三个环节;也说明美学看似因为学科定位的不确定导致了美育实践的混乱,但事实上却分别凸显了美育需要重点关注的三个基本领域。在这一背景下,有些问题就有进一步反思的必要,比如在当代教育实践中,美育往往被等同于艺术教育,这显然并不是因为艺术教育比自然和社会美育更重要,而更多是因为它更便于实施和操作。比如,它不需要组织学生走向野外,也不需要进入城市社区或其他公共空间,似乎只在教室里欣赏一首乐曲或一幅名画就万事大吉了。也就是说,这种选择并不是基于学生的需要,而更多是源于施教者的懒惰,以及现有教学资源的难以支持。但是,这种被“名作欣赏”限定的美育必然是狭隘的,它在自然和社会美育方面存在的重大缺失,必须引起教育界有识之士的警惕。
三、美育目标:自由、秩序、和谐
借助现代美学理论,我们可以将审美教育的边界由艺术拓展到自然和社会现实层面,这对建构一种完善的现代美育体系是重要的,但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现代以来,我国的审美教育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它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方式均来自对西方的挪用和借鉴,而中国自身的传统则基本被淡忘。那么,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到底留下了什么值得珍视的美学遗产?在当代中西互鉴的大背景下,这类遗产又能为美育带来什么?
在美学界,一个耳熟能详的事实是,虽然美学这门学科发端于西方,但20世纪以来它在欧美的影响力已日益式微,而在东亚、尤其是在中国则一直保持繁荣态势,人们一般称之为美学在东亚的复兴,并认为这主要源自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促动。确实,中国传统社会自西周周公制礼作乐始,以“尚文”为标志的礼乐传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相关的文化被称为礼乐文化,政治制度被称为礼乐制度,文明形态被称为礼乐文明。也就是说,礼乐既主导着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架构,又蔓延向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什么是礼乐?简而言之,所谓“礼”,包括礼仪、典礼、礼器诸层面,但根本问题是人的行为的雅化或艺术化;所谓“乐”则包括诗、乐、舞,它本身就属于美和艺术。也就是说,礼乐文化、制度和文明,本质上是一种由美和艺术主导的文化、制度和文明。而建基于礼乐的传统中国,则因此成为一个褒爱艺术的国度,具有审美共同体性质。
就诗、礼、乐的性质而言,中国传统教育基本上可以等同于审美教育,或至少是从美和艺术出发的人文教育。但如上所言,这种教育的价值并没有被限定在个体人格养成层面,而是从个体出发不断向家国天下放大。比如在个体层面,孔子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是将“文质彬彬”作为君子应有的风仪和人格表征;在家庭层面,中国人讲诗礼传家,认为诗与礼的教育可以培养良好家风;在国家层面,孔子讲“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这是将文教昌隆作为国家理想;在天下层面,中国人讲“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语),这是将世界大同的美好愿景用美来象征。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审美教育,是贯穿于个体和家国天下的一揽子方案,而不仅仅只是个体化的精神陶冶问题。这使它既区别于西方,也区别于中国现代对美育的定位。
与此一致,关于诗、礼、乐三教的价值和意义,孔子曾经做过一个简要的概述,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这句话看似在强调审美教育伴随着人一生的成长过程,但是,后世儒家却从中推导出了中国美学关于美育的一般理论构想。如《礼记·乐记》讲:“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这明显是将和谐作为乐的本性,将秩序作为礼的法则。同时,孔子讲“兴于诗”,这里的“兴”是指诗对人内在情志的提振和兴发,主要关乎人的精神自由问题。据此,所谓诗教、礼教和乐教,本质上也就是关于个体自由、社会秩序和天人和谐的教育,自由、秩序、和谐也因此成为中国传统美育的三大主题。这与西方现代仅仅将美育的价值限定在个体自由相比,显现出了它更宏阔的理论视野和实践意义。
四、可能的当代美育框架
可以认为,只要有这一价值基础存在,美学和美育就永远无法被取代,永远不会消亡。至于它在理论和教育实践上是否成熟和完善,则不过是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的技术改进问题。那么目前,它亟待解决的这类问题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按照当代美学的理论给予,应重新界定艺术教育与自然美育和社会美育的关系。其中,艺术教育固然重要,但它也仅是现代美育体系中的一个品类,无法代表美育,更无法代替美育。借助美育实践,有必要让学生既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即便囿于现有的教学条件无法真正做到让学生“行万里路”,也应该因此意识到课堂化的艺术鉴赏的局限,意识到让学生真切感受自然和社会文化,像感受艺术一样重要。就目前我国审美教育的现状看,亟待补强的是自然美育。这是因为,现代社会发展的标志是它的高度专业化和秩序化,这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但却遏制了人的多元需要,并进而损伤了人的创造力。与此不同,大自然总是千姿百态的,所谓天下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正是在讲自然世界的无限多元和无限差异性。由此,大自然不仅能以其活跃的感性对日益抽象、概念化的现实形成激活和唤醒,而且作为自由意志的隐喻,能成为激发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潜能的重大诱发因素。
三是按照中西互鉴的理念,重订美育的价值原则。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的美育以自由作为核心价值,审美教育几可等同于自由教育。与此相比,中国传统诗教也讲自由,但同时谋求在自由、秩序、和谐三者之间保持平衡。也就是说,它既兼顾了个体自由和群体秩序,又试图借助音乐化的和谐寻求综合超越。这显然是一个更稳健也更具建设性的美育方案。从中西美学史看,西方现代美育之所以将它的目标限定于个体自由,远因是西方个人主义的精神传统,近因则是康德标举的审美无利害性。但显然的问题是,人的任何活动都是以趋于价值为目标的,所谓审美无利害,也只不过是绕了一个更大的圈子来达至它更趋高远的现实目标。这就是今人所讲的美育“以无用为大用”,以审美无利害通达于审美功利主义。同样,审美教育作为自由教育,它本身就是一个背反的命题,因为任何教育都具有强制性,审美一旦诉诸教育就必然是对自由的否定。这两点说明,即便在西方,美育也无法被自由限定,而是表现出虽秘而不宣但“另有所图”的性质。自由和教育的逻辑矛盾也说明,审美如果必须诉诸教育,那么它就应该是最低限度的教育,即通过弱化教育的强制性而使教育的目标看起来像在自然实现,这就是中国人讲的“不言之教”或者“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至于它向秩序和和谐的价值延伸,也应该是自然而然的,如孔子讲:“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礼记·孔子闲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