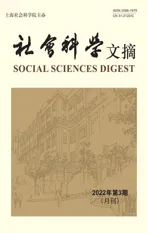网络空间军事化发展态势及其应对
2022-10-26杜雁芸
文/杜雁芸
近些年,随着国际社会愈发重视网络空间的军事行动,网络军事化发展愈演愈烈。本文通过梳理总结网络空间军事化发展态势,深入分析其成因,基于网络安全困境和网络军事化发展互为因果的关系进行尝试性的论证,对于理解国际社会应对之策的有效性和有限性具有重要意义,为避免网络空间军事化发展转向网络战提供有益参考。
网络空间军事化发展态势
(一)基于军事目的的网络冲突频发
近些年,基于军事目的和聚焦安全领域的网络对抗层出不穷。2007年爱沙尼亚政府遭遇网络攻击,致使政府和关键基础设施网站大面积瘫痪,西方将攻击者锁定为俄罗斯政府支持的黑客,声称俄罗斯是“第一个发动国家间网络战争的国家”,并将这次攻击定性为第一场真正意义上国家之间的网络战争。基于政治目的、由国家操纵、达到军事安全效果的网络冲突由此拉开序幕。之后的俄格冲突和乌克兰危机都是在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中同时爆发冲突对抗的。
网络攻击、网络冲突极易引发物理空间军事上的对抗,导致国际网络空间的战略稳定性遭到破坏。2019年以色列国防军宣布成功阻止了哈马斯的网络攻击,并对其发动军事空袭,这是以色列国防军首次通过武力攻击方式反击对手的网络攻击。由此,网络攻击诱发现实冲突的“潘多拉魔盒”已被打开,极易引发更高层次的冲突。另外,网络干预大选增加了美国对中俄等国的敌意,美国多份政府报告均凸显对抗中俄的基调,这使得国家和地区间的战略稳定性遭到破坏。如若双方在虚拟空间不加以克制,很有可能引发物理空间的军事冲突。
(二)积极加强网络空间作战力量建设
当前,大国网络安全战略中的军事色彩不断凸显,军事和国防要素在网络战略体系中的比重不断攀升,战略重心也由一般网络安全转向军事安全。美国最先建立网军并发起网络作战,也是最早将网络军事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国家。美国的网络安全议题已被纳入“高政治”的军事范畴,其网络空间战略更加激进。俄罗斯的网络安全战略相对“平和”,但“战时思维”也充斥其中。
为了有效贯彻网络空间战略,各国积极加强网络空间作战力量建设,强化自身在网络空间的军事行动能力,客观上加速了网络空间军事化进程。美军网络司令部于2010年5月正式启动,2017年升格为美军第10个联合作战司令部。美网军已成为一支独立作战力量,降低了其网络攻击甚至网络战的门槛,其对外进行军事行动更加便利化、自主化。北约在2018年建成网络空间作战/行动中心,将成员国网络能力整合到联盟作战任务中。近几年,北约将乌克兰纳入网络作战体系,矛头直指俄罗斯,欧俄在网络空间的军事对抗更加公开化,加速了网络空间的军事化进程。
(三)网络武器开发运用白热化
网络武器已成为未来战争利器,各大国争相研发运用,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常规武器系统向信息化、智能化升级;二是在常规战争或网络战争中进行网络攻击;三是非战时使用网络武器,使敌对国基础设施遭受硬毁伤或软毁伤,给其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破坏。
继“震网”病毒后,网络武器升级换代、层出不穷。2017年一款名为“想哭”的勒索病毒肆虐全球,展现出网络武器威力,也预示着网络武器扩散的形势恶化。恐怖组织、犯罪团伙可以通过攻击网络部队武器库窃取网络武器,获得网络战能力,并毫无征兆地对全球任意基础设施发起攻击,“数字珍珠港”事件很可能变为现实。
网络空间军事化发展的原因
网络空间军事化发展受到国际重视、网络军备竞赛如火如荼展开,主要归结于安全困境在网络空间的衍生和嬗变。而有关限制网络军备发展、制约网络军事冲突的国际机制尚处于空白或不完善,且网络军事化的收益远高于成本,诱使各行为体积极加强网络军备建设。因此,安全困境在网络空间的产生成为必然。与此同时,安全困境又进一步助推网络军事化的发展。可以看出,网络安全困境和网络军事化发展互为因果,相互作用。
(一)网络空间互信缺失
网络空间不互信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实体空间不互信折射到网络空间,即实体空间中的结构性矛盾折射为虚拟世界中的敌对关系。当今,中美安全困境不仅仅体现在传统疆域,在网络空间的不互信、猜忌、对抗也呈几何级数倍增。
二是各国加强网络空间博弈,恶化网络空间互信。随着网络空间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美国感到自身绝对实力相对弱化,其网络主导权也被削弱。因此,继续领导网络世界、确保网络空间主导权是美国在网络空间战略博弈的内在动力和核心目标。特朗普时期,一方面,美国把中俄锁定为其网络安全的最大挑战,伙同盟友对中国施压;另一方面,美国的单边行径也影响了其与盟友间的网络互信。各国在网络空间的战略博弈和彼此间不互信呈现一种互相影响、螺旋上升的恶性循环趋势,这势必导致网络军备竞赛不断升级。
三是网络空间的新特性加剧安全领域对抗性。虚拟空间中的两国关系不仅仅是现实关系在网络空间的投射,还将是一个新型数字领域的竞争、冲突与合作的复合体。网络空间的疆界模糊性、高依赖性和虚拟性等特点给国家安全提出了新挑战、新风险,加剧了安全领域的对抗性。首先,网络空间疆界不甚明朗,网络监听、网络窃密、网络攻击等“越界”行为随时可能发生,使国家间不安全感陡增,加深彼此间不互信。其次,现实世界对网络空间的高度依赖性,使各国政府加强对网络威胁感知和基础设施保护的重视,但同时也加深了对对方威胁感的认知。最后,网络空间具有虚拟性、隐蔽性、匿名性等特殊性,在网络空间里无法及时准确认定攻击行为、无法有效考证犯罪动机,对网络攻击或网络战采取的方式手段进行捕获和核查更是难上加难。
(二)国际机制空白且滞后
网络空间军事化发展之所以愈演愈烈,主观上是网络空间互信缺失,客观上是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机制构建尚处于起步阶段,其建章立制也在深度博弈中,这对网络军事化规约限制十分有限。一是关于限制网络军备发展、网络军事冲突的国际机制还未建立。2016—2017届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UN GGE)谈判破裂,主要基于《联合国宪章》第51条如何适用网络空间的问题,对拟议列入“自卫”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采取反措施出现争论和分歧。这折射出西方网络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就网络空间军事化和是否运用传统军事手段干预网络攻击存在着巨大的认知差异。
二是构建国际机制的某些共识已达成,但并未有效履行。2015年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就“不攻击关键基础设施”问题达成一致,但现实中的攻击事件层出不穷。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就网络主权在2015年达成一致,2021年第六届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的报告多次要求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但主权原则在网络空间的适用不仅存在着争议,而且网络主权在国际社会的践行处于“画饼充饥”的状态。美欧等西方国家一方面“只做不说”地积极维护自身网络主权,另一方面又运用自身强大的网络技术和资源优势侵犯其他国家的网络主权。
(三)网络军事化收益比高
一是网络军事化投入小,可以在军事对抗中取得非对称性优势。和传统作战相比,网络武器研制投入较少且网络攻击操作简便易施,但攻击效果不逊于传统作战,这种非对称性优势被国际行为体所看重。首先,网络武器的开发运用无需耗资庞大的社会化大生产和传统武器装备的大规模制造,只需电脑硬件设备和开发网络武器的软件程序即可;其次,网络作战无需人员的远程奔袭和装备的快速投送,随时随地可以发动网络打击,网络作战也是减少人员接触对抗、降低人员毁伤性打击的新型作战方式;最后,较之传统作战,网络攻击的门槛较低,人力与装备的消耗成本少,只要接受过计算机专业训练的操作员都可以进行网络攻击,而且计算机程序自行搜索可以向预设目标发动攻击,还可以通过感染僵尸病毒,进行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等。基于以上优势,各国都争先发展网络军事实力,提升自身网络军备建设的非对称性。
二是网络军事化收益高,取得制网权是现代战争制胜的关键因素。网络空间已经成为新型作战平台,传统意义上的陆海空天战场已充斥网络电磁波束,未来战场就是网络化的战场,交战双方的命令下达、攻防对抗都要依靠网络信息的畅通无阻。一体化作战中,陆海空天电各个部门、各个体系连为一体,网络成为现代化作战体系中的命脉和血液。因此,夺取制网权成为大国赢得战争、取得胜利的制胜机理。另外,各国积极进行有效的网络威慑,网络作战可建立一种新形式的“互相确保摧毁”的模式。由此,网络军事化发展的低投入、高收益的特点,极大地诱惑各网络大国积极抢占这一军事制高点,夺取制信息权和制网权,这势必加速助推网络空间军事化进程。
网络空间军事化发展的应对
(一)形成威慑力量以求自主性安全
随着网络空间被视为新型作战空间,网络攻击被视作新式作战手段,威慑理论也延伸扩展到网络空间,各网络大国通过强化网络威慑力量以应对网络空间军事化的发展,实现自主性安全。网络威慑中,惩罚性威慑和拒止性威慑在各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中居多。惩罚性威慑和拒止性威慑相互补充,各国通过提升网络进攻能力和加强网络基础设施防护来强化威慑力。
各国虽积极践行网络威慑,但对其有效性的质疑也从未停止。一是网络威慑能力难以测量评估和有效展示。网络军备力量的衡量没有统一标准,且网络武器一旦投入使用就会失效,没有强大实力展示如何进行有效威慑?二是决心的表达并未对潜在的攻击者产生强有力的震慑作用。三是归因溯源难成为实现网络威慑的最大障碍。归因是威慑的核心,但攻击者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难以确定,网络威慑经常处于“有威慑能力而无威慑对象”的尴尬境地。
尽管网络威慑面临诸多难题,但各个国家仍不遗余力加强各自的网络威慑力量建设:网络威慑泛化、实战化日益凸显,结合“跨域威慑”的报复手段提升网络威慑的可信度,集国家之力、联合盟友的“分层网络威慑”构筑进攻性的“共同防御”体系,以及通过国家间的集体协作来建立共同防御体系的联合威慑等。各国通过不同层面的各种手段加强网络威慑实力,寻求在网络空间的非对称优势,实现自主性安全。
(二)完善法律机制以求约束性安全
首先,调整既有国际法以适应网络空间。国际法适用于网络空间已成为国际共识,但现有国际法很难限制网络军事化发展。2017年UN GGE谈判破裂,UN GGE机制陷入停滞状态。令人欣喜的是,2021年5月28日第六届UN GGE谈判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承认国际人道主义法(IHL)适用于武装冲突期间的网络行动。尽管在IHL如何管理武装冲突期间的网络行动上仍有争议,但各国强调,国际人道主义法既不鼓励军事化,也不允许在任何领域诉诸冲突。下一步就IHL如何在国际或非国际武装冲突期间管理网络行动,以及网络自卫权和采取反措施等方面,国际社会将结合国际法和战争伦理等规约弥合分歧、探索解决之道。
其次,建立网络归因机制。一是建立国际网络归因平台机制。要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中立客观的国际平台,开展专业的溯源工作,采取相应的调查取证,并建立互联网基础设施端对端的问责制,这将震慑并制约钻溯源空子的恶意攻击行为。二是加强国际网络归因合作。这需要在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等权威国际组织的支持和斡旋下,提升国家间网络归因合作,缩小归因技术鸿沟,加强技术交流,公开已归因的全部数据,以应对全球网络空间安全上的“短板效应”。
(三)构建互信共识以求合作性安全
首先,通过建立信任措施构建互信。目前大国在网络空间达成战略互信的难度较大,可以采取先易后难的做法。作为过渡性措施,透明与信任建设机制在网络空间同样适用。早在2015年,中俄等6国共同向第69届联合国大会提交了“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更新草案,新增了规范负责任国家行为准则和信息空间建立信任措施。第四届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也提出了建立政策联络点、建立危机管控机制、建立技术法律合作机制和加强执法合作等更高层次的信任措施。当前专家组提出的信任措施,效果不甚显著。下一步,国际社会将在网络空间透明与信任建设的知易行难问题上多下功夫,找到各国共识,期待由此形成网络空间动态平衡,对网络军事化发展起到抵消对冲作用。
其次,通过负责任国家行为规范达成共识。当前,国际法适用网络空间已在国际社会形成共识,但仅停留在原则性层面,具体的规则制定存在较大的分歧。而不具约束力的“国际软法”,例如“负责任国家行为规范”在国际社会中接受程度较高,可成为今后网络空间立法的过渡。事实上,中俄和美欧倡导的负责任国家行为规范在内容实质上存在着很大分歧,但只要有共识即可形成利益交汇点。例如,限制恶意网络攻击,避免对个人及关键基础设施造成重大损害;限制恶意信息通信技术工具和技术的扩散;制定自我约束的网络行为准则,尤其在网络武器方面保持克制等方面,国际社会可以基于以上共识,找到利益共同点进行有效合作。
结语
网络军控提出至今,仍在摸索中艰难前行。只有未来网络技术发生颠覆性变革,危及全球网络战略稳定性,各国才会重视网络军控并达成共识。当然,在网络空间形成互信,消除网络安全困境,才是避免网络军事化发展的最终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