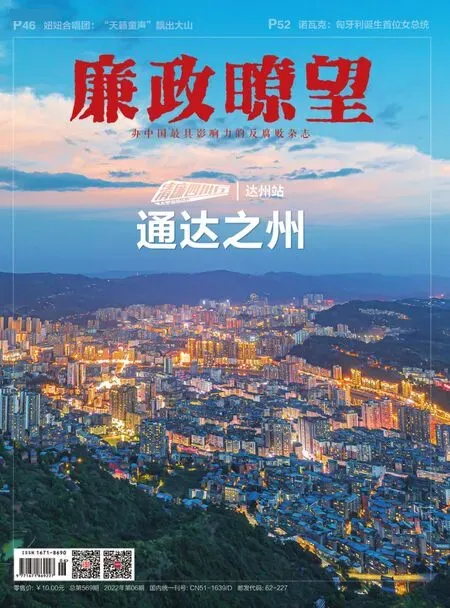苏轼一生为何只给这五个人写墓志铭?
2022-10-21曾勋
│文 曾勋
古人讲究“盖棺定论”,除了留下事迹、作品和口碑,最直接的形式莫过于用墓志铭记录墓主人的生世、品德和功绩等等。
对士人来说,墓志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而,找谁写,怎么写,大有讲究。有点身份地位的人离世后,其后人必定会找与逝者关系亲近、级别相当或者著名的贤良为其写墓志铭。自然,受邀写墓志铭的人为谁写,不为谁写,更有讲究。
所以,墓志铭不仅表征逝者生前的道德、财富、人脉、地位,其象征意义,还远远超出石刻悼文内容本身。它承载着古人的性情喜好、人情世故,亦可从中窥见当时的政治脉络。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 年),距离蜀州青城农民王小波、李顺作乱已经过去了60年,当时有谣言说六十年一甲子暴乱又会卷土重来,部分造反分子在暗中摩拳擦掌。宋仁宗命礼部侍郎张方平入蜀安抚人心。张方平进入四川后,采取了一系列惠民措施安抚民众,迅速稳定了局面。
蜀中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文教昌盛,人才辈出。这次入蜀,张方平还肩负朝廷安排的另一个重要的任务——为朝廷物色人才。他听闻眉山三苏父子文冠蜀中,便去拜访,后来又把三苏父子引荐给欧阳修,成就了“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八大家”的佳话。元祐六年(1091年),85岁的张方平逝世,谥号“文定”。苏轼听闻噩耗,对恩师的离去悲痛万分,为其撰写了墓志铭,并服孝三月。
后来,苏轼在《祭张文定公文》中傲娇地表示,我从来就不愿为人撰写墓志铭,我一生只为五人写过墓志铭,这是因为他们确实有大功大德。实际上,苏轼一生为七个人写过墓志铭,分别是富弼、司马光、赵抃、范镇、张方平,另外两人赵庸敬、滕元发的墓志铭,是他帮张方平代写的。
富弼、司马光自不必说,他们都是当时的名相。嘉祐年间,苏轼作为职场菜鸟在京城当“京漂”时,就写过自荐信给宰相富弼,夸赞富弼“勇冠于天下,而仁及于百世”。这里面肯定有拍马屁的成分,不过,苏轼的政治主张与富弼大体一致。
后来王安石主张变法得势,苏轼站在司马光一边反对变法。直到宋哲宗上位后,王安石被罢相,司马光拜相,因反对新法而被贬的苏轼、苏辙、刘挚、范纯仁等人回到中央被委以重任。所谓“志同道合方为谋”,苏轼为富弼、司马光写墓志铭,不光体现了他们政治理想的一致,也能看出苏轼对知遇之恩的报答。
苏轼为有“铁面御史”之称的赵抃作墓志铭,除了感恩,恐怕还有钦佩。赵抃跟苏洵同辈,嘉祐四年(1059年),52岁的赵抃调任成都府路转运使,当时眉州属成都府路。之前两年,苏轼、苏辙同科进士及第,名震蜀中,京师的贤良均有所耳闻。
赵抃约见三苏父子之后,推荐苏洵为试校书郎。苏轼兄弟对赵抃推荐父亲的举动心存感激,后来在书信诗文中多有提及。赵抃退休回家,琴鹤相伴,过上了清苦闲适的生活。苏轼写诗说,“清献先生无一钱,故应琴鹤是家传”,赞扬赵氏治事清廉。赵家和苏家经常诗文唱和,相互扶持,实则为君子之交的典范。
而选拔苏轼两兄弟的主考老师之一,就是四川华阳人范镇。范镇作为蜀中学者的代表,在翰林院曾多次负责贡举考试。嘉祐二年(1057年),范镇与欧阳修、梅尧臣为知贡举,选拔出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一大批有识之士。范镇支持司马光反对新法,与王安石不合,他指责王安石主张的青苗法为“残民之术”。
在北宋泾渭分明的政治结构中,苏轼毫无疑问是另类的存在。他不赞同王安石的所有新法,但在私下,他们仍在金陵喝酒唱和,好不快乐。即便王安石知道这名后生与自己的政治理想相悖,仍旧在“乌台诗案”过后,劝诫皇上“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力保苏轼。他们都以身示范,浇筑了士人宽厚仁义的可贵品格。
苏轼选择性地为敬重的师友做墓志铭,纵有政治站位和感情亲疏的考量,但正如他所言,这些人无一不是敢作敢当的耿介之士。文人惜墨如金,遇知己则直抒胸臆,文思如泉涌,这也算一种境界和情怀吧。
到后来,苏轼反对司马光将新法尽除的极端做法,结果搞得两头碰壁,此后大半辈子不是打铺盖卷走人就是在被贬的路上。不过,也正是苏轼的“傲娇”,成就了他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