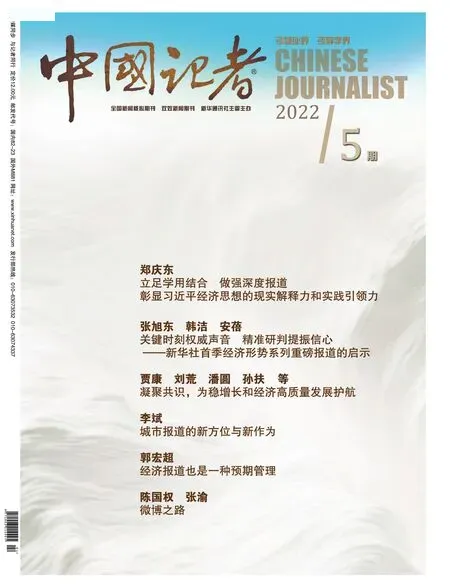疫情应急状况下的媒体工作机制
——以2022年上海疫情为例
2022-10-20李舒
李舒
樊攀
自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国内多地先后“封城”。封控管制状态下,一方面大量采编人员被隔离,很难前往新闻现场,媒体报道易出现信息瓶颈;另一方面,公众对外界信息极度渴求,自媒体和社交媒体狂轰滥炸、真假难辨。如何组织疫情应急状况下的新闻报道,做好舆论引导,回应百姓关切,成为新闻媒体的职责担当。
传统媒体通常都有自己的重大突发事件报道机制,但新媒体时代对媒体应急工作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改革和完善媒体应急工作机制,加速构建传统媒体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智能系统”,有利于扩大媒体影响力,占领舆论阵地,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雷达系统:建立智能化、自动化、大数据的信息搜集预警体系
大数据时代,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社会事件、经济事件,很多事情发生前均有预警信号,例如早在3月27日上海宣布“静态管理”之前,上海“每日新增感染者数”“长三角部分工业园区耗电数”“上海散货货运价格指数”“微博热搜话题”等先后出现异常,媒体能否建立新闻线索的大数据库,敏感地捕捉到这些信息是媒体履行“耳目”职责的关键所在。
智能社会,每个人就是一个IP,每个IP后面不仅仅是人,还有智能设备,媒体的信息来源不能还停留在“政府部门”“官方发布”和“通讯员”水平。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管理部门都在推进大数据平台建设,推动构建智能社会治理体系,媒体需要嵌入智能体系,将传统的通讯员网络转化为线上的数据情报搜集网络,希望未来能够出现“传媒指数”,真正成为数字时代无孔不入的“通讯员”。
二、指挥系统:建立基于数字算法匹配的一体化融媒体中央厨房
近年来,从中央媒体到地方媒体,纷纷建立采编联动平台,统筹采访、编辑和技术力量,构建融媒体方式的“中央厨房”,以实现“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传播”,集中指挥、高效协调、采编调度、信息沟通是“中央厨房”的基本功能。然而,熟知军事战争的人都知道,高效的指挥系统绝对不会是单向的,需要根据战况随时调整兵力布局,甚至开辟新战场,转移战略重点。当前,“中央厨房”议程设置、主题策划多是自上而下的,承担了大量“主题报道”“领导点题”的任务,对于自下而上的选题也多是基于采编人员的主观认识和工作经验拍脑袋想的,而非来自舆论场的客观算法推荐。因此内容生产难免与用户需求发生错位,造成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现象。
这里并不是说要“中央厨房”一味去迎合用户或网络舆论场,而是要通过向下对舆论场的数据抓取和算法推荐,分析整合后形成对上的传播规划和建议,将领导要求的战略重点通过计算分析出需要投入的内容生产计划和兵力布局方案,最后根据战况评估效果,这就是算法匹配。
三、操作系统:去中心化的分布式应急采编模式和远程支持协作
上海疫情“静态管理”,不少媒体的采编人员被封控在家,媒体通行证有限,记者无法到达社会新闻现场,导致高质量的新闻报道缺乏、独家新闻缺乏、调查性报道缺乏。
事实上,能否短时间内构建一支去中心化的分布式应急采编队伍,对于大范围、涉及人数众多的公共突发事件报道至关重要。以上海疫情为例,3月27日晚上海宣布浦东、浦西轮流封控方案时,留给市民至少4个小时的“抢菜时间”,陆家嘴金融市场的交易员们火速赶往办公室,以确保第二天股市能正常开市。很多媒体从业人员也都敏感地奔赴工作岗位,从而保障了媒体正常运行。其实这也是媒体关键的“布局时间”。一个2500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在工作日突然“停摆”史无前例(武汉疫情封控正值春节假期),如此重大新闻需要提前布局,重点医院、重点市场、物流集散地、方舱医院、流动人口聚居区、老年人社区、殡仪馆……这些特殊点位都需要视条件许可,或安排记者值守,或联系志愿通讯员。
这时媒体总编脑子里应该有一张“排兵布阵图”,或者更先进的是,媒体数据库抓取的重点点位,有没有记者、有没有实时数据?而针对点上值守的记者,后方有没有按业务线分工编辑汇总信息?例如医药板块、物流板块、重点社区板块、重要市场板块等。上海小区封控后,物资保障基本靠“团长”,那媒体的“团长”有没有建好,“团长”下面有没有兵力部署,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布点到位,那么每天可以汇总点上的信息,形成集束式的持续报道、专题报道、追踪报道、独家报道,不至于在封控期间端不出像样的菜。
此外,对于中央媒体来说,遇到重大突发事件驰援驻地机构是非常重要的,但更应在外围形成补充报道力量。如上海疫情报道,北京、武汉、云南的记者能不能形成远程协作,甚至按专业板块构建的“团长”可能不在上海,而是有经验的外地记者编辑,这样驻地机构的所有采编力量可以全部押到一线点上去,后方“团长”汇总消息制作新闻,最大程度挖掘人力资源,真正形成“一方有事、八方写稿”的集团军优势。
四、反馈系统:构建数字时代的“读者来信”互动、通联机制
传统媒体通常都设置了新闻热线、读者来信来访、通联部等机构,以搜集新闻线索、汇集社情民意。然而,数字时代的读者互动、反馈系统有了更深刻的内涵变化和更多元化的方式。
武汉疫情期间,中央媒体广泛收集社情民意,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人民日报》利用人民网等新媒体整合网络信息资源,迅速组织志愿者对患者信息进行筛选、核实、分类、上报,同时保持对求助患者的跟踪、陪伴和反馈,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一是党报志愿者的身份,作为党的形象的一种延伸,得到求助者高度认同。志愿工作满足了求助患者的救治、基本生活和心理需求,稳住了疫情社会基本面;二是中央指挥部门获得了地方政府医疗救治、疫情防控、社区服务等一线的真实情况和问题,志愿团搜集整理和跟踪反馈的信息能够与基层上报信息相互印证,为指挥部门掌握一线真实情况提供了重要参考;三是官方媒体得到大量社会支持,特别是后期医药和生活物资捐赠和救援,整合了社会各界力量,放大了“正能量”;四是《人民日报》新媒体借此实现了线上线下互动,这就是数字时代的媒体应急报道“新模式”。
当然,无论哪个时代,媒体应急报道机制都应包含后勤支持保障系统,解决一线记者技术、通讯、物资支持等问题,在此不再赘述。需要重视的是,如果疫情封控成为常态化,媒体的物资储备也应该实现多点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