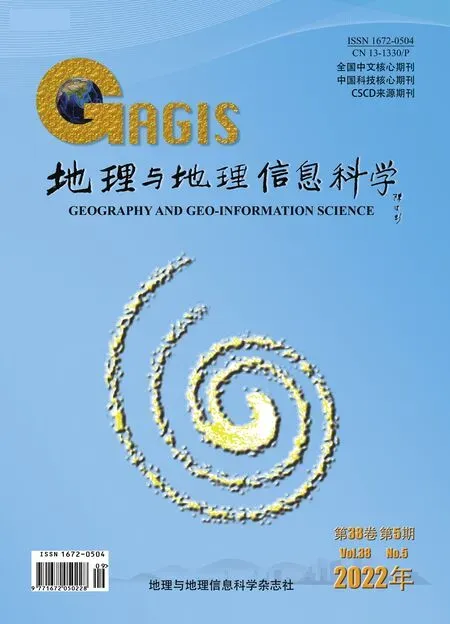长江经济带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空间错位及其机理
2022-10-12李如友,石张宇
李 如 友,石 张 宇
(1.盐城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盐城 224051;2.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浙江 杭州 311599)
0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我国劳动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作为传统农耕文明和历史文化记忆的物质载体,传统村落与非遗具有不可割裂的联系。传统村落承载着乡土社会中人们共同的记忆和乡愁,是非遗产生、发展和存续的原始土壤[1],非遗体现了传统村落居民的生存方式和文化认同,是传统村落文化的灵魂[2],概括而言,传统村落是非遗的空间载体,非遗是传统村落的文化内核。我国传统村落与非遗保护政策也体现了二者的依存关系:2012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四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明确将“非遗活态传承”作为传统村落调查与保护的审定依据,2019年文化和旅游部出台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要求让传统村落成为非遗传习和展示的空间,《“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则提出了“加强中国传统村落非遗保护”的目标任务。但当前我国传统村落与非遗分布却存在地区差异和空间错位现象,如湖南长沙市和怀化市有相同数量的国家级非遗项目,而后者传统村落的数量是前者的56.33倍,这为传统村落和非遗的保护与利用带来巨大挑战。在此背景下,对我国传统村落与非遗空间分布关系的现实特征及形成机理开展研究尤为必要。
国内外学者对传统村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传统村落的演化规律[3,4]、空间形态[5,6]、旅游开发[7-9]及活化路径[10,11]等方面,尤其注重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12-14]及其影响因素[15-17]研究。近年来,在我国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围绕该议题,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传统村落保护度[18]、乡村性[19]、活态性[20]、景观脆弱度[21]及可持续发展[22]进行了评价和分析。针对非遗的研究主要围绕其概念内涵[23,24]、保护传承[25,26]、时空特征[27,28]及旅游开发[29-32]等议题开展。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非遗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地理空间,而是具有游移性特征[24],其分布受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和经济状况等因素影响[28],在南方的分布数量和密度均大于北方,且主要集中于长江流域[33]。综观国内外传统村落和非遗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单方面分析传统村落和非遗问题,忽略了传统村落与非遗是紧密关联、相互依存的两类要素,鲜有学者对二者进行整体协同分析,对二者空间分布关系的研究更显不足。基于此,本文采用核密度、重心模型、空间错位指数等方法,定量分析长江经济带传统村落和非遗分布的空间特征,揭示二者的空间错位关系及机理,对该区域传统村落和非遗文化的整体性保护与合理化利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研究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长江经济带是中央重点实施的“三大战略”之一,空间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覆盖云南、四川、贵州、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上海9省2市,区域总面积约为205万km2,占全国的21.4%,人口约6.06亿人,占全国的42.93%(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34]。该区域也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53.02万亿元,占全国总量的46.36%(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测算。。长江经济带位于我国第二、三阶梯,地貌复杂多样,气候温暖湿润,为传统村落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地理条件,并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和独具风格的地域特色。目前,长江经济带的传统村落和国家级非遗分别占全国总数的60.95%和40.80%,是我国传统村落和国家级非遗项目最富集的区域。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发展导向下,传承和保护好体现地域文化精髓的非遗文化及其空间载体,保持地域特色文化的原真性、活态性和完整性,是促进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
本文采用的长江经济带传统村落数据来源于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委公布的第1~5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共计4 156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我国对非遗施行“国家+省+市+县”4级保护,本文主要针对国家级非遗项目展开分析,截至2021年8月,国务院先后公布了5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按照申报地区和单位进行汇总整理后,得到长江经济带国家级非遗项目1 473项(含扩展项目)。本文以公布的全部批次中国传统村落和国家级非遗为研究对象,依据传统村落的名称、地址以及非遗的保护单位,采用Google Earth定位具体的地理坐标,进而基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1∶400万数据,分别构建长江经济带传统村落和非遗(点类,Point)矢量数据库。
1.2 研究方法
(1)核密度。核密度分析(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KDE)是测量观测对象在其周围邻域中密度的非参数估计空间分析方法,可直观反映地理要素的空间集聚状态。核密度值越高,说明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越集聚,随着中心辐射距离的增大,核密度值逐渐变小,充分体现了地理现象空间扩散的衰减规律[35]。计算公式详见参考文献[36]。
(2)重心模型。重心在地理学中表示某区域某地理要素在空间上的平衡点,重心坐标是描述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的重要指标,可清晰反映区域地理现象的空间差异及其动态过程。若两类地理要素分布重心重叠,说明二者分布具有一致性,反之说明二者存在空间错位,且重心距离越大,二者空间错位程度越高。计算公式详见参考文献[37]。
(3)空间错位指数(Spatial Mismatch Index,SMI)。空间错位理论主要用于揭示相互关联的要素在空间分布上的匹配现象,在住房供求、粮食安全及旅游发展等领域[38-40]应用广泛。由于我国自然地理条件及社会经济环境存在地区差异,传统村落与非遗呈现空间分异和非协同耦合性,即空间错位[41],引入空间错位理论定量分析传统村落与非遗分布的空间失配现象,是对二者现实关系的有益探索。空间错位指数是基于空间错位理论提出的[42],可直观反映两类地理要素分布的空间相似性,相似程度越高,说明二者分布的空间错位程度越低,反之则说明空间错位程度越高。计算公式详见参考文献[43]。
2 空间特征与错位关系
2.1 空间特征
2.1.1 传统村落的空间特征
(1)从传统村落的分布地区和数量(表1)看,长江经济带传统村落在各省(市)的空间分布呈非均衡态势。具体而言,贵州、云南、湖南传统村落的数量位居前三位,分别占长江经济带总数的17.42%、17.04%和15.83%,位居第四位的浙江传统村落超过600个,占长江经济带总数的15.30%;其余传统村落数量超过200个的省份包括安徽、江西、四川、湖北,共计1 282个,占长江经济带总数的30.85%;上海、江苏、重庆的传统村落合计148个,不及长江经济带其他任一省份的数量。从东、中、西三大区域(2)东部包括上海、江苏和浙江;中部包括安徽、江西、湖北和湖南;西部包括重庆、四川、贵州和云南。看,西部地区传统村落数量(1 875个,占45.12%)明显高于中部地区(1 607个,占38.67%)和东部地区(674个,占16.22%);同时,在三大区域内部,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也不均衡,东部地区的浙江、中部地区的湖南以及西部地区的贵州、云南传统村落的数量明显高于本区域内其他省(市)。

表1 各省(市)传统村落数量Table 1 Number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each province(municipality)
(2)借助ArcGIS中的核密度工具对长江经济带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密度进行可视化(图1)。长江经济带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集聚特征明显,呈现2个高密度核心区和4个次高密度核心区。其中,皖南—浙西南高密度核心区主要包括安徽黄山以及浙江丽水、衢州、金华4市,辐射皖南和浙中、浙西地区;湘西—黔东南高密度核心区主要包括湖南怀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辐射湘西、黔东及渝东南地区;以云南大理、保山为核心的次高密度核心区辐射滇西北地区,以云南红河、玉溪为核心的次高密度核心区辐射昆明及其南部各市,以湖南永州、郴州为核心的次高密度核心区包括永州、郴州、衡阳等地区,以江西吉安、抚州为核心的次高密度核心区包括吉安、抚州、赣州、宜春等地区。就东、中、西三大区域而言,传统村落呈东部集聚,中、西部散中有聚的特征,从集聚程度看,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三大区域传统村落均表现出南密北疏的特点。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与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积淀紧密相关[13],相比地势平坦、交通便利的平原地区,地形地貌复杂的山地丘陵地区地理环境相对独立,受外界干扰较少,使村落风貌和风俗习惯得以沿袭和保存。

图1 传统村落核密度分布Fig.1 Nuclear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2.1.2 非遗的空间特征
(1)从非遗的分布地区和数量(表2)看,长江经济带非遗大体呈东密西疏的空间格局,各省(市)间不均衡性明显。具体而言,浙江、贵州、江苏非遗数量位居前三位,分别占总数的16.56%、10.73%和10.45%;四川、湖北、云南、湖南、安徽非遗数量均超过100项;江西、上海、重庆非遗数量较少,合计230项,占总数的15.61%。从东、中、西三大区域看,西部地区非遗数量最多(512项),占总数的34.76%;中部地区非遗数量位居第二(487项),占总数的33.06%;东部地区非遗数量最少(474项),占总数的32.18%。由于西部地区4省(市)疆域辽阔,面积分别是东部3省(市)和中部4省的5.24倍和1.58倍,从非遗的空间分布密度看,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

表2 各省(市)非遗数量Table 2 Number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each province(municipality)
(2)对长江经济带非遗的空间分布进行核密度分析(图2),结果显示:1)长江经济带非遗空间分布呈现1个高密度核心区、1个次高密度核心区和3个小核心区。其中,高密度核心区以长三角为核心,辐射上海、浙江及苏南、苏中地区;次高密度核心区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核心,辐射整个黔东南地区;3个小核心区分别位于湘西地区、四川成都以及湖北武汉。长江经济带非遗分布整体呈小集聚、大分散的特征,主要集聚在人口密度大、文化事业发展较好的经济发达地区(如上海、浙江、江苏)以及少数民族聚居区(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同时,成都、武汉、杭州等省会城市也是非遗文化的集聚区;非遗集聚分布区域与传统村落集聚分布区域空间耦合程度不高,表现出较强的相互独立性。2)就东、中、西三大区域而言,非遗呈现东部集聚,中、西部分散的空间格局,地域性特征明显;同时,东部地区非遗的空间分布类似于传统村落,表现出南密北疏的特点,而中西部地区非遗空间分布的南北差异不明显。

图2 非遗核密度分布Fig.2 Nuclear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2.2 错位关系
传统村落与非遗分布的空间错位具有多种表现特征,宏观上表现为二者空间重叠性及分布重心的空间偏离[43],中观上表现为二者在特定地理空间上的匹配状态[44],微观上表现为二者所处地理区位的空间关系。本文主要从宏观和中观角度,对长江经济带传统村落与非遗分布的重心错位以及二者区域分布的规模错位进行测度和分析。
2.2.1 重心错位 为定量描述长江经济带传统村落与非遗分布的空间错位特征,运用重心模型计算长江经济带及各省(市)传统村落重心和非遗重心的地理坐标及偏离距离(表3),并绘制其相对位置(图3)。由表3和图3可知,长江经济带传统村落与非遗分布的重心位置存在明显的空间偏离。非遗重心(112.729°E,29.201°N)位于长江经济带几何中心(108.477°E,28.833°N)的东面(湖南岳阳市境内),传统村落的重心(110.670°E,27.799°N)则位于几何中心的东南侧(湖南怀化市境内),二者与几何中心的连线呈以传统村落重心为顶点的近似等边三角形。从错位距离看,传统村落重心与非遗重心偏离距离达276.81 km,偏离指数为0.174。所有省(市)的传统村落重心和非遗重心均明显偏离各自的几何中心,且传统村落重心偏离几何中心的程度均大于非遗重心。同时,各省(市)传统村落和非遗分布均存在明显的空间错位现象,且错位程度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从错位距离看,安徽最突出,达189.31 km,重庆和浙江分别为103.27 km、96.19 km,位列第二、三位;错位距离超过50 km的地区还包括湖南(85.25 km)、江苏(80.03 km)、贵州(72.09 km)、湖北(60.77 km)和江西(51.63 km);上海的错位距离最小,这与其面积最小有关。从偏离指数看,安徽(0.456)、重庆(0.324)和浙江(0.271)同样分列前三位,偏离指数超过0.1的还有江苏(0.220)、湖南(0.167)、贵州(0.155)、湖北(0.127)和江西(0.114),云南(0.042)、四川(0.047)和上海(0.068)的偏离指数较低,分列后三位。

图3 传统村落与非遗分布的重心错位Fig.3 Dislocation of distribution center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表3 传统村落与非遗分布的重心错位Table 3 Dislocation of distribution center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2.2.2 区域分布规模错位 重心模型可在宏观上揭示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传统村落与非遗分布的空间错位现象,但无法阐释二者分布规模上的错位程度及模式。为此,本文引入空间错位模型揭示各省(市)传统村落与非遗分布的错位态势和程度,结果如表4所示。就错位方向而言,江苏、湖北、上海等地区的SMI值为正,说明这些地区非遗的相对分布规模大于传统村落,而云南、贵州、湖南等地区的SMI值为负,说明这些地区传统村落的相对分布规模更具优势。就错位程度(G)而言,江苏的错位程度最高,贡献率达19.33%,上海、湖北、湖南、贵州、云南的贡献率超过10%,合计贡献率达61.93%,浙江的错位程度最低,贡献率仅为2.52%。可见,长江经济带传统村落与非遗分布的宏观错位现象主要是由少数省(市)二者空间分布不均衡所致。

表4 各省(市)空间错位指数及类型划分Table 4 Spatial dislocation index and type of each province(municipality)
借鉴文献[43],根据SMI值的大小,将长江经济带9省2市划分为4类区域:正向高错位区(SMI≥5),包括上海、江苏、湖北;正向低错位区(0≤SMI<5),包括浙江、四川、重庆;负向低错位区(-5≤SMI<0),包括安徽、江西;负向高错位区(SMI<-5),包括湖南、贵州、云南。可以发现,非遗相对分布规模更具优势的正向错位区由2个直辖市和4个经济较发达的省份组成,传统村落相对分布规模更具优势的负向错位省份大多位于长江以南,这些省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且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反映出非遗向人类活动频繁且交通便利的经济发达地区集聚[17]、传统村落趋向于低城镇化水平地区[45]以及空间分布与自然地理环境具有较强耦合性[46]的差异性特征。就三大区域而言,东部地区以正向高错位区为主,中部地区兼有正、负向高错位区,西部地区则负向高错位区更为突出。
3 机理分析
长江经济带传统村落与非遗分布的空间错位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经济、社会、文化、政策四方面因素,分析长江经济带传统村落与非遗分布空间错位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图4)。

图4 传统村落与非遗分布空间错位的影响机理Fig.4 Mechanism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disloc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1)经济因素。经济发展通过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和需求,影响传统村落与非遗的生存空间和生命力,同时为非遗的专门性保护提供资金支撑,是空间错位形成的基础动力。传统村落是传统农耕文明的产物,在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经济的社会保持持续、旺盛的生命力。在传统农耕社会,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技艺和场景通过民间的口传和礼俗反映在音乐、舞蹈、戏剧、祭祀、仪式等非遗活动中,传统村落与非遗和谐共生,在发展中相互促进。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传统村落居民的劳作方式和生存模式均发生了巨大转变:传统技艺遭受现代技术的威胁,电影电视取代了民族歌舞和曲艺表演,网络游戏使得民间游艺走出孩子们的童年记忆。在现代化浪潮的影响下,传统村落因难以适应现代化和市场化趋势而走向衰落,非遗活动与传统村落居民日常生产、生活的联系不再紧密,各类从属于传统村落的非遗文化也随之逐渐走向衰落,从而造成传统村落的风貌得以延续,但地域特色文化却难以维系。同时,人们的文化生活与经济水平密不可分,经济发展不仅可以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们对非遗的关注、认识和保护,还为非遗保护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撑[47]。因此,经济发达地区尽管传统村落损毁严重,但投入大量资金,通过非遗产业化、建设专项公共文化设施等途径,在城镇化地区对非遗文化进行传播和开发利用,从而推动传统村落与非遗分布的空间偏离。
(2)社会因素。城镇化进程促进了传统村落人口流失与社会空间解体,加速了非遗的自然消亡和脱域化传承,是空间错位形成的核心动力。城镇与村落是人类聚居的两大类型,二者相互对立,城镇化进程会加速村落的衰退[13]。传统村落的田园民居、庙宇祠堂、街巷市场等自然和人工环境与节庆仪式、方言俚语、民间信仰等地方文化相互交叠,构成立体、完整的文化生态空间,成为非遗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加之人们安土重迁的思想观念,非遗文化得以长久传承。城镇化作为社会空间的再组织过程,虽然改善了乡村地区经济、环境和民生,但撤村并镇、拆房上楼不仅造成凸显地方特色的村落建筑被缺乏地域特征的建筑形态所取代,乡土情结日渐淡化,导致非遗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从根本上瓦解,影响非遗在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而且城镇化进程还带来人口流动,导致非遗传承人及受众外流,造成传统村落的空心化和自然衰退,进一步加速了传统村落与非遗亲密关系的解体。由于非遗依附于人而存在,具有传统性、流动性、生态性等特点,对非遗传承人及其受众的保护是非遗保持活力的关键,而城镇地区吸纳了非遗文化的承载主体,同时为传统技艺和民间演艺等类型非遗提供了市场和发展空间,使非遗文化随着传承人向城镇地区转移,在传统村落之外获得脱域化传承,从而促成了传统村落与非遗分布的空间错位。
(3)文化因素。现代文化的冲击激化了传统村落居民现代化生活需求与地方特色文化原真性保护的矛盾,导致非遗文化脱离原生地向外扩散,是空间错位形成的直接动力。研究表明,传统村落和非遗的空间分布与地形地貌息息相关[28,46]。事实上,文化冲击在地形地貌对传统村落与非遗空间分布的影响中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地貌复杂的地区易形成相对闭塞和孤立的地理空间,使传统村落形成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各具特色的民风民俗,在人地关系演化过程中,促进非遗的诞生、传承演替与发展,并根植于传统村落得以保存下来。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村落与外部社会的沟通和交流逐渐加强,人们的生活传统和思想观念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文化的侵扰。在现代都市文化冲击下,传统村落居民产生了追求现代化生活的意愿,但传统村落由于种种不便的生活条件和有限的改造空间难以承载其发展需要。为改善生活条件,富裕起来的居民陆续对传统建筑进行了拆除重建或翻新,使得村落景观发生改变,地方特色丧失。因此,传统美术、民俗、游艺等从属于传统村落的非遗因失去生存空间而走向消亡,或在传统村落之外得到被动保护;传统技艺、传统医药等非遗则脱离传统村落这一原生地理空间,作为部分群体的谋生手段在城镇地区得到沿袭和传承。
(4)政策因素。地方政府主导的专门性和脱域化保护路径割裂了传统村落与非遗间的原生关联,是空间错位形成的外在动力。传统村落和非遗的保护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各省地方政府在国家相关保护政策的指导下,保存传统村落的格局及原有风貌,同时保护非遗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物和场所,以保持传统村落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延续性。但在非遗的保护上,各省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了针对性较强的非遗保护政策。例如,云南和贵州在非遗资源集中区域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江西采取与经贸、旅游相结合的方式,对具有地方特色和市场潜力的非遗,在保护其原真性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和利用;江苏和湖北则要求地方政府根据需要建设非遗专项公共文化设施,用于非遗代表性项目的收藏、展示和传承。遵循这些政策,各地区采取生态圈整体保护、生产性保护、旅游开发保护以及博物馆保护等多种模式开展非遗项目的传承、传播和利用。其中,生产性保护和旅游开发保护模式均为选择性非遗保护,主要保护那些能够借助生产、销售及旅游开发等手段转化为文化产品的非遗项目。博物馆保护则是通过修建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等专门场馆,收藏、展示和传播非遗文化。这种“进城”“入馆”式脱域保护使非遗完全脱离了孕育和生存的空间载体,打破了传统村落与非遗之间的原生关联,由此促进了二者空间分布的错位特征。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综合运用核密度、重心模型、空间错位指数等方法,探讨了长江经济带传统村落和非遗分布的空间特征,并揭示了二者的错位关系及机理。研究发现:1)传统村落和非遗均呈集聚分布态势。具体而言,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呈组团状,表现为2个高密度核心区和4个次高密度核心区,贵州、云南、湖南、浙江4省在数量上具有明显优势;非遗分布呈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特征,共形成1个高密度核心区、1个次高密度核心区和3个小核心区,浙江、贵州、江苏数量分列前三位;传统村落与非遗集聚分布区域的空间耦合程度较低,表现出较强的相互独立性。2)传统村落和非遗分布呈显著的空间错位特征。传统村落重心明显偏离非遗重心,偏离距离达276.81 km,各省(市)空间错位程度有所差异,传统村落优势分布地区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而长江以北经济相对发达省份的非遗分布优势明显。3)传统村落和非遗分布空间错位格局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是影响传统村落和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基础性因素,是空间错位形成的基础动力;城镇化进程通过人的流动直接促进非遗与传统村落的分离,是空间错位形成的核心动力;现代文化冲击改变了人们对传统村落和非遗的保护意愿与传承方式,是空间错位形成的直接动力;部分地方政府主导的脱域化非遗保护机制割裂了传统村落与非遗之间的原生关联,是空间错位形成的外在动力。
长江经济带传统村落与非遗分布的空间错位只是表面现象,内在反映了传统村落与非遗的保护传承,二者相互依存、互为表里的紧密联系被割裂,不仅影响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非遗的活态传承,还为实现二者协同保护与发展提出了挑战。针对该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制定灵活的传统村落和非遗保护政策。长江经济带传统村落与非遗分布的空间错位既成事实,且存在地区差异,各地区应根据客观实际制定针对性政策,探索多样化保护与传承模式。例如,传统村落分布优势地区应积极挖掘、保护和传习非遗文化,保持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非遗分布优势地区应协调好人们生活条件改善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以及城乡融合发展与非遗文化原真传承的关系,为非遗文化的活态传承提供平台和空间。2)加强传统村落和非遗的资源整合与整体保护。保护传统村落,不仅要保护传统村落中民居、祠堂等物质文化遗产,还要保护体现传统村落独特魅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遗,不仅要保护其本体,还应保护其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尤其在传统村落改造过程中,地方政府应对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有效整合,在保持村落原有风貌的同时,加强对民间习俗、乡规民约等地方特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并且与现代文化和生活环境相适应,增强传统村落与非遗的发展性和持续性。3)完善传统村落和非遗的内源式保护与传承机制。外来文化冲击和地方政府外生式非遗保护方式导致传统村落与非遗分布空间错位,为此,一方面,地方政府应通过制度保障、资金扶助、宣传教育等多种方式,保护村落传统建筑形制和格局,保持村落景观的乡土性,为非遗文化的活态传承提供空间;另一方面,积极发挥基层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的作用,通过开展各类文化活动增强民众对地方特色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从而激发他们保护传统村落物质文化遗产和非遗的积极性和自主性,促进非遗在传统村落原生传承。
本文丰富了传统村落与非遗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视角,研究结论对于促进区域传统村落和非遗的协同保护与合理利用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价值。但受多方面限制,本文仍存在如下不足:仅从宏观和中观角度对传统村落与非遗分布的重心错位以及区域分布的规模错位进行了分析,未涉及微观上二者地理位置的错位特征,有待后续作更深入的研究;传统村落与非遗分布空间错位的驱动因素复杂多样,本文从经济、社会、文化、政策等方面选取了代表性因素进行探讨,难以全面揭示二者分布空间错位的形成过程及机理,未来需关注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