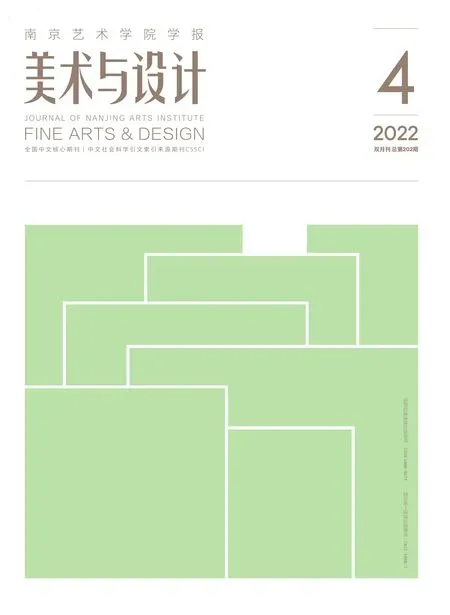道之“玄妙”与器物审美维度
——兼论《道德经》中的设计美学意蕴①
2022-10-11郑丽虹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江苏苏州215127
郑丽虹(苏州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7)
许大海(山东艺术学院 艺术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300)
器物之美是不断通过外显和内隐的形式内容带给人们以审美体悟。所谓器物外显的是指材料、肌理、结构、纹饰、颜色、工艺等可见、直观的形式,通过视觉、接触直接刺激人的感觉系统。这种反映是最直接的,但也是短暂、易逝的。内隐的则是隐藏于外显的内容背后深层次的传统文化思想及经过历史积淀所形成的审美观念和品味,它可以带给人们持久的审美回味。传统青瓷之美不仅在于它精雅细致的形态,更在于通过釉色所追求的“类玉”的精神意蕴——润泽柔和、惠及万物,即儒家所倡导的“仁德”之美。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所指出的:“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他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的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他们所带来的价值。”因此,设计视觉的审美体悟是通过多维度展现:一方面通过人的感知系统体会到的,这是表面的;另一方面隐藏于表象之后的传统文化观念,构成器物之美的核心价值。
一、道——构成器物美的本质属性
1.器:反映器物美感的外在集合
中国传统器物设计,实际上是在两个维度上展开的。一是观念层面,即设计思维、造物思想、器物审美。一是技术层面,即与造物相关的材质、肌理、色彩、工艺等。我们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上述观念——行而上的范畴系统和形而下的器物形态。实际上工艺美术领域中所谓的“器”表示器物、器具统称,指有形的实体,正如《周易·系辞上》所说“形乃谓之器”或“物周为器”。即通过材料、工艺加工技术,生产、制作的实用与美观相统一的器物。从器物功能属性看,可分为观赏器、实用器、实用与观赏兼备等等。无论哪种分类,任何器物都包含了自身的美感属性,即包含了对材料、工艺、形式、功能等内容的追求,它具有如下特征:
材质美——构成器物审美感的前提。“无以良材,难成美器”,材料往往以最直观的形式作用于人的知觉系统。中国传统器物尤其注重材料的选择,衡量优良器物的重要标准就是“材美”。由材料带来的审美愉悦,在中国传统器物不胜枚举,像和田籽玉、寿山田黄、昌化鸡血石等,即是珍贵材料,本身又是优美的造型,有的根本无需经过加工,完全是得益于大自然的造化和鬼斧神工(图1)。玉石、竹木、金属、丝麻、瓷土、漆、骨料等材质,是工匠们在长期审美实践中的经验和智慧结晶,往往通过以下方式反映出来:其一,在使用材料过程中,对精良材料的确认往往是经过比较得来的。如早期对玉石直观的认识就是一种美石“石之美者为玉”,显然这是通过把普通的石头和“玉石”这两种材质不同的石头进行比较得到的审美经验;其二,对新材料持续不断地追求。新的器物或工艺美术种类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新材料和器物的出现,同时也伴随着一种新的审美标准,如青铜合金的探索成功,瓷土、釉料的出现和不断改进,成就了跨越一千五百年的青铜工艺时代和至今广泛影响世界的瓷器。尽管有工艺发展规律的历史必然,但也离不开人们为追求新异、高品质的器物及对新材料的不断探索;其三,材料选择与环境的统一。中国传统器物制作特别强调材料与四时、环境的完备统一。即我们所说的“天时、地气、材美”的统一。任何天然材料都有其自然属性,或曲或直,或干或润,或刚或柔,或疏或密,与环境、地质、燥湿、冷暖等自然要素紧密相连,这些要素都是工匠们参考的指标,也是传统器物生产的一个重要标准。

图1 (清)天然木雕蟹盒 故宫博物院
工艺美——构成器物审美的基础,中国传统器物的美感体现在对制作工艺至臻至善的追求。从青铜的制范铸造、矢蜡法,精美的珐琅工艺,到如今无法企及的秘色瓷及各类精工细物,无不透漏着“工巧”的精髓。工艺美的特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工艺制作的专业化。中国器物工艺水平很早就已经具备专业化生产水平,分工细致,生产精密完善,早在二里头夏代文化遗址已经出现专业化青铜制作作坊,标志着工艺制作水平的提高,而官营手工业的出现对工艺生产专业化的要求更高,使得器物品质更加获得保障;其次,生产工艺标准化的建立。标准化生产是器物发展历史上的重要标志,它使生产、流通更加容易,也使器物美感具有秩序美。正如笔者在《汉代建筑用砖的规格化设计——兼论汉代器物设计中的标准化问题》所指出:“器物设计中的规格化、标准化问题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制作工艺的程式化;二是材料尺寸的规格化。”标准化的推行使器物生产更加容易推广;其三,精雕细镂。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曾评价中国传统器物的“错彩镂金”,既是这种标准。其四,简雅质朴。传统器物不仅有精雕细镂,还有简朴质雅的工艺规范,如汉代简练、粗放的“汉八刀”制玉工艺,雕琢出的线条潇洒飘逸,造型并不复杂,(图2)同样给人以赏心悦目,如“出水芙蓉”的美感享受。

图2 (西汉)圆雕玉熊, 陕西咸阳博物馆
形式美——是构成器物外在美的主要内容:它通过点、线、形态、色、光、质(肌理)等要素,按照节奏、比例、对称、平衡、整齐等形式法则,构成的器物形态。中国传统器物设计很早就已熟练运用上述形式法则,如彩陶图案中运用对比、分割、双关等构图方法进行图案绘制,产生优美、畅达的视觉效果。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传统器物的造型特别善于运用曲线对圆进行布局、营造,如汉代四神纹青龙、白虎瓦当(如图3、4)中龙、虎的造型沿着“S”形曲线进行的,这条“S”形曲线,即太极图中阴阳相交形成的线,是一条非常优美的切割线,我们也称之为中国的黄金分割线,即对圆的最佳分割线,类似的例子很多。

图3 (汉)白虎瓦当

图4 (汉)青龙瓦当
功能美——从器物的发展历史看,器具制作的初衷,是为了提高效率、为人类带来各种便利,以便更好的生存、生活。因此,衡量一件器物的品质,首先看是否能够最大的发挥器物功用。传统设计尤其注重发挥器物功能,如传统“水排”“耧犁”“犁壁”“虹管灯”等器具不胜枚举,因其机巧构造(图5),能够充分发挥器具的最大功能,解决不同用途,它们都是品质优良的器具,同时因其功能性带给人们别样的美感享受。这种美感即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体验,正如康德所指出:美不仅是外在的形式,更体现于内在“品质”。而一件优良的器物,它的内在“品质”就是它的功能性,即是否能够给人们带来最大的使用便利,解决更多的难题,是器物美感的外延。

图5 传统农具 水田梨,海南,中国农业博物馆
2.道:构成器物之美的内在规定性
对于个人来说,一件器物的美与丑是由主观认识和客观规律两个层面构成的。主观认识是建立在个体经验基础上的。很明显有人认为洛可可风格的曲线是阴柔之美的象征,而为之着迷;而有的人则认为它矫揉造作,缺乏阳刚之美。由于社会生活经历、所处阶层、职业、教育、性别、学识等的不同,即使同一件器物对不同的人来说会随时间、地点、环境等因素的变化而产生不同感受。因此,由个体经验产生对器物美的评价往往是易变、短暂的,是主观的而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器物美的规律则反映器物形态本质、普遍的标准,或者是器物造型的本质属性和法则,它不因个体差异改变,也不会随时间、地点、环境而改变。当我们把一条线段进行分割,最恰当的点就是黄金分割点,以这种比例分割线段,进行构图所形成图形的大小、宽窄、高低是最协调的,这就是构图的规律和法则,它是先天存在的,不因个体的意志而变化。中国传统器物审美体味和智慧就是建立在传统文化思想及经过历史积淀所形成的规律性认识,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特征。
实际上在道家哲学中包含了造型之美的规律和法则认识,揭示了器物之美的内在规定性和本质特征。道家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万经之首的“易经”哲学思想,而“易经”中所包含的思想源流不是凭空冥想出的呓语,而是通过观察天地万物之后,各种自然现象高度抽象化的认识,反映造型的本质规律,同时也是对器物之美的本质的认识。
“道”的内涵丰富,一方面“道”反映事物形成的本质规律;另一方面它和器物的造型相互关联,具有内在一致性,反映了事物形成过程和构成的基本要素。首先,它产生万物,是万物之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从造物的角度看,“道”构成器物造型的原形。正如《道德经·第四十二章》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一说法源自《易经》“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实际上无论“道”“易”都是事物产生、形成、运行、变化的源头,是一物之所以为此物的本质属性。韩非子在《解老》中曾这样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又说:“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不难看出,“道”是万物之形成的总规律、总法则,是使各种事物具有具体法则的东西。而“理”则是构成具体事物的具体法则。如碟、碗、杯、壶、汽车、建筑,尽管其形状、材料、大小、装饰、功能千差万别,但是从本质上看,它们没有区别,都是材料及点线面构成的容器,从装水、物品、食物到装人。因此,“容”这一概念是先天存在的,不会因为这些器物的损坏、消失而消失,它就是上述具体器物的“道”,是形成这些器物的总规则。尽管器物的材质、工艺、功能之“理”不同,但不能改变其“容纳”本质,一件精美器物的标准就是无限地接近器物造型的本质特征。
二、道之玄妙——揭示器物之美的若干特征
道尽管揭示了构成器物之美的规律和本质,但它又是最难以把握的:一方面器物形式的本质特征是相对抽象的,需要不断通过设计实践揭开它层层面纱并不断接近它的本质属性;另一方面器物造型之美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尽管本质相同,但因其材料、工艺、功能、使用习惯等差异,不同的器物又表现不同的个性美特点,也就是常说的“美美与共,各美其美”。因此,《道德经》中指出“道”难以把握,“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道”不是一般的道,它揭示的是万物形成的本质和规律。道是深奥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有欲以观其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为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它精深、玄奥,那么人们是否就不能认识万物形成的本质规律。《道德经》给出了肯定的答复,“道”是可以认识的,它的所有特征都可以用一个字来表示,那就是“玄”,也就是所谓的“玄妙”。
《道德经·第十五章》中对“道”之“玄妙”作了明确规定: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與(豫)(慎重)兮若冬涉川;犹(警觉)兮若畏四邻;俨(端谨、庄严、恭敬)兮其若客;涣(解散、融合)兮若冰之将释;敦(敦厚)兮其若朴;旷(空旷)兮其若谷;浑(混)兮其若浊”。道之“玄妙”概括为“豫”“犹”“俨”“涣”“敦”“旷”“混”七个方面,它反映了“道”之“玄妙”的本质特征。尽管上述特征反映的是“道”的特征,但正如前述“道”同样也反映了器物构成的本质规定性和规律,从中我们不难体会传统器物制造中“玄妙”之美的智慧。
“俨”为端谨,是器物形式要素的表征。从审美角度看,它体现的是技术理性下的严谨之美。从造形结构的设计出发,“俨”体现了构图的缜密、周到、和丝严缝。同时它也绝不是僵化、呆板,而是体现了设计理性中所蕴含的一种灵动。中国传统器物很多反映了这种设计特征,(图6) 明代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的搭脑、靠背、扶手、鹅脖通过自然弯曲或人工制造形成优美、简洁曲线,角牙相衬,管脚枨下装极窄的牙条,既有形式美感、又起到固定座椅的功能,可谓形式与功能的完美结合。通体没有装饰,通过精美的材质(黄花梨)肌理和质感,精确的结构比例关系、科学合理榫卯工艺,简洁形式,体现出稳定、沉穆、端庄、严谨且充满灵性的形式美学意味。从装饰看就是减少多余的装饰,重视材料本身的自然纹理和色泽。明式家具很少有多余的装饰,精于选料配料,以材料的自然纹理作为装饰,达到天然混成的自然装饰效果。

图6 (明)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 上海博物院
“敦”为厚、朴,是器物重要的形式特点。它体现的是出水芙蓉,质朴自然之美。所谓“朴”指木之未雕,未加工整理。中国传统器物特别重视自然在设计、制造中的作用,所谓“天时、地气、材美”配合“工巧”才能制作出高品质的器物。从器物的造型形式看,要求造型精练、简洁、反映造型精髓的质朴自然之美。东汉说唱俳优陶俑(图7)材料质朴,造型浑朴简练,简约流畅,毫无繁琐雕琢,神形兼毕、诙谐富有感染力,其绝妙之处通过对面部瞬间动态和丰富表情刻画,展示说书人的幽默神态。整个陶塑作品重在传神,质朴自然,在动势中表现物象的内在神韵,出神入化。

图7 (东汉)说唱俳优俑 中国国家博物馆
“旷”为空旷,也有空虚、空灵之意,也是构成器物的重要形式特征,体现器物的静谧、深邃特征,表达的是空灵、寥寂之美。“旷”并不是一无所有,它体现了构成器物各元素之间相对关系,即相互依存、相互关联,可以用“有”和“无”“虚”和“实”来表示。它有两层意思:一方面,从器物的功能看“虚”“无”是器物功能必不可少的部分,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如“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辐条与辐条之间、器物的中空部分、门与窗所形成的“虚”是车辆行走,房屋居住的必要条件,没有“无”“虚”的参与,车子很难载重,房子不能居住,就是无用之器;另一方面,“虚”“无”也是造型的必然要素,所谓“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器物的造型是虚实、有无的结合。不是绝对的虚空和荒凉。日本枯山水庭院景观设计(图8),从视觉效果看相对空旷,但通过沙粒、石子、石块及苔藓的穿插布置,营造出庭院深深深几许,此处不见山水,但似汪洋恣肆,山岭峻拔,空寂、静谧,氛围灵动,富有意境高妙的禅意景致。

图8 日本龙安寺枯山水庭院
实际上除上述“俨”“敦”“旷”等作为理解事物的形式特征外,道家所倡导的“寥”“夷”“希”“微”等观念,都能体现在器物的本质属性和美的意境中,以此指导器物选材、形式构成、装饰,其设计品格和审美趣味会妙趣横生。
三、《道德经》中设计美学思想的内涵
当代器物设计形态是多样体现:功能型、时尚型、概念型、反叛型、技术型、融合型,反映了多元化的社会需要和审美意趣。但真正能留在人们记忆中的精品却少之又少,同质化严重,即使一些所谓优秀的作品,虽然可以悦目,但很难悦心。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是过于铺陈形式,追求所谓的新异,没有根基和文化灵魂,经不起审视。仔细推敲道家的思想观念,或许能体会到别有洞天的审美意趣。
1.道法自然——器物之美自然属性
《道德经》揭示器物之美的意蕴,揭示了器物之美的自然属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认为:“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可见在道家思想中,自然是“道”的本质属性,或者是“道”的别称,“自然”这个语词涵盖宇宙万物。从道家的自然观中,不难看出“道”是构成万物的本质,而遵循、效法“自然”,即“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是理解万物形态的方法。中国传统器物制作,无论是造型、选材,还是工艺都实质上实践着这一造物的基本法则。
“观物取象”是传统造物的重要思想渊源,也是道法自然的延伸。这里的“物”实际上是自然之物,因此有包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系辞下)这一通过观察天地、自然之物造物的创举。由这一思想衍生出的朴素造型观“像天法地”“天圆地方”观念(图9),即《道德经》所谓的“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道法自然思想的延伸。中国人对圆形的偏爱和技法处理,其根源与此紧密相关。早期的陶器的碗、壶、盆等容器,包括大多数的装饰纹样都直接或间接地源自于自然物——动物、植物、山川、星辰、日月等的启迪。实际上这一思想到现在都不过时,符合自然之趣的造型一定是经典的。实际上传统器物的制作工艺,也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如毛笔选择兽毛一般采用冬季出产的为品质最佳,都是顺应自然规律的选择。

图9 良渚文化玉琮 浙江省博物馆
2.见素抱朴——器物质朴美的意蕴
“朴”也是道家哲学、美学的重要思想。朴的本义是指木皮,王褒在《洞箫赋》有“秋蜩不食,抱朴而长吟兮”。“素”为洁白的生绢,引申为质朴不进行矫揉造作的修饰。在道家哲学思想中表示原始自然质朴的存在,作为美学意义上的“素”“朴”,除含有“自然”之意外,还有简单、朴素、质实之意。朴拙、素朴、质朴、古朴、朴厚都是中国美学的重要范畴,也是传统器物造型的重要依据。在老子《道德经》中则表示原始自然的质朴存在状态,“朴散则为器”,“朴”的标准,就成为世间各类器物的制作标准。以朴散思想看中国传统器设计观,可以看到传统器物设计尤其重视素朴之美,无论是选材、造型装饰,还是制作工艺都是如此:一重视选材,尤其是自然材料的选择,强调优质材料自然天成的本性;二制作工艺符合天时之气,不卖弄巧技;三不追求过于纷繁的色彩,提出“五色令人目盲”;四强调因形、因材制作。可见在《道德经》中,美的器物也应符合自然规律,善于发现、选用天然材料,因形、因势造型,不卖弄装饰。
3.致虚极守静笃物态观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我们对器物形态本质的探索是永恒的,越是本质的东西就越简单稳定。从器物造型的角度来看,万物肇始于“无”,即所谓“无名,万物之始也”。万物起自于无形、混沌、虚静的状态,是万物之形的本质特征,越是简单的形态越接近事物原初状态。作为美学范畴的“虚极、静笃”追求无我之境的空灵、静谧的状态。从造型看越是简单的形、质朴的材料、巧妙的工艺、合适的装饰越接近“致虚极,守静笃”价值追求的内涵。它与《道德经》所提出的“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的思想观念是一致的。实际上现代主义设计所追求的 “少即多”美学观念与道家美学思想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4.万物负阴抱阳——和谐之美
道是构成万物的本质属性,它不是空洞、虚无、飘渺的,而是由“阴”“阳”两种具体元素或两种状态构成的。在道家哲学思想中,道是万物形成的根源和总法则,“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揭示了道形成万物的具体过程。任何有形物体形成都是由“道”分化出的“二”,即所谓“阴”“阳”两种基本元素构成。《道德经》所提出的“万物负阴抱阳”,包含了中国传统对构成万物基本物质即阴阳两种元素,阴阳两种元素的平衡状态是万物形成的先决条件。在基本器物造型中,阴阳两种元素、两种状态,能够达到平衡的状态,这样的器物一定是美的,甚至是经典的。2010年世博会以色列馆“海贝壳”(图10)的设计意匠即取自于《道德经》思想中的“万物负阴抱阳”的阴阳平衡观念。实际上,“万物负阴抱阳”除了包含自身的阴阳平衡观念外,还包含了由阴阳观念转化来的虚实、有无、阴阳等形式关系,这些都构成了中国传统器物造型之美的基本特质。

图10 海贝壳 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色列馆
余论
中国传统器之美的内涵丰富,表现为:其一,材料、工艺、形式、装饰等形式方面的内容;其二,器物的功能性。追求最大限度的为人提供便利,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其三,器物的思想性,即器物表象下的各种文化意蕴,包括它的美学价值、设计思维、社会意识、时代价值等。以此观之,道家思想所包含的对器物上述内容的理解,是打开理解传统器物美学价值的钥匙,值得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