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法库县叶茂台辽墓出土《竹雀双兔图》主题研究
2022-10-11王雪苗陈谷香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浙江杭州310058
王雪苗 陈谷香(浙江大学 艺术与考古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一、引言
1974年辽宁法库叶茂台发掘出一座辽代契丹贵族妇女墓葬,墓葬由一个主室、一个前室和两个耳室构成。主室安置一木构“小帐”式棺室,内东西横置石棺,但是最为特殊的是,棺室内东西板壁上挂有两轴绢画。出土时画的天杆和天头绫裱通过原来的线绳,仍悬挂在先前的铁钉之上,基本可以判定木棺室内原是悬挂了这两幅卷轴的。西面出土的为花鸟,被定名为《竹雀双兔图》(图1);东面为山水,定名为《深山会棋图》(图2)。

图1 叶茂台辽墓出土《竹雀双兔图》

图2 叶茂台辽墓出土《深山会棋图》
其中山水画为绢地青绿设色,上部绘峭峰陡起,白云掩映其间;中部左面山崖间松林楼阁,前方有两人对坐围棋,右侧有一童仆;山下的最下方有一隧道,前方辟门,门外有一宽袍大袖、头着高冠者策杖向隧道方向走去,后面跟着一前一后两个童仆,一人背琴囊,一人背酒葫芦。西面的花鸟画,上部画三根双钩竹子,上各立一雀,下部画两只兔子在吃草。竹丛下生长的三朵野花,左为蒲公英,中为地黄,右为白头翁,此外满地画了零星的车前子和杂草,中间三株植物画的鲜艳肥大,令人瞩目。
当年该墓葬被发掘之后除了考古报告之外有过一系列研究文章发表,从时间与类型来看,对于叶茂台辽墓及其出土卷轴画相关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1975年与考古报告同批发表的陪葬品鉴定文章,还有一类是在2004年及以后的研究型文章。前者更加重视对于两张绢画的风格描述和断代,而后者则更重视在功能和意义上开辟出新的视野。杨仁恺对两张卷轴作过重要的研究判定,将这两张画视为传统的书画,偏向于对两张卷轴的绘画主题、风格、年代的书画鉴定学研究。李清泉于2004年再次发表文章对《深山会棋图》进行解读,将其视为专门的陪葬冥画,从绘画题材与功能入手,对山水挂轴的性质意义进行思考。
关于这两张卷轴画的主人,即叶茂台七号辽墓的墓主人,由于并未出土相关的墓志,难以确认其具体身份,充满了神秘感。《辽宁法库叶茂台七号辽墓出土人骨研究》根据墓主人颅骨的形态观测、测量和分析得出结论:其一,墓主确为老年妇女,年龄在45-65岁之间;其二,墓主人可能有一定残疾,生前牙齿几乎全部脱落,颞下颌关节脱位、寰枕关节退行性病变以及骶骨畸形。此文推断墓主人生前牙齿几乎全部脱落的情况与其年龄有关,除此之外墓主人还有严重的牙周炎等严重的口腔疾病,可能也是诱因之一。就墓主人的社会地位来说,并无太多争议,是一契丹贵族,从葬有刻丝金龙纹尸衾等贵重物品来看,或和皇室有一定关系,与考古报告一同发表的鉴定文章也都赞同此观点。李宇峰《辽宁法库叶茂台七号辽墓的年代及墓主身份》一文进一步提出,此墓主人可能是辽朝皇室公主。一方面,法库叶茂台墓地为萧氏家族墓地,墓主身份只能是耶律氏;另一方面,墓中出土的棺床小帐与高翅帽也是公主享用的制式。墓主人为老年女性,大约生于穆宗应历初年,是一学养深厚的才女,或许信仰道教。
对于这两张画的主题,前文谈到,杨仁恺的研究方法为古典书画的传统鉴赏,故而他对《深山会棋图》主题的认识为“汉族士大夫‘山林隐逸’那种情趣”。李清泉则提出了不同的分析角度,即这两幅卷轴并非传统卷轴画,而是陪葬冥画,寄托了墓主人的升仙愿望。刘乐乐延续了李清泉的思路,对画面中的内容进行了分析,认为画面象征着墓主人即将跟随画中的主角进入仙境,而木棺床和石棺结构则象征着墓主人已经完成了生命的转化,成为了接受子孙祭祀的祖先。
以上学者都对《深山会棋图》产生了兴趣,但是遗憾的是目前并没有针对《竹雀双兔图》含义与功能的专门性研究,本文试图从《竹雀双兔图》中所绘的三株植物入手,进一步对两张卷轴的性质意义进行说明,同时对目前此墓以及其出土卷轴画的争议与问题进行梳理解释。
二、《竹雀双兔图》的年代问题
目前关于《竹雀双兔图》的年代判定目前主要依靠杨仁恺1975年与考古报告同批发表的文章《叶茂台辽墓出土古画的时代及其他》,从其风格、内容、装裱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断代。此后并无专门研究文章讨论此画年代,主要原因可能是两张轴画均为墓葬出土,其时间判定严格来说与墓葬的断代问题应该互为参照,故而即使有争议,也主要集中于墓葬的年代之争,陪葬轴画的时间争议往往是次要的,或者说只是墓葬年代判断的依据之一,最终的断代还是要取决于墓葬的具体时间。既然目前学界对于叶茂台七号墓的断代有了新的看法,那么对于两张轴画的年代推断也还有继续讨论的空间。尤其杨仁恺对于这两张卷轴画的断代仍有商榷之处,需要继续跟进并且参考目前学界对于叶茂台七号辽墓的最新研究成果。
由于其陪葬品的特殊性,需要依托于对于叶茂台七号辽墓的断代,目前学界有两类观点。首先是以考古报告为代表的,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进行判断,认为此墓年代应为辽代早期,墓葬的大致年限在公元959—986年。其次则是以曹汛《叶茂台辽墓中的棺床小帐》的观点为代表,从墓中带有浓郁道教色彩装饰品、陪葬品来判定此墓为辽代中期所建。例如壶门虎头图案与鸾鹤五云图案带有道教色彩,应出于道教极为泛滥的时期,即辽圣宗(982—1031)时期,有可能在澶渊之盟之后,公元1005—1031年。王莉《辽代四神图像的时代及相关问题》也认为考古报告将此墓时间考订得偏早,四神石棺主要是流行于圣、兴二朝(971—1055),此墓应该建于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澶渊之盟”后。李清泉对于《深山会棋图》的年代判定可以作为照应,其判定依据为辽代墓葬中出现的弈棋元素,其中宣化张文藻墓《三教会棋图》属辽代晚期作品,陪葬棋具实物的辽代墓葬,例如常遵化墓、陈国公主墓、白塔子墓、萧孝忠墓基本上都是圣宗时期以后的墓葬。这些可以说明,同时葬有《深山会棋图》和双陆棋具的叶茂台辽墓同样也不会早于圣宗时期。这也是目前学界比较主流的观点,倾向于将此墓定为辽代中期而非早期,应是确认无误的。
既然目前学界对于此墓的断代更加倾向于辽代中期,那么这两张卷轴画的年代判定则有了基础,即其创作时间的下限应该是辽代中期。但是陪葬卷轴画的断代同时也牵涉到这两张画的属性问题,若陪葬卷轴是一般的书画收藏,那么其创作时间还应考虑其上限,可能早于墓主人下葬的时间;若是将这两张卷轴视为陪葬冥画,是专为墓葬而作的,那也就不存在创作时间的上限问题了。
首先,确实一般艺术史家认为花鸟画作为独立的一门在唐代中期还未从别的画种分离出来,五代处于过渡时期,直到北宋初期才臻于成熟,中期而极盛。杨仁恺的断代所选的参照作品为黄筌的《珍禽图》和黄居寀《山鹤棘雀图》。前者为画稿,而后者已经是一幅完整的主题画。反观《竹雀双兔图》,其“技法比较稚拙,装饰性尚未洗净,但已经形成了一幅独立的作品,这正好证明了它是从附属地位逐渐演进、处于向成熟期发展中的作品”。显然这是将《竹雀双兔图》放在传世书画中进行了比较,参照黄筌《珍禽图》和黄居寀《山鹤棘雀图》,觉得此画应该处于两幅花鸟的发展阶段中间,有逐渐向成熟的独立花鸟画发展的趋势。总的来说,杨仁恺认为此画制作的相对年代有可能早到后晋天福即辽会同年间(938—947),最晚不过北宋开宝即辽应历末年(969)。花鸟画的年代稍晚,但其下限也不晚于北宋太平兴国初年即辽保宁后期,即公元979年前后。其结论基本与考古报告的对墓葬的断代互为对照,偏向于辽代早期。
此处从画面风格、技法判断作品年代是没什么的问题的,但是对这两张墓葬出土卷轴画来说确定性却并不高。这两张卷轴画出土于辽宁省法库县,在当时属于契丹族的私城,远离中原、地处偏远,辽的书画传统应该是向中原地区学来的,必然存在滞后性。唐宋花鸟画经历了前代的文化积淀与技艺传承累积,而辽代花鸟画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整体都不处于花鸟画的成熟阶段,与中原地区唐宋花鸟画发展历程并不同步。另外,以风格论墓葬绘画具有一定的难度,一是因为葬画是一种工匠画,风格、题材演变的过程中程式化特征尤其突出;其二则是葬画品质相比传世作品低,目前出土的,并且能以风格论的葬画难以与传世绘画作出比较。由于杨仁恺采用的对照作品均为中原地区的传世花鸟画,故而无论是将这两张卷轴的真实年代都应该晚于杨仁恺通过与中原地区传世绘画对比所推断出的时间。既然两幅卷轴可能是陪葬用的冥画,可能选取同时期辽墓中的花鸟画作为参照更加合适。
若将此画放置在墓葬绘画系统中作比较的话,这种采用双勾法,兼用淡彩的方式在辽墓壁画中其实很常见,并不仅仅只出现在花鸟画早期的发展阶段。例如皮匠沟1号墓(辽中期)墓室正面菊花图、辽代羊山1号墓(约1026)墓室北壁牡丹图、下湾子5号墓(辽中期)墓北壁牡丹图、下湾子5号墓(辽中期)墓室东北壁荷花图等均采用白描双钩的方式植物形态。其中羊山1号墓北壁的牡丹图不仅采用相似的技法,构图也是呈中心对称的方式,同《竹雀双兔图》一样带有一定的装饰性。同时,《荷花图》《牡丹图》中对于植物叶片的描绘也较为肥大,手法稚拙,叶片之间的前后穿插、经营位置的关系有一些错位,而《竹雀双兔图》中双勾竹、草药的面貌类似。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边远地区的绘画的发展情况来看,还是从墓葬系统绘画的发展情况来看,将辽画或者是辽墓葬画与中原地区品质最高的传世作品进行比较,由此推断出的年代都是存疑的,这两张画应该出于辽代中期,与同时期的辽代墓室壁画花鸟画风格和画法近似。或者更精确地说其创作时间的上限必然是晚于辽代早期的,创作时间的下限与墓葬时间一致,不会早于辽圣宗。
三、《竹雀双兔图》的涵义与功能
根据考古报告中的记述,挖掘过程中发现两卷轴画并不是以画卷原封随葬的,而是展开悬挂在木构棺室内。“当清理该墓承受石棺的木构棺房时,首先在东侧山压槽坊下发现山水画,画轴脱裱,已坠落在木板上面。画的天杆和天头绫裱通过原来的线绳,仍悬挂在先前的铁钉之上。至于花鸟画,则发现于木房西侧槽坊下的木板上。由此可知,这两轴画在入葬时原是东西对面悬挂的。这种方式是前所未见的。”装裱方式整体比较简陋,画心两侧既未套边又未镶边,天杆仅以竹子制成,并且天杆下方绢裱一边有破裂后针缝的痕迹。

图3 羊山1号墓墓室北壁牡丹图线稿
由于题材的不同,《深山会棋图》明显受到了学界的重视,无论是从李清泉开始的对图像深层含义的讨论,还是其他学者在风格论证中的引用,或多或少都会将《深山会棋图》视为同时代山水画发展的对照作品。反观《竹雀双兔图》,在1975年之后却并无专门性的研究文章进行过深入讨论。既然两张挂轴东西相对,从其摆放方式就能知道两张卷轴功能应当相同,或者说其含义应该相互之间存在联系,如果《深山会棋图》是为了寄托墓主人的升仙幻想的话,《竹雀双兔图》不会只是简单出于装饰作用的花鸟画。

图5 陕西韩城宋墓壁画备药图
1.传世绘画与考古遗存中的医药题材
事实上,《竹雀双兔图》的画面内容相较于《深山会棋图》更容易令人产生疑惑:在画面中间绘有三柱肥大的植物,经过比对应该是三株不同的草药,左边为蒲公英,中间为地黄,右边为白头翁(图4)。以三种不同的草药入画,这是在目前传世同时期的花鸟画中所未见的。

图4 《竹雀双兔图》局部
草药或者说医学主题在宋代似乎才开始流行起来,邓椿的《画继》曾将“蔬果药草”单独列为一门,但是这一门下内容中却仅有两名画家,并且均未谈到有草药入画,可见当时确实少有实例。宋代墓室壁画中也曾经出现过医药题材的大型壁画,即西韩城盘乐村宋墓的备药图,位于墓葬北壁画面右侧,一张桌子上摆满各种瓶罐,两名男子正在紧张备药,左侧男子手持《太平圣惠方》。右侧男子手持两个药包,上有“大黄”“白术”字样,似乎在等待左侧男子查阅。在此之前我国似乎还没有类似的以医药为核心的壁画的出现,所以当时这幅画非常受考古学界、医史学界的重视。
有相当一部分宋代的传世人物画中也出现过草药的内容,例如传为宋代孟显的《采药仙人图》(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传为李公麟的《毛女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孙钰的《毛女图》(费城艺术博物馆)等人物画的背篓中均有植物,一般认为就是草药,还有手持的灵芝,无不暗示着画面主角仙人的身份。传为宋人的《松荫论道图》,画中的道教仙人也是一位与毛女形象类似的采药男仙。辽代作品中可见辽应县木塔第四层释迦主像内的《神农采药图》,画面描绘神农采药归来时的形象,右手擎灵芝,左手携药锄,背后有药篓,与毛女类似。传为宋人的《观画图》主题便是医药,画面后方有一药摊,上面不仅有各种药草,还有动物头骨以及鳖甲。

图6 应县木塔《神农采药图》
上述人物画或者说仙释人物,其共同特点一为医药的元素,二为画面仙隐的主题,似乎可以为阐释《竹雀双兔图》的主题提供一些思路。但以上案例并不是专门的花鸟画,画中主角的身份和画面主题不难理解。而《竹雀双兔图》却采用了宫廷绘画中花鸟画的绘制方式,并没有涉及仙释人物,从篇幅和构图安排上来看,这三株植物都是当之无愧的画面中心,相比之下一般承担花鸟画中主要角色的竹雀和双兔显得稍加逊色。这样来看,此画主题和含义与画中的草药是息息相关的。
2.地黄、白头翁和蒲公英
李清泉在《叶茂台辽墓出土<深山会棋图>再认识》一文中提到过木棺室西壁的花鸟画,所绘植物或许是被认为有祛病延年功效的药草之类,除了这一猜测之外目前学界暂时还没有学者对这张画草药的含义进行过解释。
画面中的草药,品种不同,并列构图,并且占据了画面中最核心的位置,其大小也相比实物比例更加夸张,很明显不是随机或者是通过写生的方式绘制上去的,同时期的中原地区也并没有这样的作画习惯,那么必然是有意为之的。而绘制药草的意图有以下几种可能:
其一,是否墓主人是死于疾病,或者说与墓主人的身体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叶茂台七号墓棺床上两门侍尚未雕完,其余图像则全是墨画,墓主人甚至可能是暴毙而亡,墓葬内部装饰尚未来得及全部完成。
其二,这三种药是否或多或少与道教有关,这一猜测基于目前的大部分相关研究成果都强调了墓葬内部的宗教属性问题。再加上辽圣宗时期,尤其澶渊之盟之后神仙道教思想的风靡,或许带来一定影响。
其三,具有某种具体的含义,例如驻颜长生、生死悲欢等。由于叶茂台七号墓出土卷轴画具有冥画的性质,并且考虑到古代墓葬的功能和目前学界对于墓室壁画的研究理论,两张卷轴东西相对,如果《深山会棋图》确实是寄托了墓主人长生的愿望,那么《竹雀双兔图》中的草药很可能具有同样的含义。
在宋代,地黄、蒲公英、白头翁这三种药材确实被视为可以延年益寿的良药,尤其是居于画面中心的地黄。地黄最早作为益寿之物出现在葛洪《抱朴子》,其中讲述神仙方药的部分便有地黄的传说:“昔仙人八公,各服一物,以得陆仙,各数百年,乃合神丹金液,而昇太清耳……楚文子服地黄八年,夜视有光,手上车弩也。”又言:“韩治子以地黄甘草,哺五十岁老马,以生三驹,又百三十岁乃死。”唐代白居易作《采地黄者》诗,其中有一句:“与君啖老马,可使照地光。”便是形容马吃了地黄之后,膘壮有力,毛色发亮,光彩照地,这种说法可能就是来自于《抱朴子》。谢灵运《山居赋》中的一句也是此意:“采石上之地黄,摘竹下之天门。”古人希望能在衰老之前寻觅名山大川中的仙药,故而采集地黄挖取天门冬,这些都是当时被认为可以延年益寿的药物,在《抱朴子》中都有相关联的典故。孙因《越问·隐逸》便引用了谢灵运此句,直接将地黄与谢灵运联系在一起,采药、采地黄在当时已经成为了隐士的代表行为之一。
苏轼被贬惠州时,曾与龙川县令翟东玉写过一封书信,信中请求翟东玉向当时的兴宁县令欧阳叔向求要地黄:
药之膏油者,莫如地黄,以啖老马,皆复为驹。乐天《赠采地黄者》诗云:“与君啖老马,可使照地光。”今人不复知此法。吾晚觉血气衰耗如老马矣,欲多食生地黄而不可常致。近见人言,循州兴宁令欧阳叔向于县圃中多种此药。意欲作书干求而未敢,君与叔向故人,可为致此意否?
前文提到的《采地黄者》是白居易在下邽(陕西渭南)渭村见到农民遭到春旱秋霜之灾后所写。饥民在地里采地黄,拿到当时的富贵家换取口粮,而富贵人家却用这些地黄喂马,贫民只求能换一些马吃剩残料。苏轼可能是读了此句,再加上《抱朴子》中记录,便也觉得自己如同梦中所见老马一般血气衰竭,故而给翟东玉写信,代向欧阳叔向讨地黄为食。苏轼笃信地黄的效用,并且不止一次在诗文中引用,《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中另有收录一首苏轼所写《地黄》诗也与此事相关。除了苏轼,陆游也曾有诗《梦有饷地黄者味甘如蜜戏作数语记之》讲述梦中所见:“有客饷珍草,发奁惊绝奇,正尔取嚼龁,炮制不暇施。异香透昆仑,清水生玉池,至味不可名,何止甘如饴。儿稚喜语翁,雪颔生黑丝。老病失所在,便欲弃杖驰。晨鸡唤梦觉,齿颊余甘滋。寄声山中友,安用求金芝。”其中“雪颔生黑丝”“便欲弃杖驰”之语,便是形容梦中所见食地黄后的效用,无论这种食地黄可以使人驻颜的说法是否可信,但是就文献来看,宋代曾有过食地黄可以延年益寿的说法,并且地黄作为一种赋有神效的药材频繁出现在诗文之中。
再从中医典籍中寻找相关记载,前文所提到的陕西韩城盘乐村宋墓出土备药图,图中便绘有一男子手持《太平圣惠方》,此书由北宋翰林医官使王怀隐等人奉命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开始编纂,淳化三年(992)刊出。其中“神仙服地黄法”并“服地黄延年法”,记载数个地黄方,效用无不是长寿延年的,甚至可以达到“百日颜如桃花”的效果。除了《太平圣惠方》之外,使用地黄作为主药的中药文献更是数不胜数,唐代孙思邈所作《备急千金药方》中就有一地黄养性法,后又被《世医得效方》中补充收录:“使人老者还少,强力,无病延年。”可见苏轼、陆游等人笃信地黄可以延年益寿并不是无稽之谈。
除此之外,《本草纲目》中除了说明生地黄主治功能为“久服轻身不老,生者尤良”“久服变白延年”之外,熟地黄还可“固齿乌须,一治齿痛,二生津液,三变白须,其功极妙”。根据《辽宁法库叶茂台七号辽墓出土人骨研究》中的分析,墓主人生前牙齿几乎全部脱落,虽然无法确定绘制此药是与墓主人生前病症有多少关系,但是绘制地黄必然是赋予一定长生愿望的。
白头翁在《神农本草经》中又称胡王使者、野丈人以及奈何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注其名可能取自于“状似白头老翁”,并且其别名“野丈人”“奈何草”也是出自于此。不知道是否为巧合,“奈何”这一名字明显也与古代的鬼神观念息息相关。另有一种名称的解释是由于其名“白头翁”导致时人误会其效可以益寿。“赤车使者白头翁,当归入见天门冬。与山久别悲匆匆,泽泻半天河汉空。”所谓赤车使者、天门冬等均被视为返老还童的仙药,此处白头翁与这几门药并列,可见在当时被人们被视为一类。正如前文谢灵运《山居赋》中的用法一样,这些药材的益寿传说来均自于道教典籍《抱朴子》。至于白头翁真实具体的中医效用,根据《本草纲目》记载,与前文地黄一样可以治疗“齿痛,百骨节痛”。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隐蔽的线索是白头翁还有同名鸟,也叫白头鹎,同白头翁草一样,顶部毛白故同名。名字带来的特殊性,容易令人联想到白发老人,使其时常在诗文中扮演伤感的角色,有时诗意朦胧,容易分不清是白头翁草还是白头翁鸟。李白有诗:“如何青草里,亦有白头翁?折取对明镜,宛将衰鬓同。”就是看到了白头翁草,由花生情,联想到自己年华已逝、青春不再,空对春风含悲引恨,尤其是一句“宛将哀鬓同”,辛酸之意更甚,同苏轼一样发出了人生短促的嗟叹。
至于蒲公英,古称地丁,《本草纲目》中曾引元代萨迁《瑞竹堂经验方》的记载,地丁“擦牙乌须发”,且“极能固牙齿”;由此看来,熟地黄、白头翁以及蒲公英三门药均可擦牙固齿、治齿痛。除此之外,李时珍还引一《瑞竹堂经验方》中的“还少丹”,药方前有一段解释:“还少丹,昔日越王曾遇异人得此方,极能固齿牙,壮筋骨,生肾水。凡年未及八十者,服之须发返黑,齿落更生。年少服之,至老不衰。得遇此者,宿有仙缘,当珍重之,不可轻泄。”其中“须发返黑”“至老不衰”等言辞都着重强化并且夸张蒲公英的效用,跟地黄一样,与修仙驻颜联系起来。
总的来说,三种草药的具体功用可能不同,经过梳理之后,其文献材料的来源与其共同点基本可以相互对照。道教文献、中医文献以及诗文三个层次可以对照三种含义:
首先是具体的中医效用,尤其固牙齿、治齿痛,车前子、蒲公英在中医文献中又常作妇人方,与墓主人的性别、身体情况能吻合。三门药材在中医文献中均有记载,这一点与墓主人头骨研究报告中前牙齿脱落的情况相对应,应该不是巧合,而是刻意为之。其二为生死之叹,在诗文之中成为代表人生阶段的时间意象,尤其是白头翁与地黄;最后为返老还童的功用,来源于道教文献,并且都有着相关的神仙方药传说。无论是以上哪一种,明显此画的创作者对于这几种植物的选择并不是任意为之,首先画面中间的三种药材中医效用具有共同性,其次画家或者设计者很可能熟读道教典籍《抱朴子》并且了解其中的神仙方药、志怪传说,同时还熟知这三种植物在诗文之中各自代表的意象,故而才选用了这三种药材入画。
3.求仙问药与生死悲叹
其实辽代契丹人对于中药的态度极为尊崇,上文所谈到的出土于应县木塔第四层释迦主像内供养的《神农采药图》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辽史》中记述,契丹族自认祖先为炎帝神农氏。《辽史·世表》中记载:“盖炎帝之裔曰葛乌菟者,世雄朔陲,后为冒顿可汗所袭,保鲜卑山以居,号鲜卑氏。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库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见于此。”很明显可以看出契丹人对于正统身份的构建源自于神农氏,神农氏既为契丹族的祖先,又亲尝百草、播种五谷、发明农业等,契丹人对于中医药的态度可想而知。
将《竹雀双兔图》与《深山会棋图》一同考虑,从安置方式也可以看出来,悬挂画轴的棺床小帐是仿大木作建筑建造的,有学者指出,它仿效的不是宫殿,不是佛寺,而是贵族祠堂、宅第一类较为一般的建筑。如李清泉所说,这两幅卷轴画必然不仅仅出于模仿居室挂设或体现死者生前的艺术玩好。由于此画并非原卷陪葬,而是展开悬挂,应该是出于墓葬空间中的设置需要。但是这种设置方式是出于礼仪的需要,还是出于墓葬信仰的需要?很明显更加倾向于后者,因为辽代并无在墓葬中陪葬挂轴的其他案例。但是如果是为了建立起一个墓主得以永生的死后仙境,那么挂轴画和墓室壁画不同载体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从上文对于墓主人的分析已经可以得知,墓主人系一五十岁左右的契丹族妇女。出土石棺上朱雀及妇人启门部分已雕出,两门侍尚未雕完,留有部分墨线;其余图像则全是墨画。可以确认的是,石棺的部分雕刻尚未完成,墓主人便匆匆下葬了。也许是墓主人突发疾病,也许是建造过程中的问题,总之墓主人在预计完成的墓葬装饰时间之前下葬了,此时的墓葬壁画以及石棺部分都未来得及完成。从这个角度进行思考,此时卷轴画很可能承担了完成石棺及棺床装饰的任务,从完整性上给予墓葬艺术以新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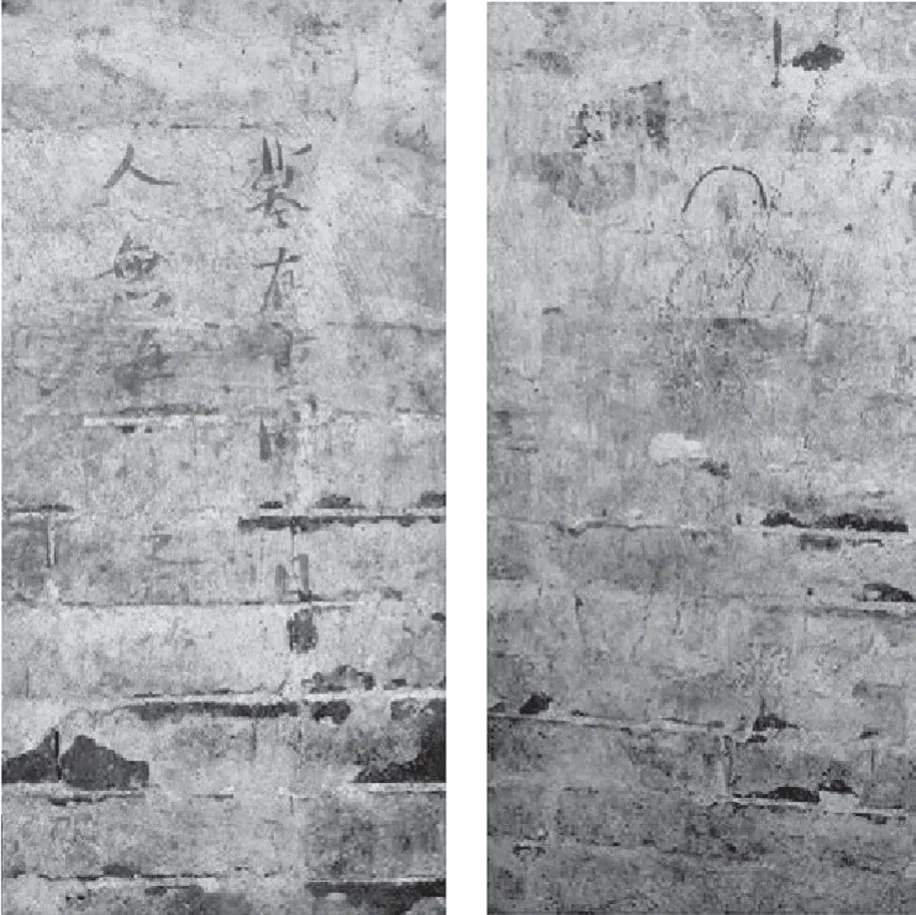
图7 山西高平汤王头村金墓后室南壁题记与人物
在对《竹雀双兔图》有了新的认识之后,再重新考虑《深山会棋图》的画面内容和主题,反思这两幅画之间真正的联系是什么。“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从前文所引的谢灵运、孙因等人的诗中也可以感受到,进山采药是一种求仙的重要手段,这种生活被隐士们所向往,而服药就是为了追求长生。再考虑《深山会棋图》的画面,无论是弈棋的行为,还是画面中执杖者身后的琴与葫芦,确实都是世外仙人的代表元素,都能说明这个画面所处的位置是一世外仙境。当然,除了塑造死后仙境之外还有一种可能性:也许这张画并没有想要特别去表达这些东西,只是对于当时所流行的仙弈题材的一种响应。因为流行,再加上墓主人或者当时的辽国皇室之间有着这种道教信仰的氛围,所以在这两张卷轴画的选择上,选择了这个题材,而不是说利用这张洞天仙弈图去塑造所谓死后的仙境。
仙人弈棋这个题材其实源自于烂柯故事,最核心的含义在于:樵人王质寿命的延长。并且通过樵夫王质生命的延长,表现出类似于“天上一天,地下一年”的时间尺度。对于这一思想,其实墓葬中早有反映,山西高平金墓就有一题记:“墓有重开之日,人无再少之颜。”前半句是表达说明后来的墓主人亡故后,需要打开墓葬与先期故去的亲人合葬,故而墓会重开,而后半句则是表达对于时间的感叹,正如李白所说的“折取对明镜,宛将衰鬓同”。巧合的是,此墓墙面上也绘有尚未来得及完成的画轴和执杖者。对于时间和生死的悲叹一直以来就是墓葬艺术不变的内核,墓室壁画早期的兴起就是为了追寻人类的终极关怀,求仙问药渐渐转为一种生死悲叹,不断开拓其存在的意义。

图8 山西高平汤王头村金墓后室北壁壁画
四、余论
目前为止,学界基本将《竹雀双兔图》定为辽画,《深山会棋图》稍有争议。例如宋画全集(第三卷第二册)中将《竹雀双兔图》标为“辽画”,主要由于此画的出土地点确为辽墓,其次制作年代也为辽代。徐英章《辽墓中出土的两幅古画》中将两张卷轴定为“辽国境内制作的具有明显特色的辽画”。但是无论从两张画的题材、风格特征来看,与典型的辽画其实不同。杨仁恺也曾探讨过两张绢画的画家身份问题,他认为《深山会棋图》主题更加接近于汉族士大夫所偏好的“山林隐逸”情趣,而其技巧风格则与荆关董李一脉相通,有较大可能是汉族画师作品。《竹雀双兔图》被怀疑可能出自契丹族画师,其原因是其布局、构图不同于汉族传统,装饰气味未脱;其次画面中间三株肥大的中药野花也少在中原画作中出现;麻雀与小兔的体态比例微有出入;再就是地面与空间等一系列因素,都有它的特殊风貌。
就本文目前对于《竹雀双兔图》的研究来说,也许能从某一侧面说明创作者的汉族画师身份。其一,同时期的辽代契丹族画师所绘墓葬花鸟画,参见敖汉辽墓、宣化辽墓等,格套化明显,并且装饰意味浓郁,似乎更加接近唐代花鸟画的风格,《竹雀双兔图》对于题材的选择、两只鸟的刻画、画面的安排等等都已经带有一定宋画的韵味,较之辽代中期墓室壁画中出现的花鸟作品更加成熟;其二,对于这几种入画草药的选择,这种含义的丰富性似乎并不像一个契丹族画师的作风,也许有着过度释读的可能性,但是无论是中药本身的药性、诗文中的意象还是道教典籍中的功能任意其中一种都不是契丹本地的画师所能了解的。
图1图2辽宁省博物院藏。
图3采自田彦国、王苹编:《大辽丹青——敖汉辽墓壁画》,赤峰: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36-37页。
图6 山西雁北地区文物工作站藏。
图7 图8 刘岩等:《山西高平汤王头村金代墓葬》《华夏考古》2020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