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烁着灵感火花的诗笔
——《艾青诗歌精选》导读(上)
2022-10-08山东师范大学杨守森
■山东师范大学/杨守森
一、有形体与无形体的形象创造
依据取材特征,在诗歌作品中,常见有形体的形象创造与无形体的形象创造两种类型。在这两种类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艾青的匠心独具、诗性智慧与独特的想象和表达。
1.有形体的形象创造,即诗中呈现的是可见的现实生活中的场景与事物,诗人的创作动力源于外在客观世界的刺激。在艾青这类作品中,其诗性创造表现在:诗人不是将外在事物激起的情感波动直接地表现给读者,也不是将感觉还原为感觉,而是经过精心的选择与组合,通过融汇着诗人真切情感的意象构成的艺术形象,说明世界、传达感情、感染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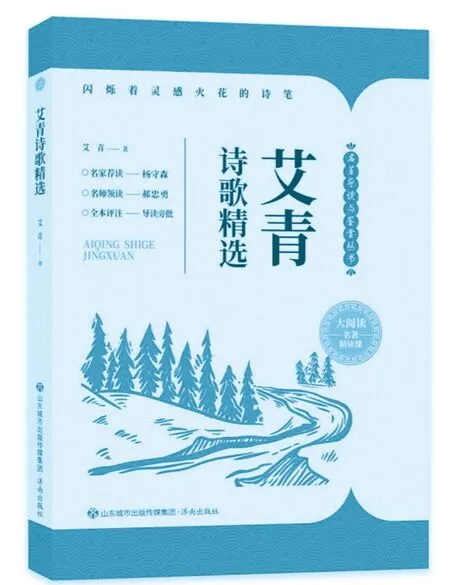
《透明的夜》是诗人早期的一篇作品,诗中描写了在“狗的吠声,叫颤了满天的疏星”的夜景下,一群“从各个角落来的”“夜的醒者”的活动。他们中有醉汉、浪客、过路的盗、偷牛的贼……他们酗酒、咬牛骨、放荡地笑……这些农村的现实景象触动着诗人的感官,然而诗中却没有诗人慨叹、评价之类的主观性文字,而是予以精心地“抛弃”“拣取”,通过特定意象组合,构成了一幅动荡之夜的形象画面。诗人的目的在于通过这幅形象之媒介,传达动荡不安的情绪给读者。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捧读这首诗 ,立即便可以唤起我们对于一个早已逝去的噩梦的回忆,从而使我们倍加珍惜今天平和的生活,并为保护和发展这生活而斗争,这就是诗的力量。
2.无形体的形象创造 ,即诗中呈现的不是可见的具象事物,其诗艺形象是诗人为其激荡于心中、不吐不快的情愫,找到的与之和谐的附着物,是“缘情找景”“缘情造景”的结果。在中国人民遭受“三座大山”沉重压榨的岁月里,诗人看到了人民中潜在的不甘忍受凌辱的反抗力,对祖国的命运满怀着再生的希望。但是,这样的情愫如何通过一个具体可感的形象表现出来呢? 为了找寻这一情愫的外壳,诗人或许曾一度苦恼过,后来,终于在“煤”身上得到了启示,于是,便有了《煤的对话》这样一首优秀诗作:
你从什么时候沉默的?
从恐龙统治了森林的年代
从地壳第一次震动的年代
这是煤的命运,字面的背后显示的却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备受压榨的命运。
你已死在过深的怨愤里了么?
死?不,不,我还活着——
请给我以火,请给我以火!
一旦送来革命的火种,人民这块“煤”就将马上燃烧,这就是诗人的坚定信念。也许正是这种信心,支撑着诗人高唱着《向太阳》《火把》《黎明的通知》,战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行列里。
“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这是一个更为博大宏阔、难以具象把握的对象,诗人却恰到好处地找到了“太阳”这一客观对应物:
当它来时,我听见
冬蛰的虫蛹转动于地下
群众在旷场上高声说话 (《太阳》)
诗人没有正面描写地平线上出现的太阳是多么温暖明亮,却用笔尖挑开地层,写了转动于地下的虫蛹,继而转向广场,写下了群众高声说话的场面。作者似乎在故意绕圈子避开他要讴歌的对象,实际上,这种“避近就远”的手法,恰恰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诗人一味写太阳的温暖明亮,恐怕写上许多也不易准确表达出早春太阳的特征。而通过“冬蛰的虫蛹转动于地下”这样一个典型细节,便可让读者如同亲身经历般感受到早春太阳的热力;通过“群众在旷场上高声说话”的场面,写出了人们迎来早春太阳的兴高采烈的心情,从而形象化地表现了革命事业给人民带来的希望。
如果从艺术手法上分析,这类作品一般是通过象征手法构成的。所以,诸如“黎明”“春”“电”“光”之类因非具象而尤具象征空间的事物,往往被诗人拿来作为寄寓较为复杂情愫的对象。这些事物,因空灵,诗人倒恰可按照自己寓情的需要,进行更为自由的想象创造。这类作品,我们可以《光的赞歌》为代表。
“光”无形无体,嗅不到、抓不着、听不见。“可望而不可即,漫游世界而无形体”,但在诗人的力作《光的赞歌》中,却成为“胸怀坦荡、性格开朗、只知放射、不求报偿、大公无私、照耀四方”的可亲可敬、令人向往的诗化形象。透过诗人形象化的创作,我们看到了“光给我们以热情/创造出不朽的形象”“一切的美都和光在一起”“从不喧嚣、随遇而安/有力量而不剑拔弩张”这样一些“光”的神态特征,以及诗人对历代暴君、奸臣仇恨光、“千方百计想把光监禁”的罪恶之控诉,对光源之一的火被盗出天庭的历史之追溯,我们自然地联想到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不屈不挠的真理之光。正是透过诗人横的细腻刻画和纵的磅礴放歌,光——这一真理的象征,便活灵活现地跃动在我们眼前了。这个形象,无疑凝结了作者对人类社会发展多年的思考和探索,高度概括了人类自有文明史以来,围绕着真理所进行的一次次斗争,揭示了“真理不可战胜”这一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