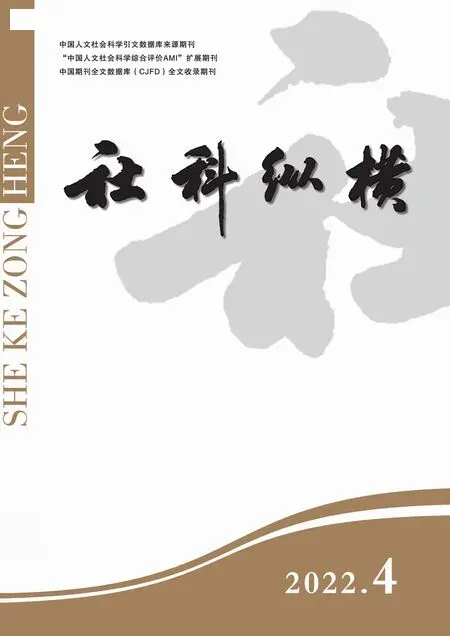纪录片中“自我陈述”和“他者叙事”视角下的中国形象建构和国际传播策略研究
——以纪录片《中国扶贫在路上》和《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为例
2022-09-21超张
韩 超张 琪
(1.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甘肃 兰州730000;2.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甘肃 兰州730000)
一、研究背景
2020年1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8年持续奋斗,我们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在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中,我们采取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积累了很多能推广、可复制的减贫经验,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奋力消除自身贫困的同时,积极主动承担国际减贫责任,履行国际减贫承诺,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代社会传播手段层出不穷,传播方式不断更新,依托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平台传播的纪录片传播形式在知识性、传播性及有效性上几无短板,是我国重点发展的文化传播形式。自2015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后,与脱贫攻坚相关的纪录片不断涌现,与此同时,由央视牵头,相关部门主导与西方国家主流媒体积极合作拍摄了一系列记录中国脱贫攻坚战伟大创举的纪录片,为中国提高国际影响力,提升国际认同感,建立文化和民族自豪感等起到了巨大作用。
现有文献中对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纪录片、国际传播手段及国家形象建构分析较为丰富,但将主题为脱贫攻坚的国内外纪录片做比较分析的相对较少。本文尝试将语言与传播结合起来,以语料分析为主,从“自我陈述”及“他者叙事”的角度出发,以中国脱贫攻坚为主题,对比研究中外不同拍摄团队拍摄制作的纪录片,并具体分析其创作角度、视听表达等表现手法的异同,以期对纪录片题材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有所启示。
二、语料分析:纪录片中的“自我叙述”和“他者陈述”
王庆福和张红玲指出,“基于自我讲述的故事,体现的是民族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由于缺乏了他者的观照,这种自我讲述的中国故事人为地割断了中国和世界的联系,在与外界的交往中,明显不被外界认同……他者讲述是从他者的角度观看自我,由于增加了他者的观照,自我就不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自说自话,而是带有他者评价与他者交往中的自我”。“自我”从讲述者本身出发,以自我认知、自我评价和自我审视的角度进行叙事;“他者”包含两个范畴,作为对立面的“他者”和作为旁观者的“他者”,因此“他者叙事”也对应存在两种情况,即“对立叙事”和“旁观叙事”。
本次研究所选取的纪录片有两部,第一部《中国扶贫在路上》是由中国人民日报社出品的扶贫纪录片,对应的是“自我陈述”下的中国脱贫故事;第二部为《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是由美国PBS公司在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的协助下制作完成的,这部获得美国“电视奥斯卡”泰利奖铜奖的纪录片,由美国导演拍摄,美国专家撰稿、主持,介绍中国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他者叙述”下的中国脱贫故事。本次研究选取两部纪录片的台词进行文本研究,探究在不同叙事视角下的事件选择、内容侧重、叙事角度及目的、语言风格上的特点,为“讲好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策略研究提供文本案例支撑。
(一)事件选择
《中国扶贫在路上》分为《减贫之路》《扶贫智慧》《志启未来》三集。第一集《减贫之路》讲述了中国扶贫第一村、扶贫工作明星村、湖南省花垣县夯来村、宁夏回族自治区闽宁镇、悬崖村的脱贫故事。第二集《扶贫智慧》讲述了贵州省乌蒙山区大方县、至善井计划、宁夏回族自治区南梁村、陕西省乾县、贵州省丹寨县、苗族村落排莫村、云南省芒摆村、沧源佤族自治县的脱贫故事。第三集《志启未来》讲述了河北省滦平县、河南省虞城县韦店集村、海南省琼海市南强村、河北省涞水县三坡镇南峪村、四川省稻城县亚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木垒县、贵州省道真县、四川省青川县、贵州布依族的脱贫故事。《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仅一集,讲述了海南省琼中县岭门村、甘肃省兰州市附近贫困山村、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福海县、山西省吕梁市临县白文镇、四川省屏山县的脱贫故事。
从所选择事件的特点上来看,《中国扶贫在路上》出于文化输出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要求,意在表现一个崛起、富裕、强大、美好的国家[1],旨在增强中国人民实现全面脱贫和共同富裕的决心和信心,因此所选择的案例均为正面案例,没有涉及我国脱贫攻坚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而《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从“他者”的角度观看“自我”,不再避讳可能存在、涉及一些扶贫工作中的问题,比如在介绍四川省屏山县的脱贫故事时,赶赴此地进行扶贫成果和过程第三方评估的重庆西南大学师生就发现贫困人员的建档立卡存在一定问题,有扶贫干部以公谋私的情况。相比于“自我陈述”的《中国扶贫在路上》,作为“他者叙事”的《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则具有某种更强的客观和真实。由于增加“他者”的观照,“自我”就不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自说自话,而是带有他者评价与他者交往中的自我,往往更容易使人信服[2]。
(二)内容侧重
通过词频来分析所选取纪录片的内容侧重,分别将两部纪录片的台词作为两个独立的语料库,利用AntConc语料库分析软件对这两个语料库进行文本分析,可以获得词频表(出现频次由高到低)表1。
根据词频表1的顺序定位字词上下文,经过对比分析可得,在“自我陈述”视角下,纪录片整体叙事是展示型的,着重表现已脱贫群众的亲身经历,介绍具体的脱贫方式;在“他者叙事”视角下,纪录片整体叙事是探究型的,着重阐述脱贫工作流程、脱贫相关干部职能及脱贫成果。

表1
具体而言,《中国扶贫在路上》共有三集,内容更加丰富,从全国近1000个扶贫典型中筛选出21个典型案例,所介绍的脱贫地区从中国南部的海南省琼海市南强村到中国北方的河北省涞水县三坡镇南峪村,从西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木垒县到东部的湖南省花垣县夯来村,跨越十几个省级行政区,可以全面展现中国各个地区的脱贫攻坚事业;从涉及的扶贫领域来看,该纪录片中的案例覆盖产业扶贫、电商扶贫、旅游扶贫、生态扶贫、教育扶贫等各个领域,多维度、多角度阐释中国扶贫给百姓生活带来的巨变。同时,该纪录片所选择的案例更多地表现政府、企业和社会其他力量所形成的合力,更注重宣传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比如展现“万企帮万村”和“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贫困地区结对子”等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的扶贫方法。
相比之下,《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仅有一集,所选择的事件和案例较为有限,仅探访了贵州、甘肃、山西、四川、海南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六个地区的贫困家庭,注重的是少而精,以几个典型案例来展示中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脱贫故事,缺乏全面性,但依然能够大体说明中国扶贫工作的进展。同时,该纪录片更多地介绍扶贫中政府的政策、方法和工作流程,如在介绍山西省吕梁市临县白文镇的脱贫故事时就讲到了中国政府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扶贫的工作布局,还介绍了驻村干部的日常工作,整村搬迁的实施方法、扶贫成果第三方评估等方面,相比《中国扶贫在路上》,其所选取的事件和案例更加直观清楚,对其他国家借鉴我国的脱贫方法和策略有更强的指导意义。
(三)叙事结构
在“自我陈述”视角下,《中国扶贫在路上》全片大多选取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同时结合脱贫群众的第一人称视角,以事情自然发展的时间顺序进行叙事,分别讲述脱贫前、中、后三个阶段的生产生活状况,叙事结构自然流畅;在“他者叙事”视角下,《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全片选取主持人的第一人称进行叙事,以“提出问题(中国脱贫工作是什么)—分析问题(中国如何进行脱贫)—总结问题(中国脱贫事业的意义)”的总分总结构对中国脱贫事业展开讲述,叙事结构清晰简洁。
从叙事结构可见,当叙事主体是“自我”时,叙事特点上更倾向于展现细节,从而丰富观众对纪录片主题的感性认知;当叙事主体是“他者”时,叙事特点上更倾向于展现整体架构,从而使观众建立起对纪录片主题的宏观认知。
(四)语言风格
在“自我陈述”视角下,《中国扶贫在路上》有风格鲜明的中式语言之美,娓娓道来,用词丰富生动,华且有实。例如“拂去岁月的尘埃,有些历史烛照着未来的道路”“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在“他者叙事”视角下,《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语言风格简洁直白,短句多,在修辞方面较为朴素,但不乏严谨。例如“Recently,I've been tracking presidential Xi Jinping's relentless pursuit of poverty alleviation.It's a signature program.He's taking his political capital on its success.”“All across China,almost three million officials have been working on the front lines of rural poverty.”
三、视听语言
(一)镜头语言
1.镜头运用
从镜头运用的角度来看,《中国扶贫在路上》和《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在片头和片尾都采用了大量的空镜头,展现了诸多中国扶贫地区的景物,交代了扶贫工作发生的环境背景以及空间背景。《中国扶贫在路上》中用到了一小部分手持拍摄的镜头,手持拍摄较为灵活,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观感的真实度。而《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则运用了较多篇幅的长镜头,更加便于记录一些细节以及某些特定事件发生的具体过程。通过使用不同的镜头运用方式,我们能够把握纪录片的侧重点以及强调一些细节、过程等。
2.纪录片整体色调
通过对两部纪录片的整体色调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中国扶贫在路上》整体色调属于暖色调,暖色调能够给予观众一种和谐、温暖的感受。相较之下,《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整体色调更加暗淡低沉,偏向于冷色调,容易带给观众一种消极、负面、压抑的感觉。在拍摄纪录片时,我们可以通过调节画面的整体色调来带给观众不同的视觉体验,加深纪录片留给观众的印象。
3.字幕的设计
在片头中,《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采用了说明性字幕,并且是黑色底色加白色文字,陈述中国在2012年及其之后几年的贫困现状,指出了中国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之后,这部纪录片运用了影像配合字幕来介绍中国脱贫攻坚的相关政策。整体来看,这部纪录片字幕设计较为规整,配色也比较暗沉。
《中国扶贫在路上》没有采用旁白或者同期声的字幕。将二者做对比,便能够感受到中国拍摄的纪录片更加让人感到轻松、积极和乐观,而《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则体现出中国脱贫攻坚的局势之严峻,营造出了一种严肃的氛围。
(二)声音语言
1.人的语言
《中国扶贫在路上》邀请了专业的播音员为旁白作配音,在中间穿插的采访视频中,同期人声也清晰标准。《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则大量使用了纪录片的讲述者兼制作人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博士自己的配音以及同期声。在他进行采访时,纪录片中受访者的声音也是不加修饰的同期声,有各地的方言,也有罗伯特自己不熟练的中国话。在人的声音语言方面,两部纪录片各有特色,采用专业播音员配音的中国纪录片更加精致正规,而外国导演拍摄的则更加朴实自然。
2.音响音效
《中国扶贫在路上》部分采用音效,例如在讲述贫困人口脱贫,过上了好日子时,添加了清脆悦耳的鸟叫声;在讲述经过扶贫工作者的努力后,留守儿童终于有学可上时,纪录片的音频中插入了孩子们玩耍嬉闹的声音。《前线有声:中国脱贫攻坚》中全程没有插入特殊音效,不似《中国扶贫在路上》精美生动。
3.音乐
两部纪录片整体音乐的区别从片头便可见一斑。《中国扶贫在路上》采用了快节奏的音乐,给人一种辉煌、宏伟的感觉。而《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的音乐则较为低沉凝重。在之后的内容中,两部纪录片的音乐也与上述规律大致符合。从观众的角度出发,《中国扶贫在路上》会更加让人感觉积极向上,表现人们对于中国的脱贫攻坚事业充满信心以及美好的期许。
4.声画关系
《中国扶贫在路上》大量采用了声画分立的场景,专业的旁白配音使得发声源并不在画面中,给人感觉更加正式、更加官方。《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则更多地运用了声画结合的场景,在更大程度上保留了纪录片的真实性。
(三)拍摄手法
1.主观与客观
任何艺术作品都是艺术家对这个世界的主观表达。真实是纪录片追求的最高目标,立足现实是纪录片最基本的要求。通过比对可以发现两部纪录片都比较客观,《中国扶贫在路上》倾向于展现更加积极的一面,多讲述脱贫攻坚战取得的美好成果;而《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除了展现脱贫攻坚取得的积极成效,也会讲述一些脱贫攻坚的成果并没有受到认可的内容。
2.旁观与介入
《中国扶贫在路上》主要采用了旁观的拍摄手法,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记录一切。《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在部分片段采用介入的拍摄手法,通过询问、采访等形式引导被采访者做出回答,介入相较于旁观也许缺乏一点客观,但是互动性更强。旁观与介入两种拍摄手法各有特色,前者更利于捕捉客观事实,后者则有利于推动本质的解释。
3.拍摄与被拍摄
《中国扶贫在路上》大篇幅采用了平行式拍摄,尽量客观地记录现实,不影响拍摄对象的话语内容及行为方式。通过采用平行式拍摄,能够增强观众对人物以及纪录片中事件的认同感。在《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中,拍摄者采用了合作式拍摄和合一式拍摄方式,在与拍摄对象配合互动的同时也会拍摄一些制作者本人的讲述片段。采用这种拍摄方式,更加易于制作者把控拍摄全局,但这种拍摄方式也存在一些缺点,例如较之于平行式拍摄更加主观,难以带给观众信服感。
四、纪录片国际传播研究:限制因素及应对策略
国际传播是指在民族、国家或其他国际行为主体之间进行的、由政治所规定的、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国际传播与国家利益相关联,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色彩[3]。在现行国际传播体制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国际传播包括跨越国界的各种形式的传播和各种传播形态,例如首脑互访、双边会谈、地区间峰会以及其他相关事务;狭义的国际传播是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例如开设国际广播电台,向其他国家发送广播节目等。由此,不难窥见国际传播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巨大影响力和作用力。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国际传播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国际传播在智能化终端普及的现代信息社会对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维护中国形象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传播好中国理念、智慧、方案,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规制权,已经上升为全局性问题[3]。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从国际舆论格局看,西方话语居强势地位[4]。目前,中国国家实力逐步提升,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定影响力,飞速发展的强劲势头迫使美国发动贸易战、出台禁止出售核心芯片等措施,同时动用大量媒体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中国威胁论”,试图联合他国共同限制中国进一步发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媒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较小,话语权较弱,在澄清谣言、反击舆论方面的软实力、硬设施都有所欠缺。有观点认为,全球90%以上的新闻信息是西方主要媒体提供的。中国国际传播还存在“声音比较小”“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等多重话语困境[4]。例如,2021年3月发生的“新疆棉”事件就是西方媒体影响、控制甚至主导舆论而我国无有效应对手段的典型事件之一。因此,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形成“中国故事,西方讲述”的传播策略,塑造更为中肯、积极的中国形象成了当务之急。而如何全面展现“中国故事”,如何使用更易被接受的“西方讲述”形式,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正确认识和选取中国故事,把握其中体现出来的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二是贴合西方接收信息的习惯,以更易接受的方式进行潜移默化的“浸透式”传播;三是利用政府和相关领域权威人士的公信力,使所传播的内容更具有说服力。
以纪录片为代表的视听作品是世界各国真实、立体、全面了解当代中国的“窗口”[5]。近年来,中国纪录片产业快速发展,制作水平不断提升,选题更加国际化,优质纪录片在海外展播,成为世界认知中国的重要窗口,具有广阔的国际传播前景。中国纪录片虽然在纪录片海外传播力建设上很有增长潜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国际纪录片传播影响力大国相比仍处弱势地位。如何提升中国纪录片的传播效果,成为当前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6]。
文化上,中西方因文化、社会制度等存在差异,认同感不强,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外话语形态。纪录片《中国扶贫在路上》和《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分别由中外不同的团队拍摄,而外方团队拍摄的纪录片在对外宣传时具有一定语言优势。由于纪录片主要背景为中国,拍摄主要对象也多为小人物,所夹杂的方言易造成误解或辨认不清,在翻译上对双方的拍摄团队都具有一定挑战性。传播渠道上,由于西方社会近年来宣传“中国威胁论”,污蔑中国在某些方面压榨人权,企图达到恶化中国形象的目的,因此,反映中国积极发展、巨大变革的纪录片一定程度上在西方遭到抵制。中国纪录片如何登上西方主流媒体并被更多人看到仍然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由于传播力量不对等,当前世界纪录片发展格局中,美国探索频道、国家地理及英国BBC等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纪录片传播与运营模式成为全球纪录片产业化经典范式[6],而中国纪录片在制作方面力量较弱,同时缺乏高精尖人才,加大了对外传播的难度。
综上,在以纪录片为载体向国际进一步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创新传播内容,以西方世界更易接受的创作模式让中国文化“走进”西方世界,体现更大的包容度,在立足于本国事业发展成果的同时也不失国际视野,将纪录片做得“生动”“有趣”“有料”;同时,也应拓展传播渠道,在移动化、社交化、碎片化信息传播浪潮驱动下,我国纪录片的对外传播不再局限于海外主流媒体,而渐渐转向社交平台、视频网站、社区论坛等这些对外传播的优秀阵地[7]。因此,除官方电视频道外也应发掘如TikTok等相关传播平台,制作符合此类传播平台特点的视频并有序投放;除此之外,对传播方面的专业人才建设仍然需要重视,要大力培养及寻找更多有志于国际传播,同时拥有一定国际视野和远见的传播内容发现、制作和执行人。在进行相关工作的同时注重培养其在跨文化传播、受众心理研究等方面有所提升,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输入更多的高端复合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