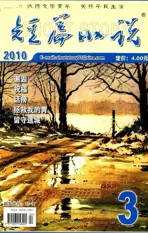那些路过我生命的女人(三章)
2022-09-17◎王晓
◎王 晓

卖鱼女
卖鱼女看起来五十上下,雨衣雨裤全副武装,连雨衣上的帽子也戴上了,雨下得着实不小。她的脸因忙碌而泛红,还有湿头发粘着,乱糟糟的,又是活鲜鲜的。
面前的澡盆里,白鲢、草混居多。几条鳊鱼、鲫鱼点缀,让买鱼人好配菜。腊月,农村人还有腌咸货的习惯。集镇上逢街应该很热闹,遇上雨天人少了一大半,生意相对晴天难做。下雨天,不能外出务工,在家腌腌咸货,弄点吃吃喝喝,正合适。这部分人今天市场居多。
卖鱼女忙得一刻不歇,是这个冷清的农贸市场的亮点。盆里抓白鲢,鱼太大了,卖鱼女左手拿袋子,右手探到鱼的身下,往上一搂,鱼出水了,借着跃起的势儿,完美地滑进塑料袋。卖鱼女的袖子有一小截没入水中。虽然穿了雨衣,套了塑料护袖,护袖的手腕处还有橡皮筋勒口,袖笼里还是会浸水,只是她顾不得了。逢街只有半天,雨天就剩两小时,错过了时候,鱼卖给谁呢。
称重、杀鱼、算账、揽客,她一人包圆。厉害了我的姐!她用的还不是电子秤,是普通秤,一手拎秤杆,一手赶秤砣。三四斤一条的白鲢、七八斤一条的草混,顾客一买都是好几条,装在一只袋子里,几十斤重,鱼又不听话,卖鱼女人一下称准。偶尔有生客怀疑斤两,卖鱼女鼓励验秤。熟客在旁边发声:她的秤你放心。
现在卖鱼,都要代杀。农村集贸也这样。只见她手起棒落,活蹦乱跳的鱼被敲晕不动了。铁钉刷嚓嚓有声刮鱼鳞,腌的鲢子要从背脊上开刀,易于入味和挂晒。她手里两寸宽的小刀应该锋利无比,即便这样,在厚厚的背脊上,从鱼尾开到鱼头还是要一把劲的。一条接一条,没个喘气工夫,半天下来,应该是一场强体力劳动。我这四体不勤的人刚刚只觉得她辛苦,此刻羡慕她生龙活虎。
一男一女在鱼摊前观望,衣着像是刚下工地,像夫妻工,男的做大工,女的打下手。卖鱼女眼尖,熟稔招呼:“叔太爷,下雨天,鱼难卖,帮我带走几条。”那语气,容不得商量。小镇上,熟人熟市,做生意差不多都这样吧。瘦高男人说买条吃吃就够了。矮小女人补充说今天没带多钱。卖鱼女赶忙添上话:“只管把鱼拿家去,两口子出门一天几百块,我还怕你们不把钱?”夫妻俩有点自豪,又有点怕露富,着急辩解:“哪有啊,哪有啊?”语气却是喜滋滋的。买了一条白鲢,又拗不过面子,让卖鱼女抱了两条草青,真的是抱,那鱼有澡盆长,两手相抄,才抱得起来。卖鱼女麻利地敲头、刷鳞、开肚、扒肠子、下鱼头。三条鱼的鱼头都按照夫妻俩的要求下下来。矮小女人说:“好容易歇在家里,买点豆腐炖鱼头汤喝。”犒劳一下肠胃,享受一下口福,他们感谢这下雨天。
有人买三条白鲢,五条草混,还顺带买两条鲫鱼当中饭菜。白鲢四块一斤,草混七块半一斤,鲫鱼呢,九块九一斤。无论买几样,杀鱼的工夫,卖鱼女把鱼钱报得清清楚楚。不同种类,不同价格,不同斤两,我遇上,早晕了。顾客掏钱出来,100、50的大票子,放在卖鱼女眼前过一下真假,确认真钞,放到涂料桶里,自己找零。女汉子一个人做生意嘛,大家都体谅。
在那旁边看久了,我发现卖鱼女的一个秘密。招揽生意时,一视同仁热情。上一个顾客鱼称好了,她不忙杀,将下一个顾客的鱼也称好,放到宰杀台边排队,这样,生意就不会跑到别人家。再忙,卖鱼女刷鱼都一样快,不猛,她说露天地里,不能太用力,出了汗,风一吹,肯定感冒,第二天就卖不了鱼了。
鱼,她已经卖了二十年,还要继续卖下去。择一行,终一生。
女鞋匠
我的玉镯子不小心碰碎了,去玉器店问师傅能不能修补,戴老花镜的玉工无能为力地摇头。我不死心,带到大市口的修鞋摊,遇到女鞋匠,请她帮我用鞋胶试试。她很为这只原本漂亮的镯子可惜,粘的时候特别用心,怕手上的黑灰抹上去,在旧毛巾上左擦右擦,又用小锉子锉平断截面的毛刺,再涂一层琥珀色的胶,握紧固定五六分钟,呵,竟然粘住了!
我问她多少钱,她大方地说算了,下次修鞋再说。我会不会来修鞋,到时候记不记得这情义,她都不计较,挥挥手叫我走。
我再一次见到女鞋匠是在校园里。一大早的校园很喧闹,门口满是家长、孩子,我小心避让着,把车开进去。拐角处,一个女人正和我同事边说话边抹眼泪——一定是不上进或闯祸学生的家长。这一幕在校园内不稀奇。
无暇顾及,匆匆走上四楼,早读的铃声,如约而至。
当女人和同事一起从教室门口经过时,我正站在门口,一照面,才认出是女鞋匠。她看起来装扮过了,头发扎成紧紧的一束,清清爽爽,不像修镯子那天那么蓬乱,或许那天巷口的风太厉害。衣服也特意换的,裤子虽是淘汰的涤纶面料,但裤缝笔直。厚底的凉鞋,明显过时,却衬得那矮小的身躯精神了几分。她把到学校见老师,看得和走亲戚一样隆重。不像这所城乡接合部小学的一些家长,趿拉着拖鞋或者打赤膊就来了。
她也记得我,用带泪痕的微笑和我打招呼。我小心询问:“为孩子来的?”女鞋匠絮絮叨叨地说着儿子不做家庭作业,给老师添麻烦,夹杂着自己的失望和无助,眼里又噙一层水,使劲忍着,不让它落。同事劝她不要急,坏习惯不是一天两天改得了的,晚上回家多督促,多检查,慢慢会好的。女鞋匠说,儿子的作业她撞破头也认不得,只有一张嘴苦口婆心地絮叨。儿子基础差,又贪玩,学习上操不尽的心。她已经准备给儿子请个家教补一补。为了请家教,她多学了几种活:修车,去花店要废弃的芥草编小昆虫,帮别人织毛衣、钩毛线鞋子,这些活没鞋修的时候能见缝插针做,多挣一个是一个。为了儿子,再苦再累,她也受得,只要他争气。
隔壁教室,一张皮猴脸不时探出窗子,朝我们这边张望,有点胆怯,有点慌乱,更多的是懵懂。
织补大师
男人的新T恤,早上穿出去,晚上回来,后背有个绿豆大的洞。看那洞眼,应该是在饭店吃饭,酒多了点,椅子后背拉的。纯棉针织的衣服,300多块买的,后背破了这么一个洞,还怎么穿出去?埋怨男人不爱惜。男人自知理亏,不争辩,说自己不讲究,照穿。他照穿,丢的是他老婆的脸。
记得步行街有个织补摊子,也见过有人送衣服去那里补。我带着洗干净的衣服去试试,看能不能修好。果然,织补大姐还守在摊子那儿。平日里,我没有精致高档的衣服,也不会那么俭省,无须和这个行当打交道,只当街景一样看过。靠近大姐,才发现她肤色黑得发亮,应该是这个巷子风野的缘故。夹在店铺之间的小巷道,夏天风热,冬天风寒,女人哪经得住四季吹。
停下小电驴,拿出男人的T恤,翻到破洞处,问大姐,这个能不能补。自然是能的。不放心又追一句:洞在后背开阔地方,又是浅色的,补了有痕可就丑死了。我对织补没把握。大姐指指身后悬在高处的 “精工织补”牌子,让我放心。问价,这么一点大的洞,竟要45元,着实吓我一跳,一件衣服的六分之一去了,下手太辣了吧。
有点不舒服,觉得织补大姐拿捏我。如果不舍这45元,那么,这几百元的T恤就是一块破抹布,只好补。大姐说可以明天来拿。正好没事,就当花45元看一场织补秀。我很想知道绿豆大的破洞补好,如何就需要六斤猪肉钱。
大姐先用一个小号的绣花绷,将破洞处绷紧。又用细针从T恤下摆里边挑出一根线,又挑出一根线,来回挑了五六根,这就是织补备线。难怪我问她能不能找到与T恤一模一样的线,她让我别烦,保证一个颜色,奥妙在这里。备好了线,大姐眼睛凑在一个带放大镜的架子上,借助放大镜,分辨破洞周边的经纬线,按照纹路,来回织补。针脚伸得很长,在破洞周围一寸左右抓牢,经得住拉拽。从衣服下边抽出的线细如发丝,又是二次利用,大姐在送针拉线时都悠着劲,不敢太用力。
大姐一直专注织补,想问问她从什么地方来,又怎么在我们这个地方站脚,一月收入多少,城管收不收管理费等,人家无暇顾及,那样的姿态,坐禅入定般保持一个多小时。我就坐在对面的小凳上闲看。针线筐边上有个名片盒,捡一张拿过来:织补大师王翠香,有刺绣厂和沿海城市大型制衣厂工作经历,专业织补羊绒衫、羊毛衫、真丝衣物、羽绒服……末了,还有联系电话。与其他名片还有个不同,上面有她自个儿的真人照片,笑容明亮,可亲可信。敢自称大师,工作内容、联系电话一目了然,还以头像展示真诚坦率,女人自我推销的本领比大学营销系毕业生管用。
在我等衣服的当儿,来来回回有五六个人拿着衣物来织补,有新牛仔裤被汗撕炸了,有真丝裙子须边了,也有貂绒大衣蛀了洞……都是扔了可惜,不补又不能穿,和我这件意思一样。虽然现在人买衣服很勤,淘汰快,也有一些因质地或意义,被多次利用。织补的收入,虽饿不着,也撑不死。粗略算一下,等人的时间,织补大师王翠香接下的业务,手工费大概有四五百块,也可能是两天的工作量。
一张小板凳,一个针线盒,一堆衣服,一年四季安静地坐在那里,埋头飞针走线。有人戏称她为织女,蛮好听的,就是不晓得牛郎在何方。还是趁她忙里偷闲了解了一些信息:湖南人,在东北学的织补手艺。跟老乡们到南京谋生活。大城市竞争太激烈,生活成本又太高。偶然的机会来这里,靠技术站住脚,靠脸熟回头客多,舍不得走。牛郎和娃娃们都在老家,她挣的钱大多汇回去,盖房,供娃娃们上学。再苦几年,娃娃们能自食其力就解放了。
大姐说,拿到她这儿来修补的衣裳,要么是上档次的,要么是心爱之物,都是要花心思的。我点头,还惦记着一直没弄明白的收费标准,大姐憨憨一笑,根据织补大概需要的时间来定,不好明码标价,但绝不会欺负人。我的小气被大姐看出来。
也许手中的物件将要修补完工,大姐的紧张有所松弛,话也多了起来。大姐说织补不像家里打补丁,一块布贴在破洞外面,补上就成。织补要根据衣裳本身的纹路,细针细线在破洞周边重织经纬。大姐的话,有点专业性,我似懂非懂。不过她将织补好的T恤往我面前一摊的瞬间,我被镇住了。怎么看都看不出这衣服曾经破过洞,完全是刚买的样子。真是太神奇了!
在我的惊叹声中,大姐露出了自信的笑容。靠技术方便别人,养活家人,织补大姐的幸福稳稳的。连忙掏出50元奉上,大姐要找零,我赶紧摇手,告诉她不用找钱。多给的5元专门表达我对她劳动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