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历史学更重要的意义,是让我们不随便滥用历史
2022-09-09徐鹏远
徐鹏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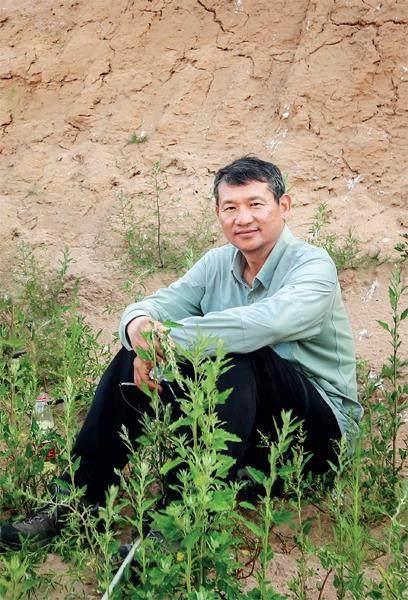
2016年7月,罗新在内蒙。本文图/受访者提供
和罗新见面时,他刚回到北京没几天。过去三个星期,他在四川完成了一趟行走,从广安出发,向西走到都江堰,然后沿着青藏高原板块的山前地带,一路穿行彭州、什邡、绵竹、绵阳。
从年轻时,罗新就喜欢到处走走看看,后来当了老师,便带着学生一起上路。2017年,他花了15天,沿元朝皇帝夏日巡幸的辇路,从北京出发,经龙虎台、过居庸关、行黑谷、越沙岭,徒步450公里抵达了内蒙古锡林郭勒正蓝旗。回来后,他把路上的见闻偶遇、途经之地的历史怀想以及种种探寻与思索,写成了一本《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作品甫一出版,广受赞誉,罗新也就此走入公众视野。那年,他55岁,已在魏晋南北朝史和北方民族史领域耕耘了29载。从1981年开始,他就在北大读书,从本科一路读到博士,从中文系读到历史系。如今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专业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古代民族史。
但这次去四川,罗新没打算写任何东西,他完全是去“追星”的。曾两次获得普利策奖的旅行作家保罗·萨洛佩科,自2013年起与《国家地理》合作“走出伊甸园”徒步项目,从东非出发,穿越中东、中亚和中国,进入西伯利亚,再跨越白令海峡,自北而南穿行美洲大陆,最终到达南美的火地岛。原计划七年完成的行走,因为疫情严重延误,去年4月才进入云南。罗新打一开始就关注着保罗的行程,还翻译了一些他的文章。在云南时,保罗从中国朋友那儿听说这件事,就给罗新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在10月到达北京时见上一面。罗新大喜,不等保罗来京,便借着暑假奔赴四川与他相会。
这是极为愉快而且轻松的一趟旅程,一路上,他只是陪伴和观察,偶尔帮保罗找找路、做做翻译。唯一的不适来自高温,由于常年调研,罗新的夏天基本都是在草原度过的,没有经历过酷暑,因此这次蜀国之行直接把他热蒙了。
暑热面前的“惨败”,或许的确印证着年龄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交谈过程中,罗新不时地就会提起自己对衰退的真切感受,他说那是一种令人灰心的感觉。这也直接影响了他在学术轨迹上的调整,近几年他有意将研究和写作转向公众,他不想再做和个人价值观无关的东西了,更不想到最后有些想说的话没说出来。
于是,在2020年春天的苦闷中,他开始动笔写下自己的第一部历史非虚构作品,关于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这个题目他犹豫了快十年,他想借此为那些历史上的弱者和边缘人发声:“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有很大的系统性缺陷,我们听到的都是胜利者的声音,对普通人没有足够的关注,整个历史呈现着一个不平等的构造。”
对罗新而言,这样的书写是他对历史的一种反抗,同时亦是对现实的一种回应。“我这样的人没有能力参与现实,我能够做的就是到历史当中去,让这样的人物能够站起来,让人们看见他们。这些被看见的历史将是未来我们思考现实时的思想素材。”他说。
用一个狡辩的话来说,我对她的故事知道得很少,所以没法写她,但是我知道影响她命运的因素是什么,我可以用很多笔墨把这个因素一点一点阐述清楚。我承认这是狡辩,(因為)即使影响我们命运的因素就是那几条,每一个人的反应却是不一样的,我们还是能够创造自己的空间的,这才是我关注的部分,但是我的确没有材料写。所以我犹豫了差不多十年,犹豫来犹豫去最后还是把它写出来了,这个缺陷当然是明显的,没有办法,这是永恒的遗憾。
写作计划的时间很长,真正有动力写是到了2020年春天,那个春天我们看到了那么多具体的人的苦难、彷徨、困惑,我也没什么能做的事情,(虽然)不知道怎么写,但做一点是一点、做到哪是哪吧。写了一点之后就忙别的事情了,一直到今年春节期间终于抽时间把它写完了。
写法上倒没有怎么考虑过,说实话这书的写作难度不大,资料也不多,需要处理的特别的史料很少,故事性也不强,线索清晰。寻找表达形式的难度也不是很大,远不如我写其他的东西。
我不敢说是贡献,只是想说我终于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其中主要是讨论佛教给中古早期的信仰者——特别是佛教的专职人员比丘尼——带来了哪些新的社会活动空间、精神空间,也就是说佛教给哪些人带来了什么样的自由和解放,又在什么程度上可能帮助了佛教在中国的大流行。我不是做宗教社会史的,我没有资格说这个话,但是我的确从我写的具体人物身上感觉到了这一点。希望将来有比我能力强得多的年轻学者能够沿着这个问题做下去,或者至少批判我也是有意义的。
很多朋友都做了(《漫长的余生》和《王氏之死》)这个比较。如果只是从写非常具体的人这个角度,是有可比较的地方。但是也有不好比较的地方,就是他写得更微观,我想写得微观可是做不到。我写的是一个中时段的观察,而他就集中在两三年,所以他的可读性更高,这是没有疑问的,写得越微观读起来越有意思。
史景迁毫无疑问有很大的价值,他让我们知道历史写作的另一个方向——我们不一定非得关心朝堂上发生了什么,还要关心真实的世界。《王氏之死》很漂亮的地方是,它处理的材料要用英文表达,据说还是用古英语翻译的,译文水平很高。
至于材料上的问题,《王氏之死》也好,他后来的一系列著作也好,我认为他是没有办法的——连他写的明清都存在材料问题,可以想象写唐代之前得有多难。我倒是觉得他使用材料的手段是很高明的,《王氏之死》里用《聊斋志异》是当作间接材料使用的,用来烘托气氛、描述细节,这是可以的,因为虽然是文学材料,但是那个时代的人写的。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用虚构材料,只要是那个时代的东西,也没有关系,它多多少少比我们今天的想象要更接近那个时代。
罗新: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们换一个表达方式来说这个问题,你写历史非虚构是为了什么?写皇帝也好,写宫女也好,它的意义不应该是在故事本身,而是故事背后蕴含着什么意义。意义是很重要的,历史学不是文学,没法追求文学创作那种形象生动,做不到的,一定要有意义才值得写。比如,从王钟儿的眼光看这个世界,和从皇帝的眼光看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
人们喜欢说历史学是追求历史真相的,这不是没有道理,但不是道理的全部。
人类的思维特征是一种历史性思维,我们喜欢拿过去发生的事情当作思想素材,来讨论现在的问题、将来的问题。这个过程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使用历史,因此如何正确使用历史,就是历史学的主要目标。所以对我来说,历史学更重要的是对人的健康、理性思维的训练,训练的结果是让我们不随便滥用历史。
我这样没有思想深度但是还楞头青在说的人被赞许了。我其实说不出什么有分量的话,无非不愿意撒谎。
叛逆的一面有没有个人性格或者个人成长背景,我自己没有能力来做这个诊断。但是我觉得,追求真理就是一个叛逆过程,就是对已有的说法发出否定。真实的知识创造一定是叛逆的,也一定在一开始是不被欢迎的。那些一上来就受欢迎、被热议的,最终都会消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也不需要担心没有人承认我的成就。
我也没什么成就,我只是不想说那些人云亦云的话,不想走那些大家都去走的路。比如我写《从大都到上都》,旅程一共450公里,其中有300公里在长城地带,不可避免地要写长城。我就避免写长城里边的明朝将士怎么样、外边的蒙古人怎么样,我想反过来写长城里边的蒙古人和长城外边的汉人,我想至少提供给读者一个不一样的长城景观——它分开的是两个政治体,不是两个民族——这才是历史事实。
我认为学术应该是每个人做每个人特色的事情,不应该热热闹闹的。固然一个时期有一些话题是众多人关注的,但是处理这些话题的方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我最近有一个说法——Diversity is the only truth,多样性是唯一真理。
在我们的生活经历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多数至上、个别人牺牲。一旦你发现你自己就是那个牺牲、那个代价的时候,你会开始尊重这些代價,你想替这些代价说几句话。我们的牺牲将会是一个永远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让这些人白白牺牲,不能让他们在现实当中已经付出了代价,然后在历史上付出更大的代价——那就是他们没有声音。这是最大的不公。
这是我们对现实的观察,这个观察刺激着我去看历史。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有很大的系统性缺陷,我们听到的都是胜利者的声音,没有那些代价的声音,我们对普通人没有足够的关注,整个历史呈现着一个不平等的构造。所以我们如何反对现实,我们就要如何到历史当中去反对历史。
我这样的人没有能力参与现实,我能够做的就是到历史当中去,让这样的人物能够站起来,让人们看见他们。这些被看见的历史将是未来我们思考现实时的思想素材。我不知道历史学家做这些工作对现实的人们有多大的帮助,也许帮助很小,但即使很小也是有意义的。
(启蒙的使命感)我年轻的时候有,现在最大的期望是满足内心的需要,我内心从这儿可以得到一定的和平。
我没有放弃,但是我知道那个不是那么简单容易。而且那个时候你不知道该做什么,现在我知道该做什么了。年轻的时候觉得书呆子才做学问,我要改造世界,经过很多年的摸爬滚打、跌跌撞撞之后,我知道我没有改造世界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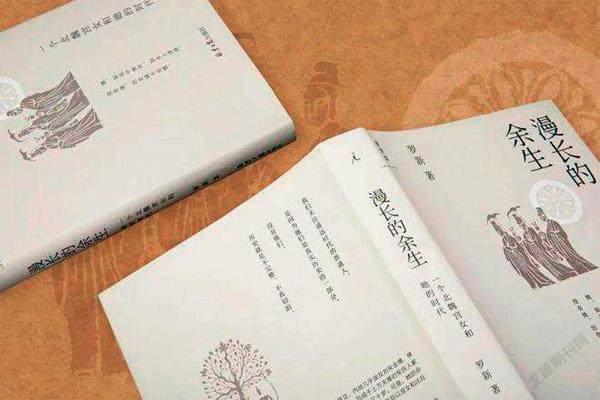
罗新作品《漫长的余生》。
对,是主动的。因为我今年59岁了,已经到了一个专业学者的学术生涯后期,要么总结自己过去的工作,要么转型做一些新的领域的工作——我现在还在这个挣扎当中。
我有的。首先记忆力不如以前,我过去看书不喜欢写笔记,因为都记得,现在被迫学习记笔记,回头看笔记再去书里找。然后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不如以前,害怕新的东西,当年从来没玩过电脑,拿个电脑就开始钻研怎么回事,有极大的热情,现在手机复杂一点都搞不动。
会有灰心的感觉。
那时网络刚刚出现,我的确活跃过几年,其实也不年轻,快40岁了。
如果不考虑更大的环境因素的话,(变化)归根结底取决于参与网络生态的人。90年代后期、21世纪初期,网络上大概没有中学生,大学生也不多,主要是各种专业人士,为了在自己的专业之外寻找一个说话的空间。这些人还是比较成熟的。
我一向不赞成这种判断。积极说话的就是那些人,就像在课堂上积极发言的永远是那几个人,这几个人代表不了一个班。
中国新闻周刊:你现在对研究和写作抱有一种什么样的期待?更偏重于学术价值还是公共价值?
我觉得两者都会有。因为年纪越大越对个人的东西感兴趣,我不希望死之前有些想说的话没说出来,想写的东西没写出来。但我毕竟是一个学者,不希望我死之后,别人不承认我是一个学者,所以当然还想在学术上做一点事情。
我不想再做和我个人的价值观无关的东西了,我要让学术为我的价值观服务,不是为学术而学术。我年轻的时候有过为学术而学术的阶段,那个时候非常强烈地批判80年代的那种学术,认为学术不应该是为启蒙。和90年代中期的环境也有关系,那个时候人们觉得做学问没什么用,也不挣钱,穷得要命,可能有那种叛逆,我就是为学术不为别的,能够这样活着我很高兴。现在不这样想了,我要选择那些和我的生命有更多关联的东西。
我那时候在中文系只想着写小说,没有参与到思想、文化启蒙的运动当中,我虽然经历过80年代,但是那时我对于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兴趣。我真正开始理解80年代是到了90年代。我到现在也是这样,总是和主流保持一点距离。
是的,我的确是。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我这样没有思想深度但是还楞头青在说的人被赞许了。我其实说不出什么有分量的话,无非不愿意撒谎。这绝不是谦虚,必须看到这一点,我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是自欺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