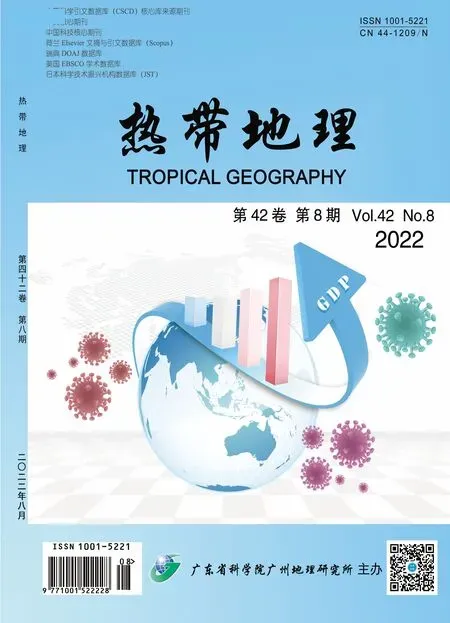“家”“业”可否兼得: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研究
2022-08-29谢永飞林莉华
谢永飞,梁 波,林莉华
(1. 南昌大学社会学系,南昌 330031;2. 江西财经大学社会学系,南昌 330032)
近年来,农民工回流现象已经成为学界和政策领域关注的重要议题。总体上,既有研究主要从宏观的结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国家战略)(蔡昉,2001;王爱华,2019)、成本-收益(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生活成本、就业机会)(Zhao,1994)、人力资本(牛建林,2015)和社会资本(刘茜等,2013)视角对农民工回流问题进行分析。较少文献从农民工个体心理决策角度出发,对农民工回流意愿、回流决策等进行深度的观察和分析,因而未能洞悉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形成过程和机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和“业”是外出农民工心目中难以兼得的文化观念及现实选择。因此,在大量关于农民工议题的研究中,呈现的是同质化的个体为了生存、就业而背井离乡,舍“家”外出;多数话语描述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艰辛和不易,以及“家庭分离式外出”对其故土旧“家”带来的影响(刘传江,2004;刘红升等,2021)。尽管20 世纪80―90年代,乡镇企业“昙花一现”式的发展曾经为研究者们(如费孝通)构想“离土不离乡”“进厂不离家”的理想型生活与工作模式提供了某种可能(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课题组,1984),但后来市场化与全球化的浪潮还是不断地把一代又一代、一群又一群的农民工卷入城市、工厂中(叶敬忠等,2018;段成荣等,2020)。然而,2008年前后,伴随着全球化钟摆的“回动”(吴淑凤,2015)、城市经济和制造业的转型发展(吴艳文等,2019),农民工对“家”和“业”的兼容式诉求变得更加强烈(黄庆玲等,2013)。由此出现了2种流动意愿及流动模式的选择:一种是农民工把家庭带到流入地城市,实现整体迁移;另一种是农民工离开打工的城市,选择向家乡回流,并在家乡就业或创业。本研究关注后一种现象,重点考察青年农民工的回流意愿。
国外从20 世纪60 年代起就有学者对移民的回流问题进行研究,并且形成了新古典经济理论、新迁移经济理论、结构主义理论、跨国主义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生命周期理论、生命历程理论等诸多视角,对移民的回流意愿和回流行为进行解释(Cerase,1974;Massey,1990;Davies et al.,1991;Cassarino,2004;Bettin et al.,2018)。与国外相比,中国农民工的回流研究起步较晚,但目前在回流意愿和回流行为的现状特征、影响因素和影响效应等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由于大部分农民工为青壮年劳动力,因此青年农民工是农民工流动大潮中的重要群体(李振刚等,2019;刘五景等,2019)。青年农民工有宽泛的内涵和外延,包括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第二代农民工等(杨菊华等,2016),其流动受到人口学、社会学、地理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关注,并成为研究热点。其中,研究的重点和争论的焦点之一是青年农民工的出路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学界存在2种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和解决方案,即城市融入抑或还乡调适(张星,2012)。从文献数量看,前者占据了青年农民工研究的主流,后者则相对较少,这与学者们普遍认为青年农民工希望融入城市生活有关(张星,2012)。青年农民工是理性的行动者(潘华,2013),回流到家乡发展的意愿不强烈(沈鑫等,2016)。但流入地的生活成本高、房价贵、工作机会减少,以及部分城市实施的对农民工不友好的政策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青年农民工回流(姚俊,2010;Mohabir et al.,2017);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等政策的实施,也增强了流出地对青年农民工回流的“拉力”(罗小龙 等,2020;戚学祥,2020;谢永飞等,2020)。从家庭因素看,配偶在老家的青年农民工,其回流意愿强于配偶在流入地或没有留守配偶者(郑文杰等,2015);孩子的居住地点也影响农民工的回流意愿(Piotrowski et al.,2013),老家有未成年留守子女的农民工选择回流的概率更高(任远等,2017),这表明留守家人会影响农民工的回流决策(Constant et al.,2002;张丽琼等,2016)。换言之,对家人的依恋和家庭责任是促使农民工回流的重要原因之一(Wang et al.,2006)。从个体因素看,流入地的月平均收入对青年农民工的回流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郑文杰等,2015);女性青年农民工的回流意愿比男性青年农民工强(徐家鹏,2014);在流入地的居住时间越长,他们回流的概率越低(喻贞,2016);教育程度越高,其回流的意愿越弱(程晗蓓等,2020);和中老年农民工相比,青年农民工回流的意愿更弱(余运江等,2014)。此外,回流意愿也受到对家乡的主观依恋、乡土情结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因此青年农民工的回流决策是有限理性(张蕾等,2012)。
综上所述,青年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和回流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已有研究对其深层次因素尚未给出确定性的回答,尤其是作为文化意义上的“家”和“业”的观念因素,这不利于精准理解和把握这一重要社会现象。因此,本研究基于个体心理决策视角,尝试揭示“家”的观念如何触发青年农民工的回流意愿以及分析“业”的想象如何强化青年农民工的回流意愿,以期深化和推进回流意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1 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1.1 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分析框架
中国的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家庭关系等虽然发生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但作为“文化-心理结构”的“家”没有被根本撼动,依然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因此,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家”有理由成为看待和解释诸多社会变迁、社会现象的一个关键切入点(肖瑛,2020)。“家”在中国文化中,不仅指住所,还指亲属关系以及被赋予的情感意义,并和“根”“起源之地”紧密相关(Su,2014)。为此,“家”是物质、社会和情感空间的综合体(Hazel, 2014)。在中国当前语境下,以城市/农村、本地人/农民工为基础的二元结构,更能反映和影响“家”的体验(封丹等,2015)①与中国农民工对“家”的理解不同,国外移民往往赋予“家”不断转换和流动的意义,在新的地方,家里的装饰或制度性的社交组织成为他们重构“家”的方式(封丹等,2015)。。为此,本研究尝试分析文化意义上的“家”对当代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其中,结婚生子(新的人生节点)、承担家庭责任、促进家庭良好发展是青年农民工重要的生命历程事件和使命,并作为“家”的构成内涵对其回流意愿产生影响②尽管有部分国内研究也涉及家庭因素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但并没有把“家”作为分析这一问题的核心自变量,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没有把家的内涵升华到韦伯意义上或传统中国伦理中的“家”的层次,只是把“家”作为一个现代性意义上的结构因素。。
“业”是影响青年农民工流动的重要因素。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工资差异,以及迁入地更高的预期收入是驱使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Todaro,1969)。为此,对于已发生迁移行为的移民而言,其通常是在比较成本和效益之后做出在迁入地居住或回流的决策(Sjaastad,1962;Todaro,1976)。就回流而言,只有当移民因失业、工资低于预期或心理成本过高等原因导致预期收入目标未能实现时才会发生(Constant et al.,2002)。与之类似,中国早期一代农民工(尤其是中老年农民工)的回流就多属于新古典经济理论所言的被动型回流。同时,他们回流后就业和创业机会有限,“业”很难得到发展,回流就意味着舍“业”,“家”“业”难以兼得。但近年来,伴随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在就业机会、工资收入、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等方面有了明显改善,这为青年农民工回流后“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贺小丹等,2021),使其可以结合自身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情况,主动选择能够实现自我发展的“业”(文丰安,2021),为其实现“家”“业”兼得奠定良好的基础,这将增强青年农民工的回流意愿(李明奇,2018)。
概括而言,流出地的“家”和“业”共同作用,有利于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生成。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成家立业,“家”“业”兼得是每一个青年农民工孜孜以求的质朴梦想和美好愿景。“家”虽然会触发青年农民工的回流意愿,但其影响还需要“业”的强化。本研究中,“家”和“业”影响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分析框架见图1所示。

图1 “家”和“业”影响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分析框架Fig.1 The mechanism of"home"and"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affecting return migration intentions of young migrants
1.2 研究方法
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其中定量数据来自国家卫健委组织实施的在流入地开展的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③数据申请网址:www.chinaldrk.org.cn。,样本量为169 000 人。从年龄、流动原因、户口性质、流出区域等方面对样本进行筛选,选择流动原因为务工经商,户口性质为农业户口,流出区域为中西部地区且跨省流动到东部地区或省内跨县/市流动的青年农民工;参考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对青年年龄上限的设置,将青年农民工的年龄范围设定为15~44岁。青年农民工的样本量为26 568人,包括有回流意愿、没有回流意愿和回流意愿不明朗3个群体。调查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方法进行抽样,因此结果具有代表性。并于2020 年12月至2021年1月开展个案访谈,访谈对象为户籍在中西部地区的外出和回流青年农民工。共访谈了12个个案,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见表1。本研究重点考察回流意愿,同时访谈未回流者和已回流者,是出于以下考虑:第一,通过访谈这两部分人群,能弥补相关文献主要关注未回流者回流意愿的不足;第二,对于已回流的青年农民工,他们的回流意愿是真实的,可使研究更有效度。
定量分析中,多分类Logistic 回归模型的因变量为青年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即中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在流入地居住时间≥1个月后,对打算在该地长期居住(>5 a)还是回流(到户籍所在省的县/区、乡镇、原居地)这一问题上的愿望和想法。换言之,本研究所指的回流意愿不仅指回到流出地村庄,还包括文化意义上的家乡(以县/区为一个文化单位)。回流意愿使用调查问卷的Q305 题进行测量,将4个答案选项合并为3个类别并重新编码,1代表回流、2 代表没想好、3 代表在流入地长期居住。模型的主要自变量为“家”,用3个留守家人变量(留守配偶、留守子女、留守父母)进行测量(附表1),另一个主要自变量为“业”,即青年农民工的就业和创业。由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没有涉及流出地就业和创业的相关问题,故使用个案访谈资料进行定性分析。

表1 个案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dividual interviewees

附表1 (问卷调查数据)样本的变量分布与定义Table S1 (Questionnaire data) the defini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variable
2 “家”的观念对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触发
2.1 新的人生节点
青年农民工处于婚育年龄阶段,结婚生子是一部分人计划中或进行中的事,这是触发其回流意愿的关键节点。一位从河南开封市兰考县到河北唐山市玉田县务工,但现在已回流到家乡的机械维修工人(男,23岁,编号DHL3)认为自己就是因为结婚而回流:“回到家的原因就是结婚。以后就不出去,就定在家里了。结婚了,有孩子了,让他有一点父爱,暂定开封了。感觉离家近,工资还可以,有休班的时候还可以领着老婆孩子出去溜达。”青年农民工对即将到来的新的家庭生活充满了期待和畅想,也重视对配偶和子女的陪伴。因此,当青年农民工在流出地和流入地的收入水平相当时,这种“家”的观念更能牵引他们回到流出地定居。
青年农民工在何时选择回流成家受到传统观念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子女在完成学业、开始工作后就可以谈婚论嫁了。即便这种观念在教育水平提高和现代化理念的冲击下有所弱化,但青年农民工的时间规划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其影响,在30岁之前成家的想法更容易被其家庭成员接受。一位从江西赣州市章贡区到上海徐汇区务工的医疗美容顾问(女,26 岁,编号CWC28)表示回老家结婚生子是大家公认的“理所应当”的事情:“我计划后年回去,估计过两年左右,家里人也要我回去。(身边回流的人)蛮多的。我们一块出来的同学,大部分都已经回老家去了。大家都是因为家里催,家里的思想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就应该按部就班,结婚生小孩。再过一段时间可能会绷不住,到了年纪应该要回家,就听家里人的,根据这种观念来。”
无论是哪种现实条件或思想观念在起作用,在组建新家庭这一人生节点上,青年农民工有一颗在大城市闯荡的心,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能够在流入地安家(郭庆,2020),既改善生活环境,也为了给子女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但来自中西部农村地区的部分青年农民工并没有丰厚的家庭资本,刚出社会也不具备充足的收入积累,现实条件仅能支持他们自己或和配偶一起在流入地“过得还行”,举家流动仍是不现实的做法。因此,对这部分青年农民工而言,由于工作年限较短,在“业”方面的发展还不成熟,资金积累不足,相较于在流入地成家,他们的回流意愿更强。
2.2 具有挑战性的家庭责任
大部分已婚且非举家流动的青年农民工期望实现“家”“业”兼得,一方面想趁年轻赚取更多的收入,另一方面又希望与配偶团聚,抚育年幼的孩子和照顾年迈的父母。但对一些青年农民工来说,由于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持其在流入地同时实现这2个目标,此时留守家人将显著增强他们的回流意愿。为准确理解留守家人对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程度,基于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以在流入地长期居住的青年农民工为参照组,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发现有留守配偶青年农民工回流的概率是没有留守配偶青年农民工的1.49倍;有留守子女青年农民工回流的概率是没有留守子女青年农民工的2.11倍;有留守父母青年农民工回流的概率是没有留守父母青年农民工的1.44倍(表2)。留守配偶、子女和父母是青年农民工的重要家庭成员,这表明留守家人是吸引其回流的重要拉力,与留守家人团聚的情感需求以及照看留守子女和留守老人的现实需要会触发青年农民工的回流意愿。

表2 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多分类Logistic模型分析结果Table 2 Analysis results of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on return migration intentions of young migrants
访谈发现,留守父母对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程度因父母的年龄和身体状况而异,其中,高龄和身体状况特殊的父母影响最大。如果父母的日常生活需要子女照顾,青年农民工就不得不更改计划提前回流,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回流选择多是在他们的职业规划预期之外。虽然没有周密规划回流后的工作和生活,但随着流出地经济水平的提高,青年农民工可凭借自身能力开展新的就业或创业。因此,回流后的他们在发展事业的同时,也能照顾到家庭成员,能够实现在流入地不能达成的“家”“业”兼得目标。一位从新疆喀什市疏勒县到江苏南京市建邺区务工,但现已回流到家乡的司机(男,25岁,编号RHL12)为照顾父母放弃了在外发展的机会:“我是2017 年返回到老家,再也没外出过。当时返回老家是因为弟弟上了大学,父亲得了重病,母亲一个人忙不过来家里家外的事情,因此回来老家,一边照顾父母,一边在老家这边发展。”
同时,留守子女也是吸引青年农民工回流的重要因素。与中老年农民工顺其自然、无可奈何的“家”“业”分离观念相比,青年农民工更重视对子女的陪伴和教育。他们大多选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陪伴孩子,要么将孩子带到流入地一起生活,要么在合适的时机回流。从访谈中发现,为了使家庭资源能支持子女获得长远的教育,部分青年农民工有比较强烈的回流意愿或已经回流到家乡。一位从湖北利川市到浙江绍兴市务工,但现已回流到家乡的自由职业者(女,35岁,编号EHL23)因放心不下留守在老家的孩子而选择了回流:“我是2015 年初(回来的),就是回来带细娃。(之前孩子)和她奶奶待在一起,那时候她还小,才两三岁。父母出去不回来的话,久了关系会生疏。我觉得这种家庭分离还是不太好,细娃还小,分开的话对她的成长和教育都不好。”
此外,现仍在流入地的青年农民工了解到流出地良好的发展后,也愿意选择主动回流以实现“家”“业”兼得。经济收入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最突出的差距,也是吸引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外出的最重要因素(喻贞,2016)。而现在,经济收入在地区之间的差距得到一定程度的缩小,其他方面的差距却逐渐凸显,如流入地高昂的房价、较高的生活成本、有限的发展空间等降低了青年农民工在流入地定居的可能性,中西部地区二三线城市的兴起则为其提供了回流发展的新思路。一位从安徽铜陵市枞阳县到上海浦东新区务工的外卖员(男,35岁,编号BWC26)认为自己想陪在父母和孩子身边,而家乡现在的发展足以支持自己回流就业或创业:“目前孩子都在老家,所以还是希望回老家,父母(也)都在老家。因为父母和孩子是自己的一个中心,所以说(对我的回流选择)影响很大。近两年(打算回流)。因为家乡发展越来越好,发展机遇也很多,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便于照顾父母和子女。”即使这部分青年农民工回流到家乡后“业”的地点和“家”的位置具有一定的空间距离,但由于县域内的地理空间范围不大、交通比较便利,青年农民工及其留守家人可以选择在周末或其他休息时间实现家庭团聚,完成养育子女和照料老人的任务,家庭功能的正常发挥可大大地解决因家庭成员长时间和长距离分离而产生的留守家庭问题。可见,流出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将成为影响非举家流动青年农民工能否实现“家”“业”兼得的关键性因素。如果流出地经济发展取得比较明显的进步,能为其提供就近就业或创业的客观条件,他们的回流意愿就会在“业”的强化下更为强烈,“家”“业”兼得可实现良好发展;反之,如果流出地的经济发展缓慢甚至没有明显的改变,非举家流动青年农民工就只能在流入地择“业”舍“家”或回流到流出地择“家”舍“业”,难以实现“家”“业”兼得的愿景。
2.3 规划中的家庭发展
部分青年农民工会考虑回流后是否有助于家庭的良好发展,他们对回流持积极态度,且制定了一定时期内的回流计划。青年农民工对家庭良好发展的考量较为长远,既有应对因工作转变带来短时间内家庭经济收入变化的心理准备,也有未来成家后新家庭的发展方向、子女的生活条件和教育环境的改善措施。当青年农民工的计划做得细致、长远时,他们的回流意愿会更加强烈,但回流行为不会马上发生,而是继续在流入地工作,积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增加一些回流的“底气”。一位从江西宜春市袁州区到浙江杭州市江干区钱塘新区务工的房地产销售员(女,24岁,编号CWC18)认为,有一定的资金积累后再回流对家庭未来的发展更好:“(我)可能在三五年后回去。原因是想拥有一定的资源、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再回去。我想跟家里人在一起,我比较倾向于家庭这一块。加上未来考虑子女教育的话,也觉得要离小孩近一点。”
综上,“家”的文化观念对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结婚生子等新的人生节点、陪伴和照顾留守家人等家庭责任方面,还体现在规划和促进家庭的良好发展方面。但“家”的文化观念对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触发作用离不开流出地就业和创业环境的优化。
3 “业”的想象对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强化
相比于“家”对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触发机制,流出地(家乡)充满希望的“业”对其回流意愿具有明显的强化作用。随着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国家政策的深层次推进,流出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提高,为青年农民工回流就业和创业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谢永飞等,2018;侯中太,2019)。这使得青年农民工即便离开经济发达的流入地,也能在流出地找到合适的非农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王爱华,2019)。同时,在流入地的工作和生活经历有利于激发青年农民工的就业和创业想法,为其回流后“业”的决策提供指导。因此,当家庭因素触发青年农民工的回流意愿时,有计划的就业和创业想法能促使其回流意愿转变为实际的回流行为,帮助他们在流出地实现“家”“业”兼得的良好发展。
3.1 回流就业
部分中老年农民工对待工作岗位更偏向于稳妥和谨慎,因为年龄和身体状况的限制,他们将回流时间定在了退休时,回流是为了养老而不是再就业。但青年农民工不同,他们在就业市场中是一支年轻的力量,他们为自己的职业规划添加了许多可能性,也接受回流后在就业方面的机遇和挑战。
3.1.1 选择新的就业地点 面对流入地复杂多变的就业环境和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青年农民工同时承担着身体和心理压力,这时流出地较为和缓的工作环境会成为其新的就业选择,加之回流后他们与家庭成员能形成一种互相支持的和谐氛围,对其回流意愿起积极的影响。不少受访者表示流出地的工作和家庭氛围更能使自己感受到生活的乐趣,一位从河南济源市到江苏南京市务工的翻译员(女,22岁,编号DWC44)表示,回到家乡做自己真正想做的工作会感觉更轻松:“我目前打算回老家。原因就是离爸妈比较近,离好多朋友也比较近,有家人和朋友在身边。我在外面务工已经一年半了,感觉不是特别舒服,就是心累,不是身体上的累,所以想回去。我还是考编吧,想做一个英语老师,感觉做老师是个比较有成就感的事情。”
非举家流动、外出工作时间短、经济条件一般的青年农民工对流出地的感情归属远超流入地,在流出地的合适就业机会将显著增强其回流意愿,促使其回到流出地。这是因为大部分青年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时间较短,对流入地的感情不深,反而更依恋有家人在的流出地。并且,经济发达地区的竞争愈发激烈,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相对安逸舒适的环境形成鲜明对比。青年农民工在两地之间流动,较大的心理落差会动摇其外出的想法,如果流出地有比较合适的就业机会,他们的回流意愿更有可能发展为回流行为。但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导致两地之间的职业差别比较明显,从事普通职业(诸如中低端的商业服务业、制造业等)的青年农民工因可以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而做出回流选择,而教育水平较高、职业发展前景较好的青年农民工则难以在流出地找到同等的替代岗位,因而其回流意愿较弱。
3.1.2 渴望好的就业条件 无法否认的是,并不是每一位选择回流的青年农民工都是“衣锦还乡”,其中也不乏因无法继续忍受流入地工作条件而回流的。他们或是从事中低端职业,工作环境和工资水平一般;或是个人境遇不顺,发展空间不大,希望回流后重新从事一份条件更好的工作。即使是在经济发达的流入地,较差的工作环境也会劝退一些青年农民工。对于具有长期就业规划的青年农民工,工作环境是必须考虑的。但好的待遇与好的工作紧密关联,部分青年农民工在流入地从事的是中低端职业,不仅工作环境差,而且工资待遇不高,使得他们很难改善生活境遇。因此,流入地的就业机会对这部分青年农民工来说如同鸡肋,当流出地有相似的职业选择时,他们出于长远考虑会有比较强烈的回流意愿。一位从宁夏中卫市海原县到宁夏银川市务工但现已回流到家乡的个体户(男,41岁,编号QHL15)这样说:“我大概是2011或者是2012年左右(回流的),在那儿打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也没有什么生意。村里的年轻人几乎都去那儿做生意,而且活儿又累又脏,当然也挣不了多少钱。回流比较好一点,这样自己也有了一个像样的工作,收入相对来说高一点儿,也和家人能够长时间的接触。身边有好多人是干同一行的,所以一切都比较好,有共同话题,也可以一起合作。”
简言之,青年农民工在追求相对较高经济收入的同时,也会关注所从事职业的工作条件和未来发展空间。由于年龄优势所带来职业选择的灵活性、职业的可替代性以及相对较小的工资水平差异,部分教育程度较低、工作年限较短、从事中低端职业的青年农民工会更倾向于回流就业,借助家庭和家乡的资源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和职业发展。
3.2 回流创业
虽然流入地的经济发展比流出地发达,但对缺少资源、基础薄弱的青年农民工而言,流入地可以是一个好的就业空间,却很难是一个可以留下来创业的理想环境。为此,部分青年农民工选择回流到家乡创业。
3.2.1 寻找独特的创业资源 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发展,经济发达地区的自然资源成本远高于经济较为落后地区,尤其是土地资源。出身于农村的青年农民工尽管很少再选择从事传统农业生产,但在创业方向的选择上仍会优先考虑养殖、种植等现代化农业,流出地的资源优势在此时就凸显出来了。一位从安徽合肥市巢湖市到江苏苏州市吴中区务工,但现已回流到家乡的个体户(男,39岁,编号BHL5)表示流出地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供自己创业使用:“(我)2014年回来的。我们做生物这方面,自己创业比给别人打工要好一点。东部那边的市场有一个问题,我没有大片的土地,但我需要大片的土地。做农副产品肯定需要大片的土地来进行种植,要有合作的地方,你看安徽这边有白湖农场,安庆有九成农场,他们都是国有企业,可以做这个方面。”
除无法替代的自然资源外,特色的人文资源也是青年农民工回流后可利用的创业资源。中西部地区是中国许多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悠久的中华民族文明和少数民族文化,在提倡文化多样性的今天成为独特的创业优势。与现代化农业相比,依托特殊人文资源创业所需的经济积累和技术支持更少,这减轻了青年农民工的创业压力。同时,青年农民工在流入地有机会接触流出地缺乏的经营方式和宣传方法,也能将流入地人际关系网络转化为回流创业的潜在市场,这是回流创业的青年农民工优于没有外出务工经历创业者的地方。当青年农民工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创业想法时,他们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综合分析会更加全面和精准,“业”对其回流意愿和回流行为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家”“业”兼得更有可能实现。
3.2.2 改变旧的发展路径 与渴望好的工作条件而回流就业相类似的是,青年农民工也会因为在流入地漂泊不定、身心受限却只能拿到不高的工资而萌发回流创业的念头。首先,在流出地经营一个“小本生意”,除去生活成本以外,青年农民工能获得比在流入地就业更高的经济收入。问卷调查显示,打算回流者的平均月收入为3 490.51元,而从访谈中了解到,在中西部地区从事普通职业的回流农民工的月收入能达到2 000~3 000元,回流创业者的月收入更是明显高于这一月收入。因此,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经济收入差距对于打算回流的青年农民工而言已不再是一个绝对的吸引条件了。一位从湖南吉首市保靖县到江苏南通市如东县务工,但现已回流到家乡的织布工人(男,32 岁,编号FHL17)就认为,之前的工作不足以支持家庭生活成本:“我是今年过年(2020 年)的时候回来的,本来打算出去的,但是因为疫情的影响一直出不去,就到屋里头干点零活。到五月份的时候出去了,到了原来的那个织布厂上班去了,后面因为工资低,觉得不划算,就回来了,想到屋里做点小生意。之前看到一个耍得好的(朋友)倒卖水果觉得还可以,就想到买个二手车,也去各个村跑跑,做点卖水果的生意。”
其次,面对流出地符合心意的创业机会,青年农民工更愿意回流以求长期稳定的发展。与中老年农民工一份工作干到底的就业观念不同,青年农民工的想法更多样多变,不局限于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寻找就业机会,更善于利用丰富的信息渠道发掘流出地的创业机会。一位从宁夏吴忠市同心县到江苏苏州市昆山市务工,但现已回流到家乡的司机(男,26岁,编号QHL29)表示,创业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早都想回来了,正好赶上我朋友说新百物流缺车缺司机,我了解了具体情况,感觉还行,而且我特别爱车,从小就有个跑大车的梦想,我就自个儿回来了,又找朋友借了点钱,买了个车,进公司开始拉货,到现在差不多快两年了。不再出去了,现在老家工作,挺好的。”
最后,由于客观因素的制约,青年农民工不能轻易改变现状,但当预想的时机成熟时,他们会遵从内心的想法回流创业。维持“家”的良好发展是青年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力之一,家庭其他成员的发展状况与整个家庭的经济发展状况息息相关,这自然而然成为影响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重要因素。青年农民工即便有强烈的回流意愿,也需要考虑近期的回流行为对家庭其他成员和整个家庭的影响,一方面是家庭生计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计划创业的经济积累。因此,也有一些青年农民工表示回流行为会发生在三四年以后。一位从宁夏固原市彭阳县到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务工的个体户(女,26岁,编号QWC87)表示,等到将来的一天,自己也要做一个“自由”的老板:“老家好,父母兄弟都在老家,我还是想回老家。看给我兄弟把媳妇娶了,我俩能在固原那边有个差不多的收入,我俩就回去。我兄弟结婚怕还得三四年吧,也就三十岁左右看能回去。想自己做点生意啥的,给别人干活不自由,你说我现在回个老家都要请假。等有本钱了,自己做生意,后面发展也快些。”
可见,在流出地和流入地各种“推力”和“拉力”的博弈下,一些青年农民工基于个人职业发展、生存安全的需要和家庭责任等方面的原因,有较强的回流创业意愿,期望实现由打工者向小业主、老板的身份转变(罗竖元,2020)。回流创业的想法是部分青年农民工一次重要的思想转折,一方面反映青年农民工对外出务工经历的自我总结,另一方面也是青年农民工开启新事业的起点,创业想法的成熟程度和实施结果基本上决定了他们回流后达成的“家”“业”兼得目标是否牢固。综上,无论是青年农民工回流就业还是回流创业,都不能否认“业”的想象对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强化作用。当“家”对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产生即时、迫切的影响时,还需要良好的“业”来强化,积极的“家”“业”结合状态才能稳固青年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和回流行为。正是因为青年农民工在一步步追求自己的回流发展梦,“家”“业”兼得才能一点点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基于个体心理决策视角,使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流出地的“家”和“业”对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过程。研究发现,流出地的“家”和“业”是影响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深层因素。1)“家”的观念触发了青年农民工的回流意愿,他们因新的人生节点、具有挑战性的家庭责任和规划中的家庭发展而回流。2)“业”的想象强化了青年农民工的回流意愿,他们因选择新的就业地点,渴望好的就业条件,以及寻找独特的创业资源,改变旧的发展路径而回流。3)“家”虽然会触发青年农民工的回流意愿,但其影响还需要“业”的强化。二者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形塑青年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家”的观念对回流意愿的触发和“业”的想象对回流意愿的强化,透视出青年农民工对“家”“业”兼得的期盼。回流后“家”和“业”均在流出地,这为青年农民工实现“家”“业”兼得创造了条件。换言之,有回流意愿和回流到家乡的青年农民工并不都是舍“业”回流者,随着流出地就业和创业环境的改善,他们当中有部分成员可以实现“家”“业”兼得。
4.2 讨论
受城市空间重构、地理迁移、社会流动、自然灾害等内外部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国外“家”的批判地理学从社会、文化、经济视角探讨“家”的广泛含义,认为“家”不是固定的地方,而是可以跨越不同空间尺度形成归属感的地方(Su,2014;罗佳丽等,2017)。但中国青年农民工对“家”的理解不同于国际移民。即便有一些青年农民工在流入地构建了自己的“家”,但那个流入地的“家”不是韦伯认为的传统意义上的“家”(中国传统文化的“家”、故乡的“家”),而是现代性意义上的“家”。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家”是一个非常具有情感和力量的词汇(陶宇等,2018),总是与根植性有关,祖辈、父母或童年生活的地方在身份中扮演重要作用,作为“家”的地方和归属感可能并不轻易随人的流动而变化(封丹等,2015)。显然,中国文化意义上的“家”不同于国外家的批判地理学对“家”理解。本研究结合中国语境把文化意义上的“家”作为方法、从文化的角度比较细致和全面地呈现了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生成过程,从而使得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呈现不同于西方移民流动的图景,拓展了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创新性地丰富和推动了相关领域的研究。在中国,“家”虽时有变动但未脱离其在社会和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总体性位置,依然支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肖瑛,2020)。因此,在对农民工群体进行研究时,可以把“家”作为一个关键的切入点,从“家”出发构建中国话语的分析框架,这蕴含了创建中国本土人口流动理论的可能性。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不足:受问卷调查数据没有流出地“业”的信息限制,本文的定量研究未能深入展开分析。
当前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流出地和流入地在就业机会、收入水平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差距。为了能够实现青年农民工回流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其回流后稳得住、发展好,“家”“业”可以持续兼得,现提出以下2 个方面的建议:其一,流出地政府要借助国家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契机,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机会、提升收入水平、解决城乡和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真正实现青年农民工“家”和“业”兼得的梦想,使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有保障、更可持续。青年农民工回流后若得不到“业”的持续强化,“家”“业”难以在流出地持续兼得,他们有可能再次外出。但受自身人力资本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又不具备在流入地举家定居的能力,这将使得这一部分人口在流入地也难以实现“家”“业”兼得,最终出现两地“落空”的情况。其二,政府(尤其是流出地政府)要加大对回流青年农民工的创业扶持,进一步强化其创业意愿,促使其创业意愿转变为创业行为。首先,以多种形式宣传流出地各级政府鼓励青年农民工回流创业的政策和创业成功的典型案例,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和环境,激发青年农民工的创业热情。其次,通过成立创业服务中心,注重创业培训效果,丰富培训内容等方式,建立有效的创业指导培训机制,提升中西部地区回流农民工的创业能力。最后,通过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建立小额信贷基金,开辟绿色通道等方式加强创业扶持政策的落实,提高创业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