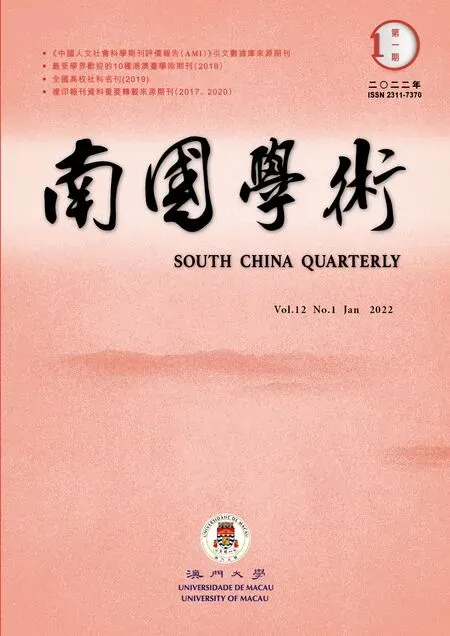江海之間:鴉片戰爭後的香港與上海轉口貿易
2022-08-16葉農
葉 農
[關鍵詞]香港 上海 百年轉口貿易
在近代百年滄桑裏,南海之濱的香港與浦江兩岸的上海,由於相似的遭遇和經歷,將命運緊緊連在了一起。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清政府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香港島被割佔,沿海實行五口通商。在隨後的數十年裏,憑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資源,上海逐漸成爲遠東最大的工商業城市,香港則因與上海存在緊密的轉口貿易(下簡稱“港滬轉口貿易”)①香港是中國沿岸的一個通商口岸,並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第三國,但它又是被英國所佔領,因此,清政府與英國政府就香港地位問題展開過多次交涉,最後定位爲外國口岸。歷史上將香港對內地口岸的貿易稱之爲“轉口貿易”,成爲其“對外貿易”的組成部分。本文即採用此含意。而成爲東方最大的轉口港。近年來,學術界雖然對百年間的港滬轉口貿易關係問題有所涉及,但卻存在着三個問題:一是對雙方的轉口貿易關係發展史未給予應有的重視,研究成果甚少;二是對兩者之間存在的貿易關係語焉不詳,沒有作系統深入的研究;三是對貿易發展過程中參與的貿易商、販運的商品、提供的貿易服務缺乏關注。有鑒於此,本文擬依據現存的史料,對港滬貿易的分期、港滬貿易商群體、港滬貿易貨物這三個方面略陳管見。
一 “五口通商”與轉口貿易的初創(1843—1860)
英國通過《南京條約》割佔香港後,獲得了在五口通商的權利。在此大背景下,香港與上海開始了轉口貿易,並具有鮮明的特點。
(一)英國與香港、上海的開埠和開港
1841年1月25日,英國以武力侵佔香港島。英國駐華全權代表兼商務總監義律(C. Elliot,1801—1875)在英資洋行的支持下,將香港島闢爲商埠,並於6月7日宣佈香港爲自由港,香港的轉口貿易由此興起,圍繞轉口貿易的其他行業如航運、航務、港口、碼頭、貨倉、保險、銀行、郵電通信等也應運而生。從此,轉口貿易成了香港的經濟支柱。
上海被《南京條約》開放爲通商口岸之前,已經是國內的貿易大港和漕糧運輸中心。英國人垂涎上海在轉口貿易方面有着獨特的地理優勢,於是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八月十五日,逼迫清政府簽訂《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並依據這些條約,在上海採取了三個步驟:開設領事館、開放港口貿易、設立租界。
11月8日,英政府任命的領事巴富爾(G. Balfour,1809—1894)與隨員來到上海。先在縣城內姚家巷租屋辦公,之後又租定一所房屋作爲英國領事館。11月17日,經與清政府協商後,將上海變爲中國第三個對外開放的通商口岸。通過對當地地理形勢的瞭解,泊船碼頭也隨之選定在上海城北——黃浦江西岸與吳淞江(即蘇州河)交會地帶。
上海對外開港後,巴富爾經過與上海道台宮慕久多次談判,大致劃定了英租界的範圍。1845年11月,中英訂立《上海租地章程》,規定了英國租界的大致區域:“前經議定,楊涇浜以北、李家場以南地基,租給英商建房居住。”②“1845年《上海土地章程》”,《檔案與史學》1(1995):4。
(二)港滬轉口貿易
上海開港後,作爲新開的口岸,雖然地理位置優越,但對外貿易的其他條件如貿易網絡、貿易商及相關貿易制度、服務保障體制等還有欠缺。而香港在英國人佔領後,原來在廣州、澳門的一批英商由於對香港寄予厚望,蜂擁而至地在香港購地建樓。1841年6月14日的第一次賣地,買得者二十餘人中大部分是英商。
然而,香港島的貧瘠落後、海盜猖獗、瘟疫流行、夏季飓風肆虐、秋冬火災爲患等惡劣條件,還是讓冒險家們有所忌憚。例如,1846年4月6日《泰晤士報》稱:“香港的商業地位已大爲降落。……已有兩家老商行結束,兩家決定遷出香港,又有兩家考慮步其後塵,僅留下一名書記,處理貨運和郵件。”
就在此時,上海的開港爲香港的這些商行提供了機會。這些遷出的香港商行紛紛向上海轉移。對上海來說,它們的到來,爲上海的轉口貿易帶來急需的要素。
一是買辦制度。五口通商後,上海等新開放口岸的內地商人大多未與外商打過交道,缺乏必要的信用關係;同時,外商對中國的交易傳統、貨幣、度量衡制度等也不熟悉;加之中國廣大內陸地區尚未開放等原因,他們不得不僱用買辦作爲在中國的代理人,爲其推銷進口商品和購買土貨。①孫玉琴:“簡述近代上海對外貿易中心地位的形成”,《中國經濟史研究》4(2004):82。
香港的買辦制度傳承自廣州、澳門。鴉片戰爭前,依託澳門與廣州兩個對外貿易中心,香山籍買辦得以形成與發展。香港開埠後,這些香山籍買辦亦跟隨所服務的洋行來到香港,又隨洋行前往上海。例如,最早到上海開設分行的怡和洋行負責人達拉斯(Alexander G. Dallas)於1844年曾向香港總部要求派遣買辦。總行立即派去一位名叫亞三的廣東人到上海分行擔任買辦。②寧靖編:《鴉片戰爭史論文專集(續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62頁。張曉輝指出:“19世紀中葉以後,隨着外國資本勢力向北擴張和上海地位的迅速上升,原在粵港地區活動的大批買辦和商人赴滬發展,使滬港兩地的社會經濟聯繫日益緊密。上海早期頭面買辦如徐潤、唐廷樞、鄭觀應等都是從南方北上的。”③張曉輝:“滬港近代城市關係史研究之我見”,《檔案與史學》1(2001):37。隨着買辦的不斷發展壯大,寧波籍買辦接替香山籍買辦,成爲上海買辦的主體。
二是貿易商。鴉片戰爭後,以英商爲主體的外商從廣州、澳門湧入香港,隨後又從香港來到上海,“英國侵佔香港後,英商洋行把香港作爲對華貿易的大本營,大大削弱了廣州市場原有的重要地位。1850年,廣州尚有外僑362人;到1859年,減少到172人。而大批英國商人則涌向上海和香港。到1859年,上海外籍人口已達408人,爲廣州的3倍”。④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市國際貿易學會編:《上海對外貿易(1840—1949)》(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上冊,第67、68、93、43頁這些洋人與洋行遷入上海,成爲剛剛開始的上海轉口貿易的主力軍,也爲港滬轉口貿易發展提供了動力。最初幾批到上海的洋行,大多數都是從廣州、香港分設過來的,如怡和洋行、寶順洋行、仁記洋行、義記洋行、廣源洋行等68家。⑤[英]勒費窩:《怡和洋行:1842—1895年在華活動概述》(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陳曾年、樂嘉書 譯,第129頁。
至1859年,在上海、香港均設有機構的洋行共有75家之多,其中以英資及英國管轄之下印度資本洋行爲主體。⑥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市國際貿易學會編:《上海對外貿易(1840—1949)》(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上冊,第67、68、93、43頁這些洋商與洋行爲香港與上海轉口貿易提供了資金及海外網絡,並通過其所雇傭的買辦們,建立了兩座城市所輻射腹地的貿易往來。
三是港滬航運聯繫。上海對外開港之後,西方國家在上海的貿易逐年增加,大批商船向上海港涌來。“上海開埠最初6個星期裏,就有7艘外國商船駛入港口。1844年,共有44艘外國商船進口,載重量爲8584噸。1849年,進口岸的外國船增至133艘,載重量爲52574噸。其中,英國船94艘,載重量38875噸;美國船25艘,載重量10252噸;其他各國船隻共有14艘,載重3447噸。1852年的最初9個月裏,進口的外國船隻達182艘,載重量78165噸。其中,英國船103艘,載重38420噸;美國船66艘,載重36532噸;其他各國船隻共13艘,載重3213噸。”⑦[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張匯文 等譯,第1卷,第401—402頁。
(三)轉口貿易的主要商品
在上海進口的貨物中,排在首位的是鴉片。洋行先是以香港代替伶仃作爲走私鴉片的大本營,大部分鴉片從印度運到香港後,儲存在香港的倉庫裏,然後隨時分運到上海及中國沿海各地銷售。⑧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市國際貿易學會編:《上海對外貿易(1840—1949)》(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上冊,第67、68、93、43頁這一時期,中國進口的鴉片都是從香港轉口輸入的,上海則是進口的最大口岸,也是最大的轉運口岸和消費口岸⑨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市國際貿易學會編:《上海對外貿易(1840—1949)》(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上冊,第67、68、93、43頁。進口值從1843年的6946030兩、佔全國的41.6%,增加到1860年的14857440兩、佔全國的59.6%。⑩具體貿易量參見:各年海關貿易統計報告;[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余繩武 等編:《19世紀的香港》(北京:中華書局,1993);姚賢鎬 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40—189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第1冊,第578頁;《香港藍皮書》(1844—1913)。所採取的手段有二:一是由大洋行控制鴉片貿易,其他洋行參與。二是使用小型快速船隻飛剪船或者航運公司的班輪作爲運輸工具。每年鴉片從香港運往上海的主要運輸工作,是大洋行的飛剪船等小型快速船隻、航運公司的班輪。爲防備海盜船,怡和、寶順等洋行都盡力設法提高本行屬下飛剪船的速度和火力。不惜資本購買曾在美國海軍中服役的舊兵艦,改裝爲飛剪船,還以高工薪來招攬英、美海軍的逃兵,讓他們爲鴉片走私貿易賣命。由於這些外國商行的快船隊是從美國海軍退役的舊兵艦改裝而成,船員是以高薪招攬的英、美海軍的逃兵,因此,他們的航海、戰鬥技術都相當嫻熟,在鴉片貿易中起了重要作用。①金應熙 主編:《香港史話》(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第113頁。
排在第二位的是絲綢。19世紀60年代以前,各類茶葉及生絲、綢緞都是經上海口岸出口的大宗商品,其他産品的出口在這一時期尚無足輕重。生絲除了直接出口英國外,出口香港的數量也比較大。此類貨物運抵香港後,再經香港轉口輸往英國、歐陸國家和印度等重要市場。②徐日彪:“近代香港航運業的興起”,《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0),第193—194頁。但由於這類貨物的貨值高,經香港轉口的數量比較小。③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市國際貿易學會 編:《上海對外貿易(1840—1949)》,上冊,第60頁。
二 “多口通商”與轉口貿易的興盛(1861—1899)
從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至19世紀末,是香港作爲自由港確立時期。19世紀50年代,上海取代廣州成爲中國最大的外貿口岸與外貿轉運中心,轉運國內的洋貨佔比高達46%;而從1864—1895年間,上海土貨轉運國外佔比約24%,在全國首屈一指。④唐巧天:“從鼎盛到中落:上海作爲全國外貿轉運中心地位的變遷(1864—1930)”,《史林》6(2007):139。再從香港與上海各自的洋貨進口貿易在全國貿易佔比來看,兩地均是中國的重要貿易港,均形成了各自的商業輻射範圍。⑤王列輝:“雙中心:滬港兩地在近代中國的地位及形成原因分析”,《江漢論壇》10(2012):70。
從香港的輻射範圍看,它集中於南方地區。表1是廣州、汕頭、福州、廈門、寧波等港口經香港輸入洋貨佔比情況,由此反映出,越是南方的港口,所佔比重越高,表明香港是南方的轉口貿易樞紐。

表1 1869—1900年各港經香港輸入洋貨佔比(單位:%)
在此時期,由歐美等國家輸入的貨物,大多先集中於香港、上海,然後再向其他港口中轉。因此,港滬轉口貿易在此時期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具有如下五個特點。
其一,香港在上海土貨出口地位重要。香港在上海土貨出口貿易中,一直佔據重要地位,從1869年的613863海關兩、佔比3.37%,上升至1887年的4512853海關兩、佔比15.21%,之後雖有所下降,但直到1900年仍爲8972985海關兩、佔比13.25%。⑥毛立坤:“晚清時期上海對外貿易中的香港因素”,《國家航海》3(2016):123—136。
其二,香港是上海進口貿易的重要來源地。1869年,香港來貨額爲3263599海關兩,佔比5.9%;到1887年,升至19431960海關兩,佔比30.8%;至1900年,爲20082044海關兩,佔比15.8%。英國及其附屬地的來貨,也然是此時期上海進口貿易的主要來源地。⑦根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海關總署辦公廳編《中國舊海關史料(1859—1948)》各有關年度貿易統計值。香港是英國來貨的三大組成部分之一,英國、印度的進口貨物有許多先運抵香港,再經香港轉運上海。
其三,港滬轉口貿易商品增多。19世紀60年代以後,雖然印度輸入中國的鴉片全部集中於香港後再轉口到上海,但隨着鴉片貿易的合法化以及受到國內土烟生産的影響,在上海進口總額中的佔比逐漸下降,而棉花、棉製品則成爲重要的進口商品。80年代末,華南各地採用洋紗自己織布,減少了洋布進口數量,洋布進口更集中於上海。在香港輸入上海貨物中,大有後來居上之勢。①張曉輝:《香港與近代中國對外貿易》(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0),第86、66—67頁。上海對香港出口貿易方面,絲綢、茶葉、北方的土貨以及上海港出口的雜貨,比重逐漸擴大,成爲上海和香港貿易中重要的出口商品。從絲綢來看,上海的絲綢出口大增,幾乎供應了全部西方國家所需。而上海對香港的絲綢出口,則因量小價微,僅有少量經過香港繞道輸往海外。
其四,中外行商設立機構相互合作。這一時期,一批洋行在兩地設立機構,進行洋行與洋行、洋行與華商之間的合作。例如,自1867年始,德盛號與怡和洋行在中國沿海貿易中合作達二十年以上。又如,自1864年起,粵商怡記與怡和洋行合作,時常將棉花從上海運到香港,由香港的洋行做其代理人。此外,怡和洋行還經常向上海的中國商人放出貸款,擔保是用洋船裝運華商貨物,這有利於吸引中國商人將生絲託運到香港。而那些新成立的洋行,則注重對華資本輸出。例如,創立於1870年的平和洋行,總部設在香港,先後在滬、津、漢等地開設分支機構。創立於1879年的隆茂洋行,總部設在香港,在上海開設分行,並建有倉庫打包設備。②張曉輝:《香港與近代中國對外貿易》(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0),第86、66—67頁。
其五,港滬轉口貿易專業貿易行形成。隨着香港與上海轉口貿易的擴大,形成一批專業貿易行,並成立相關公會組織,如上海的南洋莊、香港的南北行公所等。上海南洋莊可分爲以進口爲主的“九八行”(包括僑資分號)和以出口爲主的南洋辦莊(包括僑資坐莊,亦稱串莊)兩類,再按其經營商品和所屬幫口,分爲各行各戶。所謂九八行,即以代理南洋僑商推銷南洋物產如海味、食糖,木材、胡椒等進口貿易爲主,兼營代辦國內土特産出口。這些行號像牙釐行一樣,不自負盈虧,而是按代理進出口貨值取傭2%,故通稱“九八行”。他們多數是以內貿埠際販運爲主的閩粵花糖洋貨商,早就與南洋華僑有貿易關係,後逐步轉變爲以代理南洋僑商進口貿易爲主的進口行;也有南洋華僑或與華僑有聯繫的閩粵商人在上海新開設的同類行號。
早期上海口岸對南洋地區的出口,規模不大且多是土特産品及零星商品。19世紀60年代以後,上海南洋辦莊如中藥材、絲綢匹頭、雜糧各專業相繼形成。以藥材業爲例,上海對外開港後,兼營中藥材的廣貨行紛紛從蘇州遷滬,少數經營南藥的藥材行也從寧波遷來上海。
當時,上海對西方的貿易完全由外商洋行壟斷,而“九八行”經營的領域與洋行經營的領域有很大不同。甲午戰爭前,上海陸續開設的九八行爲數不多,著名的閩幫有福裕南、豐興號、裕泰號,廣幫有協泰和,潮幫有范德盛,本幫有同福和、鼎裕海產行等。當時,上海的海味業九八行尚無正式同業公會組織,大都參加各幫的同鄉會館,如閩幫泉漳會館、建汀會館,潮幫潮州會館,廣幫廣肇公所等。甲午戰爭後,上海南洋莊的業務有所發展,九八行除代理海味進口外,又出現了一些以代理大宗食糖進口爲主的九八行,如安記、炳記、聚德隆、捷裕等。③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市國際貿易學會 編:《上海對外貿易(1840—1949)》,上冊,第165頁。
這期間,以出口爲主的南洋辦莊如中藥材、絲綢匹頭業已漸具規模,雜糧出口則有仁誠謝璧記、春華等戶,僅有山地貨出口仍由水果店代辦,尚無專業戶。如廣幫的同永泰,於1895年由陳鳳笙、陳文笙、陳玉笙創辦,出口品種有上海、湖州、杭州、蘇州等地出産的綢緞廣綾,也出口各種土布及雜糧等。④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市國際貿易學會 編:《上海對外貿易(1840—1949)》,上冊,第167、393—400頁。
香港經營轉口貿易的“南北行”,第一家是1843年挂牌營業的澄海“紅頭船”船主、泰國潮商高元盛的“元發行”,行址設於南北行街10號,並在西環擁有可以堆放暹米和南北土產的大貨倉;第二家是能平縣隆都區前美鄉人“船主佛”陳宣衣的“乾泰隆行”,行址設於文咸西街27號,並在西環擁有大貨倉。乾泰隆初期的業務,主要是通過駕駛“紅頭船”隊“採辦中國土產運銷南洋各地,復以暹米運銷港、粵”。南北行最初衹是指經營及轉運國內大江以南和華北兩綫的貨物(早年商家稱之爲南北貨)的商行而言;其後,因爲貿易擴展到南洋各地,商家們又將經營國內及南洋土特産生意的商行分別稱爲南北行。由於不少南北行莊也採納九八抽傭的生意手法,“九八行”遂與南北行混成一片,難分彼此。最後,“九八行”被歸入“南北行”之列,而“南北行”之稱變成泛指在香港上環文咸東西街、永樂街及高升街一帶經營國內外各埠來貨、代客兌貨及依據南北行行規做買賣的商號或公司的統稱。
南北行買賣的貨物種類繁多,其經營北綫(華北綫)業務的商家主要經營中國內地的土産雜貨、工藝品、工業品等,而經營南綫(南洋綫)生意的商家則主要輸入南洋各地土産如白米、橡膠、椰子油、沙藤、椰子乾、生油、花生等大宗商品,同時將中國國內的土特産和工業品轉口輸往南洋各埠。根據貿易對象國家的不同,經營南綫業務的商號也有具體的分工,可以細分爲:印尼綫、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綫、泰國綫、越南綫、菲律賓綫等。除此之外,還有部分商行專門經營以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爲對象的東綫生意,但數量有限。
在當時經營南北貨物的商行中,大多數商行是以經營某種特定商品爲主,同時兼營其他貨品。以專營進口白米業務爲例,著名的有乾泰隆、振盛行、鉅發源、嘉元行、聯益行、廣新行、聯豐行、廣萬昌、兆豐年、榮豐行、寶泰行、茂泰行等。另外,南北行商莊中存在鮮明的方言幫群團體分野,時人稱之爲“幫”。據統計,在全盛時期,屬於廣府幫的商行約有四五十家,屬於潮州幫的商行約有二三十家,屬於福建幫的商行約有二十家,屬於山東幫的商行約有五六家,屬於其他方言群體的商行另有數十家。在業務分工方面,不同的方言幫群大致與不同的國家或地區進行互市。大體上,廣府幫商號多經營北綫生意,潮幫、閩幫大多經營南綫生意,而山東幫則以經營北綫和東綫生意爲主。①同治十年(1871),廣東軍門方照軒號召省港兩地的潮汕商人共同捐款,在廣州創建潮州八邑會館,並鐫刻慷慨捐資的旅港各著名潮商號名稱。就《創建省垣潮州八邑會館碑記》所見,當年榜上留名的有如下二十五家:合興行、廣榮盛、泰豐順行、恒豐行、和順興號、元發行、德美合、泰利行、永祥順行、永興隆行、乾泰隆行、華順泰行、永義昌行、乾元興行、廣福和行、得美行、萬福成行、和興行、和發行、建興祥行、怡豐行、怡泰行、洪合行、桂茂行、泗合春號。參見錢江:“潮汕商人與香港米糧貿易”,《暨南史學》1(2003):389—390。
19世紀50年代,經營轉口貿易的南北行行商在香港崛起,漸漸形成了若干區域性商人集團,如廣東幫、潮州幫、福建幫、上海幫等,彼此對峙。1864年初,潮商元發行高滿華、粵商廣茂泰行招雨田等邀集同行組成同業團體,並議定《南北行規約》七條。1868年,又在本街建成南北行公所,作爲集會辦公場所。它的成立,是包括與上海在內的香港轉口貿易興盛的標誌。②余繩武、劉存寬 主編:《19世紀的香港》(北京:中華書局,1994),第417頁。
上海南洋莊“九八行”,透過香港南北行中的華北綫各行進口南貨;南洋辦莊透過華北綫,將華中、華北的中國貨物、工業品等轉運到南洋地區。因此,香港的南北行各行號,爲香港與上海的轉口貿易做出了很大貢獻。
三 風雲變幻與轉口貿易的衰退(1900—1936)
踏入20世紀至1936年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前,香港與上海的轉口貿易進入到一個新階段。
(一)20世紀上半葉上海貿易分期與港滬轉口貿易發展中落
20世紀上半葉,上海作爲全國外貿轉口中心的地位一度中落。在1930年,曾退化爲華中、華東的區域性外貿轉口中心。從洋貨進口來看,以1904年爲界,上海在全國進口中的地位變化大致爲:1864—1904年爲鼎盛期(轉運國內洋貨進口佔比達46%,是全國洋貨分發的中心),1905—1930年爲中落期(20世紀初開始,天津、漢口等口岸直接外貿發展迅速,一批獨立性很強的口岸如青島、大連等興起,分流了全國進口量,1930年時上海佔比降至15%)。從土貨出口來看,以1915年爲界,上海在全國出口中的地位變化大致爲:1896—1915年爲鼎盛期(土貨外貿轉運全國佔比不斷上升,從22%上升至37%),1916—1930年爲中落期(土貨轉運全國佔比持續下降,到1930年時經上海轉運降爲17%)。①唐巧天:“從鼎盛到中落:上海作爲全國外貿轉運中心地位的變遷(1864—1930)”,《史林》6(2007):138—140。
這種狀況之所以出現,一是全國對香港貿易有很大部分是在華南各口岸進行的,佔比達70%;二是上海與西方國家的遠洋運輸較爲便利,除印度鴉片輸滬多屯集香港轉運外,其他商品多都是與西方國家直接貿易。
(二)上海自香港的洋貨進口
上海洋貨自香港進口方面,前兩個時期最爲重要的進口商品——鴉片於1917年基本停止,棉織品進口比重也逐步下降,一些工業產品逐步取代之前的商品。以1929年爲例,從香港轉運進口的西方商品中,數量較大的紗、布、棉毛絲麻織品、五金、化工、染料、機器、紙張、麵粉等計6491萬關兩。②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市國際貿易學會 編:《上海對外貿易(1840—1949)》,上册,第186頁。南洋商品經由香港轉運到上海則有較大增長,主要爲糖、米、海產品等;1929年,僅這三項商品的轉運貨值即達8071萬關兩。③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市國際貿易學會 編:《上海對外貿易(1840—1949)》,上册,第186頁。
上海的食糖進口種類較多,主要來自香港、荷印和日本(包括中國臺灣)等地區。香港是遠東食糖的主要集散地,20世紀20年代以前,中國從香港進口的各類食糖佔全國進口總數量的70%左右。赤糖主要是荷印的粗砂,還有華南土糖,白糖主要是荷印產的爪哇砂,大部分經由香港轉口。後來班輪增加,荷印食糖直接輸入上海,經香港轉口的數量銳減。④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市國際貿易學會 編:《上海對外貿易(1840—1949)》,上册,第436、454頁。
(三)上海向香港的出口
中國棉紗、棉布出口始於20世紀初期。1914年,海關關册纔有出口棉紗和棉布專項的統計數字。20年代,上海南洋莊出口棉紗和棉布以廣幫爲主,紗、布銷售地區首推香港。上海市場的紗、布的漲價,有時是因廣幫字號大量辦貨到香港而引起的。新加坡地區經營紗、布業的也以廣幫僑商居多,如聯益、鉅安都是新加坡紗布號設在上海的辦莊。在菲律賓的馬尼拉,閩幫華僑主要經營紗、布。當地的最大紗布號東成、東美都是閩幫僑商開設的,上海的閩幫辦莊如建東、建華都是採辦紗、布對菲出口的大戶。
上海對南洋各地出口土布由來已久,土布由各土布行向農民搜購,然後售予南洋辦莊各行出口。起初多是華僑託親友捎帶,數量不大。由於土布質地牢,不透陽光,能吸水,爲南洋的錫礦和橡膠園工人所樂用。早期出口的土布中有一種灰布又稱繒布,還有藍色土布等。土布每匹一卷,闊一尺一寸半(通稱一尺二寸)。20世紀初,出現土紗和洋紗混紡的土布。1910年前後,商品土布基本上改用洋紗紡織。此期間,上海郊區布莊也兼做洋紗販賣,農民賣了布,可順便買回紗。
19世紀末到20世紀20—30年代,上海南洋辦莊出口土布,計先後有同永泰、公昌和、誠昌、廣記祥,福興綸、廣裕綸等戶,每年平均約1.3萬—1.4萬件,合210萬匹左右。其中,廣記祥創設於19世紀末,負責人鄧耀生,原專營對美國出口翡翠,玉器以及綢緞衣着等,至20世紀初,兼營土布、綢緞對新加坡出口,其後也出口睡衣、針棉織品、日用百貨和雜糧等。1910年間,營業額在五六十萬銀兩左右;1921年間,高達百萬兩,以土布所佔比重較大。廣裕綸是百年老店,總行設在廣州,於1926年在上海設立分莊,專營土布、綢緞等出口,年營業額達100餘萬元。⑤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市國際貿易學會 編:《上海對外貿易(1840—1949)》,上册,第436、454頁。
中藥材出口以香港爲集散地,南洋各地都是向香港採購。上海南洋辦莊中藥材行出口品種中,以清凉劑一類的藥材銷路最多,大部分經由香港轉口。至於成藥,上海南洋辦莊中藥材行原不經營成藥出口;約在1927年以前,上海藥房如中法、中西藥房等都曾自營成藥出口。由於推銷不得法,多種成藥銷路不大。其後,委託南洋辦莊會豐商店經銷推廣,銷路乃大增,於是上海各中藥店和藥房逐漸都與會豐有業務往來,其中丸散膏丹如童涵春的人參再造丸、姜衍澤麝香膏、宋公祠參貝陳皮等,西藥如施德之痧藥水、中法藥房杏仁露等,聞名南洋各地。
上海中藥材對南洋各地出口,除大黃、麝香、甘草等銷往歐美地區,歷來由外商洋行所把持外,其他藥材一般由南洋辦莊經營。上海的南洋辦莊經營中藥材出口,大都委託香港南北貨行寄售。當時香港這種代理行有二三十家,資金幾千港元到幾十萬港元不等,都設在香港文咸西街、永樂西街和機列文街,平時各自經營,不相爲謀。這種寄售方式並不是先講好貨價,而是待貨物運到香港後,再看貨論價或定價待沽。出售後,香港的代理行九八取傭,各項費用實報實銷,實際上連同保險費、棧租、上下力等,總在4%左右;且在寄售時,香港行家對有些貨物故意壓低價格。所以,到了後來,南洋辦莊也有在港自設分莊的。
山地貨對港澳及南洋地區出口佔到70%強。上海口岸山地貨出口值僅佔全國出口總值17%。不過,上海出口的這些山地貨大部分是銷往港澳及南洋地區的。如以之與全國山地貨對港澳及南洋地區出口值比較,上海口岸所佔比重達24.2%。由於山地貨品種繁多,規格複雜,而且隨季節變化有進有出,因此,客戶關係極爲重要,雙方不是聯號就是往來多年的老客戶。平時貨運往來先記在賬上,進出口相抵後再結算。其經營方式,本幫辦莊最具代表性,如恒興、順康行等以經營各種蔬菜等山地貨爲主,水果爲次。
上海向香港的雜糧出口品種,包括各種豆類、豆餅、芝麻、油脂類(植物油以及豬油)等,廣幫、潮幫、閩幫各南洋辦莊都有經營,主要對香港出口,也有直接銷往南洋各地的。其方式由南洋辦莊向上海豆市街雜糧行買進,出貨後15天付款,打10天期票。當時,滬港輪船很多出貨後馬上打包,報關託運,貨到香港出售後再匯款來也來得及。所以,香港有總店的商家,就可利用這個條件。如無總店或分支機構在港的,國內進貨則先須墊款,吃20天的利息。這是對香港地區的做法。上海雜糧對南洋(包括香港)地區出口,以荷印、新馬和香港地區佔多數,菲律賓、暹羅(泰國)次之,安南很少。其中以綠豆數量最大,黃豆次之,花生、赤豆、芝麻、黑豆則有少量出口。綠豆是供華僑做涼飲,黃豆則製豆腐用,所以出口數量居各種雜糧之首。黃豆出口以東北産爲主,也有關內産的黃豆出口。在“九一八事變”以前,上海南洋辦莊也曾經營一部分東北黃豆(大豆)出口,一般是在上海成交後,由大連直接裝船出運;其經由上海出口的大豆,則以津浦綫裝來的居多。綠豆產於關內,天津綠豆優於明光綠豆。上海南洋辦莊所經營出口的都是這兩地的産品。此外,各類豆餅、子餅對南洋也有出口,但以黃豆餅數量較大,均作肥田之用;花生以山東、河南產爲主;芝麻則以河南産的品質最好。
(四)南洋莊與九八行
在香港向上海轉口貿易過程中,上海南洋莊九八行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此時期,這些行號共有10戶商號(參見表2)。

表2 20世紀上海南洋莊九八行及其他南洋莊戶名一覽表
南洋辦莊(山地貨業)有時也兼做一些山地貨進口,如南洋芒果、海味、白藤、胡椒等。廣幫中的聚德泰、立大成、梁球記等,都是香港山地貨行設在上海的分莊或聯號。起先港商都是委託上海的山地貨辦莊代辦,但有些年貨必須在春節前趕到,有的品種季節性很強;而且山地貨有俏有呆,如果大家都委託上海辦莊代辦,很難盡如己意,因此,香港行號後來就改在上海自設分莊或聯號,衹代本行辦貨,不與他家往來。不過,廣幫中如經營雲紗出口的廣德隆和食油出口的廣信隆等,也兼營山地貨出口。①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市國際貿易學會 編:《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冊,第468—469頁。
19世紀60年代,上海以內貿爲主兼營南洋貿易的雜糧行,以潮州幫較早,大都是汕頭行家設在上海的分莊,故也稱汕頭幫。其主要業務是代理汕頭總號採購雜糧、豆餅兼及南北貨、廣綾等,由上海運經汕頭出口到暹羅、新加坡等地區,回程的南洋物産再從汕頭轉運上海。19世紀末期,上海雜糧出口業務漸有發展,主要銷往香港及南洋各地,其中一部分仍經汕頭轉口,潮幫雜糧行在東北營口、牛莊、大連及長江一帶的蕪湖、九江等處設有分支機構或聯號,業務規模很大,一般衹做代理,不自負盈虧。這期間,上海的潮幫雜糧辦莊有仁誠、黃隆記、謝璧記等,與南洋僑商關係密切,如黃隆記是汕頭合順福的辦莊,其新加坡的聯號是四順,香港聯號是合順,經營雜糧、豆餅出口。此外,廣幫對香港的雜糧貿易也佔有一定的地位,其中如廣和興、廣德泰、司徒源記等幾家開設較早,大都在1890年左右。在20世紀初開業的東生和號,其業主方郁生、方秩臣原是廣和興的職工,經營雜糧出口,開始亦以對香港貿易爲主,兼營廣州埠際貿易,1913年後,發展到新加坡、菲律賓等地區,並在青島設有分莊,在上海潭子灣設有榨油廠,年營業額達100餘萬元,至30年代,積有資金約60萬—70萬元。1932年,拆夥改組,方郁生另設裕生和號,方秩臣另設東和泰,各立門戶。而東和泰因經營不善,不久即告歇業。①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市國際貿易學會 編:《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冊,第456—459頁。
四 “孤島”時期與轉口貿易的旺衰(1937—1941)
從1937年11月上海淪陷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變”後日軍侵入上海租界,可稱之爲“孤島”時期。在這一時期,港滬轉口貿易呈現出從此起彼伏、衰旺不一至共同興旺的格局。
(一)上海之衰與香港之旺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後,上海作爲中國對外貿易中心地位開始受到影響,也影響到香港與上海之間的轉口貿易。原本經上海進出口的主要貨物均集中於香港,它繼續發揮着重要的中轉功能,並一直與上海保持着貿易聯繫。
“孤島”時期的上海對外貿易經歷了三個階段:(1)1937年11月上海淪陷至1938年10月,是上海進出口貿易的空前衰退及逐漸恢復時期。(2)貿易的發展和繁榮期。1938年10月下旬廣州、武漢相繼淪陷後,口岸的對外貿易中心重歸上海,“孤島”進出口貿易開始復興。1939年9月歐戰爆發後,由於美國、南洋市場得到拓展,上海進出口貿易出現畸形繁榮。這種盛況一直延續到1940年上半年。(3)對外貿易的停滯期。1940年下半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止,由於沿海口岸逐漸被日軍封鎖及上海本身經濟發展的減緩,上海進出口貿易發展呈現停滯狀態。②張賽群:《上海“孤島”貿易研究》(北京:知識産權出版社,2006),第32頁。港滬轉口貿易也據此走過了相關的階段。
(二)“孤島”時期香港與上海貿易的榮枯對比
在上海淪陷後的一年中,上海外貿業務衰落,很多1936年的訂貨在1937—1938年間抵達上海,內地交通運輸斷絕,實銷量大減,貨價暴跌。一些尚在運輸途中的訂貨,多中途卸下,滯留在新加坡、中國香港、日本各埠,上海商人在“八一三事變”後不再向外訂貨,戰後外貨雖運滬不絕,卻不是對外新貿易額。
香港進出口貿易之所以突飛猛進,主要原因是戰爭爆發對上海造成巨大影響,而香港貿易則不受戰爭的影響,因此兩地的轉口有了長足的進展。1937年8月,因爲廣九鐵路與粵漢鐵路的接軌以及與內地交通網絡的興建等交通方面的影響,香港成爲遠東重要的中轉站,商船經香港則更爲繁忙。整個上海的貿易大部分轉移到香港,香港取代了上海對外貿易的優勢地位。
(三)港滬轉口貿易興衰
上海淪爲“孤島”後,香港與上海的貿易關係相當密切,香港在上海的外貿出口貿易中佔有重要地位,大大地推動了港滬轉口貿易的發展。
1.大量上海廠商轉移到香港發展。爲安全起見,在“八一三事變”前,上海一些工商行號先將其存貨及生産設備運至香港,有的還在香港開設了分廠。“八一三事變”至1938年下半年,又有17家上海工廠先後將其在滬資産遷港。①《申報》1938-12-06。1938年,在遷港的上海商號中,僅綢緞業就有4—5家。②陳大同 編:《百年商業·行業轉變史》(香港:光明文化事業公司,1941),第31-32頁。在此情況下,上海對香港的輸出激增。1938年1—9月,上海輸往香港貨值2726萬銀元,佔上海外貿輸出總額的19.22%;同期,上海自香港輸入貨值308萬銀元,衹佔上海外貿輸入總額的1.75%。③《商業旬刊》16(1939):257。
2.上海的進出口量被轉移到香港。歐洲戰事發生後,由於交通不便、運輸船隻不足及歐美各國先後採取了貿易統制的政策,歐洲各國對上海的貿易有所收縮;與此同時,上海租界的華商乘機擴大了對香港、南洋的貿易,從而使香港、南洋地區在上海對外貿易中的地位不斷上升(參見表3)。④《新聞報》1938-06-15。

表3 1938—1941年上海與香港轉口貿易總額統計表(單位:進口千金單位;出口法幣千元)
從表3可以看出,上海對香港的輸出貿易自1939年起有猛增趨勢,主要是因爲歐戰爆發前後,上海對南洋的輸出貿易激增,而其中大部分經香港轉道進行。當時,在香港不僅有港商專門進行南洋貿易,轉銷國貨;也有不少南洋僑商親自到香港採辦國貨;甚至還有不少上海廠商先將貨物出口至香港,再由香港分銷東南亞各地。同時,還有相當一部分輸往西南的商品也經香港轉運。如當時上海對香港輸出的棉紗、棉布,其中就有約40%經香港轉往中國後方。⑤《貿易月刊》8(1941):91。日本方面也認爲,上海對香港輸出的增加,“表示出經由此地對河內、雲南貿易路綫的旺盛,因此,上海租界的商勢通過與香港的交易而作爲重慶轄下的物資供給據點而繁盛”。⑥滿鐵調查商 編:《支那經濟年報》(東京:日本改造社,昭和15年,1940),第366頁。此外,還有部分上海與歐洲的貿易通過香港、越南進行。
3.日軍及其對港滬轉口貿易的利用。香港因爲一直實行自由港政策,成爲了日本商品轉運的中轉站。日軍利用“孤島”的自然環境與中國政府對“孤島”維持市價外匯的機會,採取一系列措施爲侵略活動服務。例如,它按照軍用需要,把出口物資分爲三類:一是對有關軍用的,由日軍絕對統制,嚴禁商民出口;二是對易於掌握的大宗商品如蠶絲之類,給日商以特權壟斷,以便集中掠取出口外匯;三是對一般與軍用關係不大和非軍用的物資,則允許中外商人通過讓日元可以間接套換外匯的所謂“規定手續”以後,准予自由採運出口。①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市國際貿易學會編:《上海對外貿易(1840—1949)》,下冊,第4、81、6頁。
4.在進出口商品結構上,上海自香港輸入的主要是食品。在日僞勢力的封鎖統制下,戰時租界糧食供應一直相當緊張,上海工商界便設法從香港獲取此類物品。
(四)華商及其對港滬轉口貿易的掌握
“孤島”期間,從事上海對外貿易業務的華商與洋商之間出現了明顯變化:在華商方面是,戶數增加,業務比重上升;在洋商方面是,除了日籍外,其他國籍的戶數都在減少,業務比重下降。這情況尤以出口領域較爲突出。據統計,華商進口行和出口行總戶數在1937年底共311戶(其中進口行98戶,出口行213戶),到1941年底,除中途閉歇者外,實存數增爲613戶(其中進口行115戶,出口行498戶)。而其中,進口領域僅增17戶,出口領域則增達285戶。
這一時期,華商“南洋辦莊”成爲推廣滬制輕工業品外銷南洋和香港的主力軍。由於輕工業産品的貨源是來自上海華商工廠,輸往國別又是華僑密集的地方,所以,此類輕工業産品向南洋、香港地區出口的業務多爲華商經營,洋商的經營比重較小。以戶數而論:上海南洋莊在戰前有113戶,業務較盛的1937年底約存90戶。1938—1939年時,因戰事關係,一度減少爲60戶左右。②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市國際貿易學會編:《上海對外貿易(1840—1949)》,下冊,第4、81、6頁。
(五)工業製成品及其他産品的出口
1.上海商品對香港的出口。上海對香港出口則主要是上海製造的輕工業品、布匹、絲織品、油脂類、雜貨、蛋及蛋製品、麵粉等,其中棉紡織品成爲主打。③《新聞報》1938-12-30。(1)輕工業製品。1938—1941年間,上海的輕工業製品出口“旺勢空前”,主要輸往地是南洋地區(包括作爲南洋跳板的香港)。當時,所有全國出口的輕工業産品幾乎全由上海口岸輸出;而且輸往南洋地區的經營者,“十有八九是華商出口行”,租界的華商通過香港與內地溝通貿易。1938年,上海對香港出口額爲國幣3934.3萬元,翌年即達6076.3萬元。而同期上海從香港的年進口額卻衹有200多萬元。滬貨激增的主要是生活資料及金屬製品等。④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市國際貿易學會編:《上海對外貿易(1840—1949)》,下冊,第4、81、6頁。此外,上海運往印尼的物品中還包括大量的玻璃與玻璃器皿、搪瓷、鐵器及醫藥品;輸往泰國的物品中包括草帽、藥品、電燈泡、玻璃等大宗商品;輸往菲律賓的物品中包括電器用具、搪瓷器具、鐵器及食物;輸往香港的物品中包括大量的橡膠製品;輸往新加坡的物品則以玻璃、化學品、鐵器等爲主。(2)中藥材。香港是上海中藥材出口唯一的集散地。國外購辦中藥材的,都是在香港向華商經營的莊口採辦轉運。而上海向香港出口的藥材,一向由華商獨佔。滬藥材業同業公會的會員,在戰前有一百多家,“孤島”時期逐增至五百餘家。在“孤島”期間,國外對中藥材需求的長盛不衰,外匯上更有利可圖,因此,原來衹經營內貿的中藥行號也開始做起外貿生意來,其中經營出口的由十多家增至三十多家。上海華商藥材出口行的從業人員,甚至曾把“孤島”時期視爲該業的“黃金時期”。⑤張曉輝:《香港與近代中國對外貿易》,第231—232頁。
2.棉紗、棉布的出口。1939年,上海棉紗運往香港佔上海棉紗銷售總量的1/4以上,平均每月達7500餘件。⑥許維雍、黃漢民 編:《榮家企業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150頁。這種出口構成,與上海的工業結構有關。長期以來,上海一直是中國輕紡工業的中心,其他重工業則相當落後,因此,“孤島”可供輸出的主要是輕紡工業産品。在1941年7月江海關明令禁止棉貨出口前,上海棉紗、棉織品出口到南洋各地的價值在上海對南洋各地輸出貨值總額中所佔比重是,越南、印尼達70%,菲律賓、馬來亞爲60%,泰國、香港地區在50%以上。其中,棉紗是對印尼、香港等地的主要輸出品,棉布是對香港地區、菲律賓、泰國、越南等地的主要輸出品。
(六)上海從香港輸入的主要商品
1938—1941年,“孤島”輕工業製品對外貿易旺勢空前、畸形繁榮,上海租界的華商在香港與上海轉口貿易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上海從香港的年進口額卻遠遠低於出口額。①張曉輝:“論廣州淪陷後香港在中國外貿中的地位和作用”,《抗日戰爭研究》1(2003):88。在進口商品當中,自香港輸入的主要是糧食,以米、小麥、麵粉爲主。②張賽群:《上海“孤島”貿易研究》,第120頁。1938—1940年,糧食的進口一度達到上海進口總值的20%以上。
農、礦産品是上海自香港、南洋地區進口的主要商品,主要包括越南、泰國的稻米,印尼的汽油、煤油、糖,新加坡的橡膠、藥品、香料,越南和印度的煤、麻袋,澳洲的小麥、麵粉,以及印度和緬甸的棉花。另外,煤炭、石油、紙張、煙葉、化學製品等都是上海口岸主要的進口商品。據統計,1940年下半年,上海洋米進口共225萬公擔。其中,自越南進口169萬公擔,自泰國進口爲50萬公擔,自緬甸進口也有3.6萬公擔。③《中國經濟評論》1(1941):135。1941年1—11月,越南米運滬爲266萬公擔,緬甸爲256萬公擔,泰國爲82萬公擔。同期,上海自澳洲輸入小麥25萬公擔,麵粉16萬公擔。此外,1941年,上海進口洋煤99萬噸,其中越南輸入37萬噸,印度輸入8萬噸。同期,上海自印尼輸入的食糖與石油分別佔上海食糖、石油國外輸入總額的73%和82%。④王季深 編:《戰時上海經濟》,第1輯,第71頁。
綜上所述,考察香港與上海近百年的轉口貿易歷程,它大致分爲四個階段,每個階段又各具特點:(1)開港初期,中國主要的出口商品是茶葉和絲綢,産地都靠近上海,且主要産區與上海間有較爲發達的航運和航綫,上海因此有了其他四個口岸所沒有的地理上的通商便利。作爲新開港的口岸,從香港遷往上海的商人,可以在上海口岸的對外貿易中發揮自己的優勢。爲了擴大市場,獲取更大的利潤,香港可以在條約規定的條件下自由發展。在與中國其他港口的貿易中,它也可以自由尋找合適的華商充當買辦,採購所需貨物。(2)從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至19世紀末,香港在上海這個中國最大貿易中心的轉口貿易中的重要性不斷提高。絲綢、茶葉、北方的土貨以及上海港出口的雜貨,在上海出口中的比重逐漸擴大;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已成爲滬港貿易中重要的出口商品。(3)1900—1936年,香港與上海的轉口貿易進入一個新階段。20世紀上半葉,上海作爲中國外貿轉口中心的地位呈衰落態勢,糖、米、海產品逐步取代之前的鴉片貿易。在香港向上海轉口貿易過程中,上海南洋莊九八行起到了重要作用。(4)“八一三事變”後,上海成爲“孤島”,工商業遭受沉重打擊,港滬轉口貿易呈現出此起彼伏、衰旺不一的特點。1937—1938年,進出口業務極度衰落,上海貿易銳減,從前上海在東亞所擁有的繁榮被香港逐漸取代;廣州、武漢淪陷後,上海進出口業務重新回升。1939年9月以後,上海進出口畸形旺盛,港滬轉口貿易有開始暢旺。到1940年,日軍封鎖中國的沿海口岸,上海進出口貿易被迫停滯,自此一直持續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