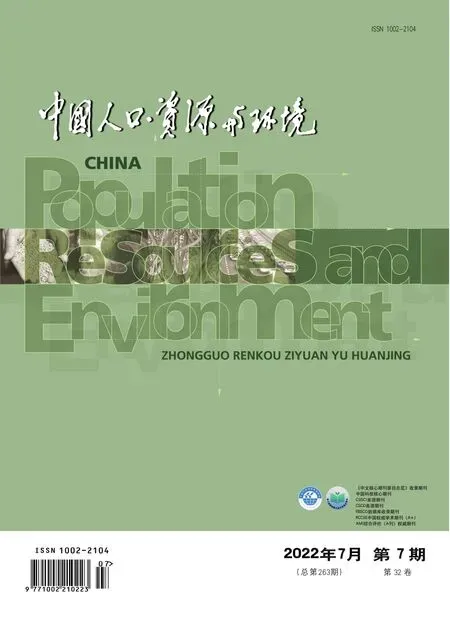乘用车燃油经济性标准研究进展:影响机制与政策评估
2022-08-15伍敬文
伍敬文,廖 华
(1.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广东广州 510642;2. 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100081;3.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北京 100081)
交通部门能源消耗和碳排放规模大、比重高、增长快,是关系各国碳中和目标实现的关键部门。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数据显示,2019 年世界交通部门能源消费几乎与工业部门持平,约占总量的29%,占碳排放总量的27%[1]。交通部门也是中国用能增速最快的部门(年均增速约9%),2019年占全国用能总量的15%,消耗石油2.8 亿t,占石油消费总量的52%。随着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交通部门是继工业、建筑业之后的第三大碳排放来源,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点部署领域。同时,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消费国,新车销量占全球三分之一以上;为控制汽车消费带来的能源环境问题,中国自2005年开始实行燃料消耗量标准,并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但目前新能源汽车受技术和基础设施限制,仍处于发展阶段。2020 年新能源汽车销量不足200 万辆,传统燃油车占比95%(2020 年全球电动车销量仅占4.6%[2])。根据《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到2025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将占新车销量的20%左右,到2035 年纯电动汽车将成为新车销售主流。根据2021 年10 月26 日国务院印发的《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到2030 年,当年新增新能源、清洁能源动力的交通工具比例达40%左右”,“陆路交通运输石油消费力争2030 年前达到峰值”。这意味着到2030 年,燃油车销量仍可能超过50%,未来十年燃油车的保有量仍可能持续增长。
因此,提高传统汽车能源效率仍是交通部门节能减排和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发力点之一。未来中国燃料消耗量标准趋严,2021 年9 月2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重点强调了要“提高燃油车船能效标准”。中国自2005 年实施燃料消耗量标准以来,2012 年加入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标准,2017 年工信部出台“双积分”政策表明要从传统燃油车节能和新能源汽车发展两方面实现交通部门绿色转型,2019 年对“双积分政策”进行修改再次凸显促进燃油车节能的重要性,2021 年开始执行第五阶段燃料消耗量标准。同时,燃料消耗量标准拓展到电动车领域和其他汽车市场,如国家标准局于2018 年底出台《电动车能量消耗率限值》。因此,燃料消耗量标准是中国汽车节能管理中的关键举措之一,加强科学分析和研究基础有利于提高政策节能效果。
IEA 将提高汽车能源效率视为是实现气候目标的重要措施[3]。为提高汽车能源效率(对应燃油效率),各国常使用燃油经济性标准(Fuel Economy Standard,FES)激励厂商投资汽车节能技术,从供给端鼓励企业提高汽车燃油效率。燃油经济性标准在不同国家由于规制对象不同而存在概念差异,如美国称企业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Corporate Average Fuel Economy(CAFE)Standards),欧盟称企业平均二氧化碳排放标准(Corporate Average CO2Emissions Standards),中国称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等。为统一,该研究主要使用燃油经济性标准概念,只在部分地方涉及中国政策时,简称“燃料消耗量标准”。回顾燃油经济性标准发展历程,历经40 多年,覆盖全球乘用车市场的80%,积累了大量文献对其进行讨论,是能源与环境经济领域的热点研究话题,相关研究发表在Scienc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等国际著名期刊上。尽管部分学者从政策层面和节能效果等对燃油经济性标准进行了综述[4,5],但该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学视角综合国内外研究梳理和归纳燃油经济性标准在实施过程中的影响机制和相关政策评估。首先梳理了燃油经济性标准的国别差异和发展趋势,接着从企业合规策略选择、消费者福利影响和政策有效性进行综述,旨在厘清燃油经济性标准的影响机制,明确研究不足。其次,结合中国燃料消耗量标准实践和国外经验,综述相关研究可为中国提供参考基础,加强政策制定的科学分析,有助于完善中国节能政策的制定、管理与实施。同时,燃油经济性标准不仅针对乘用车,也广泛实施于商用车、货车和新能源汽车,以及类似的能源效率标准也是耗能耐用品(如冰箱、空调等)中常见的节能政策。据国际汽车制造商(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Motor Vehicle Manufacturers)统计,2019—2020 年全球乘用车销量占汽车销售总量的70%,中国这一比例更高,占80%。鉴于乘用车的市场主导地位,且针对乘用车的燃油经济性标准实施时间更长,研究文献更为丰富,相关综述主要围绕乘用车市场展开。研究结论不仅可以为汽车行业内的政策提供参考,还可为其他耐用品市场的节能政策提供依据。
1 国内外燃油经济性标准比较
1.1 燃油经济性标准国际比较
燃油经济性标准最早可以追溯到1975 年,石油危机发生之后,美国在《能源政策与节能法案》中提出设定最低企业平均燃油经济性(Corporate Average Fuel Economy,CAFE)标准,旨在减少能源消耗和加强能源安全。该政策要求每个企业销售各车型加权平均的燃油经济性之和需满足法规要求。随后,燃油经济性标准逐步扩展到欧洲、日本、中国、韩国等国家或地区,几乎覆盖全球主要乘用车市场。其他国家或地区,如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也考虑实行类似政策以控制汽车排放。具体来看,各国或地区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上存在一定差异,表1总结了主要国家或地区实施的燃油经济性标准特点。

表1 主要国家或地区燃油经济性标准的实施特点
目前FES 主要是以控制燃料消耗量或温室气体为主,其中温室气体主要是限制二氧化碳排放,其他温室气体(如甲烷、含氟碳氢化合物、氧化亚氮、黑碳等)较少被纳入。相比,温室气体限制标准比燃料消耗量限制适用范围更广、更直接,可以合理反应不同燃料类型汽车的排放情况及不同空调系统的耗能情况,在应用上更为灵活;但温室气体限制标准只考虑汽车使用阶段,未考虑汽车上游生产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
在实施范围方面,起初燃油经济性标准主要针对整备质量在3 500 kg以下的乘用车。美国、欧盟等对轿车和轻型卡车分别制定标准。近年来,燃油经济性标准逐渐扩展到商用车、轻型货车、客车或三轮车等低速汽车领域,覆盖汽车类型也逐渐增加。
在实施结构上,美国第一阶段的燃油经济性标准设定了统一标准,即所有企业平均燃油经济性都要在一个限值之上。后为防止汽车生产小型化对交通安全的影响,在第二阶段开始按车轮面积大小设置限值。目前,大部分国家的标准是以车轮面积或重量大小分别设定,韩国最早按排量大小、后改为以重量为基准。
多数国家燃油经济性标准为强制性政策,但经济处罚措施较少。加拿大和欧盟一开始要求企业自愿履行,但效果并不理想,加拿大和欧盟先后在2007 年、2009 年将自愿履行改为强制履行。尽管该项政策在大部分国家是强制性政策,但相应惩罚措施仍然不明确或缺失,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政策严格性。目前只有美国和欧盟设置了罚款制度,其他国家惩罚措施并不明确,多数以取消生产资质、信息披露、口头警告等行政处罚为主。另外,部分国家或地区(美国、中国等)允许企业间进行积分交易与结转,增加了企业合规灵活度。
从标准严格程度上看,图1对比了主要政策执行国家或地区平均燃油经济性历史表现和未来标准。日本和欧盟燃油经济性标准的严格程度较其他国家高,中国在2021年后政策严格程度紧随其后。综合来看,欧盟、日本和印度的燃油经济性历史表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汽车更加节能。从政策制定进度来看,部分国家或地区已规划到2025 年或2030 年,但也有部分国家或地区出现停滞现象。后期政策也随汽车技术发展在不断调整,例如对节能技术实行优惠积分,将新能源汽车技术、其他燃料汽车包括在内等。

图1 乘用车燃油经济性国际对比
在测试工况上,各国测试工况存在差异,后逐渐采用统一测试工况全球轻型车油耗测试标准(Worldwide harmonized Light Vehicles Test Procedure,WLTP)。美国测试工况FTA 和欧盟新标欧洲循环测试(New European Driving Cycle,NEDC)应用范围较广,JC08 主要在日本使用;严格意义上,美国测试工况更为苛刻。近年来,考虑不同测试工况下汽车燃油消耗差异较大,2017年,欧盟、美国、日本、印度联合发布了WLTP,WLTP 更符合现实驾驶情况。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测试工况也逐渐采用统一WLTP,欧盟在2017 年,日本和韩国在2018 年,中国在2021 年开始采用WLTP。
1.2 中国燃油经济性标准演变
中国燃油经济性标准又称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简称“燃料消耗量标准”)执行近十六年,政策不断更新变化,与其他国家具有明显差异。表2 展示了中国燃料消耗量标准在各阶段实施特点。中国在2004年颁布第一个强制性燃料消耗量限值(Fuel Consumption Limits,FCI)标准之后,燃料消耗量具有明显下降趋势,但由于大型车需求不断增加、政策缺乏灵活性、不包括进口车等问题,限制了政策节能潜力[6]。第三阶段开始增加了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Corporate Average Fuel Consumption,CAFC)目标值,第四阶段增加“双积分”政策,政策逐步完善、增强了灵活性。

表2 中国各阶段乘用车燃料消耗量标准
中国燃料消耗量标准在不断加严,严格程度随重量增加而加严,图2展示了每一阶段的燃料消耗量标准。第一,从加严程度上(即不同阶段平均燃料消耗量限值之差的百分比),第二阶段比第一阶段加严10%,第三阶段加严19%,第四阶段加严31%,第五阶段延续加严趋势。第二,政策逐渐由阶梯形向平滑曲线过渡。起初,考虑中国汽车行业集中度不高、很多企业只生产特定车型,故采用以重量为基准[7]。到第五阶段,为防止汽车重量过度集中在某一重量范围,减少企业投机行为,政策由原来按重量分组的阶梯式改为以重量为参考的分段直线式。第三,鼓励小型汽车生产,第四阶段限值起点是980 kg,第五阶段是1 090 kg,给予小型车政策支持。第四,普通车辆限值和特殊车辆限值之间差异逐渐缩小。

图2 中国各阶段燃料消耗量标准
为代替补贴政策扶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2017 年工信部出台《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简称“双积分”政策),要求企业同时满足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CAFC)积分和新能源汽车(NEV)积分要求。CAFC 积分是指企业CAFC 达标值(燃料消耗量标准中规定的限值)和实际值(当年销售车型实际燃料消耗量)之间的差额乘以该企业乘用车生产或进口量,当实际值高于达标值时,企业获得负积分;NEV 积分是该企业新能源汽车积分实际值与达标值之间的差额,当实际值大于达标值时,企业获得正积分,达标值和实际值分别按双积分政策中的规定计算。双积分政策规定CAFC 负积分可通过NEV 正积分1∶1 抵偿,但CAFC 正积分不能交易。但在实际执行中,新能源汽车的优惠核算和双积分政策的单向结转机制促使传统燃油车油耗下降缓慢[8]。2019年对“双积分”政策进行修正,其中重要修正包括单独计算传统汽车CAFC,并规定CAFC 达到目标值一定程度时,才可以适用NEV正积分按50%比例结转,以及增加低油耗车型核算优惠(详见工信部《关于修改〈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的决定》)。相关研究发现“双积分”政策促进了新能源汽车发展,但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传统汽车油耗改进[9]。新能源汽车发展在实现交通部门碳中和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随着未来燃料结构转向电力、生物质能源及氢能等[10],未来燃油经济性标准是否将退出历史舞台,还是将如何改进以适用于其他能源类型都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2 企业应对燃油经济性标准的策略选择
燃油经济性标准规定企业销售车辆平均燃油经济性需要满足一定水平,没有规定企业采用何种方式,给予了企业较大选择空间。Klier等[11]总结到企业可采取三种策略满足CAFE标准:短期价格调整,中期调整汽车性能(国际上常用“attributes”表示,代表汽车重量、功率、加速度等性能参数[3,13],结合中国语境,简称为“性能”),长期采用技术进步。除了这三种策略,部分学者还发现厂商采用投机策略或政策漏洞来满足燃油经济性标准。
2.1 技术进步
在长期(10年左右),加强技术研发和投入,改进发动机技术、变速器系统、车身设计等,可提高汽车燃油效率,即为技术进步。为研究燃油经济性标准与技术进步关系,部分学者采用汽车微观数据展开研究。由于汽车燃油效率和其他性能(如重量、功率、加速度)密切相关,此类性能变化和技术进步都会引起燃油效率变化,故在研究中需要控制汽车性能变化[12]。
早期部分学者通过描述性统计表明汽车其他性能改进抵消了用于提高汽车能效的技术进步。Knittel[13]表明企业面临满足燃油经济性标准和消费者对汽车其他性能需求之间的权衡(Trade-off),技术进步一方面要用于汽车重量、加速度等性能增加,另一方面要用于提高汽车燃油效率,在控制汽车性能不变情况下,燃油效率将提高60%。在此基础上,更多学者进行了拓展。例如,MacKenzie 等[14]在原模型基础上加入更详细汽车性能,Ullman[15]则是对比了不同级别车型技术进步,Hu 等[12]关注欧洲市场,也有部分研究关注中国汽车市场的燃油效率和技术进步[16-17]。
部分研究表明燃油经济性标准加严、油价变化可促进技术进步[13-14]。Klier等[18]利用美国和欧盟数据发现燃油经济性标准加严提高了技术进步。Kiso[19]利用1985—2004年的日本数据发现燃油经济性标准对汽车燃油技术进步具有显著影响,至少使燃油经济性提高3%~5%。Wang 等[20]利用1978—2018 年的美国数据发现燃油经济性标准提高了轿车的技术进步。
2.2 汽车性能调整
在中期(4~5年),企业通过调整汽车性能而达到燃油经济性标准的行为可分为两类。一方面,由于汽车燃油经济性和其他性能存在较强相关性,降低汽车重量、功率等可提高汽车燃油经济性以达到合规要求。如部分文献发现在政策加严时期,汽车性能呈现出下降或增长缓慢现象;而在政策不变期间,汽车性能改进显著[14,21]。另有研究从工程设计和技术角度,发现环境规制会促使企业重新优化产品,实现以最小成本满足合规要求。如Whitefoot 等[22]发现在CAFE 标准和温室气体排放标准改革后,厂商利用汽车加速度性能和燃油经济性之间的权衡来降低合规成本。
另一方面,燃油经济性标准多基于汽车重量或车轮面积设定标准值,越重或越大的汽车面临标准越为宽松,容易促使企业调整汽车重量从而降低企业达到标准的难度,使车型聚集在政策宽松一侧。此类研究早期多集中在劳动经济学或税收政策领域,随着数据可获得性提高,其他领域也逐渐受到关注。Ullman[15]对美国汽车制造商达标预测分析中发现,美国基于车轮面积的标准将促使制造商增加车辆尺寸以降低合规负担。Hao 等[23]利用中国2014年数据发现阶梯型燃料消耗量标准使汽车重量分布过度集中地在重量段前端,重量增加间接抵消了部分节能效果。Ito等[24]利用日本汽车数据发现以重量为基准的燃油经济性政策显著地改变了汽车重量分布,汽车重量增加带来的交通安全问题造成了大量福利损失。更有研究表明,此类政策改变了企业采用两种策略(技术进步或性能调整)的边际成本,对技术进步产生扭曲[25]。与上文企业降低汽车性能不同,此类性能调整行为为利用政策设计特点,增加汽车重量或尺寸以放宽合规要求。
2.3 其他策略
在短期(1~2年)采取价格调整,企业通过降低节能汽车价格和提高耗能汽车价格来改变汽车销售结构,以提高企业平均燃油经济性;但该策略对燃油经济性的改进较小,且成本较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经济效益,只适合短期且较小幅度的油耗调整[26-27]。
当环境矫正政策存在漏洞或有机可乘时,可能会促使企业采取投机行为或“耍花招”来满足环境规制。早期美国CAFE 标准中规定企业生产具备其他燃料类型的汽车可以获得额外奖励,这导致汽车制造商通过改装传统燃油车为多种燃料装置汽车来放松合规压力[28]。同样,中国燃油经济性标准对新能源汽车具有超额积分奖励,企业除了提高传统汽车燃油效率,也可以通过多生产新能源汽车来降低合规压力[29]。也有学者发现企业通过油耗测试造假来满足标准,如大众汽车尾气排放丑闻。当欧洲引进二氧化碳排放标准时,汽车实际路况油耗和官方油耗之间差距变大,即厂商通过降低官方测试环境下二氧化碳排放而不是实际路况中碳排放量来满足标准[30]。Reynaert[31]进一步对道路燃油效率的估计中发现只有30%的技术进步转化到实际道路上,剩下70%的技术进步只存在于实验室测试环境中,不是真实的有效改进,指出此类环境规制执行中存在的危机。
3 燃油经济性标准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3.1 消费者对汽车能源效率的认知程度
提高终端用能产品能源效率被认为是减少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途径。但是,能效越高的产品价格较高,消费者常面临前期投入成本与未来使用成本之间的权衡,Hausman[32]指出理性消费者在购买决策时应考虑未来使用成本。但现实中常观察到消费者对具有明显节能潜力的技术采用率较低,导致实际能源使用与最优使用之间存在差距,被称为能源效率差距(Energy Efficiency Gap)[33]。在消费者低估汽车能源效率情况下,生产商缺乏动力提高汽车能源效率,汽油税或碳税将不会影响消费者对汽车的购买决策。相反,燃油经济性标准要求企业销售新车的平均燃油经济性要达到特定水平,从生产端提高整体销售新车的燃油经济性,直接减少消费者使用成本,提高消费者福利,这也是燃油经济性标准的支撑条件之一。因此,消费者是否低估能源效率直接关系政策成本效益分析和福利评估。但现有研究对汽车市场上是否存在“能源效率差距”持不同观点。
早期研究中,享乐模型(Hedonic Model)常用于估计消费者对汽车不同特征的支付意愿。随着石油安全问题突出,享乐模型被广泛地用于研究消费者对汽车能源效率的支付意愿,并评价消费者是否低估汽车能源效率。Espey 等[34]利用美国数据得出消费者理性地内部化了汽车未来燃料成本,不存在低估。Chugh等[35]基于印度乘用车市场数据,对比燃油效率改进的边际成本和未来节能潜力,得出消费者高估汽车能源效率。但有学者指出Hedonic 模型在处理多重共线性、遗漏变量等问题上表现不佳,估计结果缺乏稳健性[36]。
离散选择模型逐渐应用于估计消费者对汽车能源效率的支付意愿中。此类研究基于汽车销售数据、或调查数据结合随机系数模型(Random Coefficient Model)估计消费者对汽车不同性能的偏好。Busse 等[37]利用美国新车销售和二手车交易数据估计油价变动对不同燃油经济性汽车交易价格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发现油价上升可显著提高节能汽车销售价格和市场份额,且消费者没有低估燃油经济性价值。Sallee 等[38]利用二手车销售数据估计预期使用成本对二手车销售价格的影响,发现汽车价格随预期使用成本发生同比例变动,表明消费者重视燃油经济性价值。表3 总结了有关消费者是否低估汽车能源效率的研究,发现尽管是依赖于详细微观数据,研究对象相同,结论仍存在较大差异。此外,现有研究多来自发达国家,较少关注发展中国家。作者利用月度汽车销量数据结合需求估计模型发现总体上中国消费者不存在低估[39],但其他类似研究发现中国消费者对热水器的能源效率意识存在低估[40]。

表3 消费者对汽车燃油效率评价的结果对比
3.2 消费者对汽车各类性能的偏好程度
当汽车市场存在“能源效率差距”时,燃油经济性标准加严将会有效提高消费者福利;但如果考虑燃油经济性标准对汽车其他性能(尺寸、功率、加速度等)的影响,该论断不一定成立[45]。燃油经济性标准加严一方面提高了汽车燃油效率,节约消费者使用成本;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可通过降低汽车其他性能以提高燃油效率,如果消费者对汽车其他性能的支付意愿较高,那么燃油经济性标准的加严将降低消费者福利。因此,标准加严产生的福利影响取决于消费者对汽车能效和其他性能的支付意愿,相关分析应考虑二者作用大小。Klier 等[18]发现在燃油经济性标准加严时期,企业采用降低汽车马力或扭矩的举措造成的福利损失是不可忽略的。Lin 等[46]发现欧洲二氧化碳排放标准加严大幅度降低了汽车性能,由此导致的福利损失抵消了约25%的政策减排效益。也有研究发现即使在存在“能源效率差距”的情况下,燃油经济性标准加严引起的汽车性能下降带来的消费者福利损失与燃料节省所带来的福利收益相当,得出标准加严对消费者私人福利影响为零[45]。
3.3 其他影响渠道
(1)对整体汽车更新影响。燃油经济性政策加严会提高新车销售价格,增加消费者新车购买成本,促使消费者转向二手车消费市场,增加二手车使用年限,使整体汽车更新变慢,降低消费者福利[47-48]。
(2)交通安全。美国第一阶段统一的CAFE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企业改变销售组合,使汽车市场偏向于更小、更轻汽车,从而带来安全隐患,随着第二阶段CAFE政策改为以车轮面积为基准,可在一定程度减低安全隐患[49]。也有研究表明CAFE 政策加严增加了汽车重量分散程度,总体上降低了汽车平均重量,降低车祸死亡发生率,每年产生35亿元收益[50]。
4 燃油经济性标准的有效性评价
4.1 政策节能效果评估
燃油经济性标准的主要目的是激励厂商提高汽车能源效率,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故其节能效果是评价政策有效性的主要依据。Bezdek 等[51]通过政策模拟表明CAFE 政策加严每年可减少石油消耗800 多万t。另有学者收集18个国家汽车燃油经济性、标准、油价和收入等变量建立计量模型得出FES 可以有效提高汽车燃油经济性[52]。Greene 等[53]发现1975—2018 年美国交通部门减少了53 亿t 汽油和170 亿t 二氧化碳排放,其中五分之四是由燃油经济性或温室气体标准驱动。
能源效率提高是否带来预期节能效果常受到“回弹效应”影响,对诸多能源效率类政策提出了挑战[54]。如果消费者购买节能汽车会促使其行驶里程增加,那回弹效应会削弱CAFE标准减排潜力。但是,已有研究认为回弹效应的影响在10%之间[55],也有研究表明影响较小[56]。此外,燃油经济性标准只规制新车市场,缺乏对二手车市场管制,容易造成“二手车泄露”。早期研究指出燃油经济性标准加严会提高新车销售价格,其中对大型车和高耗能汽车的影响更为明显,这将导致二手车市场均衡价格上升,车主延迟报废计划[47],大型车和高油耗汽车使用年限延长,限制政策节能效果。Jacobsen等[48]发现燃油经济性标准使高耗能二手车报废率降低,服务年限延长,抵消了预期节能效果的13%~16%。
4.2 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
对燃油经济性标准开展评估或成本效益分析是政策评估中的重要环节,以便厘清政策作用机制、衡量各影响因素大小和识别政策的整体福利影响。燃油经济性标准成本效益分析需充分考虑消费者行为(如消费者对新车和二手车的选择、对汽车性能的权衡、出行行为和车辆报废计划等)、汽车制造商的应对行为(如企业采取不同合规策略的边际成本)、外部性影响(交通安全、空气污染等),以及各因素之间的交互影响[57]。此外,燃油经济标准成本效益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消费者是否低估汽车能源效率[58]。因此,燃油经济性标准的评估涉及多方面因素,是一个复杂建模问题。
早期,Goldberg[59]将汽车需求和利用的分解模型与寡头垄断和差异化产品的供给模型相结合,考虑企业可采用价格策略和产地调整来满足CAFE政策,从汽车使用和车队组成角度评估美国CAFE 政策短期影响。基于同样模型思路,Austin 等[60]在价格策略基础上考虑技术进步,从长期估计CAFE政策减少了10%的石油使用成本;相比于汽车制造商,消费者承担了更多成本。Klier 等[61]从价格调整和汽车性能调整角度发现CAFE 政策的中期成本明显低于短期。Jacobsen[62]将研究从新车市场扩展到汽油市场、二手车市场,以及总体的福利影响,且充分考虑了企业和消费者异质性;得出当考虑二手车市场时,CAFE加严对石油消费的长期影响会随着政策对二手车市场的渗透影响而增大,且价格上涨和二手车车队组成变化导致低收入家庭福利损失更大,政策总体福利影响为负,且消费者承担了更大福利损失。同时,鉴于汽车燃油经济性和其他性能的关系,政策评估中忽略二者权衡关系可能会高估企业合规成本和低估政策减排效果[22]。Reynaert[31]进一步考虑企业采用价格策略、技术进步和油耗测试作假策略的边际成本及其对市场均衡结果的影响,通过供需结构模型评估了欧洲二氧化碳排放标准的整体福利影响,发现政策福利影响为负;但在考虑政策外部性影响(交通安全、空气污染等)和纠正消费者对燃油经济性低估时,政策具有较小的正向影响。Greene 等基于翔实数据和文献证据表明美国燃油经济性标准有效地较少了石油消费和碳排放,提高消费者福利,经济效益明显[4]。Bento等[63]提出了一个多市场相互作用的研究框架分析政策总体福利影响,纳入了新车和二手车市场、消费者车辆报废计划,同时考虑了消费者是否低估汽车能源效率、里程效应和汽油市场效应,及外部性影响。
4.3 与其他政策的比较分析
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汽油税或碳税比燃油经济性政策更有效,引发了大量学者对两类政策的比较与讨论。Anderson 等[5]指出,尽管FES可以激励厂商生产和销售节能汽车,但只针对新车;相比,汽油税或碳税是对所有使用者征收,不仅影响新车购买者,还影响车主使用行为、二手车市场,以及其他部门。Austin 等[60]比较CAFE 标准和汽油税减少石油消费的成本,发现提高汽油税的成本比CAFE 标准低71%。Jacobsen[62]从企业异质性角度,同时考虑CAFE政策加严对新车市场和二手车市场的影响,发现CAFE 政策对每t 二氧化碳的减排成本是汽油税的3~6倍。Kellogg[64]发现在未来汽油价格不确定时,奖惩兼具(Feebate,对节能汽车补贴,对耗能汽车征税)可以达到最佳福利效果,而固定燃油经济性标准将导致在油价较低时过高的减排成本和油价偏高时较低的减排成本,带来福利损失。Levinson[65]表明CAFE 标准与汽油税相比,成本具有累退性特点,即低收入家庭承担更多。进一步,Davis 等[66]发现在新车市场上,CAFE 的影响是轻度累进的,但纳入二手车市场时,CAFE 相比于汽油税却是轻度累退的。
5 结论与讨论
燃油经济性标准的实施历史较长、范围广,是交通部门主流的节能政策,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碳中和目标中扮演重要角色。该研究综合各国的燃油经济性标准,从企业和消费者层面综述燃油经济性标准的影响渠道及其有效性讨论,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和启示:
(1)在燃油经济性标准的国际比较方面:各国的燃油经济性标准几乎具有相近的执行框架,但在严厉程度、惩罚措施、交易制度和设计形式方面具有明显区别。燃油经济性标准逐渐从乘用车扩展到其他交通工具,应用范围逐步扩大。但随着未来燃料结构转向电力、生物质能源及氢能等,燃油经济性标准在如何对待和核算新能源汽车方面上存在挑战。
(2)在企业应对燃油经济性标准的策略选择方面:由于燃油经济性标准对企业生产实施了一定约束,企业通常可采取价格调整、汽车性能权衡和技术进步来满足标准,多项研究表明在燃油经济性标准加严时期,企业在长期会加大技术进步以提高汽车燃油效率。除此之外,企业的合规策略中也存在投机行为,如增加汽车重量或尺寸、油耗测试作假等。此类反应行为在评估燃油经济性标准的影响时至关重要,同时也对燃油经济性标准的有效性提出了较大挑战。未来的燃油经济性标准设计需全面深入地考察企业应对行为,减少政策漏洞和企业造假行为。
(3)燃油经济性标准对消费者福利影响方面:燃油经济性标准政策有效性还与消费者的能源效率意识有关(即是否存在“能源效率差距”),但消费者是否低估汽车能源效率的研究还没有统一结论。消费者对汽车能源效率的评估关系到燃料消耗量标准的成本效益分析,是相关分析中的重要内容。相关研究随数据可获得性和建模方法改进而变化,但有关研究存在研究对象、数据、估计方法等差异,得出消费者对汽车能源效率有高估、低估、或完全评估的结论。即使是针对同一国家,使用同质数据和方法,研究结论仍然存在差异。除此之外,消费者对汽车其他性能的偏好和支付意愿也是评估燃油经济性标准对消费者福利影响的重要因素。
(4)燃油经济性标准有效性评价方面:多数研究表明燃油经济性标准节能效果显著。尽管能源效率提高导致的“回弹效应”和二手车的延迟报废会削弱节能效益,但相关研究得出该影响范围分别在10%左右,政策总体节能效果仍然可观。其次,燃油经济性标准的成本效益分析需要考虑政策对企业、消费者及其他影响,涉及新车市场、二手车市场和汽油市场,影响因素多、建模复杂、对数据要求高,结果充满较大不确定性。相关研究常依赖于较长时间历史数据,包括详细汽车配置和油耗信息,不同车型更新变化、销售价格和销量等;同时还需要消费者对不同车型的选择、使用和报废等方面数据。由于涉及因素较多,相关分析在研究方法和建模方面存在较大挑战。如建模过程中需要假设汽车行业市场类型、汽车性能是内生还是外生、模型是静态还是动态,以及需要考虑其他政策(燃油税、补贴等)的共同作用。现有研究对燃油经济性标准评估大多只纳入了部分影响因素,较少从全局给出总体估计,同时受限于面板数据较难获取,多为静态模型。
综合,现有研究证据更多来自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汽车工业发展历史较长、政策历经时间较长、数据信息管理和收集较为完善,有利于开展相关研究。例如,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开展的全国性居民交通出行调查为研究交通政策、汽车消费和消费者出行行为提供了数据来源。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是政策起步较晚,较多借鉴其他国家执行框架;另一方面,数据收集和管理是发展中国家的薄弱环节,限制了相关研究的开展。但是,鉴于各国政策差异、汽车工业发展历程、市场发展程度和消费者偏好差异,有必要对各国燃油经济性标准开展针对性研究。
中国从2005 年开始实行燃油经济性标准(即燃料消耗量标准),是汽车节能管理的重要支撑标准之一。作为提高汽车能源效率的主要政策,如何提高燃料消耗量标准的节能效果受到诸多挑战。由于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支撑,导致政策执行过程中不断调整,且不同政策相互影响,缺乏稳定性和长期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达标的动力和积极性,节能效果并不理想。例如,在政策执行前三阶段(2005—2015 年),汽车油耗年均下降不足2%,能效提升缓慢[67]。新能源汽车优惠核算和双积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提高传统燃油车能效积极性[68-69]。尽管有不少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关注到中国燃料消耗量标准的影响,但受限于数据可获得性和研究方法局限,相关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全面,未来中国应加强相关数据收集和管理。在研究内容上,中国有关研究多集中在企业对政策的响应行为上,较少关注政策对消费者的福利影响。另一方面,区别于其他国家,中国的燃油经济性标准对新能源汽车具有较大的扶持力度,政策对传统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市场同时产生影响;但相关研究较多集中在新能源汽车市场,较少将二者同时纳入模型进行分析。未来政策修正前应加强分析和研究,例如,目前的多项政策(燃油经济性标准、双积分政策、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碳交易等)并行实施是否相互影响、政策设计是否合理、未来如何改进等都亟须科学分析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