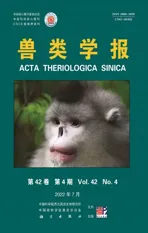重引入对麋鹿种群分娩定时及同步化的影响
2022-07-25孟庆辉柏超宋苑单云芳李俊芳张树苗白加德钟震宇张成林孟秀祥
孟庆辉 柏超 宋苑 单云芳 李俊芳 张树苗 白加德 钟震宇 张成林 孟秀祥
(1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北京 100076)(2国家鹿类保护研究中心,北京 100076)(3圈养野生动物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动物园,北京 100044)(4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北京 100081)
重引入生物学(reintroduction biology)指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将濒危物种精准引入已灭绝栖息地使种群再恢复的一门学科(Doug and Philip,2008)。保护濒危物种、文明对待生态资源是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基础(Liuet al.,2007)。濒危物种在曾灭绝地的持续繁衍是重引入生物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张付贤等,2022);对于重引入的濒危鹿类,调整其采食、消化节奏和生殖步调,使种群在原栖息地恢复并与生境植被逐渐重匹配,可实现在曾灭绝地的持续生存和繁衍(Whitinget al.,2012)。因此,研究重引入物种的分娩定时及同步化尤为重要,直接关系到濒危物种的可解濒程度。
研究不同迁地间和迁地前后种群的同步繁殖规律,不仅可为迁地保护及管理者提供精准的繁殖节律信息,而且还可为濒危物种的重引入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如利用牛和羊的同步繁殖策略,可节省饲养管理成本(周鼎年,1984;曹斌云,1994;王忻等,2009);对濒危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同步排卵的监测,可判定最佳的人工授精时机(刘维新等,1996)。目前鹿科动物的同步繁殖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4个领域:(1)同步繁殖与维度的关系:随维度增加,繁殖跨度逐渐缩小(Rutberg,1987);(2)出生同步与采食生态位的关系:如出生与牧草返青高度及牧草干物质的匹配研究(Leuthold and Leuthold,1975;Skinneret al.,2002);(3)出生同步与反捕食策略:如驯鹿(Rangifer tarandus)(Dauphine and McClure,1974;Adams and Dale,1998)、马鹿 (Cervus elaphus)(Smith and Anderson,1998)、驼鹿 (Alces alces)(Testaet al.,2000)、叉角羚(Antilocapra americana)(Gregget al.,2001)、狍 (Capreolus capreolus)(Panzacchiet al.,2008)等利用繁殖同步的产仔密度优势,降低后代遭遇天敌的损耗;(4)出生同步与交配制度的关系:多配制较单配制物种有更明显的出生季节性(Laneet al.,2010)。目前,迁地保护和物种重引入对繁殖节律的影响还尚未见相关报道。
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是我国特有的濒危物种(蒋志刚等,2006),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IUCN名录中为“野生灭绝”(蒋志刚等,2006)。1985 年从英国乌邦寺 (北纬51°58′,西经00°35′)重引入北京市大兴区南海子湿地(北纬39°46′,东经116°27′)(张付贤等,2022),截至2021年中国麋鹿种群数量已达10 000头(张付贤等,2022),是成功重引入的3个标志种之一(蒋志刚等,2006)。然而从灭绝时隔85年,从英国乌邦寺到北京南海子北纬近12°跨度迁移(宋玉成等,2015),重引入麋鹿种群是否适应原栖息地气候和生境?分娩节律发生哪些变化?这些仍是今天亟需回答的科学问题。本文对北京麋鹿种群重引入37年来繁殖同步化规律进行研究,可为濒危物种重引入及迁地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麋鹿种群概况
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又名北京麋鹿苑),是麋鹿在中国灭绝85年后,在原栖息地为重引入而复建的半散养模式保护区。保护区平均海拔9.6 m,占地60 hm2,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均气温13.1℃,极端低温-27.4℃,极端高温43.4℃,平均昼夜温差10℃~15℃;年均降水量约600 mm,邻永定河和凉水河,常年湿度在30%~70%,年均日照5 000~6 200 h,无霜期(132±9.7)d(程志斌等,2020)。
该中心分别于1985年和1987年从英国乌邦寺重引进麋鹿20头和18头[平均(14.45±0.51)月龄](张付贤等,2022)。截止目前共繁殖F21代(以1985年从乌邦寺重引入的记为F0代)。
1.2 动物样本及分组
从1985年重引入麋鹿以来,北京种群采取自由采食、饮水、活动、交配、产仔(未人工干预)的管理模式。冬季适当补饲青贮苜蓿,一天两次,时间分别为08:30和15:30,其他季节均自由采食保护区内湿地植物(孟玉萍等,2010)。
1.3 种群分娩数据收集
北京麋鹿种群分娩数据来自麋鹿重引入以来的资料记录和退休老职工记录的分娩数据等。本文采用1987年总30头麋鹿分娩数据,1997年总29头分娩数据,2007年总34头分娩数据,2017年总46头分娩数据。乌邦寺种群1980年首例分娩时间为1月25日,最后一例为9月5日**冰雪玉,鲍裕民主编.唯瑜(译).2018.我在中国三十年——麋鹿回归中国以及其它故事.38.。
本研究将重引入后1987年(重引入后成功分娩的第一年)定义为初级阶段;1988—1997年为重引入定植阶段;1998—2007年为种群扩繁阶段;2008—2017年为种群复壮阶段。
1.4 北京麋鹿苑环境数据
气象数据:2016年8月—2017年7月的气象数据由北京市气象信息中心提供,站点为大兴站(站号54594),距离研究地点10.3 km;选择气温(月平均气温)、降水(月总降雨量)、累积光照(母鹿妊娠期内的逐日光照之和)、积温(母鹿妊娠期内≥10℃日均气温总和)等气候数据。1987年、1997年、2007年的气温、降水和光照数据来自国家气象信息中心(http://data.cma.cn/)。
地上生物量测定:2016年8月—2017年7月每月的第1周,在湖底典型放牧地段上设置50 m×20 m样地,沿长每10 m划分一个观测区,面积为0.25 m2,齐地面剪下样地内所有地上植株称其鲜重,装信封带回实验室,置75℃烘箱,烘12 h后称重,后每2 h称重一次,直至恒重,测地上生物干重(孟庆辉等,2016)。1987年、1997年、2007年的地上生物量参考自北京麋鹿苑周围永定河山区(直线距离为15~20 km)草地植被数据(杜勇等,2021)。
1.5 数据整理及分析方法
同步化率:以每年最早分娩日作为参照基准日,之后个体分娩距此参照基准日的天数(Rutberg,1987);同步化率25%、50%(Rutberg,1987;Zerbeet al.,2012)、75%和100%(孙军平等,2017)分别以分娩数量占年度总分娩数的百分比计算。非同步化率=1-同步化率。
光照与积温数据:母鹿妊娠期(8月交配结束至来年4月分娩开始)内,取累积光照和每日积温均值进行计算。
分析方法:因分娩数据呈现轻度的正偏态分布(Kolmogorov Smirnov test:Z=2.670,n=138,P=0.006),采取开平方的方法进行转换,实现数据正态化(Kolmogorov Smirnov test:Z=1.024,n=55,P=0.141)。光照与积温数据首先采用ANOVA分析,若差异不显著(P>0.05),再基于方差齐性检验结果,选用LSD进行逐项比较计算降水、地上生物量与麋鹿分娩节律的相关性(孙军平等,2017)。
2 结果
2.1 重引入麋鹿种群的分娩时间
北京麋鹿种群总分娩数据139例(图1)。2—7月分娩,高峰在5月12日(xˉ=12.46±0.63,df=138,P=0.001 5),最早为2月25日,最晚为7月25日。分娩期总跨度为109~150 d(129.37±20.14,n=139),其中重引入后首次分娩(1987年):分娩期跨度116 d;重引入定植阶段(1997年):109 d;扩繁阶段(2007年):132 d;复壮阶段(2017年):150 d。

图1 北京重引入麋鹿种群不同阶段分娩日期变化Fig.1 The fawning data of Père David’s deer reintroduction stage by Beijing
1985年麋鹿重引入北京南海子,1987年首次分娩产仔,较乌邦寺麋鹿1980年分娩日推迟31 d,平均推迟35~42 d,分娩结束较乌邦寺早77 d。重引入定植阶段(1997年):麋鹿种群分娩启动较1987年推迟43 d,种群分娩结束较1987年推迟35 d;整个种群分娩期跨度较1987年减少了8 d。扩繁阶段(2007年):分娩启动较1997年提前9 d,分娩结束较1997年提前5 d,整个种群分娩期跨度较1997年延长4 d。复壮阶段(2017年):分娩启动较2007年提前11 d,分娩结束较1997年提前13 d,分娩期跨度较2007年提前2 d(表1)。

表1 重引入后北京南海子麋鹿分娩数据Table 1 The fawning data of ex-situ conservation Père David’s deer by Beijing Nanhaizi
重引入定植阶段麋鹿新种群繁殖节律逐年延迟;扩繁阶段种群分娩日期逐渐稳定,分娩启动逐年提前;复壮阶段分娩逐渐微回调,整体呈现“钟摆样”波动。但整个分娩周期跨度无明显变化 (图2)。

图2 重引入的北京麋鹿种群与乌邦寺种群(1980)的繁殖节律比较Fig.2 The parturition rhythm data of the reintroduced Beijing and Woburn Abbey Père David’s deer
2.2 重引入麋鹿新种群分娩同步化
分析1987年、1997年、2007年、2017年北京麋鹿种群的分娩数据,显示种群分娩有较强季节性定时和同步化。其中5月5日至7月1日为集中产仔期,分娩较为同步(表2);重引入定植阶段(1997年)同步化率为68.97%;扩繁阶段(2007年)同步化率为70.59%;复壮阶段(2017年)同步化率为69.57%;1987年3月10日至4月5日的26 d,同步化率为84.62%。

表2 北京南海子麋鹿分娩季节同步化和非同步化分析Table 2 The synchrony and asynchrony of Père David’s deer by Beijing Nanhaizi
北京麋鹿种群不同阶段分娩同步化率不同(表3)。重引入后首次分娩(1987年):同步化率0~25%为18 d,25%~50%为14 d,50%~75%则仅用时5 d;重引入定植阶段(1997年):同步化率0~25%为41 d,25%~50%为19 d,50%~75%则用时11 d;扩繁阶段(2007年):同步化率0~25%为45 d,25%~50%为10 d,50%~75%则只用时9 d;复壮阶段 (2017年):同步化率0~25%为34 d,25%~50%为20 d,50%~75%则只用时11 d。

表3 北京南海子麋鹿种群分娩同步化分析Table 3 Analysis of Père David’s deer synchrony by Beijing Nanhaizi
2.3 物候与麋鹿新种群分娩的关系
2.3.1 光照和积温与麋鹿新种群分娩启动的关系
麋鹿分娩启动日期与累积光照和积温有很大关联(图3),此处采用的光照和积温数据为麋鹿重引入后1985—2021年北京的平均物候数值,结果显示:当积温达到(2748.34±157.69)℃,累积光照达到(3684.77±514.26)h,麋鹿开始启动正常分娩。累积光照(r=0.891 0,n=46,P=0.006 1)和积温(r=0.753 5,n=46,P=0.009 0)对分娩启动的影响差异极显著,对分娩同步化无显著影响(F1,46=2.911,df=45,P=0.646 0)。

图3 麋鹿妊娠期累积光照和积温与出生率的关系Fig.3 Relationship between accumulated sunlight,temperature and birth rate of Père David’s deer pregnancy
2.3.2 降水量和生物量与麋鹿新种群分娩节律的关系
麋鹿的分娩峰期与栖息地单位面积地上生物量峰期相关(r=0.785 6,n=46,P=0.251 9),与降水量相关(r=0.927 1,n=46,P=0.000 8)。北京麋鹿新种群35年的平均分娩峰期为4月12日,降水和单位面积地上生物量平均峰期为5月12日至10月22日,与幼龄麋鹿出生后1~2月龄断奶采食牧草日期相吻合。
2.3.3 新种群麋鹿分娩对重引入地的恢复适应
将每年的平均分娩日和地上生物量峰值的间隔期比较,其中重引入后首次分娩(1987年):平均分娩日较地上生物量峰值期提前108 d;重引入定植阶段(1997年):平均分娩日较地上生物量峰值期提前11 d;扩繁阶段(2007年):平均分娩日较地上生物量峰值期提前47 d;复壮阶段(2017年):平均分娩日较地上生物量峰值期提前56 d(表4)。

表4 平均分娩日与地上生物量峰值的关系Table 4 Relationship between average birth day and peak aboveground biomass
3 讨论
3.1 光周期对麋鹿新种群分娩期跨度的影响
重引入定植阶段:重引入造成麋鹿种群分娩节律提前,但对分娩期跨度影响不大。这一阶段,平均产仔日期为3月27日,地上生物量峰值在7月17日,与分娩时间差为108 d左右。麋鹿幼仔产后一周左右采食牧草,50 d后陆续断奶,开始大量进食,但牧草尚未达到峰期(梁崇岐等,1993)。此阶段增加了母鹿的负担(杨道德等,2007),尚需母体继续哺乳和抚育,一方面影响幼仔的生长、生茸、越冬体重和存活率;另一方面也会使母鹿产后恢复较慢,推迟发情(孟庆辉等,2022),影响受精率、来年分娩日期和出生幼仔体重等(Zerbeet al.,2012)。
扩繁阶段:麋鹿分娩节律逐年推迟。重引入10年后,种群分娩时间整体向后推迟(39.05±5.23)d,年均推迟(3.90±0.24)d。此阶段,平均产仔日期为7月1日,地上生物量峰值为7月12日,与分娩时间差11 d左右。此阶段牧草地上生物量峰期来临,减轻了母鹿哺育幼仔的压力(孟玉萍等,2010),对母鹿影响较小,但因分娩推迟,减少了秋后幼仔的采食天数(孟庆辉等,2016),降低了幼仔越冬体重和冬季存活率,且使幼仔鹿茸生长和发情等延迟一年,造成繁殖劣势(杨道德等,2007;孟庆辉等,2022)。
复壮阶段:麋鹿分娩时间又逐渐微回调。种群分娩时间微回调了(19.14±0.86)d,年均提前了(1.91±0.08)d。此阶段,平均产仔日期为5月28日,地上生物量峰值为7月14日,与分娩时间差为47 d,2017年产仔平均日期为5月20日,地上生物量峰值为7月15日,与分娩时间差为56 d。此阶段种群分娩处于较为合理的区间内,母体恢复体况和幼仔发育都处于较好的时期(张付贤等,2022),利于母鹿继续发情繁殖和幼仔发育(Rutberg,1987)。
因此,单从分娩时间来看,麋鹿新种群已经逐渐恢复了对北京南海子湿地气候的重适应。重引入的麋鹿分娩节律和分娩期跨度与江苏大丰和湖北石首的麋鹿重引入种群是否表现类似,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3.2 重引入不同阶段对麋鹿新种群同步化的影响
重引入定植阶段(1997年):麋鹿新种群的分娩较集中于同步化率的0~25%和75%~100%两个阶段,占年度总分娩数量的71.96%。其中同步化率达到25%时,分娩率占年度总分娩数量的38.32%,可见此阶段对种群分娩启动有较大影响。
扩繁阶段(2007年):麋鹿新种群的分娩同步化率继续提升,同步化率的0~25%和75%~100%两个阶段,占年度总分娩数量的82.88%;同步化率25%~75%的分娩率则为17.12%,新种群分娩跨度也达到了最长(111 d)。种群分娩同步化率介于75%~100%的规律,与林麝(Moschus berezovskii)的研究类似(孙军平等,2017)。
复壮阶段(2017年):分娩同步化率也逐渐微回调,同步化率0~25%和75%~100%两个阶段,占年度总分娩数量的75.23%。此结果,可能跟新种群的输出(张付贤等,2022)、胚胎着床延迟(Brinklow and Loudon,1993)、疾病 (杨道德等,2007)、近亲繁殖(Rutberg,1987)、气候变化(Berger,1992)和个体的个性(孟庆辉,2014;孟庆辉等,2022)等有关联,需要继续开展深入研究,进一步推动对雌性动物卵泡分泌定时的深入理解。
随新种群的繁衍,非同步化分娩的数量逐年增加,而分娩期总跨度并未改变,与迁入地北京南海子湿地牧草生长及麋鹿所需生态位(孟庆辉等,2016)也有一定关系。1997—2017年的20年间,重引入后的麋鹿每年平均有30%左右的非同步化分娩现象,种群分娩前10%的个体和后10%的个体的个性及其采食活动等生态规律(孟庆辉等,2022)也是今后继续关注的焦点,本文不足之处在于没有进行新种群不同繁殖代数间的分娩同步关系分析,今后需要加强相关研究。
3.3 重引入地物候对麋鹿新种群分娩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重引入地的光照和积温与麋鹿种群分娩启动有较大关联,可能是光周期与下丘脑催产素分泌有关(马泽芳,2007;刘利敏,2008;孟繁臣,2017)。地上生物量峰值、降水峰值与分娩峰值尤为相关(孟庆辉等,2017),新种群麋鹿分娩峰值与重引入地的地上生物量峰值之间有一个哺乳期间隔,麋鹿幼仔出生日期和地上生物量的生长峰期并不相同,而是在一两个月后麋鹿幼仔陆续开始断奶,需大量采食牧草阶段与地上生物量峰值相匹配(孟庆辉等,2022),本文因缺乏北京麋鹿苑历史上地上生物量等相关数据,只能参考距离15~25 km永定河山区的地上植被情况(杜勇等,2021)进行分析。
在重引入定植阶段,新种群分娩节律提前,母鹿自身增加负担以响应环境;种群扩繁阶段,分娩节律逐年推迟,减少新生幼仔采食地上生物量的天数,影响幼仔越冬及繁殖潜力;种群复壮阶段,分娩节律逐年微回调并趋于稳定,种群繁殖节律达到与曾灭绝地生境的匹配。但随时间的增加,非同步分娩现象也逐渐增多。
综上所述,北京南海子麋鹿新种群在灭绝85年后,实施原地精准重引入项目,经37年的人工保护和种群内部调整,繁殖节律已与灭绝地物候达到了较好的重匹配和再适应。本文对重引入麋鹿新种群繁殖节律进行长期监测和初步总结,以期对其他物种的精准重引入灭绝地及迁地保护提供借鉴,为今后重引入种群的管理、迁地保护和濒危物种的解濒工作奠定科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