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华简《五纪》的德目
2022-07-22陈民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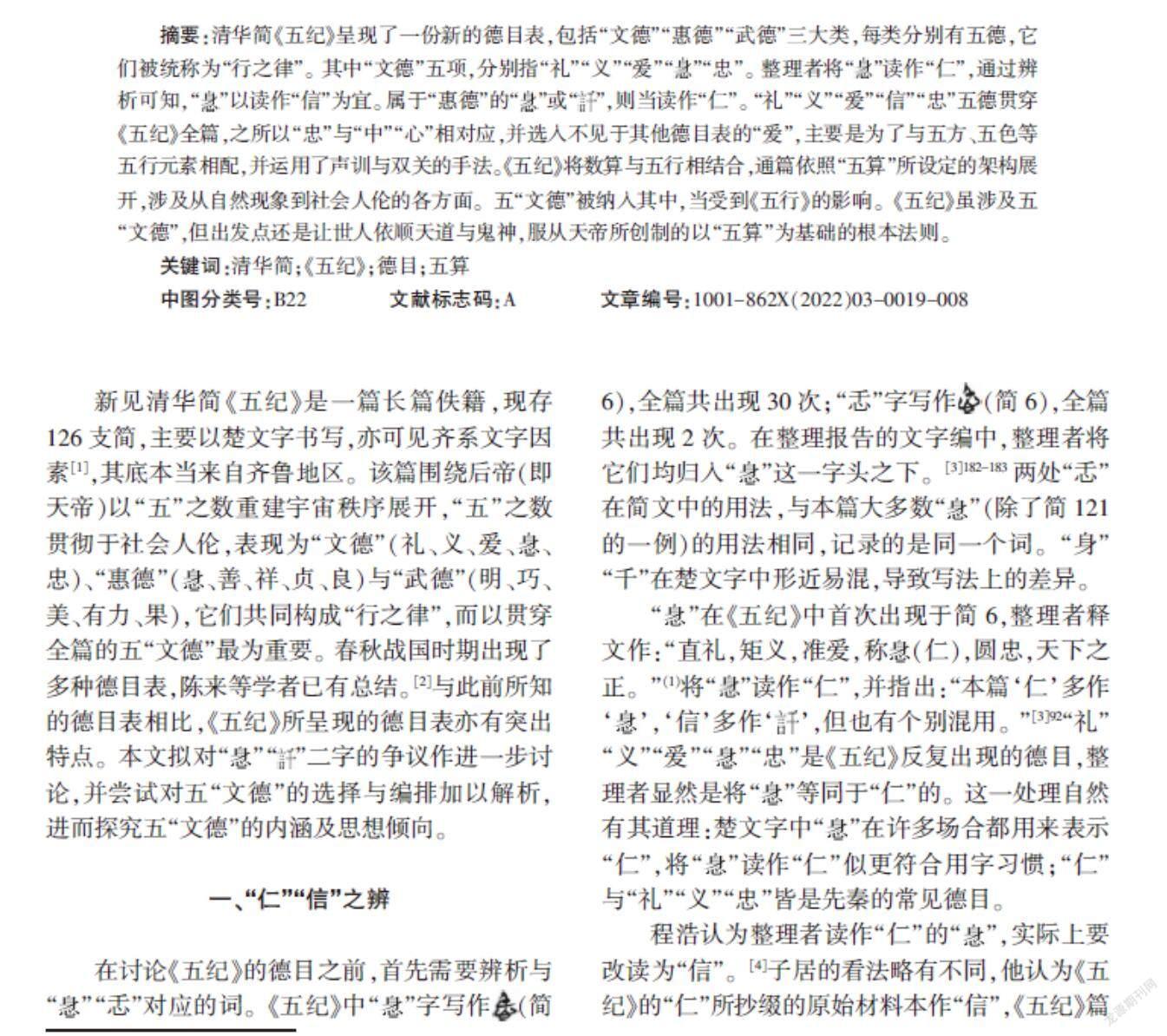







摘要:清华简《五纪》呈现了一份新的德目表,包括“文德”“惠德”“武德”三大类,每类分别有五德,它们被统称为“行之律”。其中“文德”五项,分别指“礼”“义”“爱”“■”“忠”。整理者将“■”读作“仁”,通过辨析可知,“■”以读作“信”为宜。属于“惠德”的“■”或“■”,则当读作“仁”。“礼”“义”“爱”“信”“忠”五德贯穿《五纪》全篇,之所以“忠”与“中”“心”相对应,并选入不见于其他德目表的“爱”,主要是为了与五方、五色等五行元素相配,并运用了声训与双关的手法。《五纪》将数算与五行相结合,通篇依照“五算”所设定的架构展开,涉及从自然现象到社会人伦的各方面。五“文德”被纳入其中,当受到《五行》的影响。《五纪》虽涉及五“文德”,但出发点还是让世人依顺天道与鬼神,服从天帝所创制的以“五算”为基础的根本法则。
关键词:清华简;《五纪》;德目;五算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2)03-0019-008
新见清华简《五纪》是一篇长篇佚籍,现存126支简,主要以楚文字书写,亦可见齐系文字因素[1],其底本当来自齐鲁地区。该篇围绕后帝(即天帝)以“五”之数重建宇宙秩序展开,“五”之数贯彻于社会人伦,表现为“文德”(礼、义、爱、■、忠)、“惠德”(■、善、祥、贞、良)与“武德”(明、巧、美、有力、果),它们共同构成“行之律”,而以贯穿全篇的五“文德”最为重要。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多种德目表,陈来等学者已有总结。[2]与此前所知的德目表相比,《五纪》所呈现的德目表亦有突出特点。本文拟对“■”“■”二字的争议作进一步讨论,并尝试对五“文德”的选择与编排加以解析,进而探究五“文德”的内涵及思想倾向。
一、“仁”“信”之辨
在讨论《五纪》的德目之前,首先需要辨析与“■”“忎”对应的词。《五纪》中“■”字写作 (简6),全篇共出现30次;“忎”字写作 (简6),全篇共出现2次。在整理报告的文字编中,整理者将它们均归入“■”这一字头之下。[3]182-183两处“忎”在简文中的用法,与本篇大多数“■”(除了简121的一例)的用法相同,记录的是同一个词。“身”“千”在楚文字中形近易混,导致写法上的差异。
“■”在《五纪》中首次出现于简6,整理者释文作:“直礼,矩义,准爱,称■(仁),圆忠,天下之正。”(1)将“■”读作“仁”,并指出:“本篇‘仁’多作‘■’,‘信’多作‘■’,但也有个别混用。”[3]92“礼”“义”“爱”“■”“忠”是《五纪》反复出现的德目,整理者显然是将“■”等同于“仁”的。这一处理自然有其道理:楚文字中“■”在许多场合都用来表示“仁”,将“■”读作“仁”似更符合用字习惯;“仁”与“礼”“义”“忠”皆是先秦的常见德目。
程浩认为整理者读作“仁”的“■”,实际上要改读为“信”。[4]子居的看法略有不同,他认为《五纪》的“仁”所抄缀的原始材料本作“信”,《五纪》篇作者或是误读,或是基于自身某种目的将大部分的“信”都改写成了“仁”。[5]程浩与子居已经举出了一些较有说服力的例证,在他们的基础上,笔者试作补充论证。
首先,“■”在楚文字中虽常用作“仁”,但亦有用作“信”的实例。程浩已指出,“信”与“仁”皆从“人”得声,在战国文字中常会混用[4],但未举出例证。从《简帛古书通假字大系》的总结看,“■”读作“仁”有80例,读作“身”的1例,而不见“■”读作“信”的用法;同样从“身”得声的“身”“ ”“ ”“ ”,则有读作“信”的用例。[6]可见,“■”读作“仁”最符合战国竹书用字习惯,有大量的辞例予以佐证。尽管“身”声之字亦可读作“信”,但毕竟在战国竹书中未见“■”直接读作“信”的实例。如若将视野放宽至简帛之外的材料,这样的疑虑自可打消。如《古玺汇编》收有一枚“中■”印(2706号)[7],一般视作楚系玺印。[8]长沙战国楚墓出土一枚玻璃质地的玺印,亦有“中■”二字[9],该印属楚玺。《甘露堂藏战国箴言玺》也收录了一枚“中■”玺印(7号),风格属楚。[10]郭沫若指出古玺所见“■”为“信”之异,“■”为“仁”之异[11],将“中■”之“■”视作“仁”之异体。关于长沙楚墓所出玻璃印的玺文,发掘者原释作“中身”[12];亦有学者改释作“中■”,或据楚简的用字习惯读作“忠仁”[8]。吴振武则将玺文“中■”读作“忠信”[13],此說广为学者接受。李家浩对包括“中■”印在内的战国“忠信”格言玺有集中讨论。[14]刘钊分析了战国时代“仁”“信”二字的纠葛,并指出以“■”表“信”是楚与三晋的用字现象。[15]247可见,从“人”得声的“仁”“信”与从“身”得声的“■”“■”等字常可通用,在楚文字中亦有实例,如若将《五纪》的“■”读作“信”自然不存在障碍。
其次,在“礼”“义”“爱”“■”“忠”的德目组合中,“■”读作“信”在搭配上更为合理,这可从以下两方面体现:
第一个方面,在先秦文献中,“礼”“义”是常见的一组德目,“忠”“信”也是出现频率极高的一组。“忠信”在先秦典籍中常见,如《荀子·富国》“明礼义以壹之,致忠信以爱之”等,其例不枚举。“忠信”还是战国格言玺的常见玺文。
第二个方面,本组德目已有“爱”,而“爱”与“仁”义近,如《孟子·离娄下》“仁者爱人”、《荀子·大略》“仁,爱也”、《墨子·经上》“仁,体爱也”等。如若“爱”与“仁”同时见于一组,不免重复。
其三,在以下辞例之中,“■”读作“信”显然更合乎文义:
简10“■以共友”。在该句中,“■”若读作“信”,可与“友”更好搭配。程浩举出《论语·学而》“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一句为证[4],子居则举出更多句例,强调“信”为交友之德[5],如《孟子·滕文公下》“朋友有信”、《韩非子·饰邪》“信于朋友”、《吕氏春秋·正名》“交友则信”等,其例甚夥。
简6“称■”、简13“■行称”。“称”指称量轻重之器,《五纪》将“■”与称相配。称量轻重必以“信”,子居举出《管子·明法解》“有权衡之称者,不可以欺轻重”的文例[5],可以参看。
简127“夫是故后言天又有■”。子居指出“天”与“信”相搭配的文例[5],如马王堆帛书《经法·论》:“信者,天之期也。”[16]140马王堆帛书《十六经·正乱》:“夫天行正信,日月不处。”[16]159
此外,程浩认为简11的“■严”以及简125“言■毋愳(瞿)”,“■”读“仁”更为适宜[4],则证据相对薄弱。子居还认为“■时”可与《管子·任法》“如四时之信”、《尉缭子·兵令下》“信如四時”、《文子·精诚》“与四时合信”的说法相参看[5],不过文中的“时”若指前文的“天下之时”(风、雨、寒、暑、大音),则不能与“四时”简单类比。
其四,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简121—123的一段话,整理者的释文作:
行之律:礼、义、爱、■(仁)、忠,■(信)、善、永、贞(正)、良,明、巧、美、有力、果,文、惠、武三德以敷天下。
后曰:■(信),■(信)者行礼,行礼者必明。
后曰:善,善者行义,行义者必巧。
后曰:永,永者行爱,行爱者必美。
后曰:贞(正),贞(正)者行■(仁),行■(仁)者必有力。
后曰:良,良者行忠,行忠者必果。[3]130
除了《五纪》反复出现的“礼”“义”“爱”“■”“忠”五德之外,简文又出现了另外两组“五德”,共同构成大的“三德”,亦即所谓“行之律”。在讨论“■”“■”这两处疑难之前,首先需要厘清“贞”与“永”的含义。整理者将“贞”读作“正”,笔者则认为此处亦可如字读,“贞”训“正”。“贞”系《逸周书·常训解》“九德”以及《逸周书·宝典解》“十德”之一,“贞”“良”并举亦见于《墨子·明鬼下》等文献。至于“永”,整理者如字读,笔者则认为当读作“祥”。《五纪》简102“黄帝悎(戚)永(祥)”、简103“群永(祥)乃亡”,“永”便读作“祥”,且“祥”系《国语·周语下》“五德”以及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九德”之一。《尔雅》云:“祥,善也。”“永”若读作“祥”,正可与同组的“善”“良”等相呼应。在此基础上,可将《五纪》的三组德目示列如下:
这三组德目存在互动与对应关系,如“文德”之“礼”,与“惠德”之“■”、“武德”之“明”相对应。“文德”组与“惠德”组均出现了“■”,二者显然不是同一概念。如果能确定“惠德”组“■”的含义,无疑可以进一步理解“文德”组的“■”。整理者将“文德”组的“■”仍旧读作“仁”,而将“惠德”组的“■”读作“信”。至于“惠德”组的“■”,实际上还有“■”的写法,这便是整理者所说的“■”“■”“也有个别混用”的情形。
“惠德”组的“■”或“■”,显然读作“仁”更合适,理由如下:
(一)“■”在战国竹书中虽然更多读作“信”,但正如前文所说,战国时代“仁”“信”相混,“■”亦有读作“仁”的可能。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简13、18[17]以及清华简《治邦之道》简4[18]136所见“ ”便读作“仁”。
(二)简文称“■者行礼”,而古书中“仁”“礼”往往并提。程浩已经指出“仁者行礼”合乎儒家伦理[4],但未举出具体文例。孔子以“仁”释“礼”,“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皆可为证。
(三)“贞者行■”,与“贞”相对的“■”应是“信”。《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语:“君子贞而不谅。”何晏注:“贞,正。谅,信也。”[19]一般认为此处“贞”为“大信”,“谅”为“小信”。另可参见《商君书·定分》:“名分定,则大诈贞信。”“贞信”为成语。可见,“贞者行■”之“■”读作“信”更为适宜。
既然“文德”组的“■”与“惠德”组的“■”并非一个概念,且有线索表明前者对应“信”、后者对应“仁”,那么,不难得出结论:“文德”组中与“礼”“义”“爱”“忠”并举的“■”,当读作“信”;“惠德”组中的“■”则读作“仁”,在简文中又写作“■”。
可见,《五纪》“■”“■”的使用存在混乱的情形:“■”在战国竹书中多用作“仁”,但《五纪》中除了一处读作“仁”,其他均读作“信”。此外,简9的一处“■”亦读作“信”;“■”在战国竹书中多用作“信”,但在《五纪》中读作“仁”。这一方面与战国时代“仁”“信”形音相近、时常混用的大背景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底本有关。清华简《五纪》的底本当来自齐鲁地区,不妨推测:由于齐鲁地区的“信”多写作“■”“■ ”[15]247,亦有“■”“■”的写法[20],在转化为楚文字的过程中,楚地抄手依照楚地习惯转写,又未能做到完全统一,故造成了用字上的矛盾现象。
二、《五纪》德目的选择与编排
《五纪》“文德”“惠德”“武德”所出现的道德范畴,大多有所本。其中,“文德”五项“礼”“义”“爱”“信”“忠”最为关键,在篇中反复出现,并成为联系其他五行元素的纽带。
在《五纪》全篇,“五”的观念贯彻始终。开篇追述往昔洪水滔天,扰乱天纪;后帝震恐,遂称述往古之道,修次五纪。此处“五纪”即“天之五纪”或“天纪”,“纪”者,纲纪也。具体内容作者已有交代,分别指日、月、星、辰、岁。此种“五纪”的说法,可参见《尚书·洪范》:“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马王堆帛书《经法·论约》:“日月星辰有数,天地之纪也。”[16]146在重整五纪之后,天人同德,洪水消弭,宇宙遂恢复秩序。
但日、月、星、辰、岁五纪并非《五纪》的核心内容,作者引入天之五纪,是为了推导出“五算律度,大参建常”(简2)。“五算”即“五数”,指一、二、三、四、五,作者将其称作“天下之数算”,“五算律度”犹言简22的“算律”。《五纪》简3—4云:“天下之数算,唯后之律。”亦即“五”之数系后帝制定的根本规律,世界万物皆遵循这一规律,它贯彻于宇宙,也贯穿于《五纪》的全篇,是《五纪》真正的核心。“五算律度,大参建常”意谓五数及其所蕴含的规律相参合,遂有宇宙之常法。此外,《五纪》简44亦强调“数以为纲纪”。黄德宽指出,《五纪》体现了“数算”对建立天人纲常的价值认知[21]。这种对“数”的推崇,可参看北大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天下之物,无不用数者”的论述[22],反映了战国秦汉时期注重“数”的观念。
《五纪》的思想极为复杂,而其基本思想来源还是阴阳五行之学与数术之学。五行观念盛行于战国时期,亦见于此前公布的清华简材料。[23]就五行观念的发展阶段而言,《五纪》的五行体系属于吾淳所说的“作为宇宙图示的五行”。它运用“比类”和“附数”的方式,以“五”之数为核心,将一切都纳入“五”数的结构,从而赋予五行观念数字化、结构化、教条化与神秘化。[24]《五纪》将阴阳五行与数算相结合,通篇依照“五算”所设定的架构展开,从自然现象到社会人伦,各种要素皆被纳入这一体系之中,内容如下表所示:
除了上表所列举的内容,《五纪》还将更多的概念纳入“五”的系统之中,显得极为繁复。由于与本文的讨论无關,故暂将相对次要的概念略去。李零详细总结了《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管子·幼官》《管子·五行》《淮南子·天文训》《淮南子·时则训》以及马王堆帛书《刑德》、孔家坡汉简《日书》等文献的各种五行表[25],《五纪》的五行表与这些战国秦汉文献相较,异同如次:
(一)《五纪》以五方对应五色(五章),其对应关系与《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管子·幼官》《淮南子·天文训》《淮南子·时则训》《日书》皆相同,反映了战国秦汉时期的公共知识。
(二)《五纪》虽无明确的五方帝观念,且黄帝似乎与大昊、少昊、颛顼不属于同一层次,但从大昊对应东极、少昊对应西极、颛顼对应北极的关系看,《五纪》与《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刑德》《淮南子·天文训》等文献有相合之处。《五纪》中与南极对应的稷匿(后稷),其地位应相当于神农氏炎帝。[4]《淮南子·天文训》中五帝与规、衡、绳、矩、权五种度量的对应关系,则与《五纪》不同。如果依照五方帝观念,黄帝理应补中极之缺,且他正可呼应“中”之“黄”色。然而,在《五纪》中黄帝既非中央大帝,也未纳入神祇系统,而是作为最初的人王存在,这与五方帝的说法不尽相同。《五纪》的时代,五方帝的观念应已成型,但可能因为作者有意凸显至上神后帝的地位,或者受黄帝人王传说的影响,而将黄帝与神祇系统剥离。
(三)《五纪》的龙、虎、蛇、鸟“四灵”,与《礼记·曲礼上》《淮南子·天文训》等文献中的青龙(苍龙)、白虎、玄武、朱鸟相近,但北方为蛇而非玄武。
(四)《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管子·幼官》《淮南子·时则训》的五数为八、七、五、九、六,与《五纪》的五数不同。
(五)《五纪》围绕五数敷衍出一系列五行组合,却偏偏没有《尚书》《管子》《淮南子》等文献所见水、火、木、金、土五行。但不能因此说《五纪》的时代不存在五材及五行相生相胜的观念,也不能因此否认《五纪》的时代存在五方帝等观念。
(六)其他文献的五神、五音、五乐、五味、五臭、五气、五星、五祀、五官、五路、五驾、五旂、五衣、五玉、五食、五兵、五刑等,或不见于《五纪》,或仅出现概称(如“五兵”)。
(七)《五纪》也有其他五行表所没有的元素,最突出的表现为“礼”“义”“爱”“信”“忠”五德,其中,“忠”与中极相对应。曹峰认为《五纪》的“中”居于统摄、主宰的位置[26],但也需要注意的是:“爱”与北斗相对应,“后正北斗”(简26),“匡天下,正四位”(简66),其地位亦极为突出;《五纪》简19—20称“参律建神正向,信为四正”,“信”又居于主导。“礼”“义”“爱”“信”“忠”很难说哪个可以统摄其他四者。
《五纪》的五行系统有拼凑的痕迹,它采用了战国时代流行的五方、五色相配的观念,将其作为基本框架,同时纳入自然、人伦的各类元素,从而构建出繁复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礼”“义”“爱”“信”“忠”是一大枢纽,其他元素往往需要与之相对应。这种对应,有的存在逻辑性,有的则难以看出内在的联系。之所以引入五“文德”,当是受到《五行》的影响。郭店简与马王堆帛书均发现有《五行》文本,学者多认为是“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荀子·非十二子》)的《五行》[27]。《五纪》的作者当借鉴了《五行》,选择了自己心目中的“五德”纳入其独特的体系之中。需要注意的是,清华简《五纪》的抄本有齐系文字因素,而郭店简《五行》的某些用字也有齐系文字特点[28],这或可暗示它们的来源与作者。《五行》作为思孟学派的作品,首先在齐鲁地区流传并不难理解,而《五纪》的底本亦当来自齐鲁地区。《五纪》的思想具有复杂、综合的特点,思孟学派的五行观念亦或为其所借鉴。
但《五纪》的五“文德”与《五行》的“五行”并不相同。《五纪》的作者之所以选择“礼”“义”“爱”“信”“忠”这五德,而非《五行》的“仁”“义”“礼”“智”“圣”,主要是为了与其五行体系相适应。“礼”“义”又见于《五行》,“礼”“义”与“忠”“信”是当时流传颇广的两组范畴,恰可成组引入。程浩指出,“仁”是儒家伦理的最高范畴,而《五纪》中“忠”才是统摄其他四者的那一个。[4]不过,《五纪》并不是单纯的儒家文献,不必套用儒家伦理;在“惠德”中虽出现了“仁”,但“仁”的地位并无特殊之处;“忠”虽与“中”相对应,但很难说具有统摄其他四者的地位。在先秦文献中,“忠”是与“信”等并列的概念,其地位并无绝对优先之处。“忠”在《五纪》中之所以能与“中”相对应,是与作者所设定的五行系统相适应的。《五纪》中的“忠”皆写作“中”,“中”有中央之义,在战国文字中“忠”亦多以“中”表示。作者实际上运用了声训与双关的手法,“忠”因与“中”同源,二者常可互通,故在简文中与中央之“中”、人体之“心”相呼应。清华简《心是谓中》简1谓“心,中,处身之中以君之”[18]149,便以“心”为“中”。《管子·四时》云:“中央曰土……其德和平用均,中正无私。”将中央与“中正无私”之德相对应,与《五纪》颇有可比之处。
从声训与双关的角度入手,亦可解释何以“爱”能进入《五纪》五“文德”之列。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类德目表并不见“爱”的踪迹,与其相近的是“仁”,但作者将其归入“惠德”之列,地位并不及“爱”。“爱”作为受到各类德目表冷落的概念,却成为《五纪》五“文德”之一,颇令人费解,《五纪》简47“爱曰藏”的说法当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爱”在简文中对应北方、黑色、寒冷,孔家坡汉简《日书》简464:“令北方藏。”[29]北方对应“藏”,之所以有此对应关系,是因北方、黑色、寒冷与冬季相对应,“冬藏”系先秦习语,由此不难理解简文何以称“爱曰藏”。《五纪》的作者正是运用声训与双关的手法,因“爱/薆”有“藏”义,故将其编排入五“文德”,并与北方、黑色、寒冷等元素相对应。
子居引述了《尸子》《礼记·乡饮酒义》所见德性与四时、四方搭配的记录[5],这些论述亦以声训为依据,可与《五纪》的“忠”“爱”相参看。如《乡饮酒义》将北方与“藏”相联系,但所对应的是“中”,“冬”“中”音近,属于声训,《五纪》的说法与此不同。声训与语义双关的手法,亦见于清华简《程寤》[30],是先秦文献中较普遍的现象。
程浩认为,《五纪》强调“忠”是为了化民成俗,替在上位的治民者着想;讳言“仁”是由于“仁”的内涵与绝对的“忠”其实是有冲突的。[4]从前文的讨论看,《五纪》似无此等深意。
《尸子》《礼记》虽将德性与四时、四方搭配,但未明确将德性纳入“五”的系统之中。《五纪》之外,现存的传世文献,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较早将五种德性与五方、五色等五行元素搭配。在传统的思想史链条中,董仲舒的思想看似突兀,而在《五纪》面世之后,可知在《春秋繁露》之前已有五德与五方、五色等元素相组合的五行方案。《春秋繁露》的五德为仁(东)、智(南)、信(中)、义(西)、礼(北),这与《五行》的仁、义、礼、智、圣更为接近。马王堆帛书发现有《五行》,可见《五行》在汉初尚有一定程度的流传,《春秋繁露》亦可能受到《五行》或类似文献的启发。
三、《五纪》五“文德”的内涵
《五纪》将“礼”“义”“爱”“信”“忠”视作后帝的“正民之德”:
后曰:一曰礼,二曰义,三曰爱,四曰信,五曰忠,唯后之正民之德。(简9—10)
在简6中,“礼”“义”“爱”“信”“忠”被称为“天下之正”;在简121中,这五德被称为“文德”,与“惠德”“武德”共同构成“行之律”。如果说“五”之数是“后之律”,那么“礼”“义”“爱”“信”“忠”五德便是贯彻于人间社会的基本规律。《五纪》全篇虽以天道入手,但落脚点仍是人道。
关于“礼”“义”“爱”“信”“忠”五德的内涵,在以下两段话中有所交代:
后曰:天下礼以事贱,义以待相如,爱以事宾配,信以共友,忠以事君父母。后曰:礼敬,义恪,爱恭,信严,忠畏。后曰:礼鬼,义人,爱地,信时,忠天。(简10—11)
言礼毋沽,言义毋逆,言爱毋专,言信毋惧。四征既和,忠以稽度。(简124—125)
第一段话先就五种社会关系展开,分别讲的是如何对待地位低于己者(贱)、地位与己相当者(相如)、配偶、朋友以及地位高于自己的君主和父母。较之《孟子·滕文公上》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纪》所涉及的社会关系更为宽泛。简文对“礼”“义”“爱”“信”“忠”五德内涵的揭示,与其他先秦文献有同有异,由此可进一步窥见《五纪》的思想旨趣。
“忠以事君父母”最易理解。“忠”多就敬奉君主而言,如《论语·八佾》:“臣事君以忠。”“孝”多指敬奉父母,但《大戴礼记·曾子本孝》亦有“忠者,其孝之本与”的说法。
“信以共友”,前文已经讨论了交友之道与“信”的联系,交而有信是基本的待友之道。整理者将“共”理解为供给、供奉[3]94,汗天山指出,似无“供给,供奉”同僚之理,此“共”字大概就是“共同、共处”之义(2)。按:“共”当如字读,“共友”可联系《论语·公冶长》“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
“爱以事宾配”,整理者认为“宾配”指宾客与妻室[3]94。子居认为宾客无从言“爱”,“妃”“配”相通,故“宾配”当读为“嫔妃”,《国语·周语中》:“弃其伉俪妃嫔。”《管子·小匡》:“九妃六嫔,陈妾数千。”[5]按:“宾”可读作“嫔”,《尔雅·释亲》:“嫔,妇也。”“配”与“妃”相通,“配”与“妃”皆可指配偶。《五纪》将“爱”落实到男女之情,这在先秦文献中并不常见。不过并非没有例证,如《孟子·梁惠王下》:“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管子·轻重甲》:“女华者,桀之所爱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五纪》还指出“言爱毋专”,强调“爱”不独占,则近于孔子的“泛爱众”与墨子的“兼相爱”。
“义以待相如”,整理者谓“相如”指地位相同或相随者[3]94。“相如”者,相类也,简文就社会地位而言。“义”在简文中指与地位相近者的相处之道。
最后看“礼”。所谓“礼以事贱”,整理者引述《管子·枢言》“贵之所以能成其贵者,以其贵而事贱也”之语[3]94,有学者认为,“事”应读为“使”。(3)《墨子·尚贤上》“尚贤事能”之“事”,指任用,“尚贤事能”犹《荀子·君子》“尚贤使能”。“贱”是相对而言的,指地位低于己者。《五纪》并不排斥“贱”者,如简129云“从贵立贱”,“从贵”见于《周易》蹇卦和鼎卦的象辞,“立贱”则可参见清华简《治邦之道》简3:“虽贫以贱,而信有道,可以驭众、治政、临事、长官。”[18]136“礼以事贱”,犹《论语·八佾》所谓“君使臣以礼”,亦如今人所谓“礼贤下士”。《荀子·富国》云“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强调“礼”的“贵贱有等”,则与《五纪》的旨趣不尽相同。
《五纪》还讲到“言礼毋沽”。所谓“沽”,整理者认为是粗恶之义,并引《仪礼·丧服》郑玄注:“沽,犹粗也。”《周礼·司兵》贾公彦疏:“沽谓粗恶者为下等也。”[3]131此外,亦可参见《礼记·檀弓上》:“杜桥之母之丧,宫中无相,以为沽也。”总之,“沽”指礼之简率,这是《五纪》的作者明确反对的。明乎此,我们得以进一步解读《五纪》关于祭礼的看法。
从简11“礼敬”“礼鬼”的说法看,“敬”是“礼”的内在要求,同时敬奉鬼神是“礼”的重要方面。简47—48先是引后帝之语:“天为筮,神为龟,明神相贰,人事以谋。天下之后以贞参志,上下以恭神,行事不疑。”人间的君王通过卜筮决疑,尊重神明的意志,强调“恭神”或“行用恭祀”(简17)之必要。继而提到了几种不“恭神”的现象,如“不用玉,用璞石。牺用不用大物之厚牷,幣不用良,用黎驽”(简48—49)。这种“不肤曰肤,不香曰香,不旨曰旨,不嘉曰嘉”(简50)的现象,显然便是“言礼毋沽”之“沽”了。再如“用费而不时”(简52—53),则会导致“上下不顺”“兆卦茫乱”(简54),“多费用弃,鬼神弗享”“保必不行,明神渝事,后祝受殃”(简55)。
作者认为“神不求咸”(简49),“神不求多”(简53)。正如《国语·楚语下》所云:“夫神以精明临民者也,故求备物,不求丰大。”鬼神本身不求祭品的丰厚。简文同时又称“无咸有过”(简52),“咸”者,遍也,可参见清华简《皇门》简6的“咸祀天神”[31]。虽然鬼神没有要求,但祀神不周遍、祭品过于敷衍,则无疑是不恭神的体现。
有鉴于人间祭礼的混乱,后帝遂要求统治者“恪恭皇事”(简56):“观天四时,毋迷绪事”(简58),需要按时祭祀;“由乃好美,发乃劳力”(简58),需要发动劳力,奉献“好美”之物。后帝强调“吾所得之,吾所食之,勿隐勿匿,皇后之式”(简56—57)。祭神的祭品不可隐瞒、懈怠,否则会降下灾祸,“畀汝寇刑,上下无赦”(简58)。
《五纪》所主张的祀神之道,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祭品嘉美,即“物生曰牺,币象用嘉”(简52—53)、“祭器香柔,曰唯蠲香”(简60)、“器币上色,曰唯嘉”(简61);其二,祭品不铺张浪费;其三,祭祀践时,即“春秋毋迷,行礼践时”(简53);其四,祀神以“咸”,不顾此失彼。如此,方能“四礼以恭,全忠曰福”(简61)。《墨子·明鬼下》载鬼神质问宋国大臣观辜之语:“是何圭璧之不满度量?酒醴粢盛不净洁也?牺牲之不全肥?春秋冬夏选失时?”所提出的玉器合乎尺度、酒醴粢盛净洁、牺牲全肥、祭祀守时等,均可与此参看。《五纪》对祭礼极为重视,作者之所以花较大篇幅讲述黄帝战蚩尤的故事,最终是为了强调黄帝对祭礼的奠定之功,故“世万以为常”(简108)。
根据《五纪》的设定,后帝为天地主宰,群神参与构建与维护宇宙秩序。这一秩序,核心是“天下之数算”,围绕“五”之数展开从自然到人类社会的各方面。重鬼神与祭祀是《五纪》的突出特点,这自与《韩非子·亡征》“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的看法迥然不同,而与墨家“天志”“明鬼”的观念有相似之处。但《五纪》“发乃劳力”的说法,则与墨家所谓“民德不劳”(《墨子·节用上》)有别。《五纪》与阴阳家“舍人事而任鬼神”“牵于禁忌”(《汉书·艺文志》)的旨趣颇为相近。至于黄老道家,亦重鬼神且借鬼神以为禁忌,与阴阳家近同;同时,又不惟鬼神,重视人的理性思考。[32]此外,《管子》一书亦强调对鬼神的虔祀,如“明鬼神”(《牧民》)、“立鬼神而谨祭”(《侈靡》)等。
儒家认为“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记·祭统》),《五纪》亦重祭礼,主张“言礼毋沽”,不可对祭品与祭礼懈怠。《论语·八佾》载:“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孔子此言看来与墨家相近,皆注重献祭的祭品,但孔子的出发点是维护“礼”而非“明鬼”。从《礼记·表记》《礼记·祭统》等文献的记载看,儒家亦敬奉天帝,讲求祭祀时的虔敬心态,且注重卜筮与祭祀的时日。这些儒家思想与《五纪》的相似之处,主要还是由于它们有共同的源头,即三代的大传统。当然,儒家对待祭礼的态度也有与《五纪》相异之处。儒家之所以注重祭礼,是因为“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礼记·祭统》),“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孟子·滕文公上》),祭祀是“孝”的延伸,是对社会人伦的强化。儒家所言祭礼,对象以祖先神为主,延续的是商周以来的大传统。故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而《五纪》中的祭礼,推重的是后帝以及其他自然神,而忽略祖先神,与儒家的旨趣并不相同,当是战国时期社会嬗变及鬼神观演化的产物。
“礼”“义”“爱”“信”“忠”虽贯穿《五纪》全篇,但对其道德内涵着墨无多。与“礼”相关的祭礼则有较大篇幅予以论述,当是为确立鬼神的绝对权威服务。
四、余 论
尽管《五纪》“礼”“义”“爱”“信”“忠”的德目与儒家有相契之处,但《五纪》之所以选择这五德,并非如儒家是为了推行人伦纲纪,而是意在与五行系统相整合,这从“忠”“爱”的选择与搭配以及未将“仁”纳入五“文德”可见一斑。《五纪》的出发点是让世人依顺天道与鬼神,服从天帝创制的以“五算”为基础的根本法则,五“文德”实际上是“后之律”在人间的实践。《五纪》言“民之不敬,神祗弗良”(简95),“民不敬,自遗罚”(简96),若不敬鬼神,则“畀汝寇刑,上下无赦”(简58)。正如黄德宽所指出的,《五纪》建构天与人的关系,目的是表达“人”的行为由“天”来决定。[21]从《五纪》对祭礼的态度以及鬼神观看,《五纪》与儒家也存在较大差异,而与阴阳家相近。
《五纪》的内容颇为庞杂,可以看到儒家、阴阳家、黄老道家、数术等多种思想观念的影子。这种诸家综融的特点,亦见于清华简《治邦之道》等文献[33],是战国中晚期学术思想交融的产物。《五纪》的思想虽有多元性,但其基本框架应源自阴阳家。此前程浩已经指出,《五纪》的写作可能受到了阴阳五行学说的深刻影响。[4]不过他认为《五纪》融合阴阳之学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笔者的看法有所不同,《五纪》的骨架应是阴阳之学,只是借用了儒家的德性概念。正如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也出现“祥”“义”“德”“音”“仁”“圣”“智”“利”“信”等德目,但《殷高宗问于三寿》并非儒家文献,而更接近黄老道家。(4)关于《五纪》的性质,牵涉复杂,限于篇幅,容另文详论。
注释:
(1)本文所引释文,均见《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十一)。释文兼采其他学者与笔者的观点,限于体例,不一一说明。为便行文,除了需要强调的字词,皆用宽式释文。
(2)见《清华简〈五纪〉初读》第183楼,简帛网·简帛论坛,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94&extra=&page=19.
(3)見《清华简〈五纪〉初读》第128楼,简帛网·简帛论坛,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94&extra=&page=13.
(4)参见袁青《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是儒家著作吗——兼与李均明等先生商榷》,《学术界》2017年第8期;曹峰《清华简〈三寿〉〈汤在啻门〉二文中的鬼神观》,《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陈民镇.略说清华简《五纪》的齐系文字因素[J].北方论丛,2022,(4):51-59.
[2]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269.
[3]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十一)[M].上海:中西书局,2021.
[4]程浩.清华简《五纪》思想观念发微[J].出土文献,2021,(4):1-16.
[5]子居.清华简十一《五纪》解析(之一)[J/OL].中国先秦史网站,https://www.xianqin.tk/2022/01/09/3595/.
[6]白于蓝,编著.简帛古书通假字大系[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1305-1308.
[7]罗福颐,主编.古玺汇编[G].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259.
[8]文炳淳.先秦楚玺文字研究[D].台湾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194.
[9]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楚墓[J].考古学报,1959,(1):41-60.
[10]周建亞.甘露堂藏战国箴言玺[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27.
[11]郭沫若.金文丛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216.
[12]湖南省博物馆,等,编.长沙楚墓(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419-420.
[13]吴振武.《古玺汇编》释文订补及分类修订[C]//常宗豪,主编.古文字学论集(初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509.
[14]李家浩.从战国“忠信”印谈古文字中的异读现象[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2):11-21.
[15]刘钊.从秦“交仁”等印谈秦文字以“仁”为“信”的用字习惯[J]//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8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16]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四)[M].北京:中华书局,2014.
[17]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五)[M].上海:中西书局,2015:150-151.
[18]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八)[M].上海:中西书局,2018.
[19][清]阮元,校刻.论语注疏(卷15)[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2518.
[20]徐在国,程燕,张振谦,编著.战国文字字形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301-302.
[21]黄德宽.清华简《五纪》篇建构的天人系统[J].学术界,2020,(2):5-13.
[22]韩巍.北大藏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初读[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29-36.
[23]曹峰.清华简《汤在啻门》所见“五”的观念研究[J].哲学与文化,2017,(10):45-62.
[24]吾淳.中国哲学的起源:前诸子时期观念、概念、思想发生发展与成型的历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97-198.
[25]李零.子弹库帛书(下)[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99-103.
[26]曹峰.清华简《五纪》的“中”观念研究[J].江淮论坛,2022,(3):11-18.
[27]陈来.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97-109.
[28]冯胜君.郭店简与上博简对比研究[M].北京:线装书局,2007:320-327.
[2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考古队,编.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85.
[30]王志平.清华简《程寤》中太姒所梦“六木”的象征寓意[J].中国文化研究,2020,(3):1-8.
[31]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M].上海:中西书局,2010:164.
[32]曹峰.清华简《三寿》《汤在啻门》二文中的鬼神观[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33-40.
[33]陈民镇.清华简《治政之道》《治邦之道》思想性质初探[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48-52.
(责任编辑 吴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