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亮精神分裂症病人被囚禁的世界
2022-07-07殷融
殷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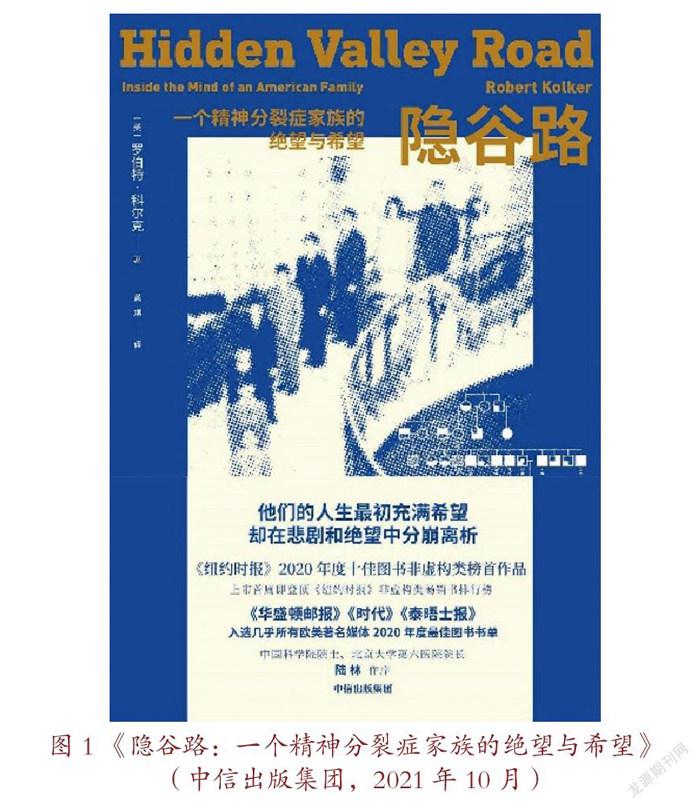
2001年,美国导演朗·霍华德(Ron Howard)拍摄完成了传记片《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将数学家约翰·纳什(John Nash)的故事搬上了大银幕。电影中的纳什在21岁时发表了鼎鼎大名的“纳什均衡”博弈理论,30岁时就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职。然而天妒英才,之后他开始出现严重幻听幻视,他有时宣称自己是五角大楼的特聘顾问,有时说自己在报纸上发现了来自外星人的加密信息,最终纳什被确诊为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在无数电影推荐榜单中,《美丽心灵》都会被纳入“心理学类必看电影”,许多人对精神分裂症的认识正是来自这部电影。然而,纳什的病症是否足够有代表性?是否如影片中所展现的,精神治疗药物会对患者大脑造成损失,造成迟钝和记忆衰退?又有多少患者可以像纳什一样,凭借自己顽强的意志战胜精神分裂?想必很少有人在看完电影后会去思考这些问题。
2020年,罗伯特·科尔克(Robert Kolker)出版了半科普半纪实文学作品——《隐谷路:一个精神分裂症家族的绝望与希望》(Hidden Valley Road:Inside the Mind of an American Family,以下简称《隐谷路》),以上问题在此书中都能找答案。《隐谷路》上市后几乎横扫了欧美所有著名媒体的年度好书书单,包括《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时代》(Time)和《泰晤士报》(The Times)等,它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读书俱乐部——奥普拉读书俱乐部——创立25年来唯一入选的纪实文学作品,它还入围了2021年度美国笔会非虚构文学奖和安德鲁·卡内基优秀图书奖。作为一本聚焦精神分裂症这一特殊甚至有些“边缘化”主题的作品,《隐谷路》到底为何能够成功“出圈”,在大众中获得如此高口碑?
一、羅伯特·科尔克与《隐谷路》简介
本书作者罗伯特·科尔克是北美当前最负盛名的独立调查记者之一,他曾在《纽约时报》《连线》(Wired)、《奥普拉杂志》(O,The Oprah Magazine)、《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和《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等著名杂志发表过许多深度报道作品,早在《隐谷路》出版前,他就已经功成名就,硕果累累。
在过去20年的调查生涯中,科尔克的笔触跨越了众多不同领域,几乎他每部作品的问世都会造成巨大轰动:2004年他在《纽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公立学校挪用公款的长篇报道《坏校监》(The Bad Superintendent),该事件成为美国公共教育史上最大胆的贪污丑闻,科尔克的这篇报道于2019被改编为电影《坏教育》(Bad Education)后,获得了艾美奖、美国编剧工会奖、美国制片人工会奖以及美国独立精神奖等十几项奖项提名,并最终赢得当年艾美奖最佳电视电影;2006年,科尔克对极端正统犹太社区的性侵案进行了调查,协助警方将一名施虐者绳之以法,并因此入围国家杂志奖(National Magazine Award);2011年,他因揭秘了一桩长达18年前旧案的真相,获得了纽约市立大学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颁发的“哈利·弗兰克·古根海姆刑事司法杰出报告奖(HFG Awards for Excellence in Criminal Justice Reporting)”。他在2013年出版的纪实文学作品《失踪的女孩》(Lost Girls)入选《时代》周刊“有史以来最出色的真实犯罪题材图书”书单,并在2020年被改编同名电影。除以上成就外,科尔克还曾挖掘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令人难以置信的生存故事,报道过反堕胎杀手詹姆斯·科普(James Kopp)的生平,记录了科学家开发出革命性基因编辑技术“CRISPR”的历史,一手揭露“提前88年出狱犯人”之谜,真实再现纽约警察枪杀黑人男青年肖恩·贝尔(Sean Bell)事件,还原了被称为“哈德逊河奇迹”的客机迫降事件[此事件后来被改编为电影《萨利机长》(Sully)]。
《隐谷路》是科尔克历时三年调查完成的最新作品。此书副标题是“一个精神分裂症家族的绝望与希望”,其中提到的家族是加尔文一家,他们住在隐谷路。加尔文的父亲多恩是美国空军学院军官,母亲咪咪是家庭主妇,他们养育了12个孩子,其中竟然有兄弟6人先后患上了精神分裂症,《隐谷路》全书正是围绕加尔文家族展开的。综合来看,本书是一部解析精神分裂症环境诱因的探索之作,是串联精神分裂症研究史的科学之作,也是引发同理心共鸣的情感之作。
二、一部解析精神分裂症环境诱因的探索之作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只有人类才会患上的特殊精神疾病,症状包括幻听、幻觉与情绪不稳定等。1908年瑞士精神科医生保尔·厄根·布洛伊勒(Paul Eugen Bleuler)指出,许多“早发性痴呆”的原发性症状是情感、联想和意志障碍,其核心问题在于人格分裂而不是智力衰退,于是,精神分裂症这一概念被正式提出。然而,一百多年的精神分裂研究史并没有击穿阴霾,精神分裂的成因至今依然被迷雾所笼罩,药物、精神分析以及电击等治疗手段也在不断触礁中艰难前行。对应到加尔文家族的病例上看,学术界对于精神分裂症的种种解释似乎都能自圆其说,但又都不能完全说得通。《隐谷路》一书在抽丝剥茧中,揭秘了导致加尔文家族悲剧的几个最重要因素。通过对加尔文家族故事的讲述,科尔克总结分析了无数个精神分裂症病患家庭所共同面对的病因与困境。
第一,父母不加干涉的管理模式。科尔克从多恩与咪咪入手,描述了他们的性格与教养特征。例如,身为军人的多恩有着高傲的自尊和极端控制欲,平时他总是忙于工作,把一大堆精力旺盛的男孩全丢给妻子,面对家中不断升级的暴力与欺凌,他只是冷眼相待,从不制止,而一旦他涉足家庭事务,又会坚持用天主教和军校的管理方式,家中的父权氛围令人窒息;母亲咪咪则根本没有足够精力去履行母亲的责任,也从来没有在乎过孩子的心理状态,当几个儿子发病后,为了“保持中产阶级的优雅和光荣”,她选择隐瞒,甚至“孩子有病”都能成为她自欺欺人的借口,假装岁月静好已成为她的本能。总之,像许多心理或精神疾病一样,如果精神分裂症有寻找原生家庭之过,那么常常可以追溯到父母冷漠、专制或不作为的亲子互动方式。
然而,科尔克并不只是浮光掠影地点出多恩和咪咪为人父母的失职之处,他还深挖了二人的性格根源,让读者看到一切其来有自。例如,书里明确告诉读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多恩亲历了珍珠港事件,在生死线挣扎徘徊,没有人知道战场上一幕幕地狱般的景象如何撕扯着他的心灵——那个时代的人甚至根本意识不到战争给军人带来的心理创伤;而咪咪也有着无法愈合的童年创伤,她曾遭继父性侵,生活颠沛流离,因此她一直渴望安全稳定的生活,企图通过不断生育建立一个理想家庭。更重要的是,虽然咪咪无能为力地看着孩子一个个步入深渊,可她从没放弃做母亲的责任,几十年来她倾尽全力照顾有精神障碍的儿子,没有丝毫怨言。在对多恩和咪咪的描述中,科尔克展现了一个优秀纪实文学作者应具备的素质:他不是让读者去评判,而是让读者去观看、感受和理解。
第二,恐怖窒息的家庭病患氛围。没有亲历过精神病患家庭的普通人,可能难以想象家庭病患氛围能成为致病因素。虽然精神疾病并不具备生物学意义上的可传播性,但科尔克对加尔文一家的调查却清晰表明,在一个大家族中心理和精神困扰是会相互“感染”的,尤其是当父母没有及时做好对健康子女的心理安抚时,原本健康的孩子也会陷入厄运。例如,加尔文家的大哥唐纳德其实很早就表现出不对劲症状,他会用极端暴力的方式压制自己的弟弟妹妹,甚至要求他们互相殴打;二哥吉姆则趁两个小妹妹为躲避大哥的暴力来投靠他时,将罪恶的手伸向了她们稚嫩的身体。
可以说,加尔文家大孩子那些暴戾乖张的举动为弟弟妹妹们“营造”了最恶劣的生存境况,进而导致他们也逐渐脱序。他们一方面要时刻忍受患者的摧残,同时还要担心自己是否有一天也会发病。正如书中写言:“对于病人的亲朋来说,这种疾病是难于用理性去面对的,而这会引来恐惧。精神分裂病人对家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感情的转移上,仿佛家庭的重心永远地倾向了病人。哪怕只有一个孩子患有精神分裂症,这个家庭内部的秩序也会彻底发生改变。”
第三,不胜其弊的治疗手段。治疗手段竟然也能成为加尔文家族悲剧的始作俑者之一,这是最让人感到吊诡的地方。医学治疗的目的本是为了让病人从疾病中康复,但对于精神疾病来说却不一定如此。早期的治疗手段极不人道,残酷的电击疗法、胰岛素休克疗法、额叶切除术、单独禁闭法以及无休止的服药都可能带来二次伤害。《隐谷路》中专门提到了加尔文家几个孩子可怕的住院经历,当时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大都没有护理学专业背景,只接受过简单的护理培训。他们会给病人服用大量氯丙嗪等药物,随意决定药量,这种方法实质上就是用大剂量镇静剂让患者陷入茫然迟钝状态。对于许多精神病人来说,治疗对健康的摧残不亚于疾病本身。
第四,错位的文化思潮。科尔克敏锐地捕捉到了当时席卷全球的“反文化”社会思潮与加尔文一家悲剧间的关联性。爆发于20世纪60到7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是西方现代思想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运动中,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试图通过各种反叛活动体现对自由表达、自我主义与潜能解放的追求,但“反文化”运动中涌动的虚无主义也让其中一些年轻人开始怀疑其生存意义。随着经典电影《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的问世,许多理论家将“精神分裂症”看作是“家庭专制”的迫害,而患者其实是神智正常的,病症只是他们的“抗争”手段。但这些理论家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精神分裂症”在本质上不是思想先锋所臆造出的文化符号,它是切实存在的,是一种会给病人和家属带来无尽痛苦的疾病。正是在这种认知失衡中,像加尔文家这样亟须治疗的家庭被抛弃了,他们成了文化战争的牺牲品。可以说,科尔克最大限度地发掘了这个故事的丰富性,他将个人叙事与社会纪实相融合,通过加尔文一家的“家庭悲剧”映照出了“社会悲剧”,使该病例具有了社会广度与深度。
总之,科尔克着墨于多维视角,尽可能挖掘了加尔文兄弟患病的各种环境变量,这种全景式的展示既让人看到了精神分裂症触发因素的复杂性,也突出了《隐谷路》一书最让人感到沉重之处:无论思维多么清晰的读者,都不能说清加尔文家族悲剧的诱因到底是什么,父母的养育问题、疯狂的家庭生活、反文化思潮、精神科学的不当治疗、大众的无知与歧视……在科尔克的叙述中,这些因素彼此相交,没有证据能表明某个因素该为这出人间惨剧负多大比例的责任。这个家庭的故事就像是一排从斜坡上滚下的小球,开始时每个小球还能沿着直线平稳运动,可在某个时间点上,一个小球发生了偏移,于是撞击其他小球,之后,这些小球开始互相轰击,场面越来越混乱,它们为彼此的滑落摁下了加速键,最终全部坠入深渊。
三、一部串联精神分裂症研究史的科学之作
虽然《隐谷路》的叙事焦点是加尔文家族,但科尔克没有仅仅将本书写成一本家族纪录史。他在对加尔文一家经历的回顾中完整再现了现代精神病学对精神分裂症的探索过程,这种独特的写法既拓展了全书的科学蕴涵,同时也突出了加尔文家族在现代精神病学研究史中的特殊地位。正如书中所言:“这整个家庭遭受的苦难也是一部朦胧的精神分裂症科学史,一部几十年来追溯精神分裂症病因和本质的历史。”
需要强调的是,科尔克之所以能以高超的笔法对全书的叙事性与科普性进行巧妙平衡,一切都基于一个事实——加尔文兄弟在一定意义上确实堪称精神病学的完美研究对象:一方面,与加尔文一家相似的病例数量极少,几乎从来没有专家遇到过同父同母六兄弟共同患病的情况,多个家庭成员患病有利于研究者澄清这种疾病是不是有一定的遗传性;另一方面,那些没有患病的家庭成员则是完美的“对照”组,有助于筛除掉大量庞杂的无关因素。
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起,加尔文一家进入到精神病学、遗传学与藥物学的视野,虽然他们自身经历了地狱般黯淡无光的日子,却为医学提供了最好的样本。《隐谷路》在讲述这段历史时,并没有像科学综述一样巨细无遗地梳理,而是有的放矢,紧紧围绕加尔文家族,重点阐述了与之密切相关的几个重要研究成果,这其中就包括对精神分裂症成因的澄清以及干预措施的改变。
首先,关于精神分裂症成因的分歧得以澄清。1986年,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精神病学家琳恩·德利西(Lynn Delisi)就开始收集精神分裂症家庭的遗传物质,加尔文家族成为她首批研究对象,书中重点提及了这一研究过程。正是利用从加尔文家族收集到的数据,德利西证实,精神分裂症与脑室增大具有相关性,患者的某些遗传特征对大脑的感觉和信息处理功能产生了不良影响,使大脑在面对环境中的触发因素时变得非常脆弱,之后许多研究重复了类似的结论。从那时起,科学家对精神分裂症成因的看法趋于一致:精神分裂症是由遗传易感素质与个体成长中各种不良经历相互作用所导致的复杂性精神疾病,那些具有精神分裂遗传潜质的人,更容易因为心理创伤而引发精神分裂症。
当然,这不代表有关精神分裂症病因的先天—后天之争已经结束了,只是如今的讨论已发展到更为细琐的层面,例如到底哪些环境因素更容易触发基因按钮,进而打开了疾病开关,其中具体的生理运作机制又是怎样的。与此同时,医学界对精神分裂症的定义也在不断改变,现在最新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把精神分裂症看作一个谱系,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精神分裂症倾向,只不过一些人位于坐标系一端而表现得特别突出。
不过,仅仅在几十年前,科学界对于精神分裂症的成因还是完全不同的看法。在20世纪中期,精神病治疗师会把精神障碍归因于患者母亲的作为,冷漠、严厉、专制的“恶母”与精神失常概念绑定在了一起。尤其是在精神分析学家弗里达·弗洛姆-赖克曼(Frieda Fromm-Reichmann)发明了“精神分裂症妈妈”(schizophrenic mother)这个术语后,“把患者母亲视为始作俑者”一度成为精神病学的业内标准。与此同时,社会文化也在传播和强化这种认知。1960年,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执导的电影《惊魂记》(Psycho)上映,影片中将杀人狂诺曼·贝茨的妄想症及犯罪原因全部推到了他已逝母亲身上。在当时观众眼中,这种情节设置合情合理。人们相信,精神分裂症患者之所以会患病,是因为他们在幼年时遭遇了母亲的变态控制,因而性情发生扭曲。这种将患者母亲污名化的看法常常使得许多“精神分裂症妈妈”既要承受儿女发病的煎熬,还要背负本不应该施加于她们身上的社会舆论压力。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精神分裂症遗传学研究终于改变了这一状况,而加尔文家族正是该项研究的起点。
其次,对精神分裂症的干预措施得以改变。除德利西外,《隐谷路》中还重点提及另外一位精神病学家——科罗拉多大学精神病学家罗伯特·弗里德曼(Robert Friedman)的研究成果。1997年,弗里德曼通过对包括加尔文家族在内的9个家族进行样本分析,追踪到一个叫作CHRAN7的基因与精神分裂症具有确定的关系。CHRNA7基因所编码的蛋白是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认知功能、感觉信息处理和记忆等各式各样的神经活动中都扮演关键角色。因此当这个基因出现问题时,就可能引发一系列精神疾病。
精神分裂症的遗传学研究验证了生物学家尼尔·韦恩伯格(Daniel Weinberger)在1987年提出的一个理论,此前研究者都认为精神分裂症症状最早出现于青春期末期,但韦恩伯格发现,许多患者的脑部异常可始于更早阶段,这些异常会引发一系列问题,使大脑的发育越来越偏离正轨。也就是说,精神分裂症其实不是在青春期发病,只是在青春期时表现愈发显著。就像书中的唐纳德,17岁那年的一个晚上,他站在厨房的水槽前一下子砸碎了10个盘子。但据唐纳德自己描述,实际上在这之前他就常常感到难以控制自己。
找到精神分裂症与特定基因的关系能表明,许多精神障碍可追溯至童年期、婴儿期甚至妊娠期,对精神疾病的预防措施也应该提前到这些阶段。弗里德曼正是这么做的,既然CHRAN7基因的缺陷会导致精神分裂,那么如果想治疗精神分裂,最好是能够在孩子出生前就能修复这一基因缺陷。后来,弗里德曼发现了乙酰胆碱——
一种没有毒性的良性营养素,他建议有精神分裂易感性的孕妇在孕期要大量服用胆碱。2017年美国医学会通过的一项决议指出,产前维生素中应该包含更高剂量的胆碱,以预防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的脑部发育疾病。因此,人类目前至少找到了一种能够扭转局面、预防精神分裂症的方法,而这一突破的背后,既有加尔文家族提供的关键性遗传学信息,也有几位科学家长达30年的不懈努力。
可惜的是,相比之下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学研究则进展缓慢,科尔克在书中对此解释较少,实际上这其中涉及许多原因。首先,不同于“单纯”的科学研究,医药研发需要投入巨额资金、时间和人力成本,这是科学家仅靠个人兴趣和有限政府资助难以实现的,而医药巨头又没有太大动力加入对抗精神分裂症的战场,因为精神分裂症药物的预期相对收益并不算高,至少肯定比不上抗癌药物;其次,有别于其他药物,精神疾病类药物在前期测试阶段很难用动物代替人类被试,因此会承担更大风险;再其次,身患其他生理疾病的病人可以基于知情自愿原则参加药物临床试验,但精神分裂症患者最主要的病症恰恰体现在思维、逻辑和意识方面,因此他们是否可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如果他们没有相关行为能力,家属是否有权代为选择?这就涉及更复杂的科学伦理甚至法律人权问题。
总之,多种原因导致了精神分裂症药物研究依然没有太大进步。目前对于精神分裂症病人来说,一旦病发,最有效的临床治疗手段就是服用一些延缓疾病发作或控制病情的药物,而病人还要承担长期服药带来的副作用伤害。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加尔文家族的男孩生长于如今这个时代,他们接受的治疗方式可能并不会有太大改變。
四、一部引发同理心共鸣的情感之作
从写作风格来看,科尔克的新闻稿一向呈现的几大特点:一是擅长营造悬疑感,叙事节奏扣人心弦;二是追求对事实和细节的极度还原,拒绝虚构与想象;三是文笔克制且富有人文关怀。《隐谷路》一书则完全符合这些特征。
在讲述加尔文家族的故事时,科尔克采用了“视点人物写作手法”,他通过选取不同家庭成员的视角,用一种“接力赛”式的书写方式,拼凑出一张完整又充满裂痕的画卷。同时,科尔克并没有直接描述患病家庭成员的病情,而是选择了娓娓道来,他将咪咪和多恩的家庭背景作为起点,详细描述了两人的前半生,包括他们自小长大的环境、他们相识相爱的过程、多恩的职场励志经历、二人婚后经营家庭的生活点滴以及各个孩子的特点。这一写法既为后文分析多恩和咪咪的性格“缺陷”做了铺垫,同时又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立体,引导读者对加尔文一家建立角色代入,通过制造巨大反差,使读者更深刻地感受到病魔的残酷。
因此,《隐谷路》在开篇中越是不吝笔墨地描绘加尔文一家梦幻而浪漫的幸福生活,读者在了解后续发展时就会越心痛不忍:短短十年间,偏执、疯狂、打斗、幻觉、凶杀以及其他种种不可思议的悲剧,一一降临到这个家庭。原本的运动天才在上大学后却开始屡屡出入校医院,并宣称自己十几岁时就试图自杀;原本的明日之星因为违反校纪被空军学院退学,还性侵了自己的两个亲妹妹;原本丰神俊逸、精通演奏的艺术少年在一次莫名其妙的爆发后,枪杀女友,然后自杀……世界上最凄惨的事情莫过于先拥有了美好的东西,然后再被毁掉,病魔像一记重锤,轻而易举地击碎了这个中产之家的美好幻景。科尔克有意突出了这种突如其来的命运转折,这样更能让读者理解人类在面对精神疾病时的无助与悲苦。
科尔克在书的后部分对加尔文家族最小的女儿琳赛进行了相当多着墨,读者可以感受到他在叙述中对琳赛抱有的深沉敬重。琳赛是彻底的受害者,面对一个庞大的患病家族,她被剥夺了在正常秩序中成长的权力。琳赛曾想和过去一刀两断,但她最终的选择是重回隐谷路,像古希腊式的英雄那样向命运发起了抗争。她背负起照顾年迈母亲和患病哥哥的责任,同时积极寻求与科学团队合作。科尔克可能希望通过琳赛的经历强调,家庭成员间彼此尊重、宽容以及情感支持永远都是对抗精神疾病的中坚力量。
在写作本书时,科尔克贯彻了20年来对自己作品的要求,他坚持以实证方式選取材料,包括父亲多恩与母亲咪咪的个人经历、子女们各自的人生遭遇以及穿插其中的精神科学变迁史。因此,书中全部细节甚至对话均有详细考证出处,科尔克在“致谢”中透露了对加尔文一家和众多研究者为其写作提供的大量一手资料。正是由于有如此细密的材料作支撑,科尔克的叙述才能具有真切且强大的情感力量。他以充满同理心的笔触和慈悲气韵,展现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困境与绝望,也展现出爱与关怀不可思议的修复能力。
如今,加尔文兄弟中的许多人已经去世了,但还有无数精神分裂症患者步履蹒跚地走在这条孤独的隐谷路上,没有人知道它是否有尽头,最终究竟通往何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2022年1月公布的数据,全球有2400万精神分裂症患者,因此,精神分裂症其实并不算一种小概率的偶发性疾病。可直到现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事实上依然都是社会边缘群体,精神分裂症则依然是最被严重污名化的疾病之一,病患常常要忍受无处不在的冷眼、非议和歧视,甚至有时导致他们无法正常工作生活的不是病情,而是社会的偏见。
偏见源于未知,科尔克用自己的书写照亮了社会的这个角落,鲜活的案例总是更能触发人类的情感共鸣。医学教科书中会“冷静客观”地列举出精神分裂症的几种不同表现及药物不良反应,而《隐谷路》这样的纪实文学则让人切身感受到这一疾病对一个个鲜活生命的伤害。因此,本书无愧于《纽约时报》对其的高度褒奖——这是“叙事新闻的壮举”,也是一次“对同理心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