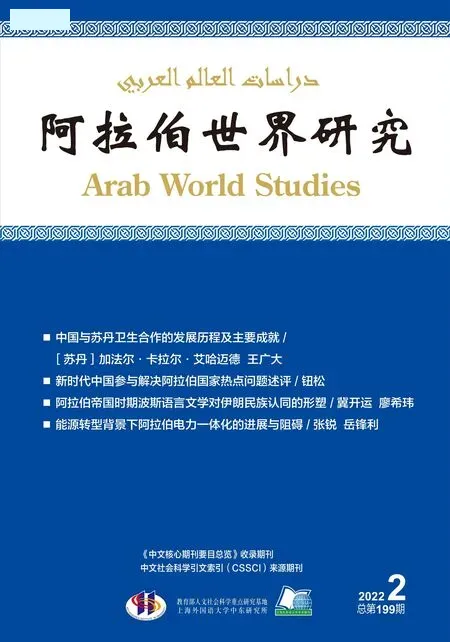以色列俄裔犹太移民的政治参与及其影响*
2022-06-30李绍先
谭 力 李绍先
以色列建国后,吸引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迁移并长期定居以色列是历届政府的基本政策。以色列开国之父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曾指出,“我们希望移民能够回归和适应新家园,能够为以色列国防军服务,成为农场的主人和定居点的建设者,我们希望移民中走出科学家。对于我们而言,犹太移民不是移民,是犹太人,就像我们一样。”(1)Ronald W. Zweig, David Ben-Gurion: Politics and Leadership in Israel, Oxon: Frank Cass, 2013, p. 244.可以说,犹太移民的迁移关乎以色列国家的兴衰存亡、民族发展和国家利益。以色列历史上经历过数次大规模移民,时至今日,其国内的俄裔犹太移民无论是在人口数量,还是文化模式和政治参与等方面均与来自其他地区的犹太移民不同。
关于俄裔犹太移民政治参与问题,国内外学界早有关注。国外学者主要从族裔政党政治(2)Vladimir Khanina, “Israeli ‘Russian’ Parties and the New Immigrant Vote,” Israel Affairs, Vol. 13, No. 7, 2000, p. 107; Vladimir Khanina, “Russian-Jewish Political Experience in Israel: Patterns, Elites and Movements,” Israel Affairs, Vol. 17, No. 1, 2011, p. 61.和历次政治选举(3)Shmuel Sandler and M. Ben Mollov, “Israel at the Polls 2003: A New Turning Point i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Jewish State?,” Israel Affairs, Vol. 8, No. 4, 2004, p. 11; Vladimir Khanina, “The Israeli ‘Russian’ Community and Immigrants Party Politics in the 2003 Elections,” Israel Affairs, Vol. 10, No. 4, 2004, pp. 164-167; Vladimir Khanina,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Israeli ‘Russian’ Street in the 2013 elections,” Israel Affairs, Vol. 21, No. 2, 2015, pp. 250-254.的视角出发,如俄裔犹太移民及其政党组织政治参与的经验(4)Vladimir Khanina, “The New Russian Jewish Diaspora and ‘Russian’ Party Politics in Israel,”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Vol. 8, No. 4, 2007, pp. 44-53.,俄裔犹太政党及移民投票,俄裔犹太移民及其政党在议会选举中的表现和族裔政治动员(5)Majid Al-Haj, “Ethnicity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a Deeply Divided Society: The Case of Russian Immigrants in Isra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34, No. 2, 2015, p. 12.以及俄裔犹太移民的投票行为(6)Majid Al-Haj, The Russians in Israel: A New Ethnic Group in a Tribal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p. 129.等问题。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也有相关成果发表(7)周承:《以色列国内苏联犹太移民政党的成因及影响》,载《西亚非洲》2010年第8期,第25-28页。。然而,前人研究对于俄裔犹太移民及其政党组织的分析常聚焦于某一阶段或某一次选举,从历史角度梳理其发展过程和行为模式尚显不足。本文通过描述苏联解体前后俄裔犹太移民(8)本文所指俄裔犹太移民的主要来源国是苏联及其解体后的独联体国家,他们曾经共享基于俄语文化基础上的生活习俗、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本文不再对其进行内部划分,而是以俄裔犹太移民统一称之。的人口、文化特征,历时考察俄裔犹太移民及其政党组织在以色列政党政治中的起源、发展与变迁,结合以色列国内的大选分析俄裔犹太移民的政治参与,最后探讨俄裔犹太移民对以色列产生的政治影响。
一、 以色列俄裔犹太移民概况
以色列建国前,俄裔犹太人就形成过多次移民潮(9)以色列建国前,俄裔犹太人开启了三次移民浪潮:1882至1903年,俄裔犹太人掀起了第一次移民浪潮。俄皇亚历山大二世遭遇刺杀,俄裔犹太人成为冲突的焦点而惨遭迫害,俄国犹太精英犹大·勒布·平斯克在目睹了这一社会现实后,发表了《自我解放》号召俄国境内的犹太人迁移。1903年逾越节期间,几十名犹太人在基什涅夫和霍麦尔遭遇屠杀,1904至1914年的第二次回归浪潮由此开始。1919至1923年间,俄国虽已爆发了二月革命,犹太人不再遭受歧视和迫害,但俄国的经济困境和不稳定的生活境遇促使犹太人不断向外迁移。,为以色列建国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以色列建国后,在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和以色列国家发展规划下,俄裔犹太人在20世纪70至90年代先后掀起了两次大规模移民潮。他们的到来为以色列增加了犹太选民的数量。据统计,20世纪70至80年代,有近30万人离开苏联,其中一半以上前往以色列定居。(10)周承:《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的形成及影响》,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截至1999年,大约有110万犹太移民从东欧地区移民到以色列,包括20世纪70年代初和1980年以后的移民。(11)Eliezer Ben-Rafael and Yochanan Peres, Is Israel One? Religion, Nationalism and Multi-culturalism, Leiden: Brill, 2005, p. 130.这些俄裔犹太人的移民动因主要是苏联解体后所面临的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安全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他们共同构成了以色列国家当时总人口的16%和犹太人口的21%。(12)Majid Al-Haj, “Ethnicity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a Deeply Divided Society: The Case of Russian Immigrants in Israel,” p. 89.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2020年数据显示,俄裔犹太移民至今依然是以色列国内来自单一原籍国人数最多的移民群体(见图1)。
在居住地选择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俄裔犹太移民在以色列政府的直接吸收政策(Direct Absorption)(13)该政策是以色列政府针对20世纪90年代俄裔犹太移民采取的政策,支持移民自由融入市场和自主选择居住地。与之前的间接吸收政策(Indirect Absorption)相比,政府不再直接安置移民,而是提供经济上的救助。下形成了集中聚居模式。这种居住方式为俄裔犹太移民提供了生活、心理、信息共享等方面的社会支持和帮助,也对政治参与产生了影响,俄裔犹太移民在亲密的生活空间和熟悉的社会网络中分享选举消息、探讨政策形势、分析政坛局势、创建政治组织、共谋政治图景、达成政治共识。以色列海法大学教授古斯塔沃·梅斯(Gustavo S. Mesch)认为,“居住在人口高度集中社区的俄裔犹太移民比居住在低度集中地区的移民更有可能参与地方选举。对这一结果的可能解释是,这些社区中存在着广泛的社会网络以及这种网络能够将不满情绪转化为政治动员的力量”。(14)Gustavo S. Mesch, “Residential Concentr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Local Politics: The Case of Immigrants of the FSU in Israe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Vol. 3, No. 2, 2002, p. 174.

图1 以色列国内犹太移民人口及其原籍国情况
在文化实践上,以色列俄裔犹太移民积极创建大众媒体,为政治参与奠定了文化基础。俄裔犹太人通过俄语大众媒体实现了自身的信息需求,俄裔犹太政党也在此构建政治文化传播的话语体系。因此,以色列国内的俄语报纸、广播、电视等已成为影响俄裔犹太人政治态度和社会实践的重要媒介。据统计,1990年至2010年间,俄裔犹太人在以色列创办了130多种俄语期刊,其中日报4种,周刊60多种,双周刊和月刊40多种,季刊和年刊20多种。(15)Nelly Elias, “Russian-speaking Immigrants and Their Media: Still Together?,” Israel Affairs, Vol. 17, No. 1, 2011, p. 73.当以色列政府意识到俄裔犹太移民在政治学上的意义及政府选举中的重要作用时,以色列国内的主要政党甚至开设了俄语竞选网站,在议会选举期间使用俄语竞选广告牌,并积极吸收俄裔犹太政治精英的选票。此外,俄裔犹太移民的教育程度普遍较高,他们中间有许多工程师、技术员、艺术家、科学家和医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以色列这个创业国度的诞生。以色列政府认为,俄裔犹太移民在科技领域中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报告称,1990年抵达以色列的移民中有50%的人拥有学位证明。(16)Sophie Hinger and Reinhard Schweitzer, Politics of(Dis)Integration, Berlin: Springer, 2019, p. 73.
在政治观点和宗教态度上,俄裔犹太移民经历过漫长的流亡岁月、寄居国的艰难生活和纷繁复杂的地区局势后,政治态度、价值观念和参政方式也有所不同。他们一方面承继了苏联的国家价值观,另一方面在物质层面上十分关注个体生活,在政治选举中倾向选择能够保证国内稳定和个人安全的领导人。“他们对民主的理解是十分模糊的,更因受到苏联即将解体的负面影响,包括90年代政治上的混乱和不稳定、国家在经济上转变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确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安全的恶化。”(17)Michael Philippov and Anna Knafelman, “Old Values in the New Homeland: Political Attitudes of FSU Immigrants in Israel,” Israel Affairs, Vol. 17, No. 1, 2011, p. 39.这些客观现实和社会处境促使以色列俄裔犹太人更加重视安全。在宗教态度上,俄裔犹太人中信仰虔诚者较少,他们推崇世俗文化,并且这一比例远远高于以色列人。对于俄裔犹太移民而言,“犹太人与犹太文化拥有着诸多含义,犹太身份的归属感也包含着许多内容,犹太人的定义不只是宗教,祈祷或信仰。”(18)Brian Horowitz and Shai Ginsburg, Bounded Mind and Soul: Russia and Israel, 1880-2010, Bloomington: Slavica Publishers, 2013, p. 155.
二、 以色列俄裔犹太移民的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民主国家政治文明的表现,以色列鼓励、支持公民参与政治活动,这既是民主实施和保证的前提,也是国家内政外交事务中的重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色列政坛出现党派林立、日益分化的现象,在对待和处理宗教与世俗、东方犹太人与西方犹太人、犹太人和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等传统问题上形成了许多中小党派,传统大党较之以往难以在议会中形成绝对的多数。这既是以色列政治生态的具体体现,也为20世纪90年代的俄裔犹太移民提供了进入以色列政坛的契机。在这种背景下,以色列俄裔犹太移民的政治参与先后经历了依附以色列主要政党、独立创建俄裔犹太移民政党以及政党政治碎片化下转型三种模式。
(一) 依附模式:以色列政党政治中的俄裔犹太移民(1990~1995年)
俄裔犹太移民对以色列主要政党的依附始于卫星名单党(Satellite Party List),该党是在以色列政党支持下建立的。此后,以色列主要政党展开了与俄裔犹太移民更多的合作。1992至1996年间,为吸引移民注意力,工党(Labor Party)首次在党内设立了34个俄裔犹太移民机构,吸收了1.8万名俄裔犹太移民。(19)Vladimir Khanina, “Russian-Jewish Political Experience in Israel: Patterns, Elites and Movements,” p. 59.1995年1月7日,工党领导人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在党内首次召开了俄罗斯劳工大会。(20)Vladimir Khanina, “Israeli ‘Russian’ Parties and the New Immigrant Vote,” p. 102.这次大会的召开是工党高层集体决策的结果,既体现了工党领导人对以色列俄裔犹太人的高度重视,又为俄裔犹太移民奠定了在主要政党中的政治地位,还为其继续吸引其他政党的注意力提供了机遇。以色列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Likud)也积极采取行动,20世纪90年代中期,17万名利库德成员中有2.7万名讲俄语的俄裔犹太移民(包括1990年以后抵达的2万名新移民)(21)Vladimir Khanina, “Russian-Jewish Political Experience in Israel: Patterns, Elites and Movements,” p. 60.。与工党不同,利库德集团并未在党内设置俄裔犹太移民组织,而是将其安排在利库德分支机构或附属部门中。以色列的中小党派也纷纷争取俄裔犹太移民的政治支持。中间党(Center Party)效仿工党做法;改革党(Shinui)采取“融合主义”原则,俄裔犹太移民及其政治精英需经过严格审核后才能加入,并要求俄裔犹太人讲流利的希伯来语和遵守改革党党内制度。

图2 俄裔犹太移民与以色列政党互动关系图
俄裔犹太移民从以色列主要政党的卫星名单党到成为以色列政党内部的重要成员,其政治地位在以色列政党政治体系中不断提高,影响力也日益增强(见图2)。这种提升离不开以色列俄裔犹太移民人口众多、参政热情高等因素。据统计,这一时期大约有6万名俄裔犹太移民与以色列各政党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其总数涉及大约8%至10%的俄裔犹太人,接近当时以色列政党政治中本土人口的总体参与率。(22)Vladimir Khanina, “Israeli ‘Russian’ Parties and the New Immigrant Vote,” p. 107.
虽然俄裔犹太移民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参与度较高,但投票模式和支持意愿总在不断变化和摇摆。以色列俄裔犹太移民与主要政党之间是依附与融入关系,存在着政治力量上的不平衡与政治话语权的不平等,这种现实使俄裔犹太人无法真正提出和实施符合该群体实际利益的政策纲领。加之初来乍到的移民群体还未完全适应和融入以色列社会,因此,俄裔犹太移民在这一阶段对以色列政党的投票与支持总是与自身的实际生活和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俄裔犹太移民认为,在以色列国家中面临的任何融入问题都是当局政府的失误和责任。如在1992年以色列议会选举中,由于利库德政府未能较好地处理俄裔犹太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在失业率不断上升,住房条件未能得到改善的情况下,俄裔犹太移民转而支持工党以表达对利库德政府在处理移民问题上的不满。 事实上,俄裔犹太移民在与以色列国内主流政党的政治互动中,从未主动、自愿地支持过以色列政党。正如俄裔犹太政治精英纳坦·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23)纳坦·夏兰斯基是著名的苏联犹太移民运动与人权运动代表,在国际上名声斐然。夏兰斯基先后在四届政府内任职,历任内政部部长、住房和建设部部长兼副总理,负责耶路撒冷地区的移民和社会事务。指出的那样,“工党在1992年的选举中应当明白,并不是其竞选活动吸引了俄裔犹太选民,而是俄裔犹太选民对每届现任政府的抗议,并寄希望于下届政府能够优先处理俄裔犹太移民事务”。(24)Bernard Reich, Noah Dropkin and Meyrav Wurmser, “Soviet Jewish Immigration and the 1992 Israeli Knesset Elections,”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47, No. 3, 1993, p. 476.
总之,20世纪90年代初期,俄裔犹太移民虽然拥有较为强大的选民基础,但参政议政实力较弱,与以色列主要政党在互动过程中存在依附、融合模式,族裔政治力量不够鲜明。因此,移民的投票意愿总是在动态中不断变化,参政议政的中心议题以改善和提高以色列俄裔犹太移民的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为主。
(二) 独立模式:俄裔犹太移民的政治参与及政党组织(1996~2002年)
俄裔犹太移民在与以色列政党短暂合作后开启了独立创建政治组织和族裔政党的努力。以色列俄裔犹太移民的政治组织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俄裔犹太移民社团,主要关注移民在以色列的适应和融入问题;另一类是俄裔犹太政党组织,这类组织拥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具体的政治纲领和稳定的俄裔犹太选民。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色列移民党(YisraelBa’Aliya,下文简称移民党)、“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YisraelBeitenu,下文简称家园党)、民主选择党(Democratic Choice)等代表性政党纷纷成功创建,开启了俄裔犹太移民在以色列政党政治体系中的独立展演。随着以色列俄裔犹太移民的逐渐融入,非正式性的俄裔犹太移民社团影响力在不断下降,以色列俄裔犹太政党也历经分分合合。时至今日,家园党依然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中占有一席之地。
1995年,纳坦·夏兰斯基在吸取了前人经验并重新定位了俄裔犹太政党的政治目标后创立了以色列移民党。该党的工作中心和宣传纲领主要集中于解决以色列俄裔犹太移民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适应与融入,提高移民的群体利益和社会地位,倡导犹太复国主义精神和价值,号召俄裔犹太移民为以色列奉献自我。在对待宗教事务上,移民党态度温和,不否认犹太教的基本要旨和理念,认为政策应在犹太教框架内进行制定。在外交政策和地区局势方面,移民党既不认可工党以土地换和平的政策,也不同意利库德强硬不退让的态度。为了能够代表以色列最广大的俄裔犹太移民利益,该党在成立后长期坚持中间路线。
家园党由俄裔犹太移民阿维格多·利伯曼(25)阿维格多·利伯曼出生于摩尔多瓦,1978年随父母迁居以色列,后服役于以色列国防部炮兵部队,拥有希伯来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专业硕士学位,曾参与创建苏联犹太复国主义论坛,担任过耶路撒冷经济公司董事会董事,国家工人联盟耶路撒冷支部的书记以及以色列俄语周刊《以色列日记》的编辑。进入以色列政府后,利伯曼历任以色列基础设施部长、交通部长、战略部长、副总理、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等重要职位。(Avigdor Lieberman)在1999年创建。家园党以世俗右翼政治为导向,汇集了大部分俄裔犹太移民精英和从利库德集团、工党、移民党及其他移民社团退出的政治骨干力量。该党遵循犹太复国主义理念,重视以色列国家安全,强调以色列国家统一和以色列是犹太人的家园,支持推进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建设。经济上,家园党提倡自由的市场经济政策、降低税收、增加对小企业的支持,提高科技投入和研发以吸引外资;政治上,家园党倡导减少官僚主义现象,认为权力分离利于政府运行;社会福利上,家园党主张在军队中服役的年轻人应享受更高比例的住房贷款,以色列政府应为6个月至6岁的儿童提供免费课外活动,还应为海外犹太人提供支持,为他们开设高质量的犹太教育学校,解决海外犹太人在面临同化、通婚后的民族认同问题。(26)“Israel Political Parties: Yisrael Beiteinu,” Jewish Virtual Library, 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yisrael-beiteinu-political-party,上网时间:2022年1月27日。
民主选择党由俄裔犹太移民罗曼·布朗夫曼(Roman Bronfman)和亚力克斯·廷克(27)罗曼·布朗夫曼和亚力克斯·廷克曾是以色列移民党中的骨干精英,因后期不满纳坦·夏兰斯基等人的一些党内政策而另立门户。(Alex Tsinker)在1999年创建。政治观点上,该党坚持左翼政治路线,致力于社会民主,反对教会人员干涉国家政治,支持国家事务与宗教事务分离,推进以色列议会选举现代化;社会层面上,该党支持世俗婚姻合法化,教育体系世俗化,提倡以色列是所有公民的共同家园,支持《回归法》,接受20世纪90年代通过伪造犹太身份而移民以色列的俄罗斯人。民主选择党与移民党、家园党共同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期俄裔犹太政治图景,成为以色列俄裔犹太移民左翼、中间和右翼路线的典型代表(见表1)。

表1 以色列俄裔犹太政党对比表
俄裔犹太移民及其政党在独立时期呈现出由左翼、中间和右翼政治路线构成的政治参与现状,不同于依附时期对移民利益的单一关注,这一阶段的政治实践更加多元化,形成了俄裔犹太政党各具特色的政治倾向、政治纲领与政治实践。民主选择党坚持左翼路线,吸引了在以色列持有左翼政治立场的俄裔犹太选民;移民党坚持中间路线,成为以色列主要政党组阁时积极争取的力量;家园党坚持世俗的政治态度,符合大部分俄裔犹太移民的文化素质和宗教倾向,自成立至今一直受到以色列社会的关注。
俄裔犹太移民在独立时期的政治参与表现出以下特点:政治参与意识由弱变强,政治自决程度由低到高,政治力量从势单力薄到羽翼丰满,政治议题从关心移民的现实利益到以色列国家安全、地区局势甚至更宏大的政治议题上,政治倾向从主要代表俄裔犹太移民利益到争取代表更广泛的世俗犹太人权益。
(三) 转型模式:俄裔犹太移民的政治变迁(2003年至今)
俄裔犹太政党为应对选民不断转变的政治意愿和内部危机,开始在以色列政坛不断转型。俄裔犹太政党在历次政治选举中或结盟,或独立,依据自身情况和国内外局势采取应对策略。
俄裔犹太政党在2003年议会选举中在不同程度上开始走向衰落。移民党内部的不断分裂和俄裔犹太人选举意愿的转变使该党只获得两个席位。民主选择党和家园党也分别加入了梅雷兹党(Meretz)和全国联盟党(National Union),这令以色列社会一度认为俄裔犹太人的政治现象将会消失。为应对困境,家园党在2006年以色列议会选举时重新以独立的政党身份竞选并一举获得了11个议席。家园党领袖利伯曼指出,“家园党制定了新的政策方案讨论以色列俄裔犹太人关心的主要议题”。(28)Vladimir Khanin, “The Revival of ‘Russian’ Politics in Israel: The Case of the 2006 Election,” Israel Affairs, Vol. 13, No. 2, 2007, p. 350.家园党还提出了解决以色列犹太国家属性和民主化的方案,即和平—人口方案。(29)顾奕:《利伯曼及其领导的以色列家园党》,载《西亚非洲》2007年第5期,第44页。2009年议会选举前,以色列不断遭遇来自加沙地带火箭弹和迫击炮袭击,俄裔犹太移民及其政党在安全问题上表现出十分敏感的情绪。家园党继续秉持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强调国家安全和开放对犹太人定义的标准。这次选举后,家园党获得15个议席,成为继前进党和利库德集团后的第三大政党。
2013年议会选举中,以色列俄裔犹太人更加支持侧重于安全和外交的政党。家园党加入利库德集团,该联盟以31席领先其他党派并成功组阁。这种联盟既解决了双方当时的选举困境,也为家园党日后能够跻身于以色列主要政党之列奠定了基础。此外,俄裔犹太移民在此次选举中对中左翼政党的支持率发生了明显变化,前进党几乎失去了俄裔犹太移民的选票支持。2015年以来,面对叙利亚局势和加沙地带来自哈马斯(Hamas)的威胁,家园党提出了具有中右翼政治倾向的竞选纲领。这既赢得了俄裔犹太人的政治支持,也吸引了许多以色列人的投票。安全问题使俄裔犹太移民及其后裔对家园党的支持率达到41.4%。(30)Michal Shamir and Gideon Rahat, The Elections in Israel 201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 127.2019至2020年选举期间,领先的利库德集团和蓝白党(Blue and White)均因无法成功组建政府致使以色列国内进行了三次议会选举,家园党分别在2019年4月、2019年9月和2020年3月大选中分别取得了5个、8个和7个席位。2020年12月23日,利库德和蓝白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因无法通过预算案而宣布进行第四次政治选举。
转型时期的俄裔犹太移民及其政党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俄裔犹太政治图谱由完整的左、中、右翼政治力量向实用世俗化的右翼政治力量倾斜。2003年以后,独立的俄裔犹太政党开始走向衰落,有的融入以色列政党,有的则从以色列政坛消失。家园党成为2006年议会选举中严格意义上能够代表俄裔犹太移民政治愿景的政党,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俄裔犹太选民日益右倾的政治倾向。其次,俄裔犹太移民的投票趋势开始由支持族群型政党转向支持以色列国内的主要政党。出现这一趋势的原因是俄裔犹太移民逐渐融入以色列社会,移民群体的生活需求和社会地位得到了满足和提高,俄裔犹太人愿意支持以色列国内的主流政党。最后,俄裔犹太政党从单一型族裔政党向混合型族裔—国家政党转变。家园党在2009年议会选举中就以国内亟待解决的安全问题为竞选口号,辅助考虑俄裔犹太选民的政治诉求,超越了以色列国内只代表单一族群利益的其他政党。
虽然以色列国内的俄裔犹太移民积极参与政治实践,不断提升参政议政水平,但在具体的参与过程中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一是俄裔犹太移民内部存在异质性。后苏联时期移民至以色列的俄裔犹太人拥有共同的俄语文化认同,但其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移民群体在来源地区、宗教信仰和政治实践等方面存在差异。以色列国内90多万讲俄语的人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来自俄罗斯,三分之一来自乌克兰,其余的则从中亚到高加索,再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和波罗的海。(31)Izabella Tabarovsky, “Russian-Speaking Israelis Go to the Polls,” Wilson Center, April 4, 2019, https://www.wilsoncenter.org/blog-post/russian-speaking-israelis-go-to-the-polls,上网时间:2021年6月30日。异质化的俄裔犹太移民在以色列政党政治体制下依据自身情况与政治态度进行多样化政治选择,政治力量也因此更加分散,这对以吸引俄裔犹太移民作为政治基础的俄裔政党而言是一种现实挑战。二是以色列俄裔犹太移民的政治参与受到代际差异的影响。成年时期移民至以色列的俄裔犹太人近年来在政治态度和政治选票上主要集中在中右翼阵营,而在以色列出生的俄裔犹太人在政治实践上更加多元化,呈现出政治参与的代际差异。据巴伊兰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主任拉里莎·雷门尼克(Larissa Remennick)的一项调查发现,三分之一的年轻选民指出,他们的政治观点与父母不同,投票模式更加多样化,年轻一代认为80%的老一代移民已成为中间偏右的一部分。在政治倾向上,25%的年轻一代将自己定义为左翼,8%的人表示他们比父母那一代更激进。(32)Ira Tolchin Immergluck, “Russians Are Coming ... to the Polls. Israeli Politicians Are Finally Waking up,” The Times of Israel, July 26, 2019,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russians-are-coming-to-the-polls-israeli-politicians-are-finally-waking-up/,上网时间:2021年6月29日。三是俄裔犹太移民的政治信心不足。俄裔犹太人认为他们在以色列国家的许多政治部门中代表性不足,移民关心的实际问题未能得到足够重视和有效解决,移民对于生活现状的失望降低了政治参与的热情。根据以色列国会在2021年第四次议会选举前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1%的俄裔犹太移民认为他们在政府中没有足够的代表权,80%的人认为在司法机构中代表性不足,72%的人在媒体中感到不足,37%的人在教育系统中感到代表性不足。(33)Tzvi Joffre, “71% of Russian Speakers Feel Inadequately Represented in Gov’t - Poll,” The Jerusalem Post, March 14, 2021, https://www.jpost.com/israel-news/71-percent-of-russian-speakers-feel-inadequately-represented-in-govt-poll-661941,上网时间:2021年6月30日。
通过分析俄裔犹太移民的政治参与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可知,未来以色列俄裔犹太人的政治实践和关注点依然会围绕提升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保障国家安全以及化解教俗矛盾展开。在提升社会经济地位上,成年时期移民至以色列的俄裔犹太人被迫失去了领取苏联养老金的机会,移民后囿于在以色列的工作年限、职业资质与劳工市场不匹配等现状而无法顺利获得或只能较少获得以色列国家养老金。经济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俄裔犹太人社会地位的提升,养老金、住房、就业等问题已成为以色列主要政党吸引俄裔犹太人政治选票的竞选纲领之一。在国家安全方面,以色列俄裔犹太人虽然看重经济保障和个人发展,但这一切在安全面前都不值一提。后苏联时期到来的俄裔犹太人在经历了寄居国不稳定的政治环境,2006年的以黎冲突和2009年的“铸铅行动”(Operation Cast Lead)后,安全问题毫无疑问成为移民心中的政治焦点,个人利益让位于国家安全。在教俗矛盾上,俄裔犹太移民与宗教阵营之间的分歧由来已久,主要集中在服兵役、犹太人身份和宗教干预公共生活等方面。宗教人士不仅被免去了服兵役的义务,也不积极参加工作。加之以色列政府还对宗教人士给予补贴,这引起了以色列社会对于公平问题的广泛讨论,俄裔犹太移民的身份甚至经常遭遇宗教人士的质疑。此外,以色列的公共生活也受到宗教限制,如安息日不运行公共交通,阻止公证结婚等,秉持世俗主义的俄裔犹太人和以色列人时常感受到宗教的束缚。
三、 以色列俄裔犹太移民的政治影响
以色列俄裔犹太移民在依附、独立和转型时期以不同的参政模式进行族裔政治实践。随着政治参与度的提高和俄裔犹太政党政治实力的增强,俄裔犹太移民不仅成为影响以色列内政外交的重要力量,也成为牵动巴以和平进程走向和中东局势发展的重要变数。
(一) 参加政治选举,左右政府组阁
俄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后,通过政治途径由被动参加到主动参与,由依附主要政党到独立创建族裔政党,这些现象与俄裔犹太移民在以色列的生存环境和未来发展息息相关。从1992年以色列议会选举中俄裔犹太移民的不俗表现来看,以色列国内主要政党在制定和实施移民政策时需要考虑俄裔犹太人的政治参与情况,他们凭借稳定的选民数量、俄语为主的宣传媒体、集中聚居的社会网络和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政党组织左右以色列政坛,具体表现在影响选举结果与左右政府组阁两个方面。
在影响选举结果方面,以色列俄裔犹太移民的人口优势和选票走向十分关键,有时甚至扮演着关键的少数和打破政治僵局的角色。“1992年议会选举,工党所获的44个席位中有4席来自俄裔犹太移民选票。当时俄裔犹太人支持工党被认为是不满利库德集团在处理1989年移民浪潮时的做法。”(34)Edith Rogovin Frankel, “The ‘Russian’ Vote in the 1996 Israeli Elections,” East European Jewish Affairs, Vol. 26, No. 2, 2008, p. 5.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数据显示,即使在2019年以色列竞选活动中,来自苏联的移民依然是最受追捧的选民之一,这并非毫无道理。该群体占全国630万合格选民的12%,约有77万选民可以进行投票,这些票数约等于以色列15个至16个议会席位。(35)“Russians are Coming...to the Polls. Israeli Politicians are Finally Waking up,” The Times of Israel, July 26, 2019,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russians-are-coming-to-the-polls-israeli-politicians-are-finally-waking-up/,上网时间:2021年6月7日。
在政府组阁方面,俄裔犹太政党多次表现出左右政府组阁的能力。以利伯曼领导的家园党为例,该党历来政治态度坚定、立场鲜明,多次造成了以色列主要政党不得不依靠其他党派或重新进行选举的局面。2002年,家园党因不满沙龙政府的克制政策而退出政府;2005年,利伯曼因极力反对沙龙政府的单边撤离计划而遭到解职;2014年,因内塔尼亚胡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打击不力,利伯曼提出“分手”;2018年,利伯曼因不满内塔尼亚胡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而辞去国防部部长职位。家园党的退出使执政联盟的议会席位数减至关键性的61席,总理内塔尼亚胡不得不选择同时兼任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和卫生部长等职务;2019年4月议会选举后,家园党拒绝加入利库德集团导致组阁失败。同年9月,利伯曼先是呼吁建立一个包含家园党、利库德和蓝白党共同构成的大联合政府,随后却拒绝加入利库德集团和蓝白党;2021年以色列议会选举后,由右翼政党“亚米纳”党领导人纳夫塔利·贝内特(Naftali Bennett)、“新希望”党领导人吉迪恩·萨尔(Gideon Saar)、家园党领导人利伯曼,以及被授予组阁任务的“拥有未来”党领导人亚伊尔·拉皮德(Yair Lapid)参与组阁谈判,形成了新一届以色列政府。然而,据《以色列时报》网站报道,利伯曼在派系会议上与贝内特和拉皮德就极端正统派政党能否成为即将上任的联合政府的一部分产生分歧,并要求立即出台限制哈瑞迪犹太人的法律。(36)“Liberman Said to Tell His Party Members Haredim Won’t Be Joining Government,” The Times of Israel, June 10, 2021,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liberman-said-to-tell-faction-that-haredi-parties-wont-be-joining-unity-govt/,上网时间:2021年6月11日。
从表面上看,2019年4月家园党拒绝加入利库德集团主要是围绕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服兵役的问题展开,而从更深层的原因分析则是以色列多组社会矛盾中的一组,即世俗与宗教之间的裂缝。根据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在苏联出生的俄裔犹太人在以色列自我认同为世俗的比例为81%,而在所有以色列犹太人中这一比例为49%。当他们谈到对宗教和政治的看法时,这一事实很明显:以色列的俄裔犹太人坚决反对宗教参与政府,大约80%的俄裔犹太人表示宗教应该与政府政策分开。(37)Angelina E. Theodorou, “Israeli Jews from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re More Secular, Less Religiously Observant,” Pew Research Center, March 30, 2016,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03/30/israeli-jews-from-the-former-soviet-union-are-more-secular-less-religiously-observant/,上网时间:2021年6月12日。然而,极端正统派政党是利库德集团的支持者和联盟者之一,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在人口上拥有较高的生育率,是哈拉哈(Halakhah)(38)哈拉哈是希伯来语音译,指书面和口头托拉的犹太宗教法律体系。字面意思也有行走之义,寓意犹太人要按律法之道指导宗教实践和日常生活。虔诚的信奉者和践行者。他们的成年男子终日专注于托拉(39)托拉在广义上指神启示给以色列人的真义,字面意思为指引,它指导犹太教徒的生活方式,几乎所有的犹太教律法与教导都可以被涵盖到托拉中。学习,养家糊口的角色通常由妻子承担。数量庞大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就这样生活在有大量孩子的单劳动力收入家庭中,落入以色列社会最贫困的阶层。他们日益成为政府财政开支的负担,还普遍拒绝服以色列的义务兵役制度,引起以色列民众和纳税人的强烈不满。(40)宋立宏:《坚守与妥协: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基要主义》,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5期,第24页。当宗教政党成为联合政府的一部分时,以色列的世俗人士难免遭受宗教教义的裹挟。正如专注于以色列俄裔犹太移民研究的记者莉莉·加利利(Lily Galili)认为,“来自苏联的移民为此苦苦挣扎,他们觉得这种宗教束缚令人反感,他们曾经因为是犹太人在苏联受苦,现在却因为被宗教政党认为是俄罗斯人而在以色列受苦”。(41)“On Multiple Fronts, Russian Jews Reshaped Israel,” National Public Radio, January 2, 2013, https://www.npr.org/2013/01/02/168457444/on-multiple-fronts-russian-jews-reshape-israel,上网时间:2021年6月13日。2021年以色列新政府成功组阁后,家园党再次将矛头直指新政府对于宗教政党的态度和行为,教俗矛盾成为以色列社会无法规避并牵动政府稳定的现实困境。
(二) 参与政策制定,影响社会发展
俄裔犹太移民是以色列“大移民”历史的见证者,数量众多的俄裔犹太人作为犹太民族的一个特殊面向,深刻影响着以色列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政治上,俄裔犹太人积极争取议会要职,推动政策制定实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色列宗教党对俄裔移民的犹太身份产生怀疑。由于宗教党当时掌握着内政部长一职,负责确认移民的犹太身份和赋予公民权等问题,这种质疑给俄裔犹太人的移民活动带来诸多不便和限制。移民党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俄裔犹太人的感情,客观上造成移民率的降低。1999年选举后,移民党将获取内政部长一职与时任总理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讨价还价作为进入联合政府的条件。2018年,以色列议会在俄裔犹太政党的提案下通过了《解放日》(Liberation Day)和《纳粹德国救助日》(Day of Rescue from Nazi Germany)法案,并在西墙举行盟军胜利纪念日的官方仪式。此外,大规模的俄裔移民浪潮改变了以色列议会的工作进程,令以色列政府一度调整了与住房和移民安置相关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从而推动了以色列小城镇发展,加快了城市化进程。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政府由依靠私人市场调控住房转变为政府主导直接进行大规模住房建设,这一变化是以色列国家整体规划和边境地区犹太化项目的组成部分,体现出这一时期国家主导与市场配合的特点。为此,以色列议会在此期间急剧增加了与住房有关的171项法案,这一数量是前十年提议的8倍,不仅法案的数量增加了,而且所涉及的住房主题种类也从4个增加到10个,补贴优惠政策也相应发生了变化。(42)Ravit Hananel, “Bills, Rights and Housing Policy: The Evolution of Israel’s Seven-Decade Housing-Related Bills,” Sustainability, Vol. 13, No. 9, 2021, p. 8.
在经济层面,俄裔犹太人为以色列补充了劳动力,增加了投资与消费。大量的移民人口为以色列工业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劳动力,以色列工业增长率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生产、生活基本必需品和日常消费品等轻工业也迎来较快发展。在经济贡献上,俄裔犹太移民良好的教育水平和丰富的研究经验为以色列日后发展高科技产业提供了智力支撑。事实上,俄裔犹太人的创新贡献遍布全球,搜索引擎谷歌和全球在线支付平台贝宝(PayPal)的创始人都是来自苏联的犹太人,有学者研究了美国俄裔犹太人的创新经历后指出,1975~2003年定居美国的近60万名来自苏联的移民中,约有54%是犹太人。(43)Sheila M. Puffer, Daniel J. McCarthy and Daniel M. Satinsky, Hammer and Silicon: The Soviet Diaspora in the US Innovation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09.与美国一样,以色列的俄裔犹太移民中也有许多高学历和高素质人才,吸收高技术人才是以色列的一项国家政策。为此,以色列专门设置了管理和服务机构,专项基金和资助计划并提供语言与职业培训。(44)艾仁贵:《以色列的高技术移民政策:演进、内容与效应》,载《西亚非洲》2017年第3期,第52-58页。
在社会层面,年轻的俄裔犹太青年积极服兵役,他们将部队服役视为“以色列化”的过程。虽然以色列国防兵的人数在不断下降,但这并不影响俄裔犹太移民的参与率,因为征兵入伍被俄裔犹太青年视为融入社会的一种途径。新移民家庭中的入伍比例一般比以色列社会高出10%,大部分人都在作战单位服役。(45)Lily Galili, “The Other Tribe: Israel’s Russian-Speaking Community and How It Is Change the Country,” Foreign Policy at Brookings, September 2020, p. 10.此外,在对待和处理巴以问题、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等问题上,家园党持有独立态度和坚定立场。以色列阿拉伯人虽然拥有公民权,但不能完全享有与犹太人同等的权利和自由。以色列阿拉伯公民需要接受审查,还要承受来自俄裔犹太政党对阿拉伯人的质疑。2009年议会选举前夕,利伯曼认为激进的以色列阿拉伯公民是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并将竞选口号确定为“没有忠诚就没有公民身份”。(46)Dani Filc, The Political Right in Israel: Different Faces of Jewish Populism,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 108.他还指出:“以色列125万阿拉伯人是一个问题,必须从犹太国家分离出去,我们建立了犹太人的国家,我希望它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国家,我们在不远的将来会看到这样一个国家”。(47)冯基华:《以色列右翼势力及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影响》,载《西亚非洲》2008年第10期,第40页。
(三) 支持定居点计划,牵动巴以和平进程
以色列在短期内接收的大量移民人口虽然刺激了国内建筑业和工业的发展,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移民与住房安置的实际问题。为此,以色列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兴建定居点以吸收犹太移民。据以色列定居点管理者估计,1990年上半年约有6,000至7,000犹太人定居在被占领土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而这一时期对房屋的需求还在不断地攀升。(48)Joost R. Hiltermann, “Settling for War: Soviet Immigration and Israel’s Settlement Policy in East Jerusalem,”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20, No. 2, 1991, p. 75.
在定居点问题上,以色列国内主要政治党派秉持不同的立场和想法,但这一时期的俄裔犹太人反对撤离定居点,认为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久的、统一的首都,反对在耶路撒冷地位、难民回归、边界划分等核心问题上让步甚至进行谈判。(49)张馨心:《俄罗斯裔犹太移民在以色列的地位及影响》,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 年第3期,第152页。俄裔犹太移民对于定居点的强硬态度主要受1990年以色列政府面对大规模移民人口时的吸收困境和俄裔犹太人对待土地顽固态度的影响。首先,20世纪90年代,当以色列政府逐步加快了移民速度,随之而来的是如何安置移民以及以色列境内交通拥堵,房屋租金上涨等社会问题。大规模的移民造成严重的住房短缺,而租金自1989年以来飙升了30%至40%。(50)“1990 Influx of Immigrants to Israel Largest Since 1949: Mideast: Approximately 187000 Emigres, Most of Them Soviet Jews, Have Arrived Since January,” Los Angeles Times, December 25, 1990, https://www.latimes.com/archives/la-xpm-1990-12-25-mn-7227-story.html,上网时间:2021年6月13日。俄裔犹太移民在定居点生活不仅可以暂时解决住房、就业和实际生活等问题,而且还可以改变该地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人口结构。以色列政府还为这一时期移居到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俄裔犹太人每月提供金额不等的住房补贴,并像其他定居点的以色列犹太人一样,为他们日后购买或租住房屋提供更好的优惠条件。(51)John Quigley, “Soviet Immigration to the West Bank: Is It Legal?,” Georg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Vol. 21, No. 3, 1991, p. 384.随着大量移民先后定居,东耶路撒冷还成立了移民安置机构——耶路撒冷发展局以处理该地区的经济和就业问题。1990年,东耶路撒冷这座城市的35万名犹太居民中,约有12万人选择住在东耶路撒冷对面的“犹太社区”。(52)Joost R. Hiltermann, “Settling for War: Soviet Immigration and Israel’s Settlement Policy in East Jerusalem,” p.76.其次,俄裔犹太移民对领土分裂持有强硬态度。以色列俄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重要动因之一是摆脱在苏联遭遇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困境,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俄裔犹太人曾深受苏联对被占领土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俄裔犹太人将定居点视为战略屏障以弥补以色列国家战略纵深的不足,一些具有极端宗教思想的俄裔犹太定居者甚至将定居点行为视作“大以色列”梦的现实实践。
以色列政府的定居点政策虽然满足了自身利益,但该问题却成为牵动巴以和平进程,影响地区局势的焦点之一。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面临着更多的竞争与挑战,他们无法获得与犹太人一样的住房条件,同时还要面对淡水资源和就业岗位等其他方面的资源争夺。巴勒斯坦人的失业率不断上升,具有优势教育背景和专业技术才能的巴勒斯坦人选择离开被占领土地区,造成该地区人才流失的困境。定居点问题也给巴以和谈带来负面影响,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表示,“俄罗斯移民到以色列已成为实现中东和平协议的主要障碍。他担心以色列国防军越来越多的由来自该社区的士兵组成,因此可能不会完全愿意反对以色列定居者。(53)Josh Rogin, “Bill Clinton: Russian Immigrants and Settlers Obstacles to Mideast Peace,” FP Insider Access, September 21, 2010,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0/09/21/bill-clinton-russian-immigrants-and-settlers-obstacles-to-mideast-peace/,上网时间:2021年6月13日。”这在事实上加剧了巴勒斯坦当局和以色列之间的鸿沟,双方可能陷入更多的冲突和矛盾中,地区局势也会因此增加更多变数。
(四) 影响以俄关系,增添多元文化要素
以色列和俄罗斯因俄裔犹太移民的存在有着独特的亲缘关系,俄裔犹太移民是两国关系发展的纽带和桥梁。历史上,俄罗斯曾是世界上犹太人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目前,以色列拥有90多万熟练使用俄语的犹太移民,即使在2019年,以色列国际移民中来自俄罗斯的移民有15,821名,占33,247名移民总数的48.2%,比2018年增长约50%。(54)《2019年以色列移民人口概况》,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网站,2020年3月30日,https://www.cbs.gov.il/en/mediarelease/Pages/2020/Immigration-to-Israel-2019.aspx,上网时间:2021年6月11日。可以说,以色列俄裔犹太人的存在是影响以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
在政治领域,两国高层加强政治互访与合作交流。俄罗斯作为巴以问题中东谈判四方代表之一,对以色列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在俄裔犹太人的移民问题上,以色列希望通过积极的政治手段吸引俄裔犹太精英移居。2001年2月,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出访俄罗斯时特意挑选了两位随行官员:一位是历任过多个部长职务的家园党领导人利伯曼,另一位是移民接收部部长齐皮·利夫尼(Zipi Livni)。访问期间,沙龙与俄罗斯犹太社团领导人进行会晤。2016年2月,以色列和俄罗斯签订了《关于促进以色列议会和俄罗斯联邦议会联邦理事会合作的协定》(55)《关于促进以色列议会和俄罗斯联邦议会联邦理事会合作的协定》(Agreement on Promotion Inter-parliamentar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Knesset of the State of Israel and the Council of the Federation of the Federal Assembl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是以色列议会和俄罗斯联邦议会联邦理事会之间就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领域签订的协定。,双方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两国间议会合作和人文交流。在2018年胜利日游行庆典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在莫斯科参加了庆祝活动,以色列是除苏联地区外唯一在5月9日庆祝胜利日的国家。(56)“Israeli-Russians Celebrate WWII Victory Day,” Al-Monitor, May 7, 2019, 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9/05/israel-russia-nazi-germany-world-war-ii-victory-parade.html,上网时间:2021年5月20日。由于俄裔犹太人曾是苏联红军的组成部分,为苏联的卫国战争做出了巨大牺牲,20世纪90年代后,当这批俄裔犹太老兵移民以色列后,自然而然成为以俄两国曾经共同抵抗纳粹的历史见证。2020年1月,普京接受内塔尼亚胡邀请,在耶路撒冷为列宁格勒保卫战遇难者纪念碑揭牌。(57)“Putin Opens Leningrad Siege Memorial in Jerusalem,” The Moscow Times, January 23, 2020,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20/01/23/putin-opens-leningrad-siege-memorial-in-jeru-sa-lem-a69022,上网时间:2021年6月12日。据统计,内塔尼亚胡在12年任期中共访问了俄罗斯11次。在2020年访问期间,普京释放了以色列人纳马·以萨迦(Naama Issachar)。2019年4月以来,她因毒品指控被关押在俄罗斯,而俄罗斯总统在以色列总理访问期间善意地赦免了她。该案件在以色列受到密切关注,她的获释被视为双边关系积极的象征。(58)Pritish Gupta, “Russia and Israel: Towards a Pragmatic Partnership,”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March 5, 2020,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russia-and-israel-towards-a-pragmatic-partnership-61949/,上网时间:2021年6月12日。
在经贸领域,以色列和俄罗斯不断改善两国的经济关系。两国在1994年和2010年分别成立了俄罗斯—以色列贸易和经济合作委员会、俄罗斯—以色列商务理事会。以色列和俄罗斯两国间的贸易结构并不平衡,以色列从俄罗斯进口的商品按比重划分依次为钻石和玻璃制品、金属、木材和能源等,向俄罗斯出口的货物主要集中在蔬菜、化学药品、机器和电气设备等。从两国进出口贸易情况可以看出,两国间的经贸往来与国内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所向密不可分,以色列从俄罗斯的进口货物多集中在原材料和能源资源项目上,出口货物则是农产品和基础设施设备。在以色列进口榜单上首屈一指的重要进口项目是未经加工的钻石,作为全球最重要的钻石加工地和世界最权威的钻石交易中心之一,以色列的钻石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钻石、特殊宝石和珠宝管理局发布的月度评论,以色列的钻石行业自2021年初以来持续从新冠疫情中反弹,钻石贸易的四个主要类别都出现了急剧增长。以色列经济和工业部报告称,2021年前五个月,以色列毛坯钻石净出口总额为7.55亿美元,比2020年同期增长150%。(59)Gilad Zwick, “Israel’s Diamond Exports Jump 150% from January-May 2021,” Israel Hayom, June 8, 2021, https://www.israelhayom.com/2021/06/08/israels-diamond-exports-jump-150-from-january-may-2021/,上网时间:2021年6月15日。在对俄罗斯的出口货物上,以色列农产品出口既得益于其高水平的农业发展,也受俄罗斯国内作物种植和气候因素的影响。在旅游业方面,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数据,2010年、2015年和2019年,俄罗斯是继美国之后来访以色列游客人数最多的国家,三年共计来访93万人次。(60)《以色列2010、2015和2019年的游客人数》,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网站,https://www.cbs.gov.il/he/mediarelease/doclib/2020/004/28_20_004t6.pdf,上网时间:2021年6月12日。
在文化领域,以色列和俄罗斯在高新技术领域之间开展合作。合作涵盖了纳米技术、能源和军事硬件等关键领域,以俄之间能够进行高新技术的合作基于以下原因:一是以色列作为全球极具创新力的国家,拥有着丰富的创新经验和人才储备。从1991年到2013年,政府投资了约1,900个项目,国家总投资7.3亿美元,超过1,600多个项目已经发展为创业公司,60%的项目成功吸引了私人资本。到2013年,仍有35%的研究生活跃在科研一线。(61)Tatiana Dmitrievna Moshkova, “Russian-Israeli Relations: The Role of the Russian-Speaking Community of the State of Israe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8, No. 2, 2018, p. 393.二是两国之间在人才交流和项目合作上不存在语言障碍。以色列拥有着数量庞大的俄裔犹太移民,在这种人口优势下,俄语也成为继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后在以色列国家最为普遍使用的语言。三是两国之间的合作模式符合双方需求。以色列为俄罗斯提供技术、人才和资金方面的支持,俄罗斯则提供开展合作研究的物质基础和其他资源,包括土地、基础设施、水源等研究条件。
除政府间行为以外,以色列俄裔犹太移民在日常生活和文化习惯上早已深深打上了“俄罗斯印记”。以色列有许多出售俄罗斯食品的商店,俄裔犹太人的聚居社区出现了俄罗斯街(Russian Street);在家庭装饰上,俄裔犹太移民选择具有俄罗斯文化元素的饰物;在节日庆典上,2010年,来自乌克兰北部城市的俄裔犹太老兵与参加过反法西斯战争的其他战友接受了来自俄罗斯的民间援助,在以色列北部城市阿什杜德(Ashdod)建立了二战犹太英雄主义博物馆。(62)“Israeli-Russians Celebrate WWII Victory Day,” Al-Monitor, May 7, 2019, 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9/05/israel-russia-nazi-germany-world-war-ii-victory-parade.html,上网时间:2021年5月20日。这为展示犹太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勇敢和坚毅提供了最好例证,也为以俄关系的合作与发展奠定了民间基础。
四、 结语
以色列的移民活动伴随着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而壮大。以色列建国后,出于对国家安全和犹太民族兴衰存亡的现实考虑,以色列政府一直将吸收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移居以色列作为国家重要的政策。为此,以色列曾一度忽略移民的年龄、肤色、性别、职业、地域和教育背景。时至今日,以色列有不同肤色、讲多种语言、拥有不同生活习惯和文化特点的移民群体。在所有犹太移民中,以色列俄裔犹太人的群体特征和社会影响十分瞩目。在国家政治方面,俄裔犹太人在以色列的参政模式经历了依附、独立和转型模式。俄裔犹太政党进入联合政府后,依据国内、国际局势,充分考虑俄裔犹太移民在以色列国家的现实利益,凭借政治优势不断扩大影响力,成为以色列政坛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以色列俄裔犹太人的政治参与和参政模式是多方合力的结果:一是以色列国家对犹太移民的政策支持。1948年,以色列《独立宣言》明确表示:“以色列将对犹太移民和流散者开放,她将促进国家的发展,造福所有居民,她将以先知们所设想的自由、正义与和平为基础,确保所有公民的社会和政治权利完全平等,不论其宗教、种族或性别。”(63)“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The Knesset, May 14, 1948, https://main.knesset.gov.il/en/about/pages/declaration.aspx,上网时间:2021年6月30日。以色列国家履行承诺,对初次踏上以色列国土的俄裔犹太移民赋予公民权并提供具体帮助,包括免费的希伯来语教育、生计培训和发放6个月的生活救助金与医疗保险。二是以色列独特的单一比例代表制(64)以色列实行一院制议会,设120个席位,各党派获得议席的多少取决于得票的多少。各政党应得议席数的计算方法是:议席总数(120)乘以某党的得票率。和多元、宽容的社会文化环境。以色列赋予每一个公民参政议政的权力,为族群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与空间。以色列开放、包容的环境吸引了更多的俄裔犹太移民,他们积极采取行动,主动参与地方、国家的政治选举,在议会选举中拥有较高的参与热情和投票率。三是以色列俄裔犹太移民拥有的人口优势、人力资本、聚居模式和社会网络等特点,这些特征加强了族裔团结,促使他们创建政治组织,为政治参与奠定了基础。四是以色列政党政治日益碎片化和以色列社会日益分裂的(65)Majid Al-Haj, Immigration and Ethnic Formation in a Deeply Divided Society: The Case of the 1990’s Immigrants from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Israel, Boston: Brill, 2004, p. 194.现实。以色列的政治体制使传统大党难以形成绝对的多数,为建立联合政府,以色列的领先政党需要中小党派的支持,这使各党派在进入联合政府时与组阁政党讨价还价,极易造成以色列政府不稳定的局面。此外,以色列国家在世俗与宗教、东西方犹太人、犹太人与以色列阿拉伯公民、左右翼政治势力等问题上难以统一,认同极化和选举身份的困境也使以色列各政党之间难以妥协,尤其表现在2019~2021年以色列四次选举中。
以色列作为典型的移民国家收获了许多实际利益。然而,由于地域、历史和现实原因,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也呈现出多元特点。为了在以色列更好地生活,移民群体在族群政治意识不断觉醒的背景下,纷纷创建代表自身利益和政治诉求的政党。然而,族群政治既有充分彰显民主,表达政治意见的积极特点,也给以色列带来深刻的消极影响。以色列俄裔犹太移民及其政治组织便体现了这一点:一方面,俄裔犹太政党数次进入政府,为以色列俄裔犹太人争取族群利益提供了合法途径,降低了族群冲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以色列现有政治体制和地区争端背景下,族群政治的兴起和发展会成为族群冲突的导火索。譬如俄裔犹太政党与阿拉伯政党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以色列的民主质量也会遭遇一定程度的冲击和挑战。大量族群型政党的出现会直接导致参与议会席位的政党数量增多,加剧了政党制度的多极化与碎片化,进而导致政府组阁的困境。(66)张建伟:《族群型政党:概念、类型及其影响》,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第34页。因此,无论以色列国家的政党政治将如何发展,族群政治始终会成为以色列政府长期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