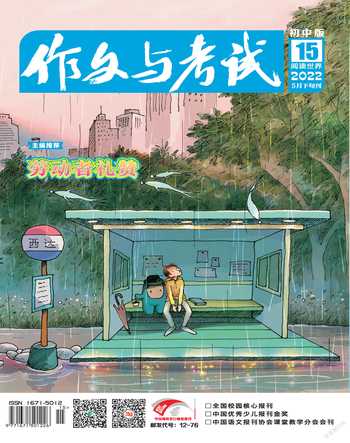无尽的爱
2022-06-29胡文捷
胡文捷
张洁,中国当代作家,是新时期首位两次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女作家,被称为“女性主义文学”的旗手。其代表作《沉重的翅膀》《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无字》等,体现了其在不同阶段下女性的觉醒意识。
作家张洁从1978年开始创作,多年以来笔耕不辍,在短篇、中篇、长篇领域,均曾获得过国内文学最高奖项。张洁在多年来的写作中,从不追逐时代潮流,不去迎合读者的心理,而是忠于自我,写她真心所想。因此,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张洁的写作风格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早期,张洁的小说中常常呈现出政治抒情与个人抒情的结合,既体现出了对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沉思、歌颂与感慨,又体现了这个时代下的人性与真情。中期,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相关的社会问题的出现,张洁的作品转向写实风格,更多地体现出对尖锐的社会问题与矛盾的揭露。中后期,张洁的作品展现出反讽式的荒诞,并逐渐加入更多对宗教与历史的思考。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这本书,便是张洁中后期作品风格转型的重要转折点。这本书写于张洁母亲去世后,正是她最为痛苦的时刻。张洁是由母亲单独拉扯长大,家中没有兄弟姐妹,而张洁本人也只有一个在美国工作居住的女儿。张洁本人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张洁正处于与第二任丈夫若即若离的婚姻关系中。因而,在张洁的生命中,与之关系最为紧密的便是她的母亲,两人一起生活了54年,她们的人生紧紧纠缠,“根本无法分清哪是她的人生、哪是我的人生”。这本书所写的,便是张洁与母亲所共度的最后80多个日夜。
这本书读起来并不容易,写作时是张洁刚刚丧母、最为悲痛的时刻。全书回忆了母亲做最后一次手术的全部细节,以及母亲突然辞世之前的种种被“我”忽略的细节。可以想象,作者在写这本书时,经历着怎样的崩溃。这本书不加任何粉饰地反射着作者当时的心境,对于挚爱的母亲离世的悲痛和深深自责,对于独自一人照顾母親的无助,对于无法给予足够帮助的医生、保姆、丈夫等人的埋怨等。
这并不是一本“讨喜”的书,它不是为了刻画一对感人肺腑的母女形象而书写的,它更像是一本忏悔之书,记录自己在母亲离世前各种疏忽和纰漏,以至于没能挽救母亲的性命。全书充满絮絮叨叨的悔恨自责的话语,后悔的情绪遍布全文。然而,读完全书之后,却突然明白了这本书存在的意义:它并不是一本文学作品,因此不会去考虑读者的阅读感受,也不会搭建任何故事架构,它只是一本抒发自我的书。因为真实,所以漏洞百出;也正因为真实,才有其独特的警醒价值。
作者与母亲之间的关系是极深的,甚至到达了一种“共生”的关系。这与作者与母亲的经历有极大的关系,她们处于同样的地位,家中缺乏父权存在,母亲为女儿倾尽所有的照顾,使得母女之间结成了牢不可破的精神同盟,在全文中,作者毫不掩饰地表达着对母亲的依恋,并认为母亲才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
也正是如此,作者为母亲是否要做手术而做出的决定,才成为她无法跨过去的坎。作者一直认为,是她让母亲做手术的决定,才最终害死了母亲,因此在回忆的所有细节中,都带有悲痛的底色。她不断回忆着与母亲所相处的最后时刻,回想起来都令人心痛:与母亲的最后一次通话,母亲和小阿姨最后一次上街买菜,母亲的最后一次苛责,在离开那个房间前她所瞥向母亲的最后一眼……
正如作者所言,一个人在五十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要比在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苦多了。还是婴孩的她从母亲的身上脱落出来,并与之共同亲密地生活,这个世界上再没有这样一个人一心一意地对她,成为她最大的精神支柱。正因为如此,对于送别母亲这件事,她拒绝接受,也第一次意识到,哪怕凭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一切,却唯独改变不了母亲离世的命运。
在作者的笔下,她始终是孤独的,她认为一直只有她自己才能照顾母亲,而先生、小阿姨等人都无法依靠。母亲只有她,她只有母亲。而当人失去那个自己最珍贵的、唯一的爱人时,她的世界便毁灭了。毁灭之后,会重生出一个新的自我,而那个没有母亲的“我”,已经是另一个生命。
如果不是张洁与母亲的关系如此亲密又唯一,是没有办法写出这样细腻、琐碎又纠缠的作品的。如果读者没有过同样亲密关系的经历,也恐怕无法理解张洁在文中那显得有些扭曲的过于强烈的感情。可是,若读者曾与张洁一样,与至亲之人告别过,便无不被她文中的描述所深深打动,以至于泣不成声,无法继续。
母亲,永远是一个伟大的名词,也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最初的连接。从生到死,生命在不断轮回着,而我们只是命运链条上的小小一环。母亲辞世后,“我亲吻着妈的脸颊,脸颊上有新鲜植物的清新。那面颊上的温暖、弹性仍然和我自小所熟悉、所亲吻的一样”。
再也没有人可以像母亲那样低低地呼唤她一声“小洁”,那个曾与她相依为命的人,就这样去了。日后,所有均已是回忆,有未能实现母亲愿想的悔恨,有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也有在那漫长和短暂的54年里,母亲所给予的无尽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