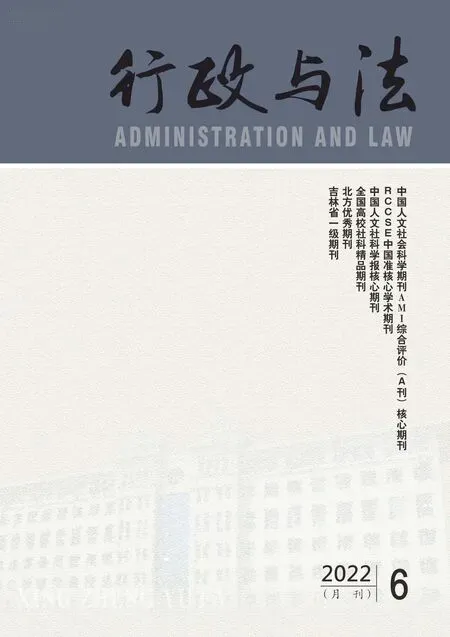环境犯罪的积极预防性刑法规制
2022-06-25周峨春
摘 要:《刑法修正案(十一)》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修订呈现出从事后制裁到积极预防的立法转向,具体表现为扩大犯罪圈并增设新罪名,干预时间前移化,从严从重处罚严重破坏环境行为。这一立法转向立足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新形势,着眼于防范环境风险和维护安全秩序的新需求,强化对集体性环境利益的保护,体现了环境治理法律体系的内在统一。预防性规制在环境风险防范方面具有正当性和实效性,但也存在适用不周延的情况,具有不确定性和应急性的特点。因此,应从回归法益保护立场、坚守罪责原则立场、奉行司法克制立场出发,对积极预防性规制进行必要的限制。
关 键 词:刑法修正案(十一);环境犯罪;积极预防;法益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22)06-0109-10
收稿日期:2021-12-07
作者简介:周峨春,青岛大学法学院,刑事法教研室主任,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刑法学、环境法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一般項目“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刑民衔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CFXJ05。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1997年第一次修订以来,环境犯罪一直是刑法重点关注的领域,2001年8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二)》、2002年12月28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四)》、2011年5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都涉及对环境犯罪的修改完善。综观历次刑法修订,环境犯罪规制呈现出从事后制裁到积极预防的立法转向,传统刑法理论蕴含的谦抑原则、法益侵害原则、消极刑法立法观被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早期化治理、风险防控原则、积极预防性刑法观。应当说,环境犯罪立法的逐步完善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
一、积极预防性刑法观在环境犯罪规制中的展开
现代社会,“人为风险超过自然风险成为风险结构中的主导内容”,[1]风险识别和防控难度的增加使得安全秩序逐渐成为公众的首要议题,防控风险和维护安全秩序成为刑法的重要任务,[2]积极预防性刑法观应运而生。《刑法修正案(十一)》顺应环境风险防控的需求,对涉及环境犯罪法律条文进行了修订,充分体现出积极预防性的刑法观。积极预防性刑法观以预防和早期化治理为核心要义,重在风险防控,以先发制人的方式防止安全秩序遭到破坏,与消极刑法观以事后惩罚为要义截然不同。
(一)扩大环境犯罪的犯罪圈
自1997年《刑法》专章专节设置“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以来,只有在2002年《刑法修正案(四》中增加了1个罪名,即“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罪”。直到《刑法修正案(十一》颁布,近20年来首次扩大环境犯罪的犯罪圈,增设了3个罪名。
⒈增设“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我国对野生动物一直实行分类保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只保护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由于对普通陆生野生动物并未予以保护,食用陆生野生动物产业催生了野生动物交易市场,增加了病毒从自然界传播给人类的风险。2020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出台决定,全面禁止食用陆生野生动物,包括普通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全面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防范病毒传播。为了切断食用陆生野生动物的供应链,《刑法修正案(十一)》专门增设“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规制以食用为目的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除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以外的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的行为。该罪的构成要件主要表现为:目的的特定性,即以食用为目的,不包括科学研究、饲养繁殖等目的;对象的特定性,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以外的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不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行为方式的特定性,即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等行为。
⒉增设“破坏自然保护地罪”。自然保护区是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载体。我国已建立自然保护区2700多个,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4.8%,[3]保护了85%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4]近年来,破坏自然保护区的行为频发,严重破坏了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在《刑法修正案(十一)》颁布之前,对于自然保护区的侵害行为只能以“污染环境罪”“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非法采矿罪”“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等相关罪名予以规制,例如甘肃省白某某、史某某非法采矿案[甘肃省祁连山林区法院(2019)甘7502刑初2号刑事判决书]中,白某某、史某某擅自进入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非法开采萤石矿80余吨,法院以非法采矿罪分别判处白某某、史某某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和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但对于在自然保护区内违法进行开垦、开发活动或者修建建筑物的行为,如若没有造成环境污染、杀害珍贵野生动物、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等情形,便无法予以规制。为了填补这一刑法空白,《刑法修正案(十一)》专门设置了“破坏自然保护地罪”,即“违反自然保护地管理法规,在国家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开垦、开发活动或者修建建筑物,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该罪在客观方面主要表现为:空间范围的特定性,即仅限于在国家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行为方式的特定性,即仅限于进行开垦、开发活动或者修建建筑物活动。[5]
⒊增设“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外来物种从原栖息地进入本土繁殖、传播,威胁到本土物种的生存,破坏本土生态系统,是生态安全的重大隐患。外来物种广泛分布于湖泊、河流、森林、草原、农田、湿地等生态系统,已成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退化的重要因素,2020年10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以下简称《生物安全法》)把“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作为重要内容,在第六十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而且在第八十一条至八十三条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刑法修正案(十一)》衔接《生物安全法》,专门设置“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即“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入侵物种,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这是刑法对于外来物种入侵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退化等紧迫问题的及时回应,体现了刑法保障生物安全、生态安全的积极姿态。该罪在客观方面主要表现为:行为的违法性,即违反《生物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行为方式的限定性,即非法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入侵物种,且情节严重。
(二)设置环境犯罪行为犯
自1997年《刑法》专章专节设置“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以来,立法机关多次调整入罪标准,完善环境犯罪罪名体系,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不断对环境犯罪入罪标准进行明确和细化。从整体来看,刑法对环境犯罪入罪门槛的调整呈降低趋势,干预时间呈前移化趋势。《刑法修正案(十一)》颁布之前,环境犯罪的类型主要表现为实害犯和危险犯两种形态。按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规定,“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才构成犯罪,按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二款“破坏性采矿罪”的规定,“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才构成犯罪,两款罪名都把造成严重后果作为犯罪的成立要件,属于实害犯;按照《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条第一款“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规定,“将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的”即构成犯罪,“倾倒、堆放、处置”行为并不要求造成实质损害,而是对环境法益的一种风险,因此“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属于危险犯。《刑法修正案(十一)》将环境犯罪的类型由实害犯和危险犯[6]扩展为实害犯、危险犯、行为犯三种。行为犯与实害犯、危险犯相比,只要求有危害行为而不要求造成危害结果。一个罪名属于何种类型的犯罪,取决于对犯罪侵害法益的理解。[7]将“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设置为行为犯,其侵害的法益是生态安全,不同于一般的环境要素一旦造成损害后果是严重和深远的,因此需要刑法的前置化保护。再者,外来物种入侵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复杂和长期的过程,一般可以分为引入阶段、定殖与建群阶段、扩散与危害阶段,[8]其危害往往在入境后很长时间才显现出来,所以《刑法修正案(十一)》前置对“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的干预起点,对入境行为和入境后的处置行为进行控制,即发生“非法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的行为就构成犯罪,体现了刑法干预的预防化与早期化。
(三)从严从重处罚环境犯罪行为
⒈增加“污染环境罪”的量刑档次。《刑法修正案(八)》將“污染环境罪”的罪状设定为基本犯和结果加重犯两类,即“严重污染环境的”和“后果特别严重的”两种情形,分别对应着“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和“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两档刑罚。由于《刑法修正案(八)》对于“污染环境罪”罪状的规定过于模糊,刑罚的规定过于轻缓,给司法适用带来了诸多困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的形式细化了“严重污染环境的”和“后果特别严重的”内容,解决了罪状模糊不清的问题,但刑罚轻缓的问题司法机关囿于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对于特别严重的污染环境行为也只能适用最高七年有期徒刑的刑罚,无法实现“罪责相当”的平衡。《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污染环境罪”的罪状设定为基本犯、情节加重犯、情节加重犯和结果加重犯混合的三类,即“严重污染环境的”“情节严重的”和“情形特别严重的”三种情形,分别对应着“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和“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详细列明了“情形特别严重的”四种情形,实现了罪状的明确化,有效解决了罪责不相适应的问题。
⒉明确法条竞合情况下的择一重处罚。在“污染环境罪”与“破坏自然保护地罪”中均明确了这一原则,“污染环境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发生竞合时,例如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排放、倾倒有毒物质,可能构成“污染环境罪”,也可能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投放危险物质罪”刑罚严厉(最高刑罚为死刑)且刑事责任年龄更低(14至16周岁即可构成)、可以限制减刑(投放危险物质被判处死缓的,法院可以对其限制减刑)、严重的不得假释(投放危险物质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不得假释);“污染环境罪”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发生竞合时,例如污染环境致使永久基本农田功能丧失或者永久性破坏的,可能构成“污染环境罪”,也可能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二者之间“污染环境罪”的处罚更重。“破坏自然保护地罪”与“污染环境罪”“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非法采矿罪”“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等罪名发生竞合时,需择一重罪进行处罚,体现了立法机关从严从重惩治环境犯罪的立场和力度。《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础上,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我国刑事立法总体轻刑化的趋势下,对严重破坏环境的犯罪行为从严从重处罚,体现了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二、积极预防性刑法观在环境犯罪规制中展开的正当性
(一)集体法益保护的理性选择
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分为个人法益和集体法益。集体法益又称为超个人法益,是指一切社会成员均可以享有和利用的法益,不能将某一部分分配给社会中的部分成员,[9]具有广泛性、不可分性、非排他性的特点。集体法益相较于个人法益更加重要,是个人法益的集合体,加之风险社会理论对集体法益重要性的凸显,各国的刑事立法都加强了对集体法益的保护。集体法益的价值是维护秩序,个人法益的价值在于保护个人自由,二者之间不仅仅是形式和量的区别。法益性质的不同决定了保护手段的不同,以保护人身法益和财产法益为中心的传统刑法,对于犯罪的认定和处罚更加注重实害结果,即只有在实害结果出现时才启动刑法。[10]而集体法益具有广泛性和不可分割性,一旦造成实害结果则影响重大。而且,对于集体法益的侵害虽然并不直接侵害具体的个人法益,但是对于集体法益的损害后果最终会危及具体的个人法益。因此刑法在出现行为或抽象危险时应提前介入,不必等到个人法益受到侵害或者具体的危险结果发生,将集体法益作为个人法益保护的前阶,以实现对集体法益的前置性保护,这就是法益保护的前置化。[11]以环境犯罪中的“污染环境罪”为例,《刑法修正案(八)》修订之前的“污染环境罪”将“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危害结果作为犯罪成立的要件,体现了以个人法益为中心的保护原则,《刑法修正案(八)》将其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的”,围绕着集体法益构建犯罪构成,犯罪构成由个人法益保护向集体法益保护设定的转向,直接关系到刑法手段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刑法修正案(十一)》也将集体法益作为保护重点,新增18个罪名中有17个罪名涉及集体法益保护,包括公共安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等,其中环境刑法所保护的集体法益从章节设置来看,概况的集体法益是社会管理秩序,而具体性的集体法益则是环境利益,它是环境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环境需要的满足,不是部分人的私利,而是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12]除前置化保护外,《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于环境刑法的修订还运用了扩大处罚范围、加重处罚力度等保护集体法益的必要手段,背后蕴含的价值目标即对环境风险的防范和对环境利益的保护。从整体来看,集体法益的保护是为了避免社会的混乱,而不是为了对具体的侵害行为实施制裁,在突出集体法益的同时,实际上是弱化了对个体法益的保护,[13]个体法益的损害不是犯罪成立的要件,只能成为犯罪成立后量刑的依据。例如,自《刑法修正案(八)》修订后,《刑法修正案(十一)》重新将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纳入《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污染环境罪”的规定中,但由犯罪成立要件变为加重处罚的情节。
(二)环境治理法律体系的内在统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列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强调“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健全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环境治理现代化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选择,同时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直接检验。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必须摒弃传统环境治理理念和方法,注重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预防、从局部治理转向全过程控制。2020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为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构建了七大体系,其中符合环境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法律体系是环境治理现代化实现的重要保障。
综观现有的环境治理法律体系,源头预防和全过程控制已成为环境法和民法的基本原则:201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条关于环境保护基本原则的规定,明确提出了“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环境治理原则,为源头预防和全过程控制提供了立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九条提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源头预防和全过程控制由“绿色原则”的具体化实现了在《民法典》中的价值渗入。绿色化已成为环境治理法律体系的趋势,环境法作为环境治理基本法和环境刑法的前置法天然具有绿色化属性,民法为了发挥环境治理的功能也趋向绿色化。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刑法的绿色化也成为必然。刑法实现绿色化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事前的源头预防,一种是事后的末端修复。在末端治理的各种措施中,环境修复是目前最符合环境犯罪特点的处理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已广泛应用。在理论界,有学者依据罪刑法定原则探讨将其纳入刑法规范,作为刑法明确规定的责任形式。[14]相较于末端治理的环境修复,源头的事前预防则是环境犯罪治理的更优手段。其中,积极预防性刑法观的预防与刑罚的预防在功能上存在本质区别,前者的预防通过前置干预时间、加重处罚力度等方式防止损害发生,后者的预防则是在损害发生后,通过对犯罪的惩罚而防止犯罪再次发生,因此,属于源头预防的“防止发生”相较于属于末端惩罚后客观效果的“防止再次发生”更有助于环境的保护,将环境损害遏制在萌芽阶段,符合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三)维护安全秩序的现实需要
当今社会风险无处不在,严重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安全,引发了人类对安全秩序的担忧,安全在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自由、平等、安全)序列里被赋予更多的关注,[15]成为追求其他价值的前提条件。传统刑法的价值选择与功能设定正发生深刻变化进而转向安全刑法,风险成为刑法理论重构与刑法规范调整的直接诱因,保护风险社会下的安全秩序成为刑法的基本任务,更加凸显刑法的工具属性,在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重大法益的保护时,刑法不能只作为“最后手段”发挥惩罚的功能,还应该发挥“先手”的预防作用。[16]
《刑法修正案(十一)》关于环境犯罪法条的调整体现了基于维护安全秩序的考量。首先,基于保护生态安全的考量。20世纪中期以来,生态问题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存而被广泛关注,并逐渐上升为安全问题。从微观层面来看,生态安全是人的健康及生命活动不受生态危险威胁的状态,[17]从宏观层面来看,生态安全是一个国家不受生态环境和资源制约与威胁的稳定状态。在保证生态安全的前提下,才能解决人类的生存威胁问题和国家的持续发展问题。各种环境侵害行为中,环境污染作为危及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造成的生态恶化屡见不鲜,有重要生态功能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以及重要的河流、湖泊遭受的环境污染愈发严重,而原有的刑罚设置较为轻缓,无法匹配污染行为的危害性。《刑法修正案(十一)》针对此种问题提高了刑罚幅度,增加了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处罚措施。同时《刑法修正案(十一)》还专门增设了“破坏自然保护地罪”,我国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保护动植物种群、湿地以及自然遗迹等自然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功能的特殊性决定了必须对其进行特殊保护。其次,基于保护生物安全的考量。生物安全是生物有关因素对人体健康、生态环境以及社会、经济所产生的危害或威胁状态。[18]当前,生物安全问题已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新冠疫情的暴发及蔓延暴露出各国对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种种不足,将人类推入“生物安全风险最严重的时代”。[19]《刑法修正案(十一)》针对生物安全风险防范问题,在环境刑法中特别增设了两个罪名,一个是“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一个是“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以防止生物流动与传播带来的安全风险。最后,基于保护国家安全的考量。在和平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代替国与国的关系,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20]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生物安全之于国家安全的作用更加明显,加强生物安全的治理和保障,不仅关系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践行,也是应对当前非传统安全领域重大风险的迫切需要。[21]
三、积极预防性刑法观在环境犯罪规制中的限制
作為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环境刑法的修订必须基于环境治理现代化的立场,回应人们对生态安全、生物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诉求。面对层出不穷的环境问题,扩大规制范围、提前介入的时间、增加处罚力度已经成为环境刑法修订的常态化内容。常态化的积极干预有助于实现常态化的安全秩序,但同时也会引起人们对于刑法过度干预化、处罚界限模糊化的担心。积极预防性刑法规制符合环境治理现代化的需求,在环境风险防范方面具有种种优势和合理性,但同时也具有不确定性和应急性。因此,对环境犯罪规制中的积极预防性刑法观进行必要的限制尤为重要。
(一)回归法益保护立场
法益是刑法保护的国家、社会和公民的核心利益,它是刑法存在的根基和规制的边界,即法益确立的标准和保护的规则决定着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限度。[22]保护法益是刑法的根本任务,法益遭受侵害是刑法介入社会生活的依据。积极预防性刑法负有防控社会风险、维护安全秩序的责任,以干预早期化、扩大规制范围、增加处罚力度作为基本方式,而这三种方式却不断冲击犯罪边界和处罚边界。在积极预防性刑法的规制下,犯罪边界和处罚边界呈现逐步扩张的趋势——安全秩序遭受威胁→为保障安全扩张刑法边界→新的安全威胁出现→再次扩张刑法边界……[23]随着刑法边界的扩张,法益的制约功能也逐渐弱化。法益的制约作用在设定犯罪和刑罚的阶段最为明显,如果在此阶段偏离法益设定犯罪和刑罚完毕,便贴上了规范的标签,违反规范的行为便构成犯罪并应受刑罚处罚——这便形成了与“法益论”相对应的“规范论”。与“法益论”以法益侵害作为构成犯罪的依据不同,“规范论”对于犯罪的界定不以法益侵害为中心,而是根据是否违反规范来判断是否构成犯罪。“规范论”实际上是刑事违法性的概括,正如刑事违法性只是犯罪的形式特征一样,“规范论”对于犯罪的界定也只驻足于形式,其偏离法益界定的犯罪往往没有实质社会危害性,这不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不可否认“规范论”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安全秩序,但其可能将没有实质危险的行为纳入犯罪进行处罚,造成刑法的过度干预或不当干预。而“法益论”以法益遭受侵害或危险作为刑法介入的依据,要求被惩治行为所造成的危险必须具有向实际危害结果转化的现实可能性,避免刑法的过度干预或不当干预。法益理论原本就是为了防止国家刑罚权恣意化而创设的,且实践已经证明法益保护是限制国家刑罚权最有效的方式,回归法益保护的立场,以法益为中心确立犯罪和刑罚,可以避免或纠正积极预防性刑法在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偏差。[24]
环境安全秩序恰是刑法所要保护的法益,法益保护的立场有助于识别需要保护的环境安全秩序,而偏离法益的识别,往往发现的是对于环境安全秩序的心理感受,即环境安全感。积极预防性刑法把环境安全感作为刑法保护的法益还有待商榷。环境安全秩序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状态,相对确定并可估量,而环境安全感是主观心理状态,往往由主观臆测或猜想形成,具有不确定性并无法具体估量。随着认识提高和时空转移而发生变化,在对环境安全感进行保护时会陷入无从着手的困境,即我们以何种标准来确定主观感受以及是否得到保护,环境安全感的高度抽象性,难以显现为生命、自由、健康、财产等实体性法益,不具有形式上的具体可能性。[25]以对环境安全秩序的主观心理感受作为刑法规范产生的依据,其合法性和正当性存在诸多问题。法益保护的立场为环境安全秩序的范围设定了限制性门槛,防止将不明确的环境安全感纳入刑法的保护对象。
(二)坚守罪责原则立场
罪责原则也称“非难可能性”,是刑法的基本原则,认为行为人应该为危害社会的行为受到非难或谴责。罪责原则确立初衷是为了限制刑法预防功能的滥用,限制国家刑罚权,被视为刑罚正当化的必要条件,[26]要求发挥预防功能必须以罪责相适用为限度,罪责是刑罚的基础,刑罚必须与罪责相符。积极预防性刑法为了保护集体法益,防止社会风险转化为现实危害,把对危险行为的规制从“非难可能性”转换为“预防必要性”,这一转换符合风险社会下维护安全秩序的内在需求,但风险预防的实现不能违背罪责相当这一基本原则,否则就会造成刑罚失当。因此,只有坚守罪责原则对预防必要性的制约才能保证积极预防性刑法的正当性,[27]罪责原则是预防机能的上限,[28]不可逾越。
罪责原则对于积极预防性刑法观在环境犯罪规制中的限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罪名设置。首先是环境侵害行为“质”的衡量。积极预防性刑法以防范风险为价值考量,风险行为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并不都具有现实危险性,刑法不能把所有造成风险的行为都规定为犯罪,而应将“风险行为”与“危险行为”区分开。“风险行为”具有侵害环境法益可能性,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可能性极低不能转化成现实危险。而“危险行为”具有侵害环境法益的确定性,只是侵害结果未现实发生。比如,行为人非法丢弃外来入侵物种,虽然没有造成破坏生态系统和物种多样性的侵害结果,但威胁到丢弃地物种的生存。“风险行为”是可容许的且不应该受到责难,而“危险行为”是不可容许的且应该受到责难。即便如此,并不意味着要将所有“危险行为”规定为犯罪,“只有对那些离发生实害距离很近并且发生实害的概率较高的危险行为,才能实行犯罪化。”[29]其次是环境侵害行为“量”的衡量。并不是所有“危险行为”都应该受到责难,应该有“量”的要求,积极预防性刑法的目的和功能是为了预防严重的“危险行为”转化成现实的重大危害,只有严重的“危险行为”才应该受到责难,而不是预防一般的“危险行为”,一般的“危险行为”不属于积极预防性刑法规制范畴。二是刑罚设置。相较于造成环境实际损害的行为,环境“危险行为”的违法性程度要低,根据罪责衡平原则,对于环境“危险行为”刑罚的设置,应采取入罪轻刑化、刑罚宽幅化的方式,即对于一般的环境“危险行为”设置轻缓的刑罚,而对于情节严重的行为设置较重的刑罚,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行为设置更为严厉的刑罚。如此设置既能发挥环境刑法的积极预防功能,又符合罪责原则要求。罪责原则和积极预防性刑法并不矛盾,在风险社会的条件下坚持罪责原则,应该对罪刑设置的传统观念进行适当调适,“改变犯罪一定是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的行为的观念”,[30]而根据风险防范的需要增设轻罪,并设置宽严相济的刑罚,保持对风险行为正当的积极干预。
(三)奉行司法克制立场
刑法在社会治理方面经历了从“危险防御”到“风险预防”的转变,[31]其自身正发生着从保障法到防卫法的转变,逐渐成为社会防卫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预防危险、追求安全和助力社会控制成为优先的价值选择,刑法与警察法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不清。”[32]《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破坏自然保护地罪”和“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既发挥了刑法社会防卫功能,同时还带有应急性特征。积极预防性刑法本身就是对传统规制手段的超越,再叠加应急性的特征,容易造成积极预防性规制手段的滥用,除了在立法阶段坚守法益保护和坚守罪责原则的立场两方面予以限制外,还应在司法阶段奉行克制立场。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入刑,体现了司法克制立场对积极预防性刑法的限制和补足,其在防范交通风险方面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展现出积极预防性刑法的积极作用,但粗放的“一刀切”式的执行方式造成了“醉驾”入刑过度适用,不但挤占了公民自由权益的空间,还造成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33]直到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量刑指导意见,规定“醉驾”入刑应综合考虑被告人的醉酒程度、车辆行驶道路、行车速度等情况,各地法院根据指导意见区分不同情况定罪量刑,限制了“醉驾”入刑的滥用。
司法克制立场可以有效化解积极预防性刑法扩张带来的危险,其对于环境犯罪规制的限制应体现在定罪和处罚两个方面。一是定罪。环境刑法对于环境犯罪的规制采用的是“立法定性+定量”,即在法益侵害性基础上以情节要素作为衡量是否构成犯罪的条件,如“污染环境罪”规定的“严重污染环境的”“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规定的“情节严重的”以及新增的“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非法引进、釋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对“情节严重”的规定,都是通过情节要素体现行为的可罚性,即使个别罪名没有规定情节要素,根据《刑法》第十三条“但书”条款规定,也应进行情节要素衡量。在司法过程中,司法者应严格遵循“立法定性+定量”的定罪要求对环境侵害行为进行衡量,首先进行法益侵害性的定性分析,即是否具有造成严重危害重大风险,其次是情节的定量分析,即是否达到了严重的程度。在进行定量分析时,应区分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界限,通过第十三条“但书”条款的实质解释,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二是处罚。与风险行为犯罪化相匹配的应是处罚的轻缓化。谦抑性原则是刑法始终如一的本色,即使在风险社会下亦应保持。积极预防性刑法观通过立法扩张不断突破谦抑性原则的界限,降低了环境犯罪的入罪门槛,所以需要在司法处罚方面采取轻缓化处理方式,以限制立法扩张对谦抑性原则的突破,谦抑性原则在风险社会下的实现在于立法扩张与司法克制的并行不悖和张弛有度。[34]在处罚轻缓化的实现方面,司法者应灵活适用认罪认罚从宽、不起诉、定罪免刑或缓刑制度。[35]
【参考文献】
[1]劳东燕.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J].中国社会科学,2007,(3):126-139.
[2]高铭暄,孙道萃.预防性刑法观及其教义学思考[J].中国法学,2018,(1):166-189.
[3]高吉喜,徐梦佳,邹长新.中国自然保护地70年发展历程与成效[J].中国环境管理,2019,(4):25-29.
[4]王昌海.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与发展研究进展与展望[J].林业经济,2019,(10):3-9.
[5]别涛.惩治环境犯罪的新利器——刑法修正案(十一)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分析[J].环境经济,2021,(2):13-19.
[6]付立庆.中国《刑法》中的环境犯罪:梳理、评价与展望[J].法学杂志,2018,(4):54-62.
[7]张明楷.污染环境罪的争议问题[J].法学评论,2018,(2):1-19.
[8]石雯.关于外来生物入侵法律控制之我见[J].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2006,(3):244-247.
[9]刘艳红.积极预防性刑法观的中国实践发展——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的分析[J].比较法研究,2021(1):62-75.
[10]孙国祥.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及其边界[J].法学研究,2018,(6):37-52.
[11]王永茜.论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J].环球法律评论,2013,(4):67-80.
[12]周峨春,孙鹏义.环境犯罪立法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45-46.
[13]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刘国良.安全刑法:风险社会的刑法危险[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3):38-41.
[14]杨红梅.生态环境修复中刑法正当性适用问题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130-139.
[15]魏汉涛.风险社会背景下环境刑法变革要提防两种倾向[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57-63.
[16]李梁.环境犯罪刑法治理早期化之理论与实践[J].法学杂志,2017,(12):133-140.
[17]王树义.生态安全及其立法问题探讨[J].法学评论,2006,(3):123-129.
[18]梅传强,盛浩.论生物安全的刑法保护——兼论《刑法修正案(十一)》相关条文的完善[J].河南社会科学,2021,(1):24-34.
[19]姜涛.生物刑法的保护法益与发展路向[J].河南社会科学,2021,(1):11-23.
[20]王江丽.安全化:生态问题如何成为一个安全问题[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36-47.
[21]司林波.国家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建设:从理论到实践[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20):75-89.
[22]田宏杰.刑法法益:现代刑法的正当根基和规制边界[J].法商研究,2020,(6):75-88.
[23]胡霞.国家安全视阈下刑法的预防性路径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7,(5):30-48.
[24]房慧颖.预防刑法的天然偏差与公共法益还原考察的化解方式[J].政治与法律,2020,(9):101-109.
[25]冯文杰.法益抽象化、精神化问题的中国型塑[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148-155.
[26]张晶,舒洪水.预防罪责理论介评——以德国刑法学说为主线的展开[J].河北法学,2012,(11):36-42.
[27]冀莹.“英国预防性刑事司法”评介与启示——现代刑法安全保障诉求的高涨与规制[J].政治与法律,2014,(9):115-124.
[28]王鈺.罪责原则和客观处罚条件[J].浙江社会科学,2016,(11):48-57.
[29]张明楷.“风险社会”若干刑法理论问题反思[J].法商研究,2011,(5):83-94.
[30]周光权.积极刑法立法观在中国的确立[J].法学研究,2016,(4):23-40.
[31]陈海嵩.环境风险预防的国家任务及其司法控制[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15-25.
[32]何荣功.预防刑法的扩张及其限度[J].法学研究,2017,(4):138-154.
[33]解志勇,雷雨薇.基于“醉驾刑”的“行政罚”之正当性反思与重构[J].比较法研究,2020,(6):54-75.
[34]田宏杰.立法扩张与司法限缩:刑法谦抑性的展开[J].中国法学,2020,(1):166-183.
[35]周光权.积极刑法立法观在中国的确立[J].法学研究,2016,(4):23-40.
Active Preventive Regulation of Environmental Crime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Amendment Ⅺ to the Criminal Law
Zhou E’chun
Abstract:The amendment of the Amendment Ⅺ to the Criminal Law to environmental crimes presents a legislative shift from post-sanctions to active prevention,which is embodied in:adding crimes to further expand the crime circle,the time of intervention is moving forward,and severe punishments Serious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This legislative shift is based on the new situation of my country'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focusing on the needs of preventing environmental risks and maintaining safety and order,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of collective environmental interests,and reflecting the inherent unity of th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legal system. Active preventive regulation has legitimacy and effectiveness in environmental risk prevention,but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ncertainty and contingency,which can easily lead to incomplete application.Therefore,necessary restrictions should be imposed on active preventive regulation,mainly including the position of returning to the protection of legal interests,the position of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guilt,and the position of pursuing judicial restraint.
Key words:amendment Ⅺ to the criminal law;environmental crime;active prevention;legal interest prot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