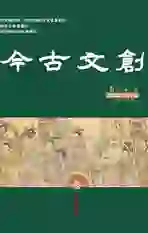鲁迅与契诃夫作品中“小人物” 形象的对比分析
2022-06-24杨岚
杨岚
【摘要】 鲁迅与契诃夫都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他们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讥讽的笔调反映了封建腐朽的社会制度和复杂的社会矛盾对“小人物”生存空间的打压,从而揭露了社会的丑恶、人性的复杂和冷漠。他们都对民族生存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同时主张以社会变革来换取底层人民的幸福。本文通过对短篇小说《祝福》和《苦恼》的对比分析,探索他们笔下“小人物”的形象和命运。
【关键词】 小人物;主题思想;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22-004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22.013
“小人物”指处于社会底层,被歧视压迫的人们。最早开创“小人物”主题的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果戈里也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对于“小人物”命运的关怀和同情,契诃夫又在前人的创作基础上赋予了“小人物”新的内涵。他的小说以紧凑精练、言简意赅为特点,与法国作家莫泊桑和美国作家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正因为契诃夫来自社会底层,明白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所以他同情人民,始终坚持民主主义的立场。契诃夫使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注重描写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塑造出了众多典型的小人物形象,如《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教师“别里科夫”、《文学教师》中的主人公“尼基丁”、《苦恼》中的车夫“姚纳”等等。鲁迅的创作深受契诃夫的影响,郭沫若曾说过:“鲁迅的作品与契诃夫的极相似,简直可以说是孪生兄弟。假使契诃夫的作品是人类无声的悲哀的音乐,鲁迅的作品至少可以说是中国的无声的悲哀的音乐”。[1]鲁迅通过作品中塑造的典型人物对国民性的弱点进行无情地批判和揭露,力求树立文化自信,达到“立人”的目的。他笔下的“小人物”大多命途多舛、愚昧懦弱。如《祝福》中的长工“祥林嫂”、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孔乙己”、《阿Q正传》中的主人公“阿Q”等等。本文则主要通过对短篇小说《祝福》和《苦恼》的对比分析,探索他们笔下“小人物”形象和命运的相似性。
一、故事情节的相似性
(一)主人公悲惨命运的相似性——丧子丧偶
《苦恼》是契诃夫短篇小说之一,曾被托尔斯泰列为其著作中的“第一流作品”。故事情节通过一个身份地位极低,甚至拉一天车也买不起一包燕麦的“车夫”展开,老车夫姚纳不仅生活困苦,遭遇更加不幸。在他的妻子早早离世的情况下,儿子也不幸追随他的母亲离去,他的内心忍受着沉重的哀痛,想与人倾诉他所遭遇的不幸,来缓解心中的苦闷。于是他不断向他的客人提及他不幸离去的儿子,然而等待他的不是无视就是侮辱。在偌大的彼得堡,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他居然找不到一个愿意驻足来耐心听他讲述完悲惨故事的人。最终,万般无奈下,他对着相依为命的小母马诉苦吐怨。
《祝福》是鲁迅创作的短篇小说。“我真傻,真的”这一话语在小说中出现了四次,表达了她内心深深的自責,这也便是她讲述儿子去世的开场白,刚开始讲述时,大家都觉得很新奇,有的人也会被这个悲惨的故事所打动,甚至难过到流泪。然而,随着祥林嫂讲述的次数越来越多,人们不仅不再安慰她,反而觉得很无趣不想再听了。而祥林嫂很受挫,她知道人们不再同情可怜她,所有的苦痛只能自己一个人忍受。回想一生,她觉得自己的命不好,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离去,似乎都与自己有着密切的关系。小说中有写到祥林嫂通过“捐门槛”赎罪的片段,处于一个封建落后的旧社会,她不知自己的最终归向,世人的看法让她成为了一个罪人。祥林嫂原以为捐完门槛后,鲁镇的人不会说她是一个晦气的女人,就算有鬼神一说,那她也自然可以坦然面对。在冬至的祭祖活动中,她坦然地去准备祭祀用品,却被四婶慌忙喊住:“你放着罢,祥林嫂!”“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2]从这时起,祥林嫂已彻底绝望,慢慢走向死亡。
(二)寻找倾诉对象,诉丧子之痛——惯用语的相似性
两人每次和人诉说时所用的语言几乎一样:姚纳反复地说“我的儿子死了”,祥林嫂则以“我真傻,真的”开始她的讲述。有人把这视为情节反复,提出祥林嫂以同样的话语诉说阿毛的悲惨故事,听者鉴赏的态度与说者深重的痛苦形成了对照,加深了作品的寒冽程度。[3]这类“小人物”的存在丝毫不被世人重视,他们的存亡如同自然界的一根杂草生灭一般。阶级意识影响了人们看待人的眼光,也阻碍了心与心的交流沟通,冷漠的社会让人变得自私麻木,“姚纳”和“祥林嫂”让我们看到了社会中的底层人物在遇到重重打击,想要寻找帮助时,世人的冷漠嘴脸。《苦恼》中的姚纳和《祝福》中的祥林嫂他们都愿意将自己最悲痛的事情讲给人们听,无奈没有人真正的同情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漠视,支撑他们继续生活下去的力量也变得微弱。通过对姚纳找寻到的四个倾诉对象的描写,可以发现这四位倾听者的地位和身份越来越低,从军官到浪荡的青年,再从扫地的仆人到他的同行——住在一个房间的年轻车夫。姚纳四次找人倾诉,四次均以碰壁告终。“我的……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4]这样的表述在小说中出现了三次,每次小心翼翼地跟人提起自己儿子去世的事,语气里不仅带着伤感、无奈,还有想要他人听他诉说的期待。文中这样描述道,一听别人接上他的话,脸上立马洋溢起笑容,就连身子也转向后面给人家讲述。这部分的细节描写突显了姚纳对于倾诉对象的渴求,对于一个生存境况差的老车夫来说,他追求的并不是要多拉客人来满足自己衣食住行的需求,而是想要寻找一个能听他讲述故事的人。然而,无一例外,大家都选择无视姚纳,拒绝与之沟通。不仅上流阶层漠视姚纳的存在,不接纳他,就连同一阶层,相同身份的人也排斥着姚纳。当时的俄国社会缺乏温情,哪怕同一个阶层,人与人之间也像是不能融合的两个世界,每个人都困在了自己世界里,最终,姚纳也只能把自己内心的苦闷倾诉给听不懂人类话语的动物听,让人们对“小人物”的遭遇更加同情,也对底层人民的命运有了更为深刻的把握。EFABF40E-8C50-4958-97B0-8FA08EDDDC67
二、“小人物”的异化
哲学中通常把“异化”的概念表述为:“主体由于自身矛盾的发展而产生自己的对立面,产生客体,而这个客体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凌驾于主体之上,转过来束缚主体压制主体”。[5]社会的异化主要体现在国家制度将人们分成不同的等级,上流社会不仅歧视底层人民,还压榨剥削劳苦大众的劳动力,打压着底层人的生存空间。少数人统治着多数人,金钱、地位、阶层才是划分是否交往的考量标准。
(一)底层人物——人际关系的异化
《苦恼》中的姚纳作为一个在大都市彼得堡赶车的车夫,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不了丝毫影响。他的存在如蝼蚁一般被人漠视,在失去了妻子的情况下,儿子的离奇死亡是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种伤痛压抑在老车夫的心中,始终无法排解。他想找人倾诉,他的职业决定了他的倾诉对象多是他的顾客,可是顾客们只关心自己能不能快点到达目的地,不断地漠视老车夫的话语。军官的回复是“哦……他是害什么病死的”,在姚纳以为终于找到了倾诉对象时,军官却冷漠的催促他,“快点吧,赶你的车吧!”因为对于军官来说,车夫儿子的生与死与他没有任何利益冲突,所以他选择忽视。一个人的冷漠可能是由于个体决定的,但是一群人的冷漠就一定是社会大环境所影响的。当他回到大车店,想要和一个年轻的车夫讲述他的故事,车夫的表现是忽视他的话语,继续睡去。因为他只关心自己的生计问题,别的一概不管。在这种功利主义的人际关系下,人们已经丧失了人道主义关怀,拜金主义、金钱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冷漠、麻木、隔阂像是一堵无形的墙阻碍在人们心间。
《祝福》中的祥林嫂也是一个淳朴善良、安分守己的农村妇女。但无奈,接连失去了两任丈夫又失去了儿子,就连她自己也觉得她是一个“不祥”的人,也有人称祥林嫂是一个没有“春天”的女人。人们也可以从她身上看见强烈的反抗精神,比如在嫁第二任丈夫时的宁死不从,对于婆婆恶行的不屈服,但经过分析可以发现祥林嫂的反抗精神也是出于对封建礼教的维护和顺从。她无人倾诉心中的痛苦,她既改变不了别人的看法,又不能改变自己生活的现状,带着无可奈何的哀叹和对封建社会的失望走向她的末路。鲁镇上的每一个人对于祥林嫂的个体意识并不在意,鲁四老爷一家看中的是祥林嫂是否能成为一个质优价廉的劳动力,祥林嫂的婆婆将她视为工具,通过让她改嫁来换取高額的彩礼,鲁镇上的其他人更是把祥林嫂的故事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种种精神枷锁将祥林嫂逼上绝路,她别无选择,走上末路。然而,对于一个死者的尊重也没能在鲁镇体现,鲁四老爷认为祥林嫂死亡时间很晦气,更是破骂死去的祥林嫂是一个“谬种”。在底层世界,人与人的关系由利益作为参照物,甚至能带给笑料供其愉悦也能够维系一段虚假的关系。
(二)奴性思维——人格的异化
社会环境决定了“小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他们也依然可以反作用于环境。他们的“反抗精神”竟然也是对于封建统治的保护。《苦恼》题记“我向谁去诉说我的悲伤?”可知本文的主旨不在于“悲伤”二字,而是向谁诉说。小说的主题从同情底层人物转向描述底层人物不被理会的孤独意识。“姚纳”和“祥林嫂”在遭受重重打击后,他们先是通过倾诉给他人来缓解苦闷,在受到别人的漠视后,没有反思“感同身受”在那群人身上永远也得不到体现。慢慢地,他们接受了这个既定的结局,“祥林嫂”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她也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之人,通过“捐门槛”这个事件就可以感受到祥林嫂的无知和愚蠢。面对莫须有的罪名,从来不思考为什么要承受。与其说封建礼教和神权崇拜让祥林嫂成为一个悲剧,不如说她自己也不自觉维护着封建礼教。鲁迅对之所持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苦恼》里的老车夫也应该重拾生活的信心,不能把自己的存亡交在陌生人的口中。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可以对自己的环境做出改变,也可以对不平等的阶级意识奋起反抗,做一个有骨气的人。
更为可恨的地方在于姚纳受过被歧视的滋味,他竟然还歧视女性。他寻找的第五个倾诉对象是那群“婆娘们”,并称她们为“蠢货”。心中还暗喜那群人会因听到他的故事感动的号啕大哭。姚纳的心里也存在着强烈的等级意识,对他的客人十分尊重,对他们的称呼也很敬重。而“女性”在他的心中等同于“蠢货”,也是他寻找倾听对象中的另类人。可见,一个受社会毒害的人也正在毒害着他人。祥林嫂和姚纳最大的不同在于,姚纳的人格上存在明显的劣根性,他们都是失去儿子的父母,可是祥林嫂清楚儿子的死因,反复诉说着“我真傻,真的”是出于自责的抱怨,她认为儿子的离去是因为自己没有起到监管的责任,原因在于自己。而姚纳对于儿子的死因并不清楚,他的儿子在医院躺了三天就离世了,但是他并没有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反省,竟然认为孩子的离世是上天的旨意。如果说祥林嫂的反复提及是出于对儿子的忏悔,那么姚纳的诉说实际上是想让大家关心他失去妻子和儿子的处境,对孩子的死并没有一点忏悔之意。对比之下,鲁迅先生塑造的“祥林嫂”这一形象更具有典型性和悲剧性,姚纳这一形象在人格上就带有分裂色彩,处于底层却看不起底层人物,寻找倾诉对象的顺序也体现了身份地位的高低排序。所以,比起祥林嫂他的可怜显得更为可悲,可以说他的悲惨命运一部分也是由自己造成。
三、《苦恼》和《祝福》创作的社会背景及主题的
分析
(一)对封建礼教和阶级意识的批判
契诃夫将人与马进行对比衬托,暗示出社会下层人民生活状况和牲畜们无差,充分暴露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小说运用极为深刻的细节描写刻画人物,折射出处于大环境中人们的集体心态,揭示了社会的黑暗和人际关系的冷漠无情。19世纪80年代,俄国正处于沙皇统治下的黑暗时期,沙皇的专制制度使得当时社会中的人等级制度分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麻木冷漠,处于上流阶层的人不仅拥有着大量的物质财富还掌控着治理人民的权利。“金钱至上”的人生哲理在俄国人心中蔓延开来,而处于最底层如“姚纳”这一类人成为社会的牺牲品。贫富差距极大,使得这类人的生存空间更小了。契诃夫始终用着冷峻的目光叙述着底层人民的生活,冷静、客观地为人们还原当时俄国最真实的社会。EFABF40E-8C50-4958-97B0-8FA08EDDDC67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这样评价道:“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辛亥革命的爆发推翻了帝制政权,人民并没有迎来幸福的曙光。鲁迅娴熟地运用典型化的创作方法,采用了融现实与历史于一炉的手段,“杂取种种人”,创造典型形象,勾勒出沉默的国民的灵魂,从而使典型具有极大的艺术概括力量。鲁迅的《祝福》创作于20世纪20年代,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时期。政权被军阀官僚夺取,中国的广大底层人民依然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腐朽的封建礼教如同枷锁般禁锢着人民的思想,森严的等级观念對人们思想的限制,导致了祥林嫂的悲惨命运。
(二)对于人性的冷漠自私、麻木无情的揭露
“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其主题揭示了“小人物”心灵的隔阂问题,处于同等阶层的人也无法互相理解,“苦恼”不仅是车夫姚纳一个人经历的,更是笼罩在整个俄国社会中。人们都已经无法互相关心帮助,沟通对于人们来说似乎是多余的,都活成了单独的个体。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让人们感受到了一颗被冷漠而孤独痛苦的心灵在嘶吼。“奴化”思想蔓延在他们心中,文章中的主人公受制于社会的种种制度,可都无怨无悔的甘于忍受别人对他的控制和打压,面对别人的侮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已经失去了一个独立完整的人格,仍然想通过别人对他的安慰释怀心中的痛苦,已经丧失了拯救自己精神和灵魂的能力。《祝福》中的“祥林嫂”也只是被封建礼教残害的一个代表,通过描述祥林嫂去世后鲁镇人“祝福”的场景,人们继续迎接着祭祀活动带给他们的快乐,让祥林嫂的离去显得更加可悲,一个身份低微的人离去不过是一片树叶的掉落,惊动不了他们的心。鲁镇人热闹非凡的生活场景更加突显了人性的冷漠、无情,人际关系变成了一张张利益网,人与人的交往变得复杂、工于心计。
契诃夫和鲁迅两位作家通过现实主义的手法,折射出对于人性的失望和怀疑,都突出了小说中想要表现出的社会大众的“孤独意识”。《苦恼》和《祝福》在题材和艺术手法上有极为相似的部分,选取的都是以小人物为主体,以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为题材。鲁迅也曾表示,契诃夫是他顶喜欢的作者。[6]由此可知鲁迅先生的小说创作与契诃夫小说具有关联性,但鲁迅并没有简单地借鉴、模仿。他所塑造的祥林嫂这一中国旧社会农村妇女的悲剧形象比契诃夫笔下的车夫姚纳更具深刻性和典型性。他们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上创作出了带有本国文化色彩的作品,并且他们始终带着对于希望的探索,想要通过对于国民身上劣根性的批判,重塑国民精神。
参考文献:
[1]郭沫若.沫若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96-199.
[2]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刘研.契诃夫与中国现代文学[M].北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4]契诃夫.契诃夫短篇小说[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5]王若水.“异化”这个译名[J].学术界,2000,(03).
[6]徐阳.苦恼与祝福之比较[J].大众文艺(理论),2009,(07).EFABF40E-8C50-4958-97B0-8FA08EDDDC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