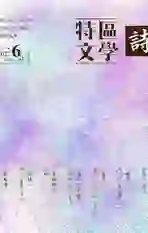《关系》
2022-06-23吉木狼格
只有在山里的夜晚
你才能感到
什么东西在慢慢逼近
什么东西又在慢慢远去
一些声音毫无由来地响起
又毫无由来地消失
如果你睡着了
你就是它的一部分
如果你醒着
并且在听和想
你就注定要和它作对
哪怕你很小,它很大
诗人简介:
吉木狼格,彝族,四川凉山人。1963年生。1981年开始诗歌写作,非非诗派成员,“第三代诗歌”代表诗人之一。著有诗集《静悄悄的左轮》《月光里的豹子》《天知道》《立场》等。2016年发起成立十诗人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并执导纪录片《诵魂》等,现居成都。
世 宾:醒和睡的对抗
它是谁?它是什么?是生生不灭的大自然?有可能,但我以及诗人都无法(至少诗人没有)说出它具体是什么。它其中的一部分是睡,“如果你睡着了/你就是它的一部分”。我们能知道的就是关于我们的睡,它无知无觉,关闭了恐惧、欲望,处于遗忘的茫茫旷野里;可以肯定,它是听和想的敌人,不然就不会“如果你醒着/并且在听和想/你就注定要和它作对”。
人是因为听和想而成为人,也因为听和想而从生生灭灭的无限性里抽身出来,获得了有限性,它使我们从万物的合唱中成为独唱者,从无瑕中成为缺陷者。这就是人的命运。
《关系》这首诗所指的关系是醒和睡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作对的关系。为什么要作对呢?这只能是一种悖论式的存在。
诗人仿佛站在醒着的这一边,“你就注定要和它作对/哪怕你很小,它很大”,虽然人很渺小,但通过有限性與无限性之间的对抗,建立了有限性在世界的主体地位,人类通过不断强化知的意识,在广袤无边的无知无觉的旷野中,仿佛点亮了一盏微弱的灯,给自己照见了前路一小块地方;而其它地方依然淹没在漫无边际的黑暗里。
由于人类意志中的存在,在如此强烈的对比下,人类没有退却,把对抗作为一种天命,深埋在自己的命运里。在这里,诗歌触及到了那个由知和人的意志打开的世界。
《关系》这首诗没有去建构那个难以描述的世界,但它通过暗示,让人知道它的存在。口语诗揭示的存在,寄生于知识的基础之上,没有诗歌指向的知识,就可能意会不到诗歌所指的意思。
这不是口语的高明,而是它的弱点,口语诗最终只是寄生的写法。
吴投文:由孤独情境所引起的生命感觉的唤醒
置身于山里的夜晚,在孤独与清寂中,一个人的感觉似乎变得特别敏锐。吉木狼格的这首《关系》写得非常别致,把山里的一切都处置在一个虚晃的背景中,他并未描绘山里的情景,而是聚焦在感觉上,似乎什么都没有说,又似乎说得很多。
如果要把这首诗限定在一个明确的主题上,恐怕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另一方面,此诗也并不属于那种所谓的“无主题”诗歌,在其朦胧含混中还是有一个隐微的意义指向,标题“关系”就是一个提示。这是一首写得极妙的诗,适度的口语化蜿蜒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路径中,有无相生,意在言外,曲尽其妙。一个人久处尘世的喧嚣中,很难体验到孤独的奥妙,无法安稳自己的内心而听到内心的声音。此诗实际上涉及到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一个人处身于孤独的情境中,他的内心更靠近自己的真实处境,往日那些被忽略的细微事物会凸显在生命被压抑的知觉中。
诗的首句“只有在山里的夜晚”,表明是在一个相对隔离的环境中,这可能也与诗人自己的切身体验有关。一个人只有身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能感到“什么东西在慢慢逼近/什么东西又在慢慢远去/一些声音毫无由来地响起/又毫无由来地消失”。到底是什么东西,到底是什么声音?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只是诗人在此地此时的感觉而已。这是一种生命感觉的唤醒,一种由孤独情境所引起的生命感觉的唤醒。某种意义上,这是人的一种丰富性体验,带有现代性情境下反思生命存在的意味。不管你醒着还是身在梦中,处身在这样的情境中,你就躲不开这种特别的体验。
诗的结尾是恰到好处的延伸,“你就注定要和它作对/哪怕你很小,它很大”,在此,小与大的对比,不正是这种体验的强化吗?不过,我又疑心解读此诗,压根就是多余的,关键是静下心,好好读上几遍,一切尽在不言中。
向卫国:“纯诗”或一个量子诗学的案例
读吉木狼格这首诗,让我想起80多年前的一桩公案。
1935年,卞之琳先生的《鱼目集》出版,刘西渭(李健吾)先生很快撰文评述,高度肯定。针对小诗《断章》,他说:“我们诗人对于人生的解释,都是装饰。”卞之琳却不认同,甚至认为李健吾的有些解释是“全错”,对《断章》一诗,则说“我的意思也是着重在‘相对’上。”(卞之琳《关于〈鱼目集〉》)
今天看来,两人分歧产生的由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李健吾先生似乎很重视诗歌反映社会人生的功能,而卞之琳先生的诗歌观念则偏重于对“纯诗”的追求。他强调诗歌的“智性”,这是诗歌“现代性”的重要表征,而以诗来表现“相对”的主题,显然是一个抽象化的哲学主题。
吉木狼格的《关系》并没有强调处于“关系”中的具体事物,而更着眼于对“关系”本身的探讨;仔细推敲,此诗中的“关系”显然也是一种“相对”关系。“什么东西在慢慢逼近/什么东西又在慢慢远去”;“一些声音毫无由来地响起/又毫无由来地消失”;“如果你睡着了/……/如果你醒着……”等。全诗12行,第3、4行,第5、6行,第7-11行各包含一对既矛盾又同一的相对关系:逼近/远去;响起/消失;就是它的一部分/和它作对。三对“关系”之间的关联物—“什么东西”或“一些声音”或“它”—从作者到读者都不知道它们到底是“什么东西”,因而诗的着眼点只在“关系”本身,而不在发生关系的事物。
诗的最后一行“哪怕你很小,它很大”,也因为不知道“你”是谁,“它”是什么,它们的关系也就完全有可能反过来,“你很大,它很小”,因而“你”与“它”的“关系”也是相对的。
纵观全诗,除了第一行明确说明诗歌的场景设置是“山里的夜晚”之外,全部内容就是一个人的主观世界(第二行用了“感到”一词)中的两个层次,六对不明“关系”的存在。第一层次,“你”分别与“什么东西”“一些声音”“它”的关系。“你”不知道是谁,因而可以看作任何人;相对的另外三种因素也没有明确所指。第二层次,与“你”相对的三种因素,又各处于两种不同的状态“关系”,即“逼近”还是“远去”,“响起”还是“消失”,“就是它的一部分”还是“和它作对”,完全取决于其对立面的“你”处于何种状态。也就是说,回到第一层次来看,与“你”相对的三种因素,都成为“薛定谔的猫”。换句话说,此诗中的“你”与另外三个基本元素形成一种量子关系。至此,本诗大概也就可以看作是一种量子诗学意义上的纯诗了。
周瑟瑟:当代诗与第三代诗歌的“关系”—作对与突围
吉木狼格是“第三代”代表诗人之一,是目前可以看到新作的“第三代”诗人之一。
我写过一篇《“第三代”诗人现在怎么样了》的文章,是以梁晓明为案例追问那一批诗人的创作现状,《作家》《诗林》等多处有刊发与转载。想必当年的“第三代”诗人应该能够看到,反馈到我这里的消息是“写不动了”“完成了历史使命,就不要写了”“写不写是命运”之类的话。“第三代”诗人有的消失了,不再写作了,坚持写作的人作品数量并不多,写作状态也大不如前。
写作是写作者的生命,没有了写作,那属于你的文学就死了。我认为作为写作者还得写。年轻时那么狂热,而人到中年后却离开了诗歌,长久丧失了写作的动力。
有人对我说“不是不想写,但要恢复写作并非易事”。一把好刀,生锈了,要耐心磨刀才能重新上山砍柴。
每次看到当年的“第三代”诗人还在创作,我是欣喜的。如果他們中有谁有新作出来,我总会格外关注,再忙也要抽时间看看。咦?写得还行,但没有新东西。如果发现比原来有所不同,哪怕有一点点突破,也会引起我的思考。
据我观察,对于那一代诗人来说,改变是很难的,他们的江湖地位决定了写作观念的固执,一条道走到底是他们一生的想法。要么干脆放弃写作,“老子不写了”的心理比比皆是,而突破就无从谈起,连写作瓶颈都免了。坚持在写的往往写出让读者极为失望的作品,“出丑了吧,写不了就不要再写了”。陈旧的表达,还停留在那一套诗歌观念上,走不出“第三代诗歌”久远的光芒,不管怎么读都是“第三代诗歌”那种调调的搞法,如此下去的确没有写的必要。
新鲜的活力是诗歌最起码的,虽然先锋已死,但新鲜的活力是写作的底线。
我多次入川,生活在那里的“第三代”诗人的状况如何呢?杨黎保持了永远的活力,在北京生活多年,又到南京,再回成都,“橡皮”“废话”为当代诗歌贡献了不少硬货。何小竹诗歌小说多有新作,像杨黎一样,近年对于年轻人的传帮带也值得称道,他们的诗歌美学吸引年轻人追随,让年轻人远离俗不可耐的诗坛,让一个写作者能够以独立与清醒的写作姿态开始写作,而没有站在非文学的那一边,这是他们晚年对于当代诗歌的又一贡献。我关心他们的状态,李亚伟身体消瘦还在开餐馆,杨黎也消瘦了,尚仲敏、吉木狼格身体健康,肥头大耳。酒肉玩乐让硕果仅存的“第三代”诗人总体上活得滋润,从而让他们的写作与诗歌生活保持了一定的活力。
当代诗歌与“第三代”诗歌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从吉木狼格这首《关系》可以得出结论:“什么东西在慢慢逼近/什么东西又在慢慢远去/一些声音毫无由来地响起/又毫无由来地消失。”就是这样的关系。“第三代”诗歌当然有其美学遗产,诗中所写的“什么东西”在我这篇文章,我用来指“第三代”诗歌也未尝不可。“第三代”诗歌已成历史,它的美学遗产“慢慢逼近”又“慢慢远去”,“毫无由来地响起”又“毫无由来地消失”,正是“第三代”诗歌与“第三代”诗人的命运。
对于当代诗歌来说,“如果你睡着了/你就是它的一部分/如果你醒着/并且在听和想/你就注定要和它作对/哪怕你很小,它很大”。这或许就是“第三代”诗歌与当代诗歌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应看到当代诗歌“睡着”与“醒着”的两个状态。
吉木狼格虽然在写“山里的夜晚”的声音与你的接受关系,但我借此来说他们那一代诗人与当代诗歌之间的关系。“你就注定要和它作对/哪怕你很小,它很大”。“作对”是对的,当代诗歌必然要摆脱旧有的诗歌美学牢笼,从当年的“第三代”诗歌中突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吉木狼格这首《关系》意味深长。
宫白云:探求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关系”
“关系”一词错综复杂又会让人浮想联翩,大到社会的、经济的、哲学的、宗教的、自然的等等“关系”,小到具体的人与人、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体现出“关系”浩瀚纷繁博大精深的本质。
此诗以“关系”为题不仅暗藏了这些诸多的属性,又内在地还原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本相,任何“关系”都离不开人,人是“关系”的本原。
此诗以“山里的夜晚”与“你”之间产生的“关系”,道破了人与自然相辅相成、相偎相依、天人合一的真相,它跳脱了一般人“在山里的夜晚”的庸常思维,把自己的特殊体验(“什么东西在慢慢逼近/什么东西又在慢慢远去/一些声音毫无由来地响起/又毫无由来地消失”),新鲜准确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语言极简,意味却隽永,充满了神秘性与奇异性。它是山里夜晚的灵性与“你”灵魂的相遇,在我们愣神的刹那,诗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带动我们的思维和他一起进入一个冥想的境界—“如果你睡着了/你就是它的一部分”,这是深思熟虑的冥思与天地本源的极致融合。那说话一般的语调释放的却是神启一般的哲学内涵,可以说瞬间就把人代入了其中,那种与天地合一的美妙,启示着麻木的思维驰骋起来,与诗人一起去探求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本源性“关系”,试想自己在那样苍茫空旷孤独寂静的山里的夜里“睡着”或者是“醒着”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而诗人“醒着”的冥想无疑是奇异而与众不同的,“注定要和它作对/哪怕你很小,它很大”,这种以人的渺小去对峙天地的博大,折射的是生命背后隐藏的伟力,足以以小博大,这就是人与万物之间的精妙“关系”,也是此诗用人称“你”而不是人称“我”的精髓所在,“你”是阔大而千变万化的,“我”是个体有局限的。
诗人以“你”运筹帷幄,不显山露水,自然松弛地把人与自然天地那种万物合一的“关系”呈现得淋漓尽致。
赵目珍:生命主体作为什么而存在?
吉木狼格的这首诗,主题已经非常明确了。他要探讨的是,作为生命主体的人在面对外在的自然时,应该作为一种什么样的形态方式而存在。其实也就是探究生命个体与外在自然的内在“关系”。诗歌首先渲染夜晚山中的环境氛围,进而指出人在“睡着”与“醒着”的两种状态下,分别与夜晚之下的空山(包涵与山有关的空间中的各种事物)所构成的不同关系。在前者状态中,人已经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人所崇尚的“天人合一”精神;后者状态下,人独立于自然之外,与自然“相对立”,或如诗人所说,是一种与自然“作对”的状态。这种状态让人联想到现代人所推崇的“意识(精神)独立”。我隐约读出,诗人认为前一种状态是胜于后一种状态的。因为“天人合一”的境界在中国人看来,是人与自然所应达到的最和谐的状态,是一种至高境界;而个体的“意识(精神)独立”一般指现代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言。在大自然(天道)面前,这种状态一般不会出现,它与庄子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迥然有别,庄子所言与“天人合一”恰好是一致的。尽管诗人所言“醒着”时的状态,也可能存有从主观出发对天地、宇宙欣赏的一面。但主客观保持对立的姿势,从境界上而言,已经落了一层。因为我们所推赏的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向来都是“欲辩已忘言”“相看两不厌”这样一种进入到了物我冥合状态的关系。这与后人阐释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中的“见”字是读jiàn还是xiàn,有一致之思。当然,最后还可以联系到王国维“境界说”里所提到的“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此诗中两种关系之间的差别,也正是“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二者之间的差别。读者自可细细体味。
高亚斌:诗人还是选择了“醒着”
在《关系》一诗里,吉木狼格没有进行任何过渡,就直接切入到了一个具体的生活场景,定格于一个“山里的夜晚”。“山”跟“夜晚”都是寂静的意象,“山”是在空间上远离人烟的地方,而“夜晚”则是在时间上的万物静谧的时刻。诗中还有一个隐匿的存在,那就是虚拟的“你”,其实也就是“我”或诗人的自指。正是由于诗人摒弃了俗世的各种浮华和喧嚣,才能够抵达这“山里的夜晚”,成为一个孤独的聆听者,一个静默黑夜中的唯一清醒者。《关系》一诗充满了神秘主义的玄学气息,诗人化身为神秘的通灵者,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慢慢逼近/什么东西又在慢慢远去”。这一情形,类似于西川在《在哈尔盖仰望星空》中所写的:“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你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听凭那神秘的力量/从遥远的地方发出信号。”但在深山的夜晚,并没有“什么东西”,有的只是人内心的某种感悟和召唤,越是处在空旷与寂静之中,就越是能够倾听到这种内心的声音。每个人可以选择被山或者黑夜接纳,成为它的一部分,或“注定要和它作对”,这无疑是生命个体的共同宿命,也是我们与世界之间别无可能的两种关系。于是,“醒着”和“睡着”,也就成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与外部妥协,或毫不妥协地“和它作对”。显然,诗人是选择了后者。
徐敬亚:中国现代诗的极品
2013年春天第一次读这首诗,便认定它是一个难得的精品。经过几年后再读,我想应该给予它更高的定位—中国现代诗中的极品。
这首诗的经典性在于,它把格外宏大的、抽象的、物质世界中仿佛不存在的哲学化“关系”,用最平白、最浅淡的汉语从容地表达出来。全诗没有使用任何形式的诗歌修辞,也没有一个生僻的汉字,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都可以轻松认读。
在西方哲学的认知中,这一定是一次惊心动魄的生命体验:无边的黑夜中,有东西在“逼近……远去”—这是幻默中的触觉,是外部世界对主体循环式地压迫。有一些声音“响起……消失”—这是冥想中的听觉。最后6行是高潮—是主、客体的正面对峙:主体的“睡”与“醒”、“听”与“想”,以及双方形体、实力对比的“大”与“小”。短短一首诗,充满了哲学的硝烟。是不是太哲学了呢?即便从理性角度对人类主客体关系进行分析,我们还能找到更多的、更大的关系吗?
这不是哲学,一切关系在吉木狼格这里,全部溶化成了东方式的内感!强大的外在世界幻化成了全方位包裹着他的山与黑夜,二者进一步化成了一个“大”的“东西”!最妙的是,睡了的人,变成了自然的一部分。而醒了的人,注定与自然作对。这,已经不再仅是诗,或者并不局限于哲学,而进入了世界观一类的人性选择,或者说是吉木狼格说出了生命灵性中原本暗含的、不甘与不宁的抗争元素。
对于诗来讲,一切都沒那么高深。不过是诗人在黑夜深山中的几丝感觉。功夫到了家,便能感受到黑暗中隐藏的一切,如同深山禅师感知风吹草动。高明的诗人常常会出现灵魂出窍的时刻,那就是妙手偶得的高光降临之际。可以说,没有一首诗的出身是简单的。简单往往是放弃了多少繁华之后的简单—干净、纯洁、透明、随意。
不对,平淡词语的背后隐藏着吉木狼格的良苦心用心。我觉得诗人深知西方哲学主客体那一套。证据是,他把诗的题目定成了《关系》。而如我挑毛病,恰恰是这个具有西化意味的《关系》,使东方式的诗意受到微损。如改成《山里的夜晚》,便更深藏不露。
最后我数了数:全诗只有94个字,去掉重复的,大概70字左右。
韩庆成:山里的境界
《关系》是首届“中国好诗榜”榜首诗歌。如同诗的标题,这首诗自始至终在表现一种无处不在的却又常常被人忽视了的“关系”—山里与山外的关系,近与远的关系,响起与消失的关系,以及可能是作者重点要表现的睡着与醒着的关系,听和想与作对的关系,很小与很大的关系。
这些关系情形不同,却又互相关联。如果说从山外到山里是从俗世来到了世外,那么这种自觉或者偶然的避世之举,让诗人的听和想得以到达一个新的境界之中。后来的醒着、作对乃至以小搏大,都是在这个新的境界中得以产生。
我特别喜欢诗的后半部分:“如果你睡着了/你就是它的一部分/如果你醒着/并且在听和想/你就注定要和它作对/哪怕你很小,它很大。”它告诉我一种清醒的力量,以及不苟且、不畏惧的“山里”精神。
霍俊明:一首“纯然”的诗
吉木狼格在《关系》一诗中强化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生疏远近相互抵牾的一面。
起句“只有在山里的夜晚”成为整首诗非常关键的开端,它直接引领了全诗接下来的走向和精神意指。
“山里的夜晚”是精神化的场景,它指向了封闭而久远的非功利的自然空间,它对应于人类本源和体验最为本真的一面,所以任何事物和声响都会被格外地放大,而各自携带的意义或启示也同样被强化。这是纯然放松的隐逸和自我放大或缩小的时间。人与事物、声响的关系因此获得了本质化和终极意义上的精神叩访的效果。
这首诗没有多余的句子和虚饰的成分,而是恰如其分地指向了空间、关系以及主体的核心和交织。就像在山中黑夜降临或消隐的事物与声响一样,它们自身就是世界和意义本身,而人是其间的镜像还是引导性的主体都未为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