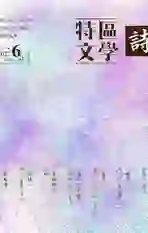诗歌的一咏三叹
2022-06-23曹梦琰
小引
夏多布里昂说:“每一个人,身上都拖着一个世界,由他所见过、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即使他看起来是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旅行、生活,他依然不停地回到他身上所拖带的那个世界去。”对于一个诗人,诗歌是他自己历史的呈现物,它们带着他对彼时彼刻的洞穿与此时此刻的盲点,用年轻的时间化解老于世故的时间。“如果你唱段京戏,用长腔把我绕进去,让我回到出生以前/让我的身体一咏三叹/我会更加地喜欢”(《山坳》),用异国强悍的腔调击溃母语的顽固“我深爱着汉语,偏偏要在英语里爱得最厉害”(《80号公路》)。每一次的冲击—一首现在的诗带着它成熟的语调平息过去的号啕,而那首青春时代激情燃烧的诗则逆袭了岁月,让此刻所有寡淡的言谈都噤若寒蝉,每一次冲击的遗留物都叠加在了诗人的诗歌史中,构建他自己。时间既是破坏者,也是建设者。诗歌是时间的遗留物,是那保持着一个人生命痕迹的繁复结构。
在诗人路也的时间遗迹中,有江心洲上“一个像首饰盒那样小巧精致的家”(《江心洲》),带着淳朴的自然气息、生命欲望和对侵入其中的工业气息的轻松化解:“远方来的货轮用笛声使我们的身体/摆脱地心引力”“我们志向宏伟,赶得上这里的造船厂/把豪华想法藏在锈迹斑斑的劳作中”。轻率而让人羡慕的轻盈,这首写于2004年的诗(包括同时期的很多首诗中)毫不犹豫地展露了写的力量—在自己和世界之间,在腐朽与神奇之间。在后期出版的一本诗集的自序中,路也说:“上天的恩赐是拥有的,曾经赋予我一个‘江心洲,即便那只是把异乡当了故乡,并且被证明只是子虚之镇乌有之乡。”这个精巧的家终为陈迹,连同那段南方情缘。异乡、故乡却在她的生活与诗歌写作中一语成谶。
另一时间段中,时间的遗迹一如她的履历,是动态的,是旅行的,是快速跨越不同文明、历史相距甚远的不同文明的那种眩晕与怪诞:“那国已3000年,这国才300年/这国在时间之轴上刚刚走到那国的公元前/于是我说,从那个国来到这个国/就等于从21世纪返回到了殷商时代/只是,它的标志不是青铜器/而是航天飞机和微软”(《内布拉斯加城》),也是故乡的陌生与异乡的熟悉。从《江心洲》到《地球的芳心》,似乎隐隐暗示了人们在这个世界的处境—从来,你都只可能占据其中一点,只有在那一点上,你才是中心,这是我们的渺小与骄傲。他者和世界是我们的窗户,决定了你作为中心发射点所散发出光芒的最终去向与回应—是偏居一隅的江心洲,还是地球上一起打开的窗户?当然,也有不曾改变过的,是那颗真正柔软的心,诗人之心,女性的芳心:“诗人的心脏/是柔软的、踉跄的、铅笔手写体的心脏/能模拟全人类的心绞痛和心梗/有琥珀色泽和云母状花纹”(《心脏内科》)。虚弱甚至略显病态,但是它美丽,痛他人之痛。这段诗歌履历呈现给了我们诗人的成长,事实上,从更早的、小小的爱情诗起,就已经开始了。每个人总有一种开始的方式,去接近你的命运,而时间往往证明,那让我们开始的动机与苦闷总是那样短暂和易于破碎:“其实所有爱情都是昂贵的/都像荔枝一样容易腐烂,朝不保夕”(《在增城吃荔枝有感》)。我们选了江心洲作为出发之前的家,选了异国旅行的痕迹,接下来是,旅行之后的回来。如夏多布里昂所说,在不同的世界里旅行,又回到自己身上所拖带的那个世界中去。路也的长诗《木渎镇》就是回来,回到甜美的母语中,回到“苏绣之意”的雅致—那个曾作为异乡的南方所赋予她的湿润与柔软中,甚至回到更早的北方,那些“无比正确的大山”和“明哲保身的荷花”。回到前朝,回到中世纪。我们会看到一所秀致之城,然后是它的黑暗,黑暗之外,地球之外,是宇宙的璀璨。
分析了诗歌遗迹的每一层结构,再整体端详这纹理深浅不一的复杂建筑,这就是我们要探索的东西。原本炎热的夏日午后,狂风乍起,靠窗的书桌上,未完的诗稿被风卷入天空,直到暴雨冲淡字迹,纸张混合着泥泞;桌下的废纸篓里,那些写好了又被遗弃的诗稿……每一首诗都有自己的命运,而命运中此刻被我们读到的一个诗人的所有诗歌,以它们的斑驳、不完整和延续呈现为一个诗歌建筑,一首属于他自己的唯一的诗。
路也在诗歌中处理的信息有些驳杂,她自己的写作也倾向于铺陈,所以诗歌本身并不属于精致的类型,尽管不难发现精致的句子。她的诗歌确实有几分传记的意味,这也决定了它所呈现出的繁复与粗粝。很多句子是未经转化的引用与嵌入,当然,于她所选取的坐标而言,这些的确是微小的细节。对于时间本身而言,一个伟大诗人的一生不过是尘埃的一瞬;而对于宇宙而言,国家甚至算不得尘埃。路也诗歌中如历史年谱大事记般一掠而过的句子,她那些跨度过于大的比喻,并非浮夸。僅仅是,当我们选取了更辽阔悠远的时空坐标,这些看起来大而不当的词与物仅仅是细节,宏细节:“一段木制的栈桥上/一双红色布鞋的鞋底缝隙里沾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另一双是白色旅游鞋,有着十七年的乡愁”(《密苏里河》)。当诗人发出第一个音之后,一段长腔就开始绵延,一咏三叹,把我们带回比自己更久远的母语中:“别了,我无比热爱的元音和辅音/从此把母语当成最后一门外语/只跟汉语较劲,将方格稿纸当成耶路撒冷”(《一九八七》)。
一、发音练习
“我要改编一首歌来唱/歌名叫《我的家在江心洲》/下面一句应当是‘这里有我亲爱的某某”(《江心洲》)。这首歌没有一直唱下去。就像诗人某天抱着一棵有“北方之美”的大白菜诗,顿悟自己“很像英勇的女游击队员/为破碎的山河/护送着鸡毛信”(《抱着白菜回家》)。同小巧精致的江心洲之家一样,这样一首毫无发声障碍的歌只属于子虚乌有之乡。美并非限于江南的潮润,还有这棵北方大白菜的“健康、茁壮、雍容”。它甚至涵盖不美,滑稽的历史与政治,令人伤怀的破碎。“文学在政治中找见自己的影子,又把这影子破却在政治里,换句话说,就是自觉到无力……”。诗人终有一天会觉得无力,勿论入世或避世。“从这两公斤里提炼出一毫克的幸福/一微克的回忆”(《巧克力邮包》),路也后来的诗集《地球芳心》中有一辑《元辅音》,我们可以从那些诗篇中找到散落的发声碎片: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元音、辅音、爆破音,美声唱法,梦呓、絮叨、咳嗽……每一次都是练习,练习如何去投入生活和世界,它们保留了诗人轻快的呼吸,却不会再有满满的自信唱出一首完整的歌。仅仅是提炼,在破碎生活的每一次的发音练习中,试出最动人的音:“嘈杂话语里唯有元音在空气中闪烁”(《密苏里河畔的晚餐》)。—用受伤的喉咙、劳损的身体、柔软的心支撑这一次次的练习:“我有劳损/因跟不上这个火热的时代”,“我有病/有不为人知的悔、非实用的愁、温和的警惕/真空的紧张,以及抽象的疼痛”(《淡粉色》)。万古愁,宇宙之痛,形而上对形而下的无力。37FE82A2-9835-4662-8B6C-933BC956FB0E
旅行在路也诗歌中直接的投影是,语言和发音的转换、交换与渗透。萨义德认为:“每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语言也是不断寻找异质的、可与之相竞争的另外一种语言:“再以十四行诗的韵律研磨成粉/免不了夹杂进一丝亚得里亚海风”,“读着《古诗源》中的魏晋部分/第一口喝下,顿感/风云际会”(《一杯咖啡》)。诗人押的是“风”这个韵,一丝海风的蝴蝶效应,异国芬芳的尘埃凭借轻盈的渡力与汉语诗歌相遇。捕风捉影,囫囵吞枣,歪打正着,其中不乏美丽的误会与错误。有关诗歌翻译的趣闻很多,一种语言如何在被另一种语言的误读中重新发现自己。奥维德的《变形记》中,有一个关于谣言女神的故事,谣言随风散播,这其实是个美丽的比喻。神秘感维持于彼此对对方的谣言和误解中。但是也同样在误读与被误读的往复中,成为现代诗歌写作的诗人们面临的困惑:“我被译来译去,成了一个病句”(《国际航班》)。我们已不再自欺欺人地唱那旋律熟悉的歌,用母语安全的腔调。除非盲视盲听,我作为中心点所接纳的信息早已不是桃源,强大、杂乱、甚至有些完全不为我们所知的东西在染指诗人发音的喉咙。除非你选择假声,除非你想丧失对这个世界和自己的真实感—你只能艰难地,练习另一个、更多个音。这个过程的危险在于丢失自己的发声方式,变成怪里怪气的汉译本英文或别的什么文,强哽在喉咙里,一呼吸就散发出隔夜奶酪的酸腐。
喏,并不是每次相遇都是美好的,也并不是每一次练习的体验都让人兴奋、心领神会。但是路也在自己的诗歌中找到了很好的练习方式,剥落每一种语言身上沉重的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外衣,它们变得单纯而易于沟通:“屋檐下的风铃念了一段独白,听得出元音辅音相拼”(《奥马哈的春天》),“对着星星祈祷时/要发多少爆破音”(《这是我的行李》),“拆开又装起来的梦呓、轻轻的絮叨和浅浅的咳嗽”(《这是我的行李》)。仅仅是,发音,像初学说话的婴童,体会那纯粹的声音与世界撞击时的怦然心动;或者,听从身体的悸动,任由它梦呓与絮叨,与万籁的声音相合:“他最终会开口说话/用茫茫白雪封了大地的那种语调/用千山万水都听得懂并跟着一起诵读的语言”(《卡索街801号》)。说出,唱出,在一次次的窃喜与挫败之后,如有神助,再次押上了韵,万物都有一个隐藏着的相同韵脚,我们校准自己的音,练习它到至臻,完美中的完美,它们就一同颤抖、共鸣。这是诗人的野心,你也可以说是芳心。她喜欢用铺陈词语的方式罗列出和心有关的若干词,这是近乎简单粗暴的方式。野心是胸怀,芳心是柔软。她说地球是她的故乡,而江心洲只是曾经的乌有之乡。可是,“刚绕过一个小岛,天地衔接处就盖了封印/月亮孤单的身影打动地球的芳心”(《芦苞芙小溪》)。江心洲从来没有消失过,江心的光芒扩散到了天地衔接处。它是地心,就在这一刻,是野心和芳心,甚至是他乡与地球之乡交汇的第一缕目光。我们的故乡足够大也足够小,这头顶的日月星辰呵:“让快乐遍地都是,让一生成为一道优美的圆弧/以高高飞翔来抵御一颗星球的绝望”(《寄往水码头,致JM》)。
诗歌,韵的衔接让它优美,我们兴奋得忘乎所以。为这相逢与共鸣—异国中的母国,消融的语言界限,这首尾相衔,象征完满的圆弧。诗歌,好的诗歌,却一定会有它突然的坏韵,那别扭的孤独,无可抵御的语言绝望,失声……
诗人路也在《内布拉斯加城》这包括了从A至N的十四首詩歌的组诗中,声音很缓和,几乎没有突兀的比喻和毫无顾忌的铺陈。这是独白的语调,征兆我们处境的孤独,无视时间、他人,甚至自己。寂静之下的暗潮,调整性的失声。因乏力而忍耐,却在长久的忍耐后,一声长叹,像蓬勃的种子,所有枝叶与花朵都呼之欲出:“教堂尖顶笔直,想把天捅破,想弄清自己/究竟指向生前还是死后”,“我只剩下了半生,请替我做个决定吧:/是该用来流浪/还是该用来结婚?”。孤独时,我们会对自己发问,对生死、宇宙发问,伺机从寂静中找到一个突破口。孤绝冷清的音渴望回到美丽的韵之中,通过对话、反讽,甚至仅仅是沉默的对视:“中央街道拱起/弧度约等于我对人生的思考”,这弧度,半个圆的孤独,等待它的另一半。“半个脸”“部首和偏旁”“诗里写坏的那一句”“半生”甚至“山东半岛”—这些不完满,孤独中永恒的主题。写作从孤独中呼之欲出,从沉默中呼之欲出。也许柏拉图那古老的有关诗歌的断言并非完全不成立,诗人模仿,但不仅仅是模仿那比理念低了一层的事物本身,还要模仿理念中的完满—这是诗歌的责任。孤独则是它的灵魂,残缺而卓越的灵魂。
路也的诗歌中有不同的圆:优美的圆弧,那多少带了点理想主义的“高高飞翔”与圆满;“时钟多走一圈”,时间不被察觉的重复与流逝;“快乐与激情的圆周”,短暂易逝的美好幻觉。直到这组诗的最后一首“N”,与第一首的孤单相合,一个圆;极致的孤单,那一半的圆弧迎向生命的圆满,仿佛未曾闭合的圆弧之尾延伸出另一个更大的圆;发芽、吐穗、开花、结果,循环之圆,每一有机过程的骚动与蜕变:“物质生命存在于机体各个肢体的器官,总体存在于每一部分;但又表现为生命,它寓一于众,从而合众为一……”当然,寂静之后,是又一次的发声练习,清凉圆润或结结巴巴;或许因为坏了一句被丢弃,或许它有一个张灯结彩的完满结局。写作有它的命运,命盘也是一个圆。寂静会周而复始地被打破,孤独找自己的突破口,这种过程一旦开始,可能就呼出了写作中的华彩,但寂静和孤独才是写作的深度。所以,让那一刻停留、持存,这可敬的对立面—哑然、失声。
二、另一首
“我知道,这一个又一个寂静的日子/将发芽,将吐穗开花,将结果,将会有一个总和/但须在另一个国度/—永远是,当然是,而只能是”。诗人宣称:“我深爱着汉语,偏偏要在英语里爱得最厉害”,“从此把母语当成最后一门外语”。所以,那“另一个”,永远是,当然是,而只能是母语。诗人胡冬认为:“回归必须是通过向西的方式去完成,它必须跟那个家已不存的家背道而驰,而且开放的母语是没有防线的。只有抵达现代性的极限—为此我们迎来了后现代性,我们才可以发现未知的汉语性。”在其它的语言中重新发现汉语,它如另外一门语言那样的陌生感与新鲜感,就算诗人不把它作为使命,也会作为一种本能。否则,纯熟却重复的写作将如何继续,陷入一个个雷同的圆满中?诗人终于呼唤出了“另一个”,那重新被发现的母语。所有的发音练习,那些漫长的孤独与寂静,似乎都在等待这一首,另一首。这憋过青春期的长腔,憋过浪迹时的长腔,终于发出,一咏三叹。37FE82A2-9835-4662-8B6C-933BC956FB0E
长诗《木渎镇》,且不论诗歌的直接对话对象“你”,更深层的指涉是母语。她化身南方的“评弹之韵”,化身北方的“道德文章”;她的媚俗、苦难、被误解、被消费,以及她的强大与坚韧。
南方是路也诗歌中的重要坐标:生活,情感和语言。参照南方,路也的诗歌其实很北方,铺陈是其中之一。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作为消解某种主流意识形态、政治话语或历史话语的存在,她的诗歌几乎也形成一种过于直白的话语体系。就我个人的看法,很多句子是难以接受的,阐释与铺陈破坏了完整性。
北方是风骨,南方是呼吸,她的诗歌中都有体现。“船娘的歌调里明显放了糖/岸上饼屋散发枣泥、松子和芝麻三种滋味/哦,世俗快乐从未减少过/只是桨声里隐约着浮躁之音,听上去已不是原声”。甜腻浮躁的声音,降了一格的现实。尽管诗人在开头已经试好了苏州之音,南方之音,甚至预先设定了这曲子的悲壮:“而同样是这一个你,最终以血写的诗篇/献给这个苦难的国度”。
因此诗人不得不调整,再次校音。掠过人、现代工业与科技的侵略地,她的目光投向一块净土:“就在这个小镇的神经末梢上/端坐了一座小山,它有着乡愁的海拔”。直接指向母语的过去,甜美伤感的乡愁,这是高度,用以丈量诗人与诗歌的尺度—傲视降格的现实和它媚俗的声音:“它们开放,没有皇亲国戚的血脉,亦无奴婢的容颜/更听不懂佛寺钟声与天空的交流/它们开放得宁为玉碎,开放得仿佛正在这尘世上流亡”。这也是母语一贯的命运,她圆滑的部分好风凭借力,入朝堂入史册。她孤傲的那一部分在时间中流亡,美丽、虚弱甚至破碎,却坚韧地等待每一世,每一时,与那些不愿做道德文章的人相遇:“真理总在远离庙堂的荒山野坡,光芒万丈”。
所以我们说母语的苦难。当诗人校准了音,进入到历史的悲歌中,苦难的画卷一幕幕展开—伤痕累累的母语,那些每一个因发声而惨遭屠戮的人:“你居于最黑暗最核心的腹腔,让破衣烂衫飘成旗帜”。抵御与化解这暴虐的,依然是那顽强而柔韧的歌,在现实苦难中本能地悲歌,“放声大哭,哭得一泻千里/哭声必须让上帝听到”;对话未来的智之歌,“玻璃糖纸在你手中叠出花样繁多的工艺/一只亲手制作的小帆船将驶向未来,驶进时间之河”;诗歌、诗人和母语,都需是情智两全。因为深情,会无視暴虐的胁迫,免于沦落为美丽的附属品;因为智慧,过去能够以某种方式得以保存,延续。否则我们就是感情或理智的囚徒。
母语的波折远不止于苦难带来的厄运和对它的救赎。这让人不屑的消费时代,却又无孔不入的消费时代。再加上几千年顽固的麻木,旧疾新病,她几乎窒息:“汉语因上进心大于才华而变成口号,几近昏厥”。好了,现在我们可以谈一谈诗歌的直接对话者,和母语休戚相关的诗人的命运。源于母语的脉管,诗人是血液,有时平缓流淌,它们一同感受时光的静谧,有时彼此倦怠,相看两相厌。但诗人最重要的时刻是那些沸腾、几乎要挣断脉管的时刻,用自己的新鲜催动母语迟滞的触感: “从肢体节奏和衣袂飘动之中/分明感觉到你的存在”。时至今日,似乎诗人与母语的命运已经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两个极端。流亡,用乡愁的深度来探测母语的深度。或者,成为安全模板中精致的工艺品,不会对母语有任何贡献,却能做出好看的摆设,如鱼得水。
太过窒息与压抑,诗人需要再做一次调整:“满山的草木在做深呼吸/山谷说:睡吧,睡吧,亲爱的孩子”。歌近尾声,柔和地安抚亡灵,以及活着的、受伤的灵魂。南方作为坐标再次出现,与它共同决定我们位置的已不只是另外一条坐标。不是我、北方、异国他乡、母语、历史或现实,而是它们全部的交汇,南方被弱化,因此才不突兀,好像它从来都和它们是一体,不可分割。这是诗人的成熟。
这首诗歌的负担有些重,当然它并不意味着结束,尽管我有意用距现在最近发表的它作为收尾的部分。就这首诗歌的写作来说,我并不认为诗人调整到了最好的状态。诗歌真正呈现事物的能力和文字表现力之间是有差距的。不过,当诗人决定了放逐自己,旷日持久地与流亡的母语一同沉浮,我们就会期许某些时刻的到来—那沸腾的血液转化为母语的福音:“让越狱的心望得见地平线,望得见光年之外的星辰/为了不让过去变得陈旧”。
曹梦琰,女,生于1986年,文学博士,现供职于江苏理工学院,致力于当代诗的研究与批评。已出版专著《语言的躯体—四川五君诗歌论》。37FE82A2-9835-4662-8B6C-933BC956FB0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