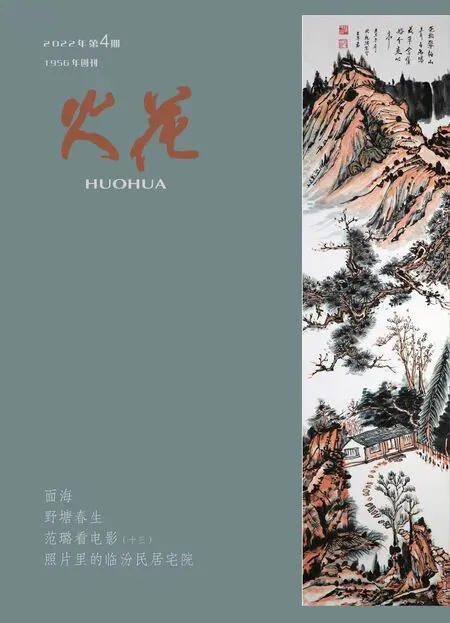雪事
2022-06-16高洪珍
高洪珍

北方的冬天,必定是有雪的。有雪的日子大多是有记忆的。
一
1978年家门前柳树儿发芽,爷爷给我折一根柳枝做笛哨时,我忽然发现身材魁梧的爷爷直不起腰来了,整个身体跟一直塌陷的日子一样,打开锅盖就是一锅玉米碴子粥,稀稀拉拉一点精气神也没有。好在到了暮春,眼看着日子开始好起来,锅里开始有了高高的白面馒头,总算不用母亲外出借米借面,日子紧巴可尚能过得去。母亲在每次烀饼子的时候,就会在一圈金黄的饼子中间嵌上两个白白胖胖的白面馒头。那馒头在蒸气缭绕的朦胧中,像一对白白胖胖的娃娃,可爱又让人食欲大振。每次掀锅时,我都站在娘的身旁,恨不得一把抓来吃。娘把这对白白胖胖的馒头,麻利地从锅里提溜出来,放在一个干粮垫子里,晾好后,将皮剥去,掰成四块,将其中一块放进爷爷的手心里。我盯着爷爷将这四分之一的馒头,掰成我指头肚那样大小放进嘴里,慢慢咀嚼。我嘴里的唾液跟着他下颌一动一动的白胡子在运动。之后,他闭着嘴,像是准备做一件大事一样,使劲地往下咽。有时候馒头像是一块石头堵住食道,咽不下吐不出,他背转身子,我们装作看不见,心揪得疼。
爷爷依旧跟往年一样忙那些该忙的活儿。麦子该上粪了,该浇水了,该准备割麦子的家什儿了。找出挂在墙头的镰刀,找出去年剩下的草绳子。只是,爷爷气力不足,割不动麦子了。爷爷的身子渐渐佝偻、瘦弱,但是,这场麦子,他是要在场的。
在生产队那些年,哪场麦子不是他扬出的!那时候,他英武的样子许多人都羡慕的,甚至在教育自家孩子时,都以学爷爷那样把麦场扬成一弯甚至两弯月亮才算好。打麦扬场,爷爷是可以左右开弓的。站在两堆麦子中间,爷爷就像一位英勇无敌开弓射箭的将军,斗志昂扬。每一堆麦子旁站着一名拿木锨的壮劳力,他们也是在众人中挑选出来的精壮汉子。嚓,左边的壮劳力已经把小麦上满了锨,爷爷迅速将簸箕侧斜给左边,一送一接,爷爷顺势就将簸箕里的麦子随风扬出左前方;紧接着,右边壮汉的木锨上的小麦已经来到,爷爷的簸箕迅速侧斜给右边,又是一个天女散花般的飞扬,簸箕里的麦子迅速飞出右前方,又很秩序地稳稳落地,摆成一长溜。随着左右不断夹攻,那飞扬落地的麦子,弯成两弯金黄的月亮。白花花的麦糠,已经规规矩矩飞到了另一边。那时候的爷爷是庄稼汉里的巧把式。
屋后的小树林里,有一畦菜地。一到夏天,草苗就比赛似的你追我赶地长,爷爷是喜欢这些草和苗的。他拿着马扎,来到菜地,先是在地头上坐一会儿,与这些草和苗说一会子话,就跟见了久违的老朋友一样:“几天不见,长这么高了。”言语中透着亲切,也透着忧虑。爷爷费力地起身下到地里。他总是在蹲下身子时,顺手将马扎往身后一塞,马扎的一对前脚着地,他半斜着身子靠着。这个曾像山一样的汉子,如今却也只能土堆样堆在地上了。
爷爷的身子就像被抽离了筋骨,软塌塌的,站立不稳,蹲下起不来。爷爷不能去地里干活,就在家帮母亲纳鞋底,做线穗子,看孩子。钢铁一样的汉子,变得沉默寡言了。他在怀疑自己到底怎么了?强壮结实的身体,怎么就突然没了力气,没了精神?曾有几次,我放学回家,看到爷爷坐在院子里发呆,他是想起了什么?
那双骆驼鞍的靴子仿佛坠着他的身体,摇摇晃晃走不动。
冬天爷爷最常穿的就是那双骆驼鞍靴子。千层底,黑粗布面,上面两道硬邦邦的箍,穿在脚上,有些沉重。下雪时候,爷爷总是穿着这双骆驼鞍的靴子,背上粪筐,去雪地里捡还冒着热气的牛粪,咔嚓咔嚓的脚步声凝重而亲切。如今,爷爷的脚步越来越没有气力,走起路来有些飘,过去的强壮游离了他,只剩下虚弱的身子。爷爷时常望着墙角的粪筐出神,他再也不会与它一起去砍柴、收粮,去田间地头与那些放牛人一起聊天了。
1979年正月初二的夜里,大雪纷飞,爷爷躺在炕头上,奄奄一息。簌簌飘落的雪花,像被天空看不见的一双大手抛洒着,仿佛要掩埋什么,又像要带走什么。年幼的我们都有些害怕,偎在一起,说不出害怕什么,却又真得从内心里害怕着什么。雪花无声地飘落,把夜拉得很长很黑。就在我们又害怕又要睡下去的时候,爷爷睁开了双眼,看看身边年幼的我们,看了看父亲,他用细弱的声音说:“我——对——不起——你——娘——”说完,眼角滚下一大滴泪水。爷爷的气息渐渐微弱,渐渐消失。在大雪之夜,走完了他八十三岁的人生之路。
一场雪的到来,仿佛是为了完成一种仪式,告别尘世,或者回归泥土。
二
爷爷去世后,不常来我家的奶奶偶尔会过来帮母亲照料小妹,却很少在我家吃饭。奶奶个头不高,微胖的脸庞上总泛着红晕。我以为那是长久风吹日晒的缘故,后来才知道那是血压高的一个明显标志。她捻动那双尖尖的小脚,摇晃着微胖的身子,慢条斯理的样子。当然,那双小脚换谁也快不了多少。稀疏的白发,在脑后挽成一个发髻,跟她微胖的脸庞有些不相称。
奶奶总穿着那件蓝色粗布大襟袄,黑粗布大腰裤子。常年用着一口大锅,做着一个人的饭。饭总是糊在锅底上那么一点点,跟浆糊似的,看上去连那口锅都喂不饱的样子。奶奶也总是会把锅底上的那些糊了的用铲子铲下来,放在那只裂了好几道纹的蓝花粗瓷大碗里,一点不剩地吃下去。她喜欢吃野菜团子,比如:春天的曲曲菜、福子苗、腊子菜、荠菜……做的菜团子里面菜多面少,面只做菜的粘合剂而已。菜粘粥稀稀拉拉,看上去也仅有野菜。每顿饭都只有一样儿咸菜,就是自己刮来盐碱土,淋成咸水腌制的萝卜或者菜叶子,吃起来又苦又咸。爷爷活着的时候,逢年过节,母亲打发我们兄妹去叫奶奶过来一起吃饭,她是定不会过来的。母亲就只好把盛好的饭或包好的饺子让我送过去。奶奶极少包饺子,我吃过奶奶包的饺子,大长大长的,有点像是扁食,里面的馅儿是不会放肉的,油也少得可怜,奶奶却吃得津津有味。
奶奶一个人睡一个很大的炕,她仿佛不知道什么是寂寞。一个大火炕,她睡在最北炕头那边,炕南边放一辆瘸了腿的破旧纺车。一年四季,奶奶都会让纺车唱出自己的歌。那辆纺车应该算是她的伙伴,也是她房子里最值钱的东西。火炕和锅台之间垒起一个小灯台,上面放着一盏小煤油灯。如豆的煤油灯光,也只有在天彻底黑下来才点起。有月光的日子最好,白白的月光,洒在屋子中央,离奶奶的锅台不过尺把远,奶奶就借着这一地的白月光吃饭、睡觉。月光透过窗棂,铺在炕上,照亮奶奶寂寞的夜晚。直到一次骨折,奶奶才搬来与我们同住。
三
奶奶晚年享受着天伦之乐,享受着从来没有过的幸福日子。天天白面馒头,顿顿有炒熟的青菜,不再天天吃自己腌制的咸萝卜了。过去盼望的一切都在自己不再奢望的时候到来。奶奶心中仿佛想到了什么。后来,在奶奶的断断续续的回忆里,我知道了有关爷爷奶奶的故事。
十七岁的花季少年,英俊潇洒,黑亮的眼睛里透着睿智。这个老师学生都喜欢的年轻后生,写得一手好字,打得一手好算盘,不善言语却聪明好学。人们预测着这个少年的未来肯定是个文化人,吃国家饭,是公家的人。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少年春风得意的时候,突然得了一场叫天花的病,发烧,无力,浑身长满疱疹,痛苦的呻吟日夜煎熬着父母的心。有病乱投医,做父亲的不知从哪里听来的土方子,用盐巴搓疱疹,给孩子消毒。不成想,疱疹遇盐反而害了孩子,少年中毒身亡。这少年就是我大爷爷的儿子,也就是我的伯伯。伯伯的死,犹如晴天霹雳,大爷爷满心寄托的希望,一下子成了泡影。
在鲁北农村,大部分人存在着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有儿子的家庭,腰杆子特别硬;有儿子,就能延续香火;有儿子,就不怕别人欺负;有儿子,就能够在祖宗面前好交代。他们信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失子之痛,让大爷爷在村人们的唏嘘哀叹声里,抬不起头来。二爷爷也就是我的亲爷爷心疼自己的哥哥,害怕大爷爷从此一蹶不振,毁了自己,就让儿子过去陪伴大爷爷。
父亲那时候也就五岁。奶奶只有这一个儿子,她心里一百个不愿意,碍于大爷爷刚刚丧子,奶奶也不好当面说什么。大爷爷天天把孩子带在身边,害怕一不小心会把孩子弄丢。陪孩子也成了大爷爷一天到晚的精神寄托,每天除了干活,就是逗孩子玩儿,一个钢铁一样的汉子,在孩子面前温柔似水。在孩子的陪伴下,大爷爷慢慢走出了那段不堪回首的痛苦时光。邻居们也发现,大爷爷再也离不开孩子。再忙再累,只要见到孩子,大爷爷一向严肃的脸上充满笑意,眼睛里闪烁着慈爱与温和的光。
奶奶想把儿子要回到身边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她看见儿子每天都很开心,并不十分想念她。隔了一条胡同,近在咫尺的娘儿俩并不经常见,即使有时间儿子跑回身边,也只是拿了吃的就走。孩子的世界里只有温暖的爱,没有一丝芥蒂。奶奶不能说,也无法跟儿子说什么,本来穷苦的日子,更多了一份没有儿子陪伴的苦。她跟爷爷天天闹别扭,不理爷爷。爷爷是个读书人,生性温和,没脾气,又非常敬重自己的大哥,怎么好再张口把孩子要回来?爷爷忍受着奶奶时不时地数落,也只是默不作声做自己该做的事。奶奶对大爷爷的态度越来越冷淡,甚至在儿子结婚一事上,奶奶用拿不出钱跟大爷爷置气。僵到份上,谁也不让步了,也就真把儿子留在了大爷爷身边。
人大多都是认命的,更何况一个女人。再执拗,也拗不过命运的安排;再执拗,也逃不过大饥荒的那些苦日子。吃了上顿没下顿,一个好几百口人的村子,死的死,逃的逃,走不了的,大多是饿在炕上爬不起来,在院子里出不了门。死了的,尸首无人收,活着的连哭也不哭了,就把死的当睡着了吧。也就在那一年,食量大的二爷爷(我的亲爷爷)饿死了。
作为一个女人,儿子送与他人,丈夫也不在人世,日子该怎么打发?最初的日子,奶奶是怎么熬过来的,她从不说与他人。热闹的家她不羡慕,凄冷的夜她独自熬煎。
四
一腔愁怨无处诉,万分感慨心头雪。
1993年十月的那场雪来得太早,是人们所没有预料到的。棉花还站在地里,上面还开着没有开完的花,冬萝卜还长着它满头的绿缨子,玉米还齐刷刷地列队般站在地里,天空就集聚了仿佛好几个世纪的云,厚得吹不开,掀不动,阴沉得很。后来淅淅沥沥飘起了雨,一下就是半月有余。连绵的秋雨,像扯不断的思绪,分不清白天黑夜,分不清天地人间。十月初,忽然来了一股冷空气,把先前的秋雨一下子冻了个趔趄。哗啦哗啦的雨,仿佛加了消音器,瞬时没了声音。雨夹着雪花,如生出翅膀的白蝴蝶在天地间狂飞乱舞。房顶上,树枝上,沟沿上,雪花所到之处,都留下隐约的白。
踩着泥泞,我天天往返于家和学校。那时候我已经怀孕待产,每天早上捎好一天的饭菜,去二里外的小学去上班。雨雪泥泞掩盖了原来的羊肠小路,我只好循着两个村子之间的盐碱地茬行走。那些盐碱地边上长着绊子草的地方还是能成步的,只是低洼处积水过多的地方,泡了数天,像经过发酵的面,看上去很光滑,一脚踩下去就拔不出来。那时候我的身子重得很,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大约二里来地,最少也得二十分钟,甚至半个多小时。
雨雪天路上没有行人,只有我在天地之间踽踽独行。每天回家晚了,奶奶总会嘱咐母亲到大门外接我,怕我出意外。那个时候全村也没有一部电话,即使真有意外,也不会像现在一个电话就能联系到家人。
十月初六傍晚,母亲擀了我最喜欢吃的面条。奶奶也喝得脑门上汗涔涔的。雨雪天,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喝上一碗炝锅面,胃里舒坦心里也舒坦。那种温暖,一辈子都忘不掉。早来的雪是有柔情的,无声无息,落地为泥,直到天黑,南墙下的积雪才有了些白。
早上还没起床,就听见父亲扫雪的声音。我赶紧起床去看雪。打开门,一种特别刺眼的白,让我忽然有些眩晕。厚厚的积雪铺了一地,树上房子上像一夜之间被画上去的,一尘不染。这时候,父亲小声告诉我,奶奶病了。不知道是雪的白还是听到奶奶生病的消息,我一下子没回过神,再一激灵,我赶紧迈步到奶奶跟前,奶奶微闭双眼,口中不时地溢出血来。那鲜红的血,令我又是一阵眩晕。大雪无声,奶奶亦不出声。
我天真地以为,或许在雪停之后奶奶就会好起来。我心里记挂着学校那些孩子们,也没有太多犹豫,就告别了奶奶,踏上了去学校的泥泞的路。上了一天的课,我的心始终忐忑不安,担心奶奶能不能扛过这场风雪。北风不停地刮着片片雪花,我沿着雪花飞来的方向望去,茫茫的雪花那边就是我的村庄我的家,还有我生病的奶奶。回家的路,我步履蹒跚,却心急如焚。迈进家门,人们进进出出忙碌着给奶奶做火烧,做打狗棍,做放米的罐子。奶奶安静地躺在灵床上,戴上了冬天最常戴的黑平绒遮耳帽,睡着了一般,面色肃静。她不再惦记我,惦记我即将出生的孩子了。奶奶重回孤独,她不害怕。起灵的时刻,大片雪花如扯不断的棉絮,铺天盖地飘落下来。是灵幡,是呼唤,还是爷爷的絮语?再次相见,他们是否不再提及当年?
奶奶下葬的第二天,天大晴,我的儿子降生。生命的起承转合,在一场雪中完成。
来世间化雪为泥是雪的宿命。也总有那么一场雪下在心头,下在记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