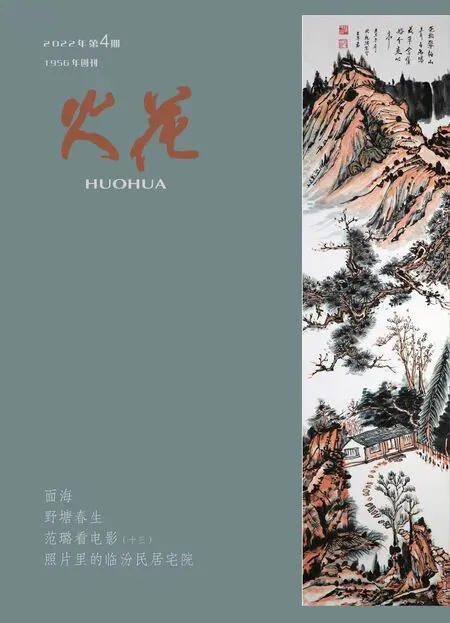面海
2022-06-16王淼
王淼
上篇
黄明望起身,走到那扇边角满布灰尘的方窗面前,望向数百公尺外的一片风景。远方的天空与海具有一种灰色的基调,掺杂着模糊的白与暗蓝,像是干硬的水彩颜料被调和在一起,与海岸的边坡上头几幢民宅、布置显眼的民宿,构成一片低彩度的冬日景象。
再过几天就是除夕了,黄明望想。大约一周之前,他才好不容易自忙杂的桃源市区中抽身,搭上数小时的客船来到这儿。
一月的空气又冷又湿,强劲的海风吹得窗框吱嘎作响。他默坐在床沿,置放在一旁的木制书桌上头积了浅浅的一层灰。那张低矮的单人床铺紧抵着墙,上头的被单才刚换洗过,因此显得干净齐整。其中一面玻璃脱落的木制书柜及一旁书架上的书籍和物品则早已丢弃,或者转送给他人。黄明望再次环顾这个他生活了十余年的住所,同时有股熟悉及疏离的交杂情绪自心底升起。
走廊底突然传出一阵点状而紧凑的脚步声,接着在他敞开的房门前停下。他的大黄狗——泥巴正晃着尾巴,以那对棕色的眼珠望向黄明望。他走向前,同时俯下身子,以手掌沿着泥巴头部至颈背的方向抚去。
“噢,泥巴。”黄明望喃喃地说。自从它年纪渐增之后,就不曾再像从前那样,跳上陌生人骑乘的摩托车,随之在岛上四处兜转了。
黄明望走下楼,他的黄狗泥巴紧随其后。
厨房的火炉开着,上头置放一锅方形的陶瓷容器,不断有蒸气自玻璃锅盖的缝隙间窜出,里边的白粥正沸腾冒泡。黄明望从柜子里取出数个瓷碗与碟子,并抽出几副木筷,将它们摆放到店里的木制小方桌上头去。
这间餐馆坐落在沿着缓下坡道而建的巷弄里头,整列的家户前方铺着方形石砖,连接主要道路旁的小型市场,一路通往低处种植作物的小径。店门口的狭长磨石子地板上,常年堆放了数个水桶与扫具,并牵起细绳挂放抹布。高处则吊着一副挂牌,上头写着:黄赶场料理。
店长黄赶场经常出海。遇到海象不佳的时候,渔获往往非常惨淡。
“每条我所捕获的鱼都来自、也属于那片大海,没有人能够因此而责怪,或索讨什么。”他常这样对身旁的人说。店面不甚大,仅能够容纳下四张大圆木桌,以及一面靠着墙的小方桌。旧黄的墙壁上粘贴着暗褐色的价目表与数张海报。空闲的时候,他们一家人便会聚在那儿一块看电视。
黄赶场将那一大锅粥自厨房里拿了出来,而黄明望的母亲周孝素则在后头拿上几个罐头与数只小汤匙。他们面对面坐下来,泥巴的身躯偎在黄明望脚边。父亲黄赶场将罐头里的腌渍食品添入碟子中,随后又盛了一勺锅里的稀粥,倒盖进手掌大小的瓷碗。
他们静默祝祷了一会儿,才开始用饭。自小,黄明望一家便有这样的习惯,在开饭之前,于心底默念一段祷词,或长或短。然而这并不全然与宗教信仰有关,或者说一直以来他们所信仰的,便就只是信仰本身。
黄明望将电视打开,转到新闻频道。上头正播放近日寒流来袭的相关讯息。
“最近的确是愈来愈冷了,外头那个塑胶桶内壁与里边的水交界处,甚至都结上了一圈薄冰。”黄赶场首先发话。
黄明望没有应答,过了一会儿才说:“来这里的路上,我有发觉海风比以往潮湿,而且更冷。”
黄明望抬头望向父母的脸庞,发觉他们似乎更加衰老了。父亲黄赶场身上穿一件无袖汗衫,外头披上薄外套,双脚踏踩着拖鞋。母亲周孝素仍穿着昨晚的长袖棉质睡衣。
“最近店里的生意也很差,或许大多数的人都回内地过年了吧!”周孝素说。
自从黄明望到北京读高中,后来上了大学后,便愈来愈少与家里联络。刚开始还会定期打电话或传讯息问候,过节时偶尔写信回去。之后往来的频率便逐渐减少。去年黄明望刚大学毕业,找了一两份工作兼职。黄明望回想,距离上次回到这里,似乎已是两年多前的事了。
“今天清晨我自己去海上垂钓,几只鲈鱼和黑鲷上了钩。”黄赶场说,“天空仍然阴阴的,云压得很低。昨天半夜还下大雨,外边看起来与起雾没两样。”
黄明望看见圆木桌上摊放几张浸湿了血水和碎冰块的旧报纸,同时想起,之前曾随着父亲在傍晚出海的片段。
那时下着若丝的雨,仅能透过小船上的灯源与露出在外的皮肤,感受到落下的冰冷雨点,而天空的大半边已然暗了下来。父亲黄赶场正神情专注而谨慎地控制手中的钓竿,调配来回拖动与收线的力道,准备待鱼力耗竭后再大力出手。
透明的线绳在暗黑水面上不断拉扯与折返,并间歇地反射微弱之灯光。
一段时间后,一只跳动不已的沉重身躯落到甲板上来,黄赶场将它收进潮湿的渔网中。黄明望盯着它发亮的鳞片与圆睁的光滑眼珠,全身开始冒出冷汗。
很多年之后,他才渐渐地、很粗略地了解到那鱼那时的不安,其中还带有点敬畏的成分。
黄明望将碗碟叠起,并去外头拿湿抹布擦拭桌面。黄赶场起身步向厨房,清洗水槽里的脏碗筷。
母亲周孝素上楼换外出服,准备上市场买些蔬果。“黄明望,你要陪我一起去买菜吗?”周孝素朝楼下喊。
“不了,妈,我带泥巴出去逛逛。”黄明望说。他在那件薄外套外头,再套上一件厚羽绒衣,并戴上一顶毛帽。他摸摸泥巴的头,示意它朝外走。
黄明望沿着坡道向上,经过相邻的几间家户。这排十余间住家,除了黄赶场开设的餐馆之外,还有贩卖药材、冰品和杂货的店面,都是以住宅的形式,里头的布置未经过多改动,就直接当作店铺。两侧的店家都只在门边高处挂上小小的招牌,从外头看来毫不显眼。
他小学以前,最喜欢去到那间招牌上画有人形般侧卧的米黄色人参、店里堆满成排木抽屉和各式玻璃瓶罐的中药材店。那里的老板常常将双脚倚在一竹编凳子上方读报,并让黄明望坐在旁边的木板凳上头,陪他聊天或一起看电视。有的时候,他会从柜台的铁柜里,拿出某种有梅子味道的、指甲盖大小的糖,那样的滋味总会让他想起切块芭乐上头撒的甘草粉。
此时,冬日的阳光温煦又淡薄。这座邻近海岸的村庄沿着山丘而立,作物与住宅之间的小径十分狭窄,多处设置的阶梯边,铁栏杆和地面上爬满了锈褐色的水渍。许多人家在阳台花砖的围墙上方晾晒衣服,光线穿过冷湿的空气,向下透在瓷砖地与湿润的墙角边。一起风,挂置着的衣物便都鼓胀起来。
在此道路不宽、体积也不甚大的离岛上头,代步工具几乎都以自行车和摩托车为主。若不是要到岛另一头的市区去,附近一带的居民平常只徒步行走——在楼房、菜圃、杂草和电线杆之间穿梭,不时能够聆听几声鸡啼与鸟类拉长断续的叫声,显得缓慢复又静寂。
黄明望走到一处住宅之间并不宽敞的空地,约摸只是两户相邻住家的占地大小。这儿停放了附近居民的单车与摩托车,泥灰色的混凝土地上置放着许多大型盆栽——缅栀花、大花曼陀罗、树牵牛、南美假樱桃……与一些杂生的低矮灌木。天气晴朗的时候,邻居们便会在靠墙的一侧,晾晒自家的厚棉被与被单。
他将那台父亲的银灰色单车牵出来,顺道至一旁光线昏暗的杂货店买罐常温运动饮料,同时将它卡进车身上的铁制水壶架。
他将单车向上牵至高处的主路后,才跨上坐垫,并让泥巴跟在后头,开始缓慢地踩动踏板。
下篇
瓦瓦住在一间独栋的铁皮低矮楼房里头。每天清晨,他的父母会将近几天来捕获的冷冻渔货和一些甲壳类海鲜,载运到市场里,并在垫着帆布的石桌上方,将冰块铺满整个台面,塑胶篮子则叠置在一侧的湿黏地板上,融化后的腥臭冰水会直接流进前方的排水渠道里。不过,处理食材的平台上方一直有清水流过,冲洗沾满血污的刀具和砧板,溢出的脏水不断泼溅到地上,瓦瓦的父母因而需要穿上雨鞋工作。
瓦瓦经常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等待清晨时分就出门的父母,在夜晚打理完一日的扫除作业后归来。
那时,黄明望每天上午都要步行到他家门口,再使劲按着一旁的电铃或拍打铁门。待瓦瓦出门之后,他们便会各自骑着那两辆蓝白色与铁灰色车身、上头塑胶膜没有拆除的单车约二十分钟的路程,到达位于海岸边的小学。
瓦瓦的身型瘦小,眉毛杂乱而粗黑,深色的脸上那连着长睫毛的眼睑覆盖住眼球上方;耳前推平的短硬头发紧贴面颊,一对高又宽大的耳朵轮廓外翻;笑的时候,长板状门牙时常露在外边。旁人常说,他只要再系上几条色彩纷呈的手链与脚链,便像是涂上彩漆的泥雕像了。黄明望总是觉得,他看起来的确像是那么一尊小小的神祗。
那间临海而建的学校只有两层楼高,廊柱边上的白漆长年受到潮湿海风的吹拂而剥蚀,空气总是溽热又闷炽。每周大约有一两天,黄明望和瓦瓦将外衣裤塞进背包里头后,便会径直翻过操场侧边低矮的竹围篱,去到学校旁的海岸潜水,或者在潮间带滞淤的海水中捡拾一些海洋生物。
闲暇的课余时间,黄明望除了偶尔留在店里帮忙,就是与瓦瓦一起跑遍这座岛上的山和所有的海岸。
他的泳技还不错,多数时候,黄明望总会想象自己是长年生长在砂土中的柔软水草,随着数条大小不一的鱼,在穿入的光线里游动与摇摆。
平日,黄明望与他在岛上探索的行程都是没有特定目标的,他们因此一致认为自己并不在找寻什么,而比较接近于发现。他们曾经骑着单车到岛上最高的那座山丘,并在昆虫的鸣叫声中,指认天上的星星。回程的路途上,还在间隔遥远的晕黄路灯下,与直飞而来的金龟子迎面撞击。
数天以来,黄明望常循着山丘的道路向上爬升,或者沿着海岸线骑乘。他的移动缓慢而接近于漠然。“你看。”黄明望对着泥巴说。他将单车倒倚在贴向一侧的长杂草上方,空气中混合着羊的排泄物和泥土的潮湿气味。他们坐在一处湾澳边的临海悬崖,并在那儿望向不同程度深浅的灰色云层。直到后方那片打散的水红色阳光淡去,潮湿的灰蓝转浓,才起身往家的方向而去。
最近店里的生意非常冷清,往往一整个下午都不见任何客人上门。除了黄赶场仍然按照平常的作息,附近的几间店家在清扫完家户内外之后,就都拉上铁卷门暂时停业。
黄赶场习惯在上午一边播放广播电台,一边整理手上清晨出海时使用的钓具,或将瓶装酱油依次分装进塑胶罐子里头。周孝素则在一旁打理其它的事务,偶尔抬头望向墙上静音的电视。
圆桌上的铁盆里装盛一些肉品和叶菜,零落的葱姜散置在一旁。那台老旧的国际牌收音机持续地播报着,里头传出的歌曲和舒缓的谈话声像是某种冷淡的气味,与纱门穿渡而入的阳光一同向下沉降。
每天午饭过后,黄明望便会拿出纸拖把,来回沾黏房间地板上的尘灰和毛发。他四处走动时,地板鞋拍在地面上发出间续的响音。多数时候,他会半倚坐在床边回讯息,同时点开音乐串流,任由连接蓝牙的移动式音响连续播放。有时他便什么也不做,桌上摊着他带来的几本书,就这么从那扇窗子望向远处那从来不曾改变的风景。
连日的阴雨似乎并没有要暂缓的迹象,空气非常湿凉,雨滴落在靠近坡道那侧的窗沿上,敲击着半透明的浅蓝绿色建材。目所能及的景物都在接连而至的雨水中发出各样声响。远处的雨线要落得慢一些,散射的阳光自云层的缝隙间穿透而下,在灰蓝的海面上形成流动的破碎光块。
这里不管在哪儿,都可以见得到海,黄明望心想。他在台北的这几年来,时常只能够望见割划成块状的灰色天空。他承租的小套房在一间转角处的便当店楼上,就位于一块深棕色大型招牌正后方。广告牌的横条阻挡了大半阳光射入,他的居所因此阴暗又潮湿。黄明望有时会望着那扇积满灰尘、加装了铁栅的窗户,觉得自己也许就在这座城市的反面,在数条弯折的亮黄色霓虹灯和一块巨大的广告牌背面。
黄明望在这段时间里时常沉默不语,他的父母每晚在十点之前,就将自己房间的灯熄灭,木门上方那片方形的毛玻璃因而不再透出光线。狭窄的走廊顿时暗了下来,只剩下那盏圆形的黄色壁灯仍提供微弱的照明。泥巴常常蜷缩着身躯,偎在床头边电暖炉附近的磁砖地板上取暖,很快就打起盹来。黄明望仍旧习惯熬夜,直到睡前才走向浴室冲洗身体,然后躺回床上闭眼休息。
除夕当天晚上,黄赶场和周孝素忙着在厨房里备料和炒菜,墙上的电视不断播送节目。黄明望将门口的日光灯打开,发出一种噪声般的滋滋声响。不久后,数只昆虫和蛾类扑翅前来,在长条灯管附近周旋不去。
黄明望取下挂置在门边衣架上方的厚外套,与泥巴一起步出家门。连下了数天的阴雨此时终于暂歇,空气仍然非常冷冽,上空的云层遮去一部分的星星和月光,踩在湿润的泥土地上,不时会发出挤压空隙的短促水声。他们朝海岸的方向走,那栋临海民宿的饭厅只余下半开的灯光,里头传出老板和他朋友的谈笑声。
在经过一间不过平方米大小的庙宇后,黄明望跨坐在立灯下方的堤岸,投下的昏黄光线切割出数道阴影。靠岸处有几艘小船停泊在灯光所不能及的地方。泥巴与他一同面向沙滩后方那片无尽的漆黑。
远处的渔船缩为数个光点,以无法觉察的速度向远方驶去。
黄明望想起,他曾经在一个清晨见过出租屋外边的那条街道,那样静止而安静的风景就好像是从观景窗的方框里向外望出去一样。之前的某个夜晚,他也曾在夜半下楼喝水时,发现家中楼梯间昏暗的灯光穿过其侧之玻璃,透映在厨房靠近外侧的窗和墙壁的那片浅淡满月状光块。
黄明望闭上眼,在心中描摹海的样态。天空似乎又开始飘下细雨,他仔细聆听海浪拍打的声响与气味。往后,他会尝试在黑暗之中时常默诵与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