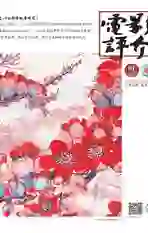诺兰的幻影宇宙:论三重学科对科幻银幕的支撑
2022-06-11谢燕红李刚
谢燕红 李刚
叙事就是讲故事,[1]但讲好一个故事,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讲故事的人来说,在决定如何讲述故事前,首先要寻找故事的素材。一般来说,故事素材多来源于讲故事人在某一生活领域的实践经验,例如,司汤达从军、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流放、王蒙下放、张贤亮劳动改造等,这些直接的经验为古今中外的作家提供了丰富的故事素材。但正如很多作家所苦恼的,能够作为故事素材的直接生活经验总有枯竭的时候。来自书本的间接生活经验虽然也可以作为故事素材,但相比前者,在细节的生动性、丰富性、情感性上多有欠缺,连张艺谋这样善于讲故事的导演在谈到中国电影产业问题时,也不免感慨:“我个人觉得是剧本荒,好剧本太少了!”[2]衡量一个剧本好坏的重要标准无疑是看它能否讲好故事。
在各种电影类型中,科幻电影在讲述故事时,可谓难乎其难,因为题材的未来性与想象性,讲述者缺乏所谓的经验。《电影艺术词典》将科幻电影定义为:“科学幻想片,简称科幻片。以科学幻想为内容的故事片。其基本特点是从今天已知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成就出发,对未来的世界或遥远的过去的情景做幻想式的描述。其内容既不能违反科学原理凭空臆造,也不必拘泥于已经达到的科学现实,创作者可以充分展開自己的想象。违反基本科学原理的幻想式的或现代神话式的影片,不是科学幻想片。”[3]由此定义可知,科幻电影重在描述未来科技发展的多种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讲述故事不再重要,相反,因为科幻电影需要向观众展示一个复杂的未来世界或科学理论的发展,借助一个圆融而通俗的故事载体显得尤为必要。否则,不仅观众无法理解电影描述的科学世界,科幻电影也等同于科学纪录片了。由于故事素材在现实生活中无法直接取得,科幻电影的故事讲述就具有相当难度,处理不当,要么沦为科学元素的附庸,故事变得无关紧要;要么无法讲清楚电影描述的未来科技,让观众看得一头雾水。能否在科技描述与故事讲述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是科幻电影成功与否的关键。近年来,克里斯托弗·诺兰操刀的科幻电影,从《盗梦空间》《星际穿越》到《信条》,获得了从普通观众到电影研究者的称赞,诺兰成为当今科幻电影的现象级人物,被称为“新千年的库布里克”。诺兰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他用电影的形式诠释了他对前沿科技的深刻理解,更取决于他用镜头讲述了逻辑严密的故事,而这些故事是由科学、哲学、人学三个维度共同支撑起来的。
一、科学:情节发展的驱动力
科幻文艺作家赫伯特·W·弗兰克认为:“科幻电影所描写的是,发生在一个虚构的、但原则上是可能产生的模式世界中的戏剧性事件。”[4]科学理论本身不具备戏剧性,它是缜密的实验论证与严谨的逻辑推理的结果,这就与电影所要求的故事戏剧性产生根本冲突。此外,科学经验是绝大部分观众所不具备的实践经验,科学经验若要进入可作为电影故事素材的大众经验层面,有赖巧妙的转化。在实际操作中,这种转化经常被简单化处理,如争议颇大的电影《上海堡垒》便是一例。这部电影可简化为地球人击退外星人侵略的故事,片中虽有一些科幻元素,如对外星飞船、上海大炮的设计与想象等,但如果剔除这些元素,故事仍然可以成立。因为主题和剧情都是传统的战争题材电影的通常设计,电影情节的发展并不依赖科学理论来推动,甚至可以将这部电影视作披着科幻外衣的抵御外族侵略的战争片。反观诺兰的科幻电影,就恰当处理了科学与剧情之间的关系,如果去除科学元素,诺兰的电影便无法成立,科学与故事成为一个圆融的整体。也就是说,诺兰科幻电影的步步推进,是通过科学理论或技术来推动的,一切都与关于未来的科技想象环环相扣。
作为科幻电影,情节应为探讨未来科技服务,科学需成为情节发展的推动要素,而不是相反。在《星际穿越》的开头,主人公库珀送一对儿女上学,在路上发生了两个事件,第一是汽车在路上爆胎,第二是发现了一架飞行了十几年的无人机。汽车爆胎后,女儿墨菲埋怨父亲给她取的名字,这就引出了与“帕金森定律”和“彼德原理”并称为20世纪西方文化三大发现之一的“墨菲定律”。墨菲定律指的是: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往往会发生。女儿不愿意被称为“坏事”,而库珀则要女儿关注“可能性”。库珀对可能性的强调构成了他未来种种行为的性格因素或动力,无论是后来寻找地球外可生存星球、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与损坏的飞船对接,还是飞入黑洞,都因其相信某种可能性的存在。作为统计学原理的墨菲定律,在影片开头的呈现即为后续情节埋下了伏笔。因为无人机的电池可以为整个农场提供电力,在发现无人机后,库珀便带着儿女开始一段捕捉行动。无人机在无人干涉的情况下,依然可以依靠太阳能电池在空中飞行十几年,这是新能源技术在未来的发展和应用,但通常飞行在万米高空的无人机却大幅降低了飞行高度,从而可能被库珀所捕捉,显然是太阳能电池的动力已经不足以维持它在高空飞行,并且由于地球环境的恶化,GPS导航也无法发挥作用,果然随后便出现无人收割机失灵与库珀一家躲避沙尘暴的情节。由此可见,地球磁场的变化影响到无人机的航向,而沙尘暴则令无人机的太阳能电池无法再吸取能量,情节的发展完全合乎科学事实。库珀最终接受NASA的要求,是他亲眼目睹地球即将无法生存的证据,对他来说,只能放手一搏,才能为家人争取到未来生存的可能。诺兰对墨菲定律的理解,以及对可以飞行十几年的无人机的科学想象就这样完美地推动了情节发展,这也是诺兰科幻电影与其他类型电影在情节驱动上的重要区别。
《信条》依然延续了诺兰一直以来的叙述搭建方式。时空穿越型的科幻电影始终是好莱坞所青睐的主题,罗伯特·泽米吉斯指导的《回到未来》系列、詹姆斯·卡梅隆指导的《终结者》系列都是时空穿越电影的经典之作。在这类电影中,故事的主要框架往往依据法国科幻小说作家赫内·巴赫札维勒在小说《不小心的旅游者》(1943年)中提出的祖父悖论以及平行宇宙概念。问题在于,尽管有时空穿越的科学理论作为故事背景,上述电影只是将其作为情节的转换方式,在时空穿越这个行为完成之后,各个角色会在另一个时空中正常行动,如同我们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一个地方,影片很少再讨论时空穿越这一未来科技对角色在穿越后的行动所施加的影响。即便如《回到未来》与《终结者》系列,时空穿越的理论也没有得到深刻的展示,除了回到过去和未来这个大背景,时空变换没有能够影响角色在未来或过去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在完成穿越之后,情节发展、人物行为就与时空穿越理论分道扬镳。《信条》的情节不仅因时空穿越而产生,穿越之后的行动事件也直接由时空理论推动。为此,诺兰专门设计了物质的逆向行动。在一段汽车追逐戏中,女主角被困在一辆高速倒行的车辆中,因为女主处在逆向时间中,从她本人的视角看,她是在正常行驶,但对身处正向时空的人来说,这辆车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两车车头相对的逆行,而是两车车头相向的逆行——前者所谓逆行是同一时空中相对于道路的逆行,后者才是相对时间的逆行。这一行为方式在以往的时空穿越电影中从未得到表现,时空穿越也从未影响角色的行动。在诺兰这里,产生了与穿越行为相对应的故事情节,他不仅大胆想象了时空穿越的科学理论,而且在故事情节的微观层面呼应和印证了该理论。在电影结尾处,尼尔从死亡状态复活,为主角开门的情节也是逆行时空理论的合理设计,可以设想,如果男主角利用枪械工具等其他方式把门打开(这往往是大部分科幻片的简单做法),情节虽然也是合理的,但科幻的效果显然会大打折扣。科学在诺兰的科幻电影中不是单纯的背景,也不是简单的故事框架,而是实实在在影响情节发展的关键要素,反之,电影的故事情节也恰如其分地解释了科学理论本身。我们常说诺兰的电影“烧脑”,因其展示了高深的科学理论,而由科学所推动和承载的故事在本质上根本不可能由浅显讲述来完成。
二、哲学:叙事立意的升华
诺兰的科幻电影,特别是近年来赢得极佳口碑的《记忆碎片》《蝙蝠侠三部曲》《盗梦空间》《星际穿越》和《信条》,不是一种简单的科学叙事。诺兰提升了故事的立意,融入关于人类生存、社会发展的哲学思考,其电影叙事也就成了一种哲学叙事。
英国通俗文学研究学者斯特里纳蒂曾经说过:“大众文化是通俗文化,它是由大批工业技术生产出来的,是为了获利而向大批公众销售的。它是商业文化,是为大众市场而大批生产的。”[5]作为一类大众文化,科幻电影也难以突破所谓“获利”的困境,为大众提供娱乐而非意义是好莱坞电影信奉的准则,正如阿尔特曼所言:“关于类型片的任何概括性理论都必须从这样一个事实出发:即好莱坞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一种娱乐形式。”[6]科幻电影的娱乐性集中体现于导演对于未来科技的想象以及各种刺激性场面的展示,观众沉浸其中,对科幻电影的追捧也就乐此不疲。但摩里塞特也认为:“一部叙事作品如同一幅画一样,首先要有一个视点来给它提供表面的合理性和意义。”[7]没有意义的叙事是没有灵魂的叙事,制作一部纯娱乐的“爆米花”电影从来不是诺兰的追求。《记忆碎片》对理性至上主义的批判,《蝙蝠侠三部曲》对难以维序的准则与权威的理解,《星际穿越》对传统思想同一性的质疑等等。[8]类似的哲学思考和文化批判在整体上将电影提升了一个层次,在叙事建构中升华了故事的立意。
2010年上映的《盗梦空间》,或许是诺兰科幻电影叙事哲思体现最为明显的一部。电影剧情游走在梦境与现实之间,被誉为“发生在意识结构内的当代动作科幻片”。该片通过对人的多层意识的定位,讨论了真实存在与意识存在的哲学命题。关于人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才是真实存在的问题,多部好莱坞电影都有讨论,《超能查派》把人的意识转移到机器人里,《阿凡达》把男主角的意识转移到外星人身体里,类似设计层出不穷。在上述电影中,当意识被转移到一个新的载体后,原先承载意识的身体实际已经失去了效用,完全可以被舍弃。这种对意识转移的设定在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如《黑客帝国8:我,机器人》中有过深刻的思考与表述:“赛博格形象展现了后人类社会可能出现的人类离身性问题、可能遭遇的人性和道德危机。”[9]但上述电影却未能较好地延展这一话题,它们对意识的转移叙事更像一种达尔文式的进化,呼应的是现实社会中人们祈求个人能力不断提升的世俗欲望,“乌托邦”想象效果甚于哲学思考。在《盗梦空间》中,诺兰的哲思与阿西莫夫不谋而合,指向的是人的真实存在与当下存在的意义,而不是通过意识转移或进化将人本身予以抛弃,毕竟“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0]柯布在多层意识领域穿梭,最终目的是回归现实世界。诺兰通过这样的故事搭建提醒观众,科技无论多么发达,都是为人类服务的,都是以现实生活为旨归的。人自身存在,科技才有意义,人类需要活在当下;脱离肉身的纯粹意识领域不啻人类的灾难。这样的哲思是具有情怀的哲思,也是有温度的哲思。
有这样的哲学立意,诺兰科幻电影最终指向貌似遥远的未来,实则是活生生的当下。《星际穿越》为人类寻找到新的家园,无论这家园如何具有科技感、未来感,人之所以为人的属性始终不变。库珀的故居在未来空间站被原汁原味保留下来,不仅仅是为了向做出巨大科技贡献的墨菲致敬,也是用历史提醒人类,我们曾经的样子以及我们未来应为的面貌。《信条》中阻止未来人指挥萨特企图毁灭人类的行动,凸显了诺兰对当下的重视:哪怕没有未来,也要保证当下的现实生活,因为没有当下便没有未来。他对“熵”这个物理概念的哲学思考更印证了这一点,随着“熵值”的不断增加,混乱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也意味着未来是一个混乱的世界,对“熵”的逆转是通过否定未来从而肯定当下来实现的。诺兰的科幻叙事遵循着这样的哲学原则,即“哲学有着同一个出发点和落脚点,那就是人及其现实生活。”[11]由此,科技才不是冷冰冰的科技,故事也不纯粹是科技的故事,而是关系活着的人以及我们生存的世界的故事。
三、人学:成就故事的情怀
当代西方的人学思想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提倡关怀人、尊重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以及主张人格平等、互相尊重的人道主义。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学思想在欧洲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王权与神权以及资本主义扩张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自那以后,人学思想始终贯穿西方文学、艺术的各类作品。诺兰通过人学思想在电影故事中的注入,呼应了西方数百年来的人文价值观以及20世纪以来对唯理主义的批判,正如他接受采访时所述:“一边是宏大的宇宙,其规模之大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是人性,他们在这个铁皮船里要如何生活,这样会产生何等鲜明的对比。”[12]诺兰的科幻叙事反对“人道主义的僭妄”,营造了令人感怀的人文情怀,具体体现为开拓精神、牺牲精神和重情精神。
从本质上看,《星际穿越》可谓向16世纪开启的大航海时代致敬的作品,与《加勒比海盗》系列、《怒海争锋》《哥伦布传》《金银岛》《鲁滨逊漂流记》等反映大航海时代的电影相似,都是对资产阶级早期开拓冒险精神的认同与传扬,只不过该片将航行的方式由跨越海洋演变成穿越宇宙。此类主题的电影由于塑造了小资产阶级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展示了所谓独立、自由、合作的西方普遍價值,一直占据西方电影的主流地位,好莱坞更是将这种开拓精神与“美国梦”的实现联系起来,使之成为国家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宣传。在叙事重点上,这些影片又各有侧重,《加勒比海盗》系列、《怒海争锋》等突出表现主人公如何战胜和克服海洋的滔天巨浪,《鲁滨逊漂流记》则讲述新兴资产阶级在经过漫长旅程后如何在一个陌生和荒芜的环境中独自生存与发展的故事。在《星际穿越》中,诺兰将其进行整合、融通,从而将资产阶级的开拓冒险精神作了完整表述。电影中最打动观众的一个情节无疑是库珀驾驶飞船与受损的空间站对接的过程,配合汉斯·季默大气磅礴的配乐,影片将宇宙航行的极度危险与人类坚强不屈的伟大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女主角布兰德、反派人物曼恩孤身一人在一个陌生的星球建立殖民地的故事,无疑是鲁滨逊孤岛生存的星际版本,只不过前者继承了鲁滨逊的开拓精神,后者则成为开疆辟土中“小我主义”批判的对象。韦伯将清教伦理精神视作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信仰,这是因为清教徒始终怀着一种使命感、神圣感在创业,把开拓疆土、扩大产业、增加财富视为天职。《星际穿越》的动人之处也正在于此,该片将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开拓故事粘连在一起,塑造了星际时代新的航海英雄,由此激发了观众感同身受的思想情怀,与西方数百年来坚持的社会精神与价值观形成共鸣。
与开拓冒险行为并行的牺牲精神,实现了电影的大众煽情效果。这是英雄主义电影的通常做法,也是引发观众情感投入的最有效的手段。英雄主义电影往往为了满足观众爽快的观影体验,一是在叙事上会设置一帆风顺的故事情节,英雄无所不能,无往不利,而反派一击则溃,最后皆大欢喜。观众虽然在观影过程中充分体验了酣畅淋漓的观感,过后却无法留下深刻印象,因为这样的情节往往缺乏深度。二是塑造悲情英雄的形象,以悲剧的方式来展示英雄的牺牲精神,此类电影或许可以获得口碑,“爆米花”味道却不浓郁。诺兰在牺牲故事的设计环节上,体现出他的巧思,其英雄主义叙事中的牺牲精神往往带有“主角光环”,可称之为“半悲情主义”。《星际穿越》中,库珀为了给布兰德留下生的希望,只身一人进入黑洞,这确实是一种牺牲精神,但此后的故事如我们所知,库珀也因此拯救了地球,并与女儿重逢。《盗梦空间》中柯布为了保护队友撤离,主动选择被困梦中,当然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柯布最终也脱离了险境。《信条》更是如此,一开始主角为了保守秘密,宁可自杀,却因此经受了考验;结尾处尼尔也是主动选择牺牲自己,才为无名氏打开了那扇门。诺兰电影大幅度渲染牺牲精神,一方面唤起了观众对英雄的同情之心;另一方面,当牺牲成为胜利的敲门砖,或者说故事转折的节点,牺牲也带来了行动最终的成功,由此观众既看到牺牲的意图和行为,实现了悲剧的“移情效果”,又与主人公共同体验了任务完成之后的成就感。
有一部分科幻电影被称为“硬科幻”,改编自刘慈欣同名小说的《流浪地球》即被视作典型的硬科幻电影。硬科幻电影以追求科学(可能的)的细节或准确为特性,核心思想是对科学精神的尊重与推崇,刘慈欣计算机高级工程师的身份,保证了《流浪地球》的科学严谨性。诺兰导演《星际穿越》与《信条》时,聘请了加州理工学院的理论物理学家、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基普·索恩作为科学顾问,由此确保了片所涉及的各种科学想象的自洽性。但硬科幻电影如果仅仅局限于对未来世界的科学建模,满足于通过各种电影特效凸显科技的未来感,科技会因缺少情感的支撑而变得冰冷乏味。《盗梦空间》中的爱情、《星际穿越》中的亲情、《信条》中的友情都体现出诺兰科幻叙事中的重情精神,并响应了美国生物学家戴维·埃伦费尔德的呼吁,即理性应加强与情感的合作,这里所谓的理性也包含科技至上主义的认知。由此看到,在《星际穿越》中,诺兰将父女之爱视作一种量子力学,这或许还不能完全被观众所理解,但的确将故事的情感推向了高潮。在近三部科幻电影中,《信条》的兄弟之情或者说同事之谊表现得不如前两部那么动人,这也是《信条》最受质疑之处。无论是《星际穿越》还是《盗梦空间》,都将情感作为故事发展的主线之一,并在电影中以各种方式进行展现,而在《信条》中,友情并未贯穿始终,当观众看到结尾处,才对无名氏与尼尔的友情恍然大悟。无名氏看到尼尔离开时流下的眼泪没能给观众足够的时间体味,电影便结束了,这或许是《信条》在情感叙事上的不足或缺憾。
无论是小说家还是电影编剧,在讲故事的能力上总有一天会江郎才尽。很多文艺作品被批评为图解政治或者图解理论,原因多半于此。科幻电影也会出现“图解”的问题,从而导致科学问题与故事叙事的脱节。诺兰的科幻电影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答案,毕竟科幻电影所展示的未来世界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无法形成经验的,问题并不在于“图解”,而是如何“图解”。诺兰的故事将想象中的经验与现实中的经历有机结合,正如他自己所说:“一切不会无中生有。这些创新不仅拓展了叙述的边界,也考验着观众的认知能力,更需要在传统与创新之间保持平衡。”[13]当科学、哲学与人学三者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支撑,一个令科学家、电影人和观众都满意的科幻电影叙事便水到渠成。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259.
[2]张艺谋.我等米下锅啊,好剧本太少[N].大河报,2012-03-02.
[3]电影艺术词典编委会.电影艺术词典[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18-19.
[4]张东林.科幻电影:在幻象与本体之间[ J ].电影艺术,1994(01):40-45.
[5][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文化和传播译丛:通俗文化理论导论[M].阁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6.
[6][美]查·阿尔特曼.类型片刍议[ J ].宫竺峰,译.世界电影,1985(06):74-86.
[7][美]布·摩里塞特.“视点”论[ J ].闻谷,译.世界电影,1991(02):35-62.
[8]王传领.克里斯托弗·诺兰电影的文化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7:86-96.
[9]劉晓君,谷红丽.《硬科幻小说的复兴》中的后人文主义思想探析[ J ].外国语言文学,2020(03):249-259.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11]徐彦龙.论哲学的现实旨趣及生活价值[ J ].北方论丛,2019(03):120-125.
[12]Mtime时光网.独家专访克里斯托弗·诺兰——“探索新世界是我们的本性”[EB/OL].(2020-09-17)http://news.mtime.com/2014/11/06/1533672-all.html.
[13][荷兰]米克洛·凯斯,孙永君.在克里斯托弗·诺兰《盗梦空间》中作为叙事观念的叙述转喻[ J ].当代电影,2017(01):85-88.
【作者简介】 谢燕红,女,江苏常州人,常州工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李 刚,男,江苏徐州人,江苏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