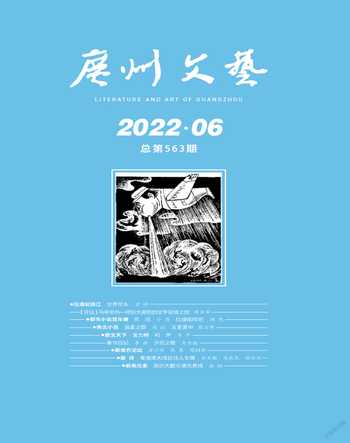夕阳之歌
2022-06-07吴佳骏
吴佳骏
雷 鸣
浓云低垂下来,像天空做的一个梦。远处的山梁上和近处的树巅上都铺满了黑色颗粒状的东西,整个天地之间都被一种不安的氛围笼罩着。风在不断地盘旋和叫嚣,复仇似的折磨着这个春末的乡村黄昏。夜就要来临了,有两只蝙蝠倒挂在瓦檐下,好似在等待着什么。沉睡了一个冬季过后,它们在怀疑自己是否还能飞翔。其中的一只,刚张开它披了黑纱的双翅,想贸然闖入黄昏的怀抱。这时,它听到从远处传来一阵隐隐的雷鸣。它迅速收起黑纱,犹豫而谨慎地把自己裹紧。
比蝙蝠裹得更紧的,是坐在瓦檐下一个表情木讷的男子。他的脸膛黝黑,像是才出窑不久的一个变形陶罐。许多年以来,他就那样孤寂地坐在那里,沉默着,自己跟自己守孝似的。他的母亲尚在世时,兴许是见他可怜,每天夜幕初降时分,都要端张凳子紧靠他坐着说话——她说记忆中没有雪的冬天,说晚霞映照下的麦田和池塘,说雨夜里赶路人的悲喜,说错过了花期的桃林深处的小径……
他的母亲在说这一切的时候,他那空洞、呆滞的目光始终望着远方。他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忘记了身旁的母亲,甚至忘记了自己。但他的母亲相信他在聆听,就像她相信自己的讲述不但能使失语的儿子听到,还能使天上的神灵也听到。
有很多次,他的母亲讲着讲着就流下了眼泪。她知道自己老了——她的牙齿只剩了最后一颗,她的腮帮已经凹陷,她的眼睛一个月前就失明了,她的两条腿也开始站立不稳。她不知道要是哪天自己走了,她那坐在瓦檐下的儿子该怎么办。她深刻地明白,那残破的瓦檐虽暂可替儿子遮挡住骄阳和暴雨,却最终无法遮护他走完他的一生。
光阴是冷酷、易逝和模糊的。两年前一个铺满月色的夜晚,他的母亲在他的沉默和眺望中远去了,变成了一只驮着落日飞翔的大雁。他没有哭泣,更没有悲伤。他已然见惯了太多的死亡,故母亲的死早已被他看淡。他没有为母亲送葬。当他的两个妹妹痛哭着将他们的母亲送上山时,他仍坐在瓦檐下,望着漫天翻飞的纸钱和一路飘摇的白幡,跟做梦一样。他的两个妹妹没有责怪和埋怨他,她们理解和同情这个哥哥,一如她们理解和同情她们彼此生活里的风霜和疼痛。
他的母亲死去之后,他更加孤寂了。他白天和黑夜都坐在瓦檐下,把自己坐成了一座雕塑。他的两个妹妹恳切地告诫他——现在母亲不在了,天黑前必须进屋,把房门锁紧,连月光也不要放进来。可他丝毫不听妹妹们的劝告,他是个习惯了黑夜的人。他从不惧怕黑夜,也从不惧怕黑夜里的磷火和魂灵。
但就是这个沉默、木讷的黑脸膛汉子——历来什么东西都没怕过的汉子,却唯独在他的母亲逝去之后开始惧怕一样东西——雷鸣。他只要听见天空中有或沉闷或响亮的雷声发出,他就会抱紧自己的头,瑟缩成一团,跟瓦檐下倒挂的蝙蝠没有什么两样。
那也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他跟着几个同样是黑脸膛的汉子到一座小城的地心深处去挖矿,他们幻想着能够在那里挖到黄金和钻石。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他们带着祥和与祈祷的心情走入地下。他们集体商量好了,只要这次能够活着从黑暗深处回到地面,就各自回家种十亩桃花送给爱人,种十亩草药送给父母,再种十亩高粱送给自己酿酒喝。但那次他们的运气实在太差——走入地下半个小时不到,就被一个震耳欲聋的雷鸣炸得失去了知觉。等他苏醒过来时,已经不会说话了,而其他几个汉子,则被永久地埋在了地底。
他被人送回故乡后,就成了一个活着的死人。
夜就要来临了。在这个春夜来临之前,浓云低垂下来。风在不断地盘旋和叫嚣。不多一会儿,从天边传来一阵隐隐的雷鸣。那雷鸣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响,欲将黄昏撕裂似的。在雷鸣声中的瓦檐下,倒挂着一只惊悚的蝙蝠,寂坐着一个惊悚的人。
小 径
那是一条阴森、弯曲的小路,它的一端通往密不透风的丛林,另一端则通往荒无人烟的峡谷。在我的记忆里,这条小路更像是一条脐带,它既连接着山村的日月和炊烟,也连接着乡里人的生死和歌哭。
我至少有十年没有走上这条小路了。我之所以决定要再去走一走,是看还能不能通过行走,拾回和聚拢那些业已散掉的记忆叶片,或点燃和捕捉到时常在我睡梦中出现的那些熄灭的火花。
淅淅沥沥的小雨不停地下着——下在路两旁葳蕤的树木上,也下在树木湿滑的青苔上。我侧耳聆听着雨声的密谈,感觉记忆也在随之膨胀、发芽——它们是春雨浇灌下生长出的竹笋和野山菌。那一瞬间,我想起许多的旧事——一个秋天的早晨,有位嘴上叼着烟的男子在小路上迟缓地走着。他的手里拿着一把锃亮的弯刀,可他既不砍柴,也不割草。他只用刀在自己的脖颈和手腕上比试,待刀刃快要挨着皮肉了,他又慢慢地将弯刀放下,像一个僧侣放下手中的木鱼锤,转而迷恋起了红尘。
小路上异常安静,只有两只绿头灰翅的鸟雀跟在男子的身后——它们要么是嗅到了空气中的血腥味,要么是被死亡本身所吸引。那两只鸟,一只是男子的前世,一只是男子的今生。约莫一刻钟过去,天光日趋明亮了,那两只鸟雀朝男子喊了几声,就不知去向。那个男子抽完烟盒里的最后一支烟,坐在一棵黄杨树下默默地流泪,边流泪边用弯刀在黄杨树的枝干上刻下一个人的名字。那个名字,可能是他自己的姓名,也可能是他新逝母亲的姓名,还可能是他深爱着但前不久跟人跑去了异乡的女人的姓名。
还有一件旧事,发生在那年有雾的冬天。一个身穿褐色毛衣、神情沮丧的女人躲在小路左边的翠竹丛中。她那哭得红肿的眼睛布满血丝,好似干枯枫叶上的红色叶脉。浓雾形成的天然帘子,遮挡着她的恓惶和羞涩。她已经在那里等待很久了——她在等待一场浓雾,也在等待一个裹着浓雾来与她相见的男人。自从她的丈夫去年瘫痪在床后,她就学会了等待——等待三个孩子快快长大,等待丈夫尽早从痛苦中得到解脱,等待天空每日都下大雾,等待那个男人每天都能来竹林里见她。一旦那个男人出现,她就可以获取一袋大米、几袋食盐、一块猪肉或几斤面粉。她特别需要这些救命的食物,不然,她跟三个孩子,以及丈夫都很难熬过寒冷的冬天。只要能让一家人活命,她甘愿牺牲自己的贞洁、道德和良知,也不怕背负上任何带侮辱性的骂名,更不怕死后会下地狱,永世不得再投胎做人。
往事像弯曲、阴森的小路在延伸,我已经十年没有走上这条小路了。我不想被往事淹没或掉进往事的深沟里去。我想变得清醒和通透一点,便顶着细雨朝小路另一端的峡谷方向走。当我从那棵刻着名字的黄杨树和那丛躲藏过女人的翠竹旁路过时,我故意不去看它们。我知道,它们是另一道峡谷和深渊。我希望曾经在这条小路上发生过的一切,都能像被厚厚的落叶掩盖住的青石路面,封存在遥远的岁月岩洞中。
我不打算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不管是什么样的道路,走得越远,丢失的就会越多。到最后,可能连返回的勇气都没有了。细雨滚成水珠从树叶上坠下来,砸在我的脸上,有轻微的疼痛感——薄荷似的疼。我的脊背升起一股寒意。我转身朝回走,路面比刚才阴湿,脚踩在上面,步步都有踏空的感觉。我小心谨慎地走着,忽然,我感觉身后有窸窸窣窣的声响传来。我扭转头,竟看见一个小孩子战战兢兢地站在我的身后。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或许比我先来到这条小路上,也或许自从我踏上小路的那一刻起他就尾随着我了。我不认识这个孩子,但又觉得很面熟。我怀疑他是从我的记忆和印象里跑出来的,专为来小路上与我相遇。我没有多问什么,想牵住他的手,但被他拒绝了。
他说他没有名字,只想跟着我走。他还说他并不需要我的引领,他只是怕黑和雾,怕鸟和刀子。
春 事
天将明未明之际,布谷鸟就在薄雾里叫了。它的叫声里藏着一把剪子,不但可以剪去夜色里的杂质,还可以剪去农人的睡眠。她就是在床上翻身的时候,听到这勤劳地监督农事的鸟叫声的。她爬起身,再也无法入睡。她本想拉亮灯,又怕惊醒和刺激到身旁睡得正酣的两个孩子。于是她只能摸索着穿衣服,一缕隐隐的白光从窗子和墙缝里透進来,照在她那睡眼惺忪的脸上。
即使那只布谷鸟不叫,她每天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床的。她的体内本来就住着一只布谷鸟,不分季节、不分晨昏地在催促她,这使得她总是比黎明醒得更早。她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生火做饭,灶间暖红的火光跟她的年龄一样熠熠生辉。做好饭后,见孩子们还在梦中,她又将鸡鸭赶出栅栏,将两头黑山羊牵去野地里吃草,给笼子里的十只兔子喂水……忙完这一切,晨曦也就照临大地,她也度过了一天中四分之一的时光。
从前,她的丈夫在家的时候,他会跟她一同早起。他不忍心妻子被那只该死的布谷鸟催老了容颜,更不忍心她的苦难从黎明就开始。虽然他不是太爱他的妻子,但他到底是个有同情心和责任心的男人。他看到妻子起床后忙碌的身影,自己也不愿意闲着,跑去地里除草、翻土、播种、施肥……他想与妻子一道,迎接日出和惠风,梦想和光明。她目睹丈夫同甘共苦的表现,心里升腾起彻骨的甜蜜。
可是突然的一天,她的甜蜜瞬间就消失了,这让她的日子变得无比漫长和寂寞。那也是一个有布谷鸟叫唤的薄雾时分,她像往常一样被鸟声催醒。但说不清为什么,她总觉得那次布谷鸟叫唤的声音有几分凄凉和幽怨,跟平常叫声的清脆和响亮不同。而且,它还叫得特别急切、尖锐,暗含一种离别和垂泪的音调。她躺在床上,心异常地慌乱,这是她从未有过的情形。她想迅速爬起床,穿好衣裤去厨房做饭,但那床却像安装了磁铁似的,紧紧地将她吸附住。她数次从床上坐起来,又数次躺下去。她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黎明,也猜想到将有什么大事发生。布谷鸟仍在屋外催命似的叫,曙光已透过墙缝和窗子钻到屋内的地板、木床,以及她因忧思而略显苍白的脸上。她再也不能赖床了,她绝不允许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比她起得还要早。她挣扎着爬起床——这可能是她做母亲后起得最晚的一次了。她来不及梳理乱发就去开门干活,谁知,木门刚一打开,几个怒气冲冲的彪形大汉便闪电般闯进了屋。她大喊一声,靠在门框上,身子瑟瑟发抖。随即,她的丈夫就被那几个汉子押解着从屋内走了出来,连外衣外裤都没穿。她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两个熟睡中的孩子也被吓醒了,跑下床拉着她的衣襟哇哇地大哭。看着丈夫被人用绳索捆走的狼狈模样,她知道自己永久的黑夜降临了。
她想去把丈夫给追回来,但她是脆弱和渺小的。她只是一个女人,只是两个幼童的母亲。她没有力量去反抗她所遭遇的一切,就像她无力抗争她那多舛的沉如磐石的命运。后来还是在她带领两个孩子去看守所探视丈夫的时候,才搞清楚丈夫被抓的原因——两个月前,她那忠厚、勤劳、善良的丈夫带领一帮人到处去寻衅滋事。他被人规劝回村后,还不服气,仍在暗中唆使人继续闹事。他表面上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勤快的庄稼汉,实际上却是个地道的阴谋家。他骗过了夜夜睡在枕边的妻子,也骗过了家门前那只日夜叫唤的布谷鸟。
丈夫被抓走后,她的睡梦多了起来,还经常被噩梦吓醒。她那原本就比其他人长的白昼,又增添了一个序曲和尾巴。那只布谷鸟的叫声越来越喑哑,她知道春天很快就要过去了。她想牵出圈里的耕牛,去把闲置的水田犁一犁。不然,她跟孩子们来年都得饿肚子。这些笨重的农活,以前都是她丈夫干的,现在只能落在她的肩上了。
她肩扛犁铧,左手牵着牛,右手牵着孩子,孩子又牵着孩子,一步一步地向春阳朗照下的水汪汪的农田走去。
窗 下
那是一间朝阳的老房子,红褐色的土墙被日照晒得斑驳。远远看去,像是刚剥了皮的黄牛的肌体。那扇雕花的木窗就镶嵌在这面土墙上。只要太阳升起,木窗就被阳光镂刻成了一朵莲花。莲花的根部,还有一条戏水的游鱼——鱼被水牢囚禁着,也被阳光囚禁着。若是天下雨,阳光没有出来,那朵荷花和那条游鱼就只能安静地待在木框内,把自己变成挂在墙上的一个旧物件,装饰着这个枯燥、难熬和阴沉的日子。
每天从早上到傍晚,他都坐在木窗的底下。他的前面有一张桌子,桌上搁着一本处方签和一支笔;左侧是一个木架,上面整齐地排满了各种大小不一的白色瓶子;右侧则是一个跟他的身高差不多的柜子,柜面上端正地写满了各种植物的名字:茯苓、黄芪、甘草、大黄、豆蔻、丁香、柴胡、白芍、紫苏……
或许明眼人早就看出来了,他是一个乡村医生——大约五十多岁,脸孔瘦长,秃顶,额头有刀刻似的皱纹,下巴上生着玉米须似的胡子。他戴着一副老花眼镜,镜架总是悬在鼻翼上,像两片厚实且蒙了灰的玻璃。没有病人光顾的时刻,他会把眼镜摘下来,用布包裹好,像收藏一件遗物那样放进桌上的皮质小盒子里。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扇木窗看。大家都以为他是在看那朵荷花和那条游鱼,其实他看到的都是些跟木窗无关的东西——他看到太阳睁大血红的眼睛在蓝天上哭泣,看到成群的山羊在跟一片枯黄的野草下跪,看到炊烟在参加一棵老树的葬礼,看到一片草花在祭祀远走的春天……
很多病人都说,他不大像一个医生,而是像一个乡村哲学家。他老是以美学的思维来分析病情,以诗人的感悟来理解疾病,这使得他在患者中的口碑极差,但他又无疑是患者最为爱戴和崇敬的人。作为这个村庄里唯一的医生,多年以来,他以高超的医术救治过许多人的生命。在面对任何一个活生生的患者之时,他从来都是严谨、负责和慈悲的,丝毫不像诗人或哲学家那样信口雌黄,说一些冒犯社会的话,干一些触怒众神的事,发一些无关痛痒的牢骚。他开的每一张药方,都是一剂安魂汤。
在他的行医生涯中,有三位患者是他印象深刻的。第一位是个小孩子,他来老房子找他的那天,他正被昨晚做的一个梦所困扰。那个孩子问他:“你为何一见到蝌蚪就担心河流干涸,为何一到黄昏就想念消失的萤火,为何一端起饭碗就觉得愧对金灿灿的稻谷,为何一闭上眼睛泪水就止不住地朝外流?”他回答不出孩子的问话,只知道孩子的病很严重,可又开不出为其治病的方子。第二位是个中年妇女,她来老房子找他那天,他正被第一个小孩子的病情所困扰。那个妇女说,她最近老是失眠,耳朵里时常听到某些奇奇怪怪的争吵声。她听到去年的一场雨和前年的一场雨在争吵到底是谁打落了今年的第一片黄叶。她听到屋后的两枝桃花在争吵究竟是谁辜负了春光和放走了一对偷情的蝴蝶。她还听到一个自己跟另一个自己在争吵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自己。他茫然地望着这个活在听觉里的妇女,他想给她开一张方子,可他翻遍了祖传的医书,都没找到世界上有这种病的案例。第三位是个老人,他来老房子找他那天,他正被第一个小孩子和第二个中年妇女的病情所困扰。那个老人拄着拐棍,一见到他就笑。他问老人笑什么,老人也说不知道,只说自己笑了三天了,就是停不下来。他告诉老人:“你若不说出笑的理由,这病没法治。”老人听他这么说,嘿嘿地笑着沉思了片刻,才慢吞吞地说:“我笑秕壳草长得比麦子多,笑锄头和镰刀上的铁锈比自己脸上的老年斑多,笑逃跑的人比返回的人多,笑毛病比健康多,笑死去的比活着的多。”他听老人说完,自己也想笑,一笑就哭出了声。他诊断不出这个老人得的什么病,他也诊断不出那个小孩子和中年妇女生的什么病。这是三个奇怪、特殊和复杂的患者。这三位患者离去后,他一直闷闷不乐。
在忧伤的时刻,他老是喜欢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扇木窗看。他不是看那朵荷花,也不是看那条游鱼。他是一个医生,也是一个病人——他的病情比那三位患者还要严重。
三 月
一个彷徨之夜过去后,三月就到来了。我跟随门前的流水和鸟鸣一起醒来。我看见草木在清风中摇晃,看见野鸭在池塘里洗濯翅膀,看见花朵在路边寂寞地开放,看见蔬菜在院子里头顶着阳光……我从我看见的这一切身旁走过,我是三月里的一个过客,三月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个驿站。
我沿着三月的小路行走——我老想到什么地方去,在这个阳光静好、岁月明亮、泛着红酒味道的早晨。小路上起了斑斑的青苔,绿一块,青一块,这让我想到那些坐在墙根下晒太阳的老人们脸上的黑斑,它们都是日月镌刻在人间的胎痕。
小路是冷清而幽寂的,人走在上面,自始至终都被一种深沉的静包裹着。我漫无目的地朝前走,左边的野地里开满了淡黄色的小花朵,右边的野地里开满了淡紫色的小花朵。风从正面吹来,两边的小花朵都在欢呼和舞蹈。它们跟我一样,寂寞得太久了,三月也寂寞得太久了。我想弯腰采摘一把小花,插在三月的发髻上,将之装扮得窈窕一些,让二月回过头来心生嫉妒,让四月停下脚来不愿匆忙赶路。可我刚要弯腰,就看见野地的那头跑过来一男一女两个小孩。他们跟小花朵似的充满活力,蹦蹦跳跳地互相嬉闹着。那个小男孩在摘小路左边的小黄花,那个小女孩在摘小路右边的小紫花。他们在比赛谁摘的小花多,如果谁赢了,仿佛三月就会奖励给谁一个缓慢的生长——让他(她)永远活在草长莺飞和柳绿花红的季节。我呆呆地看着这两个孩子欢快地与我擦肩而過,我不知道,当他们跑过去的那一瞬间,会不会从我的身上看到自己多年后的模样。
我转过身去看他们,想跟他们说几句话,但他们已经跑远了,像两道黄色和紫色的回忆,消失在三月空旷的野地上。我带着怏怏的心情继续朝前走,我不想再弯腰采花了,我要将这些小巧、可爱的小花朵留给下一个或两个乡下的小孩子。他们比我更需要这些花朵,每一朵小花都是一个小孩子的一个小小的梦想。没有梦想的孩子是可怜的,没有在三月的土地上采摘过野花的孩子是可怜的。
我没有挽留住那两个孩子,我也是可怜的。以至于我都走出很远了,还在不停地回头看他们。我希望他们能够重新跑回来,与我相遇,与他们的中年相遇。我相信,他们总有一天也会长到我这个年龄,长成三月里一个怀旧的过客。然而,他们终归还是跑远了,消失了,没有再返回来与我相遇。
前来与我相遇的,是一只蚂蚁和一只蜗牛,我在回头看那两个孩子的同时也看到了它们。它们一直跟在我的身后,像两个旧相识。我走一步,它们也爬行一段。或许它们早已爬行了若干年,才爬到了我的后面。正如我行走了若干年,才走到了三月里来。它们爬得不容易,我走得也不容易。我不知道我们去的是不是同一个地方,我只知道它们追不上我。它们之所以赶来与我相遇,不过是希望我能捎带它们一程。我明白它们的心思,我不也是在借助三月捎带我一程吗?我顺手摘下一片草叶,让它们爬到草叶上来休息,然后我拿着草叶继续行走。
可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我刚让蚂蚁和蜗牛在草叶上躺好,我的身后就跟来一个人。他战战兢兢地望着我,想说什么,又始终不开口。我没有理睬他。我继续朝前走。我走快一些,他也跟快一些;我走慢一些,他也跟慢一些。后来,我停下脚步,问他到底跟着我干什么。他嗫嚅了半天,才说想跟我一起去三月里踏青。他怕自己一个人迷了路,走到五月或六月里去了。他需要一个带路的人。我真诚地告诉他,我也不能保证让他顺利找到来时的路,因为我也是一个跟着三月在走的人。他说他相信我,就不再说话了。
我不认识这个人。我带着他,还有蚂蚁和蜗牛一起结伴朝前走。我们都不清楚要到哪里去,但走着走着,他就成了我的一个影子。我问他:“你真就那么相信我吗?”他点点头,说了一句:“如果你也迷路了,那我们就肩并肩地沉默着走到下一个三月。”
炊 烟
夕阳就要落山了,它将最后一抹血红色的光辉洒在地平线上,也洒在那个从后山的岩洞里背柴回家煮饭的老妇人身上。那些柴是她去年秋天从一棵椿树和一棵麻柳树上砍下来的,经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天,树枝尚未完全干透,它们的体内还流淌着大树的血液。若不是这个老妇人急忙要将它们背回家投入灶间焚化,它们始终还在盼望着等下一个春天来到后再重新发芽呢——每一根被砍断的树枝,都像一个被流放的人,到死心里都在想着怎样才能回到它出生时的冻土和家园。
老妇人垂着头,陷入深深的沉默。四周的一切鸟鸣虫叫都噤声了,晚风也打起了哈欠,睡意昏沉的样子——它总是要赶在天黑之前进入梦乡。干柴压在老妇人的脊背上,那高出她头颅的凌乱枝丫刺向夕阳,仿佛她的后背上长满了犄角。她走一段路,就要将背筐放在一块石头上歇歇气。她生病了,腰和腿都疼,肺和肝也疼,骨骼和神经也疼,她预感到自己来日不多。昨晚在睡梦中,她又梦见了牛头和马面,它们要强行带她去一个地方,一个遥远而陌生,没有病痛的地方。她很想就这样跟着它们走了,再也不再醒来。但正要上路时,她又突然想念起她那在远方打工的儿子。她挣扎、告饶、祈求,恳请牛头和马面再宽限她几天时间。她已经给儿子捎去了消息,让儿子无论如何赶回家来看她一眼。她的儿子也亲口答应了,说这几天就赶回来——这是一对血肉相连的母子之间的约定。
几分钟时间过去,老妇人又气喘吁吁地背着干柴朝家走。她要赶在夕阳落山之前回到灶房,将干柴变成屋顶上飘荡的炊烟。她相信,只要她的儿子看到缭绕的炊烟和嗅到炊烟的味道,就会跟着炊烟回到她的身边——他从小就是个爱望着炊烟遐想的孩子。
夕阳的血色越来越暗淡,她脸上的血色也越来越暗淡——如果说夕阳是一个天上的落日,那老妇人就是一個地上的落日——它们共同在见证着天地之间的悲喜和苦乐。
大概又过了十几分钟的时间,老妇人回到了灶房。她没有再歇气,她立刻开始生火煮饭。自从儿子允诺她回家那天起,她就一日三餐都提前做好饭菜等待他的归来。她想最后给风雨兼程的儿子做一顿可口的饭菜——这饭菜的味道,只有她才能做出来。
不多一会儿,屋顶上的烟囱就冒出了白烟——那白烟既是干柴的魂,也是老妇人的魂。烟雾在屋顶上空盘绕,也在老妇人的心头盘绕。夕阳已经完全落山了,黑暗也逐渐吞噬了村子周边的树木、河流和道路。她一个人孤寂地坐在灶门前的凳子上,微弱地闪烁的灶火映衬着她那衰老的脸颊。她没有起身拉亮电灯——那电灯的钨丝已经断了有些日子了,她找遍了整个村子,也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让灯泡重新亮起来的人——她也不再需要过多的光源,单是那灶间的柴火就足以照亮她的黑夜和晚景。
她深深地意识到,她的儿子至少在今晚是不会回来了。但她仍然在等待,她不时地朝灶间放一根干柴。她不能让灶火熄灭,她要给儿子点燃夜间的火把。灶上的大铁锅里,烧着一锅热水,那是她专门替儿子烧的泡脚水和洗澡水。她知道儿子大老远赶回来看她很辛苦,他需要一锅热水来解乏——这是她现在唯一还能够替儿子想到并做到的事情。
她的儿子上一次回家,是去年的七月还是九月,她有点记不大清了——最近她老是失忆,除了儿子,她几乎什么事都不再能想得起来。那次她也是实在想念儿子了,才谎称自己病重骗儿子回家。结果儿子回家来看见她好端端的,第二天就生气地走了。直到现在,她都还在为这事而自责。但这次她是真的病了。她的腰和腿都疼,肺和肝也疼,骨骼和神经也疼。她担心自己很难挺过今夜。在黄昏时分去岩洞背柴的时候,她就想着干脆将自己也放进灶间用干柴焚烧了,化作一缕炊烟,飘去看看她的儿子——假如儿子不愿意回来,她就只能去看他。
夜深了,夜凉了。这个病重的老妇人,倚在漆黑而冰冷的灶门上,神思恍惚地在继续等待她的儿子。她的儿子也许夜半时回来,也许黎明时回来,也许永远不再回来。
责任编辑:杨 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