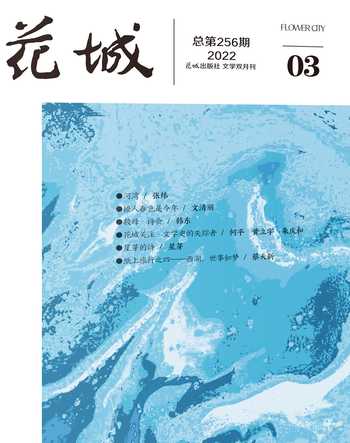引言:他们是失踪者,也是西西弗
2022-06-04何平
何平
2022年初,“收获文学榜”发榜,浙江舟山小说家黄立宇发表于《野草》的《制琴师》排名中篇小说第二。舟山和文学期刊《野草》所在地绍兴都是今天文学地理的“小地方”,故而,黄立宇小说《制琴师》的入榜也就成为上年度“收获文学榜”的一个小小的文学事件。
大约十年前,2012年前后,我曾经在湖南岳阳、江苏南通、江苏泰州和北京通州等地进行“基层文化建设的文学参与”的田野调查,发现从当时的文学资源分配上看,在刊物、大学、文学活动、作协、书店、影剧院等平台或个人,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而县城及农村的文学资源基本被掏空,偶尔能遇到可数的坚持写作的80年代文学遗民。比如就文学期刊而言,我们按照行政区划看,非省会城市的市一级及以下的文学期刊,有影响的可能就是《野草》《文学港》等可数的几家。所以,《制琴师》出自《野草》也成为一个新闻关注点。新时期文学初期,县城及农村聚集了相当多的优秀作家,这当然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导致的文学人才下移有关系,但也离不开县城文化馆、群艺馆、工人文化馆等“文化单位”在基层作家成长过程中提供的物质和精神支持。生于20世纪60年代,现在仍然在江苏靖江工作和生活的作家庞余亮也有类似的观感:“县城写小说的人越来越少了。其实80年代在县城写小说的人还是很多的,50年代出生的很多作家的写作都是从县城,有的甚至从村镇开始的,那个时候县城里的文化馆有很多写作者,或者说囤了很多文学的存量,80年代文学有一个集中爆发的过程,跟这些文学存量是有很重要的关系。”每一个写作者的文学学徒期开始的地方有大有小,他们肯定或多或少都有过被更大范围知道,甚至被文学史经典化的雄心,但文学史是吝啬,甚至残酷的,具体到一城一乡某一个“邮票大”的地方,成为大师、巨匠,或者列名于文学史的人只是少数。
如果做一个广泛的田野调查,几乎每一个地方,无论多么小,都还有默默写作的——地方上文名甚著,而在更大范围里却无名的“小地方”作家,他们数十年坚持写作和“有文学”的生活,是我们时代细小的文学西西弗(出版人、评论家李伟长近日在朋友圈推介樊健军小说集《冯玛丽的玫瑰花园》时说:“中年,不分男女,是一段必不可少的时间,小城里的西西弗。”他可能说的是樊健军小说的人物,但很多写作者其实和他们小说的人物一样,是更细小的文学西西弗)。从今天整个文学生态来看,这些细小的文学西西弗不只生活和写作于行政区划和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小城”,甚至在比小城更偏僻之地。在稠人广众中,在时代的喧哗和骚动中,他们安静地静默地写,如果不通过一定的方式展示和呈现,是极容易被忽略和湮没的。朱学勤有篇流传甚广的文章,题目叫《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同样,无数细小的文学西西弗也成为我们文学史的失踪者。
黄立宇提供了三篇小说《翡翠》《丁香》《睡在树上的鱼》,选一《睡在树上的鱼》。朱庆和提供了四篇小说《去南京见一个叫张芹的女人》《我们的新郎,那么害羞》《我的哥哥叫罗成》《高楼上》,选二《去南京见一个叫张芹的女人》《我的哥哥叫罗成》。依据是这三篇小说,小说家与他们笔下的人物有情而无间,作者的敏感、宽宥和慈悲是小说人性的底座,也是小说的节奏和声腔。这样的小说家诚实地生活在我们悲欣交集的人间中并写作着。
问题一:你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写作?请介绍下自己的个人写作史,包括发表情况。
黄立宇:第一次在公开刊物上发表,是在1986年,那是一篇充作电大论文的文学评论。之后有文字陆续见诸报刊,1994年调舟山市文联,任文学编辑。1995年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我的写作,完全是受20世纪80年代文学大潮的影响。前期接受的文学都是一些后“文革”时代的烂书。看了这些烂书,让我一度产生错觉,以为所谓的文学并没有什么,以为自己也可以。后来我在上海一家书店,看到《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精装本,一套四本,总价二十多块,差不多是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我坐在书店的门槛上犹豫了一个下午。当然最终我把它拿回了家,被母亲臭骂了一顿。不知道为什么,在文学上一张白纸的我,就认定那才是真正的文学。文学的光芒第一次照耀到我。
1997年,我在《收获》杂志发表短篇小说《一枪毙了你》,颇具影响。之后相继在《花城》《大家》《钟山》《作家》《芙蓉》《青年文学》等刊物发表作品。至2001年,我在网上创办了“新小说论坛”,那里聚集了鬼子、艾伟、叶开、徐则臣、盛可以、曹寇、李修文、张楚、朱山坡等中国最富活力的一批作家。同时,我的创作开始陷入困惑和停滞。一帮深受西方文学浸染的年轻的写作朋友,对我的作品提出了批评。要命的是,我非常认可他们的观点。阅读的深入,使我的写作隐入越发的迷惘。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停止了写作,写了东西也不投稿,我的电脑成为文字的廢墟。《制琴师》完全是一个意外,《野草》杂志要我友情支持,我就支持一下,没想到还受到文坛的认可,这是后话。
其间,我出版了小说集《一枪毙了你》、散文集《布景集》,曾获浙江省优秀作品奖、首届“三毛散文奖”,入选“收获文学榜”及各类选刊选本。
朱庆和:我是1998年开始写作的,先是写诗,2000年开始写小说,断断续续,一直写作至今。2000年,与李樯、林苑中、轩辕轼轲、育邦等办刊《中间》,2002年与韩东、于小韦、刘立杆、李樯等创办“他们文学网”,主编“他们”网刊第二期。这两年自己打理一个诗歌公众号“隐匿之歌”,去年开始与韩东、钟岚、徐全编辑诗歌公众号“英特迈往”。已在《人民文学》《诗刊》《芙蓉》《长江文艺》《青春》等发表诗歌300余首,在《今天》《上海文学》《芙蓉》《红岩》《雨花》等发表小说40多万字,并有诗歌、小说入选多种文学选本。2016年出版小说集《山羊的胡子》,著有诗集《我们柒》、电子诗集《苜蓿与水草》,独立出版诗集《我的家乡盛产钻石》,诗集《橘树的荣耀》即将出版。短篇小说《在集市》获第三届“紫金山文学奖”,短篇小说《春雪》获首届“雨花文学奖”,短篇小说《没有思绪的旷野》获“金陵文学奖”佳作奖,小说集《山羊的胡子》获第六届“后天文艺奖”(这是个民间奖)。
(按:黄立宇和朱庆和都在国内重要文学期刊发表过文学作品,而且写作和发表都经历过文学的论坛时代,这对于我们观察世纪之交的媒介变化和文学,提供了实践性的案例。)
问题二:在你个人持续的长时段写作时间里,你感觉到周围的写作者和写作生态的变化是怎样的?
黄立宇:我的写作并不是持续的,而是中断和零碎的。作品发表后的短暂喜悦,并未带来持续的写作动力,我的创作激情一般来自阅读,而阅读又让我对自己产生深刻的怀疑。我始终处于这样的徘徊。当然日常生活的平庸与纷扰也是一个原因。生活在小城,文学和写作相对处于寂寞的、零散的、边缘化的状态。具体到我与周围写作朋友的交流,有一段时间极其频繁,书店有好书,书店朋友立刻通知,一抢而光,并成为我们几天后激烈争吵的焦点。同时写出来的作品,又以朋友首肯为最高荣誉。他们心怀纯粹,羞与官方为伍,甚至长期不在文联、作协和刊物的视野之内。连我这个编辑,拿他们的稿子还要贴尽脸面。
中国的文学传统对文采、意境和宏大题材过于看重,想象丰沛和表达精准的好作品并不多见,许多热门作家一直处于发作品的焦虑状态,沉醉于写作的巨大惯性和文字的自我繁殖。一方面是日益僵化的文学机制,文学评判标准的老朽与真正的文学批判精神的缺席,另一方面,民间自生自灭的大量优秀文学作品的存在,才是中国文学生生不息的地下长河。文学机制的僵化,使民间的一批有才华的年轻作者的写作热情消磨殆尽。
朱庆和:我从开始写作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因为从小没受过什么文学熏陶,大学也没学文学专业,完全是凭着兴趣和一腔热血,自发地去找文学书看,看得多了,就试着去写,把60年代之前的作家都作为学习的榜样,和同时代的人比试,想着怎么能发表和出名,太功利和急于求成。二十年过去了,新人辈出,我几乎还在原地,反倒不急了,感觉写作真的是一辈子的事。从这二十多年的写作和见证,我感觉写作者只要有一定的才华,坚持不懈,肯定能写出来。在我接触的写作者中,老的越写越好,新人不断涌现,蔚为壮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至新世纪初,写作阵营不自觉地会有官方、民间,或者是知识分子、民间的分野,那时候因发表渠道少,志趣相投的人抱团取暖,盛行办民刊,后来网络成为新的交流工具,他们就办文学网站、编网刊。现在整体创作环境似乎不再像以前那么分化,大体趋向平和,可能是因为理想主义者少了些,都懂得如何生存,都知道“有奶便是娘”的道理。但我想,文学圈有一点很好,就是好东西不会被埋没。
(按:黄立宇和朱庆和都提及文学权力分配及其写作者的位置,虽然他们都在各自的小文学圈写作,但南京和舟山的不同文学区位以及文学交往圈,尤其是深度介入文學BBS的经历使得黄立宇对文学写作黑暗期有更深刻的体认,当BBS文学黄金时代过去,文学生活也会被改写。)
问题三:你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写作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大致是个怎样的状态,或者说写作之于你生活的意义。
黄立宇:我生活在小城,我的情感和行为方式,最初都是它赋予我的。我虽然到过国内外很多地方,但我一直没有在其他城市生活过。我已经退休,非常享受现在自由自在的生活,我基本在上午写作,有几百个字就很满足。写作令我自省和观察,教会我如何自处,并以宽容之心对待现实。无论我在生活里是多么地不堪,但写作始终给我一种体面感。我喜欢所有美好的物事,我爱好的东西太多,喜欢摄影,也做过平面设计,曾经想当一名画家,也考过以前的浙江美院,最后我在文字里找到了自己。我热爱写作,我是一个散漫的人,说写作是我的生活方式的一种更为合宜。那种一个晚上写一万字,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我写得很慢,一篇小说的开始通常是草率的,写着写着经常会扔掉。大量的半成品堆积在电脑里,少有重拾的兴趣。我平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上过大学,知识结构有缺陷,阅读也不成系统,更不具备一个成熟作家的写作才华,好在我对文字的喜爱,和对生活的热情和敏感,使我一直葆有对文学的热情。
朱庆和:每天按部就班地上下班,然后忙孩子、忙家务,直至深夜才拿起笔来,写点东西。最近可能是年龄大了,感觉精力不如以前,往往睡醒一觉,凌晨三四点钟起来写一点。我不喜欢有点想法就记下来,在落笔之前都存在脑子里。我钟情于写作的原因,我想大抵是上学时受的束缚太多,写东西就是要摆脱束缚,自由地发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实际上就是实现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写作或者是想着写作这回事,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这并不是说写作有多高尚,其实它跟打牌打麻将一样,只是一种精神上的填充。不写的时候,我可以看书、看影碟、构思、打腹稿什么的,总之是自由的,整个身心是放松的、快活的。
(按:他们都不是所谓的专业作家,也不是文学专业科班出身,他们首先是我们身边的人,这个专题一开始的关键词是“他们在人群中写作”。文学对他们而言,是美好、体面和自由。)
问题四:你觉得你的写作和整个同时代写作是怎样的一个关系?
黄立宇:我的写作无足轻重,与同时代的写作不构成映照关系。我的文学谱系里,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暗自神伤的小人物,社会现实的残酷与坚硬,底层的软弱与无助,一击而溃的尊严。我所认为好的东西,都在它的细微处,那些不经意的地方。
朱庆和:我有些懒惰,写得不多,也很慢,当然这都是借口,我感觉还是底子薄,受专业训练太少的缘故,写法单一,视野方面也很狭窄,所以相对于同时代的写作者来说,我跟不上趟了。现在脑子里有三四十万字的东西,慢慢来吧。这事真急不得,反观以前写的东西,真是惭愧,就当练笔吧。
(按:写作首先是对写作者自身发生意义。)
问题五:你的日常写作中能够感觉到同行之间的相互激励、欣赏、支援和批评吗?
黄立宇:我并不需要应酬场合上的可以想象到的那种赞美,它使我莫名的难过。我的写作的荣誉感,总是来自身边朋友的首肯,他们的首肯,甚至超过在刊物上的发表。他们喜欢的,往往是我文字上的一些特质,或某种生机。批评总是难免的,我总是乐观地想,他们之所以批评我,前提是因为我的作品尚还能看,这真是我莫大的安慰。有个朋友对我的评语是,一个原本可以更好的作家却早生了二十年。确实,一个作家难以跨越时间的羁绊。我平静地接受这一点。
朱庆和:在日常写作和文学交往中,因我较为内向,也不去投稿,经常有老师、朋友帮忙,才使得诗、小说得以发表,结集出版,这名单太长了,就不列了,我在心里都感激他们。感觉这也是我能坚持写下去的动力。当然批评的也有,但当面说的不多,没说你好,那就是批评,得有自知之明。
(按:对于有的写作者而言,写作者之间的友情和彼此声援可能就是特别单纯的文学意义上的。)
问题六:谈谈你对“文学青年”的看法,包括文学青年从八十年代到现在的演变。
黄立宇:就像我在《小说选刊》刊发的《制琴师》创作谈中谈到的那样,当年我们对文学的爱好,看似说是自主选择,实则是文学大潮的时代裹挟,尤其是小地方的青年人,冷暖自知,缺乏生活的可能性,文学给了他们最初的温暖。20世纪80年代,文学盛行,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是文学青年。这个标签似乎从一开始就是贬义的,文学青年一直处于自我角色认同与社会评价低下的纠结之中。年轻时,当别人知道我是写小说的,我都会有一种无力感和羞耻心。同时又觉得,他们说的文学跟我一毛钱关系没有。
80年代的文学青年,大部分都拿着这块敲门砖,完成了世俗化的角色转换,他们当官的当官,下海的下海,当他们反过来嘲讽文学的时候,其实文学早已抛弃了他们。
朱庆和:文学青年,顾名思义就是热爱文学的青年,我觉得痴迷文学可以,但不可因为此举而耽误了其他事情,把生活搞得一团糟。我没经历过80年代,不知在那时文学青年是一种什么样的称谓,我想大概应该是一个褒义词。到我们开始写作时,因为写的东西没发表,感觉别人称呼你为文学青年,是一种羞辱。所以,总是偷偷地写,生怕别人知道。发表了文章,都不好意思拿出来。现在的话,文学青年,这个称谓提得少了,但说一个人喜欢文学,总感觉语气里还带有一种轻蔑或者不屑的味道,跟“二逼青年”差不多。我现在态度淡然了,碰到别人会说自己是文学中年,或者资深文学青年,年龄摆在那儿,还有什么可辩解的。
(按:确实,“到现在,文学青年似乎成了一个贬义词”。)
我们能够读到的文学史都是一部隐没了失踪者的历史。可以举几个例子。我在写邱华栋作家论的时候翻到他1989年出版的小说集《别了,十七岁》(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一套十五种的“小作家丛书”,收入的作者都是当时被看好的“少年作家”。时至今日,三十多年过去,这十五个“小作家”成为“大”作家的只有邱华栋一个。文学少年能够完成作文到文学转身的很少。
按照《深圳青年报》和安徽《诗歌报》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的统计,“1986——在这个被称为‘无法拒绝的年代’,全国2000多家诗社和十倍于此数字的自谓诗人,以成千上万的诗集、诗报、诗刊与传统实行着断裂”。那是一个文艺和青年纠缠不清的时代。可是时至今日,还在写诗的还有几许?类似的情况,我们看八十年代的历次文学评奖,看当时的文学期刊目录,能够坚持到今天且被读者记住的又有几人?
对社区或者BBS蜂起的时代,我们看看“天涯社区”这一历史留存大致就会有一个直观的印象。这些社区和BBS,在当下可能会转型为APP、微信公众号或者豆瓣那样的公共性的写作和发表平台。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安妮宝贝在“自序”《网络,写作和陌生人》中说:“网络对我来说,是一个神秘幽深的花园。我知道深入它的途径。并且让自己长成了一棵狂野而寂寞的植物,扎进潮湿而芳香的泥土里面。”“很多人在网络上做着各种各样的事物。他们聊天,写E-mail,玩游戏,设计,恋爱,阅读,或者工作。而我,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情是在写作。”小、个性、自由书写、非营利等,这可能是当下被资本命名的网络文学排除而隐失的一个重要传统。黄立宇和朱庆和都是这个BBS文学时代的遗民。何其快也,也才十几年,BBS已然是文學遗址。
本专题的朱庆和,并不像黄立宇那样生活在小城,但在文学城市南京,他的文学半径只触及有限的朋友。如果不拘泥于行政区划和地理空间,朱庆和其实是和黄立宇一样的“小地方”的细小文学西西弗。
故而,本专题提醒我们向下、向基层、向边缘、向稠人广众的文学生活观察和挖掘我们时代的文学。谨以此致敬那些细小、隐微的写作者或者一种精神生活,致敬他们文学史不载的“在人间”写作。
2022年4月5日于南京
责任编辑 李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