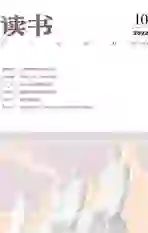爱能否跨越边界?
2022-05-30钟志清
钟志清
父母来自伊朗的朵莉·拉宾雅(Dorit Rabinyan)是当今以色列文坛一位备受瞩目的杰出女作家。她用夹杂着波斯文化元素的希伯来语揭开了以色列一个特殊族裔群体—伊朗犹太人的面纱。这一族裔群体在以色列国家的政治版图中多年处于边缘化地位,在中国更是鲜少得到关注。
以色列伊朗犹太人是指从伊朗移民到以色列的犹太人及其后裔,这一群体在伊朗拥有悠久的历史,甚至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六世纪居鲁士大帝征服巴比伦时期。《圣经》中的《以斯帖记》写的就是波斯宫廷内部犹太人争取生存的故事。尽管时至今日,尚未有考古与历史研究证明位于伊朗哈马丹神龛里的墓确属以斯帖, 但是,学界一般认为犹太人从那个时代起就生活在波斯,即后来的伊朗。
现代伊朗犹太人与以色列国家的关联要追溯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在伊朗产生了影响,伊朗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几经沉浮,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达到其黄金时代。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国这一历史事件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伊朗犹太人移民以色列。按照统计,早在一九四八年到五十年代中期,便有五万多伊朗犹太人移民以色列。五十年代中后期到一九七八年,又有大约两万五千人移民。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后出现了新的移民高峰,一九七九年,大约两万犹太人离开伊朗,一部分人移民到以色列,另一部分人移居美国和其他国家。目前,以色列境内的伊朗犹太人超过十三万五千人,其中大部分出生在以色列。
拉宾雅的父母是在五十年代初抵达以色列的第一代伊朗犹太移民,他们定居在特拉维夫附近的卡法萨巴(KfarSaba)。与其他移民到以色列的东方犹太群体类似,多数第一代伊朗犹太移民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專业人士所占比重较小,无疑也遭受到操纵国家话语霸权的欧洲犹太人的歧视。况且,他们使用波斯语,与使用希伯来语的本土以色列人交流非常困难,与来自其他中东国家讲阿拉伯语的犹太人的交流也有很大障碍。加之,他们在新犹太国家被要求抛弃其文化价值与习惯,以便接受一种新型的以色列身份。类似的文化歧视令移民以色列的伊朗犹太人非常挫败,他们消极抵抗国家政策,主动与社会隔离,自我边缘化,有些人甚至决定重新回到伊朗。据不完全统计,一九四八到一九五三年,便有大约百分之七的伊朗犹太人决定重回伊朗。
但是,伴随着下一代在以色列出生,以色列境内伊朗犹太人与欧洲犹太人之间的文化隔膜逐渐得到缓解。新一代伊朗犹太人通过在以色列接受教育和服兵役等举措,适应了以色列的生存环境,能够教父母如何做以色列人。父母为了更好地与子女沟通,也去学习希伯来语和犹太复国主义理念。在渐趋适应并融入以色列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也有一些伊朗犹太人在以色列政治生活中担任了要职。比如一九五七年随家人移民以色列的莫法兹(Shaul Mofaz),相继担任过以色列国防部长、交通部长和副总理。一九五一年随家人移民以色列的卡察夫(Moshe Katsav)曾经担任以色列第八届总统。当然,伊斯兰革命之后移民以色列的伊朗犹太人同样面临着融入以色列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的困难,他们对以色列的社会文化与经济情势抱有一定的期待,而以色列又无法符合这种期待,因此矛盾仍然在继续。
拉宾雅属于第二代伊朗犹太人,也可称之为伊朗裔犹太人。她出生于一九七二年,在以色列接受教育、参军、担任新闻记者等。从二十几岁就开始尝试文学创作,与其他第二代东方裔犹太作家不同,拉宾雅没有直接把流散地语言,具体地说是波斯语直接转换成希伯来语,但却继承了波斯语中的某些文化元素,如韵律、乐感等,将其转换成地道的希伯来语,创造了别具一格的表达方式。其处女作《波斯新娘》(一九九五)以祖母的故事为蓝本,揭示了伊朗某古老犹太社区童婚制对女性的戕害。第二部长篇小说《我们的婚礼》(一九九八)的背景转换到当代以色列,但与早期作品在主题方面具有关联,再现的是移民以色列的伊朗裔犹太人被边缘化及其难以融入以色列社会的困境,尤其反映出负载着古老文化传统的移民能否完成身份重塑、融入以色列社会的问题。
第三部长篇小说《爱的边境》(二0一四)则触及中国读者所关心的巴以问题,揭示出当代以色列语境中不同族裔群体的命运。《爱的边境》的情节源自拉宾雅的个人生活经历。二00二年十一月,身为富布赖特基金得主的拉宾雅在纽约结识了巴勒斯坦艺术家哈桑·胡拉尼,并与之相恋。胡拉尼一九七四年出生在位于西岸的希伯伦,曾经就读于伊拉克的巴格达艺术学院。二00一年到纽约举办画展,后在纽约继续学画,画画,二00三年回西岸探亲,在一次旅游时途经多年未曾得见的地中海,下海游泳时溺水身亡。拉宾雅恩悲痛之余,搁置自己撰写了一半的小说,耗时多日记载他和胡拉尼的爱情经历,这便是我们今天读到的长篇小说《爱的边境》。
小说以其独创性一举夺得当年的伯恩斯坦奖,引起了以色列读者的广泛关注。二0一四年七月,加沙向以色列投掷了多枚炸弹,以色列人在防弹掩体中阅读这部作品,对巴以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后来,小说入选以色列公立学校阅读书目,目的是要让年轻一代更好地了解巴勒斯坦人。但在二0一五年,以色列文化部命令将此书从中学生阅读书目中删除,认为这部反映以色列犹太人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爱情的作品会变相鼓励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跨种族婚姻。以色列文化部长甚至公开宣称拉宾雅恩是民族的敌人,作家本人也遭受到生命威胁。这一禁令把一部文学作品转化为政治宣言,在以色列引起轩然大波。以色列的顶尖级作家奥兹、约书亚、格罗斯曼和沙莱夫纷纷表示抗议,支持拉宾雅恩。在某种程度上,以色列文化部的禁令反而推动了《爱的边境》的销售,使之在中东和欧美得到广泛接受,很快便被翻译成近二十种语言,《纽约时报》头版为之刊载了书评。面对舆论压力,以色列文化部不得不放松禁令,允许一些教育工作者讲授《爱的边境》。二0一九年,小说被以色列超级影星、曾被《时代》周刊列为百名世界最有影响力人物的加多特(Gal Gadot-Varsan)拍成电影。
小说的希伯来文名为Gader Haya ( ),字面含义为“树篱”或“藩篱”。这道藩篱既是政治边界,又是身份边界。现实生活中的以色列作家和巴勒斯坦艺术家在《爱的边境》中则以男女主人公的形式出现。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冲突、困境与死结喻示着巴以地缘文化政治话语中的种种复杂性。
小说开篇便向读者展现出以色列伊朗裔犹太人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身份困境。女主人公、来自以色列的丽雅特以富布莱特学者身份在纽约攻读翻译学,借住在朋友的公寓里。两位来自联邦调查局的成员例行公事,对她进行盘问。其伊朗犹太移民后裔的身份显然引起联邦调查局警员的特殊“兴趣”:
“那你的亲戚还有住在伊朗的吗?”
“没有,”我答道,这场对话的新方向使我逐步获得了信心,“他们都移民去了以色列,都成了以色列公民,自从—”
“那你自己呢?你最近去过伊朗吗?”
“完全没有。”
“你也许去哪里旅行过,”他再次尝试,“去寻寻根之类的?”
“如果你说这个的话,伊朗并不是一个绝佳的去处,”我向我的护照伸了下头,“他们也许会让我入境,但我不确定我能出来。”
他喜欢我的回答。他带着一丝丝微笑看着我的护照,把它翻回他用手指卡住的那页。(中文版《爱的边境》10页)
寥寥数语,表明在美国这样与伊朗敌对的国家,主人公伊朗犹太后裔的身份显然非常敏感,以色列伊朗犹太人遭怀疑的概率远远大于本土以色列犹太人。女主人公遭受盘查的原因则是她这个外表看去极为中东化的女子在咖啡馆写作时遭人举报,举报者仅凭主观断定她是在用阿拉伯语写作。由此让人感受到“九一一”之后整个纽约城弥漫的紧张气氛,以及持有中东某些国家护照的居民得不到信任。耐人寻味的是,随着情节的发展,女主人公真的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建立了亲密关系,这便是构成小说中心情节的爱情故事。与之相恋的哈米一九九九年持艺术家签证来到纽约,经常被错认为巴西人、古巴人、西班牙人,甚至以色列人。身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他很难凭借艺术才华在美国获得成功。就这样,两个来自异乡的边缘人在纽約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暂时忽略了民族之间的敌对界限,迅速地走到了一起。
但是,仅凭爱情无法跨越横亘在他们中间的界限。丽雅特出生在特拉维夫,那是一座拥有世界上最漂亮海滩之一的现代化海滨城市。丽雅特曾经与前任男友住在特拉维夫海边公寓,享受地中海的日出日落,潮涨潮落,且获得高级潜水证,在沙姆沙伊赫自由自在地潜水。而哈米这个在希伯伦长大的人,不会开车,不会游泳,不会放枪。这些特点表明他与现代年轻人的生活格格不入,在年轻的以色列人眼中显得不可思议。二人之间的反差实际上与以色列封锁占领地的现实状况有关。据哈米自述,他有生以来通过以色列国防军的重重封锁与道道关卡才见过三次大海,这里指的是加沙那片海域,他向往有朝一日加沙的海能变成大家的海,然后他们(他与丽雅特)“一起”学会在里面游泳。字里行间其实蕴含着一个巴勒斯坦阿拉伯年轻人对和平的向往,以及与以色列犹太人平等生活的憧憬。与之相对,不太热衷于政治的以色列人丽雅特却难以理解“一起”的含义,或者说对其用法并不十分敏感。这种差异既表明这对异族情侣之间的情感隔膜,又预示着二者之间隔着一道难以跨越的文化屏障,也可以说政治鸿沟。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在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内,伊朗犹太人尽管经历了前文所说融入以色列社会的痛苦,但是他们仍旧是犹太人,拥有优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社会地位。
以色列犹太人与异族通婚是一个社会现象,甚至如作家所言,触及以色列人害怕自己会失去中东身份的核心问题。丽雅特在与哈米交往时其实心怀模糊国族界限的恐惧,担心有朝一日其犹太身份会融入哈米的巴勒斯坦身份之中,害怕其犹太身份被吞噬—尽管她有意告诫自己,哈米代表的是个人,而不是巴勒斯坦民族。与哈米开始交往时,充斥在她脑海里的则是以色列宗教电台—以色列国家新闻台播放的宣传信息,称以色列每年都有年轻的犹太女孩被引诱皈依伊斯兰教,嫁给绑架他们的阿拉伯男人,还被带到乡村,被毒害,被殴打,和她们的孩子们一起挨饿,被像奴隶一样绑缚。以色列宗教电台哀叹这些“以色列的女儿”是“迷失了的灵魂”。这类联想一方面表明现实生活中阿以两个民族通婚,尤其是犹太女子嫁给阿拉伯男子在以色列社会得不到认可与祝福;另一方面,也表明主人公本人对与哈米的深入交往怀有难以去除的恐惧、疑虑乃至自责。这种纠结使她从来没有勇气向父母坦言与哈米的爱情,给姐姐也造成他们在一起不过是鱼水之欢的印象。
从社会学层面看,近年的学术研究表明,以色列犹太民族与阿拉伯民族年轻人之间的通婚现象有所增加。这些异族通婚的家庭成员跨越了集体标准与囯族界限,青年男女多因爱情而成婚,但是最终难以完全跨越以种族、阶级、民族、宗教为基础的集体身份鸿沟与社会秩序,进而暴露出种种问题。而犹太女子与阿拉伯男人之间的恋爱,或者通婚,则更让以色列国家深怀恐惧。按照以色列回归法,犹太母亲生下的子女即为犹太人,因此,犹太女子一旦嫁给阿拉伯男子,其后代无疑会成为犹太人,长此以往,甚至会对犹太种族形成一种威胁。就像拉宾雅恩的好友雅艾拉所说,即使在纽约,犹太女人与阿拉伯男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也会遭禁。而且,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以及巴勒斯坦人自然出生率增长极快,数十年后,犹太人或许成为那片土地上的少数民族。对于年轻一代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来说,以色列归还“六日战争”时期占领的土地已经不再符合其期待,“两个国家”的概念也已经过时。他们把信念寄托在阿拉伯人的出生率上,并期待其变为现实。
从心理学层面看,女主人公的恐惧既来自对自身安全的不确定,也包括害怕自己会认同恋人拥有的巴勒斯坦人身份,这是犹太复国主义教育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话题。丽雅特非常留心哈米用阿拉伯语与亲朋在电话中交谈时是否使用“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之类的字眼,甚至当告诉对方每个士兵在服兵役时期都会得到一部《圣经》时有种奇怪的背叛感,像是把机密情报交给了敌军。
两人关于国族问题的第一次争论由《圣经》引起,当年十八岁的丽雅特在参军时把颤抖的右手放在《圣经》上,宣誓效忠以色列国家;哈米则将其比作手持冲锋枪和《古兰经》,指责以色列用强大的军队对付平民。哈米盘问丽雅特是在哪年服兵役,进而将两人所代表的国族间的敌对推向一个小高潮,且与现实生活中的巴以冲突建立起联系。一个富有戏剧化的细节描写是,十五岁的哈米和几个阿拉伯男孩多年前因在希伯伦涂鸦一面旗子遭到以色列士兵逮捕,被囚禁四个月;在遭到逮捕的那一刻,他看到几个以色列女兵,丽雅特显然身在其中。丽雅特在脑海里无疑也浮现出与哈米擦肩而过的场景。换句话说,时空的转换使当年处于敌对方的二人融为一体。但现实中,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孩童经常因为扔石子、涂鸦等行为而遭受以色列士兵的惩罚,这一冤冤相报的局面短期内不可改变。恋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实际上隐喻着两个民族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爱的边境》不再是发生在两个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而是展现两个敌对民族之间复杂关系的国族叙事。
政治家们关于在巴勒斯坦这一片土地上能否建立两个国家的争论也成为情侣日常生活中不可回避的话题。哈米抱有双民族幻想。在他看来,巴以两个民族之间不可能施行公平的分割,无论是土地,还是水源都不可能公平分割,所有的河流最终都将流进同一片海域。就像风景与天空,同时属于两个民族。而丽雅特则坚决主张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两个国家,只看重实际的和平条约及类似于“政治边界”和“国家主权”之类的术语。他们天真地企图说服对方,动摇对方的立场,或是毁掉那个立场。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陷入那重复的、翻来覆去的、无用的争吵中。
如果说丽雅特与哈米之间的争论限于一对恋人之间,但关涉到时下阿以民族问题的话;那么随着情节的推进,丽雅特与哈米家人及朋友在饭桌上的争论则更多地表现在民族层面上不可调和的异议。哈米姐姐的朋友泽布拉对丽雅特在场感到不便,并不掩饰因其在场使用英语而感到心烦,她面带一丝微笑,高挑的眉毛里露出霸气,对丽雅特说:“你现在是我们的一员了。”这显然忽略了丽雅特所持有的政治立场和民族情感。而在聚餐接近尾声之际,哈米的哥哥瓦西姆与丽雅特之间就以色列现在与未来面临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瓦西姆在争论时语言犀利,态度傲慢,充满敌意与挖苦,认为回到一九六七边界,乃至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国之前没有边界的历史当中同样不可逆,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以色列将成为那片土地上的少数民族。总体上看,丽雅特在阿拉伯人中是孤单的,缺乏生存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拉宾雅恩以敏锐的目光将巴以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换句话说,如果巴勒斯坦不能建国,其实对以色列也不乐观,引发的问题则是如果犹太人作为少数民族生活在阿拉伯人占多数的国家内,其安全系数如何?这些问题不知是否引起以色列右翼人士的深思?
两个年轻人的真挚情感能否跨越国族之间的敌对鸿沟,其實是本书一个悬而未决的话题。当哈米与丽雅特分别回到了拉马拉和特拉维夫,既是象征意义也是现实生活中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典型地理坐标之后,即使二人仅仅相距四十公里,但拉马拉与特拉维夫所代表的两个地理坐标永远难以交汇,二人也不可能再有机会见面。抵达特拉维夫的丽雅特重新回到熟悉的生活秩序和老习惯中,回到原来所有的细节和简单的舒适中。尽管哈米打破僵局,主动给丽雅特打了电话,从丽雅特的哽咽中也可以看出她对哈米真情依旧;但是在哈米生活的拉马拉,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巴勒斯坦人起义时留下的痕迹随处可见,到处是废墟、武装、贫穷、绝望与疲惫。尤其是当时以色列正在西岸建造隔离墙,那是一堵灰色混凝土墙,蜿蜒远去,像一道丑陋的伤疤,把村庄和果园一分为二。随着中东和平进程的搁浅,这道隔离墙预示着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和平之路遥遥无期;也预示着生活在这个大背景下的青年恋人可能会被永远隔离。小说结尾,哈米和另两个阿拉伯青年乘坐黑车避开以色列哨兵关卡来到雅法,投入大海怀抱,却溺水而亡。哈米之死,成了解决或者淡化这种矛盾的一种方式。